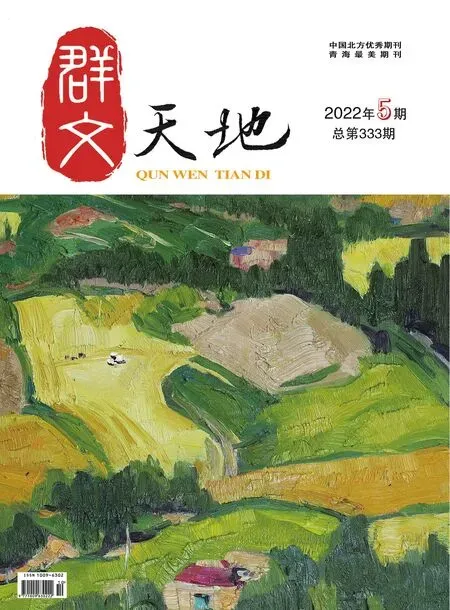谈谈河湟“花儿”的发展创新
——以“花儿”歌手索南孙斌的创新为例
衡淑荣 杨生顺

人民公园江河源雕塑 万马奔/摄影

“花儿”,又叫“少年”,是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四省(区)汉、藏、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民族人民中的一种山歌。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形式多样、曲调优美、异彩纷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高原风格,深受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并且被人称为“西北之魂”。在我国民歌百花园中,别具一格,占有独特的地位,堪称珍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河湟“花儿”具有自身的作品特点、演唱特点和传承特点。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河湟“花儿”面临着发展创新的问题。文章以“花儿”歌手索南孙斌为例,主要从作品内容、作品结构、演唱方式和旋律方面浅谈河湟“花儿”的发展创新问题。
一、“花儿”的定义与分类
传统“花儿”无音乐伴奏,人们口耳相传,所以是徒歌。传统“花儿”内容大多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生活,故为情歌。2009 年9月28 日至10 月2 日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花儿”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西北“花儿”分为3 种,分别是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和六盘山“花儿”。学术界则大多把西北“花儿”分为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河湟“花儿”又叫河湟“少年”,在曲式结构和文本结构方面,与洮岷“花儿”有明显的区别。曲式结构方面,洮岷“花儿”曲令甚少,只有三四种;河湟“花儿”则有250 种以上的曲令。曲式结构方面,洮岷“花儿”多三句式,也有四句、五句、六句乃至更多句式;河湟“花儿”多四句式,也有五句、六句乃至更多的句式。
二、传统河湟“花儿”的基本特点
(一)作品特点
从语言节奏来看,河湟“花儿”的结尾形式多样,但最有特色的就是二字尾。二字尾是河湟“花儿”区别于洮岷“花儿”以及中国其他山歌的重要标志之一。譬如四句式“花儿”:“千万年不倒的太子山,万辈子不塌的/青天;若要我俩的婚姻散,除非是天覆/地翻。”此作品第二句的“青天”和第四句的“地翻”为二字尾。五句式“花儿”:“你骑上骡子我骑上马,在一座店儿里/住下;快刀子摆下十二把,我不害怕,血身子陪你者/坐下。”此作品第二句的“住下”和第五句的“坐下”为二字尾。六句式“花儿”:“阴山里蹲一只绿鹦哥,学人的话,惊跑了阳山的/大鹿;尕妹是园中的红樱桃,摘不上它,园墙上踏一条/大路。”此作品第三句的“大鹿”和第六句的“大路”为二字尾。索南孙斌的 “花儿”也恪守着这一基本特点,诸如《阿哥们是孽障人》《心上的花儿给大家唱》等概莫如是。
(二)演唱特点
河湟“花儿”讲究独唱和对唱。独唱常见于田间地头、林莽草野和偏僻独行处,用来抒发和宣泄自我的情感和思想。独唱作品很多,上述列举的“花儿”皆为独唱。对唱的作品多见于“花儿会”或男女约会之时。如下:
女:
你搭的凉伞儿我搭上,
我俩儿地边里走上;
你买的笛杆儿我吹上,
吹颤音指头儿抖上。
男:
毛布掌的新鞋你趿上,
那我就净脚片走上;
我折的花儿哈你插上,
我把你带靠儿搂上。
女:
一把手肩膀上轻搭上,
我俩儿大街上走上;
三万元的“刮刮乐”你刮上,
高兴者大秧歌扭上。
男:
由不得个家地肘巴上,
两把手前后儿甩上;
褚褚里的钱儿你花上,
金手链我给你买上。
……
“花儿”是情歌,内容大多表达的是男女的爱情和婚姻生活。通过对唱,男女之间了解了思想,沟通了情感,从而成为知己。“花儿”对唱是男女之间互诉衷肠、谈情说爱的民间歌唱艺术。索南孙斌的“花儿”大多是独唱,也有对唱,他与张存秀演唱的《拉夜船》 《好心肠》,就很好地传承了“花儿”的传统情感内容。
(三)传承特点
传统“花儿”传承的一大特点就是口耳相传、口传心授。有的“花儿”歌手,从小就听父母亲唱,在幼小的心里种下了“花儿”的种子;有的人在放羊放牛的时候跟着牧人唱,渐渐学会唱“花儿”;有的拜师学艺,传承“花儿”艺术;大多数的人则通过“花儿会”学习传唱“花儿”,“花儿会”是“花儿”文化的集合体,在河湟地区入选国家级“花儿会”名录的有5 个,分别是大通老爷山“花儿会”、互助丹麻土族“花儿会”、乐都瞿昙寺“花儿会”、民和七里寺“花儿会”和临夏松鸣岩“花儿会”。除此之外,河湟地区还有100 多个大小不等、规模不一的“花儿会”。“花儿会”上,各地各路多民族“花儿”唱家云集,喜欢“花儿”的人们积极参与,渐渐就学会了许多曲令和歌词。在对索南孙斌的访谈中,我们发现除了“花儿”磁带,民间艺人及朱仲禄、冶金元、马俊、雷有顺等人对他的影响很深。
三、河湟“花儿”的发展创新
河湟传统“花儿”音乐曲令,虽然都有优美的旋律,但大部分“花儿”都是上下两个乐句的简单反复。这样的音乐结构,歌词容量十分有限。这就需要以传统“花儿”为基石,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对河湟“花儿”进行创新。这里以青海“花儿”歌手索南孙斌的创新为例,从作品内容、作品结构、演唱方式和传承发展方面谈谈河湟“花儿”的发展创新问题。
(一)作品内容的创新
要不断创新“花儿”的抒情内容。传统河湟“花儿”的下片,通常以抒情为主,绝大多数表达的是人们的爱情婚姻、生活情感。随着社会的开放和思想的进步,传统“花儿”的抒情内容显得有些单薄了,有必要进一步扩展情感内容和表达内容。也就是说,除了抒发当代人的爱情婚姻外,还可以描述并表达更多更深层次的文化内容。索南孙斌就作了这方面的创新。他说:“现在‘花儿’表达爱情的少了,劝人心、劝酒、夸人、夸家乡的作品多了。譬如到了大通,往往唱这样的‘花儿’:从西宁来到了大通县,老爷山,带来了民族的情感;没拿个礼当着难见面,我就送上几句心中的少年。”从这首“花儿”作品可以看出,作品的起兴与传统作品相比有不同之处,“带来了民族的情感”显然是现代“花儿”歌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的产物。
(二)作品结构的创新
作品结构的创新有很多种,主要的创新以下两种:
一是创新发展濒临消失的多句式“花儿”作品。传统受河湟“花儿”多为四句式、五句式和六句式。六句式作品中又多为“两担水”,又叫“截断腰”。如:“眉毛弯弯一张弓,弓一张,箭射了天上的凤凰;盼来盼去一场空,空一场,难心上加上的愁肠。”此外,还有一种六句式,如:“河里的鱼儿团河转,为什么不下钓竿?锄草的阿姐们满楞干,为什么不盘个少年?莫说是小姊妹拾掇得干,还说是阿哥们硬缠。”这种六句式作品极少,甚至已经消失,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创新。
二是作品结构的拆合。这种作品创编也是有先例的,而且比较成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如“ 白牡丹白得耀人哩,红牡丹红者破哩;尕妹身旁有人哩,没人是陪我者坐哩。”人们通常用“白牡丹令”来演唱这首作品,但也有人进行了创新,把这首作品的上下片一分为二,中间加入了用其他曲令演唱的“花儿”,也就是说,人们为了舞台表演的需要,两头用“白牡丹令”起和收,中间则加入了一首或几首用其他曲令演唱的“花儿”作品。这样的拆分与合并,使“花儿”舞台表演不再单调,满足了人们更加丰富的文化需求。索南孙斌也作过这方面的创新,他曾经尝试着将“下四川”和“走西口”两种曲令结合起来,男的唱“下四川”,女的唱“走西口”,实现了彼此的衔接,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他还将“上去高山望平川”拆分为首尾两部分,中间插入了“白牡丹令”和“妹妹的山丹花令”,结果效果非常好,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
(三)演唱方式的创新
传统河湟“花儿”有独唱和对唱两种方式。在网络和城市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在延续这两种演唱方式的同时,还应作进一步的创新。因为传统河湟“花儿”的独唱,都是一人唱一首作品,对唱也是一人唱一首作品。当联体式“花儿”过长时,每首作品的上片与下片、作品与作品之间就留出了较大的空档。如果曲调单一,听众往往会产生不耐烦的情绪。面对这种情况,索南孙斌作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创新。
一是男女歌手唱一首或一组“花儿”。如下:
女:
天上的日头儿照云哩,
地下的花儿们俊了;
男:
尕妹的模样儿耀人哩,
阿哥们见了时晕哩。
女:
双双对对的牡丹花,
层层(嘛)叠叠的菊花;
男:
亲亲热热说下的话,
实实(嘛)落落的记下。
女:
头买了鞍掌者二买了马,
三买了梅花镫了;
男:
头爱了人品二爱了俊,
三爱了满脸的笑了。
……
这种创新,改变了传统“花儿”一人一首作品的演唱方式。“花儿”拖腔长,一首“花儿”作品倒是新颖别致,若唱连曲式作品,如不改编曲令,就显得非常单调呆板,很容易让人困倦。为适应舞台表演,满足群众视听需求,就需要改变传统的单一连曲式唱法,即每首作品两人来唱,一人唱上片,一人唱下片,如此依次向下,有男有女,在参差变化中,避免了上下片之间的停顿,不仅轻松演唱完成了一组“花儿”作品,而且有效消解了听众的倦怠情绪,满足了老百姓的文化心理需求。这样一种演唱方式的创新,并非轻松就能完成的。需要二人之间的默契衔接与灵敏反应。所谓默契,就是二人非常了解彼此的唱法特点。譬如,起音不能太高,高了后面的就会更高,越往后越高,加之中间缓歇时间本来就短,唱到最后就会筋疲力尽。歌手二人要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连曲式“花儿”表现得尽善尽美。索南孙斌深谙此道,他声音饱满高扬,在唱这种连曲式作品时,他往往让对方先唱,自己后唱,后面自己唱时,再加以控制,尽量回到对方的音域中去。如此一来,对方也接唱舒适,整首作品演绎下来,就显得和谐动听了。
二是一家三人唱一组“花儿”。譬如《雪白的鸽子》(“仓啷啷令”),如下:
孙毛措(索南孙斌的女儿):
左边的黄河(嘛噢哟)
右呀面的石崖(么噢哟)
雪白的鸽子(么)
噌愣愣愣愣愣
仓啷啷啷啷啷
扑噜噜噜噜噜
啪啦啦啦啦啦响呀
水面上飞呀来(嘛噢哟)
才让卓玛(索南孙斌的妻子)和孙毛措合唱:
雪白的鸽子(么噢哟)
青天里飞来(么噢哟)
尾巴上连了个
噌愣愣愣愣愣
仓啷啷啷啷啷
扑噜噜噜噜噜
啪啦啦啦啦啦地响呀
尾巴上连了个
噌愣愣愣愣愣
仓啷啷啷啷啷
扑噜噜噜噜噜
啪啦啦啦啦啦响呀
惹人的哨子(么噢哟)
索南孙斌主唱,后半部分与才让卓玛合唱:
阿哥连尕妹俩(噢哟)
一对对鸽呀子(嘛噢哟)
他俩是天世着
噌愣愣愣愣愣
仓啷啷啷啷啷
扑噜噜噜噜噜
啪啦啦啦啦啦飞呀
下来的对对(么噢哟)
他俩是天世着
噌愣愣愣愣愣
仓啷啷啷啷啷
扑噜噜噜噜噜
啪啦啦啦啦啦嗖地飞呀
下来的对对(么噢哟)
《雪白的鸽子》的文本很长,传统作品三段反复无变化,若不是其中有生动鲜活的模拟像声,则容易让听众产生厌烦情绪。为适应舞台化表演,索南孙斌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大胆地将童声、男女声融合起来,交叉互补,快慢结合,消除了传统的《雪白的鸽子》作品反复、拖腔长、乐段间歇长等问题。这一改编集中体现了索南孙斌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既是文化的传承,也是文化的创新。
(四)旋律方面的创新
河湟“花儿”的旋律大致是固定的,但还是不断被人们创新。地域不同、方言不同、民族不同,都会改变“花儿”的旋律。由此河湟“花儿”中有许多“子母令”,譬如“撒拉令”就有13 种,“好花儿令”就有5 种,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河湟“花儿”的旋律变化一直在进行。
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山野的河湟“花儿”唱起来比较缓慢舒缓,声音抑扬,善于抒情。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速,“花儿”的节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迪斯科音乐风格流行之际,索南孙斌曾经把传统“花儿”改变为摇滚“花儿”。如由张启元作曲、索南孙斌编词的《青海是祖国的好地方》,包括唱词5 段,说词1 段,内容如下:“青海是祖国的好地方,(可可西里,莹莹藏羚羊)江河源头歌声亮;青海湖鸟岛美名扬,(可可西里,莹莹藏羚羊)百鸟儿在欢唱……” 这首“花儿”用“拉拉令”演唱,说唱结合,通过增强节奏,打破传统“花儿”舒缓的节奏形式,改编人们在城市舞池中舞蹈的欢快节奏。这样一种改变,突破了河湟“花儿”数百年的传统农耕文化背景,意味着城市“花儿”音乐的崛起。
索南孙斌对传统曲令也进行了改编,特别是对《雪白的鸽子》的改编十分成功。2012 年,他参加了山西电视台“歌从黄河来”比赛,获得了周冠军。这次参赛,他对这首作品进行了进一步的创编,第一段是慢板,第二段将“哎”增加为12 拍,第三段结束时的“哎哟”加入了高音和假音,使这首作品更加完美。
索南孙斌只是河湟“花儿”创新中的一个代表,还有很多人都在为此努力着。
“花儿”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就会被时代逐渐淘汰。通过创新,河湟“花儿”才能散发出诱人的魅力。当然“花儿”的创新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相信通过人们各种形式的创新,河湟“花儿”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丰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