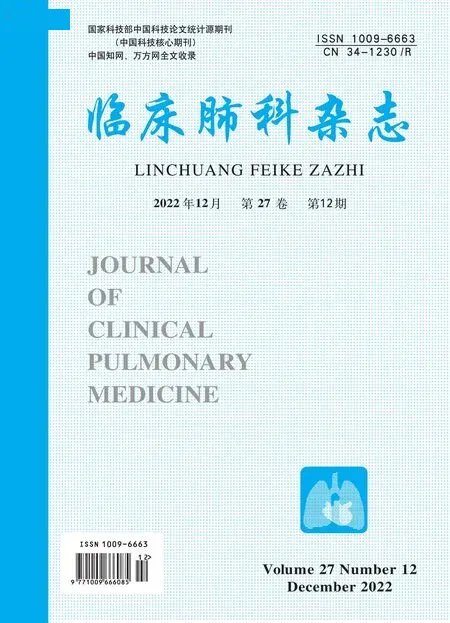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生物学机制研究进展
张明娜 生红梅 刘佳育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已逐渐成为晚期肿瘤的一二线治疗方案,通过下调T细胞的抑制功能发挥作用,激活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虽然免疫系统的激活是ICIs治疗的基础,但它也是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immune 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背后的驱动因素。 ICIs相关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 pneumonitis,CIP)是一种由ICIs引起的临床、影像和病理表现各异的肺损伤,是引起 ICIs 相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Meta分析提示[1],CIP占抗PD-1/PD-L1相关死亡的35%;在临床试验中CIP的发病率可达5%[2],但真实世界人群的研究显示其发病率可高达19%[3]。CIP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为排除性诊断,且可能导致免疫治疗中断、终止,甚至危及生命,鉴于此,本文总结了CIP可能的生物学机制及预测性标志物,以期对CIP的识别及管理有所帮助。
CIP的生物学机制尚未得到明确阐述,目前认为ICIs可以激活T细胞,对抗肿瘤细胞,被激活的T细胞也可以攻击正常组织[4],导致免疫相关毒性;激活的免疫系统也可能导致自身抗体的产生和炎症因子过度释放,肺组织固有生长因子的作用等相关因素共同影响促进发生CIP。
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表达于T细胞表面的细胞毒 T 细胞抗原 4(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和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 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等免疫检查点,可以诱导免疫耐受并阻止自身免疫,但这些检查点可以被癌细胞有效适应以逃避免疫监视,CTLA-4抑制剂增强了T细胞对肿瘤相关新抗原的应答,耗尽了肿瘤内局部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并改变了肿瘤微环境的平衡,使其解除免疫抑制[5]。PD-(L)1抑制剂阻断了PD-1/PD-L1途径对T细胞的抑制,增强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毒性[6],从而杀伤肿瘤细胞,而被激活的T细胞也可以攻击正常肺组织。研究[7]发现CIP患者的BALF标本显示,主要由CD4+T细胞为主的淋巴细胞增多,且观察到中央记忆T细胞(central memory T cell,Tcm)数量增多及Tregs上CTLA-4和PD-1表达降低,PD-1+和CTLA-4+Treg对CD8+T细胞、传统T细胞(如Tcm)和巨噬细胞的促炎症反应有负调节作用[8-9],因此,激活的肺泡T细胞数量增加和抗炎Treg抑制表型的减弱,可能导致T细胞活性失调。Lubli等人[10]在一小组CIP患者中,对肿瘤组织浸润的淋巴细胞和浸润CIP病灶的T细胞,进行了T细胞受体互补决定区(complementarity determining region 3 of T cell receptor,TCR CD3)测序,发现这些部位的T细胞库有显著重叠,这支持了一种假说,即由ICIs激活的T细胞可能对肿瘤和肺组织中共有的抗原发生反应,在抗肿瘤治疗同时对正常肺组织产生免疫反应,同时因T细胞活性失调,可能引起过度的免疫反应,进而导致CIP的发生。
Suzuki等人[11]发现在CIP患者的BALF中,CD8+T细胞中PD-1+PD-L1+细胞的比例与CIP的严重程度相关;有研究显示[12-13]抗原呈递细胞固有的PD-1或CD80在细胞表面与PD-L1顺式相互作用,阻止PD-L1与PD-1在T细胞表面反式结合,抑制T细胞中PD-1信号转导,鉴于这些发现提出另一种假设,T细胞中的PD-L1可以与PD-1顺式相互作用,而这种顺式PD-1/PD-L1相互作用可能调节肺组织的自反应T细胞,而ICIs对顺式PD-1/PD-L1调节的破坏可诱导自反应T细胞的异常激活,从而导致严重的CIP。目前这些基于临床或实验室的研究假说尚处于不成熟阶段,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对肺组织损伤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来明确。
自身抗体
肿瘤患者免疫耐受的破坏可以增加自身抗体产生[14],因此ICIs作用时,自身免疫得到增强。Gowen等[15]发现毒性相关自身抗体的抗原靶点在受irAEs影响的器官中高度表达的蛋白质中显著富集,且或参与免疫病理相关的细胞通路,提示特异性自身抗体可能在irAEs的发展中起着潜在的致病作用。CIP作为一种器官特异性irAEs也有类似的机制,最近一项在ICIs治疗的患者进行的大规模自身抗体筛查,发现在2例CIP患者的队列中发现治疗后血浆中抗CD74水平升高,随后在10例CIP患者的确认队列中证实了这一结果,与治疗前相比,这些患者血浆CD74自身抗体中位数增加了1.34倍[16]。CD74是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I(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II)的胞内伴侣分子,可表达于免疫细胞表面,包括巨噬细胞[17],作为巨噬细胞迁移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的高亲和力受体,刺激炎症介质的表达。CD74不仅有抗原递呈作用,还可以调节免疫稳态,正常人肺组织中CD74表达水平适中,而CIP患者肺组织中CD74表达水平显著升高[16],可以推测ICIs激活免疫系统后,高水平的抗CD74与肺组织中过表达的CD74相互作用,可能导致肺组织局部炎症反应,从而导致CIP发生。
炎症因子
ICIs破坏免疫耐受,增加T细胞的活化和免疫反应,血浆和BALF中炎症因子水平升高可能参与了CIP的发生。研究显示[7]在CIP患者的BALF中明显存在CD4+T淋巴细胞为主的淋巴细胞增多;辅助T淋巴细胞(helper T,Th)2细胞是CD4+T细胞的一个亚群,可以产生IL-4、IL-5、IL-6、IL-9、IL-10、IL-13等细胞因子而导致过度的炎症,Kowalski等[18]发现CIP患者BALF中IL-6表达显著增加,IL-6是一种重要的炎症反应因子,可诱导急性期蛋白(acute phase proteins,APP)促进T细胞增殖,这些证据支持了T细胞过度激活和增殖导致细胞因子过度级联释放的假设,进而导致过度的免疫反应。
Wang等[19]的研究发现CIP患者血清和BALF中白细胞介素(IL)17A和IL-35水平显著升高,且与CIP严重程度相关,且CIP患者外周血Th17、Th1细胞的百分比显著升高,Th17/Tregs和Th1/Th2比例较高。IL-17是由Th17细胞、自然杀伤T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产生的一种细胞因子,可以促进T 细胞的激活和刺激上皮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产生多种细胞因子而导致炎症的产生,IL-17的异常表达被认为参与多种疾病过程,包括哮喘、肺炎和肺纤维化[20-21]。IL-35是Tregs分泌的一种抑制细胞因子,可由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1诱导表达,可以抑制效应T细胞的激活和功能分化,如IL-17A+Th17细胞等,但促进Tregs的扩增,可形成正反馈,与肺纤维化形成相关[22], 有研究报道间质性肺炎是CIP最常见的病理类型[23],这些证据支持可能是IL-17/Th17通路的激活参与了CIP的发病机制,即ICIs破坏免疫耐受,Th17与Treg比例失衡,活化的T细胞产生高水平IL-17A,可刺激TGFβ1的分泌,从而诱导IL-35的表达,再加上IL-17A水平升高,激活静止的成纤维,促进自身免疫性肺炎的发展,而发生CIP。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是一种高度特异性的促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也是一种有效的血管通透性诱导剂,肺是全身系统中VEGF表达最高的器官之一,它可影响肺的发育和成人肺结构的维持,有报道称,VEGF对肺内皮细胞的影响可在多种肺疾病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动脉高压及急性肺损伤[24]。Iwai等人[25]发现VEGF阻断可防止小鼠模型中免疫相关性肺炎的加重,抗VEGF抗体可以控制小鼠模型中CIP的症状,尽管观察到CIP小鼠模型的肺组织中VEGF的表达水平降低(考虑与肺泡内大量渗出液稀释有关),但仍然是CIP模型中肺泡内大量渗出液足够的关键因素,这支持了一种观点,即当肺组织固有VEGF作用和PD-1信号阻断引起的免疫系统激活原有炎症加重同时存在时,就会发生CIP。
预测生物标志物
CIP临床及影像学表现均缺乏特异性,目前仍为排除性诊断,需要鉴别感染、肿瘤进展等多种疾病[26],发现一些预测或能提示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外周血标志物对临床上CIP的早期识别和管理有一定帮助。
嗜酸性粒细胞可以在多种免疫功能中作为调节细胞或效应细胞,还能通过发挥抗原递呈功能而激活T细胞和聚集肿瘤特异性CD8+T细胞[27-28],绝对嗜酸性粒细胞计数(absolute eosinophil count,AEC)水平较高,可能反应了嗜酸性粒细胞的激活状态,可介导T细胞在肺组织中的浸润,多因素分析显示[29]基线外周血AEC是CIP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高AEC组(≥0.125×109/L)较低AEC组CIP的发生率更高,且高AEC组,有较长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和更好的客观缓解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提示基线外周血AEC水平可能是CIP发生及ICIs治疗临床效果的一个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但因低AEC组也可发生CIP,说明其敏感性略差。因此,在临床应用ICIs前,应特别关注外周血AEC升高的患者(特别是AEC≥0.125×109/L的患者),以早期发现CIP。
Yoshida等[30]观察到一例应用Nivolumab的CIP患者血清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erum soluble interleukin-2 receptor,sIL-2R)升高,且升高水平与疾病活动相关,sIL-2R是一种可溶性的IL-2受体,来源于活化的T细胞,被广泛认为是T细胞介导疾病活动的生物标志物,包括,但不仅限于结节病和恶性淋巴瘤,过度活化的T细胞可能导致CIP患者血清sIL-2R水平升高,限于仅为个例报道,且sIL-2R升高不能良好区分肿瘤本身活动还是发生CIP,特异性较差,能否用于预测CIP的发生和评估疾病活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近一项回顾性研究[31]发现,与基线相比,外周血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IL-10在CIP发病时显著增加,而ALB显著降低,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高水平IL-6和低水平ALB与CIP严重程度显著相关,多因素COX模型中只有IL-6与CIP患者的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显著且独立相关,提示IL-6升高是CIP严重程度的独立生物标志物,也是早期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已知IL-6在感染、自身免疫反应中升高,也与肿瘤诱导炎症的程度相关[32]。CIP发生时IL-6、IL-10等炎症因子水平升高与T细胞过度激活有关,但IL-6在感染中也可升高,因此需要在除外合并感染确诊CIP的前提下,监测外周血IL-6水平对CIP的严重程度及预后可能有一定提示作用。
展望
鉴于各种肿瘤类型的临床疗效证据,ICIs的使用在未来会继续增加,CIP作为有一定发病率且致死性高的不良反应,需要引起临床的重视,CIP的生物学机制尚未明确,目前认为T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与CIP发生密切相关,自身抗体的产生、细胞因子的释放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也在CIP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一定作用;且监测外周血AEC、sIL-2R及IL-6等对CIP发生发展及预后有一定提示作用,对CIP生物学机制的明确阐述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早期识别CIP并制定最佳诊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