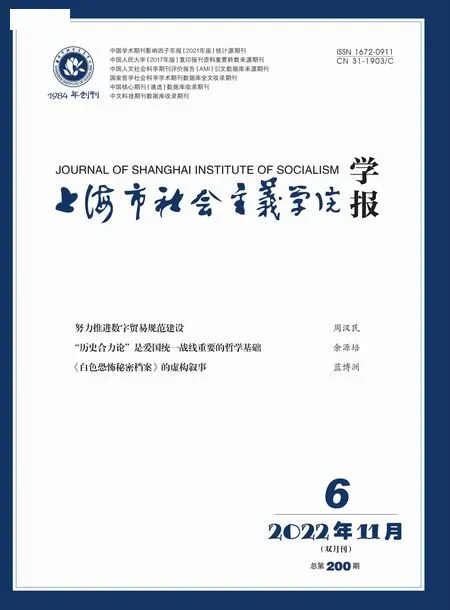《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的虚构叙事
蓝博洲
(上海中华文化学院,上海 200237)
1995年9月,台湾独家出版社出版了由台湾前“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口述,徐俊荣、黄志明、公小颖整理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在该书中,谷正文自称破获《光明报》案,逮捕了蔡孝乾、张志忠等中共在台地下党领导人,同时吹嘘了具体经过。由于白色恐怖的警示作用,这段台湾革命史被湮灭了。由于两岸长期对峙隔绝与禁忌,大陆对这段台湾历史更加陌生。于是,随着近年来谍战影视与图书的风行,谷正文这本以反共观点随意口述的回忆录,竟而被大陆一些媒体、民众,乃至专家学者不加甄别地引用,作为解释中共台湾地下党历史的唯一材料。
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然而,大陆知识界还是有头脑清楚的人出来澄明真相。在网络上看到,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刘岳与干部曹楠的《“谍海孽雄”谷正文真相》,对《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的“有关史实及谷正文的历史做了部分考证,还历史之真相”。论定“他出于其反动立场和自我吹嘘的需要,采用故意隐瞒、张冠李戴、夸大事实等手法,多处严重失实。”可惜的是,他们的批判仅止于该书的大陆时代。台湾部分则未曾触及。毒瘤未除。
就我个人长年对台湾这段史实调查研究的理解,我完全同意刘、曹两先生对谷正文叙述手法的定性批判。按理,这样一本不值一读的书,把它回收,再生为洁白可用之纸即可。无奈,大陆网络上加油添醋编造的虚假讯息却一波接一波,层出不穷。因此,不批判此书是不行的。问题是,面对全篇都捕风捉影,“采用故意隐瞒、张冠李戴、夸大事实”等似是而非的手法叙事的历史情节,真要一一指出其虚构之处,虽是必需,却也是浪费心力的劳动了。
台湾前“保密局”特务谷正文重出江湖的语境
历史地看,台湾前“保密局”特务谷正文重出江湖是在1988年。彼时,港台舆论正热烈争论正式接掌台北国府的李登辉在青年时期“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公案。针对“台独”派郑南榕的《进步时代》指称“李登辉没有出卖台共”的文章,同年10月1日,李敖主编的《乌鸦评论》创刊号刊出“安辰”(李敖的化名)《共产党李登辉出卖同志的官方证据》,指出“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应该是谷偷卖给他的)《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第186到190页,所谓“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载称:“叶城松于卅六年十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而叶城松(31岁)等五人后来判死刑,“‘奸匪李登辉’逍遥法外”,“事实乃是,他早在做共产党的当时,就自新了,他出卖了共产党同志,做为晋身之阶”。
10月7日,自称是“名列第六名‘反革命叛徒’”的“将军”,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是“破获匪谍有功”的“保密局”组长的前“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随即在《乌鸦评论》第二期,发表《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替李登辉辩驳说:“根据‘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记录,省工委蔡孝乾等于卅五年七月由上海抵台,发展组织……卅六年“二二八”事件时,仅有党员七十余人。卅七年六月“香港会议”时,有党员四百余人;卅八年八月党员增至九百人。在台大的组织,仅有“法学院支部”……其中并无“李登辉”之名。四十三年,嘉义警察局奉准警务处,在嘉义县捕获叶城松者,供称系台大法学院支部,其入党介绍人为“李登辉”,为嘉义县籍,经核对,此一李登辉,并非台大农学院学生,早于卅八年经港逃回大陆。显系同名之误。”
同期 《乌鸦评论》另刊李敖 《“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吗?》,质疑谷正文 “同名之误”说。10月21日,该刊第四期,同刊谷正文《李登辉究竟有几位?》与李敖《共产党李登辉的种种》。谷正文除了提问 “李登辉究竟有几位?”之外,也“提出一些事实”来说明“李登辉并无共党背景”。首先,他说,1949年10月他亲自办过“台大法学院支部”案,“捉放中的戴传李,查明是小组长,王明德、詹昭光都是党员,多次谈话中,都没有发现‘台北的李登辉’”。针对这点,李敖质疑说,“他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做过那么多次谈话,会能在漫长的四十年后,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记得”?
11月11日,《乌鸦评论》第七期,又再同刊谷正文《请寻找另一个李登辉》与李敖《还有另一个李登辉么?》李敖和谷正文之间,“关于台湾这个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是否就是当年那个出卖共产党同志的李登辉问题”的论争,就在各说各话,没有定论的情况下,暂时告一段落。
1990年2月,就在国民党“主流”与“非主流”斗得水深火热期间,青年李登辉的“共产党背景”再度曝光。这次,秘辛的揭露者却是原先极力替李登辉“漂白”,坚决强调“那个李登辉”不是“这个李登辉”的特务谷正文。3月8日,他在出身“蓝衣社”的滕杰组织,以老国代为主的“反李派”的“推荐林洋港、蒋纬国参选委员会”记者会上,根据李敖所引那份原本被他否认的“国家安全局”编印的《历年办理匪案汇编》,“滔滔不绝地”把青年李登辉涉及“共谍案”的经过,“讲得活灵活现”,并拿出这份“官方文件”,让记者竞相拍照[1]。
由于谷正文对待青年李登辉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态度,前后不一,两年前极力“漂白”,两年后却极力“涂红”。结果,他所说的话,不但没有起到什么“反李”的作用,还因此让社会大众对国民党特务起了更恶劣的印象。
1989年10月23日,谷正文在李敖发行的《一百.一百.期》丛书,第63至68页,发表了一篇《桂花巷失落的人和事》,虚实交构,绘声绘影,描述了中共地下党人吕赫若与“辜显荣的儿媳,辜振甫的嫂子,辜廉淞的妈妈——辜颜碧霞”(“惕红”)的暧昧关系,并在他遇捕时由她协助驾着Austin车脱逃的经过。由于吕赫若不会开车,本文的虚构性不证自明[2]。
就在这样的暖场铺垫之后,谷正文在《独家》开始口述吹嘘他的捕谍伟业,并以《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为名出版。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定位应该就很清楚了。尽管如此,我还得举出几点实例,才能让更多读者不再轻信他所编造的谎言。
关于《光明报》案的虚构与相关证言
谷正文在“《光明报》事件”一节宣称,他到台湾后所抓的第一批“匪谍”是“台大的政治系学生许远东、戴传李(王明德和吴振祥)等四人”。其中,关键人物戴传李“有一个妹妹从小被送入蒋渭水家中当养女,叫做蒋碧玉”。《光明报》则是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经过戴传李的自白后”,谷正文“大致明白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本身就是一名资深共产党员,他担任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在该中学里安插了许多随国府撤退来台的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如罗卓才、张奕明,此外还积极在校内外吸收成员。而《光明报》便是基隆市工委会的宣传刊物”。于是8月15日“凌晨三点五十分”,谷正文“亲率三个行动小组荷枪实弹冲进基隆中学”。他自己带领“第一小组”,“直捣校长宿舍逮捕钟浩东……”。“二十分钟后”,他“将钟浩东太太蒋碧玉带到印报器材前面,钟太太眼见大势已去,并未进行反抗与辩驳,只是淡淡地说:‘这次我们输了,我想我是难逃一死,不过,能够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会瞑目的。’”“经过三天三夜的侦讯”,他们“一共先后逮捕了四十四名共谍及涉案分子。其中共有钟浩东、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依‘搜集军政情报,开展兵运工作,俾便于匪军来犯时阵前策应,协助登陆’之叛乱罪名处以死刑,其余三十六人则分别被处十五年、五年、一年及交付感训的判决”。他又夸称令他“颇感安慰的是,戴传李兄妹及其他三名台大学生仅被处以交付感训最轻的处分,而且并未入狱”[3]66-72。
谷正文在叙述这段情节的时候,“《光明报》事件”已经通过我在1988年发表的《幌马车之歌》而为人所知了。因此,他也不能任意虚构历史的情节,只能根据可见的文献,通过乌贼式的叙事语法,达到他想误导读者认识历史事实的目的。
首先,诚如李敖的质疑:“他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做过那么多次谈话,会能在漫长的四十年后,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记得”行动的时间是几点几分吗?其次,蒋碧玉不是戴传李的“妹妹”而是二姊,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舅舅蒋渭水的“养女”。再者,据谷正文自夸,他“采用智取原则办案”,“仅一两次使用暴力逼供”,经以 “《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解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切入,“长达十多小时的无边漫谈”之后,戴传李“自白”供出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基隆市工作委员会的组织等。而在逮捕蒋碧玉之后,“经过三天三夜的侦讯”,“一共先后逮捕了四十四名共谍及涉案分子”。据其叙事逻辑来看,言外之意,钟浩东及其组织是被戴传李“出卖”的,而蒋碧玉则导致“四十四名共谍及涉案分子”被捕[3]66-72。
谷正文所说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其事,但也不是事实。当然,也可能是口述整理者根据“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的记载而编写的情节。
相对地,我在1990年与1988年采访当事人戴传李与蒋碧玉的说法如下:
“我从高雄移送到台北保密局的当晚,就开始被刑求。”戴传李回忆说:“他们要我脱掉上衣,打着赤膊,躺在一张长条椅上,然后用绳子把我绑紧,让一名剃光头、长得胖胖的打手,用布缠住我的大腿,再用拳头用力捶击。他们要我承认我有加入共产党。那时候,我才24岁,可我知道利害轻重。我心里清楚,他们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才要用刑。如果我承认的话,他们一定会继续用刑,一直刑到我没东西可说为止。所以,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熬过刑求这关,绝对不能承认。因为说了更惨。我不承认,他就打。足足刑了有一个钟头,才将我拖回押房。我的大腿虽然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外伤,可往后两天,却一直拉不出屎,屙不出尿,动也不动地躺着。后来,我大概每隔两天便被提讯一次。我记得,当时里头有个叫做谷正文和一个姓赵的特务。他们两人似乎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或是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我觉得那位姓赵的特务多少还像人。至于谷正文,他对我们的态度真是坏透了。几乎所有的刑求都是他下令执行的。我觉得,他已经根本不是人了。他自己也曾经对我们说,他因为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所以早上起床后,从来不洗脸,也不刷牙。我被捕两个星期后,看到姐夫钟浩东也被抓进来了。”
“王明德失踪了几天,我不放心,于是就要还在台大就读的弟弟戴传李,离开台北避一避。”蒋碧玉说:“戴传李立刻就与另外八名同学南下高雄,到一名孙姓同学家。然而,就在孙家,因为组织不够严密,他们九人也就当场被捕。浩东听到了这个消息,从此不敢住在家里。八月底,有天……到了半夜,大概是一点多钟吧。我听到粗暴而急躁的叩门声。宿舍里的人都知道是宪兵特务来了,没有人敢去开门。我于是起身去开门。门一打开,一名领队的特务头子看是我开的门,便以一副嘲讽的语气对我说:校长太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要来解放你们。……他们入内后,当然是一阵粗暴无礼的搜索。然后,那名特务头子就派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抓人。在这等待的空档,他又故意与我谈马克思的辩证逻辑,谈人民民主专政……等到那些人又回来时,那名头子就命令我和当时才18岁的妹妹换衣服,准备上车。上车前,我要把最小的儿子托付给教务主任的太太张奕明。张奕明安慰我说不会去太久的,小孩还要吃奶,还是带进去吧。这样,我连小孩的衣服、尿布也没带,带着才五个月大的婴儿,跟着妹妹被押上车。”[4]
两相对照,加害者与受害者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叙事,你愿意相信哪种说法是相对符合事实的?我是相信受害者。但大陆不少人却宁肯相信加害者的说法。例如,北京西山纪念陵园的墙体就铭刻着“蒋碧玉”所说的一段话:“能够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会瞑目的。”这样的叙事肯定政治正确。但出处也肯定是谷正文的那本回忆录吧。我在陵园开放之初去凭吊烈士时,没有特别用意地随口提问说,据我与蒋碧玉相处至其过世为止的记忆,她不曾说过这句话,不知出处哪里。
至于谷正文所谓“四十四名共谍及涉案分子……其中钟浩东、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处以死刑,其余三十六人则分别被处十五年、五年、一年及交付感训的判决……戴传李兄妹及其他三名台大学生仅被处以交付感训最轻的处分,而且并未入狱”。根据“国家安全局”印 “机密”文件 《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该案的处刑档案所载及《中央日报》的相关报道,即知它与事实还是有所出入的。事实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于1949年12月10日,枪决张奕明、钟国员、罗卓才、谈开诚等四人,其余 ‘钟浩东等十八名’移送感训。”1950年10月14日钟浩东同案三人枪决,其余十一人分处十五年以下不等刑期。其后,钟浩东的表哥邱连球与逃亡后被捕的蓝明谷与钟国辉等又陆续被枪决。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最后,谷正文在这节更为狡猾而恶毒地编造了一个其谎言叙述源头的关键伏笔:因为钟浩东的口供而提供了地下党领导人老郑(蔡孝乾)身份的线索。
刻意塑造蔡孝乾的腐败形象
关于蔡孝乾,谷正文如此塑造他的形象:“他浑身上下散发出来长征老干部特有的傲慢”,对自己第一度落网时的仪表——“笔挺的高级西服,搭配着一条花色鲜明的领带”,“感到非常满意”[3]84。
“他的党龄很深,党性很强”,但“眼神却闪烁不定”,看起来“很注重物质生活”。“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3]85
“自从民国三十九年元旦第一度落网”后,“拒吃局里为他从中华路买来的水饺大餐”,想改吃“延平北路波丽露的牛排”。“留下了许多具体线索,使侦防组得以在短短时间内,连续破获吴石、刘晋钰、 朱谌之、 严秀峯等人的案子。”[3]87,128
最恶毒的是,在“台共四大头目狱中互斗逼疯老大蔡孝乾”一节中,谷正文又借由虚构的张志忠批判之口,编造落实了蔡孝乾“如何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如何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份,以及生活是如何的糜烂,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吃饭,在永乐町看戏”等奢浮形象。最后,蔡孝乾由于“精神病”住进台大医院等[3]137-141。
事实上,蔡孝乾于1950年1月29日在泉州街自宅第一次被捕。2月6日乘机逃走,到4月27日在台南县嘉义区竹崎再次被捕。但记忆力好到可以记住几十年前的几点几分的谷正文,所述日期却完全与事实不符。这样,他一面之词所说的事情还能信吗?
然而我们看到,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中共台湾工委为何遭受大破坏》一文,就“据谷正文回忆”写道:“历史事实证明,蔡孝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有日本经营的基础而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便迷恋于奢华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钱不够花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孝乾竟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5]
问题是,商人身份本来就是蔡孝乾的身份伪装,而他又联络了哪些上层?至于指控他“挪用组织经费”“向岛内一些富人炫耀”等,也是没有具体内容与根据的莫须有之词。
另外,关于蔡孝乾的“出卖”而导致整个组织被破坏之说,我另有一文探究,这里就不再赘叙了。
关于张志忠及其儿子的虚构叙事
我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与精力处理谷正文的满口胡言了。最后,我想借由该书如何描述他“评价最高”的张志忠来结束这篇不值得写却又不能不写的文章。
谷正文说:“民国三十九年二月间,我综合了陈泽民、朱谌之、吴石等人的口供,分析得知共谍组织武装部长藏在台北新公园附近的中西大药房二楼。二月七日深夜,我们在监视多日之后采取逮捕行动。那一日天气特别坏,很湿冷,或许正是由于天气的关系,张志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沮丧的,完全不像一个从事武装斗争者那么精神奕奕。‘知道你们会来,我等很久了。’这是见面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3]122
首先,根据1950年5月1日张志忠在“保密局”关押时所写字条与8月20日“杨春霖供述笔录”所载,他是于1949年12月31日上午在台北万华大马路被捕。所以,他的被捕与后来被捕的“朱谌之、吴石等人的口供”扯不上一点关系。再者,一个久经考验,负责地下党武装工作的革命者,竟会因为“天气的关系”而“非常沮丧”,乃至于束手就擒。这样的叙事,你能信吗?
谷正文又说,他也“合乎情理”地答应张志忠的 “申请”,允许他们夫妻 “把十岁大的杨杨(扬)接到所内共同生活”。由于杨扬的天真、慧黠,惹人“爱怜”,他们夫妻“也连带受到了较好的待遇”[3]122-123。
问题是,1947年6月4日出生的杨扬,在当时,再怎么算也不可能是“十岁大”。事实是,未满三岁而与母亲季澐同时被“保密局”逮捕入狱的杨扬,于1950年9月2日同被移送“军法处”看守所第45号押房。而张志忠夫妻得到的“较好的待遇”,就是先后“被由李元簇手拟的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所谓的二条一)执行枪决”。
谷正文轻易地就把这笔血债算给作为李登辉副手的李元簇了。然后继续吹嘘说他曾多次前往探视杨扬,并有两度带他到淡水河口垂钓,甚至状似慈祥问他“恨谷叔叔吗?”又说,“大约一年”,张志忠夫妻枪决之后,杨扬“经由保密局一位同事收养监护”。他还强调,许多类似杨扬这种父母被枪决的匪谍的孤儿,“大多由保密局同事收养”。他“自己也曾收养了陈泽民的两个小孩”。而杨扬“不爱读书、很不听话”,“偷窃、逃学和顶嘴”,终于在逃离监护人处后,被领回“保密局”,并由他“安排到保密局汽车保养单位担任修车学徒”[3]123-124。
问题又来了。首先,诚如李敖在为《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作序时指称,“谷老告诉我,毛人凤对他说过:‘你比我还狠!’可见此公狠毒,故无待我们历史家论定也”。然而,恰恰是这个自称“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的“狠毒”的台湾前“保密局”特务,竟而在晚年回忆时大言不惭地提到了“合乎情理”之词,甚而摇身一变为慈祥的“谷叔叔”,乃至于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敢于违背事实,虚构了白色恐怖加害者收养那些受害者的孤儿的情节。再者,根据“安全局”机密文件“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叛乱案”所载,所谓“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后来办了“自新”并未被枪决。那么,“狠毒”的谷正文为何又要收养他的两个小孩呢?历史的讽刺与荒谬,恐怕莫过于此吧。
实际的情况是,杨扬一天也不曾被“保密局”特务收留过。
1950年9月27日,张志忠的弟弟张再添到“军法处”看守所,把他接回嘉义新港老家。初中毕业后,他反抗叔叔对他的管教束缚,不愿继续升学,就出去做事。到了1967年12月12日,他阿公逝世。张再添不清楚他的收信地址,也就没法通知他回新港奔丧。后来,他收到杨扬的贺年片,赶紧寄出回信,告知祖父去世与丧事办理的情况,希望在军中服兵役的杨扬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可以回来看看。然而,杨扬已因想做较轻松的文书工作而掉入圈套,盖了印,写了去大陆做情报工作的切结书,进退不得。他并没有利用春节回家看看,却以“混蛋的家伙”自称,给叔叔寄了一封告别的回信,最后强调,“我闭目沉 ‘思中’国的一切,我热爱它”。1968年元旦,通过部队的通知,张再添得到杨扬自杀的消息,随即赶去台北,把杨扬火化后的骨灰坛带回新港老家,附葬在父亲张志忠与母亲季澐 (衣冠冢)的墓穴里头[6]。
然而,事情到了谷正文的嘴里却变成:杨扬“修车技术尚未学到”,已经学得了“抽烟、喝酒、赌博”,“十六岁那年”(1963年)还“学会了嫖妓”,终因赌债所逼,而拿出“张志忠夫妇临刑前不久,替他缝在衣领内的一封密函”,去向日据时期农运领袖的“华南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刘启光勒索。他还煞有其事地说,“张志忠夫妇”交代杨扬,“这封信很重要。平常不要拿出来,要是有一天你遇上了什么很大的困难再把它打开,拿去找刘启光伯伯”。结果,第一次要了“五百元”,“不到一个月”又要了“三千元”。“隔了一个礼拜”,再要“五千元”时,密函却被刘启光“偷袭抢走”,并“立即撕得粉碎”。那天夜里,刘也“心脏病发送医,随即转送日本进行心脏导管手术,总算保住一条命”。杨扬虽曾戒赌,最后还是“一夜豪赌,又欠下了一笔巨款”,而“选择了在修车厂里上吊自杀”。“他没有留下遗书,但警方却在他衣袋里找到一封柏杨的回信。不久之后,柏杨将杨杨的故事,写成一则感人的报道,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刘启光“看到这则报道”,也因“多年来极力避讳的共谍嫌疑,却意外地被人在报纸上披露”,因而“紧紧握着当天的报纸”,心脏 “导管破裂”而死了[3]122-127。
从修车厂开始吃喝嫖赌,借张志忠夫妇临刑前缝藏的密函勒索刘启光、上吊自杀,到刘启光吓破心导管而死,再到柏杨的回信,统统都是谷正文瞎编出来的情节。如果根据他所提柏杨在报上公开发表的有关杨扬的故事内容来看,他所叙述的许多内容却与柏杨所写不同。其次,刘启光死于1968年3月2日[7]。柏杨所写报道发表于1968年1月26日《自立晚报》专栏。这样,刘启光就不可能是看到报道而“惨遭吓死”的。再者,杨扬自杀的现场是有一张写在印有“海军标准格式”的便条纸上指名给柏杨的遗书。但与杨扬给叔叔回信的稚拙笔迹对照来看,两者显然不同。问题是,两种笔迹只能有一个是杨扬的。这样看来,杨扬的“自杀”背后显然还隐藏了复杂的、不为人知的“事情”吧。
从事实出发看待历史
事实,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出发点。那么,谷正文《白色恐怖秘密档案》所说的事情能有多少是“符合历史”的事实呢?有多少是可信的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结束这篇不是学术论文的打假文章。那就是,绝对不要再不加甄别、批判地引用台湾前“保密局”特务谷正文的谎言来论断台湾地下党的历史了。否则,就不自觉地成为他的反共论述的共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