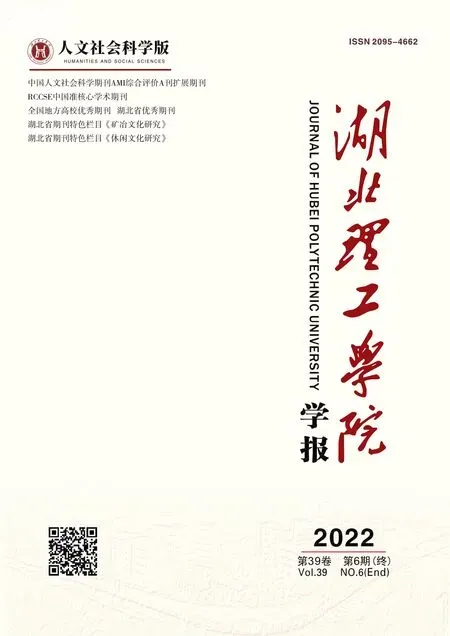中国人年龄焦虑背后的文化探因
韩 晴 雷应鸣
(1.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人文学院,阿姆斯特丹 1081 HV;2.西安工程大学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
“焦虑”作为一种情绪状态,通常是心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各大心理学流派对其认知都有不同的观点,综合来看,焦虑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同紧张、焦急、恐惧和羞愧等感受相联系的情绪状态,而且往往是人们因为对某种尚未发生的危险的预期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反应。焦虑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可分为不同的种类:临床上通常根据焦虑的程度,分为一般性的焦虑和需要治疗的焦虑症;也有研究者根据焦虑持续的时间,分为长期焦虑和短期焦虑等;还有从导致焦虑的直接原因和影响因素角度,分为学习焦虑、人际焦虑、认知焦虑等。针对形成焦虑的原因的研究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和人类学等方面入手,如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就认为社会文化是焦虑产生的根源。
个体对于生存和发展的焦虑是广泛存在的。比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会体会到因年龄增长而带来的不同程度的紧张和恐慌,这种情绪即年龄焦虑。同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年龄焦虑更为显著。比如:小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女性在三十岁之前要结婚,否则就要成为“剩女”;在高校或者机关单位工作的人员,三十五岁要评上副高或晋升科级、四十岁要评上正高或晋升副处,不然就机会渺茫;大众媒体以十年为一刻度把人群划分为70后、80后、90后,各种报道中出现80后或90后到了要做什么事的年纪;《人民日报》曾有文章指出,现在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观念从三十而立变成三十而富,好像三十多岁你还没有富,你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1],等等。西方国家也有广泛的焦虑,但他们无论是读书、就业还是结婚,对于年龄似乎并不苛求,这种“到了什么年龄一定要做什么事情”的焦虑似乎并不常见,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年龄焦虑更为强烈和普遍。
年龄焦虑为何成为中国人目前普遍存在的焦虑呢?很多学者将这种焦虑归因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或者是中国对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的适应,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阵痛的表现之一。这种认知有一定道理,但其实并不能解释为何中国人对年龄更为关注,因此可以说并未触及中国人普遍年龄焦虑的本源。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指出,个体普遍性焦虑感的原因是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文化态度及社会所提供给个人的选择决定着个人在社会中是否会受到强烈的心理折磨,因而焦虑实际上是社会属性的[2]。年龄焦虑的实质是生理年龄、心理年龄与社会角色之间关系的失调和错位,换句话说,社会结构与个人行为之间存在张力,当个人自然年龄和现实生活状态与社会角色期待产生矛盾时,主观上产生担忧、迷茫,甚至悲观、恐惧的心理,这就是我们日常体会到的年龄焦虑,而社会角色期待的内容就植根于文化,因此,这种普遍存在的年龄焦虑,要从中国的文化源起、文化内核以及文化心态中找到答案。
一、文化源起:农耕文化对时间节点的强调
黑格尔曾将古代世界范围的文化划分为三个类型:高原游牧文化、大河流域的平原农耕文化和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3]。钱穆也有相似的划分,他提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三分法,认为自然环境的差异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4]。无论哪一种划分,中华文化的根基是典型的农耕文化这一划分确凿无疑。中国古代长期是农业社会,漫长的农耕文明奠定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农业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同时农业社会中习惯以农事节律安排时间,这种自然节律的划分和强调也延伸到日常生活,继而影响到人生理念和生存方式。
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建立在农业节令和自然观察基础上的,“不违农时”是十分重要的准则。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同气候的联系十分紧密,因此农时的掌握之于农事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以时令为线索的生产、生活经验促成了自古以来的物候学以及历法知识的发展,并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夏小正》就是一部重要的农事历书,战国时《逸周书·时训解》中已划分了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候;到了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将“年”释为“谷熟也”,明确地以农业生产为单位确立时间单位的计量。时节确立后,为了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不违农时”就显得尤为重要。《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吕氏春秋·当赏》中也指出:“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①即农时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不可误也不可错,按照农业节律、四时寒暑去播种收割,便能五谷丰登、民心安宁;倘若错过农时,会影响一年的生计,甚至给国家的安定带来影响。
人作为农事活动的主体,也被纳入到自然之中,人对自然物候变化的体验就成为对自然生命过程的体验[5]。中国人对时节的体察和感知细致入微,“时”作为自然的重要属性,代表着自然的运行秩序,由于人对自然的高度依赖,决定了观念领域对自然价值的全面肯定,这种适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观念和自然的法则也逐渐延伸到社会生活中,成为人行为的法则。农人的农事耕作,由“天时”指令,而农人的日常生活基本也是围绕农事活动而展开,因此,也要遵照“天时”的规律。这种天时与人事相联系的整体观念,贯穿于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6]。例如《礼记·月令》中就将一年中的十二个月做了仔细划分,帝王、公卿、百工及至黎民百姓的政治和日常行为,都被纳入到四季的变化中,自然的时序更迭为人事的运作提供了尺度和依据[5]。有学者指出,《月令》的主题是一年的国家主要政治事务,但这些政治事务安排、施行的根本依据却是自然界的天地四时节律。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自然政治观念,它只有放在农耕文明的框架下才得以理解[7]。也就是说,这种自然时间对人间事务的规范,四时节律对人生节律的影响,就源自于中国古老的农耕文化,其中核心思想就是一切的个人活动和国家行为,都应当遵从天地四时的运行秩序,春行春令,夏行夏令,“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否则就要承受天灾人祸的惩罚。
对于个人而言,时间的节律感也被带入到每个人的生命中。中国文化习惯将个人的生命同宇宙自然联系起来,人与自然节律的协调也发展成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如何阐释“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一个复杂深奥的命题,历来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但从最表层的意思来解释,就是“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②,即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这样,自然的四时节律也就成了人生节律的根本依据,原本存在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节律感也被带入到中国人的具体的年龄观念中。首先,在个人生理年龄方面,自然中一年四季要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人的生命活动也要顺应自然的节律变化。如我国最早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就曾对人的生命节律做了详细的规律,对人的一生的不同年龄节点、一年之内的周期变化、一天之内的气的规律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并提出了相应的养生和诊治的方法;其次,在社会生活方面,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的观念深入人心。天地有四时,人也有少壮中老,《礼记·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曰幼, 二十曰弱,三十曰壮, 四十曰强,五十曰艾, 六十曰耆,七十曰老, 八十、九十曰耄, 百年曰期、颐。”③就是按照人体生长和衰老的自然变化,把人生以十年为一阶段进行了划分;而孔子又对于个人每个阶段应当实现的期望做了说明:“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8]就把每个年龄段应达到的境界做了详细的规定,后来成为历来士人君子参照的标准,李贽就曾评价说“孔子年谱,后人心诀”,也就是自此,以十年为一阶段的年龄划分法以及对整岁年龄的强调在中国文化中植根,人在到达相应的年龄尤其是某个整岁的年龄时,也被社会普遍预期应达到相应的成就。
如此,农耕文化孕育下,最初发源于并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观念和对节律的强调被带入到国家活动、社会活动乃至个人的生命中。农耕文化对节律和节点的强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年龄观,“不违农时”才能获得丰收,国家的日常活动也要按照节令而动,个人的生命,无论是在生理年龄还是在年龄的社会预期中,也都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人生要完成的事情都有一个相应的最佳时间,儒家更是清晰地规划了特定的年龄节点需要达成的成就。自然有“天地四时”的运行秩序,农业耕作和作物生长需要遵照时节,违背天时便会遭到天灾的惩罚;对于中国人来说,人生在世也有做某些事情的最佳时间,比如结婚生子要在三十岁之前,事业有成要在四十岁之前,六十岁要含饴弄孙等等,否则就错过了应有的时机,错过就意味着耽搁,耽搁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种对年龄节点的强调,反过来也成为对错过最佳时间点的恐慌,以及对一旦错过这个时间点就无法完成某件事情或达成某项成就的恐慌,无形中就成为一种压力、一种催促,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成为一种绝对正确,因此可以说,农耕文明对时间节点的强调是导致中国人年龄焦虑的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
二、文化内核:重生轻死与进取精神
农耕文明的内向性和现实性也影响了中国人对待生死的精神,表现为重生轻死,即重视现世的生活,而不是弃绝现世追求来生。人生有限,而人们又渴望无限的超越性,这种精神渴望往往通过某种信仰实现。中国人并不缺乏信仰,但中国人的信仰中缺乏终极性和神圣性,并没有对死后世界的构建。宗教为了满足人们追求无限的精神需要,想象和设定一种“终极实体”,这种终极是人类感受的极限,但又是一种无限的力量,使人有可能超越有限的人生,从深陷于有限存在的困扰中彻底解脱出来,产生一种宽慰感、宁静感、安全感和神圣感[9]。宗教信仰往往将这种超越寄放在死后的世界,例如基督教认为人死后等到末日审判的那一天可以复活进入天堂,佛教把人的生死放入“六道轮回”,将现世视为“空”和“无”,希望超越六道轮回达到涅槃境界,进入“极乐世界”。无论是“天堂”还是“极乐世界”都是同现实生活和现世人生割裂的彼岸,使人认为似乎这一生无论境遇如何,之后还会有更圆满幸福的归宿。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这种彼岸的构建,即使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中创造了一套“神仙体系”,其中的“仙境”和“仙山”是同现世相接的,甚至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而神仙也多是现世生活修炼到长生不老的人,从东晋时期也形成了神仙积学可致、长生有道可学的普遍看法,“神仙体系”的核心意义还是在于对现实人生的珍视。因此,从古至今,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宗庙祭祀活动还是民间对天神祖灵、佛祖菩萨的崇拜,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对人世之外的彼岸或鬼神世界感兴趣,而是寻求现世人生的心理平衡,目的还是为了现实生活的需要。 这种客观上人人都有一死的事实和主观上死后无所寄托的终极信仰缺失带来的就是对现世的眷恋和重视,所有的现世活动都成了因必死而做的积极补偿,如何度过这有且仅有的一生,就成了每个人要思考的命题。
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更是倡导积极乐生、重生轻死,倡导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儒家也有生死关怀,但重点是放在对“生”的关怀,缺乏对现实的超越精神。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8],就是以生观照死。杜维明就曾指出,儒家精神具有此世性,即“服膺于当下此世的内在合理性与意义”,而且“这种服膺和信守绝非消极地随世所转或接受现状,而是由从内部转化此世的坚定决断所促成的”[10]。因此,儒家要求生命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单纯地活着,而是要有所成就,把积极进取作为人生在世应当践行的生活方式,要秉承“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8]109的信念,去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8]94。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人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奋发有为,形成了将功德作为人生的意义的价值观,追求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具体的做法上,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荀子·大略》中记载了孔子教导子贡的一段对话,就是这种态度的鲜明反映。子贡认为学习太辛苦了,就想休息,而孔子则指出无论是“事君”“事亲”,还是与朋友相处,哪怕是劳动耕作,都不能停止学习的步伐,何时能停止呢?孔子曰:“望其圹,皋如也,颠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④即只有当死后化为一抔黄土时,才能真正停下来。儒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进取精神被后世之人不断秉承发扬,已内化为重要的民族精神,例如宋代的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等等,都是这种人生价值观的写照,而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俯拾皆是。
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奋勇向前,但伴随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而来的也会有潜在的焦虑。首先,积极进取就会带来终日乾乾、不进则退的紧迫感。因为人生有限,要想在有限的人生中建功立业,就要做到“君子之学,必日进则日新,不日进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⑤。人生中的时时刻刻都要力争上游,否则就会有后退的危机,而且哪怕身处逆境,也要能够百折不挠、迎难而上。如此一来,人活于世,时刻处在一种鼓舞和鞭策之中,倘若这种鞭策过于急切,就变成了一种催促和压迫。其次,将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反过来看,或者推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对平庸的谴责和不容,也容易带来现实人生的恐慌感。儒家给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张,似乎倘若资质平庸,能把个人修养提高即可视为一种成功,但在实际的执行上,“修身”只是起点,而“平天下”才是要达到的终点,前者因后者才产生自己完整的意义。换而言之,人活一世,最担心的就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8],一个不显不达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倘若生前未能有所成就,死后也不被后世称道,那么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孔子自己都曾说:“四十、五十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8]宋代张栻对此的解释为:“后生可畏,以其进之不可量也。然苟至四十、五十,犹于道无所闻,则其不能激昂自进可知。”[11]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若还没有“闻道”,人生也就显得基本无所成,而若一个人无才无德,终日饱食又无所事事,更会被批判指责。
年龄是人生的标记,是时间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中国人的年龄焦虑也可以说是这种此生此世要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带来的焦虑感在每个个体上的表现。中国人的信仰中没有一个终极的人格神可以祈祷倚助,也并不寄希望于死后的世界,因此就对现世人生抓得更重,再加上从汉朝以来的两千多年,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正统的思想,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和内核,儒家倡导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已内化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这种重生思想和进取精神影响下的现实人生,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建功立业、名垂千古,就像是不停地与时间赛跑,由此导致的现实人生的紧迫感就会非常强烈;倘若在某个年龄段并未实现应有的社会期待和个人期待,甚至人到中年一事无成,则恐慌感随之席卷而来。重生轻死和积极进取精神潜在造成了人生在世一事无成的恐慌感和虚度光阴的负罪感,对现世的深刻眷恋变成要在现世有所成就的压力感,催人奋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转而成为现实中焦虑的来源。
三、文化心态:群体意识下的人际压力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指出: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不是西方那种民族国家,其身份认同感源自作为文明国家的悠久历史。文明型国家不同于民族国家,文明型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也不一样,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就是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12]。的确,在农耕文明和儒家思想的双重作用下,群体意识可以说是中国人文化心态中最典型的特征,这一点也是中西方文化上的一个典型分别所在:西方重个体意识,中国重集体意识。所谓个体意识,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因为具有独立人格,每个人的选择和行为,他人都不能强加干涉;所谓群体意识,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就是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群体的公共意志[13]。农耕文明中,人地关系相对稳定,从土地引出的血缘、亲缘关系十分紧密;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建造依赖于群体合作,因而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也被纳入到家庭中,而家家户户又被纳入到宗族、村社等更大的群体之中,原有的血缘宗法制成为维系社群组织的纽带,直至进入权力等级社会。因此,社群组织的群体意识增强,人们养成服从的品性[14]。儒家思想对自我进行了进一步的消解,将个人纳入“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宗法血缘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以“忠”“孝”和“克己复礼”对每个人在这个网络中的行为进行规范,个体固然有自己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只有在群体中才能体现,胡适就曾说过:“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15]因此,中国人很少将个体视为孤立的,而是其父之子、其兄之弟、其子之父,个人的存在在群体中被消解。
可以说,千百年来的文明教化将群体意识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中,每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个人意志要服从集体意志,个人人格要依附于集体的共同人格。这种根深蒂固的群体意识的积极作用就是集体主义,负面作用则是导致对“他人”的过分强调而缺少独立人格。金耀基说,中国人被安置在一个关系网络中,人乃是“关系的存在”(relational being)[16],因此个人永远要顾及他人的感受,所有人要有集体的思维和集体的行动力,不能我行我素。这种群体化的社会人际关系落实到普遍的社会生活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对群体意识的强调让我们产生了依附于一个更强大力量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但也时刻让我们神经紧绷,尤其是可以避免出现两种倾向:第一是特殊,第二是落后。特殊,就是跟大多数人不同,脱离了主流的思想模式和行动方式,带来的后果就是被群体视为异类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俗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这个道理;落后,就是个人的发展不如周围的人,从年龄的横向比较的角度来说,倘若一个人的学习、事业或家庭的发展不如大多数的同龄人,就是一种落后,落后也可被视为一种特殊,而中国对于落后的态度也可以用另一句俗话来说明——落后就要挨打。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诚如其言,在群体意识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生活,自我的人格和自我的意志存在的唯一的合理的方式就只能是同群体相协调,每个人都希望置身于社会和群体之后,而不愿成为独树一帜的那个。
对于个人生活来说,这种群体意识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对个人幸福感和成就感的追求。幸福和成功是每个人要追求的理想,甚至可以说是个体在人生在世的终极目标和希望所在,但群体意识占主导的文化中,对“何为美好人生”与“何为个人成功”的界定却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换而言之,中国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是同群体相联系的,会受到个人与他人或环境的关系的影响,甚至是由他人所决定的,因此有学者将中国人的幸福观定义为“社会取向的幸福观”,以区别于欧美文化中“个人取向的幸福观”[17]。个体主义文化强调情感的重要性,提倡追求个体的快乐和幸福;但在注重集体观念和感受的中国文化中,个人情感并不是决定个人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个人的幸福是同他人、家庭、集体等群体关系联系起来的,只有当个人的幸福得到了这些群体关系的认可和祝福时,个人的幸福感才真正确立,也就是所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成就感也是如此,成功的标准是群体标准和社会标准,成功不是自己看到和觉得成功,而是要周围的社会和群体看到和觉得成功,个人对成功的体会和感知往往要通过外在的肯定和赞誉才能实现,因此,追求社会认定的成就才是中国人自我成就感实现的重要方法。总体来说,个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就建立在群体对个人的认同之上,群体掌握了衡量的尺度,当个人行为偏离这个尺度时,便很难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
这种对群体意识的内化和强调正是导致当下年龄焦虑的最直接和最广泛的因素。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写道:“在集体主义的中国,一个人是不完整的,他甚至都不能构成存在的单元,必须结婚生子构建一个完整家庭,才会构成一个被尊重的独立单元。”[18]这样的观点略显偏激,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群体对个人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之大,让人不能特殊、不能落后。以晚婚和晚晋升为例,这两件事情就既是特殊又是落后:对于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来说,单身可能对她而言并不是困扰,但被催婚甚至被逼婚才是导致她焦虑的根本原因;对于一位40岁左右的男性来说,平凡也不是问题,但时刻被催促晋升的压力才会产生内心的焦虑,而所有的催促和逼迫的主导者,正是周围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甚至领导和同事。个体作为这种群体关系中的一员,是无法同群体割裂开来的,因而也就无法忽略集体意志,个人无法满足群体期待时就产生焦虑。
四、重审现实:当下的年龄焦虑
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当今的中国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孕育的民族思维习惯和民族心态依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对年龄的审视和焦虑。“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三十而立”也成为大多数人所期待的成功的节点,错过时间便有一事无成的忧虑;已经内化为民族精神的儒家精神赋予每个人“时不我待”的进取精神,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所成就、创造不平凡的一生,倘若庸碌平凡,不能在某个年龄点之前功成名就,恐慌则不可避免;而现实中对“正确”和“成功”的衡量尺度则掌握在个人所处的集体之中,这又带来了对自我的压抑和矛盾心理。以文化中的群体心态为例,现代社会的组织结构扩展了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构建方式,每个人生活所在的群体也发生了改变,“群体”所代表的除了自己的家庭或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范围以外,还可能是自己的同学圈、工作圈或因各种条件聚集的人际交往圈。尽管“群体”的范围发生了变化,但这种群体意识并没有被动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强化了。随着网络的发展,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等即时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表面上似乎每个人都有了更广阔的宣示自我的空间,每个人都拥有了更多的自我选择权,个体的存在从未如此明显。但事实上,交际圈的扩大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也被迫让更多的他人信息涌入自己的生活,让能够影响自己的“他人”也无限扩大,甚至完全陌生的人都有了对自己人生指挥的权利,这也给人生带来更大的焦虑感。时至今日,中国人的年龄焦虑的每一个方面依然可以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根源。
那么,普遍的年龄焦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从整个国家来看,中国人的年龄焦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因为有时不我待、赶超争先的年龄焦虑,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勤劳、更努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就曾说过:中国人的勤奋,令世界汗颜,甚至有一点恐惧。世界银行公布的各国15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中,中国一直都处在约70%的高位,2010年达到了78.2%⑥;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201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12.4%⑦,再除去15岁以下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和青少年,也就意味着,中国几乎所有处于合法工作年龄的人都在工作。国家的发展正是有赖于每一位国民,过去四十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此。但另一方面,这种年龄焦虑感也让人变得更功利、更急迫,导致个人价值观的扭曲化和片面化。早在十年前,一项《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就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金钱成为多数人认同的幸福的同义词[19],人们追求同样的价值,人生的价值观也趋向一元化、同质化。物质财富成为人生成功的标准,人们对年龄相连接的财富数量的主观预期被强烈提升,获得成功所花费的“期望时间”也在不断压缩,人们承受更大的“超时”的焦虑,担心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达到某个目标,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会逐渐减小[20],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在尽量早的年纪有车有房,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成为所谓的人生赢家,不能形成健全的价值取向。
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每个年龄阶段都经历了年龄焦虑,我们应当如何对待这种焦虑呢?只有正视这种焦虑,才能更好地对待它,在与焦虑的共处中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其实从上文分析的三个文化因素以及对现实的考量中,我们也可以推出一些解决方案,那就是:尊重生命规律,保持适度焦虑,克服过度焦虑,培养独立人格。农耕文明强调时节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规律,尊重生命规律就意味着不误事,但也不能过分求快,人生无法跳级,放平心态,二十岁不要希求五十岁的成功;重生轻死的思想让我们对人生倍加珍惜,保持适度的焦虑有利于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过分焦虑则可能带来过分功利,导致价值观的扭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独立的人格才不会盲从,获得不必融入圈子、不必迁就他人的自由心态。当下,有很多人提出“慢生活”“无龄感”等概念,也是缓解过度的年龄焦虑的一种方法。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也要尊重每个人选择如何度过一生的权利,正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说过的那样: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注 释
① 参见《吕氏春秋》第二十四卷《不苟论·第四》,中国基本古籍库,景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第424册83页。
② 参见《黄帝素问灵枢经》,中国基本古籍库,景上海涵芬楼藏明赵府居敬堂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第365册57页。
③ 参见《礼记正义》(一),郑玄注、孔颖达疏,中国基本古籍库,武英殿十三经注疏本56页。
④ 参见《荀子》,中国基本古籍库,景上海涵芬楼藏黎氏景宋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第317册39页。
⑤ 参见《河南程氏遗书》(四),中国基本古籍库,六安涂氏求我斋所刊书130页。
⑥ 参见世界银行动态统计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TLF.CACT.NE.ZS。
⑦ 参见《中国老龄化与健康国家评估报告》,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10月:https://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china-country-assessment/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