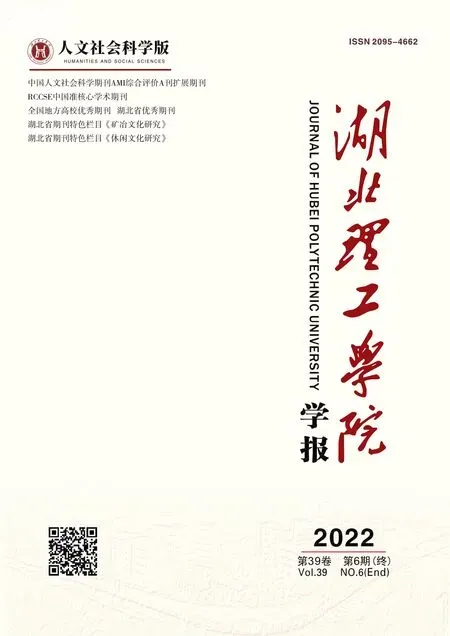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明天》中的生命伦理书写
王延博
(浙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凭借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后现代拷问得以在群英辈出的当代英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学界对其作品的评述也往往聚焦于此。然而,作家继承自19世纪维多利亚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和人文传统总被忽视,其对科技伦理命题的探察也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早在1983年出版的小说《水之乡》中,斯威夫特就从生态伦理与核伦理问题入手,呈现了当代英国社会在冷战中的普遍焦虑,回应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思辨。而在小说《明天》(Tomorrow,2007)中,他将这一批判性的思考不断纵深,着眼于科技进步触发的生命伦理问题,展现了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与对话。《明天》通过一位母亲的自述,在个体记忆的不断闪回中探讨了避孕药对传统婚恋观的解构,人工授精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和未来基因工程可能招致的灾难,流露出作家浓厚的民族忧患意识,同时对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有所启示。
德国技术哲学家卡拉菲里斯指出,在生物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下探讨生命的本质不可避免地要考量现行的伦理观念,因为“它处在一种对生命问题进行理解的阐释学的传统(精神和文化科学)和一种解释及实际改变生命的功能性传统(生物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双重关系中”[1]335。也就是说,避孕药、人工授精术、基因工程、克隆等科技赋予了人理解并改造生命规律的能力,但该如何应对家庭结构的震荡、定义生存的意义不免令人困惑。斯威夫特通过文学想象,在传统与现实的时空对话中从家族延续、情感救赎与生命的内在价值等侧面对生命伦理问题不断求索。
一、避孕药与个人主义伦理
小说开篇,女主人公普拉想起20世纪60年代在大学校园里领口服避孕药的人总是排起长队。在崇尚性自由的时代,人们可以暂时规避自然规律,控制受孕与生殖。“让这个时代如此新,和以往的时代如此不同的是一小片药:一天一次21天,然后停一个礼拜。一种科学,一种社会的魔法。”[2]11随着女性口服避孕药的大肆生产,性从传统的婚育观念中解放出来,纯粹的快感可以被售卖和消费。“避孕使性行为同生育过程可以完全分离开来,人们可以‘享受纯粹的性快乐’,而不必顾虑令人沮丧的意外受孕和生殖……这就减轻了性交后会产生的后果的担心的心理压力,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性观念,使性关系远比过去自由。”[3]153在普拉眼中,身处媒体讯息泛滥、文化愈加开放的90年代,孩子们更早地接触了性知识,16岁的年纪就相当于过去的18岁。时代的飞速更迭剥去了性神秘的外衣,令人窒息的快节奏使女主人公对未来道德观念和伦理环境的变化感到迷惘。
同时,通过人物对传统婚恋仪式的回溯以及代际间价值观念的变迁,斯威夫特揭示出避孕药催生的个人主义伦理冲击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普拉的记忆中,婚姻在60年代的英国似乎成为了一种束缚,一种被人们嘲笑的过时的东西。由于避孕药将性、爱和结婚的联系割裂,婚姻便沦为了枯燥的准生证明,失去了宗教和传统价值赋予的神圣意义。“还有学者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中称,由于‘作为快乐源泉’的性观念的出现,现行道德已成为一片‘堆满支离破碎的信念碎片’的‘荒原’。”[4]4此外,避孕药也模糊了爱情和放纵的界限,个人主义伦理取代了传统的家庭观念,使人产生了不确定和焦虑感。人类试图用技术细化和操纵自然的安排,使生育可以成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机械行为。普拉在对孩子们讲述战前人们的生活经验时提到“你们的父亲可能正是在他父母婚礼的当晚受孕的,就像是小巧、完美而又过时的配方步骤。行为与目的完美地结合在一起”[2]99。可以看出,对战后出生的一代来说,传统的家庭道德逐渐让位于个人自由,仪式感在祛魅一切的时代变得滑稽且无意义。
科利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战后英国的家庭结构尤为坚固,且夫妻普遍要承担照顾双方老人和养育子女的义务,可将其称为“道德家庭”(the ethical family)。而这种家庭结构却由于经济技术的变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道德家庭规范受到的第一个冲击是技术冲击。避孕药为年轻女性提供了掌控人生的机会:性行为可以不再像以前那样导致怀孕了。”[5]105由此,女权主义的诉求和男性的风流不羁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对找寻“自我”的渴望超越了维系“我们”的诉求。普拉自述了父亲对自己的呵护,丈夫麦克的父亲对他的祝福,并且向女儿讲述老掉牙的求婚礼和过圣诞节时亲子间的谈话仪式等。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将家族三代和两个姓氏紧紧绑缚在一起,成为亲情联结的信念体系。但在宣扬个人主义和理性万能的当下,她时刻担忧依靠亲情维系的家族纽带会分崩离析。作家着眼于在科技进步和传统价值缝隙中挣扎的个体,对自我解放的潮流可能演变成自私的伪装,彻底与传统决裂感到焦虑。
此外,斯威夫特借普拉之口,质疑了激进女权主义者提倡借助避孕技术摆脱成为“生育工具”的片面立场,表达了人类孕育生命的普世愿望。诚然,避孕技术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承担母亲的伦理身份不再是个体的必然选择,女性可以有更多的个人空间和职业抱负。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生育是对女性的极大束缚,“孕妇为自然力量所俘虏,就成了植物和动物,成了储备的能量库,成了孵化器,是个卵子”[6]197。但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忽视了孕育生命的冲动和血脉相惜的亲情是人类最基础的情感归属,成为母亲也是自然赋予女性的特权和财富。在普拉看来,“爱就是爱,不要让我成为半个女人,我会拿你们交换20幅提香的画作吗?不会”[2]127。女主人公的心声旨在引发人们对陪伴和生命的思考,在她看来,亲情的互动超越了一切世俗成就。
小说中,由于口服避孕药在战后英国社会的流行,人们可以单纯享受性快感而不用考虑结婚和组建家庭的压力,现代社会正在加速脱离传统,在避孕技术的助推下,保守的婚恋观被遗忘,神圣的仪式感逐渐消退,个人主义伦理瓦解了过时的“道德家庭”。
二、人工授精术的伦理困境
斯威夫特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并未止步于避孕药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影响。在揭示了人类孕育生命的恒久愿望后,他开始着眼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小说中,由于一直无法受孕,普拉决定人工授精,但却面临着难解的伦理困境,她担心“这个选择真的是‘我有多么想要你父亲的孩子’还是‘我多么想要一个孩子’”[2]150。令她万分为难的是,孩子与父亲的统一关系发生了分裂,甚至成为了对立的选项。如果接受了其他人的精子是否意味着爱情的贬值和对丈夫的不忠?这是否意味着对孩子的渴望超过对伴侣和婚姻的重视?这些困惑始终在她脑海中萦绕,挥之不去。学者王学川在《现代科技伦理学》中阐述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道德疑虑:
尤其是供体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是妻子的卵子与第三者的精子结合,这与通奸致孕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或者会使妻子认为若用自然的方式(性交)接受供体的精子亦无不可。这至少是妻子不忠于丈夫的一种表现。而且,供体人工授精出生的儿童存在,使第三者进入婚姻的排外身心关系,破坏了婚姻的心理、物理统一性[7]159。
由此看来,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固然有助于缓解当代社会的生育焦虑,但同时颠覆了以血缘共识为基础的家庭结构。女主人公在备孕前歇斯底里的疯狂举动也恰恰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在决定采用人工授精后,普拉和丈夫到威尼斯度假,看似想要重温往日的激情,实则暗示了两人要与爱情诀别。普拉觉得,从此他们之间会混入陌生的血缘,真实的婚姻将一去不复返。于是,她不断向麦克求欢,甚至试图阻止精液流到体外,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对真实东西的急切渴求”[2]159。同时,因为遗传的关系,普拉认为,如果自己在丈夫之前去世,那么麦克可以在儿女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来寄托哀思,但要是丈夫先一步离世,自己却无法获得同样的慰藉。人工授精虽然满足了主人公孕育生命的渴望,但延续丈夫的家族血脉却也意味着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诚与恒久的精神陪伴。
此外,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也会造成代际间伦理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困惑,科学技术可以帮助孕育生命,但无法保障家庭和谐。让普拉感到纠结的是,如果把真相告诉女儿和儿子,他们是否会在生物学父亲和养父之间进行抉择,如何定义父亲这一伦理身份是否会变得困难?“第三方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将由你们决定,必须由你们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2]189同时,孩子们对待血缘和家族延续的态度也困扰着普拉。一方面,她担心血脉传承的断裂会让他们在永恒的“寻父”焦虑中疏离现在的家庭与亲情;另一方面,让她感到惊慌的是,在技术理性主导一切的当代社会,儿女或许早已服从于现代科技的规训,他们可能会因为与众不同而感到兴奋,甚至沉浸在技术创造一切的狂喜之中。
尽管斯威夫特指出生命科学在服务人类生活时会带来棘手的伦理困境,但同时也暗示亲情的联结是巩固家庭结构的救赎路径。虽然在生物学意义上普拉一家显得有些特殊,但主人公夫妇也同其他父母一样承担家长的伦理责任。在普拉的回忆中,当孩子们游泳遇险时,丈夫奋不顾身下水救援。“他怎么知道现在将你们从礁石边冲走的水流不会像冲垮你们9岁的身体一样冲垮一个成年人呢?”[2]210相较于普拉,丈夫麦克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更多。每当面对孩子们的时候,他可能联想到自己不能生育,妻子与别的男性曾经“亲密接触”,在儿女的脸庞上无法辨识遗传的印记等令人不快的体验。由此,他必须要克服所谓男性尊严的心理障碍来实现对孩子们的关爱。但在儿女遇到危险时,他展现了作为父亲的勇气和担当,暗示了只有跨越血缘壁垒的亲情才能弥合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伦理观念之间的鸿沟。斯威夫特在访谈中指出:“我们在《明天》中看到一种反讽,一个不那么真实、半人造的家庭在另一个意义上其情感的纽带要比很多百分百由生物关系联结的家庭更加有效、绑缚得更紧。”[8]116他意在说明情感守护和伦理责任的承担是人类可贵的精神财富,能够化解血缘隔膜,而脱离了爱的生命设计会给人类文明带来威胁。
透过女主人公矛盾复杂的心理,小说展现了人工授精给婚姻和亲子关系带来的挑战。同时,人物对亲情的守护和伦理责任的勇敢承担为当代社会走出伦理困境指明了救赎之路。
三、尊重生命与未知的明天
通过普拉的叙述,我们获知现如今身为成功商人的麦克曾经是饱含热忱的生物科学研究员,他的身份蜕变揭示了英国社会功利主义思潮泛滥的时代症候,披露了科研精神中审美意识与诗性的缺失,触发了人们对生命价值评判标准的思考。当麦克还是一位勤奋的生物学学者时,他整日沉浸在探究大自然生命奥秘的纯粹乐趣中。“他的研究领域是软体动物,重点在于探索蜗牛壳的构造与意义,以及整个进化和生态学的重要价值。”[2]18但在“撒切尔主义”的影响下,市场需求促使麦克放弃了成为科学家的愿望,转行做了售卖科技逸闻的出版商。普拉感叹:“在你们的生活中,科学只是变得有利可图。”[2]16作家从小说人物职业规划的改变表达了对当代英国科研环境的担忧,当自由市场的思想深入社会肌理,生命价值被世俗的价格替代,科研工作者还能保持初心,虔诚地探索自然界中的生命现象吗?
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默顿曾指出,某一类科研的存在是由社会价值的标尺来判断的,而对工具理性的推崇早在17世纪的英国就显出端倪。“发生的情况是,对传统的规范失去了敬意,并出现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倾向,即从功利主义的、(经济上)理性化的观点看待相沿成习的价值。社会活动都按照它们在促进眼前目标方面的工具性功效而受到评价。”[9]290小说中,科学功利主义的观念在政府“帝国复兴”战略的推动下不断深入人心。与传统的生物学相比,基因遗传不言自明地成为了未来生命科学关注的焦点。在普拉看来,DNA已经是丈夫关注的热门话题,“我认为他在担心的是做一个‘只是自然’的人,仍然穿着短裤在萨塞克斯闲逛,甚至不知道DNA的存在”[2]226。自1953年人类解锁了双螺旋的基因结构,其巨大的实用价值便吸引各国不断投入科研力量。斯威夫特担忧的是人们在为改写自然规律而狂喜时,会忽视基因工程对生态环境和物种改良的系统性影响。
通过女主人公对未来的忧思,作家思考了基因工程可能带来的灾难。如果人类像对待非生命体一样改造自身,那么机械化和同质化的改良会让人成为无差别的“超人”,打乱进化的节奏,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自我复制。当普拉想到通过人工授精出生的儿女意味着两个传统家族姓氏的终结时,她思考了所有生物物种延续的意义。“胡克家族的最后一代,坎贝尔家族的最后一代。这真的重要吗?最后的莫西干人……最后的渡渡鸟……当所有东西都由克隆定制和基因工程来完成,那么是不是男性会更真切地怀念古老的火炬传递式的父性,女性也会怀念母性的真切体验?”[2]244在她看来,也许我们的科学技术在某一天可以复活一切生物,甚至制造新的生命,但是这些复制品无法替代独特的生命谱系与自然的馈赠,反而将抹除一切个体性与多样性。同时,“可能引发严重的伦理问题:如人的面目、本性和情感的改变,家庭和社会秩序失常,人类遗传进化紊乱和基因库退化”[10]513。如果人类依仗着克隆技术对生态系统肆意妄为,按照绝对自由意志操纵生命体,终将会被反噬,走向自我毁灭。
柏格森指出,人类的因果机械论和智力对无机材料世界的把握无法套用在对生命的理解上,生命是一种冲动和绵延,而我们对非生命体的改造追求的是恒定和静止。因此,当人依靠生命进化获得的知识去改造生命便显得吊诡。“我们不但不看那种冲动的整体,它跨越各代物种,将个体与个体、物种与物种连接起来,将整个生物系列汇集成为奔涌于材料之上的一种洪流。”[11]213科技对生命的无限改造无异于截断生命的流动,将其分割、嫁接、重组最后固化。斯威夫特在小说中通过普拉对未来世界的担忧回应了柏格森的这种思考,即人们将生命的意义完全寄托于对外部环境的改造,使手段替代了目的,形式僭越了价值。
因此,普拉的担忧引发了该如何构建完整生命意义的疑问。人不能只关注对外部生存环境的改造,甚至妄图操纵基因来获得永生,在精神层面的奋发向上才是使生命延续的应有之义。观察小说人物的代际承续可以看出,科技的进步并没有使人生活得更加安逸和充实,反而带来了更多危机。麦克的父辈经历过二战和国家的由盛转衰,而麦克和普拉这一代人时刻承受着冷战带来的恐慌,同时,通过人工授精孕育的孩子带来了新的伦理困境。想到儿女的未来时,普拉感叹:“你们这两个冷战期间出生的婴儿正逢其时准备出生在一个不再冷酷的世界里……现在,几年过去了,看起来不太好,我们甚至被告知气候变得太暖和了。”[2]226在她眼中,全球变暖带给下一代的挑战似乎更加严峻,那么他们要怎样去面对呢?或许作家在叙述小说人物一家团结一心彼此守护时就暗示了答案。西美尔指出,对于精神阶段的生命来说,制造一种独立的、有意义的内容也是内在的。我们的想象与认识、我们的价值与判断以及它们的意义,它们实质性的理解和历史作用全都在创造性的生命之外[12]25。也就是说,生命在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也在能动地创造情感与道德,由爱触发的伦理意识使我们将其他生命体纳入自我的生命领域欣赏和珍视。
生命哲学家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的逻辑和知识体系无法将人类社会的道德与历史文化概念化,并加以推测和运算,人的意识与精神是超验的。“即使对人类精神的起源进行研究以前,人就在自己的自我意识内部发现了意志的至高无上性、发现了与行动有关的某种责任、发现了使各种所有事物都受思想支配的能力、发现了从其个人自由的堡垒内部出发抵制所有各种侵害的能力。”[13]18这一论断表明,人的意识活动与精神世界和自然科学强调的客观实在是不可通约的。小说中,普拉对孩子们未来的担忧也说明了这一点,“有时候我觉得你们生活在某个冷酷和治愈的世界当中,每一个故障都有解决的办法,每一次震惊都轻松应对”[2]101。在她看来,技术手段似乎成为化解现代社会矛盾的不二法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概念和公式化的思维去思考,以便快速满足眼下的需求。但对改造成果的痴迷使人们忽视了每一次改变都要负担相应的责任。
小说结尾处,斯威夫特以“诺亚方舟”的意象指涉了未来人类自我救赎的希望,对人们能否在世俗的挣扎中反思狂热的工具理性,创造一个新的精神世界提出了质询。普拉的孩子们曾经画过一幅诺亚方舟的画,其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诺亚和他的妻子,而你们两个承担了这庄严的角色,你们不只是在幸运的乘客中间,而是开始掌舵”[2]229。作为充满人文情怀的作家,斯威夫特在小说中展现传统仪式的意义、孕育生命的渴望、朴实真挚的亲情和伦理意识的价值,意在指出人们应该关注内在生命的成长,这是化解环境危机、保证种族延续的要义。
四、结语
在小说《明天》中,斯威夫特思考了“避孕药”“人工授精术”和“基因工程”等给当代英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在生物科技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传统的婚恋与家族观念被不断解构,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感持续衰减,科技本质主义的思潮催生了现代文化危机。在因果决定论的支配下,生命的流动被阻隔,审美的、艺术的、诗性的和情感的创造成为了僵化的形式结构,现代人只能依靠可以被预测和计算的实践排遣内心的孤独感。不可否认,科学革命极大地满足了社会进步的需求,但当人类现有的伦理道德无法为其改造外部世界和自身的能力背书时,人对片面知识的狂热会颠覆生命自我超越与生成的本质。小说中,正是得益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普拉才能得偿所愿,成为一位母亲,这表明斯威夫特绝未抱有回到前现代伊甸园的幻想,反而肯定了科技的积极面。他担忧的是科技与人文割裂,会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的绝对自治力量。这一警醒回应了斯诺所说的“应当把科学同化为我们整个心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4]16。小说《明天》展现了人类孕育生命的恒久愿望,肯定了亲情的救赎力量,揭示了生命之流无限的创造性,彰显了当代英国知识分子浓厚的民族情怀与时代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