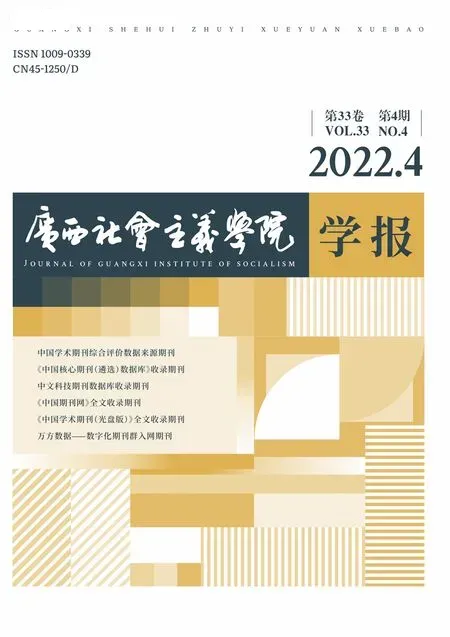追寻文明史迹:骆越科技文化续论
李 妍,覃彩銮
(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28)
科技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综合实力的体现,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标志与动力。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建立和巩固时期,是经济文化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重要发展时期。秦汉时期,随着岭南的统一和郡县制的推行、大批中原人的南迁和中原文化的传入,骆越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得到发展。在手工业生产方面,不仅种类增多,而且制作工艺日趋精良,产品质量有了新的提升,其中包含着诸多的合理性、技术性和科学性,反映了骆越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一、陶瓷器烧制技术
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数百万年时间里,主要是在打制石器、采集渔狩、茹毛饮血、以洞群居的蒙昧岁月中度过的,而文明的曙光则是在距今约一万年前开始出现,主要标志是开始出现磨制石器、原始农业、陶器烧制、家畜饲养和巢居等。其中工艺最复杂、科技含量最高的首推陶器烧制,它涉及陶土的选择、加工、器形塑造、焙烧等工序和技术。
在骆越故地的南宁邕江、柳州柳江两畔及附近的洞穴里,发现有许多距今10 000 年至8 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遗址里发现有大量的陶器(片),在南宁犳子头遗址还发现呈大片块状红烧土(应为制陶泥料)。骆越故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器(片),多呈灰褐色,内夹有细粒石英砂,陶壁较厚,质地较粗糙,外壁多饰有绳纹,器形主要罐、釜类。据研究,骆越故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现的陶器,皆为手制,并采用露天焙烧,形态原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之一。
通过考古学研究,可以揭示原始陶器的发端与演变过程,即陶器是原始人类在用火过程中偶然发现并生发烧制的灵感。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懂得用火(先是使用或保留天然火种,而后是人工钻木取火),用火烤熟食物、取暖,甚或驱赶猛兽。原始人类在用火过程中,发现经过火烧过的泥土变成褐色硬块,长时间不会腐化。这种现象的反复出现,增加了原始人类的感性认识,进而用泥拌水捏成雏形器,放在火堆里焙烧,直到烧成褐色陶质为止。在此经验的基础上,先民们便选择土质细腻、少杂质的黏土,经过拌揉(可增强泥料的密度和黏性),捏成适度的器形,然后放入火堆里焙烧,当温度到达800 摄氏度左右时,便形成陶器。陶器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是人类第一次通过物理变化和化学反应使物体的本身发生质变,即通过火的作用,改变了自然材料的物理属性,使土变成了陶,赋予了泥土新的生命力。因为在陶器发明之前,原始人类曾制作过各种石器、木器、骨器或蚌器等,虽然包含着各种技术,但其制作只是改变了原材料的形状,而未改变其材料的物理属性。陶器的烧制又同原始农业的产生和人们的定居生活密切相关。陶器的出现,极大地方便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可以用陶器来烹煮或盛储食物,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有利于提高人们的体质健康,同时也为后来陶瓷艺术的发展和审美观念的提高开启了先河。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使之与时俱进,在传承过程中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与品质,实现新的超越,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随着中央封建王朝相继对岭南的统一,大批中原人进入岭南地区,给岭南输入了掌握先进生产技能的劳动者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带来了中原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岭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骆越制陶业和生产技术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考古发现可知,这一时期,骆越地区的制陶业无论是生产规模及产品质量,还是烧制技术乃至科学元素,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提高。
首先是轮制技术的发明与采用。所谓轮制,犹如民间制陶作坊里使用的用一块圆形实木,底部中间设一圆孔,套入轴心,圆木即可转运。制作时,把制陶泥料放在圆木盘上,转运圆木盘,制陶者双手捏住泥料,凭着经验,制成需要的器坯。如今看来,此种制陶方法,已属传统手工技艺,不足为奇。但在生产力尚较低下的上古时代,这种轮制制陶法的发明与使用,则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艰苦摸索、反复实践、不断总结与改进才得以实现的,凝聚着先民们的创造智慧和进取精神,在制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采用轮制制陶方法,运用了力学的原理,通过木轮的旋转,工匠凭着经验,可以从容制作各种形制的陶器,不仅提高了制陶效率,而且可使陶器日趋规整、器壁厚薄均匀,其中包含着诸多的科学、合理因素。因此,在骆越故地发现的陶器,不仅器物规整,造型圆润,而且器壁上多保留有呈流线型的细长指纹线痕迹。
其次是陶窑的发明与应用。由泥塑的陶坯要真正成为陶器,需要火的焙烧,当温度达到800~1 000摄氏度时,器坯才会发生质的化学变化,变成陶器。史前时期采用露天焙烧法,直接把器坯放在火堆里焙烧,不仅焙烧时间长、耗柴多,而且每次焙烧的陶器数量少,陶色呈灰褐色,火候不均,陶质也较粗脆。随着骆越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有了新的发展,于是相继出现了第二、三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农业与商业的分工,一方面人们生活中对陶器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包括陶器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陶器开始成为商品用于交换。于是,出现了专门制作陶器的工场与工匠。因此,如何提高陶器的烧制效率,提高焙烧温度,增加产品种类与数量,提高产品质量,已成为骆越工匠追求的目标。春秋战国时期,骆越工匠经过不断摸索与实践,发明了专门用于烧制陶器的陶窑。早期的陶窑形式为竖形窑,形似马蹄,故称“马蹄窑”。这种窑为半地穴式,即在地面挖一直径及深度约1 米的圆坑,露天部分用泥土筑成高、宽约1 米的圆窿形窑壁,穹形顶上设有一圆孔,作为焙烧的出烟孔;窑腔下半部用土筑成窑箅,箅面上留有若干小孔,焙烧时火焰可通过窑箅进入窑床;底部一边设有小窑门,供放入柴草焙烧。使用时,先把制成且已晾至半干的陶坯有序地放置在窑箅上,然后从窑门放入柴草,点火焙烧,直至烧成陶器为止。汉代时,陶窑结构有了进一步改进,主要是窑床体量增大,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严密。考古工作者在合浦县发现一处汉代大型制陶工场和陶窑群,共发现21 座陶窑,多数陶窑保存完整,特别是窑床上部的穹窿顶内壁,尚保留有烧成红褐色遗迹,说明这些陶窑曾反复使用过。这一制陶工场及窑群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汉代窑址。这些陶窑为大型马蹄,穹窿顶,高、宽各约2 米,烧制陶器的容量明显增大,数量和品种明显增多。估计该工场烧制的陶器多数是作为商品,用于交换。采用陶窑焙烧的方法,是对前期露天焙烧的革命性变革,是制陶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采用陶窑烧制技术以后,不仅可以有效节省柴草,缩短焙烧时间,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提高窑温,提高陶器硬度与品质,使得窑床里的二氧化碳得以还原,使窑床里的陶坯受温均匀,陶器颜色呈较纯的灰白色。因其结构细密、质地坚硬,故有“印纹硬陶”之称,标志着骆越陶器烧制技术的新发展。
其三是陶器纹饰的印模技术。在陶器上施以纹饰,源于史前时期,主要是通过手工刻画或绳索压印于器壁上,其作用是使之形成皱褶,便于手捧时平稳而不易滑脱,同时也兼有美化陶器的作用,可以说是开创了陶器装饰艺术的先河。到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骆越的陶器装饰艺术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其美化与审美功能要大于实用功能。工匠们将需要装饰的花纹图案刻在木板、泥模或石片上,有序地压于陶坯上。如在骆越故地发现的饰有规整的水波纹、米字纹、菱形纹、夔纹、方格纹、云雷纹、弦纹等,考古界统称之为“几何印纹”。采用模板压印陶器上的纹饰,不仅省时省力,而且压印的纹饰规整、美观。因此,骆越工匠采用模板压印纹饰,是陶器装饰史上的一种创新,其中同样包含诸多科学性和合理性,并且对后世陶瓷器的花纹装饰产生深远影响。
二、干栏建筑构建技术
“干栏”源自壮语,“干”意为“上面”,“栏”意为“房子”,即建在“上面的房子”,全意是“建在栈台上的房子”,即离地而居的木构房屋。因此,“干栏”已成为现代建筑学或我国传统建筑结构中的专用名称。根据语言学的研究,壮语来源于先秦时期的古越语。由此也可见,离地而居的干栏建筑亦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到史前时期。
据研究,早期干栏建筑源于史前时期的“巢居”。骆越及其先民居住的岭南地区,气候炎热,雨量丰沛,江河纵横,地面潮湿,瘴气浓重。史前时期,更是森林密布,猛兽横行。先民们为了避开潮湿的地面,防止猛兽袭扰,确保居住生活安全,在走出前期赖以栖息的山洞以后,迁移到河谷平地,便选择在粗大的树杈间“构木为巢”或“依树积木,以居其上”。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为了方便耕作,先民们开始在耕地附近营造聚落,立木为柱,架楹揖茅,人居上层,下层敞空,标志着早期干栏式住屋的形成。此后,干栏建筑构建中的合理、科技因素便相伴而生,并且呈现出与日俱增的趋势。
春秋战国开始特别是到秦汉时期,随着青铜文化和冶铁业的发展,金属工具在骆越的农业生产及各项手工业中的应用日趋广泛,促进了干栏建筑的发展。从贵港、合浦等骆越故地汉代墓葬出土的铜或陶质的干栏建筑模型可知,当时的干栏房屋平面呈长方形,底部有4 根立柱支撑,立柱上方为规整长方形屋体,前面开设门口和窗口,门前设有围槛,四周墙体呈密封状,顶部呈陇瓦状,似是以瓦盖顶。这是目前岭南地区所见的年代最早的干栏建筑实物资料,标志着骆越人因地制宜、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干栏式建筑的新发展。
从骆越及其后裔壮侗民族流行营造和居住的干栏式建筑可知,自秦汉以来,随着金属工具在建筑营造中的使用和营造经验的不断积累,干栏建筑营造技术也不断提高,干栏建筑结构亦日趋完善。首先是斧、锯、凿、刨等金属工具在干栏木构建筑中的使用,使得木料的砍伐与加工的效率大为提高。据传在春秋时期,作为我国木构建筑技术的鼻祖鲁班,相继发明了锯、钻、刨、铲、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和榫卯与穿斗构造法,开创了中国木构建筑榫卯与穿斗构造的先河。秦汉时期,木构建筑有了新的发展,其代表如史书记载的阿房宫(今陕西咸阳)建筑群、长安都城等。随着秦始皇统一岭南和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大批中原人进入岭南,中原的木构建筑技术也随之传入,骆越人逐渐掌握了木构榫卯与穿斗技术,并应用于干栏式建筑的营造。例如以四根圆木料为柱,在立柱的中、上端,各开凿纵横向的卯眼,另将纵向和横向的梁木、桁木两端的榫头插入立柱的卯眼中;中层用桁条依次排列,铺上木板,形成楼层;顶部用桁木构成“人”字斜坡式屋顶,钉上椽条,用陇瓦覆盖;四周墙体用木板或砖头砌成。
骆越人构建的离地而居的干栏式建筑,具有诸多合理、科学的因素。首先是适应当地气候炎热、地面潮湿、瘴气浓重、毒蛇猛兽横行的自然环境。居住层建于平台上,利于通风,避开了潮湿的地面,又能防止猛兽的袭扰,确保人们居住生活的安全。这是骆越人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营造的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其次是合理利用空间。将房屋架空,底层可以用来圈养家畜,既方便管理,又能积蓄家畜粪便作为肥料。其三是巧妙利用力学的原理。采用木构件的榫卯构造方法,合理利用木构件的合力、拉力和应力,将立柱、桁条、梁木紧密地连结为一体。其四是用烧制的陇瓦覆盖屋顶。其特点因瓦片呈弧凹形,既利于排泄雨水,而且经久耐用,又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因瓦片之间有间隙),适合南方炎热多雨的环境下居住。所有这些,是骆越人在长期的干栏营造和居住生活过程中不断总结和改进的结果,并且对后来干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左江花山岩画颜料应用技术
分布于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是距今2 000 多年前骆越人留下的绘制艺术杰作,是骆越人举行盛大祭祀仪式的形象反映。2016 年,左江花山岩画以其宏大的规模、独特的风格、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价值,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也是目前我国唯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岩画。
据调查,在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畔的悬崖山壁上,共发现82 处岩画,绵延200 多公里。其岩画皆用赫红色颜料绘成,画面上以人物图像为主,占全部图像的90%以上,其余为犬、鸟等动物,刀剑等兵器和铜鼓、钟、铃等乐器。其中以宁明花山规模最大,图像最多。在花山临江一面长210 米、高约50 米的宽大崖壁上,至今仍保留有近2 000 个图像,为国内外所罕见。这些岩画已穿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经受了风吹雨淋和阳光照晒的洗刷,许多岩画至今仍色彩鲜艳,风采依旧。据研究,花山岩画图像颜色之所以能长久保存下来,除了当时骆越人对作画地点的合理选择(画面崖壁上方有突出的岩石可遮挡雨水)和灰黄色石灰岩具有良好的吸附稀释的颜料作用之外,还与当时骆越人对颜料的选择与加工技术有着极大的关系。
左江花山岩画究竟是使用何种颜料绘制,为何经久不褪,这些颜料又是产于何处?这是研究左江花山岩画的重要问题之一。为了弄清岩画的颜料及经久不褪的成因问题,化工专家曾提取宁明花山画面上因崖壁风化而崩落的石块上附着的赫红色颜料进行化验,认定其颜料属赤铁矿。赤铁矿是氧化铁的主要矿物形式,自然界的赤铁矿有多种形态与名称,如亮闪闪的钢灰色晶体称为镜铁矿,鳞片状的称云母赤铁矿,松软土状的称赭石,球状密聚的称为肾铁矿,纤维状的叫笔铁矿等。依据其成分,可分为钛赤铁矿、铝赤铁矿、镁赤铁矿、水赤铁矿等。左江花山岩画的赫红色颜料属肾状铁矿,这是一种放射状的集合体,有肾状的表面,属于赤铁矿呈松软的红褐色土状,古称“赫石”。调研发现,在花山岩画分布的左江一带,既蕴藏着鳞片状云母赤铁矿,也有松软的红褐色土状赤铁矿,而且矿层较浅,有的裸露于外,宁明花山山脚下及附近就发现有裸露的鳞片状或软化成粉末状的赤铁矿,因其红褐色的色泽较为醒目,因而易于引人注目。至目前,尚不知骆越人如何发现并使用赤铁矿为绘画颜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如绘制宁明花山规模如此之大、图像如此之多且高大的岩画,颜料的使用量是相当大的,其间需要经过采掘、粉碎、加工、稀释等的复杂过程。例如在采掘到因风化而松软的赤铁矿后,即使已经呈粉末状,但其中必定还会含有颗粒,需要进行辗磨,再行筛滤,才能获得纯正的颜料粉。正是有了负责颜料采掘、储备、加工、稀释的工匠,为负责绘画的技师提供了足够的颜料保障。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有专门的技术,如在岩画颜料里掺有动植胶的成分,既可以使颜料充分分解,又可以增强绘于崖壁上的颜料的附着力。这应是骆越人在漫长的绘画实践中不断摸索、反复实践的结果,反映了骆越人对动植物胶质功用的认知,进而采用专门的方法和技术提取动植物胶质的方法。虽然目前尚无法知晓当时骆越人是提取何种动植物的胶质或提取的方法,但其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岩画上的各种图像,皆采用色块涂抹法绘制,无论是大色块的头部和身躯,还是粗线条上举的双手和半蹲式的双脚,色泽均匀,饱满圆润,既无空隙,下方亦无滴墨或渗迹,可谓浓墨重彩,着墨流畅,大有酣畅淋漓、一气呵成之势。这有力说明,早在两千多年以前,骆越人不仅拥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而且还掌握了颜料加工和调配的科学技术。
四、纺织技术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四大要素,衣则居生活四大要素之首,可见人类对衣着的重视。衣着与纺织密切相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早在荒远的史前时期,衣着和纺织已开始萌芽。原始先民在采集和狩猎过程中,用兽皮或树叶缀成可遮风御寒的“衣服”。到了新石器时代,地处亚热带的岭南地区,自然界中生长着许多含有纤维的麻、蕉、葛、棉类植物,原始先民在采集活动过程中,逐步增加对富含纤维的各种野生苎麻、蕉或葛类植物的认识,逐步懂得提取根茎里的纤维,经过加工,用纺轮将细长的纤维捻结成线,增加了纱线的韧性和拉力。从考古发现的资料看,原始先民从各种植物里提取的纤维,最早是用来织成渔网,在网的下缘,缀以石质坠,上缘缀结具有浮力的浮标,布于溪河间捕鱼。从骆越地区出土的陶质或石质算盘珠形纺轮可资为证。纺轮是史前时期用来捻线的一种工具,提取的植物纤维,经过加工后,获得细长和富有韧性的纤维,通过纺轮旋转的力学原理,将纤维纱捻纱成线,用以强风捕鱼。先民们对于自然界生长的含纤细纤维植物的观察与认知,进而提取其纤维,利用纺轮捻结成线,织网捕鱼,开启了早期纺织技术之先,其中包含的诸多朴素的科技因素,凝聚着骆越先民的智慧,为后来纺织技术的发展积累了经验。
先秦时期,随着骆越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金属工具的使用和经验的积累,其纺织业有了新的发展,骆越人利用或提取植物纤维的种类日趋增多,纺织技术有了新的提高。1985 年,考古工作者对武鸣县(今武鸣区)马头乡安等秧战国墓群进行发掘时,在17 号墓里,发现一块用麻布包裹的铜片[1]。该麻布质白,轻柔且有光泽。经测量,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11 根,结构紧凑平整,纺织工艺精致,是骆越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麻织实物。这说明在战国时期,骆越人已经能够纺织出轻柔、细密的麻布,并且形成相配套的苎麻脱脂、提取纤维和纺纱、织布技术,出现早期的纺织机。据古籍记载,早在商周时期,骆越人纺织的“卉服”,已成为贡品进献商周王朝,驰誉中原。如《尚书·禹贡》中“岛夷卉服”记载:“孔传:‘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孔颖达疏:‘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春秋战国时期,骆越人生产的质薄凉爽的夏布,已驰誉中原。
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一和大批中原人的南迁,中原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亦随之传入骆越地区,促进了骆越纺织技术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纺织原料呈现多样化,包括苎麻、葛条、芭蕉、竹子、古终藤、勾芒木、吉贝(棉花)、桄榔须、蚕丝、树叶、楮树皮等;二是出现了人工种植的苎麻和养蚕,为骆越地区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原材料;三是流行使用织布机,包括手摇纺车和脚踏纺车;四是纺织品种类和产量增多,品质提高;五是出现了织品的印染;六是新出现提取漆树原料,应用于织品的保护。
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骆越各地发掘的墓葬里,发现了大量的纺织品和织布机构件,其中以1976 年发掘的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纺织品、纺织机部件最为丰富。出土的《从器志》(随葬品)上,记录的纺织品有成匹的缯、布以及用缯、布制成的衣服和装载其它物品的囊袋。麻织品原料有苎麻和大麻,皆为平纹组织,有粗细两种。经纺织部门鉴定,麻织品支数在200S/1 以上,经纬线相当细密,说明当时纺织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丝织品主要有绢和纱,经纬密度为每平方经线41 根,纬线31 根,相当精细。同时还发现有许多黑地桔红回纹织锦残片,出土时颜色鲜艳,其原料应为蚕丝。墓葬里还发现麻织的漆丽纱帽,外表涂生漆,呈青黑色,网孔稀疏,经纬度为每平方厘米经线18根,纬线10 根。另外,墓葬里还发现梭、翘刀、纬刀、吊杆、调综棍、纺锤棒、卷经板、绕线棒、锥钉等纺织机的零件或梳纱工具[2]。
纺织是骆越手工业生产中工序复杂、技术难度大、科技含量高的一项手工业。从提取纺织原料到纺织成布,需要经过选择或种植富含纤维的植物、提取植物根茎里的纤维及抛浆处理、纺捻成纤细纱线、将经线纱布于篦并组装于织布机上、以梭带纱线(纬线)反复织成布料。其中的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有专门的技术与技能,都包含有科技文化的因素。而骆越地区的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麻织品、锦织品和绢织品,经纬纱精细,结构紧密、平整,品质上乘。如此精细的织品,不仅需要有操作熟练、技术精湛的织工,而且还要有一套精细的纺纱设备,其过程环环相扣。从出土织品的精细度来看,首先是纺纱环节的精细,包括麻、葛类纤维的梳捋和蚕茧的抽丝,可为布纱于篦创造条件;其次是纺织机的使用,从出土织机构件和面料细密程度看,当时骆越人应是使用脚踏织布机,而脚踏板提综开口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它省去手工提综环节,可以专事投梭和打纬,提高了纺织效率,而且织出的织品结构紧密、平整;其三是对织品的浸染,其中涉及染料材料的识别、提取与加工,每一项需要有专门的技术,都包含有科技的因素。
此外,骆越人造船、制漆、玉器和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所有这些,构成了骆越科技文化体系。在骆越科技文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中原地区科技文化的影响。骆越人在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科技文化过程中,根据自身生活需要和审美情趣,发挥其创造智慧,不断开拓创新,极大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丰富璀璨的科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