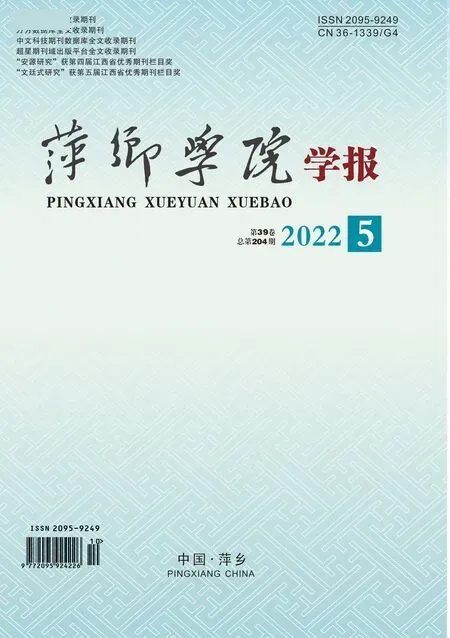试论海明威小说生态意蕴的丰富性
——以《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为例
徐筱虹,刘天艺
(1.南昌师范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2.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大自然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笔下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他的很多小说都展现了人和大自然的冲突,并以此为背景展现人的不屈意志与内在尊严,他说:“我总是按照冰山的原则来写作。那就是浮出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还有八分之七藏在水下。你知道的东西可以省略不写,这样反而加固了你的冰山。”[1]水上八分之一和水下“八分之七”的组合使海明威作品形成了言简意丰的艺术效果,拓展了其作品的叙事张力。
20世纪,随着生态主义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兴起,学界将文学批评置于地球生物圈这个广阔的语境之下,“把切实存在的环境问题和文学文本相结合,探讨人类与自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等”[2]。海明威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大自然的征服、敬慕以及将大自然作为心灵归宿等生态主义意味日益受到了关注。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是海明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篇小说从内容上来看属于狩猎题材,主要讲述了富裕的美国夫妇麦康伯雇佣猎手威尔逊一起在非洲打猎的故事,麦康伯在与蛮荒自然地相对中艰难实现心灵突围,最后在鼓起勇气猎杀野牛时却死在了身后妻子玛格丽特的枪下,结局出人意料,在戛然而止中引人深思。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紧凑,主要人物只有三个,却在有限的叙事中体现了多层次的生态主义内涵。表现出了海明威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个体精神生态的多层次思考,具备了丰富的生态主义意蕴。
一、对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思考
人类中心主义是与生态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是生态批评和整个生态思潮首先要批判的一种反生态的思想观念[3]107。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必须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广泛地树立关于‘人无力去影响自然进程’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把他从骄傲的地位上击退,使他一寸一寸地叹息着放弃他曾一度认为是属于自己的地盘”,使“他承认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事物”[4],才能改变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态度。生态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质疑人类干扰自然进程、征服自然的权利,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力倡导大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就可以发现海明威以人物对自然的征服为故事起始,颠覆了习惯性思维中的“自然工具论”,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
1. 以征服自然反思人类的残酷
小说中的大自然本是沉静博大的。小说这样叙述:“树林后面是一座地面上尽是圆石的悬崖,还有一片一直伸展到一条小河旁的草地,河底尽是圆石,河对岸是森林。”[5]8万物都在各自履行着自我的生命轨迹,“人类只有融入自然,成为其中一分子,才能与自然建立一种真正的和谐关系”[6]。但是人的到来破坏了这一切,甚至残暴地中止了某些生物的生命进程。
麦康伯夫妇用钱雇用了枪法极好的职业猎手、扛枪人还有一些土著仆人陪着他们在非洲打猎,用金钱一路护航、开辟他们得以体验勇气和力量的征服王国。而这种征服在当时非常普遍,“欧美有一些有钱人喜欢到非洲去打猎,他们以猎得狮子、犀牛、野牛等大动物为荣。但是打猎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那些有钱人大都既不熟悉野兽出没的场所,枪法又不高明,不得不雇用人来陪他们打猎”[5]6。以猎杀大动物来彰显征服意志从而获得荣耀感,这本来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典型性体现,动物们被彻底物化,沦为了人类确证自我的一种工具。
生态批评家鲁克尔特认为:“人类悲剧性的缺陷是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眼光,他想要征服、人格化、驯化、侵犯以及开发每一个自然事物。”[3]112这种悲剧性的缺陷导致了生态的失衡、退化,给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麦康伯们的猎杀对于大自然的生灵来说就是这样一场灾难,狮子、羚羊、野牛先后倒在了他们的枪口下。一向吝惜笔墨的海明威在小说着重铺叙了杀戮现场,小说中反复写到了羚羊不可思议地跳,突显了它们在面对枪弹威胁时的惊恐与求生本能。写到狮子和公牛的时候,海明威更是变换了叙事视角,以内聚焦进行了叙述,狮子在被实心子弹击中肋腹时,“胃里突然有一阵火烧火燎的拉扯感,使它直想呕吐”。接着子弹又打中了狮子的下肋,“而且一直穿过去,嘴里突然涌出热乎乎的、尽是泡沫的血。”受了枪杀的公牛“蹬着那双洼下去的小眼睛,狂怒地大声吼叫”。内聚焦手法的运用成功还原了狮子和公牛作为独立生命形态的存在,将它们的生理反应和内心感受直接呈现给读者,令读者内心自然生发出对以麦康伯为代表的杀戮行为的谴责。
2. 以大自然作为生存典范反思人类的无能
如果说海明威以麦康伯对大自然的伪征服和伤害为代表性行为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的话,那么他在小说中更以大自然质朴的生命力量作为生存典范讽刺了现代人生命力的衰退和无能。
熟悉海明威作品的读者都知道,狮子是海明威崇拜的动物,是力量和勇气的化身。在这部小说中,狮子威仪的王者风度跃然纸上。狮子中枪后埋伏在了野草丛中,海明威再次使用内聚焦叙写了它的反抗,它“全身疼痛、难受、充满仇恨,它全身残余的体力都调动起来,完全集中着准备发动突然袭击。它能够听到那几个人在说话,便等待着,积聚全身力量做好准备,只等那些人走进野草丛,就拼命一扑。它听着他们说话……等他们一走进野草丛边缘,它就发出一声咳嗽似的咕噜,猛扑上去”[5]23。即便疼痛难忍,狮子仍然在有勇有谋、不慌不惧地面对对手。在接下来连续性的枪弹攻击中,即便后半身被打烂了,狮子也依然在往敌人的方向爬去。正是这种以命搏杀的勇气和坚韧让威克逊由衷感叹它是一头“呱呱叫”的狮子。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到与狮子形成鲜明对照的麦康伯。先是尚未谋面只是狮子的吼叫声就已经让他彻夜难眠;尔后是荷枪实弹的他手握来复枪,身边有专业猎手保护,但在狮子从野草丛扑出来的瞬间,他飞速逃跑;即便并没有眼见最后的枪杀现场,午夜时分他还“在梦中突然被那头脑袋血淋淋、站在他面前的狮子吓醒,心怦怦地乱跳”。狮子给麦康伯带来了无尽的恐惧,却也把纵然一死也无畏无惧的决绝烙进了麦康伯的心里,使他在潜意识里学会了面对对手和伤害决不妥协的精神,正是因为如此,麦康伯在第二天才忽然有了猎杀公牛的勇气,变成了威克逊眼中天不怕、地不怕的“斗士”。
坚韧的生命力量在大自然并不是狮子所独有,小说中的公牛同样也是如此。从对公牛中枪后的描写,我们不难看出海明威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赞美,而在两相对照中,也可以发现海明威对以麦康伯为代表的现代人的无能和怯懦的批判。
二、对人与人关系的思考
“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人类陷入了自然的残酷报复和人对人的残酷迫害的双重灾难。”[3]110征服、控制自然催化出来的是人处于人类社会时同样以绝对的自我中心,以自我立场物化他人,无视他人本同于自我的主体性存在,在对他人的掌控中把自我利益最大化。这种人和人之间的猎杀在小说里突出表现在麦康伯和妻子玛格丽特之间。
关于他们的婚姻,小说中非常直白地写出了本质所在,他们于对方而言一个是美色,一个是金钱,交易式的关系却也使得他们的婚姻获得了一种平衡。夫妻俩计划中的非洲之行给他们的婚姻平衡链中注入了考量对方的新元素,从而使得他们向来平稳的交换式婚姻受到了剧烈冲击,这个新元素就是与大自然野性生存相顺应的男子气概。
身处蛮荒大自然,麦康伯的财富失去了补偿其男子气概的作用,玛格丽特在两个男人原始生命力量的比照中轻视丈夫,明目张胆地钻进威尔逊的帐篷,即便被麦康伯发现也毫无愧色,甚至在麦康伯深陷被背叛的痛苦之时仍然毫不遮掩对威尔逊的喜爱,直露地说漂亮的红脸男人威尔逊“他真的非常可爱”。这个时候的玛格丽特认定了麦康伯的胆小,自信可以牢牢控制麦康伯,自信无论自己做什么或说什么,麦康伯都不敢离开她。
如果说玛格丽特利用狮子事件宣示了她在两人关系中的掌控权,那么麦康伯则是在猎杀野牛中尝试颠覆他们现有的关系定位。猎杀野牛时麦康伯没有转身逃跑,而是“兴致勃勃”“热切”“脸上闪闪发亮”地渴望着接下来的追猎。
“你变得勇敢得很,突然变得勇敢得很”,他的妻子轻蔑地说,但是她的轻蔑是没有把握的。她非常害怕一件事情。
麦康伯哈哈大笑,这是非常自然的衷心大笑。“你知道我变了,”他说。“我真的变了。”
“是不是迟了一点呢?”玛戈沉痛地说。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而现在他们俩的关系弄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人的过错。
“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迟,”麦康伯说。
玛戈默不作声,只把身子朝后靠在座位的角落里。
这段对话在简洁的表达中内含了两人应对麦康伯忽然“变勇敢”的心理变化。玛格丽特先是想以轻蔑麦康伯的方式来又一次占得上风,但明显已经底气不足。而麦康伯毫不在意的“衷心大笑”则表明玛格丽特已经完全影响不了他的情绪,此时的他对自己有独立判断、能够主宰自己的行为和立场,不再是玛格丽特任意揉捏下忍气吞声的“胆小鬼”。失去对麦康伯的控制意味着什么,玛格丽特显然非常清楚,因为美色本就会衰退,更何况还是不忠的美色,但她已别无他法,只能是“默不作声”。
麦康伯和玛格丽特在婚姻中对征服权的争夺折射的是现代人博弈化的相处状态。人和人之间疏远、淡漠,站在自我立场、从自我需要出发审视他人,把他人物化成自己某一种需求的缩影,意欲通过绝对掌控使自我需求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人和人之间的和谐荡然无存,这实际上是在上演着另一种层面的猎杀。
三、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思考
与自然的对立、与他人的疏远,个体自我在紧张尖锐中也日益分裂,失去内心的和谐与完整。“自命为中心和主宰的人既失去了自然家园,又失去了精神家园,成为无家可归者。”[3]110人的内心往往破碎不宁,充满了内在矛盾。这在海明威许多作品中均有表现,尤其是《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表露了海明威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切关注。
1. 玛格丽特
这部小说发表之后,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就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关于她最后射杀丈夫麦康伯的一枪是谋杀还是误杀,读者们各执一词。小说中对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着墨不多,但通过其外在表现却可以发现其在精神世界和人格上的矛盾性。
玛格丽特起初出现的时候有情感真诚的一面。她看到丈夫临阵逃脱、但周边人仍然佯装狮子是麦康伯猎杀的,反应是快要哭出来了、肩膀瑟瑟发抖,玛格丽特接受不了丈夫的怯懦和周边人的虚伪。她不搭理麦康伯,污辱挖苦他,对丈夫的失望显露无遗。这个时候的她在威尔逊眼里是个“顶顶好的女人”,因为她有羞耻感,也不遮掩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二十分钟后,她就显现出了非常世故理性化的一面。她笑着解释和接受了丈夫的逃跑,和威尔逊调情,甚至在晚上公然出轨威尔逊,即便麦康伯发现后毫无愧意。
在野牛事件中,玛格丽特同样显现出了两面性。在男人们热血沸腾的时候,她非常坦诚地质疑他们开车追猎动物的公平性。麦康伯陡生男子汉气概,玛格丽特在理性中仍然企图掌控局面,失败之后“沉痛”“默不做声,只把身子朝后靠在座位的角落里”。这个时候,玛格丽特的感情和理性都在受到剧烈冲击,对未来婚姻生活的迷茫加上眼前血腥捕猎现场的强烈刺激让她在麦康伯遭遇险境时向他身后开枪。这一枪与其说是冷静的谋杀,倒不如说是玛格丽特在连续刺激下的失控行为,是其自我人格精神世界崩溃的一种体现。
2. 麦康伯
小说题名为《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暗示着麦康伯在此之前长久的不幸生活。麦康伯正值当年,长相英俊,有钱有美妻,不幸从何而来呢?为了让读者得到答案,海明威在小说中让麦康伯经历了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起初,他是懦弱的。从听到狮子吼叫到与狮子相对时的转身弃逃再到午夜梦回时被狮子吓醒,表现的都是他的恐惧,害怕而无力面对,亦如他面对玛格丽特的状态。从他发现妻子不忠后二人的谈话中,读者隐约可以知道玛格丽特在十一年的婚姻中并不是第一次出轨而且毫无悔意,麦康伯痛苦愤怒却完全无计可施,对不忠的玛格丽特无法舍弃又无可奈何。把狮子事件和玛格丽特的出轨交织在一起叙述,就充分表明了自然生命力的退化、血性和男子气概的缺失是造成麦康伯“不幸生活”的根源,即便尊严反复受辱,他也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面对和捍卫。
从这个角度来看麦康伯面对公牛的变化,也就能很好地理解小说名中“短促的幸福生活”的含义了。麦康伯在猎杀公牛时出现了和狮子相同的场景,同样是受伤野兽的隐匿反攻,但这次他不害怕了,无所畏惧地搜寻、面对从灌木丛跃出的野牛不退不避,即便只是射中野牛的犄角迸出碎片和碎末,也仍然是“直挺挺地站着”不停开枪。在那一刻,麦康伯驱除了根植内心的恐惧,以他一直所缺失的“人”的姿态直面对手,在对自我生命力量的体验中实现了长久以来的精神突围。这也许正是他的“幸福”所在,敢于面对并且有所行动。只不过身后枪声响起,一切都仓促结束,但从这短暂的幸福时刻却已经充分印证了麦康伯长久以来的自我缺失。
3. 威尔逊
威尔逊在作品中是个有“硬汉”气质的人物,他参加过战争,历经枪林弹雨看淡生死,性格刚硬。但海明威并没有简单地处理成一个正面人物,而是深入展现了他在精神和观念上的复杂性。
在对待大自然上,威尔逊呈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从小说的很多描写中可以看出威尔逊对大自然的亲近,他“欣赏着这清晨的露水气味、碾碎了的蕨薇气味和在晨雾中显得黑魆魆的树干”;他熟悉狮子、野牛等动物们的生活习性,能准确预判狮子和野牛面对猎杀时的反应,并且对此是十分敬慕以至于发自内心地称赞它们“呱呱叫”。但这种崇拜却丝毫不会影响到他的冷酷猎杀,比如说他坚持不在车上开枪射杀动物,看似是在进行“平等”的生命较量,但又如玛格丽特所指责的那样,却又理所应当得开车驱赶追捕动物消耗着它们的精力以保证猎杀的成功。从中可见,威尔逊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实则是以保证自我利益为前提的,也正是基于此,他才能没有任何心理冲突地对动物们进行猎杀。
事实上,在对待人群上,威尔逊洞察人情世故而又冷漠唯我。小说中几次写到他的蓝眼睛是“神情极冷淡的”“机枪手是没有表情的”,威尔逊敏锐体察了人性人情,却不会被此掀起一丝波澜。所以,玛格丽特投怀送抱,他能坦然接受;即便麦康伯愤怒不已,他也没有丝毫愧疚;在麦康伯被玛格丽特枪杀之后,他也还是不惊不讶。
从以上可知,威尔逊在小说中并不是海明威理想人格的化身,他体现出来的是现代人的纯粹自我化状态,以自我立场为中心面对大自然和人群。威尔逊与玛格丽特、麦康伯虽然个性不同,但却又和这两个人物一起,共同展现出了现代人自我精神生态的失衡与和谐人格的缺失。
四、结语
小说结局往往是作家观念的集中体现。即便海明威在小说叙述中并没有明确玛格丽特是否有意谋杀,但麦康伯的死却已充分表明了人类重新拥有生命勇气和力量的失败,海明威似乎以此中断了人类重新获得自我,复归自然的努力。这样一来,整部小说也就在“死亡”中强化了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类精神生态的多重思考,而最后悲剧性的结局也更加促人深思该如何实现人在自然与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生存。
综上所述,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虽然篇幅短小,但却体现出了多层次的丰富的生态主义思想内涵。作品以对人和大自然的关系进行的思考为显,内在隐含了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人自身内心世界的深层挖掘。在简约叙事中彰显丰富意义空间是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正是海明威创作形成其独特艺术个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