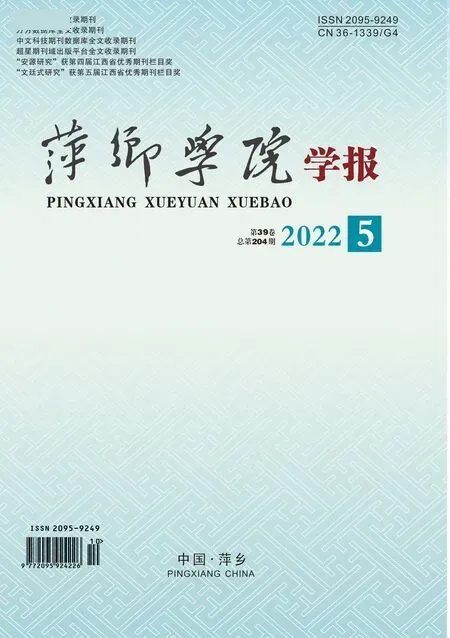试论丁伯刚小说的苦难书写
朱淑芳,易志文
(萍乡学院,江西 萍乡 337000)
丁伯刚,江西省60后作家,现任九江市作协副主席,江西省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自1989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天杀》开始,丁伯刚一直笔耕不辍。迄今为止,丁伯刚总共发表了二十多部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斜岭路三号》以及一本散文集《内心的命令》。纵观丁伯刚的小说,不难发现苦难是其小说叙事的鲜明特征。
一、丁伯刚苦难书写的具体呈现
苦难是文学中永不过时的重要母题之一。纵观丁伯刚所有的小说,不难发现苦难是其小说叙事的鲜明特征。其小说苦难书写的具体呈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生存的艰辛,二是精神的困境,三是情感的异变。人存活于世,首先要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可是他作品中很多人物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异常艰难,身世的凄惨、生理的折磨以及他人的摧残毫不留情地压迫着他们。而那些原本就受生存重压的人再加上陷入精神上的困境,他们的人生显得更加悲凉。精神上的困境不仅能啃噬人的内心世界,还会从内在引起外在的莫名疼痛。精神方面带给人的创伤往往更加难以承受和愈合。更为不幸的是,本就受到生存与精神方面双重打击的芸芸众生,又因为人与人之间异化了的情感而再次受到创伤。
(一)生存的艰辛
底层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丁伯刚着力书写的对象。底层人群往往经济上贫瘠、地位上低下,基本的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当人们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才能更好地追求高层次的需要。然而,丁伯刚作品中很多人物连最基本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
1. 身世的凄惨
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出身底层,他们有的幼时丧父,唯有与寡母相依为命;有的自小便无父无母,只能四处漂泊。稍微占些篇幅的人物出场一段时间之后,作者大多会适时插入一段对人物身世过往的交代。不幸的身世带给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作家也不会刻意插叙交代。
作品中存在不少孤儿寡母式的形象,主人公往往早年丧父,只能与寡母相依为命。《来客》中的大头出生便丧父,与母亲艰苦度日。小说《酒》中,阳鸡婆与其寡母亦如此。
如果说,孤儿寡母式的形象已经让人倍感同情,那么孤儿形象也许更加惹人哀怜。不管是《唱安魂》中的天峰还是《艾朋,回家》中的姐弟,虽然他们的生母并未离世,但是都无情地抛弃了他们,这不就相当于是完完全全的孤儿吗?也许,被生母摒弃所带来的痛苦比从一开始生母就辞世所带来的痛苦更为强烈。当然,小说中也的确不乏那些幼时双亲便不幸离世的孤儿,如《夜行船》中的家婆。
2. 生理的折磨
生理上的折磨一是体现在人们赖以生存的吃穿住行得不到必要的满足。《天河谣》中,玉民从小吃不饱、穿不暖。《城市与狗》中,王老子白天捡破烂,晚上住在自己搭的简陋窝棚。
生理上的折磨二是体现在人们受病痛的侵袭。这种病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的可探寻的疾病,这一类送到医院基本上会有明确的诊断结果。如《失窃》中患心脏病的王建设。另一类则是由心理引发的生理上的极度不适,如莫名其妙的头晕。此类疾病在医生检查之后往往显示无碍,但患者又确实感到莫名的不适,这种不适严重时造成的伤害绝不亚于前者,如《艾朋,回家》中连续不断地“主动生病”的艾朋。
3. 他人的摧残
《禁闭》通过展现三个罪恶灵魂在一间屋子里相互猜忌、相互伤害的斗争,提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观点。人的苦难除了源自本我之外,还会有来自他人的摧残。作品中的人物所受到的“他人的伤害”中的“他人”大多是以“本地人”的身份出现。作为“外来人”的主人公常受“本地人”的欺压。
《两亩地》中的吴建在当地地痞流氓的威胁下,一次又一次地被敲诈勒索。《有人将归》中,孙宇立一家在异地备受欺凌。
(二)精神的困境
评论家施军曾说:“失去了苦难的精神性含义,也就相应失去了幸福的精神性内涵。”人所受到的来自精神上的伤害,相比于那些外在的创伤,更能彻底地击溃人。小说中精神的困境主要体现在虚弱心理、永恒孤独以及命运恐惧。
1. 怯懦多疑的虚弱心理
丁伯刚笔下的人物,很大一部分都有怯懦多疑的虚弱心理。陈莉在《此心安处是吾乡》中指出,丁伯刚小说中的人物总是患有“虚弱症”,患“虚弱症”的人完全没有自我,完全被外界所牵引[1]。哪怕是生活中的一点小事都能引起主人公心境的巨大变化,他们自我的那一面在面对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显得极其单薄、脆弱。正因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他们比常人更能感受到不安与痛苦。可是这些并没有引起他们行为上的反抗,他们往往如入深渊、困于其中、难以自救。评论家张定浩在《文学与重复》中指出,丁伯刚作品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在重复着某种痛苦的行为,这种重复起初是不自觉的,慢慢地可能会转变为有意识的重复[2]。小说中人物痛苦行为的重复与他们的虚弱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所带来的胆怯、懦弱和多疑,致使他们连反抗的尝试都鲜有,只会一次又一次被动地接受重复的痛苦。为了将人物复杂的心理充分揭露,行文中常有大段的心理描写。丁伯刚对人物复杂心理的描写似乎某种程度上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所采用的“对白形式”和“复调手法”。
《轻声说》中的杨江河,因公开课的失败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充分暴露了其生性怯懦、敏感多疑的虚弱心理。公开课后,被虚弱心理支配的杨江河变得既不会上课,又不会管理学生。听闻学生要带人来报复后,他整个人恍若失控。此事最终虽了,但是杨江河已经陷入了痛苦的重复之中。
2. 生死皆存的永恒孤独
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人存在于世必然面临孤独,尤其是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强化,个体与其他生命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彻底跨越的鸿沟。小说中的人物不只是畏惧在世时的孤独,他们同样也害怕死后的孤独。他们总是力图挣脱孤独的漩涡,却“终食败果”。丁伯刚虚构的小说中似乎存在一个“鬼魂世界”。个体生命的终结并没有让人从孤独中解脱,孤独同样被带入死后的“鬼魂世界”。对死后孤独的叙述,是丁伯刚苦难书写的独特之处。
《唱安魂》中,正值壮年的天峰因一座孤坟引起了对死后孤独的畏惧,吓得像个失魂者。天峰的养父母同样如此。养父母在世时,极度害怕天峰离开。双方断绝关系后,年老的养父母势必要恢复养子关系,因为他们害怕孤独终老,死后无人祭拜变成野鬼。
《何物入怀》中的姨婆无儿无女,为了摆脱孤单,她不辞路远日日去汪成家。当一伙人为已故姨婆做道场时,许多老人都羡慕她死后如此热闹。由此可见,对死后孤独的畏惧,同样存在于这众多围观者身上。
3. 面对命运的强烈恐惧
丁伯刚的创作带有一定的宿命思想和迷信色彩,这是一定社会状况下落后观念的遗留反映,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作品中一步一步地陷入不幸命运中的生命个体。作品中不管是农民还是接受过先进教育的底层知识分子,都对命运充满了恐惧。
《唱安魂》中的天峰联想到近期一系列事情的出错,愈发觉得自己的一生将真如面相大师所言:孤寒。《抢劫》中的兴建经历一系列变故后,更加笃定命运的无法抗拒。
汽轮机排出的乏汽以直接空冷系统为主要冷却方式,在此基础上配置改进型海勒式间接空冷系统,从主排汽管道抽取部分乏汽送入DICSSAC,如图1所示。DICSSAC作为辅助降低背压的一种优化措施,可提高机组真空度,使机组安全、经济运行。蓄冷是指夜间低温时段,干式空冷换热器分出一半冷却单元用来冷却凝结蓄冷水箱里的循环冷却水。在第二天高温时段,蓄冷水箱里的低温循环冷却水与流出干式冷却塔的较高温度循环水按一定比例混合,喷入喷射式凝汽器,进一步降低背压[7]。
尽管命运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仍然要坚信,人在命运面前绝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可以发挥作为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去和不幸的命运抗争,从而改变自身的现状。
(三)情感的异变
丁伯刚的作品中无论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还是爱情和友情,都不再美好。它们如同发生异化一般,完全丧失了真善美的那一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非但没有成为安抚人心的“良药”,反倒转变成了苦难的“催化剂”。
1. 千疮百孔的亲情
亲情往往被认为是人世间情感当中最纯朴、最坚固的。在作者的小说世界里,亲情变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早已丧失了它的温暖与牢固。
陈莉在《此心安处是吾乡》中认为,《天问》所写的就是一场父子之间的战争。父亲想在学校多住几天以便积攒吹嘘的谈资,儿子则因为强烈的自尊心想尽早送走粗俗的父亲。二人由此产生冲突。父亲装病报复儿子,让儿子受到众人谴责;儿子则在父亲迷糊时,试图掐死父亲。父亲回家不久便传来消息:无疾而终。小说的篇名叫《天问》,发出的便是对父亲身死于何故的疑问。这看似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其实作者已经给出了答案。父亲自小历经艰难险阻,然而最终却因与儿子之间千疮百孔的亲情寒心而死。
变异的亲情不只是体现在父母与儿女之间,在其他的亲属之间亦如此。《天杀》中的姐妹小洪、妹伢二人与《斜岭路三号》中的月季、小月二人有着相似地扭曲了的姐妹亲情。两对姐妹各自都为争夺一个男人而相互算计、相互伤害。
2. 畸形扭曲的爱情
丁伯刚笔下的爱情,男女双方的地位往往不对等,双方的结合只是为了各取所需。一旦这段爱情对其中某一方没有可利用之处,这段爱情不久便会破裂。这种畸形扭曲、缺乏真情实意的爱情注定得不到“善终”。
《何物入怀》中,兰兰与汪成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善果”,因为他们的爱情既是不平等的,又是相互猜疑、相互算计的。迫于吴家施压,汪成与兰兰成婚。婚后,二人嫌隙不断。小说结尾,作者举重若轻地写到兰兰身心俱损,二人分居。
《天杀》中的郑芜之并不爱女友小洪,只是为了满足“本我”的欲望和之纠缠。后来,郑芜之还将他的“魔爪”伸向了小洪的妹妹妹伢。郑芜之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姐妹二人是为了寻求依靠。这段扭曲的爱情给三个人都带来了不幸:郑芜之彻底堕落,姐妹二人则受尽蹂躏。类似的情形亦发生在《斜岭路三号》中。
爱情当中,倘若有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甚至成了另一方的累赘,那么这段爱情立马就会破裂。小说中的爱情如玻璃一般极易破碎,归根结底在于它从初始就是畸形的、异化的。《失窃》中的杨青秀得知丈夫患病后,立马改嫁。
3. 脆弱多变的友情
友情同样蒙上了苦难的面纱。丁伯刚笔下的友谊,往往是脆弱多变的。也许相识数载的老友,突然就变成了明争暗斗的敌人。哪怕双方表面上以友相称,但实际上都暗自算计着、怨恨着。曾是密友的他们变成敌人之后比陌生人更加懂得如何伤害对方。
《有人将归》中的孙宇立和北林相识数年。北林帮助孙宇立从工厂调动到自己所在的机关,然而孙宇立却伺机顶替了北林的职位。歌珊之行中,二人心中都暗暗地嘲笑、蔑视对方。在《水上的名字》中,郁夫与高海林相识数载,甚至称得上知己。可是生病的郁夫却对为自己提供帮助的高海林满怀妒忌,他嫉妒高海林可以自由行动。高海林面对郁夫充满恨意的目光感到如芒刺背,同时,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也恨着郁夫。
二、丁伯刚苦难书写的缘由
自1989年丁伯刚第一部小说《天杀》的发表,再到近年的新作,“苦难书写”一直贯穿丁伯刚长达几十年的创作。究竟是何缘故让丁伯刚如此热衷于书写苦难呢?
(一)自身的人生经验
自身的人生经验是作者苦难书写的丰富来源。丁伯刚本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阅读体验与其热衷于书写苦难的创作倾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丁伯刚本人的成长经历是曲折多艰,从小到大的经历成为他写作题材的重要来源。少年的他生过几次大病。先是得了肺结核,其后又发生尿血,再是长疮疖。这三次重大疾病都让他陷入痛苦之中,使他深刻地体会到生命难以承受之重。这些经历就像伤疤永久地镌刻在丁伯刚心尖,影响着他的创作。他曾言:“毕业后出来工作,又是极度的生活重担……等到个人事业刚有点转机,便又是疾病和因身体的病残而来的对整个一生的绝望。”[3]从这些自白中,我们可以发现贫穷和疾病给作者带来的不只是肉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打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时常受到贫病的折磨,陀氏自身痛苦的经历在其作品中同样有迹可循。丁伯刚和陀氏从这一点上来说是有着相似之处的。丁伯刚小说中不少人物同样受着疾病和贫穷的双重压迫,例如《宝莲这盏灯》中的陈宝莲、《水上的名字》中的郁夫。作品中对这些人物生平的布局,有着丁伯刚自身成长经历的影子。
丁伯刚的生活环境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小城镇,居住于小城小镇的农民和底层知识分子的艰苦生活是其小说的重要素材来源。同时,遗留于乡村、城镇的落后观念带给人的创伤也被丁伯刚纳入笔端。长年往返于乡村和小城镇的丁伯刚以一种平视的态度将生活于此的底层人物作为自己着力刻画的对象。他自身就在小城小镇生活过,对底层人物的日常艰辛有着细致入微的体验,因而能够更好地勾勒出一批真实的农民和底层知识分子形象。《来客》中的大头不曾上过学,自小在村中干活谋生。《水上的名字》以农村出身的底层知识分子郁夫为叙述对象。在乡村、城镇的生活,不仅促使外在可见的“显性日常苦事”成为作者创作的素材来源,同时渗透在小城小镇中的“隐性落后观念”也成为作者的叙述切入点。如《唱安魂》中提到孤坟中的鬼会变成野鬼、会遭受欺侮。
丰富的阅读体验进一步充沛了丁伯刚的苦难创作。丁伯刚鲜与生活的热闹场亲近,经常独自一人看书。他对九江的各个书店都非常熟悉,就好像是他开的店。丁他爱读陀氏的著作。陀氏的作品大多描写底层人物的悲苦,丁伯刚的作品中也主要是以底层人物为叙述对象,作家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陀氏作品的影响。丁伯刚看了好几年的心理小说,对心理小说的广泛涉猎,促使其在叙述人物内在心理的困苦时格外娴熟。此外,作者还阅读过许多关于宗教类的书籍,宗教当中有关苦难的解说不在少数。广泛地阅读各类书籍,不仅增加了丁伯刚的文化知识,更是丰富了思想、发展了思维,使得作家在创作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所读书籍的影响。
(二)漂泊的异乡经历
丁伯刚是一个异乡人,早年的迁徙经历影响了他的创作。作家1961年出生于江西九江,1964年,母亲带他回到安徽老家生活了十多年。1977年他随父母再次迁到江西定居后,便再没回过老家。弗洛伊德曾提出的“早年记忆”对作家产生深刻影响。童庆炳在《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中提出“童年经验是指从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体验……一个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创作中不断地吸收他的童年经验的永不枯竭的资源。”[4]丁伯刚早年往返于江西和安徽的经历,是他创作的“不竭资源”。漂泊的异乡经历促使丁伯刚在创作时不由自主地更加关注异乡人身上特有的苦难。作家自身的异乡无根之感常被投射到作品中的异乡人身上。
江腊生在《异乡的焦虑与坚定的书写》中提到,丁伯刚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似乎都不“在家”,而是在“异乡”艰难前行。丁伯刚说自己整个人基本上已给劈成了两半:一半在老家,另一半在异乡;一半是灵,一半是肉。每天都在挣扎,每天都在撕裂,每天都在用这一半去寻找另一半[5]。从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丁伯刚的异乡经历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的出场地点都是在一个叫“歌珊”的地方。“歌珊”在希伯来语中有着“边疆”的意思,在圣经中歌珊还是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长达数百年的一个地方。由此可见,“歌珊”一词本身就隐含了异乡漂泊的意味。
(三)独特的个性心理
丁伯刚在创作中偏于书写苦难与其独特的个性心理有着紧密的关联。张佐邦认为“作家的个性心理包括作家的个性气质和生命意识。所谓个性气质,主要是指作家的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特点在行为方式上的表现,它是作家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所谓生命意识,在此特指一个作家看待人生独特的眼光,衡量世事的心理尺度,以及明确的政治信仰,人生信念等等。”[6]丁伯刚个性心理的形成,既有来自先天的遗传,也有来自后天的塑造。从荣格的“心理类型说”理论来看,丁伯刚属于“内倾型”气质,其特征为孤僻内向,极为敏感,喜欢安静,从内心思索,用自己的感受去理解事物[7]。与他相识多年的蔡勋直言:“老丁是过度敏感的人,生活中许多事务,于他而言无异于一种粗暴的干涉和侵犯,让他烦不胜烦。”丁伯刚曾发表过一本随笔集《内心的命令》,单从书名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丁伯刚有一种倾向于从内心思考的的气质特征。总的来说,丁伯刚的个性心理是以敏感、忧郁、悲观、易焦虑、喜深思为主要特征。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带有个人的特征,丁伯刚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奋进,忠实于自身的体验,坚持不懈地甚至有点固执地继续着自己个性化的创作。丁伯刚独特的个性心理促使其偏向于并且擅长于叙述社会生活的苦难。他凭着自身对社会生活特有的敏感,将苦难描写得更为直接、形象、深刻。敏感忧郁的气质,让他对人世间的苦难有着更加细腻的观察力和更为深沉的情感体验。在《宝莲这盏灯》、《马小康》、《酒》等多部作品中对贫苦生活状态进行了细致描写。他毫无掩饰地披露“受难者”永无宁日的内心世界,那些受难者的内心纠葛一定程度上也是丁伯刚自身生活体验的反映。作品中有一些人物甚至带有作家的某些个性特征,这是作家在创作时不由自主地带入进去的,如《水上的名字》中多愁善感的郁夫。由此来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丁伯刚独特的个性心理一定程度上铸就了他的苦难创作。
(四)悲悯的创作观念
丁伯刚悲悯的创作观念促使其对苦难主题有着密切的关注。他曾说:“实际上我写作是有一个总主题的,这就是写人的无救与无助,及对拯救的向往与吁求。出于这样一种创作观念,丁伯刚常常将人物置于无助与挣扎之中。作者将人类看作是被放逐的一群,极力地书写着人在现实中的渺小与无力。他通过作品展现人类所面临的各种苦难,以期借此警醒人们要去思考如何获得解救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作为一个著述者,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文化信念、精神信念,要有一个完整而充盈、能与整个外在世界相抗衡的内心世界。丁伯刚“写人的无助及对拯救的向往”的创作观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因而其小说中的人物大多处于一种如深陷泥潭般难以解脱的状态。
在展现人的无助时,丁伯刚偏向于写人在精神和心灵方面的挣扎,对心灵上以及精神上的描写甚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大段关于心理、精神方面的描写,生动地刻画了人物内心跌宕起伏的心理变化历程,揭示了人物精神上的无助。《天杀》的主人公一方面为自己的卑劣无耻感到自责,另一方面又反复坠入罪恶的深渊之中难以自拔。这种心灵的激烈抗争透过文字跃然纸上,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人物内心的煎熬。
三、丁伯刚苦难书写的意义与局限
丁伯刚小说的苦难书写既是个人情感的宣泄,又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更是对人类灵魂的追问。
(一)意义
周保欣曾言:“文学中的苦难,首先折射出的是作家自我内心的困难和危机。”丁伯刚经受过背井离乡、屡次患病、经济贫乏和写作受阻等多重困难,这些遭遇给作者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丁伯刚将这些经历赋予其笔下的人物身上,通过写作释放、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伤痛。《天河谣》和《夜行船》是两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该小说暗含了作家自己对当初不得不迁徙的无奈以及再未回过老家的复杂情结。对作品中人物迁居经历的构写,在一定程度上是丁伯刚多年背井离乡的内心苦闷之情的抒发。疾病的描写在丁伯刚作品中比比皆是。对疾病的反复书写也是作家受病痛折磨过的心灵的折射。小说的主人公大部分出身底层,经常被生活的重担所压迫。由此可见,丁伯刚在叙述受苦难压迫的人物的同时,也将自己内心的苦闷宣泄了出来。
丁伯刚曾说:“……自喜欢上小说以后,可以说一心一意弄了一辈子……现在基本上把自己写成一个白发老翁了,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没有丝毫后悔的意思。”丁伯刚是一个真正热爱读书写作的人,他的创作并不掺杂任何物质利益的成分。吴洪森曾说 :“丁伯刚热爱文学写作的心情非常纯净,功名利禄的世俗影响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于他而言,写作是一生的理想追求。丁伯刚认为宗教的最大意义在于吁求或祈求,他曾言:“我在内心甚至还有一从未跟人说过的狂妄的想法,就是以自己的写作来重述宗教的基本主题。”带有知识分子责任感和悲悯情怀的丁伯刚在写作上更为具体的追求是通过写作唤起人们对拯救的向往。丁伯刚的创作是遵从内心的,他致力于通过书写苦难来展现人的无救与无助以传达一定的精神文化理念,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丁伯刚用冷峻的文字无情地将人的苦难生存状态赤裸裸地展现出来。其作品读起来令人感到格外沉重,这样一种冷酷的笔调也许有些残忍,但是作家绝不是为了宣扬苦难才如此着笔。他将人类的某一方面的生存状态用自己的文字尽可能地呈现出来,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去坦然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的存在。作者书写苦难的目的是给人警醒、予人反思,从而引起人们对苦难生存状态的关注。只有在更明确地洞悉人生真相的基础上,人们才更加懂得要加强对自身生存困境的关注与重视。作者在洞察人类灵魂深处的探索过程中,对命运、死亡、人生意义等重要问题的思索借助作品中的受难者诉诸出来。丁伯刚对人类根源性难题的不懈探索精神,值得我们景仰。
(二)局限
毋庸置疑,丁伯刚小说的苦难书写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也难免存在局限性。首先,叙述基调过于压抑、低沉,缺乏温情,作家甚至有意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弱化。在丁伯刚构造的小说世界里,几乎没有温情可寻,人性的闪光点似乎也被刻意地隐藏起来。其次,缺乏艺术技巧的运用。小说中人物的成长经历,基本上是用几段文字平铺直叙,读来有些生硬乏味。最后,丁伯刚揭露了人类的苦难生存状态,但是没有为人类如何从苦难中得到救赎提供策略。有的作家将苦难的消解寄托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关怀;有的作家寄之于理想的乌托邦;有的作家直接主张与苦难相抗争。作家在揭开残酷现实的同时,也应当尽可能地提供一份超越苦难的策略。
四、结语
歌德曾说:“母题是一种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丁伯刚对苦难主题的书写放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其作品对苦难的叙述是多样的,小说中反映的绝大多数都是他所见闻过的极为真实的人间苦难。丁伯刚将自己对人世间苦难的独特领会诉诸笔端,因而其对苦难书写的具体呈现并不流于泛化、模式化,而是明显带有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