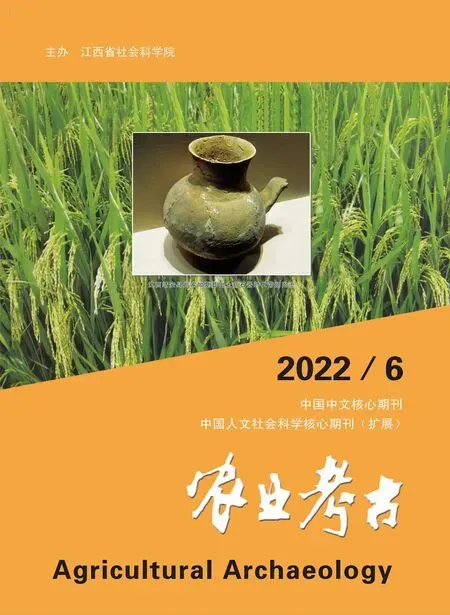整体呈现中国古代村落的形态与文化
——马新《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评述
王日根
中国史作为一门学科,经历过“流水账簿”“帝王家谱”“民众史”“政治史”“心态史”等主流话语的不断转换,有关村落研究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有的为数不多的村落研究长期以来更多出现在建筑学、人类学或社会学中,是历史学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部分①。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新教授积数年之功独立完成《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两部巨著,分别由商务印书馆2020、2021年出版,聚焦于体现中国文明底色的村落,从上古一直延续到明清,整体、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国村落形态与村落文化的发展史,将考古发现、传世文献相互结合,将各个时代串联起来,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一、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的全景呈现
马新深刻认识到美国民族学学者塞维斯的酋邦理论、经济史学者施坚雅的区域市场体系说、法制史学者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以及日本学者的有关理论,虽然已经形成了有关中国乡村的各种范式,但多多少少都有隔靴搔痒之感,体现不出中国村落的历史性、村落演化的阶段性以及村落与城市间的区别与联系,有的仅仅是区域范围的考察,难以全局性地阐明中国古代村落发展的一般轨迹。马新欲开辟的新路是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从中国古代村落发生与发展的独特道路出发,建立起中国式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古代村落发展史研究的基本范式。
马新认为:中国古代村落经历了从聚落到村落与城市即普通聚落与中心聚落的演变,村落从早期到中古,再到近代不断嬗变,宗法色彩、地缘观念、赋役基本单位观念成为基本的底色,村落形成之后具有鲜明的延续性,延续数百年直至上千年的村落已经考古挖掘得到证实。村落的自然属性来自宗法血缘,村落的行政属性则来自赋役的承担和作为编户齐民所拥有的各种权利。这种两合性成为其历久而弥新的内在动力,无论是乡里制、乡村制,还是都保、里甲乃至保甲,村落都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村落的形成与农耕文化密切相关,依凭村落,农耕文化延续至今,其水井、广场、道路、庙宇乃至村墙将村落凝聚起来,其邻里守望的精神内涵传承不竭。祭祀娱乐为举村共同事务,集体精神与合作意识从不缺乏,因此,“村落始终是城乡一体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始终是城市之外的基本聚落单位,始终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始终是宗法血缘组织赖以依存的躯壳,始终是农耕文化基因得以绵延的媒介,始终是离开村落的人们的精神家园。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则必须以乡村振兴为基础,必须是城乡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1](P444-445)。马新将中国古代村落研究从既往的局部与个案研究推进到断代直至纵向的系统研究,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且能从村落社会结构出发,总结出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这条路径不应是西方城市化的模式,而应该是中国式城乡融合、共同繁荣的路径,这种对自我发展道路的觉醒,无疑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马新中国古代村落社会结构研究的现实意义亦由此昭示出来。
马新研究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的演变,细致考察了原始聚落向村落的递进、商周村落组织及其功能、战国秦汉村落乡里建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村落的重构与差异、隋唐五代时期村落形态的发展,直至宋元明清乡政建设和村落地位的稳定确立,使中国古代村落形态描画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揭示了其中的历史阶段性和地域差异性。马新认为,原始的村落处于稳定状态,地域固定,延续成长,逐渐分化为城邑与村落,形成“城乡二元结构”,且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之中,人口流动、人口聚散规模时小时大,但村落逐渐成为可以依赖的基本税收单位。马新从考古资料中梳理出延续数千年的村落,可见村落的稳定性与延续色彩。马新还特别提到唐代以来乡村中就出现了草市,宋元明清则进一步发展成为镇市与市镇,这是与自古中国就广土众民、地域差异明显,彼此互补性强密切关联。马新指出:镇市与市镇并非只是字词的组合不同,而是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市与镇的沿革状态。镇市是宋代常用的概念,突出的是镇的地位与意义;市镇是明清时代常用的概念,突出的是市的地位和意义[1](P444-445)。这样的概括是特别精到的。最初镇的军事性色彩较重,北宋官方将镇作为一级行政设置,置于县之下,镇上设置文武官员,负责地方治安、经济和社会事务。镇的经济功能体现在征税方面,所征税收高于行政开支,推动着镇制的进一步发展。到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发达、贸易的促进等是市镇勃兴的重要途径。如果说宋元时期镇市有较明晰的行政定位,那么明清市镇则有更多自由空间,一些较发达地区则设置巡检司或派驻官员,加以治理。这些市镇总体上实施的仍是乡村管理方式,尽管它们可能发展成州县政治中心之外的次级区域中心,但时常会在近代以来的商品经济与城市化浪潮中走向沉沦[1](P459)。
除了关注中国古代村落的社会组织形态,马新还聚焦于村落中的住宅与坟茔,即阳宅和阴宅,聚焦于村落中的庙宇、宗祠与戏台这类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和一致性观念的公共场所形态,聚焦于村落中的水井、池塘、道路、村墙和村学等公共空间,尤其是村落中的墟市、作坊与店肆更是带动村民认识外部世界、联络外部世界的重要纽带。村落或可区分为集村和散村,规模的差异经常表现得特别地悬绝,大到上万人的村落,小到三五户的村落,小村落时常也会走向村落的集合。
由此,我们或许还应该更深入地认识村落中村民的固着性与流动性,关注本村人的流出与村外人的流入,关注村民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纵向看这一过程,能观察到王朝统治者的思想倾向、政策影响力和商业活动、物资交换、利益追逐等对村落产生的分化与更新作用。马新已经将市场化作为村落研究的一个重要指标,事实上村落会因为所处位置分化出中心村落和普通村落,也就意味着一些村落逐渐跻身于城镇的行列;一些村落则长期默默无闻,有的一直处于行政控制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地带,有的则出现空壳化或被废圮现象。
马新从历史时期不同阶段村落的演进中看到了王朝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变动,作者指出:宋元明清时期的乡村社会继续着自两税法所发轫的变化:一方面,税赋制度不断地由税人向税地转变,通过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基本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由赋税制度变动而引发的乡村人口流动愈演愈烈,旧有体制难以有效地控制与管理乡村。因而,这一历史时期的乡村组织与村落制度一直处于调整与变动之中。至清代中期,大致稳定为以保甲制为基础的乡村组织体系。[1](P341)村落社会的变动一直不断地进行着,人口规模、职业流向等时常或显或隐地呈现出时代的差异性。学界留意过村落的行政建制与自然建制之间的差异,如保长与村长,村长与族长之间是什么关系,刘铮云提供了保长即村长的证 据[2](P377),孙 海 泉 对 获 鹿 县 清 代 档 案 的 研 究 则显示行政村往往是若干自然村的组合[3]。马新总结说:“就清代中期以后乡村设置情况看,王朝统一规定的只是保、甲、牌三级制度,并未明确乡、村两级的建置。因而,虽然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乡政的恢复现象,但从名称到内容都无一定之规;而且,县级行政之下,也不全是完整的乡村之制,有以县统村者,还有县下设里、里下设保、保下设村者;但多数情况下应当是乡、村两级建置。”[1](P444)由此,我们又能辨析出中国乡村之制明显的地域差异。
学界研究往往强调一些地区的重要性,极端描述由村落蜕变为城镇的案例,却较少关注不那么重要的长期处于王朝视野治理视野之外的村落,描述这些惯常的村落是马新的强项,她能在沉静中把握到历史深处的脉流。
二、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的深度挖掘
站在中国立场观照中国古代村落文化,或许不能仅将村落文化看作是官方文化的乡村版,也不单是精英文化的映照,中国古代村落自有自己文化生成与衍化的轨迹。王朝统治者在文化树立方面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宗族与宗法长期成为村落的凝聚纽带,在秩序协调、亲情凝聚、文化向心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族规家训多为族人子弟树规立制,确定名分,建立等级秩序,这些规制或多与国法相配合,约束着村落居民。不过王朝官方的教化与村民固有的“野性”之争长期存在,二者时常并存,形成二元文化景观,特别是被官方定义的所谓“淫祀”,往往是禁而不绝,且不断层生,有的还由“淫祀”转化为“正祀”。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由此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图景。
村落生活的生动性一方面体现在天然率性的文化活动方面,这些文化活动往往与祭祀活动相结合,与生产活动相结合,秧歌、田歌、山歌形式多样,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另一方面体现在村落频繁的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方面,凡修路、架桥、凿井、建舍等往往是倾村而出,协力完成。农忙季节相互间的互助、换工普遍存在且延续不绝,成为集体观念和意识形成的重要表征。
马新认为,村落居民之间充满了浓厚的乡邻之情,邻里守望既是村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进而上升为一种伦理法则,内化为村民的价值取向,规范和引导着村民的生活,绝非一盘散沙可以一言以蔽之的。马新指出:“中国古代村落自产生起,便有着较强的共同体特征,在长期传承发展中,村落中的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一直较为丰富,既有祭社、祭神、驱傩、求雨、腊祭等祭祀活动,又有修路、架桥、凿井、建房等公共事务,还有春节、上元、清明、端午、中秋等各种各样的节庆娱乐。对于村落的公共活动与公共事务,村民往往普遍参与。”[4](序言,P6)井田制度虽然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但井田观念却一直主导着村落民众的思维,“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P358-359)
中国古代村落文化还存在于人生礼仪中、节日习俗里和教育传统上。人们在冠婚丧葬中因现实条件和环境不同,各地各阶层存在着差异性与变通性,人们在节日习俗中利用地方特产,或奉献给祖先和神灵,或集体聚饮,载歌载舞,人们重视子弟教育,后来逐渐走上应科举之途,呼应着王朝的正统文化,不过,正统文化往往官方化、精英化,越来越远离村落本源,村落文化则更多地保留着原始基因,以一定的张力与正统文化保持着某种距离,村落文化更加活泼,更加朴素,正统文化则更多一本正经,更多刻板。显然,我们也不应忽视村落文化时常成为官方文化的源泉,双方势必相互影响,彼此互摄,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熟人文化品格,农耕文化特征。马新认为:中国传统市民文化是正统文化、村落文化和工商文化的混合体,不具有独立、稳定的文化品性,而表现为很强的依附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马新认为,中国古代村落文化是一种具有完整内涵和鲜明特征的主体文化,而中国传统市民文化则一直未形成独立、稳定的文化形态,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和不确定性。其根源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市民群体形成较晚,且一直未形成完整的市民阶层,缺少自身的价值归宿与文化自觉,处于正统文化与村落文化的制约与浸润中。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文化,又是源远流长的主体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她具有强大的吸纳与消解能力,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历数千年而不失其本。佛教及其他各种宗教都在村落文化中被吸收和改造而实现了中国化[4](序言,P6)。
马新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长期延存的原始文化基因的论述是颇具独见的,原始信仰、神话传说、原始艺术、婚丧习俗、节庆娱乐等都保存着若干未被正统文化驯化的由远古而传承的文化内容,这些“野性”基因催生出中国古代村落民间歌谣、游神赛会、民俗民风中诸多充满活力的文化迸发,使自古及今的村落居民保持着一定的文化品位和雅化色彩[4](P354)。
以往学界较多地强调村落民众的愚昧落后,却少看到村落百姓的家国情怀、进取之心与明显的凝聚力,这些均为片面地借用西方主流话语有关,无视了中国古代村落中的活力、生机与文化精神[2](P440)。马新从对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看到了中国村落民众的慷慨好客、宽大大度、友善仁爱[2](P505-506)。
马新总结中国农民的特性,概括了三点,即平民性,半分散性、半自足性,中国古代农民忠君报国、依赖与认同官府,是王朝政治统治延续的坚强根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多抱有改变社会地位的政治进取心,改善经济地位的致富追求,他们在集体劳动中培养起集体精神,形成互助结社的文化传统,涵养出邻里守望的大爱情怀,他们忧别人之忧,福别人之福,深怀道心、慈悲心和博爱心,热情好客,让外人如沐春风。这些弥漫在村落之中的温馨之气或许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乡愁”,虽朴实无华,却温暖你我。
三、村落是中华文明生成和滋长的沃壤
我们常说中国人的根在乡村,具体说也就是在村落,那里能带给人们安逸感,每一个游子都将村落视作母亲缝制的襁褓,能给人以归属心;那里也能带给人们荣誉感,俗语常说“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光宗耀祖是中国人人生价值实现的终极追求,村落中的人们会将游子们的成就镌刻在村人的记忆中、谱牒里乃至村碑上,衍化为村落精神和信仰图腾,激励后生晚辈。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毁灭掉那里有生命的村落,而应该将其振兴起来,使其变得越来越美。
以往人们多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可在中国,村落则成为略高于家庭、家族的社会细胞,有的家族数百年固着于一个村庄,用家族的辉煌书写着村庄的历史,有的家族迁入一个新的村庄,与固有的家族协力开发,实现村庄的跃升。不同家族间有时会产生利益冲突,村庄上的矛盾也可能世代累积,形成相互争斗不已的局面,不过,建基于村庄基础上的乡镇、州县官员往往以灌输儒家和谐伦理为自己的职志,移风易俗乃至训民型俗,逐渐实现着村庄的良风美俗化。无数的族谱、家训、行状、墓志铭乃至碑刻都书写着古已流传的美德懿行、勤劳励志、百折不挠、奋发进取的生动故事,形成延续不断的模范画廊。村落的地理位置或千百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人口的生生不息、兴衰起落、出出入入却上演着一幕幕生动活泼的华章。
因此,我们说村落是中华文明生成和滋长的沃壤是允当的,无数中国人经乡村苦读,科举及第,走向宦途,将中华文明成果惠泽到其所任职的地方,待到年老致仕,他们往往又回到故土村落,成为乡绅阶层,投身私塾、家学,滋养着后学,源源不断走向外部大世界,这一传统的返回村落模式于今虽然失去了延续的机制,但对传统文化的倡导仍然鼓励着无数在外游子踏上怀乡的旅程,去体味浓郁的泥土气,去沐浴厚重的乡野风,去重拾已有的辉煌,信心满怀地走上民族复兴之路。
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主体是农耕文明,却也兼容了其他诸多文明因素,沿海区域的海洋文明、草原地区的游牧文明也纷纷为村落文化所吸收;凡野生动物的驯化、凡外来物种的引入都无障碍地进入村落社会之中,所谓农林牧副渔,均融入村落居民的生计之中,形成具有兼容并包色彩的村落文化,中国村落文化仍继续发生着与时俱进的新跃进。
在这个意义上,马新《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堪称顺应时代要求,是两部体大思精、促人进入村落历史情境的好书。
注释:
①人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乡土中国》,三联书店2013年版;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三联书店2002年版;兰林友《田野中国莲花落: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夏吾交巴《仪式与族群认同 金沙江流域一个村落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王宏涛《人类学视野下西部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等。历史学方面的著作,以侯旭东的《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