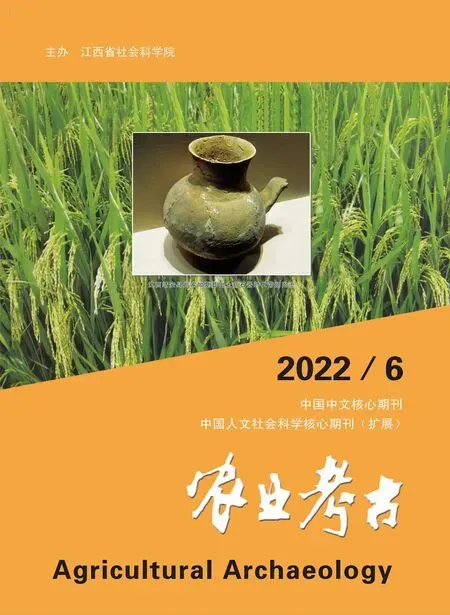从宋代农村粮食贸易看官府与富民的多重博弈*
余 猛
宋代富民阶层①的崛起,引发了其与地方官府关系的诸多变化,考察二者关系的变化对深化认识富民在宋代乡村社会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富民与官府的关系反映在乡村社会的诸多领域,农村粮食贸易即为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在宋代众多参与农村粮食贸易的经济主体中,官府和富民是对粮食市场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体,二者既相互合作,又竞争对抗。官府利用市场和行政手段压制富民在粮食贸易中追求厚利的同时,又主动利用富民,并采取一些激励手段鼓励富民按官府的社会目标进行粮食买卖。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宋代农村粮食贸易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官府与富民在粮食贸易中所呈现出的多重博弈关系,并借此研究表明富民已成长为宋代国家乡村基层治理所依赖的重要力量。
一、宋代农村粮食贸易的主角:官府和富民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宋代乡村社会商品的种类较之前代更加丰富,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粮食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②,粮食贸易成为乡村社会商品交易的大宗。在影响农村粮食贸易的多种力量中,最主要的是官府和富民。
(一)官府在粮食市场的买卖活动:和籴粮米、广积仓储和救济平市
向民众征收赋税,作为国家机构运行之需,是历代王朝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宋王朝以二税作为赋税的重要构成,“国初二税,输钱、米而已”[1](P7751)。但两宋边境长期受若干少数民族贵族政权军事威胁,战事不断,两税入库之粮难以满足兵食所需,为此,官府取“和籴”之法,通过市场来购买军需之粮。北宋时期,河北并边驻军的军粮便主要依靠籴买供应。嘉祐元年(1056)冬十月,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就建议“并边十一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2](P4450)。元丰元年(1078)二月,河东都转运司陈安石言:“年谷屡登,合广计置,乞于河北权住籴见钱京钞内支三十万缗市粮草, 以备朝廷缓急移用。”[1](P6867-6868)“(元丰元年)八月四日,诏拨提举河北籴便司钱钞十万缗,应付河北路转运司秋籴;八月五日,诏三司借明年解盐钞五十万缗,付陕西路都转运司市粮草;八月二十六日,诏赐钱二十万缗,付鄜延路经略司市粮草封桩;九月十九日,诏三司续支末盐钱二十万缗,付河东转运司市粮草”[1](P6868)。可见,经由市场和籴粮草来供应军需已成为官府普遍运用的手段。
除了军粮供应需要借助市场购买以外,国家还利用仓储系统购置储备粮食,以便灾荒或乏粮之际,无偿分发或低价出粜给受灾民众,以保民生。以常平仓为例,淳化三年(992)六月,太宗诏:“京畿大穰,物价至贱,分遣使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以常参官领之。岁歉,减价以粜,用赈贫民,以为永制。”[1](P7197)景德三年(1006)正月,“上封官请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各置常平仓……每岁秋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凡收籴,比市价量增三五文,出粜减价亦如之”[1](P7197)。天禧四年(1020)八月,真宗“诏益、梓、利、夔州、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并置常平仓”[1](P7198)。因此,早在北宋初年,常平仓的设置便已在全国普遍展开,其宗旨就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1](P6041)。灾荒时节,官府便利用仓储之粮广行救济。景德三年(1006)三月,诏:“开封府、京东、西、淮南、河北州军县人户阙食处,已行赈贷。其客户宜令依主户例量口数赈贷,孤老及病疾不能自存者,本府及诸路转运使、副并差去臣僚,同共体量,出省仓米救济。”[1](P7960)宣和六年(1124)十一月,诏:“河北、京东夏秋水灾,民户流移,继踵于道。可令应所过州军随宜接济。若常平、义仓不足,即发封桩应干斛斗赈给,令实惠及人。”[1](P7975)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无论是军粮和籴,还是仓储籴粜,其数量都是不小的,这表明官府一直作为粮食的“大买主”和“大卖主”活跃在农村粮食市场上。
(二)富民在粮食市场的买卖活动:反季节出售和跨市场转手贸易
由于粮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众多,决定了粮食贸易的参与者也十分广泛。除了官府以“大买主”和“大卖主”的身份参与市场粮食贸易外,还有直接从事粮食生产的广大小农,以土地租佃经营为主的乡村上户,从事粮食转运贸易的担夫、船户、行商,以及在城市、市镇坐地经营分销的坊郭上户、商铺之家等③。这些人群中,经济实力较强的乡村上户、城郭上户、商人和牙人,绝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讨论的“富民”④。
宋初以来,随着“不抑兼并”[3](P478)土地制度的实施,契约租佃制逐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大量粮食开始以地租的形式集中在富民手中。“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2](P621)的现象早在宋初鼓励垦荒的同时就已普遍存在,因此时人感叹道:“井田既废,既不均田,又不限田,则天下之田,大率富人兼并之田矣。”[4](P521)在占有土地和财富的基础上,富民集中了自身资本、土地和小农的劳动力优势,并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获取地租收益。从相关记载来看,一些农业主产区的富民,通过地租获得的粮食收益是十分可观的。北宋秦观言:“大农之家,连田阡陌,积粟万斤,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饶。”[5](P524)魏了翁也说:“后世田得买卖,富者数万石之租,小者万石、五千石,大者十万石、二十万石。”[6](P368)这些记载虽不免夸张之嫌,但至少表明一些乡村富民因广占田亩,往往积粮阔绰、仓储丰盈。“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独炊而自食之,其势必粜而取钱以给家之用”[7](P1064),即富民会将大量的地租以商品的形式投放到市场上,换取货币或其他生活所需之物,因为这既能解决粮食地租的单一性与富民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又可以满足富民群体财富积累的追求。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不平衡,为富民将手中的粮食低买高卖获取利润提供了条件。当“农事方兴,青黄未接,三月、四月之间,最是细民艰事之时”[8](P29),贫苦农民“皆四处告籴于他乡之富民,极可怜也”[9](P109),甚至有的“下等农民之家,赁耕牛,买谷种,一切出于举债”[10](P714)。也就是说,广大小农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农业再生产得以进行,不得不倚靠富民而出数倍之息。到了“八、九月之交,农人有米,质债方急,富室邀以低价,十月以后,场圃一空,小民所有,悉折而归大家”[11](P667),粮食收获季节,供过于求,急于还贷的贫农只好低价售粮给乡村富民,秋收不过数月,贫民又因缺粮乏食不得不再向富民高价购买或借贷粮食,一遇灾荒,“或以农器、蚕具抵粟于大家,苟纾目前”[12](P86)。这表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小农粮食需求的长期性之间的矛盾,为富民转化手中的余粮以获取厚利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遇。
此外,还有不少富民从乡村收购粮食,进行长途贩运贸易。斯波义信在《南宋米市场分析》一文中已清晰地揭示了农民生产出来的大米,如何通过步担、乡村富家、客商、米牙人、米铺经营者转输销售给城市或异地的粮食消费者。在斯波义信的讨论中,特别指出了富民在粮食交易中的重要性以及他们能够获取较高经济收益这一商业特质,“就构成市场的经济机能来看,在乡村,富农和客商比总是零碎经营的米铺、米牙、步担等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在这一点上,副业的以至非职业的商人尤其是米船、富农,比起专业商人来,他们具有的经济意义大得多。再从经营内容来看,富农商人和兼营运输业的米船,他们的资本大都雄厚,经营也是多方面的,概括地说是赚大钱的买卖”[13](P303)。由此也不难看出,富民是宋代农村粮食市场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
二、官府与富民在宋代农村粮食籴买市场中的博弈
粮食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发生变化,丰收之年,由于农户粮食剩余增加,流向市场的余粮增多,市场粮价随之下降,较低的粮价往往吸引了官府和富民大量收购,这时二者之间成为市场竞争者。建隆元年(960)正月,太祖诏:“河北频年丰稔,谷价甚贱,宜命使置场,添价散籴粳糯,以惠彼民。”[1](P6851)绍圣四年(1097)九月,“三省言:‘闻怀、卫州今岁丰稔,米谷价贱,恐尽归兼并之家。’诏河北转运司、措置籴便司、西路提举常平司以时计置籴买。”[1](P6878)官府在丰年之时动用国库之钱大量收购粮食,冠冕堂皇地打着“以惠彼民”的旗号,实则是担心粮食“尽归兼并之家”。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控制粮食采购成本关系到仓储系统能否保持正常运转。因此,官府一般在丰收之年粮食价贱之时大量买入,荒灾之年,市场乏粮价高之际再低价出粜米谷,这不仅能缓解民生困境,而且可以实现粮仓经营收支的基本平衡。绍兴二十八年(1158)九月,权两浙路计度转运副使汤沂言:“诸路州县,每岁秋稔,谷不胜贱……盖缘秋成之时,所在不曾措置籴买,兼并之家乘贱收积,以幸春夏,邀求厚利。”[1](P7568)这一记载表明,若官府不加入“乘贱收积”之列,至春夏青黄不接时,就只能任凭富民高价出售获取厚利。
官府作为具有较强购买力的买主,一旦参与粮食市场收购,往往能够成为左右市场价格的买方。“秋成之际,开场收籴,少增时价以诱致之”[1](P6900),这是乾道二年(1166)六月中书舍人王曮等进言请求官府收籴粮食的建议,就是试图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排斥富民与其竞争,达到收籴粮食的目的。这种方式,在一些经济基础较弱、富民财富能力有限的地区,自然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富民财富能力强的地区,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通常,官府籴买价格并不是由地方官随意而定,而是根据官方的“时估”定价机制来确定,以此形成一个指导价格。时估一般每旬一定,受市价制约,又与市价不同,官府买卖物品,大多按时估支付价钱。如熙宁年间的市易法,便规定“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1](P6813)。但是具体收购粮食的地方官很难根据市场变动及时调整粮价,这从宋代史料中对时估与市价的明确区别便可看出。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徽宗诏:“已降处分,州县行户止令纳免行钱。其见任官合买物色,令依在市实直收买,以宽民力。访闻州县奉行弗虔,尚用时估收买,显见违戾。”[1](P3724)这里的“实直”就是市价,也就是说,相对稳定的时估并不能和随着市场行情而变动的市价完全保持一致。因此,价格决策的非灵活性致使官府在粮食贸易中难以获得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
官府在粮食收购中,有时也因地方官员行政不力等因素,不能根据市场状况及时收籴,错失良机。元祐元年(1086)八月,司马光说:“向者有因州县阙常平籴本钱,虽遇丰岁,无钱收籴。又有官吏怠慢,厌籴粜之烦,虽遇丰岁,不肯收籴。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斤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当收成之初,农夫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籴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2](P9350)即因地方官的各种弊病和制约因素,造成粮食收购的赢家多为富民群体。
分析师建议,种植户、储户要密切关注货源质量,做好储备工作;如果储存较大,则要有序出货。对于华北地区种植户来说,目前多数货源都已经入窖,建议密切关注货源质量,做好库内通风、保温等工作,防止货源质量出现问题。(信息来源:安徽农网)
相对于地方官员而言,富民因根植于乡村社会,对乡村民众的经济需求了如指掌,对乡民邻里的困境心知肚明,往往能够迅速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到粮食。针对此种情况,宋代不少士人都有议论。熙宁六年(1073),沈括上奏说:“浙人以治田为生,所入甚广,急欲得钱,贱粜于有力之家。”[2](P6008)南宋思想家陆九渊言及抚州金溪县农民时说:“今农民皆贫,当收获时,多不复能藏,亟须粜易以给他用,以解逋责。使无以籴之,则价必甚贱,而粟洩于米商之舟与富民之廪,来岁必重困矣。”[9](P109)也就是说,小农大多因急需用秋粮换钱以偿逋负,仅有的余粮甚至部分口粮,大都低价卖给了当地富民。
当然,多数时候官府并不甘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官府与富民最大的区别在于官府是掌握特权的一方,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于是,就出现官府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富民竞争的行为。仁宗朝时,御史中丞杜衍在与仁宗议论常平法时言:“今豪商大贾,乘时贱收;水旱,则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图厚利,而困吾民也。请量州郡远近,户口众寡,严赏罚,课责官吏,公籴未充,则禁争籴以规利者。”[14](P10190)元符元年(1098),“泾原经略使章楶请并边籴买;豫榜谕民,毋得与公家争籴”[14](P4245)。这些记载表明,官府采取非常规的手段限制富民争籴并非个案,而是常用的手段。
以和籴军粮而言,最初仅为应急措施,“皆非常制”[14](P4241),后因军需浩繁,朝廷时常要求各地籴买粮食,故“又有坐仓、博籴、结籴、俵籴、兑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14](P4243)。这些名目各异的取粮之法,都属于官府直接参与粮食购买活动,或按户等强行抑配,或用官告、度牒充当支付,并非公平交易。以俵籴而言,熙宁八年(1075)始推行于澶州、北京一带,其法为“度民田入多寡,预给钱物,至收成时,令于澶州、北京及缘边入米麦粟封桩,候有备”[2](P6489),“崇宁中,蔡京令坊郭、乡村以等第给钱。俟收,以时价入粟”[14](P4245)。括籴之法为“官储有乏,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14](P4245)。均籴之法是由“转运司摊定一州一县,合籴都大石数,会计一州一县逐等第都计家业钱,纽算每家业钱几文,合籴多少石斗”[1](P6921)。这些打着和籴的名号,实际上依据田亩、户等以及家业钱抑配籴买粮食的方法,使得富民成为主要的承担对象之一,因为富民群体多为“田连阡陌,家资巨万”[15](P2197)的“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1](P6045)。也就是说,在这一不公平竞争中,赢粮之家的富民不仅无法参与粮食购买的市场竞争,而且还成为官府重点掠夺的对象。
如此一来,官府与富民的经济矛盾趋于激烈。官府亦知矛盾若进一步激化,不仅难以顺利和籴到粮食,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由官府在粮食出粜中的局限所决定的,下文会有叙及,暂不多说。故朝廷有时也会采取补官奖励、旌表富民等方式,给予他们适度的心理安慰,以此拉拢富民。例如,“参军卢澄者,陈留县大豪也。尝入粟,得曹州助教”[2](P1977)。开禧二年(1206)四月,宁宗“下纳粟补官之令”[14](P740),即采取官职奖励的方式抚慰入粟的富民。绍熙四年(1193)八月,光宗诏:“诸路安抚、转运、提举司,如实有旱伤州县,许劝谕官、民户有米之家赴官输米,以备赈济……其出米及格人,仰逐司保奏,依立定格目推赏施行。”[1](P8005)也就是说,富民等有米之家可以依据入纳粮食的多少,获得相应的官职奖赏和激励。
由此可见,在粮食收购市场中,官府凭借其“大买者”的经济实力和行政强制力,在市场上强势进入,强势收买,占据优势。活跃在乡村城市的众多富民,充分利用自身对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可行性,以及在熟人社会中经营的便利性,灵活地在粮食市场中应变经营,同样也是粮食市场不可忽视的买方。这些富民的手中,多数掌握着为数不少的粮食储备,以至于在官府急于收籴粮食之时,常常通过一些强制手段来迫使富民把粮食出售给他们,但是这些强制手段大多被限制在不太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同时国家还通过一些激励手段来鼓励富民售粮。
三、官府与富民在宋代粮食粜卖差异化目标下的博弈
在粮食粜卖环节中,官府主要以稳定市场、保障民生为目的参与其中,对于富民而言,则是为了售粮以赚取差价。多数情况下,官府对富民们通过转手贸易获得正常经营利润不做过多干涉,只是借由商税的征收来分享富民粮食贸易的利润,以此达到官民两利的结果。但当官府以稳定市场、保障民生为目的的粮食出粜,因自身诸多局限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时,富民便成为国家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补充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二者间的博弈便在所难免。
宋代官府出粜粮食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应对荒灾之年和季节性的粮食短缺问题。早在淳化三年(992)六月,太宗下令创设常平仓时便明确指出:“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遂为永制”[2](P737),即把常平仓储低价出粜以救济贫民之事制度化。天禧四年(1020)二月,真宗“令唐、邓等八州发常平仓粟,减价出粜,以济贫民”[2](P2183)。庆历四年(1044)春正月,“陕西谷价翔贵,丁丑,转运司出常平仓米,贱粜贫民”[2](P3533)。这些都是官府通过减价出粜,稳定市场粮价,救济贫民的事例。旱涝、灾荒之时,官府也会采取低价出粜粮食的办法,帮助小农渡过难关。景德元年(1004)九月,“鄂州言民饥,诏开仓减价出粜以救之”[1](P7959)。绍兴三十一年(1161)正月,诏:“雪寒,细民艰食。令临安并属县取拨常平米,依市价减半,分委官四散置场,广粜十日。”[1](P7398)也就是说,官府在荒灾之年低价出粜粮食,以应民生之需。
官府以稳定市场、保障民生为目的的粮食出粜,尽管初衷甚好,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大多不能如愿。一是国家粮食储备有限,遇重大灾荒,往往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景祐元年(1034)秋七月,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余万,岁饥不足以救恤。”[2](P2690)绍兴二十九年(1159)闰六月,提举两浙路市舶曾愭言:“赈济户口数多,常平桩管数少,州县若不预申常平司于旁近州县通融那拨,米尽旋行申请,则中间断绝,饥民反更失所。”[1](P7397)因此,宋人李觏曾指出常平米谷“至春当粜,寡出之,则不足于饥也;多出之,则可计日而尽也”[16](P143)。有时也因仓储管理混乱,导致储备粮食被侵支或不堪食用,无粮应急。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臣僚言:“国家置常平、义仓,为水旱凶荒之备。近来州县循习借用,多存虚数。其间或未至侵支,亦不过堆积在仓,初未尝以新易陈,经越十数年,例皆腐败而不可食用。”[1](P7572)原本作为水旱凶荒之备的常平义仓,在真正面临灾伤需要出粜粮米时,有的甚至面临无粮可粜的窘境。
三是官府出粜粮食的地点辐射范围有限。官府开仓救灾,设置的粜米地点多是在县治所、市镇等地,难以覆盖灾情发生的各地。绍兴十年(1140)三月,臣僚言:“诸处粜米赈济,只及城郭之内, 而远村小民不沾实惠。”[1](P7978)乾道四年(1168)四月,司农少卿唐瑑言:“福建、江东路自今春米价稍高,民间阙食。郡县虽已赈粜,止是行之坊郭,其乡村远地,不能周遍。”[1](P7404)也就是说,一些乡村偏远的受灾之处,因远离州县,并未享受到官府低价赈粜的实惠。
因此,仅仅依靠国家粮食储备平价出粜来解决民食艰辛的困境,收效往往有限,这便为活跃在粮食市场中的富民提供了成长空间。“今富人大姓,乘民之急,牟利数倍”[14](P4548)。他们或见到利好,争与出粜,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乐平明口人许德和,闻城下米麦价高,令干仆董德押一船出粜。既至,而价复增,德用砂砾拌和以与人,每一石又赢五升。不数日货尽,载钱回”[19](P700)。有的富民预测市价看涨,闭廪不粜,“富室不怜贫,千仓尽封闭。只图价日高,弗念民已弊”[10](P644)。
针对此种情形,肩负着赈灾救济重任的地方官员通常会采取官方限价政策,禁止有积粮的富民趁机加价倒卖。“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立赏禁人增米价”[20](P309)。然而,这一做法有时也因严重损害了富民的利益而适得其反。开宝五年(972)秋七月,陈从信对赵光义说:“今(开封)市中米贵,官乃定价斗钱七十,商贾闻之,以其不获利,无敢载至京师者。虽富人储物,亦隐匿不粜。”[2](P287)也有少数地方官员主动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来解决米价上涨问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饥,谷价方涌,斗钱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众不知所为。公乃命多出榜沿江,具述杭饥及米价所增之数。于是商贾闻之,晨夜争进,唯恐后,且虞后者继来。米既辐辏,遂减价还至百二十。包孝肃公守庐州,岁饥,亦不限米价,而商贾载至者遂多,不日米贱”[21](P19)。但如此熟谙市场规律的官员毕竟是少数,而且靠市场自动调节供求,需要具备畅通的信息传递、便捷的交通和开放的区域市场条件等多重因素。
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选择运用“劝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谓“劝分”,是指官府劝谕富民无偿捐赠粮食或低价出粜粮食,以帮助贫困民户。“劝分”关键在于“劝”,官府通常采用道德感化方式劝喻富民。如南宋后期,在抚州主持赈灾的黄震,在劝谕富民低价出粜赈灾的榜文中便写到“救荒之法,惟有劝分。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国法也。富者种徳,贫者感恩,乡井盛事也”[15](P2201)。
“劝分”是两宋时期国家应对灾荒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方式,面对官府“劝分”,不少富民响应号召,积极主动参与赈灾。天禧元年(1017)四月,江淮两浙制置发运使李溥言:“江、淮去岁乏食,有富民出私廩十六万石粜施饥民。”[1](P7962)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多户富民共同参与赈济的情况,如“庐陵郡统县八,间遇水旱疾疫,凡邑之大家,分任赈恤之事,某家发廪,某家给薪刍,某家药病者,某家瘗死者。以是流殍稀鲜,县官推勘分赏”[22](P759)。南宋时期,“劝分”之策更加广泛地运用于赈灾济贫,绍兴六年(1136)二月,右谏议大夫赵霈称:“去秋旱伤,连接东南;今春饥馑,特异常岁。湖南为最,江西次之,浙东、福建又次之。今日赈救有二,一则发廩粟减价以济之,二则诱民户赈粜以给之。”[1](P7345)根据张文的研究,两宋时期“各地一遇荒灾,往往行劝分之政,将劝分视为荒政的一部分,尤其是越到后来越依赖于劝分”[23]。而在劝分实际执行过程中,如前所述,财富力量不断增长的富民阶层,已经成为国家维持基层社会稳定所依赖的重要对象。
一些富民之所以愿意与官府合作,响应“劝分”,低价出粜赈灾救济,目的是希望在乡里社会获得更高地位。宋廷规定,响应国家“劝分”者,根据捐赠或出粜粮食的多少,给予不同等级的荣誉旌表或官职奖励。淳化五年(994)正月,太宗诏:“诸道州府被水潦处,富民能出粟以贷饥民者,以名闻,当酬以爵秩。”[1](P7326)南宋董煟言:“国家赈济之赏非不明白,五千石,承节郎进士迪功郎;四千石,承信郎进士补上州之学。”[24](P7)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富民出粜粮米的行为。也有一些富民是为了实现救济乡里的理想。如吴芾在赞扬其侄捐金散谷救济乡里的诗中就写道:“闻人急难如在己,见义勇跃无不为……此心但欲济邻里,身外浮名非所希。”[25](P475)
无论是为了满足自身获得社会地位的追求,抑或赢得乡里社会的尊重,都使富民与官府在粮食粜卖市场的博弈中,获得了更多可以凭借的力量。富民既然被赋予了一定的乡治权,就不可能彻底避免其以权谋私,运用手中的权力在粮食粜卖市场中大做文章。同时,获得乡里社会承认的富民长者,也可以利用其与广大佃农、贫农间的紧密依存关系来削弱官府干预富民参与粮食粜卖市场的成效,这些都使得官府和富民间围绕农村市场粮食贸易所展开的博弈进一步复杂化。
四、结论
粮食在宋代已经成为大宗商品在农村市场流通。作为交易主体的官府和富民在粮食贸易中既有同是买者的竞争关系,又有买者(官府)和卖者(富民)的合作关系,还有同是卖者但目标不一致的对立关系。因此,表面上看,官府和富民是两个经济主体来参与粮食市场的交易,实则是国家与富民关系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反映。
首先,富民是宋代的基层统治必须依赖的重要力量之一。尽管民间参与农村粮食贸易的经济主体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在市场中起主导性作用的是那些由乡村地主和富商组成的富民。面对战争军需,国家和籴筹粮,多数需要富民的支持才能完成任务;面对灾荒肆虐,国家欲发廪赈灾,也需要对富民“劝分”才能缓解灾伤。其次,在农村粮食贸易的复杂博弈中,地方官府正因认识到富民拥有凭借财力和地缘左右市场行情的优势,故无论“和籴”还是“劝分”,大都以满足富民阶层的合理诉求来诱导,使其粮食买卖活动符合国家预期的社会目标,一些富民也因积极响应国家的粜籴号召,因而获得了国家认可的乡里社会地位。
因此,从官府与富民围绕农村粮食贸易所展开的多重博弈可以看出,富民阶层开始成为宋代乡村社会多元共治的主体之一,宋代统治者也认识到富民阶层对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性,因而既利用富民的财富来增强国家力量,又辅之以激励安抚等措施来保护富民阶层的成长壮大。
注释:
①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是林文勋教授及其学术团队近二十年来重点研究的一项课题。他们认为,唐宋以来“富民”阶层的崛起,使得唐宋及其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了与以往显著不同的历史特征,形成了一个新的“富民社会”。“富民”阶层的崛起,引起了中唐以来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引起了国家乡村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的重大调整。由此,林文勋教授提出了五个有关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理论体系的学术论断:(1)“富民”阶层是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新兴阶层;(2)“富民阶层”一经兴起便迅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中间层、动力层和稳定层;(3)“富民”与国家的关系是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最核心的关系;(4)“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5)中国传统社会依次经历了上古的“部族社会”、秦汉魏晋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并最终向着“市民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这一社会演进即为中国古代史的新体系。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研究的由来与旨归》,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②全汉昇在《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2年版)中指出,宋代长江上游的四川,中部的湖南与江西以及下游的三角洲,都是稻米的重要产区,除供当地人口食用外,还有剩余作输出之用。湖北与两淮,因地接金国,米产甚少,须输入上述各地的米。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稻香出版社1997年版)中也认为宋代米经过农民本身和富农地主及商人之手大量投入市场,成了远程流通商的重要商品之一。包伟民在《宋代的粮食贸易》(《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中也指出宋代粮食贸易的特性之一就是任何农业生产区,无例外地都会有一定的商品粮输出,不管它的输出量如何,或者其输出所影响的范围有多大。
③斯波义信在《南宋米市场分析》(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五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一文中认为:和米市场有关的商人主要有步担、富家、客商(米船)、米牙人、在乡富农等;在《宋代商业史研究》(稻香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认为宋代城市粮食消费的主体是官僚、军队和市民,农村主要是富农、地主和小民。全汉昇在《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华书局2012年版)一文中认为南宋粮食运销的主体是商人。梁庚尧在《南宋的农村经济》(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认为宋代农村市场粮食贸易的主体是农家、地主和商人。龙登高在《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认为宋代农村市场粮食贸易的主体是小农。郭正忠在《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认为,宋代乡村粮食贸易的主体是乡村居民、商人和各类专业户。姜锡东在《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一书中认为,宋代粮食贸易的主体是商人、地主、官吏和农民,其中商人又分为米铺户、长途贩运商和米牙人。
④林文勋教授认为“富民”主要是以农业致富的群体,但也包括了以工商业和其他途径致富的人。宋代实行“五等户制”,按照户等的划分,“富民”主要是乡村中的上三等户。作为富民,占有财富和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是其显著的社会特征。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理论体系》,载林文勋、黄纯艳主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53-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