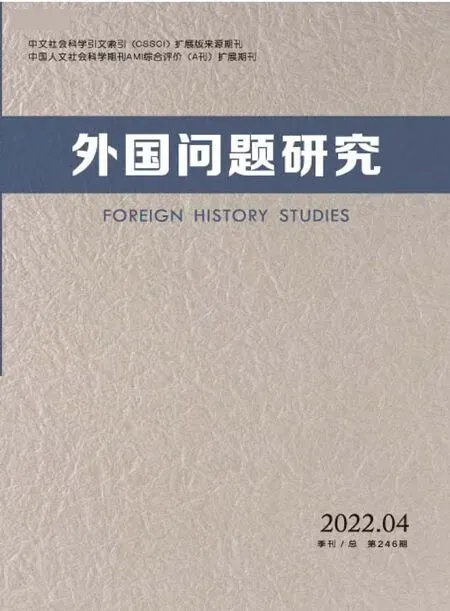爱因斯坦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抵制与批判
李晔梦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062)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不仅是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巨人,还是一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伴随着20世纪末新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料的不断挖掘与呈现,国际学术界对爱因斯坦的研究历久弥新。(1)国外学术界对爱因斯坦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多,尤其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就设立专门的项目(Einstein Papers Project)整理、翻译和出版爱因斯坦的文献,包括著述、讲话、回忆录、日记等,目前已出版15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还有大量其他学者整理和撰写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涉及爱因斯坦民族主义观念的有David E. Rowe and Robert Schulmann, Einstein on Politics: His Private Thoughts and Public Stands on Nationalism, Zionism, War, Peace, and the Bomb,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Max Jammer, Einstein and Religion: Physics and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eter L. Galison, Gerald Holton and Silvan S. Schweber,Einstein for the 21st Century: His Legacy in Science, Art, and Modern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Alice Calaprice, Daniel Kennefick and Robert Schulmann, An Einstein Encyclope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Ze’ev Rosenkranz,Einstein before Israel: Zionist Icon or Iconocl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国内学术界围绕爱因斯坦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重点集中于“相对论”的介绍、生平传记、作品集以及个人信件、图片等。关于爱因斯坦人文思想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其和平主义主张、伦理道德观念、教育文化思想等。爱因斯坦的民族主义观念是其人文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与系统的研究。(2)国内学者较早对爱因斯坦关注的是科学史家许良英,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组织整理翻译了3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尤其是第三卷收录了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的诸多论述。近年来关于爱因斯坦相关文献的翻译整理热度不减,不仅包括其本人作品的翻译,也包括外国学者撰写的爱因斯坦传记,例如方在庆编译的《我的世界观》(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张卜天翻译的《爱因斯坦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马怀琪等翻译的《爱因斯坦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等。总体来看,这些成果更多是对爱因斯坦的生平和科学思想的整理,研究爱因斯坦民族主义思想的数量较少,仅有杜严勇的《爱因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1期)、张腾欢的《在民族感情和世界主义之间——论爱因斯坦的犹太观》(《世界民族》2018年第2期)和《谁拥有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卡勒与希提关于犹太民族权利的争论》(《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5期)等成果中有所涉及。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爱因斯坦对于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强烈反对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一批富有社会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爱因斯坦起初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所弘扬的独特性是引发国家和民族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作为一名深受纳粹种族主义迫害的犹太人,他逐渐意识到在当时的世界局势和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下,完全放弃民族主义只是空想,也不可能为犹太人赢得独立和解放。爱因斯坦的思想所体现出民族性、世界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博弈与张力,折射出欧洲社会犹太群体的共同境遇与心路历程。在极端情绪、种族主义依旧肆虐的今天,重新梳理爱因斯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理解其人文主义情怀仍然具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爱因斯坦对德国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
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席卷世界,其引发的政治狂热弥漫了整个欧洲,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而且与欧洲格局乃至世界秩序密切交织。爱因斯坦“恰恰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愚蠢神话达到顶峰的时代”。(3)方在庆:《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8页。青少年时代,他就深刻地感受德国人的民族情绪。1911年,受奥匈帝国皇帝的邀请,爱因斯坦到布拉格大学担任理论物理讲座教授,之后的经历让他对民族问题有了更深的感受。布拉格大学的教职员工主要由捷克人和德国人组成(当时的该大学实际上分裂为德语人群和捷克语人群两个圈子),许多德国教授在捷克人面前普遍具有种族优越感且充满敌意。“这种情况下让那些不赞成与捷克人敌对的德国人也很难真正与捷克人交往……在他们看来,德国人随意说出的每句话都是侮辱他们……结果连善意的德国人要想与捷克人保持友好关系都十分困难。”(4)菲利普·弗兰克:《爱因斯坦传》,吴碧宇、李梦蕾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2页。而犹太人作为布拉格最大的德语群体,被大部分捷克人等同于德国人。而对于德国人来说,犹太人又是“染上捷克习性”的劣等人,在此工作的犹太人更深处于民族偏见的夹缝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爱因斯坦离群索居,深切地感受到民族隔阂已成为欧洲社会最大的痼疾,究其“祸端”正是长期流行的民族主义。
在普法战争以来的德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严重扭曲了社会机体,人们开始习惯于从民族视角来解释战争、经济与道德等各种问题,民族间关系长期紧张。一战的爆发导致德国知识分子阵营分裂,出现了“俾斯麦的德国”和“歌德的德国”。“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之外,还存在一个‘知识分子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两派知识分子利用‘知识的武器’互相攻防。”(5)菲利普·弗兰克:《爱因斯坦传》,第123页。“两个德国”代表的是整个德国社会相互博弈的两种力量,尤其是“俾斯麦的德国”主张以民族主义为基点来营造德意志式的帝国。爱因斯坦自1914年起回到德国柏林生活,由于“目睹了恶性民族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和平主义与国际主义理想”。(6)芭芭拉·沃尔夫、泽夫·罗森克兰茨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永远的瞬间幻觉》,北京依尼诺展览展示有限公司译,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然而“对于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来说,犹太人与和平主义者是他们战争失败的替罪羔羊。他们认为好像是那帮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导致他们战场落败,而任何那帮运动的支持者都成了他们暴怒的对象”。(7)菲利普·弗兰克:《爱因斯坦传》,第166页。在这样的环境中,尽管爱因斯坦对政治不感兴趣,但犹太人与和平主义者的双重身份把他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一战前夕,德国政府要求知识界必须公开申明支持战争的立场。战争爆发三个月后,93位德国科学家发起《致文明世界宣言》(ManifestototheCivilizedWorld),核心内容是论证德国文化与军国主义传统是完全一致的。爱因斯坦公开拒绝在宣言书上签字。与此同时,爱因斯坦的朋友格奥尔格·尼古拉(Georg Nicolai)医生起草了《告欧洲人书》(ManifestotoEuropeans),呼吁欧洲人要保持理智,并获得了爱因斯坦和其他3位知识分子的签字支持。宣言指出:不能把德国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否则就是在为这场野蛮战争辩护,更会危及各个国家的根本生存。“民族主义的激情不能成为这种心态的借口,而它根本不够资格被世界称为文化。这种思维如果普遍传扬在知识分子之间,那将是大大的不幸……更会危及各个国家的根本生存。”(8)这一声明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个关于非科学命题的声明,由于与政府唱反调而在德国被禁止,直到1917年才在瑞士发表。关于宣言的内容,参见弗雷德·杰罗姆:《爱因斯坦档案》,席玉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22页。
这一时期,爱因斯坦还参加了致力于建立“欧洲联盟”的和平主义组织的反战集会。1915年10—11月,爱因斯坦完成了《我对战争的意见》(MyOpinionontheWar)一文,对德国人在与俄国人交战胜利后所表现出的“贪婪与自大”非常惊愕,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反民族主义立场。(9)Albert Einste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6: The Berlin Years: Writings, 1914—1917, trans.by Alfred Eng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vised ed.), 1997, p.96.在1916—1918年担任德国物理学会主席期间,他不断强调民族主义不仅是科学精神的绊脚石,也是酿造灾难的根源。1922年6月在德国和平联合会上,爱因斯坦评判当时的欧洲形势,呼吁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在不同民族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桥梁。1931年9月3日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撰文反对把扩军备战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提出要限制民族主义者的国家主权,他指出:“国家是为人民设立的,而人民不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10)200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德国政府把这一年定为“爱因斯坦年”,并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爱因斯坦的这句话被镌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以警示后人。“除非所有国家都一致同意限制自己国家的主权,并联合抵制任何公然对抗或者秘密违反仲裁法庭裁决的国家,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目前这种普遍混乱和恐怖的状态……实现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在于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被夸大到扭曲程度,并贴上‘爱国主义’这个让人同情却又被滥用了的名字的标签。”(11)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方在庆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79—181页
30年代希特勒上台以后,力图实现德国集权主义的“一体化”,把“纯洁血统”作为实现德国社会重组的手段。“纳粹政权用尽各种手段,以团体意识取代个体价值观,使得整个德国社会都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与无所不在的控制网络中。”(12)孟钟捷:《德国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大量“无生存价值的生命”被无情地淘汰,这些人包括非雅利安人(主要指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遗传病患者、同性恋、反纳粹分子等。当时的大多数纳粹专家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犹太人是文化破坏者,他们不具备真正的文化素养,只会对周围文化产生有害影响”。(13)Dana Arieli-Horowitz, “The Jew as ‘Destroyer of Culture’ in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Patterns of Prejudice, Vol.32, No.1, 1998, pp.51-67.在纳粹的种族主义观念下,爱因斯坦的科学体系被标签为犹太人的“伪科学”,1933年5月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Beobachter)上刊登了德国狂热的纳粹分子菲利普·勒纳(Philip Lenard)的文章,公开指责爱因斯坦及其理论完全是任意炮制出来的陈词滥调,德国人把爱因斯坦当作伟大的科学家“是何等的谎言”。(14)两年后,勒纳在一次演说中讲道:“自然科学过分强调爱因斯坦,他依旧占据支配地位。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德国人成为一个犹太人的信徒是不值得的。自然科学完全起源于雅利安人的,德国人必须找到自己探知未知事物的方法。希特勒万岁。”(参见菲利普·弗兰克:《爱因斯坦传》,第240页)1936年,勒纳在他的《德国物理学》(German Physics)一书中宣称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物理学”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与顽强和热切地渴望真理的雅利安科学家不同,犹太人缺乏理解真理的能力到了惊人的程度。”(参见艾丽斯·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年谱》,范岱年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3页)由于“相对论”被打上了“犹太物理学”的标签,爱因斯坦成了“劣等头脑杜撰的伪科学的典型代表”,他的反民族主义言论、和平主义主张以及同情社会主义的态度被看作“危险分子”的象征,因此他被列入需要首先清洗的科学家的名单。而彼时爱因斯坦正在美国,当得知自己的书籍被焚烧、大批犹太人被驱逐等一系列坏消息之后,爱因斯坦辞职并来到比利时。
此后德国的形势急剧恶化,纳粹分子接二连三搜查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公寓,又以“给共产主义革命提供资金资助”为罪名查封爱因斯坦的住所。当听说纳粹报纸悬赏5 000美元要他的人头时,爱因斯坦打趣地说:“我真不知道我值这么多钱。”(15)Fred Jerome and Rodger Taylor, 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Piscatawa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7.在对德国绝望之后,爱因斯坦在英国牛津度过了一段流亡时光,10月份他来到美国开始了他的“普林斯顿时代”。
二、爱因斯坦对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抗争
德国的经历使爱因斯坦从内心深处更渴望自由平等的生活,正如他在1933年3月所写的:“只要我可以选择,我只会生活在一个政治自由、宽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政治自由指的是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宽容指的是尊重任何个人的意见。在目前的德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16)芭芭拉·沃尔夫、泽夫·罗森克兰茨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永远的瞬间幻觉》,第127页。然而定居美国之后,他痛苦地发现这个国家也远远不是理想中的乐土。30年代的美国经济萧条、社会矛盾尖锐、民心低沉悲观,各种右翼、左翼思潮流行于社会。随着德国的扩张,来美国避难的犹太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包括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医生以及各类专业人才。爱因斯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帮助,美国官方及社会舆论把他称作“流亡犹太难民群体的精神领袖”。然而让爱因斯坦深感纠结的不只是亟待安置的流亡犹太难民,还有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普林斯顿随处可见,甚至美国所有的常春藤大学中犹太学生都寥寥无几,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员工中加上爱因斯坦也只有两名犹太人,至于黑人更难有机会进入。普林斯顿所在的大学城种族界限分明,电影院里黑人和白人需分区就座,占总人口约两成的黑人屈辱地生活在白人世界之外。
爱因斯坦对此深感痛心,多次公开批评白人种族主义,而身体力行抵制这种现象。“在爱因斯坦诸多鲜为人知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想之中,最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对民权的声援以及对种族歧视的直言反对。”(17)弗雷德·杰罗姆:《爱因斯坦档案》,第160页。1946年5月3日,宾夕法尼亚林肯大学授予爱因斯坦名荣誉学位,爱因斯坦对学校的师生讲道:“我到访本校是代表着一项重要的事业。在美国,有色人种与白人被隔离开来,这种隔离不是有色人种的弊病,而是白色人种的弊病。我不想对此保持沉默。”(18)Albert Einstein, “Speech to Lincol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Faculty, May 3, 1946,”in Fred Jeromeand and Rodger Taylor, eds., 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 p.142.1946年9月16日爱因斯坦在全国城市联盟大会的致辞中讲道:“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国家最严重的沉疴便是黑人的待遇问题……是对缔造美国的先辈们的‘人人生而平等’原则的践踏……人们很难相信,通情达理的人居然如此顽固地抱着这样深的偏见,总会有一天历史课的学生会嘲笑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19)Albert Einstein, “Message to the National Urban League Convention, September 16, 1946,” in Fred Jeromeand and Rodger Taylor, eds., 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 pp.144-145.
爱因斯坦还公开支持各种反对种族歧视的团体。1937年成立的“非洲事务委员会”(Council on African Affairs)以“去殖民化及反对种族隔离”为宗旨,爱因斯坦长期与该组织保持密切联系。1950年前后,爱因斯坦在接受黑人学生报《切尼记录报》(TheCheyneyRecord)的专访时直言:“不幸的是,种族偏见已成为美国传统,而且不分是非地一代代传承下去。”(20)Albert Einstein, “Interview with the Cheyney Record, October 1948,”in Fred Jeromeand and Rodger Taylor, eds., 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 pp.148-149.在亚特兰大的一次研讨会上,爱因斯坦又表示:“每个以正义为念的人都会感激各位,因为你们愿意联手对抗这股正在可悲地伤害这个国家尊严及名声的邪恶力量。”爱因斯坦的言论在民众中产生很大影响,被印在T恤及各类海报和月刊上。(21)弗雷德·杰罗姆:《爱因斯坦档案》,第160页。
作为一位有良知的公众知识分子,爱因斯坦不仅抵制种族主义,而且极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各种压迫行为,他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一起以《国家周刊》(NationalJournal)为阵地发表时论。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由于反对冷战思维和同情共产主义运动,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当作重点“关注对象”。尤其在“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盛行的年代,爱因斯坦和卓别林等文化人士受到了一系列的监控与审查。(22)从1932年底开始一直到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爱因斯坦长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秘密调查,留下了1 000多页的“爱因斯坦档案”,强加给他的“罪名”包括“犹太可疑分子”“黑色人种代言人”“俄国间谍”“赤色分子同路人”“颠覆分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等。调查并不限于爱因斯坦本人,还包括对他周围人的监控,参见“Albert Einstein, 1950,”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 Records. Bufile Number: 61-7099, Albert Einstein: Part 1 to Part 9.在联邦调查局档案“红色前锋组织”的清单下,列举爱因斯坦参与的黑人民权活动、“为黑人公民辩护筹款”活动、支持“南方促进人类福祉研讨会”等等。在联邦调查局所掌握的材料中有一份长达15页的清单列举了爱因斯坦与“反动组织”的“联络及往来”,其中还有两处被局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批示过。
在与白人种族主义斗争的过程中,爱因斯坦的内心充满痛苦与忧伤,他在给比利时伊丽莎白王太后的书简中写道,到处都能听到“德国的脚步回音”,“美国人已经用狂热顶替了(德国人的)位置”,“多年前德国的不幸再度重演”。“大家默许恶势力还向它输诚靠拢,我只能无力地旁观”。(23)弗雷德·杰罗姆:《爱因斯坦档案》,第309页他告诉自己的欧洲朋友们,美国四处流行着“蛮横与流言”,“极端情绪无处不在”。他觉得自己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与人群的疏离感”。在心灵历经煎熬的同时,爱因斯坦更加向往远离极端民族主义与扩军备战、人人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一时期,爱因斯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更加深刻,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强调民族主义瓦解了民主的基础,破坏了“学术自由和保护宗教上的少数”“个人权利不可侵犯”这些民主法则。(2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论科学与教育》,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7页。第二,民族主义引发了道德衰败。他指出:“当占据一席之地的民族纷纷向暴君们低下了头”,“世界的其余部分对那些道德衰败的症状也已逐渐习以为常了。人们丧失了反对不义和维护正义的起码反应——这种反应归根结底是防治人类不至于堕落到野蛮状态的唯一保障……为了保卫公理和人的尊严而不得不战斗的时候,我们绝不逃避战斗。”(25)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许良英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01—102页。第三,民族主义蒙蔽了知识分子精神。爱因斯坦反复强调科学的普遍性、公有性与国际性,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不仅是科学的代言人,也应是公众良知的晴雨表。但残酷的现实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反动的政客设法通过提供虚假的外部危险来误导公众,让他们怀疑所有智力上的努力”。(26)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第56页。他呼吁知识分子要尽最大的努力摆脱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控制,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1950年,爱因斯坦曾公开致信“科学的社会责任协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谈及知识分子的国家使命、个人良知、相互协作与道德责任。(27)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第256页。第四,民族主义损害了文化的普遍价值。爱因斯坦强调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文化贫困现象,“只有人类还重视精神财富,就有理由防止这种文化上的贫困化……并重新唤醒现在被民族自大主义掩盖了的更高级的团结互助精神。正是因为它,人类的价值才可以不受政治与国家边界的影响。人类将为每个民族取得能够存在下去的工作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文化价值”。(28)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第256页。第五,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死敌。爱因斯坦一贯主张撇开国家、民族、阶级、社会地位等狭隘立场,从国际主义的角度思考全人类的问题,建构世界和平。原子弹爆炸之后,他多次提出要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联手建立一个“超国家安全体系”(有时也表述为“世界政府”),其使命是“裁决一切军事问题”“干涉地区争端和不稳定”,而摆脱民族主义的羁绊则是“超国家安全体系”的首要条件。(29)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自述》,王强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288—296页。
三、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主义的认知
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南部小城乌尔姆(Ulm),1岁时就随父母去了慕尼黑,该地区深受法国大革命所传递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等理念的影响。在这里生活的犹太人并不坚守犹太习俗,他们已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环境,大部分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同化。爱因斯坦的父母把他送进慕尼黑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读书,其意图就是让他有更多的机会与非犹太教的孩子交往。爱因斯坦的父母跟很多被同化的犹太人一样,并不信仰犹太教,但也没接受基督教洗礼,保留了一定的犹太性(比如遵守某些犹太传统),也承认自己的犹太身份。(30)Denis Brian, Einstein: A Life, New York: John Wiley&Sons,1996, pp.4-5.然而,在爱因斯坦的童年时代依然明显感受到了犹太孩子与非犹太孩子的区别,他突然对犹太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宗教感情的驱使下,他竟然接受犹太教教义(遵守饮食规定,并遵守安息日)。”(31)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London: Simon & Schuster UK Ltd., 2007, p.16.成年之后爱因斯坦的解释是他当时看到了“人的原始激情盛行”“追逐欲望的残酷性”,并期望从宗教中寻找解脱的答案。但是,当他发现了宗教中的盲目、虚无以及对权威的崇拜后,又把满腔热情投入科学之中,期望以科学为寄托获得崇高的精神境界与个性的解放。后来的生活经历使爱因斯坦进一步意识到无论是否信仰宗教,他和犹太人及犹太民族的关系是割舍不断的。在爱因斯坦的著述及演讲中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毫不隐讳,对犹太文化的赞赏也随处可见。他在1938年写成的《他们为什么要仇视犹太人》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他对犹太性、犹太文化的特征以及反犹太人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坚守“犹太人的信仰”是“犹太人集团”的共有特征。所谓“犹太人的信仰”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宗教的坚守,一个放弃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依旧是一个犹太人,正如“蜗牛去掉它的壳仍旧是蜗牛一样”。在他看来,塑造犹太人的精神要素是犹太传统:“几千年来使犹太人连接在一起,而且今天还在连接着他们的纽带,首先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一切人中间的互助和宽容的理想……犹太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3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第25页。1943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在一次演讲呼吁犹太人团结起来,致力于对真理与知识的追求、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实现。他讲道:“今天这个世界中的人们,都被原始的本能控制着,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残暴……我们遭受残酷迫害的原因无非是我们高举了和平的理想,并且我们民族中最优秀人物用行动践行了这个理想。”(3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自述》,第93页。
源于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的浓厚情感,爱因斯坦同情犹太人的境遇,但另一方面,出于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他又担心阿拉伯人的民族情绪。他一方面主张犹太人逃离欧洲、回归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但又排斥单一“民族国家”,拒绝极端民族主义。他艰难地游离于“犹太人”与“世界公民”之间,一直处在民族主义感情与世界主义理想的纠结之中,尤其定居柏林后,爱因斯坦深为犹太青年的痛苦境况所担忧,“反犹环境严重阻挠了他们正常地求学或为争取安全生存而斗争”。(34)Albert Einstein, “How I Became a Zionist,” in D. E. Rowe and R. Schulmann, eds., Einstein on Politics: His Private Thoughts and Public Stands on Nationalism, Zionism, War, Peace, and the Bomb, p.151.此后,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立场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爱因斯坦首次接触犹太复国主义是在布拉格。当时布拉格有个深受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圈,主要关注哲学、艺术与宗教问题。爱因斯坦在此结识了文学家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并与哲学家雨果·伯格曼(Hugo Bergmann)以及作家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35)布罗德观察到了爱因斯坦“那种自我封闭式的罕有的性格特点”,他还以爱因斯坦为原型创造了一个文学形象,其特征是“总是带着几分严厉和冷酷无情,毫不犹豫地在世界面前径直展现他的灵魂,而人们所看到的,却是其灵魂的纯洁、完美无瑕的表面”。参见菲利普·弗兰克:《爱因斯坦传》,第39页。等人成了朋友。1917年《贝尔福宣言》(BalfourDeclaration)发表以后,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积极与爱因斯坦接触,想借助名人效应推进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联盟领导人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曾与爱因斯坦多次交往,他感受到爱因斯坦对犹太复国主义态度的显著变化,正如爱因斯坦的自我认知:“从做人的态度上说,我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作为犹太人,我赞成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努力。”爱因斯坦还强调说是“德国的反犹主义浪潮”唤醒了他的“犹太民族感情”,也成为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动机”。(36)Fred Jerome, Einstein on Israel and Zionis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9,pp.10-11.1919年前后,有朋友写信询问爱因斯坦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爱因斯坦的答复是:“我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很热衷,但我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民族在此回归家园,我无意移民巴勒斯坦,我所感兴趣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大学。”(37)Ze’ev Rosenkranz, Einstein Before Israel: Zionist Icon or Iconoclast? p.70.1921年4月,爱因斯坦在纽约发表讲话,他说道:“我们犹太人(必须)再一次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存在,并且必须重新获得我们民族兴盛所需要的自尊。我们必须学会再一次热情地宣布我们对祖先和历史的忠诚;我们必须再一次以一个民族的姿态承担起旨在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任务。仅以个人身份推动人类文化发展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着手去干那些只有民族族群才能完成的任务。也唯有如此,犹太民族才能重新恢复起社会的健康发展。”(38)芭芭拉·沃尔夫、泽夫·罗森克兰茨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永远的瞬间幻觉》,第142页。1931—1932年,爱因斯坦在访美期间,多次重申“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共同体必须着力实现先辈在《圣经》中确立的社会理想,同时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共有的现代精神生活的重镇。为此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所大学是当代犹太复国组织最重要的目标之一”。(39)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第334页。
第二,坚持“双民族国家方案”(Bi-national Solution)。《贝尔福宣言》指出:“英皇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National Home)”,但并没有界定“民族之家”的内涵。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犹太世界、英国和阿拉伯世界中产生了严重分歧,贝尔福本人最初的表述也只是“在英美或其他国家保护下建立一个民族文化中心和民族生活的集中地”。也正因为如此,《贝尔福宣言》被称作“20世纪最模棱两可、最富有争议性、也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文件”。(40)Martin Kramer, “The Forgotten Truth about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Mosaic,Jun 5, 2017,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forgotten-truth-about-balfour-declaration, 2021年10月2日。1897年的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对“民族之家”的解释是:“得到公众承认、受法律保护的‘犹太民族之家’,即民主主义语境下‘犹太人的实体国家’。”爱因斯坦对此并不认同。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诸多流派中,爱因斯坦认同以阿哈德·哈姆(Ahad Ha-am)为代表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精神家园”和“克服民族主义缺陷的模范社会”。当时,爱因斯坦与阿哈德·哈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及当时的犹太代办处主任阿瑟·鲁宾(Arthur Ruppin) 一起主张“双民族主义方案”,强调“如果犹太人不与他们的邻居友好相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工作将会建立在流沙上”。认为犹太人的目标必须是与阿拉伯人一起建立进步的文化社区。
1921年,爱因斯坦接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哈依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的邀请,到美国为建立希伯来大学筹款,其所到之处激起了很大反响,而爱因斯坦为希伯来大学筹款的努力一直持续到他去世。(41)Israel Kasnett,“Albert Einstein and Israel,”Ledger Online,March 26,2019, http://www.jewishledger.com/2019/03/albert-einstein-israel/,2021年7月13日。1923年,爱因斯坦访问巴勒斯坦为希伯来大学成立发表演讲,这也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巴勒斯坦之行。尽管他对故土具有深厚的感情,但在建国问题上,他与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派产生了分歧,坚决反对欧洲式的民族国家对少数族裔的忽视,认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共同生活才是最终目标。1930年1月28日,爱因斯坦在致巴勒斯坦阿拉伯报纸《巴勒斯坦》(Palestine)的编辑阿兹米·爱尔-纳沙什比(Azmi El-Nashashibi)的信中写道:“人类的未来必须建立在各国人民亲密团结的基础上,而且必须克服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地区的未来只能建立在两个民族都以此国家为家园并和平合作的基础上。基于这个原因,我期望伟大的阿拉伯人民能够真正理解犹太人在犹太教的古老发源地上重建他们民族家园的需要;我期望通过共同努力能够找到让大量的犹太人在这个国家定居的方法……我认为两个民族不应该彼此仇恨和互不信任,而是在彼此的国家和文化事业上相互支持并且寻求同情合作的可能性。”(42)芭芭拉·沃尔夫、泽夫·罗森克兰茨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永远的瞬间幻觉》,第149页。1934年前后,爱因斯坦再次强调:“我非常愿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而不希望创立一个犹太国”。(4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第19页。到二战爆发前夕,爱因斯坦又在一次逾越节晚宴上表示:“基于我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解,我不太接受建立一个拥有边界、军队和世俗权力的犹太国的概念。”(44)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p.520.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标志着爱因斯坦“双民族国家”理想的破灭,他曾经对朋友说:“不管是出于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的考虑,我从来不认为建国是个好概念。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有战斗下去。”(45)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0页。
第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20世纪上半叶,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阿以冲突越来越明显,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46)1944年,他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阿拉伯史学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围绕巴勒斯坦的历史权利展开了激烈辩论,爱因斯坦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尤其是恐怖主义行为有很多批判。参见张腾欢:《谁拥有巴勒斯坦:爱因斯坦、卡勒与希提关于犹太民族权利的争论》,《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5期。犹太阵营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用“马卡比精神”占领巴勒斯坦,尤其是以兹维·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最为激进,主张以武力夺取巴勒斯坦,这种状况使爱因斯坦非常忧虑。1929年,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定居点的事件后,爱因斯坦对魏兹曼说必须要警惕“普鲁士式的民族主义”,“假如我们没有找到和阿拉伯人诚实合作与诚实协商的途径,那么我们就并未从我们两千年来所遭受的苦难中学会什么,那么我们就活该承受即将加于我们的命运”。(47)弗里茨·斯特恩:《爱因斯坦恩怨史》,方在庆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第251页。居住美国期间,爱因斯坦在多种场合阐明自己的观点:英国人的分而治之为巴勒斯坦问题埋下了祸根,英国人所谓的“分治”是一种出于私欲的“帝国动机”,也是“奸诈手段”的淋漓表现。他一方面批判阿拉伯人的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也深切担忧犹太阵营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怕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行列里发展起来的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损害——会持续下去,甚至在没有犹太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48)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论犹太人问题》,第19页。以色列建国后,爱因斯坦依然为巴以民族的和平相处而呼吁,强调能否克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犹太人能否在巴勒斯坦真正立足的关键点,“对于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阿拉伯人民,以制度给予完全平等……我们对阿拉伯少数民族采取的心态,正是犹太民族道德标准的真正试炼”。(49)弗雷德·杰罗姆:《爱因斯坦档案》,第140页。
1948年12月4日,在亚博廷斯基的追随者、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代表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访问美国前夕,爱因斯坦与阿伦特等犹太知名人士向《纽约时报》联名致信,信中列举了犹太右翼势力所犯下的一些罪行,如屠杀阿拉伯人的“代尔亚辛事件”(Deir Yassin),称他们具有“纳粹式法西斯主义者的明显特征”、把“伊尔贡”(Irgun)定性为“恐怖主义的、右翼的、沙文主义的组织”,认为贝京所宣扬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大杂烩”。(50)AlbertEinstein, “Einstein Letter Warning of Zionist Fascism in Israel,”http://wilsonweb.physics.harvard.edu/HUMANRIGHTS/Einstein_Letter_Warning_Of_Zionist_Facism_In_Israel.html,2021年3月3日。正是由于不赞同犹太人以及以色列国家在建国前后的一系列民族主义立场,爱因斯坦与以色列国家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1952年11月,魏茨曼总统去世后,希伯来语日报《晚报》(Ma’ariv)总编阿兹列尔·卡勒巴克(Azriel Carlebach)发起一场公众运动,敦促以色列政府将总统职位授予爱因斯坦。11月17日,以色列驻美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正式致函爱因斯坦,表达希望其担任总统的意愿。18日爱因斯坦向政府正式回函婉拒了邀请:“对于以色列国授予我这个职位我不胜感激,但又同时感到诚惶诚恐难以接受,我一生都在与客观物质打交道,因此在正确地处理人民的事务和发挥管理职能方面缺乏天生的禀赋和实际的经验。”(51)Israel Kasnett,“Albert Einstein and Israel,”Ledger Online,March 26,2019,http://www.jewishledger.com/2019/03/albert-einstein-israel/,2021年7月13日。他私下说过:“要是我当总统,三五不时我就得说些以色列人民不爱听的话。”(52)弗雷德·杰罗姆:《爱因斯坦档案》,第140页。虽然拒绝了总统职位,但爱因斯坦对于以色列国家的情感与关切一如既往。1955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在以色列独立7周年纪念日的演讲稿中,提及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冲突、共产主义阵营与所谓自由世界的对峙、“老式的争霸势力的斗争”“被煽动起来的政治激情”“战争与毁灭的风险”“阿拉伯人的敌对”及“恐怖主义的根源”等。(53)Fred Jeromeand Rodger Taylor, 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 pp.227-228.这篇演讲稿搁笔于4月13日爱因斯坦重病期间,5天之后即4月18日,爱因斯坦走完了他76岁的人生旅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也成了他坎坷人生的谢幕词。爱因斯坦生前非常关注希伯来大学,但由于不喜欢希伯来大学中的民族主义氛围,也从未在大学就职。但1950年他已立下遗嘱,把自己的手稿交由希伯来大学管理,后来希伯来大学专门建立了爱因斯坦档案馆。(54)爱因斯坦去世后,围绕他遗稿的出版问题,普林斯顿出版社与希伯来大学之间产生了很大争议,参见M.J.Klein, A.J.Kox, and Robert Schulman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ublisher’s Foreword, p.Ⅺ.
爱因斯坦对民族主义,尤其是披着爱国主义外衣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他在《时代的继承者》一文中提出了“人类共同体”(Human Community)的概念,强调知识与文明的进步必须克服族群偏见。他写道:“知识和文明的进步只不过是继承祖先的劳动成果……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严重灾难却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觉。我们看到,为了让人类遗产成为祝福而不是诅咒……必须克服民族与阶级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有当他达到这样的高度时,才能为改善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做出贡献。”(55)原文出处不详,但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认为,很可能写于1931年前后。参见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第274页。在对德国心灰意冷流亡到美国后,面对同样充斥着种族主义的氛围,爱因斯坦着眼于美国所宣称的立国之本“自由民主”,痛陈种族主义的种种问题,毫不避讳地揭示其对道德、精神和普世价值的巨大伤害。而在面对犹太人问题上,尽管爱因斯坦不懂希伯来语也不信仰犹太教,但并不妨碍他对犹太民族怀有浓厚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爱因斯坦又超越了单纯的犹太民族和犹太国家情感,尤其是对阿拉伯人境况的关注和对各民族平等的追求深刻体现出他的世界主义的理想。爱因斯坦的思想认知不仅真切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世界和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辉煌,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所建构的“全球治理体系”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罗素生前曾这样评价道:“在所有我所知道的公众人物中,爱因斯坦是最使我衷心敬佩的人。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人……在滑向战争的世界中,他挺身为和平而奋斗;在疯狂的世界中,他保持清醒;在狂热盲目的世界中,他自由开明。”(56)方在庆:《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第103页这一评价在今天看来依然精准且耐人回味。但不可忽视的是,爱因斯坦不是圣人,他的精神世界是复杂、多元的,甚至是矛盾的,尤其是他长期生活在欧洲,对东方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因此他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体现出明显的认知局限。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兹维·罗森克朗兹(Ze’ev Rosenkranz)整理的《爱因斯坦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展现了爱因斯坦从西班牙旅行到中东、经过斯里兰卡到达中国和日本的旅行见闻,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表达出一种刻板印象和片面、偏激的描述,(57)参见Ze’ev Rosenkranz, 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The Far East, 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129, 193.说明这位“人文主义偶像”的思想中同样有知识盲点与认识误区。随着爱因斯坦私人文献的进一步披露,这些方面恰恰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与关注的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