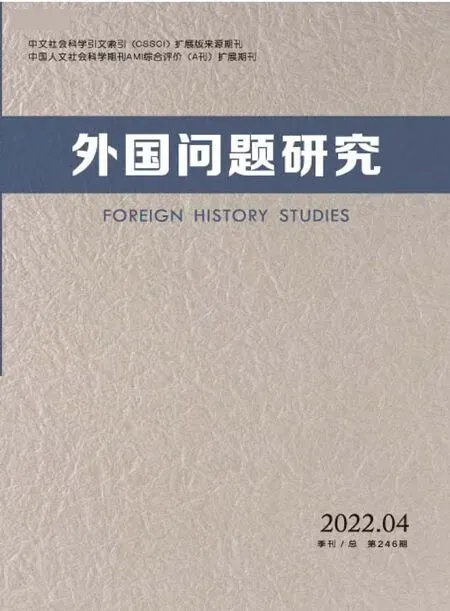疾病、死亡与早期美国南部信仰格局的改变
丁见民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美国南部在早期历史上与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尤其是加勒比与巴西相似,甚至被看作加勒比地区的北部边缘。这一地区的种植园与温暖湿润的气候,为蚊虫以及水生寄生虫的滋生提供了一种极为适合的环境。蚊虫传播类疾病——尤其是疟疾与黄热病——以及水生寄生虫导致的痢疾,在当地温暖而潮湿的气候中肆虐,而寄生虫如钩虫以及几内亚龙线虫的感染在田间无处不在。南部肆虐的各种疾病,或以暴风骤雨式的瘟疫肆虐,或以悄无声息的病痛困扰民众,不同程度地塑造着南部社会。如果从疾病医疗史的角度考察美国早期南部信仰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南部肆虐的各种疾病对于依靠从英国派遣传教士的安立甘教会的影响与冲击,虽然是渐进式的却极为深远,在18世纪推动着南部信仰格局的改变。
南部疾病医疗研究是美国疾病医疗史中最为深入的领域之一,中外学界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众多。与美国南部史研究类似,南部医药研究主要是围绕黑人和奴隶制开展。(1)主要著作参见William Dosite Postell, The Health of Slaves on Southern Plantation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1; Todd L. Savitt, Medicine and Slavery: The Diseases and Health Care of Blacks in Antebellum Virgini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8; Kenneth Kiple and Virginia H. King, Another Dimensions to the Black Diaspora: Diet, Disease, and Rac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harla M. Fett, Working Cures: Healing, Health, and Power on Southern Slave Plantation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即使是在关于性别、(2)Marie Jenkins Schwartz, Birthing a Slave: Motherhood and Medicin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社会独特性(3)Todd L. Savitt and James Havery Young, eds., Disease and Distinctiveness in the American South,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乃至边疆地带(boderlands)(4)Mark Allen Goldberg, Conquering Sickness: Race, Health,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Texas Borderland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6.的研究成果,也会频频涉及种族和黑人等问题。毫无疑问,奴隶与奴隶制是美国南部社会的典型特征,确实给后者打上了深刻烙印。不过,其他的角色比如医生、传教士等也或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这一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5)相关成果参见Thomas J. Ward, Black Physicians in the Jim Crow South,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2003; Steven M. Stowe, Doctoring the South: Southern Physicians and Everyday Medicin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中外学界关于疾病与美国南部传教士的研究较少,两位学者的论文关注到疾病对传教士的影响及其反应,(6)Bradford J. Wood, “‘A Constant Attendance on the God’s Alter’: Death, Disease, and the Anglican Church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1706-1750,”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100, No. 3 (July 1999), pp.204-222; 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18, No. 3 (August 1952), pp.289-302.也有些学者在论及其他主题时或多或少有所涉及,(7)主要著述参见John Duffy, Epidemics in Colonial America,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3; H. Roy Merrens and George D. Terry, “Dying in Paradise: Malaria, Mortality, and the Perceptual 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outh,”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50, No. 4 (November 1984), pp.533-550; Dana P. Arnema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6; 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不过这些成果却没有系统地从南部信仰格局变动的角度考察这个课题。故此,本文以当时的各种信件、报告和早期叙事材料为基础,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聚焦各种疾病对美国安立甘教会传教士的冲击,分析疾病的影响与传教士的应对如何改变美国南部的信仰格局,促使南部信仰格局实现本土化转型。
一、南部疾病与外来传教士的病痛困扰
17—18世纪北美南部安立甘教会的大多数传教士是由英国的外国福音传播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派遣的。他们从欧洲远涉重洋来到北美,面临着当地各种疾病的威胁。流行病学家指出,任何地方的新来者对于当地各种疾病的抵抗力,都比不上本土人。因此,传教士在到达北美南部的最初数年中,不出意料地出现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事实上,他们的疾病发作被看作殖民地生活的开始。传教士面对的疾病威胁首先是给南部社会带来恐惧的急性传染病——黄热病。1706年查尔斯顿暴发一种被叫作“瘟疫性热病”(pestilential fever)的流行病,其元凶可能就是黄热病。约翰·奥尔德米克森(John Oldmixon)写道:“近期的疾病暴发于1706年,导致查尔斯顿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民众死亡。”(8)John Oldmixion, The British Empire in America, London: Printed for J. Brotherton and J. Clarke, 1741, Vol.1, p.515.外国福音传播协会的一位传教士恰恰在疾病暴发期间来到南卡罗来纳。他报告说:“9月20日……当地正在流行一种瘟疫性热病,对初来乍到的欧洲人尤为致命。我亲爱的朋友、你们真诚而忠实的传教士塞缪尔·托马斯(Samuel Thomas)先生于1706年10月10日死于这种疾病。”(9)John Duffy, “Yellow Fever in Colonial Charleston,”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Vol.52, No. 4 (October 1951), p.192.显然,托马斯在到达北美后即患上黄热病并死亡。面对黄热病的威胁,传教士怀疑他们是否还有幸存的机会。1738年12月,圣乔治教区的斯蒂芬·罗(Stephen Roe)报告说,从去年夏季开始,他就面临着间歇热、痢疾、咳嗽和吐血的威胁;在此后的两年中他“每时每刻不在遭受着各种热病的困扰”,以至于他可能难以活下来了;“一种热病要么持续性地要么间断性地困扰着我,让我倍感煎熬”。(10)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p.59.1745年查尔斯顿黄热病暴发期间,传教士依然有感染的病例出现。外国福音传播协会的一位牧师于1745年11月报告说:“现在以及此前的一段时间内,查尔斯顿面临着一种恶性疾病即黄热病的困扰。在疾病暴发期间,民众骤然死亡……”他补充说,他的一位同事患病严重,可能也感染了黄热病。(11)John Duffy, “Yellow Fever in Colonial Charleston,” p.195.
在早期北美南部,疟疾几乎无处不在,对初来北美的安立甘传教士造成了更大的困扰。疟疾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由间日疟原虫引起的,患者病情较轻;还有一种镰状疟原虫引发的,患者病情危重。早在1687年,弗吉尼亚传教士约翰·克莱顿(Rev. John Clayton)将间歇热列举为攻击英国土生人口的首要疾病,而该殖民地另外一位成员写道,他的妹妹已经出现2—3次疟疾发作,她感到她的“季节适应”(seasoning)已经平稳度过。(12)“Letter to Capt. Henry Fitzhugh, July 18, 1687,”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Vol.3, No. 2, (October 1895), p.161.传教士弗朗西斯·勒乔(Francis Le Jau)本来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信心满满,但是在1706年来到北美后却发现,疟疾成为困扰他一生的麻烦。1708年9月,他宣称,16个月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极为糟糕,他的家人总计9名成员也都同时患病。1715年他估算得出,在来到北美的10年中他有6年都在患病。(13)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p.59.
大部分传教士报告提及的是轻型疟疾,但来自圣约翰教区的一位传教士罗伯特·莫尔(Robert Maule)表明,他所患为恶性疟疾。1709年他报告说:“我患上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连续三个月持续受到疟疾的折磨,并以最为剧烈的腹痛结束。这种疾病如此严重,以至于我觉得它会带着我走向末日。”(14)H. Roy Merrens and George D. Terry, “Dying in Paradise: Malaria, Mortality, and the Perceptual 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outh,”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50, No. 4 (November 1984), pp.541-547; Gerald N. Grob, The Deadly Truth: A History of Disease in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68.1716—1717年,南卡罗来纳的两位传教士也抱怨疟疾的存在。威廉·布尔(William T. Bull)于前一年宣布“这里一个极为健康的夏季预示着一个疾病流行的秋季”,寒热相间的疟疾在8—9月份一直困扰着他。另外一位牧师威廉·盖伊(William Guy)遭到同一种疾病的严重困扰,以至于他决定在次年11月到新英格兰去疗养,但是这种疾病的“剧烈暴发”严重削弱了他,使得他无力启程。1717年,布尔再次遭到这种疾病的打击。他向协会解释未能及时回复信件的理由时说:“8月份一种寒热相间的疟疾降临到我身上,病情一直持续到9月底,大大削弱了我的身体。”在此后的数年中,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报告说,他们患上过疟疾。(15)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292.
1720年代以后,传教士患病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1725年11月5日,布莱恩·亨特(Brian Hunt)写道,我“在这里患上寒热相间的疟疾,导致我身体虚弱,这是它的再次发作”。托马斯·默利特(Thomas Morritt)于1727年夏季描述了他所患疾病的细节:“起初我病发于胃部剧烈的翻腾以及间歇性的腹泻,迄今已经持续6周。”1730年代,传教士患病的情况似乎更为严重。1734年11月6日,塞缪尔·加尔登(Samuel Garden)在信件附言中解释了卡罗来纳疟疾暴发的普遍性:“我们整个殖民地都经历了一个疾病肆虐的秋季,大多数牧师都患了病,不过我自己正在从一种顽固的间歇性热病中康复。”1738年秋季,一种疟疾热病在卡罗来纳流行,一直到冬季还威胁着民众的健康。一位传教士写道,他“自从8月4日以来就患上一种名叫疟疾热的严重疾病,一直持续到12月末。没有人认为我能活下来,但是感谢上帝我正在康复”。(16)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p.292-293.甚至到1760年代,从英国来的传教士依然面临着疟疾的打击。当时北卡罗来纳一位传教士说:“我和我的家庭成员都在面临着一种严重的疾病即疟疾的折磨,这种折磨通常被称为季节适应。所有新到者都会面临这种折磨,它开始于月初,一直持续到12月末……”(17)Joseph I. Waring,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South Carolina, 1670—1825, Columbia: The South Carolina Medical Association, 1964, p.2.
经常困扰安立甘传教士的第三种疾病是痢疾。从英国来的传教士们经常患上急性病菌性或慢性(阿米巴)痢疾。前述的传教士勒乔于1706年来到卡罗来纳后很快患上痢疾,直到1717年去世都未能完全摆脱它。1708年3月13日,他在一封信件中写道:“从1707年6月到9月28日米迦勒节(Michaelmas),我持续发烧,11天后变成间歇性发烧,最后变成痢疾和感冒……这种病痛已经反复发作7次,我一直都没有完全康复。” 在1708年夏季的通信中,他告诉上级说:“在过去的16个月中,我的病情根本就没有好转……去年夏季,我患上另外一种更为严重的痢疾,它使得我在家卧床3个月。”(18)Frank J. Klingberg, ed., The Carolina Chronicle of Dr Francis Le Jau, 1706—171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6, p.34.1710年7月5日,传教士吉迪恩·约翰斯顿(Gideon Johnston)告诉协会秘书长说:“伍德先生(一位同事)患上痢疾且病情严重,极为危险。这种疾病是当地气候所导致的疾病之一,在今年对许多人都极为致命。”(19)Dana P. Arnema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6, p.230.
其他传教士也同样为痢疾所困扰。1727年,托马斯·莫里特抱怨说,他出现严重腹痛和腹泻并断断续续拖延六周。他的身体变得如此虚弱显然是由于脱水和电解质失衡所致,以至于他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履行他的日常宗教职责。他报告说:“今年这些疾病对许多人来说是致命的。”(20)Dana P. Arnema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p.233.1763年,约翰·麦克道韦尔(John Macdowell)提供了对这种疾病或许是最为生动和形象的描述。他宣称:“我所患疾病是一种顽固性腹泻,没有任何药物或者医生能够治愈,它仍然在继续。”尽管医生建议这位传教士改变环境,恢复身体健康,但是他自己却发现:“在过去的四个月中,我没有一天或者一夜能够好好休息。我屡屡患上这种疾病,尤其是当我感冒时情况更为糟糕。现在它对我的影响已到如下地步:我一个夜晚里不得不起夜15次以上,我的肠胃、背部以及腰部都出现了最为令人苦恼的疼痛。”(21)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p.295-296.
在18世纪的北美南部地区,安立甘传教士所患疾病不仅仅局限于上述三种,败血病、寄生虫病等其他疾病也威胁着传教士的生命。1738年斯蒂芬·罗在写给福音协会的信中描绘了一幅传教士处境悲惨的画面:“自去年8月开始,我患上一种持续不断的热病,一种间歇性热病数次复发,还患上一次痢疾、一次感冒,最后一次患病甚至严重到吐血。”难怪吉迪恩·约翰斯顿说,这位传教士的身体成为“各种疾病的展览区”(Scene of diseases)。(22)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p.52.
二、南部疾病与外来传教士的死亡
患病的传教士面临着不同的命运选择,其中病情严重者最终走向死亡。这无疑是疾病对传教士最为明显的打击。第一,黄热病是导致传教士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1699年查尔斯顿的黄热病瘟疫引发普遍的恐惧,当地的5名传教士染病而亡。(23)“Extract of a Letter from Hugh Adams to Samuel Sewall, Feb, 23, 1700,” Diary of Samuel Sewell, April 22, 1700, in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5th Series, Vol.6, 1879, pp.11-12.其中就包括波士顿著名牧师科顿·马瑟的叔叔。科顿得知,查尔斯顿的所有牧师都已经死亡,尤其是他的叔父也成为这场最具杀伤力的灾难的牺牲品。(24)“Cotton Mather to Mrs. Joanna Cotton, Boston, August 23, 1699,”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4th Series, Vol.8, 1868, pp.403-404.1702年以后,外国福音传播协会保存了安立甘教会传教士患病和死亡的大量资料。1702年该协会第一位到达卡罗来纳的安立甘传教士塞缪尔·托马斯(Samuel Thomas),于1706年死于黄热病。1733年,亚历山大·加尔登(Alexander Garden)出任南卡罗来纳安立甘教会牧师,服务于空缺已久的圣詹姆斯·桑蒂教区,但是他在到达后不久就患上一种热病,并在四天后死亡。(25)George W. Williams, “Letters to the Bishop of London from the Commissaries in South Carolina,”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78, No. 1 (January 1977), pp.214-217.
第二,疟疾也是导致传教士丧命的元凶之一。罗伯特·莫尔从1709年就开始备受疟疾折磨,数年后他死于一种“肺痨和持久性热病”。另外一位牧师于1710年在查尔斯顿提及疟疾。他报告说:“这种疾病是在今年气候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对许多人都是致命的。”(26)H. Roy Merrens and George D. Terry, “Dying in Paradise: Malaria, Mortality, and the Perceptual Environment in Colonial South,” p.542.传教士勒乔在南卡罗来纳任职的11年时间内从未摆脱疟疾的困扰,他的健康日益恶化。到1717年,他已经卧床不起,无法说话,最终在9月份去世。(27)Dana P. Arnema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p.118.几乎在同一时期,另外一位传教士很高兴地宣布,他和家人虽然都经历了“疟疾”的“严重发作”,但已经完全康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于次年秋季死于这种疾病。(28)John Duffy, “The Impact of Malaria on the South,” in Todd L. Savitt and James Harvey Young, eds., Disease and Distinctiveness in the American South,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p.35.第三,痢疾也是患者病痛与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710年,吉迪恩·约翰斯顿报告说,痢疾“在今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我对它的恐惧程度远胜其他任何疾病”,它已杀死约翰斯顿的数位同事。(29)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p.41.当时信件中偶尔出现的一条便签可能表明一个传教士的命运。据报告,1751年罗伯特·斯通(Rev. Robert Stone)“在患上血痢很短时间后”死亡。(30)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296.
最后,扁桃体周炎(quinsy)、斑疹伤寒、铅中毒等其他疾病也会导致传教士丧命。传教士威廉·盖伊1724年3月26日写信给协会秘书长报告说,他“患上了一种扁桃体周炎(这是一种对当地居民极为致命的疾病),但是我几乎完全康复”。(31)Dana P. Arnema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p.269.他和另外一位传教士斯蒂芬·罗在1734年给秘书长报告说,他们分别患上一种“持续性热病”(constant fever)和一种“稽留热”(continued Fever)。学者约翰·达菲(John Duffy)认为,这两位传教士所患疾病可能就是斑疹伤寒。(32)John Duffy, Epidemics in Colonial America,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200, 218, 222.还有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则是铅中毒,这种铅中毒在1709—1712年间南部低地地区尤为盛行。吉迪恩·约翰斯顿就遭遇了铅中毒。1709年2月18日,勒乔告诉英国上级说:“代理主教约翰斯顿在过去数月中病情严重,但是他有望康复。”在同一天的第二封信件中,他写道:“代理主教约翰斯顿病情严重,一直持续五个月……在过去四个月中我们面临着暴风雨,许多人都患上了奇怪疾病,他们无法控制四肢,面临着难以忍受的疼痛……”(33)Frank J. Klingberg, ed., The Carolina Chronicle of Dr Francis Le Jau, 1706—1717, pp.49, 52-53.
需要指出的是,长老会和公理会也像安立甘教派一样,对牧师的要求很高。在殖民地时期,他们的大部分牧师都是来自新英格兰,其余则来自英国。这些教派的传教士和安立甘教士一样,很容易感染当地的疾病。查尔斯顿公理会的数名牧师在履职不久后去世。1691年到达的本杰明·皮尔庞特(Benjamin Pierpont)比其他大多数人都幸运,但也于1698年可能死于天花。他的后继者休·亚当斯(Hugh Adams)遭遇一系列疾病的打击,他自己列举出来的疾病就有腐烂性热病、间日疟、水肿、猩红热、腺鼠疫、痛风以及其他疑难病症。亚当斯很快辞职返回英格兰。他的替代者约翰·科顿(John Cotton)遭遇1699年的黄热病流行,在到达数月内死亡。在来到北美南部14年后,牧师内森·巴西特(Nathan Bassett)于1738年死于天花,其他4位殖民地时期的传教士履职2—5年后就死去了。殖民地时期最后一位公理会牧师威廉·坦南特(William Tennent)于1777年死于热病,去世时年仅37岁。(34)Daniel J. Tortora, ed., “A Faithful Ambassador: The Diary of William Hutson, Pastor of the Independent Meeting in Charleston, 1757—1761,”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Vol.107, No. 4 (October 2006), pp.273-306; Vol.108, No. 1 (January 2007), pp.32-100.
传教士因病死亡的总人数已经难以清晰统计,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卡罗来纳传教士因病死亡的数字窥见一斑。1700—1750年间,大约50名传教士被外国福音传播协会派遣到南卡罗来纳。其中,17人在到达北美的十年内死亡,占总人数的34%;4人在该殖民地生活超过20年,占8%;21人最终辞职,占42%。在辞职者中,半数将健康不佳列为辞职原因,几乎所有人都抱怨他们出现不同程度的患病情况。在北卡罗来纳,尽管传教士规模没有那么大,情况也不容乐观。记录表明,1700—1750年间有12名传教士在该殖民地服务,其中3人在来到当地5年内死亡,另外5人由于患病辞职。因此,在来到该殖民地5年时间内,12名传教士中的8人或者死亡或者由于患病辞职。(35)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p.301-302.也就是说,18世纪上半期外国福音传播协会派遣到整个卡罗来纳的传教士总计62人。其中27人在来到后5年内或者死于患病或者由于患病辞职,占总人数的43.6%。如果把时间延长到十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5人,占总人数的比例为56.5%。需要注意的是,疾病毫无疑问在他们的辞职中发挥了作用。(36)John Duffy, Epidemics in Colonial America, p.241.
此后传教士因病死亡的现象依然存在。1766年8月当查尔斯·伍德梅森(Charles Woodmason)到达南卡罗来纳出任安立甘传教士后,他发现许多传教士死于各种热病,当年夏季有4名安立甘传教士和3名长老会传教士死亡。这促使他写信给伦敦主教说:“这个国度曾是传教士的坟墓,这个夏季情况尤为严重。”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列举了近期死亡的28名安立甘教会、清教徒和路德教会的牧师名字。(37)Richard h. Hooker, ed., The Carolina Backcountry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and Other Writings of Charles Woodmason, Anglican Itineran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3, pp.4-5, 200-201.美国独立后,或许是由于更多的传教士出生于北美本土,南部传教士的死亡率降低,但是那些来自其他地区的传教士仍然面临着极大危险。1817年,黄热病夺去了查尔斯顿数位传教士的生命,其中包括圣公会主教西奥多·德翁(Theodore Dehon)。
三、外来传教士的多重选择
各种疾病对传教士的心理造成严重打击,他们的心态开始发生某种变化。约翰斯顿说出了很多传教士的心声,他评论了“我自己的各种情况,以及我后来所观察到的许多情景,疾病和死亡导致我的思想出现混乱和困扰”。外国福音传播协会派到南卡罗来纳的第一位传教士塞缪尔·托马斯,在到达数月后遭遇一场严重的热病,故而他“已经对生活感到绝望”。1716年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疾病后,勒乔欢呼道:“我有时在想,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患病,但是上帝却希望我再经历更多的磨难,我已经为永恒做好准备。”不过,也就是在同一封信中,他对未来感到悲观:“我的力量在流失,我想我可能时日不多。”(38)Bradford J. Wood, “‘A Constant Attendance on the God’s Alter’: Death, Disease, and the Anglican Church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1706—1750,”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100, No. 3 (July 1999), p.209.这或许是这位著名传教士的心声。心态改变后的安立甘传教士从18世纪开始经常要求“换换空气”,到被认为更为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选择主要有三种:到巴巴多斯、百慕大或者巴哈马等风景优美的健康之地;短途迁移到当地另外一个教区或者到北美北部地区;返回英国。
传教士的第一种选择是到西印度群岛改换生活环境。1705年到南卡罗来纳担任牧师的安德鲁·奥奇里克(Andrew Auchileek)最终选择到百慕大任职。他在报告中解释说:“南卡罗来纳流行一种瘟疫性热病(黄热病),导致很多人死亡。”(39)Dana P. Arnema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p.209.1717年1月3日,勒乔写道:“极为不幸的是,我旧病复发,在三周内病情如此严重,以至于我认为我有生命危险。”因此他请求协会允许他暂时离开南卡罗来纳:“如果我的身体虚弱到需要换换空气,我恳请尊敬的协会让我离开数月到百慕大或巴巴多斯去……”两周后再次请求离开南卡罗来纳,以便于他能够从顽固疾病中康复。1717年3月18日,他在写给伦敦的信件中最后请求:“如果你们认为我在巴巴多斯等热带气候中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也能够改善我虚弱的身体状况,我很乐意按照命令到上级指定的地方去。”(40)Dana P. Arnema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pp.231-232.
他们的第二种选择是在北美各地迁移。安立甘传教士出于健康原因请求从低地地区的教区转移到高地地区或者山区,而到北部各地休养或者任职则是更佳选择。1744年塞缪尔·昆西(Samuel Quincy)在其家人健康遭到沉重打击、妻子和长子死亡后提出,尽管他认为整个卡罗来纳都是不健康的,希望转移到北部去,但是如果能到另外一个教区“换换空气也是可以的”。(41)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p.261.1747年4月,詹姆斯·莫伊尔(James Moir)写信给福音协会说:“去年秋季疟疾袭击了我。它是如此顽固,几乎无药可医,让我出现黄疸,毫无缓和征兆,故而除了到高地地区休养外别无他法。身在高地地区的我目前正在康复,从我患上的所有疾病中恢复过来。”(42)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294.1751年3月正当痢疾流行病在卡罗来纳肆虐时,威廉·兰霍恩(William Langhorne)到达当地的一个教区。次年,他在写给英国上级的信件中“请求尊敬的协会,在卡罗来纳疾病肆虐季节把我调到某个健康环境中工作……将我从多切斯特的圣巴塞洛缪教区(St Bartholomew’s Parish)调到圣乔治教区……这完全是出于我身体健康的考虑,圣乔治教区处于更有益于健康的环境中”。不过随后的信件中他抱怨说,他尚未收到任何答复。(43)“St Bartholomew’s Parish as Seen by its Rectors, 1713—1761,”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Vol.50, No. 4 (October 1949), pp.197-200.短途旅行的另外一个典型是,1765年7月安立甘教会传教士艾萨克·艾默里(Isaac Amory)决定离开他的圣约翰教区,而退却到更为凉爽的“山区”,直到8月末或者9月初才返回。(44)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pp.258-259.
对于南部传教士来说,能到气候凉爽的北部旅行或者居住生活是一种不错的选择。1736年,南卡罗来纳克里斯特教区的托马斯·莫里特以身体健康原因请求去北部旅行:“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内,我的健康状况极为糟糕。近期我又两次患上严重疾病,几乎危及我的生命。这些疾病使我的身体虚弱不堪,甚至不能履行我的职责。” 不久以后,他从该协会辞职。(45)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297.圣海伦娜教区的威廉·皮斯利(William Peasely)也同样请求转移到北部传教。他在1756年的信件中说:“我请求您了解,这个国度经常暴发的疟疾降临到我的身上,大大损害了我的健康。我请求协会将我派遣到北部的某个布道站……”(46)Dana P. Arneman, The Medical History of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p.120.还有资料记载,1767年6月8日,查尔斯顿传教士温伍德·塞尔詹特(Winwood Serjant)与其夫人乘船北上,其目的是到波士顿附近的坎布里奇圣公会教堂任职。(47)Carl Bridenbaugh, “Charlestonians at Newport, 1767—1775,” The South Carolina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Vol.41, No. 2 (April 1940), p.44.南部上层妇女安·麦尼考尔特(Ann Manigault)的日志也提及,传教士唐斯先生(Downes)及他人乘船前往费城。(48)Ann Manigault and Mabel L. Webber,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Mrs. Ann Manigault, 1754—1781,”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Vol.21, No. 1 (Jan. 1920), p.21, note 89.甚至到18世纪末期,从英国而来谋求牧师职位的传教士也不断迁移以躲避疾病。当查尔斯·凯莱布·科顿(Charles Caleb Cotton)来到查尔斯顿的第一个夏季,他为炎热、蚊虫和热病所困扰,从查尔斯顿逃到乡村高地,侥幸避免黄热病的感染,但也正是在那里他感染了疟疾。在发现当地气候极为不利于健康后,他于次年再次逃到安大略,并在那里出任安立甘教会的牧师。(49)“The Letters of Charles Caleb Cotton, 1798—1802,”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51, No.3 (July 1950), pp.140-142, 217-218, 220, 223-226.
对于来自英国的传教士,第三种选择即返回英国休养当然是上策。在整个18世纪,传教士们不断抱怨说,他们及其家人遭受着严重的“疟疾”病痛。那些病情严重者通常请求返回英国。1738—1742年间,南卡罗来纳有不少于6名传教士在写给其组织的信中表明他们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一位传教士宣称,他在过去7年中每年都会感染这种疾病;他们都说,他们不得不卧床数月,其中4位传教士请求返回。(50)John Duffy, Epidemics in Colonial America, pp.210-211.蒂莫西·米勒查普(Timothy Millechamp)在为安立甘教会服务14年后,因为身体健康欠佳而辞职。1745年10月15日,他报告说:“自从我来到这里后,除了一年外我在其他所有年份中都备受疾病困扰。面对它们对我身体沉重的打击,一旦我的身体健康需要,我必须离开这里返回家园。”次年,他因为“热病”暴发再次请求返回英格兰,但是英国福音协会并没有匆忙作出决定,而是在等待四年后才批准了他的请求。(51)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298.
到1760年代,返回英国的传教士不减反增。根据安·麦尼考尔特的日志记载,1765年初佐治亚牧师怀特菲尔德(Whitfield)经陆路前往费城,然后计划在六七月份动身前往英国。(52)Ann Manigault and Mabel L. Webber,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Mrs. Ann Manigault, 1754—1781,”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and Genealogical Magazine, Vol.20, No. 3 (July 1919), p.208, note 20.1768年4月26日,南卡罗来纳公报宣布:“上个周五,詹姆斯·格拉兰(James Crallan)……动身前往伦敦。詹姆斯·格拉兰是圣菲利普教区的布道者助理。”(53)Ann Manigault and Mabel L. Webber,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Mrs. Ann Manigault, 1754—1781,” p.11, note 14.1768年5月,麦尼考尔特再次提及:“牧师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及其夫人为了恢复他们的健康前往伦敦。”(54)Ann Manigault and Mabel L. Webber,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Mrs. Ann Manigault, 1754—1781,” p.11,note 19.
传教士出于健康原因要求离开北美殖民地,很多牧师选择离职回到英国,或者暂时离开牧师职位到其他地方恢复健康。这会进一步加重坚守职责的传教士的负担,使得他们更加难以圆满完成的自己任务,进而动摇南部安立甘教会的权威地位,为其他教派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协会官员亚历山大·加尔登拒绝牧师以“换换空气”为理由离开南部。他发现:“如果传教士的请求都得到批准的话,这里的每一位传教士都可以在夏季离开,未来夏季留下来的传教士不过2—3人而已。”(55)George W. Williams, ed., “Letters to the Bishop from the Commissaries in South Carolina (Continued),”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78, No. 4 (October 1977), p.298.
四、传教士患病死亡与南部信仰格局的本土化
外来传教士的患病、死亡和离职给坚守岗位的牧师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职责压力。本来,所面临的病痛就使他们很难完成最基本的职责。吉迪恩·约翰斯顿写道,失明和跛脚的双重打击使得他卧床不起,延缓了他递交报告的时间。尽管有时传教士会在患上严重疾病后完全康复,但也经常会面临某种程度的残疾和身体无力。在1736年的信件中,亚历山大·加尔登写道:“我重新患病已经将近25天……但是我却丝毫没有康复,以至于我无力拿笔写下我的名字。”(56)George W. Williams, ed., “Letters to the Bishop from the Commissaries in South Carolina (Continued),”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78, No. 3 (July 1977), p.242.更为麻烦的是,这些坚守岗位的牧师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当他们的数量不足时,他们感到有必要“竭尽全力地服务于职位空缺教区”。不过遗憾的是,牧师们通常无力满足所有教区的需要,相反他们不得不根据他们的健康状况和周围社会情况做出妥协。1717年9月,传教士哈兹尔(Hasell)沮丧地向协会写信说:“由于疾病肆虐,我们近期没有召集牧师全体大会。布尔先生在今年夏季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患有严重疾病;长期以来我都处于一种极度虚弱的萎靡状态,需要服用药物。” 1718年10月他仍然被一种“长期顽固性疾病”困扰,这种疾病使得他无力行使其各种职责。哈兹尔再次报告说,牧师们无法集会,因为他们的经常性集会地点查尔斯顿,“在过去的整个夏季都充斥着天花和恶性热病”。(57)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299.
传教士身体健康的恶化迫使那些坚守岗位的牧师经常走访空缺教区。尤其是当民众健康状况恶化之时,通常也是夏秋季节的疟疾多发时期,教区需求也大大增加。教会官员亚历山大·加尔登被迫将牧师的年度走访转移到春季,因为“这个殖民地的秋季通常是疾病多发时期”。(58)George W. Williams, ed., “Letters to the Bishop from the Commissaries in South Carolina (Continued),” p.213.他在1740年4月报告说:“许多天来,我只身一人应对这份职责,一天4—12个葬礼,许多病患要走访。让上帝高兴的是,在整个疾病流行期间上帝允许我身体较为健康。但是我很快就患上了原有的疾病,这让我感到疼痛难忍,几乎无力抓笔……”(59)William Howland Kenney, III, “Alexander Garden and George Whitefield: The Significance of Revivalism in South Carolina, 1738—1741,” The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71, No. 1 (January 1970), pp.296-297.
走访严重的病患可能获得丰厚的信仰回报,这促使传教士们能够忍受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经历。约翰斯顿不喜欢走访患者,因为“暴露在各种肮脏、难闻气味以及各种恐怖的现象之下,并非令人愉快的经历”,更为重要的是这可能会危及传教士的健康甚至生命。在1739年流行病期间,亚历山大·加尔登写道,他在圣菲利普教区没有得到其他牧师的帮助,因为那种疾病“被认为是具有传染性的”。罗伯特·斯莫尔(Robert Small)曾在克里斯特教区为加尔登提供了帮助,但他很快患病并在一周内去世。(60)George W. Williams, ed., “Letters to the Bishop from the Commissaries in South Carolina (Continued),” p.297.
即便牧师距离教区太远或者自己也患病,未能及时为死亡的民众举行宗教仪式或者提供安慰,但他们至少要为死者举行葬礼仪式。约翰斯顿发现:“一天三场葬礼,有时一天四场葬礼,现在都很常见,成为一种没日没夜的负担。”同样,加尔登写道:“一天埋葬5—10人,有一天埋葬11人……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在炎热的低地地区埋葬死者使得他们感到冗长乏味,不过对葬礼的熟悉使得安立甘传教士必须履行他们的职责。(61)George W. Williams, ed., “Letters to the Bishop from the Commissaries in South Carolina (Continued),” South Carolina Historical Magazine, Vol.78, No. 2 (April 1977), p.146; George W. Williams, ed., “Letters to the Bishop from the Commissaries in South Carolina (Continued),” p.215.患病和死亡导致牧师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1731年6月1日,丹尼尔·德怀特(Daniel Dwight)在一封信件中宣称:“自从1730年12月21日以来我患上了一种严重疟疾,已经无力履行我的职责。”(62)John Duffy, “Eighteenth-Century Carolina Health Conditions,” p.293.
传教士的患病、死亡和离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南部安立甘教经常会出现牧师职位空缺。伦敦管理者试图填补传教士的空缺,但是传教士的频繁死亡使得这种补充极为困难。到1716年,该协会已经为南卡罗来纳的10个教区派遣了传教士。不过,1717年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总督报告说,6个教区依然出现教职空缺,因为当地有4位牧师死亡,另有2位牧师转移到他处。另外,南部不利于健康的声誉也使得它很难招募到新的传教士以取代那些死者。正如一位传教士在1711年所说:“气候的致病性……会妨碍传教士来到这里。”难怪在1706—1750年间,南卡罗来纳各个教区牧师空缺的时间占1/4,每个教区牧师空缺时间平均超过11年。(63)Bradford J. Wood, “‘A Constant Attendance on the God’s Alter’: Death, Disease, and the Anglican Church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1706—1750,” pp.207-208.
18世纪初期南卡罗来纳安立甘教会的大多数传教士都是由外国福音传播协会提供。从英国补充死亡或者离职的牧师空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可能需要数月,而新的牧师也可能死亡、离开或者被调离。各教区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过程:教区传教士职位空缺或者传教士患病严重以至于无法履行职责。教会官员威廉·特雷德韦尔·布尔(William Tredwell Bull)于1718年写道,在过去的两个月内,他几乎无法履行其职责:“在这个疾病肆虐国度,我的身体在患上任何疾病后都恢复得极为缓慢,我担心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呼吁英国总部派遣更多的传教士来北美。1751年,弗雷德里克王子教区报告说,教区长已经死亡,而他们也无法从邻近教区获得任何帮助,因为那里也出现了教职空缺。三年前官员加尔登也报告说,他和他的助理都患病在身,请求该协会另外派遣人员协助他,如果他去世的话派人取代他。(64)Peter McCandless, Slavery, Disease, and Suffering in the Southern Lowcountry, p.52.
各种疾病的盛行瓦解了民众对包括安立甘教会在内的各个教派的信心,进而减少了信徒数量。南部不利于健康的环境阻止了安立甘教会的牧师们满足教众的各种期许以及各种信仰需要。因为疾病盛行以及牧师的缺乏,许多南部信徒放弃对这种有组织宗教的依赖。这也解释了1728年布莱恩·亨特所写:“一些教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信奉上帝,那就是待在自己家中而不与外界联系。”(65)Bradford J. Wood, “‘A Constant Attendance on the God’s Alter’: Death, Disease, and the Anglican Church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1706—1750,” pp.218-219.1747年,约翰·福代斯(John Fordyce)写道:“自从我来到这里,除了一两个家庭外其他几乎所有家庭都有成员死于这种疾病,尤其是大部分死者都是户主。这大大减少了我的教众人数。”(66)William Curri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Climates and Disea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Printed by T. Dobson, 1792, p.389; David Ramsay, The History of South Carolina From Its First Settlement in 1670 to the Year 1808, Vol.2: Charleston: Printed by David Longworth, 1809, p.84.
在此情形下,北部清教教派乘虚而入,迅速补充传教士,并对各种疾病盛行和人口死亡做出积极应对。一方面,清教教会与英国安立甘教会相比拥有一个主要的优势,那就是他们能够更迅速地补充传教士。北美殖民地安立甘教会牧师的任命需要远在英国的主教批准,这意味着北美安立甘传教士多来自英国,等待时间很长。相比之下,清教教派则更容易在北美招募到牧师,因为其牧师人选不需要英格兰主教的任命。另外,在众多新教派别中,浸礼会是最为成功的典型。他们取得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传教活动孜孜不倦,但更大原因则在于他们不要求传教士有太高的教育程度,故而传教士很容易被替换,且他们通常从当地招募,比那些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拥有更强的对当地疾病的抵抗力。
另一方面,清教牧师也与安立甘教会争夺宗教权威,对当地盛行的疾病与死亡作出应对。这首先是表现在宗教教义解读上的争夺。1740年,福音派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到来后,对安立甘教会发起挑战。他认为,各种疾病的流行显示了上帝对南部殖民地的审判,其原因在于顽固不化的安立甘牧师。在到达南卡罗来纳不久,怀特菲尔德写道:“上帝的审判近期已经在他们中间出现,天花在不断传播。我希望,他们能够学会接受正义。”安立甘教会也通过向教众布道阐释宗教信条。1750年,查尔斯顿的塞缪尔·昆西成为南卡罗来纳安立甘教会中第一位将布道词出版发行的传教士。昆西的布道词展现了殖民地时期传教的三种重要功能:试图解释痛苦出现的原因,以永生安抚患病的教众,强化安立甘教会及传教士的文化权威。(67)Bradford J. Wood, “‘A Constant Attendance on the God’s Alter’: Death, Disease, and the Anglican Church in Colonial South Carolina, 1706—1750,” pp.216-218.但安立甘教会在争夺宗教权威时明显处于下风。长老会牧师约书亚·史密斯(Josiah Smith)针锋相对地出版两份葬礼布道词,就布道词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安立甘教会牧师进行争论。另外,这些清教牧师也积极参与疾病预防和救治,承担教区的济贫、食物分配等世俗职能。于是,一些杰出的清教牧师在南部当选教堂执事,对当地的宗教事务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结果,在疾病肆虐的南部地区,英国派遣传教士的患病、死亡和离职,大大削弱了安立甘教会的权威,强化了清教各教派的力量和影响。在各个殖民地建立之初,南部就逐渐确立了宗教宽容政策,以吸引长老会、浸礼会、胡克教与法国胡格诺派。到1700年,清教徒在南卡罗来纳开始占据多数。虽然安立甘教会在18世纪初期也大力修建教堂,吸引信徒,但是1730年代以后,瑞士、德国、威尔士与苏格兰-爱尔兰的众多清教徒纷至沓来,清教徒在南部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到美国革命前夕,安立甘教会已经丧失其主导地位。1778年,新独立的南卡罗来纳与英国教会解除关系,安立甘教会在更名为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后很快就成为该州的一个少数派教会。
结 语
美国早期南部以其黑人奴隶制、种植园经济闻名于世,这种独特性为南部社会乃至后世的学者广泛关注。除此之外,南部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在信仰上与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地区不尽相同。北部地区居民以清教徒居多,信仰多以清教教派为主,马萨诸塞殖民总督小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 Jr)在移民北美之初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清教徒的“山巅之城”。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美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的清教色彩逐渐淡化,实现从“上帝选民”到“社区公民”的转变,(68)原祖杰:《从上帝选民到社区公民:新英格兰殖民地早期公民意识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但是在信仰上这些地区依然以清教教派为主。相比之下,南部各个殖民地在建立之初多以安立甘教会为主,而马里兰则是天主教徒的庇护所。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南部也逐渐实现了宗教宽容, 但在殖民地时期安立甘教会的主导地位还是存在的。
18世纪以后北美南部地区的宗教派别逐渐脱离英国的控制,成为新独立国家中的单独教派,毫无疑问是当时美国政治、经济演进的结果,具有内在的发展逻辑。不过,各种疾病在南部地区的盛行引发了安立甘传教士经常性的患病、死亡、缺席和辞职,确实推动了这一结果的形成。安立甘传教士从英国长途跋涉来到北美南部,在当地面临着各种疾病威胁,不断患病和死亡。这迫使他们或者短期迁移到其他被认为更为有益于健康的南部教区或者北部任职,或者到加勒比地区的巴巴多斯、百慕大等地恢复健康,甚至离开北美返回英国。结果是,许多南部教区牧师职位多年空缺,而那些留任的牧师们也仅仅能服务于少数教区,很少能到其他教区传教。于是,在安立甘传教士缺乏的情况下,许多民众纷纷转向清教各个教派寻求心灵安慰和宗教服务。清教教派尤其是浸礼会,能够在美国迅速招募适应性本土气候和疾病环境的传教士,故而在吸引信徒上比安立甘教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到19世纪初期,浸礼会、卫礼会、长老会等清教教派已经成为北美南部社会中的主导性教会,当地信仰格局实现本土化,宗教的多样化局面开始形成。
——“零疟疾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