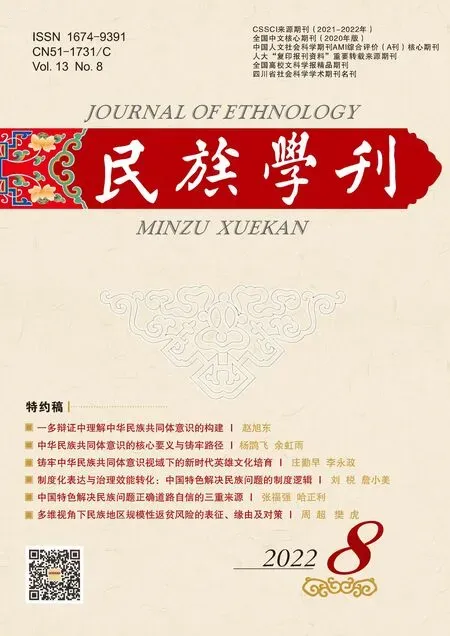世界主义的文学与人类学
——迈向整体人类学的跨学科新话语
王偞婷 蔡栋梁
20世纪以来的跨学科研究视角,为文学与人类学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上世纪80年代左右,文学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学问在西方兴起,并迅速引入中国学术界得以发展。在中西并行的学术推进中,文学人类学产生了一批理论价值较高、影响较深远的著述,与比较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进行渐次深入的对话交流,逐步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表述主张和系统理论方法的跨学科新话语。国内学者①普遍认为,文学人类学的话域肇始于以加拿大学者弗莱的“原型批评”研究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实践,认为这是一条引导文学研究者在人类学理论方法中寻找资源、从而对西方文学的发生与演化进行阐释的全新路径。与此同时,文学人类学又与20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学学科内部发起的“文学转向”密切相关,以克里福德·格尔茨、玛丽·道格拉斯、维克多·特纳、保罗·拉宾诺等西方人类学家发起的“文化诗学”或“阐释人类学”等研究为代表,把文学理解为某一特定文化的文本,并试图在方法论上发起对人类学写作问题和学科性质的重新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以沃尔夫冈·伊瑟尔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家,又进一步将该学问推进至本体论意义上的探究,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等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中,将文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予以展开:人为何需要文学?人为何会想象、虚构、表述、书写?人又如何通过文学来表述和塑造自己?促使文学人类学更进一步运用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工具向人类表述的本质研究这一核心逼近。
近年来,西方学者奈吉尔·拉波特(Nigel Rapport)和艾伦·威尔斯(Elle Wiles)等,也对文学人类学近半世纪来的学术演进与成就做出归纳,并试图在当代西方学术谱系中重新定义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拉波特(Nigel Rapport)在2012年的《牛津文献指南》(Oxford Bibliographies)中为“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撰写了关键性描述,认为其事实上涵盖三个研究领域:首先是探讨文学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经历中所起的作用,其次是对人类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的研究,最后是揭示人类社会状况的整个复杂情况(包括叙事在意识中的作用、创造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性质、以及人类学如何公正地证明经验的主观性等)。威尔斯(Ellen Wiles)则在《文学人类学的三个分支:素材、风格和主题》[1]一文中,将文学人类学比喻为“具有三个分支的树干”(a central stem with three branches):第一个分支是将文学文本作为民族志的原始材料;第二个分支是对一种新的民族志文学创作模式的运用;第三个分支是对文学文化生产实践的人类学考察。笔者认为,目前中西学界业已对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并将其归纳为主要的三个分派:一是以广义上的文学文本为对象和资源的人类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方法和目的的人类学反思和创新;三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对人的表述本质进行根本追问。尤其是对第三分派所关涉的表述问题的探究,使得文学人类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意识、核心意识正产生碰撞、构成反思乃至重塑,呈现出迈向整体人类学的话语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反思“普世”:对人文社科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置疑
在文学人类学迈向整体人类学的话语构建中,英国学者奈吉尔·拉波特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他著述颇丰,其中:《散文与热情:人类学、文学与福斯特的创作》①《超越性个体:迈向人文的与文学的人类学》②《我是炸弹——权力的另一种人类学》③《常人:人类学的世界主义——人类学方法与历史》④《世界主义之爱与个体性:超越文化的伦理参与》⑤等几部重要作品,囊括了其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关于个体性与整体性、创造性与超越性、人类学世界主义等充满哲学本体论意味的重大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呈现了当前西方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话语特征与发展趋势,即逐步将文学与人类学推进至整体性思考:如何对所谓“整体”进行反思,又如何对所谓“个体”实施关注、书写与回归,并最终如何构成文学与人类学之世界主义的美好愿景等。从学术谱系上看,拉波特的研究可谓是对前人伊瑟尔的继承与超越,他们的研究路径都是对所谓文学人类学“第三个分派”的推进与拓展,试图引导一种哲学本体论式的整体性研究范式。正如拉氏在其第一本文学人类学理论专著《超越性个体:迈向人文的与文学的人类学》②一书的扉页中,就开宗明义地引用伊瑟尔的叩问来明确彰显这一意图,来直指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核心: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可能性中,找到了一种永不满足的快乐?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什么,也无法停止这种发挥我们潜力的游戏?文学人类学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沃尔夫冈·伊瑟尔 《迈向文学人类学》⑥
而绝大多数新理论和新话语的诞生,往往都是从对本领域重要理论的反思开始的。在迈向整体人类学的理论推进中,文学人类学也有这样一个起点:即对19世纪以来以人类学为首的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与方法论上的置疑和反思。在拉波特看来,这一置疑从两个视角展开。
一是对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反思。19世纪以来,传统的人类学将研究对象着眼于、乃至局限于所谓“整体”,而这一“整体”往往被历史的、社会的、族群的等等“宏大叙事”所限制。作为人类学对象的“个体人”被简化与抽象化,以致“整体人类”也被“一叶障目”。如同布莱恩·特纳(Bryne Turner)所描述的那样,尽管以人类学为首的社会科学的诞生有着18世纪晚期“普世主义”革命运动的背景,但其在19世纪的教育和社会政策体制下建立起来后,仍保存有浓郁的“民族主义”精神,肩负着致力于振兴特定民族传统的使命。这使得“社会科学”(sociology)成为了近似抽象和概括的术语,它的发展是为了解释和理解地方(大多数情况是国家),而不是全球的命运;成为了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地方科学。[2]人类学家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在更早时期对人类学学术史的研究中也做出过同样的反思,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对象之间、以及与更大的社会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人类学强大的神话色彩和持久的浪漫原始主义风格,一直与它的科学愿望和主观获得“数据”的方法间存在着矛盾,使其不得不面对各种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的整合问题。[3]尤其是19世纪以来,针对部落、村庄、社区、社会、种族和民族等特定人群(对象)的人类学研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使得人类学变得越来越像社会学和民族学,更多是通过对特定群体的关注来获取全过程、同一性和普遍人类状况的具体知识。近年来,亦有以徐新建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以中国的实际情景为纲提出相同的反思:“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知识范式,人类学在中国主要以进化论为根基,强调英美的科学实证倾向,忽略了人类学自‘两希’传统以来的哲学根底,因而导致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社会学与民族学,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与创新性。”[4]拉波特在近年来对人类学世界主义问题的讨论中,也鲜明指出了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的这种局限性和狭隘性。在他看来,人类学家拒绝普世主义的话语,专注于“民族志”和“地方志”似的田野调查,局限于“本土性”差异的过度解读,从而忽视了人类学固有的普世的、世界主义的本质性目标。[5]
笔者认为,对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反思事实上是一种回归。正是因为人类学,人类才得以被看作一个被思考的整体。人类学的“世界主义”视角从一开始便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显著贡献,更是其奠基现代社会科学的立足之本。自一开始,人类学就借助进化论把社会发展中差异不同的人群表述为分布在时间轴上不同位置上的整体。随后,人类学又借助传播论、文化相对论等将具有不同人性和特征的文化要素连结起来,又运用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等哲学范式来试图阐释这些不同人群的普遍共性。从研究传统上看,尽管现代人类学随着学科分工常常以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姿态出场,并分化出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若干分支,来一一对应不同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文学等方方面面。但是,人类学一头扎进具体社会人群,以具体社会作为调查研究对象的最终目的,仍应是以对整体人类研究为终极目标的。人类学始终肩负着对整体人类关怀的崇高使命。
二是对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分类、专业化、部门化的方法论路径的反思。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中丢失的“整体性视角”,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弊端的显现。20世纪以来,任何跨学科的新话语都意识到分门别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在将人文主义的个体进行肢解。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是只注重和抽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而遮蔽掉其它更多的方面。用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来说:“定义就是设限”[6]。拉波特就十分推崇王尔德的学术方法,认为他一生都在抵制草率快速进行学科过度分类,而罔顾事物多元全貌的方法论顽疾。用王尔德的话说,“多元即是真实。真实即是,它的反面亦是真实。”[7]那种对具体事物操之过急的本质化或概括性描述,往往会让我们忽略掉事物多元性里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真实细节。上世纪末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产生,正得益于人类学与文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实践与突破,它们打破了文学与人类学在固有学科方法上的界限与范畴,主动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艺术研究等人文学科,以及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等更多社会科学,乃至哲学,实施交融与互惠互动。
总而言之,个体生命具有独立的、自在的意义,在被外部环境生成之前或者被外部语言表述(或言说)之前,其本身就已是完整的自在之物。任何草率的、快速的“切割”或“分类”,对它来说都是一种限制,甚至是一种妄加的论断。以拉波特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家们,正是从对长期以来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过度强调分类化、专业化、定义化、部门化的研究方法的深入反思出发,试图为人类学研究寻找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和新的方法论路径。这种路径既关注个性的特质,又强调多元的表达;既关注个体的创造性,又不忽视其超越性;既关注细节的表述,又展现生命变化的丰富性。一种文学的人类学新方法就此得以可能:“对自身的本质追问就像一个艺术工作,需要通过想象力、知识自觉和游戏来不断创造与再创造。正是通过对个体的超越,人们才得以创造自我与自己的传统。”[5]除此之外,文学人类学研究还必须在其思想最深处嵌入“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自我与他者”等辩证统一的哲学因子和整体性视角,使其对任何形式的简化主义和本质主义都采取谨慎的保留态度。只有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完整的个体生命之中,我们才能使得研究对象真正地从所谓历史的、种族的、文化的和生物学的限制条件中解放出来。因此,文学人类学除了需要寻求一套如何“有效关注个体”的理论,还必须实践出如何“正确书写个体”的方法。
二、书写“个体”: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构建
文学人类学要对“个体”实施有效关注,必须建立其完备的理论工具,尤其是要将个体对特定社会文化环境有意识和富有创造力地融入作为考察对象。拉波特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个体性”(individuality)这一关键范畴,试图梳理出“个体性”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对“个体性”这一关键概念的阐释上,拉波特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为先驱,并将尼采对个体极富原创性和人文主义之色彩的解释作为重要的理论依据。尼采指出,个体最为核心、客观和固有的本质,就是自我创造与自由。
为了更进一步阐释个体的创造性和超越性本质,拉波特更以尼采的名言“我是炸弹(I am dynamite)③”为书名,通过对四个个体生命历程的研究来深入阐释“个体性”的内涵。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构建了一个具有原创性与特殊性的哲学大厦;难民工程师兼业余天体物理学家本·格拉泽(Ben Glaser)在新的土地上从事着极其复杂和富有成效的知识再生产活动;雷切尔·西尔伯斯坦(化名)是一位移民兼政治活动家,他用自己的经历解释了通往个体“完成”的道路,这一道路使他过上了勇敢而持续的漂泊生活;画家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创造了一个富有远见的画像和经文作品,既有吸引力又十分古怪。拉波特试图用这样一些鲜活的案例说明,每一位个体都过着一种“自我意识强烈地专注于自己某个生命项目(life project)的生活……他们将精力用于设计和完成属于他们的项目,从而在他们的意识生活中实现对世界秩序非凡的控制”③。尼采、格拉泽、西尔伯斯坦和斯宾塞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并没有将生活置于他人的生活中,而是将他们的生活置于抽象之中,把他们的生活变成了艺术作品。拉波特试图用他们的生命历程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成功地置身于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叙事之中,处于一个显著展开的独立的关系世界的中心。在此基础上,拉波特试图引申出,个体所具备的一种对非个体的、社会结构的或制度性的力量所拥有的“存在权力”(existential power)。他质问道:到底是谁、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个体的生活?每一位个体采取的行动方式和这些行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个体行动的解释权最终来自何处?拉波特的观点是,那些将追求某个生命项目看作自己生活的人,才能够在实现特定目标方面看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并成功地赋予自己的行动以特定的力量、稳健性和独立性,最后成功逃脱外部势力和其他可能误导他们个体生活因素的外部影响。③于是乎,个体所具备的这一“自我控制”的主观性是可以延伸至自我行动的“客观性”的,并能进一步延伸到动机阐发和意义解释的“主观性”上。最终,“主观性”与“客观性”都将与自我的主观领域产生关系。③换句话说,个体的“主观性”与社会的所谓“客观性”共同决定着自我的表述;而由于社会符号交换的模糊性,个体性甚至不需要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表面地表述或传达。社会和社区同时由公共的共性和个体的多样性同时表述。
在拉氏之前,伊瑟尔就将文学人类学理论上升至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从根本意义上去追问了人的表述本质。他的答案是,自我的呈现与超越是人的基本需要,人类正是通过文学来实现这种自我呈现与超越。[8]而与拉波特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来自美国的当代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⑦在这一问题上亦做出过重要论述。他重新挖掘了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本体论层面对人类表述本质的创见,将人类实践和人类历史看作由“诗性智慧”主导的创造性行为。在维科看来,诗性智慧是一种从肉体生发出来的天然的想象力。人类的各门技艺和学问,都起源于这一粗糙的创造力,是一种诗性的或创造性的玄学。维科尤为强调生命个体的身体感官,认为“人类本性,就其和动物本性相似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各种感官是他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9]赫兹菲尔德由此建立了自己的人类学观,认为人类学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运用多感知对人类常识进行批判的理论实践。[10]
从伊瑟尔到拉波特和赫兹菲尔德,他们从不同视角对人的表述本质进行了评估,进而获得了重新看待文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在伊瑟尔那里,文学是人类虚构与想象的产物,是“超越世间万事之困,使人类得以摆脱束缚天性的后天构架”[8]。在赫兹菲尔德看来,“诗性智慧”是人类创造文明与世界的本源,人类学是基于“诗性智慧”的理论实践。人类学应当成为一门兼具批判性和实践性的,对人类理论实践这一创造性行为的历史学或语用学研究。[10]而拉波特则明确提出,人类学需要用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为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的个体做出辩解,也为长期以来被传统社会科学所“压制”的人文研究做出辩解,进而主张一种关注个体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学人类学研究。[5]在他看来,个体生活所依赖的权力关系并未受到现实政治、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关注。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不仅仅是自由个体表达的形式,更是其形成的起源。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从来都应受到个体表达的约束和型塑。从本质上说,个体意识(即使它毫无疑问地存在于社会文化环境中)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超越性:即对公共控制的摆脱和对同一性表达的扬弃。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范式就在“写文化”的反思思潮中,从表述形式的角度挑战了科学主义民族志的合理性。人类学方法论逐步从科学结构主义转向文化相对主义,涌现出诸如《妮萨》《维塔》等注重报道人自我叙述和表现报道人“在场”的实验民族志,试图将话语权还给报道人。阐释人类学也从文化符号入手,寻找隐藏的文化含义,用“深描”来分析某特定社会的代表成员在特定时间所理解的经验的深层表述与意义。笔者认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动摇了科学民族志的传统范式,将人类学的研究目的转为寻找和阐释文化含义。遗憾的是,实验民族志并未能真正走出本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束缚,以格尔茨为代表的反思则更多侧重于人类学写作这一方法论层面。直至《人类学诗学》[11]的出版,一种与文学关联的人类学新范式才真正得以出现,使得文学人类学作为全新的理论与方法实践横空出世。在《人类学诗学》中,一批学者推进了对人的文学性、文学能力、虚构能力等本体论上的探讨,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故事讲述者”(Storytellers)。同时提出,文学人类学不仅是人类学在文本选择策略上的探讨,更关乎其在“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的抉择。近几十年来,像《人类学诗学》的作者们以及伊瑟尔、拉波特、赫兹菲尔德等一批学者都试图为文学与人类学带来全新的整体性理论视角,试图从对人的界定开始,把虚构、想象、个体性、诗性等表述问题引入研究的核心。以拉波特为首的当代文学人类学家,更进一步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书写实践上,将“个体”纳入人类学领域中心,使得这一理论视角对包括文学与人类学在内的当代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获得了一种巧妙而引人注目的重新评估。这一评估不仅关乎对个体予以关注和书写的理论与方法创新,更进一步引导出一个经由“个体”回归“整体”的世界主义愿景。
三、回归整体:呼唤文学与人类学的世界主义
近年来,以拉波特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正在将学术抱负从理论建构转向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努力。他们试图将“个体”从文化、习俗与社群中进一步解放出来,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整体”相关联,从而呼吁一种解放的世界主义文学与人类学。[12]拉波特在近著《常人:人类学的世界主义》④一书中,就回顾梳理了自康德以来世界主义理论的发展变化,并提出要在道德与政治上呼唤出一个关于人类学的世界主义规划。“世界主义”(cosmo-politan)一词实际上源于康德在18世纪末的创造,用于表达一种个体与世界之间存在的张力:成为人意味着栖于某一个体之身、某一特定的时空之内(此处为“polis”,取“城邦”之意),也意味着成为具有多样能力和责任的重要实例,从而成为人类整体(此处为“cosmos”,取“宇宙”之意)的一部分。拉波特认为,康德在构想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人类学”概念时,清楚地表述了其理应实现一种世界主义规划的愿望。因而,他决心对康德的这一意志予以继承和发展,认为文学与人类学应当致力于对特定人类生活和主观现象,以及特定空间和场所下进行的个体生活进行观察、书写与研究,从而获得对人类普遍规律和宇宙事实的进一步理解。
拉波特力图在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找寻一条回归“整体”的文学与人类学研究之路。他尤其强调人类学要“以世界主义为生命计划和世界观,去想象‘常人’(anyone)的世界”④。在这里,拉波特提出并阐释了三个具有创获性的观念:第一,“人类”是一种现象,人类学应确定该现象的普遍条件和各组独特特征;第二,“常人”(此处指“任何个体”)是人类演员,应被视为“普遍个体”从而与“人类整体”关联;人类由此被定义为“个体性”的客观环境。因此,“个体性”来源于人性,人类被实例化为“个体性”。第三,人们可以设想一套规范,这是礼貌的人际互动的普遍伦理,即“国际政治”。这也是一种社交媒介,将在任何地方为每个人提供创造个人生活能力的生活空间,包括个人的世界观、身份和“生命计划”(life project),并使他们获得这样做的权利和鼓励。他认为,人类学应当为这一“世界主义规划”提供证据,将“人类”和“常人”看作人类本质的一部分,从而视为一种本体论。④
拉波特的“常人”(anyone)这一关键概念是区别于“每个人”(everyone)的,其目的是为了强调“常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来自于“他”或“她”的未来(也就是他们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因为,人类学将根据“他”或“她”所创造与书写的个人生活来定义人的能力。“常人”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无论从微观到宏观,都是内在且不可消弥的。笔者认为,“常人”这一概念,正是拉波特对其“个体性”概念在道德与政治层面上的特殊呈现,旨在强调其对于个体与整体关系的理解,更在于其提出的文学与人类学所实现的“使人成人”(becoming)的过程和目标。文学与人类学的世界主义倡导,拥抱未来是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内在权利。无论前人具有怎样的文化、社群、宗教、娱乐、世界观和生命规划,无论今人的渴望与期盼为何,个体都拥有以自适的方式去实现“使人成人”(成为他们自己)的权利。个体的“常人”与世界“人类”一样,没有完成,没有终结,一切都还在进行之中。
因此,文学与人类学都肩负着“写人”并提供全球性知识的道德使命。世界主义或将成为它们的道德纲领。文学家与人类学家也许能利用文学书写与人类学知识来确保全人类的普遍福祉。尽管世界主义的观念起源于西方,但在拉波特这里是开明的、面向世界的、面向未来的。因此,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它不同于启蒙运动所提倡的要在习惯和传统中获得上帝启示和不受审视的知识的人类理性;尽管启蒙运动也倡导不受社会结构和分类限制的自由,主张将个体从封闭社区中固定的、不平等的和非个体的姓名与职位之中解放出来。世界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不同于全球化,是真正跳出一切社会结构和知识传统的范畴。因而,我们也要特别警惕“文化多元主义”“普世主义”等背后隐藏的话语权力。世界主义的文学与人类学要求我们不仅从经验和客观的角度来阐明人类能力的本质、个体意识、创造力和个人成就的生命项目;在道德上试图阐明人类可以充分发挥其经验和表达潜力的条件;更在美学上促进对人类身份和尊严的欣赏与推崇。这也是拉波特对人类学这一伟大学科的道德和伦理期许。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并付诸努力:人类在任何地方都有能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应当被给予空间和机会来使一切具有创造意义的潜力得以实现,并为此制定和实现他们个人的“生命规划”。“常人”(任何人)可以在任何背景之下理性合法地观察和书写人类生活,从而观察与书写整个世界。
四、结语
文学人类学勃兴于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并逐渐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话语。作为这一理论话语的承袭者,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学者多从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互动上探讨该学科或话语的起源。叶舒宪在述评西方文学人类学研究时提出:“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构想分别来自文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这两大方面。”[13]徐新建也认为:“文学人类学既是西方文学与人类学界一批前沿学者的积极主张,亦是一种逐渐向其他学科领域扩展、渗透的新理论和新方法。”[14]但在笔者看来,仅从学科交叉互动的视角探寻文学人类学在西方的源起并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使我们难以跳脱原有学科的束缚,将对文学人类学的理解局限于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之中。事实上,许多西方学者在谈论文学人类学的兴起时,总会将其与20世纪的“文学转向”(literary turn)相关联。而无论是文学界还是人类学界,学人们又基本认同“文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根本动力源自20世纪西方学界最为标志性的思想变动——“语言学转向”⑧。
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以现代语言学为标志的语言哲学,使得西方学术史上的“语言学转向”对西方几乎所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流派都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诸多新思潮、新学科、新话语的诞生都与这一转向相关,文学人类学也不例外。人们对语言的重新发现与认识,促使文学与人类学也以新的视角进入反思之中。文学人类学便在其两大基础学科文学与人类学的反思过程中孕育而生。就文学而言,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引起了理论的嬗变,形成了文学的新观念和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尤其是在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交流中,文学新观念与新范式进一步促成文学与人类学的话语牵连。西方文学人类学虽未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设立新分支,但却在更深更广泛层面上进行了文学理论的“人类学化”。而随着20世纪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极大的反思与扩展,人类学家的著作不仅有望成为科学记录的“客观”依据,也成为新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直至“写文化”论争爆发,人类学彻底发生了文学转向,迎来了新的时代主题:“文学”替代了传统的“他者”,民族志的“文本写作”替代了传统的“参与观察”,广义的文学体裁替代了传统的民族志专著,对意图的不确定性的具体化替代了确定性与权威。人类学正式进入到文学人类学时代。在新时代我们基本可以确信这样一个新的论断:文学即人类学,人类学即文学!
因此,文学与人类学在新时代的反思也是具有同源性和共同性的。它们都需要对过去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与重塑,不仅对19世纪建立起来并长期笼罩在科学主义之下的以人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进行反思,更要将长期被边缘化的文学研究重新进行评估和运用。人类学必须借助文学来反思诸多立场与方法上的缺陷,获得更为多元的超越性视角和更具生命力的整体性呈现。文学也必将走入人类学表述的核心和根本之中,在人类的不同表达时代和阶段发挥功效,创造与书写着人类未来。
而在诸多的反思视角之中,对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的切入,是一个切中要害的关键点。回归至个体生命的人,文学与人类学才能真正探寻人类表述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以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拉波特为代表,文学人类学基于对以人类学为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反思,正在对所谓“个体”实施关注和书写,从而最终回归“整体”视角,构成世界主义人类学的美好愿景。
当代西方文学人类学研究呈现出的这种整体转向的趋势也深刻地启示我们:如果20世纪的文学人类学是以破除科学为己任的一次思想反叛,从而使得文学与人类学在相互走进的过程中突破或超越过去的束缚,那么它们仍未完成自身的使命。它们仍旧在科学与人文相对立的二元结构之中徘徊不前。新世纪的文学人类学应该何去何从,从而对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做出话语贡献?也许,除了激发人类学获得新的人文主义的生命活力,文学人类学还需要获得一个更具超越性的学术方向。这一方向,便是冲破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桎梏——破除“二元”,走向“归一”——回归表述的生命个体,迈向整体的文学与人类学!
注释:
①笔者译,原书名为The Prose and the Passion:Anthropology, Literature and the Writing of EM.For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笔者译,原书名为Transcendent Individual:towards a Liberal and Literary Anthropology ,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3(originally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ublishing Company in 1997).
③笔者译,原书名为I am dynamite:An alternative anthropology of power,Routledge 2003.
④笔者译,原书名为Anyone:The Cosmopolitan Subject of Anthropology Methodology & History in Anthropology,Berghahn Books 2012.
⑤笔者译,原书名为Cosmopolitan Love and Individuality:Ethical Engagement beyond Culture,Lexington 2018.
⑥此段引文见Nigel Rapport,Transcendent Individual:towards a Liberal and Literary Anthropology ,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3,p5.
⑧比如,尼古拉斯·罗伊(Nicholas Royle)在其著作《转向:一种文学理论》(Veering:A 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专章论述了文学理论界的“文学转向”,并指出“文学转向是一种难以把握的概念,主要是有关于语言学转向的讨论”。参见Nicholas Royle,Veering:A Theory of Literature,2011,chapter 7,DOI:10.3366/edinburgh/9780748636549.003.0007。批判人类学家鲍勃·斯科尔特(Bob Scholte)在其重要文章《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The Literary Turn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中也指出,当代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事实上与2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三个学术动向相关:就英美文化人类学而言,分别是批判人类学、女性主义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出现。参见Bob Scholte,The Literary Turn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Critical Anthropology,1st Edition 2012,ImprintRoutledge,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