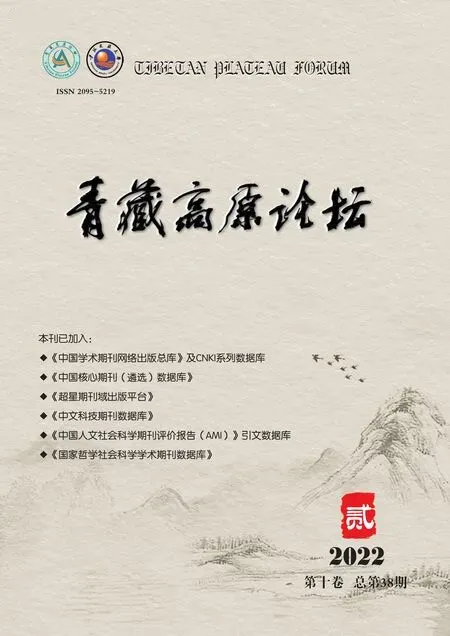黄慕松认定龙厦“亲英”的原因分析
曾 谦 苗佳琪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龙厦是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坛上一位非常重要政治人物,长期以来对他是“亲英”还是“亲汉”一直存在争议。1934年黄慕松入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后,在递交国民政府的报告书中称龙厦属于亲英派,随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沿用了这种说法,亦称龙厦是亲英派。自此之后,龙厦属于亲英派一直是社会上的主流看法。2000年,喜饶尼玛教授发表《试析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桩冤案——龙厦其人其事》一文,指出龙厦不属于亲英派,而是属于亲汉派,并指出1934年黄慕松“入藏伊始,并未对‘龙厦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一番调查了解,便偏听偏信,凭主观印象,不惜给龙厦带上亲英帽子,而求自我安慰。同时为了息事宁人,承认西藏地方的既成事实。可惜龙厦是时正身陷囵囤,不能向中央大员们申诉。”[1]
喜饶尼玛教授此文发表之后,在学界引起了比较大的轰动。唐洪波发表《龙厦与“龙厦事件”》认为龙厦走的是既不“亲英”也不“亲汉”的第三条道路[2]。周伟洲先生编写的《西藏通史》(民国卷)基本上也持同样的观点。各位学者的观点都有相当翔实的材料作支撑,各自的论证也都有一定合理性。本文无意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而是希望弄清楚为什么黄慕松会对龙厦作出他属于是“亲英”分子这个推定。对这个问题,喜饶尼玛先生虽然进行了解释,但却有些过于简略,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是从黄慕松个人经历和所处的现实环境出发,来探讨他认定龙厦属于“亲英”分子的真实原因。
一、蒙藏委员会与黄慕松对龙厦“亲英”的初步印象
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国民政府“籍谋恢复中藏原有关系起见,先从感情联络、藏事调查入手,特派慕松入藏致祭,并加追封”[3]。虽然黄慕松长期从事边务工作,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和处理边疆事务的经验,但却一直都在北部的蒙古地区活动,没有直接接触处理过西藏事务。于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国民政府便在黄慕松入藏随从人员中安排了一些熟悉西藏情况的蒙藏委员会官员,以帮助其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随黄慕松赴藏的刘朴忱、陈敬修、林东海、蒋致余、巫明远等5名参议人员中,除了林东海是外交部参事,巫明远是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副处长外,刘朴忱、陈敬修、蒋致余3人都曾经或正在蒙藏委员会工作。黄慕松随行参议人员的这种人事安排,显示出蒙藏委员会对黄慕松西藏之行具有巨大影响。
在西藏期间,黄慕松极其依赖以刘朴忱为代表的蒙藏委员会官员,不仅多次和他们一起开会讨论相关事宜,甚至还让他们代表自己和噶厦进行会谈。如1934年“九月二十四日,噶伦送公函一件,内容仅注重边界问题,对于根本上之中藏政治关系,并未提及,是日八时,召集全体职员会议,决议推刘总参议朴忱前往噶厦商询一切,再定办法”[4];“九月二十七日,派刘总参议前往泽墨噶伦私宅,对慕松办理中藏问题所持之态度加以说明”[5];“十月八日,派刘总参议、巫参议往噶厦,亲递第二次复函,由泽墨、郎中、哲康、彭休四噶伦接见,当经刘总参议加以说明”[6],等等。说明以刘朴忱为代表的蒙藏委员会官员在黄慕松赴藏政治活动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龙厦自1914年从英国回到西藏后,受到十三世达赖的重用,被任命为负责政府财政工作的“孜本”。到十三世达赖晚年,龙厦愈发受到重用。“这时,正是我父亲青云直上的时期。在担任孜本、征粮检查局负责人的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任命我父亲为藏军司令顾问。我父亲还常常为达赖喇嘛草拟一些重要文件,甚至可以左右达赖的重大决策,成为噶厦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7]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龙厦越来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由于1912年之后西藏和内地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国民政府很难获得西藏方面的信息。于是,便借助在蒙藏委员会工作的藏族官员了解龙厦的政治倾向。1928年蒙藏委员会成立后,来自于康区的格桑泽仁等藏族人士进入蒙藏委员会担任委员职务,成为中央政府了解西藏情况的主要渠道。格桑泽仁向国民政府提交《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提出自己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些具体建议。该建议书虽然没有涉及龙厦的政治倾向问题,但他们却认为十三世达赖具有亲英倾向[8]。在此情况下,作为十三世达赖亲信的龙厦,自然也难逃亲英嫌疑。格桑泽仁在蒙藏委员会委员的职位上连任17年,是中国国民党的第一个藏族党员,多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参加过国民党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外,他还在军事委员会中任有军职,先后担任过参议、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四川行营边政委员会委员等。1946年,格桑泽仁去世时,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并给予公葬,蒋介石亲送“勤贤足示”的挽幛。格桑泽仁比较受国民政府高层重视,所以他的看法在蒙藏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内部是很有影响的。
最早明确指出龙厦政治倾向的是西康的刘家驹。刘家驹1929年以“西康民众协进会”代表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呈文指出:“龙虾(即龙厦)夫妇曾留学欧洲多年,颇具才识,向为达赖所倚重。惟其历史素无新旧色彩之表现,是以一般人对之有莫大之疑惑与希望。藏局之转变如何,龙厦实有举足轻重之势。彼若接近新派仍主亲英,则藏局终陷于濒危,而莫可收拾;然彼若接近旧派,则俟至相当时机,必能拥护国民政府,更有与班禅合作之可能。”[9]在该呈文中,刘家驹等人虽然说龙厦“其历史素无新旧色彩之表现”,但文中“彼若接近新派仍主亲英”的言语,说明他们认为龙厦一直是比较“亲英”的。刘家驹是1929年在格桑泽仁的邀约下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呈文说明龙厦政治倾向的。在前往南京之前,刘家驹曾任西康巴安县立小学校长兼县府教育科科长,和格桑泽仁等人交好,他的看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内地藏族人士对龙厦政治倾向的大致看法。在刘家驹向国民政府呈文后,蒙藏委员会开始对其进行重用,任命他为蒙藏委员会藏事科科员。1931年升任科长,并兼任《蒙藏周报》社藏文股主任,1932年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蒙藏委员会没有以官方的形式表达对龙厦的看法,但从1929年后刘家驹的仕途发展来看,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还是比较认可他的观点的。
曾经去过拉萨,和龙厦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刘曼卿认为,他属于亲汉派人士。刘曼卿在《康藏轺征》中曾专门辟出一节对龙厦进行介绍。说她到龙厦办公的地方和他相见时,(龙厦)身穿“中国清代大礼服、戴大凉帽,……拱手立门侧”,待刘入内时“直行中国旧礼”[10]。在刘曼卿临返回南京之前,龙厦诚恳地表示,希望她“祈告中央,藏政府非不予奉行三民主义,然以人之顽固,幸勿操急,徒致纷扰。以云外交,藏人决以中原行动为行动,断不致单独有所表示。再者内地军备,闻远内地军备,闻远不及列强,请加意准备,使内足以镇变护边,外足以御侮持平为要。并嘱吾继续为藏努力,对中原要士亦应鼓吹注意边事。望得间二度重来,吾将尽力保护”[11]。虽然刘曼卿十分肯定地认为龙厦属于亲汉人士,但由于她是国民政府文官处派遣的半官方官员,而且在返回南京不久便离开了政府工作岗位,所以她的观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蒙藏委员会还有待商榷。
总之,由于蒙藏委员会官员对黄慕松影响巨大,且蒙藏委员会内部一直认为龙厦有亲英的倾向,所以黄慕松可能在入藏之前,就受此观念的影响,认为龙厦存在亲英的嫌疑。
二、九世班禅与黄慕松对龙厦“亲英”的基本认识
龙厦出生于日喀则市南林木县,家族世袭领地在日喀则市谢门通县达那地区。这两个地方都距离扎什伦布寺很近,很可能在龙厦很小的时候,九世班禅就认识了他。龙厦二十多岁的时候和当地一个贵族家的女儿成了亲。结婚之后,龙厦在拉萨做官,定居于拉萨,他的妻子平时来往于拉萨和日喀则之间负责庄园里收租及耕种事宜。
九世班禅和龙厦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比较大的矛盾。1922年,十三世达赖成立征粮检查局——“包细勒空”,龙厦为该机构的负责人。“龙厦一上任就向扎什伦布寺征收3000千克青稞和1000个银币的年附加税。”[12]九世班禅拒绝缴纳新增加的赋税,指责称这是不合法的。“(龙厦)坚持认为班禅喇嘛能够缴纳新征收的税收,他以对扎什伦布寺喇章的财产和领地进行清理、勘测后所指定的《增勘赋税粮办法》为依据,认为扎寺完全有能力支付新的税额和驮畜差税。他竭力使达赖喇嘛相信,班禅喇嘛拒绝纳税背后的真正动机,是班禅对达赖至高无上的权威的不满。”[13]在龙厦的压力下,1923年九世班禅离开扎什伦布寺,前往内地。龙厦随即率军一直追击到阿里地区,才停止下来。
由于赋税征收问题,九世班禅对龙厦的评价非常负面。如1924年九世班禅给十三世达赖信中写到“作为老师和徒弟,我以前曾给您圣者去过许多次信,是您的那些别有用心的无知且怀有恶意的官员们在我们之间造成了隔阂和麻烦。……那些以破坏仁慈温和的解决办法为目的的邪恶的官员们,去从中设置种种困难何障碍。”[14]九世班禅性情温和,很少使用比较激烈的语言去评价他人。他如此形容龙厦,说明他对龙厦确实极其憎恶。
龙厦1929年被任命为藏军司令后,大力扩充藏军。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藏军的人数增加到了2200人,并且这些部队还新建了代本司令部,购得了包括防雪眼镜、帐篷和火炉等各种各样的装备[15]。1930年,在龙厦就任藏军总司令的第二年,康藏之间爆发了历时三年之久的武装冲突。康区的民间势力是九世班禅的重要支持力量。1929年6月,代表西康民间势力的“西康民众协进会”在给国民政府的请愿书中,曾这样说到“班禅为西藏教主之一,其资格地位,与达赖不相上下。藏内之旧派及康藏一般民众对之皆深表同情,望其速归……班禅始终拥护中国政府,曾受偌大牺牲,今政府如不欲解决藏事则已,如欲解决藏事,以理以势,均不能不重视班禅,以资号召。应请政府从速欢迎班禅来京,共商大计”[16],极力要求中央政府重用班禅。在康藏双方冲突中,九世班禅坚决支持西康民间力量,反对藏军方面的进攻。如,康藏冲突爆发后,九世班禅“亲身来京,要求武力解决藏事”[17]。于是,这就使当时身为藏军总司令的龙厦不可避免地再次站到了九世班禅的对立面。
九世班禅出走内地之后,一直心向中央政府。1931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九世班禅特地从东北赶赴南京参会。1932年,国民政府授予九世班禅“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的称号,将他视为爱国、“亲汉”代表人物。同时,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对会内组织人事进行调整,大量吸收九世班禅下属人员进入蒙藏委员会藏事处。“班禅堪布康福安为贵会驻印度通讯处主任,即关于藏事处科长等职,亦非在班禅驻京办事处任有秘书科长职务者不能存在。……迨后该执事不独未予办理,而藏事处要职,反尽成班禅部属,不啻于班禅驻京第二办事处。”[18]虽然言语有一定的夸张,但却反映了九世班禅部属开始执掌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现实。
十三世达赖圆寂之后,班禅及其下属人员积极筹划准备,希望能早日返藏。如1933年班禅驻京代表罗桑坚赞曾对报界称:“班禅回藏问题,在达赖未圆寂前,已表示欢迎。今既逝世,藏之教政,更不能无人主持,故班禅回藏,实为目前急切之图。”[19]指出,在十三达赖喇嘛圆寂的情况下,九世班禅要早日返藏主持西藏的政教大局。虽然没有资料证明龙厦在九世班禅返藏问题上究竟持何态度,但1934年龙厦运动失败之后,新闻界却爆出龙厦反对九世班禅回藏的新闻。如《申报》1934年曾发布新闻称:“藏军下级军官四人承认与隆夏尔等结合,拟铲除华人势力,而阻止班禅喇嘛回藏也”[20]。这则新闻的刊布,进一步坐实龙厦反对班禅的事实。
“西藏地方政府人员自民国以来,分为新派、旧派及现政府派三派,换言之即亲汉、亲英与保持西藏人办藏事独立派。亲汉派为三大寺喇嘛、僧官及年久任事久者。亲英派为留学英国或印度,与英国在大吉岭所办英文学校学生,以及民元川军哗变时受害之官吏最深者。”[21]黄慕松把西藏地方政治派别划分为亲汉、亲英及现政府派三个派别。龙厦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判有罪入狱,肯定不属于现政府派。龙厦和九世班禅存在非常尖锐的矛盾,而九世班禅属于亲汉派代表人物,所以龙厦也不可能是亲汉派人物。这样,在黄慕松眼里他便只能属于亲英派人物。
三、龙厦事件与黄慕松对龙厦“亲英”的最终确定
1914年龙厦受十三世达赖指派出国留学,“龙厦在英国学习期间,学会了英语的一般会话和基本语法、词汇,并且熟悉了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建立的世袭君主制的‘民主的’的政治制度。”[22]龙厦的儿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他父亲的这一段经历时说:“在此期间,我的父母也学会了一些英语,并先后去法国、意大利等地游览。”[23]回到西藏之后,龙厦仍保留着鲜明的英国色彩。对于这一点,即便认为龙厦是“亲汉派”的刘曼卿,也有非常深切的感受。1930年刘曼卿到龙厦家里做客,龙厦大太太“遗吾数年前在英小照,袒胸垂,不亚西方美人”,十分自豪自己在英国的经历,把自己在英国的照片送给刘曼卿。宴会时龙厦“座中尝以英吉利语相笑谑”[24],用英语和刘曼卿开玩笑。
龙厦做派新潮,按照他的表现无疑属于亲英派分子。但黄慕松却非常慎重,并没有因为他表面上英国色彩浓厚,就轻易认定其属于亲英分子。如对擦绒就是一个例子。擦绒的住宅“洋派”十足,“建筑的外表为藏式,惟入门升楼,则见阔级折梯,已带欧风”,“进应接室,则小桌沙发,居然洋派十足。仆人献茶,咖啡及牛乳,小匙拨方糖,自忖何以至西餐室”[25]。在拉萨期间,黄慕松到擦绒家,发现“擦绒之房屋为西式结构,有庭院花木,饭厅可容纳百人,中无直柱。办公厅在其后,幽静而明净,沐浴室亦清洁”[26]。很显然,擦绒的英国色彩是非常浓厚的,但黄慕松经过观察之后,却认为“擦绒自不免仍有亲英嫌疑,但据各方报告观察,可目之为中立派,其主要目的在恢复其原有地位,亲汉亲英均无不可”[27]。
由此,黄慕松在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亲英派时,更多依据的是此人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一般表象。对龙厦亦是如此。黄慕松《报告书》中在确定龙厦是亲英派分子时,曾专门列举了龙厦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以此证明他确实属于亲英派分子。“隆(龙)夏自知大员到藏,亲汉派必将抬头,本人为反对班禅、反汉最力之人,必不见容于大员,故结党徒僧俗官员百余员,拟于中央大员未到藏前,谋杀热振、司伦、泽墨噶伦,自为藏王,改变旧制,创立国会,求英保护,拒绝中央大员入藏。”[28]凡此种种,虽然有些事情黄慕松并不一定十分清楚,但龙厦反对噶厦、学习英国民主制度的基本事实,是毫无疑问的。
1933年12月24日,噶厦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称“对中央大员入藏一节甚表欢迎”[29]。此电报表明,以泽墨噶伦为代表的西藏噶厦政府是欢迎黄慕松入藏的。在黄慕松一行前往西藏的路上,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欢迎。如在岗拖,担任总招待员的琼让“为人老谋深算,富机诈心,与现在首席噶伦为姻亲。沿途招待,尚称周到”[30]。到达拉萨后,黄慕松所受的欢迎更加热烈,“藏兵及近卫兵约千人全服武装,新鲜整齐,列队致敬。哲康笨许两噶伦及四品以上全体官员鹄迎入帐,鼓乐喧阗,礼节隆重”[31]。泽墨噶伦欢迎黄慕松入藏,而龙厦反对泽墨噶伦。这在黄慕松看来,龙厦自然属于“拒绝大员入藏”的“反汉亲英”分子。
1933年12月,在黄慕松前往西藏之前,龙厦曾以私人名义致函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告知国民政府派遣大员入藏协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有关事宜,提议英国关注此事[32]。1934年4月25日,在黄慕松启程前一日,英国派驻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的助理诺布顿珠到拉萨活动。5月10日,龙厦召集僧俗官员70余人及三大寺一些代表拟定“改革”计划,正式启动龙厦运动。该运动在龙厦的带领下,主张组建类似于英国议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该组织“曾以秘密方式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如对噶伦的产生,要每四年选举一次,必须直接从西藏大会的候选人中选举”[33]。由于龙厦在诺布顿珠到达拉萨后开始正式实施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具有英国色彩,且这次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英国的议会制度,所以龙厦改革失败后,很快便被认为是一场亲英分子的失败。1934年7月4日,在黄慕松还未抵达拉萨之前,先期抵达拉萨的蒋致余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致电称,“前捕九人,均有力亲英分子,除龙厦仍监禁外,余流各宗”[34]。蒋致余对藏情颇为了解,在国民政府高层中很有影响。他在黄慕松抵达拉萨之前,认定龙厦属于“亲英分子”,他的意见无疑会对黄慕松产生极大影响。
龙厦运动失败后,黄慕松明显感觉英国在西藏的影响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黄慕松在向国民政府呈递的《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奉派入藏后英国在藏活动之情形”中,曾这样写到:“哲孟雄政治主任威廉逊及比尔爵士,约于八月初先到桑耶寺朝佛。噶厦以比尔乃无职之英人,婉拒其请。比尔抵桑耶寺时,即驰书噶伦,要求来拉萨一游。行至公卡宗暂住,以待噶厦答复,每日必电话催至拉萨电话局噶厦以迅予答复,侯至七天之久,仍无答复,乃返江孜。”[35]此事件发生在龙厦运动之后,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联系,但这两件事情先后发生,把它们结合起来,很容易让黄慕松得出:龙厦属于“亲英”分子。龙厦运动失败使亲英势力受到打击,造成噶厦拒绝英国人比尔进入拉萨。
四、“亲苏分子”与黄慕松对龙厦“亲英”的另类思考
龙厦运动是西藏近代史上学习英国议会制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具有鲜明的英国色彩。龙厦被逮捕之后,西藏噶厦对他以“密谋杀害西藏地方政府在职噶伦”“共产党分子”“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要杀人,毁灭宗教”等罪名,进行了审判。在西藏地方政府强加给龙厦的诸多罪名中,“亲苏分子”这个罪名最让人匪夷所思。不仅龙厦本人拒不承认这个罪名,而且当时很多人也认为这个罪名非常荒唐,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龙厦亲近苏维埃俄国。龙厦是“亲汉”或者“亲英”分子都有一定的事实支持,而龙厦“亲苏”明显地缺乏相关证据支持。
“职入藏后,并未见到俄国在藏有丝毫势力。现今藏人畏惧俄国之共产制度,则西藏与俄国外交关系,此时似尚不易联络也”[36],黄慕松认为西藏和俄国之间不易联系,并不认同噶厦对龙厦的指控。“泽墨为精明强干、老成持重之人,在今日西藏环境之下实为不可多得之人才。查泽墨随侍达赖甚久,川军入藏后,彼随达赖逃印,奔走于印度、大吉岭之间,森姆拉会议彼与夏扎噶伦出席,在藏任噶伦二十三年,资深望重,手段圆滑而毒辣。”[37]黄慕松认为泽墨噶伦“精明强干、老成持重”,以他为代表的噶厦确定龙厦罪名,远不是胡乱定罪那么简单,其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很深的意图。
《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作者梅·戈尔斯坦也注意到噶厦指控龙厦“亲苏”这个问题,“对龙厦的正式指控,是说他领导了一个大约有100名僧俗官员的组织,他们企图杀害一位噶伦并阴谋推翻噶厦政府,用布尔什维克制度来取代它”,并进一步指出“这后一条罪状是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遗嘱》中推导出来的,达赖喇嘛在其遗嘱中曾发出警告:西藏面临共产党占领的威胁,存在着像发生在外蒙古的宗教遭到毁灭的危险”[38]。梅·戈尔斯坦的这个观点虽然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噶厦把龙厦和苏维埃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系起来。
泽墨噶伦和龙厦之间一直存在比较深的矛盾。在十三世达赖在世时,“龙厦曾几次在达赖喇嘛面前抱怨赤门的工作和行为,并建议应当给赤门降职处分”。所以泽墨噶伦虽然长期担任噶伦的职务,但却一直处在政治权力的边缘位置。“由于他和龙厦及土登贡培没有处好关系,所以他在达赖喇嘛当政的最后几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39]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龙厦运动矛头直指泽墨噶伦。如在龙厦等人起草的请愿书中,“指责赤门噶伦所做诸多不公道的事实,要求改善政府的职能和工作效率”[40]。之后,该组织的嘎雪·曲杰尼玛又向泽墨噶伦告密,说龙厦企图暗杀他。这就造成泽墨噶伦对龙厦极其痛恨,非常希望用严厉的方式对龙厦进行处罚。
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迅速波及到俄国和外蒙古地区,外蒙古的藏传佛教受到沉重打击。对于发生在外蒙古地区的这种社会现象,十三世达赖及西藏政教高层是有认识的。如十三世达赖曾在其《政治遗嘱》中这样说到:“尤为严重的是,当前五浊蔓延,赤色主义尤其猖獗,在外蒙古,禁止寻访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随意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喇嘛活佛当兵,佛教被毁灭,寺院荡然无存,据说这样一种制度已在库伦建立起来。”[41]西藏是个政教合一的地区,教权高于政权,政权是为教权服务的。鉴于苏维埃俄国在外蒙古地区实行消灭藏传佛教政策的事实,只有给龙厦扣上“亲苏”的帽子,才能坐实龙厦“毁灭宗教”的嫌疑。在1920年左右,曾有几批俄国人以学佛为名潜入西藏。虽然没有材料显示龙厦和这些俄国人有何联系,但噶厦还是以此为借口,给他扣上“莫须有”的“亲苏”罪名,加重对他的处罚。
当然,噶厦对龙厦处予“亲苏”的罪名,另外一重意思就是在中央政府和英国之间进行政治“骑墙”。在对龙厦等“亲英”分子进行打击的同时,不公开和英国破裂关系。假设以“亲英”的名义对龙厦进行定罪,就等于公开表明噶厦是反对英国的,不利于和英国搞好关系。反之,如果以“亲苏”的名义对龙厦进行定罪,则表明他们不反对英国,有利于在中央政府和噶厦之间进行平衡,实现他们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噶厦藕断丝连,不愿意断绝和英国联系的做法,黄慕松深有体会。如在藏期间黄慕松“百般劝服藏中有力分子,使之脱离英国势力,然彼等均置之不顾”[42]。可能是基于以上对噶厦图谋的思考,黄慕松并不认可对龙厦“亲苏”的定罪,认为龙厦实际上是“亲英”的,而噶厦之所以不以“亲英”的名义对龙厦进行定罪,其主要是因为“精明强干”“手段圆滑而毒辣”的泽墨噶伦为了掩饰其背后的个人意图和政治目的。
总之,关于龙厦“亲英”还是“亲汉”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每一种说法都有其自己的证据和逻辑。黄慕松本人虽然并没有和龙厦进行过会面,他认定龙厦“亲英”主要通过他人的言说确定的,但这个结论的背后有他自己的证据和逻辑。今天,当我们讨论黄慕松对龙厦所作的“亲英”结论时,如果从他的角度出发,结合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或许能让我们对他所持的观点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