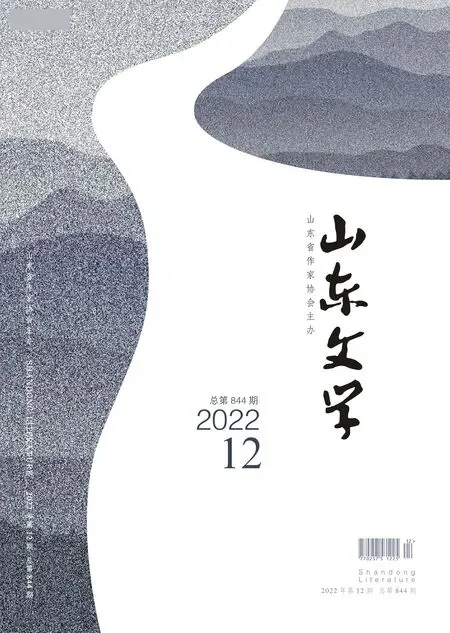何处是乡关
吴正峻
人都是有来处的。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总是有一个地方承载着我们对童年和亲情的回忆,或恨或爱,都无法抗拒。这个地方是家乡,是故土,也是人生开始的胞衣地。
每次看到关于故乡的文字,字里行间,深情地讲述土地的亲、方言的美和人们心中对故乡的孺慕与眷恋,就会特别羡慕那些有故乡,或者说有着故乡记忆的人。因为无论他们身在何方,心中总有一个故乡去恋,去愁,也无论他们是衣锦还乡荣耀四里,还是落魄归来舔舐伤口,故乡都将是他们内心深处最后的一块精神圣地。有故乡的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丰满和充盈的。
我应该也是有故乡的,虽然一直以来,我都无法确认自己的故乡究竟在何处。
中国人喜欢叙老乡,尤其是那些离开了故土在他乡生活的人们,遇见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便凭白多了一分亲近,酒桌上也多了一个喝酒的话题和理由。自然,不可避免的也常会有人来问起我的故乡,但每次都让我非常地纠结,总要犹豫片刻,然后很不情愿地告诉他,我的老家在何处,如果再很“不幸”地遇上了一位“老乡”,听他热情地描述老家里的人情事物,我便有种做了贼般的心虚和不安,只好呵呵地应着,不敢搭话,也不忍心再去解释。
看,我说的是老家,而不是故乡。因为“老家”在我的认知中,是父辈带给我们的,是填写在各种表格中那个“籍贯”一栏中的地方,但我肯定那并不是我的故乡,不仅因为我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感情,更重要的,那里没有我童年的记忆。当然,我也可以告诉他们我的出生地在哪里,但这也与我理解中的故乡同样没有丝毫的关联。
幼年时,我的生活轨迹是在不断流动的,如一叶舟,随着父亲的桨橹四处漂荡,去过太多的地方,见过太多的人,让孩童时期本就残缺不全的记忆,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以至于无法串起一个完整的童年。
曾经一度以为我的故乡就是军营,因为当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第一次睁开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就是在一所部队的卫生院里,身边看到、触摸到的都是绿色的身影,而在我懵懂的幼年记忆中,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包括我的父亲。而当我终于可以认清那位年轻的叔叔姓王,那位年长的伯伯姓李时,突然在某一天,我就和那些大大小小的箱笼、包袱一起被装上了汽车,含着眼泪将那些不值得携带却是我视若珍宝的木枪、木马赠送给刚刚才玩熟的小伙伴们,他们喜笑颜开,我却不舍得放手,却不知,这一别或许就是永远。
从一座军营去到另一座军营,还是那些绿色的身影,也同样都喜欢拧我的小脸蛋,摸小雀儿,我却要重新去甄别他们的面孔,还要怯怯地用零食和玩具去贿赂那些同龄的陌生孩子们,然后幸福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这一切又仅仅只是一个从整体上完全可以忽略掉的章节,还没有完全展开,便又重新开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是乡村,已经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我究竟搬过多少次家,只知道那些年里,我丢掉了许多珍爱的物件和喜欢的人。
等到了上学的年纪,再是不舍也是要与父亲分开了。于是跟着母亲和弟弟又来到一个新的城市。
还是一座军营,五湖四海的汉子,天南地北的方言,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院子大了些,楼房高了些,人多了些吧。好在我终于不再漂泊,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不用再重复经历那些分别和难离。
这之后的人生便基本固定在了这个城市,求学、生活、结识新的同伴,直到长大成人。也曾以为这里就是我的故乡了,但不知为何,总是觉得自己与这个城市之间少了那份亲近与真正的归属感。
少时的我想不明白原因,直到有一天,当一个人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离去了,我才终于意识到,原来在这个城市里的家,在这个城市里的青春记忆并不完整,它是缺失的。
母亲调动工作来到这个城市,也是因为她的故乡便在这个城市的乡下。这是她的故乡情结。在外久了的人,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能够离故乡、离亲人更近一些,心里也多了一份依靠。只可惜外婆长年生病,基本无法出门,自然也帮不上什么忙。家在外省的奶奶倒是有时会来看望,但我的大伯也是一位军人,老家还有几个同龄的堂兄弟同样需要她照看,只能来去匆匆。每次分别都抱着我们不肯放手,嘴里念叨着手心手背都是肉,泪眼婆娑,总是为难,想要一碗水端平,却反而都惹了埋怨。
父亲的部队离家很远,一年里只有一次探亲机会。长时间见不到他,我对父亲的印象都变得有些模糊。我时常分不清,在那些同样穿着绿色军装的人群里,哪一个才是我的父亲。我会时常叫错人,然后引来善意的哄笑和温暖的“举高高”,当然还有一旁母亲的尴尬。其实我是知道的,父亲不在人群中,我只是想他了,就是想喊一声“爸爸”。
很多年里,母亲都是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母亲的工作很忙,还要时常值夜班,所以我和弟弟基本上处于放养状态。白天还可以请邻居帮着照看,到了晚上,为了安全,就只能把我们反锁在家中。我们住的房子是民国时期盖的办公楼改建的,窗户巨大,还正对着部队小礼堂的大门。当礼堂里有电影或演出,看到别的孩子被大人领着,有说有笑地去看电影或在门口院子里玩耍,心里就感到委屈。兄弟俩会一起扒着窗户栏杆,像被虐待的囚徒一般大声哭嚎,那叫一个惨烈,引得看管礼堂的战士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匆匆去唤来母亲。自然,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一顿胖揍。
母亲揍人很凶,她会用父亲留在家里的旧皮带抽我们的屁股,一下子便会肿起一道和皮带一样宽的红印,很痛!我那时很傻,想要表现男子汉的坚强,不肯哭。弟弟看到我被打,自己还没挨上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所以母亲便轻易放过了他,只盯着我揍。不过我最多也只能承受三下,还是忍不住要哭的。其实我能体会母亲的辛苦,也一直很努力表现得乖巧听话,甚至武力强迫弟弟也要像我一样乖,但显然这只是一厢情愿。
不过,住在部队的院子里还是有诸多好处的。母亲忙于工作,几乎很少有时间做饭,便可以委托警卫连的战士领着我们去吃部队食堂,小青菜烧肉圆、土豆红烧肉、喷香的大锅饭,我童年对美食的记忆大都是从那里获得的,即使现在想起来也仍然垂涎不止。
年轻的战士们精力充沛,无事之余会领着我们这群孩子玩耍,教我们踢球、游戏,教唆孩子们之间摔跤打架,胜者便可获得触摸他们步枪的权力。这可是真的钢枪!黝黑的枪身、雪亮的刺刀、好闻的枪油味儿,只是摸一下都会兴奋得大叫,如果再表现得好些,还有可能去拉一下枪栓、扣动一次空枪扳机。这种诱惑我们男孩子哪里能抵挡得住?于是个个杀红了眼,奋勇争先,不肯言败。大人们似乎也希望看到这些,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支持。当然,从战士们身上学到的,还有一些偷奸耍滑、捉弄使坏的点子。所以,在学校里,我们这些部队子弟多是比较顽劣调皮的。上课说话、传递“鸡毛信”、用捉来的小虫欺负女同学那是常事,我就常常被老师罚站或是放学时被留下来训斥,也让我从小有了“吴老留”和“吴老站”的外号。现在回想起来,好笑之余,倒也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因为童年缺少父爱而让性格变得柔弱怯懦,只是委屈了那些年教过我的老师和同班的女同学了。
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裕,城乡间的差别也很大,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拥有一个城市户口,便是一种身份,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于是那些生活在乡下农村里的亲戚们,对我们家便平白地多了一份客气与敬重。父母自然也常常会接济一下他们,一些多出的衣服、不用的物品,常带回去分给大家,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一到逢年过节,总是大包小包的拎去,再塞满了蔬菜土产拎回来,我们也自然成为了村里面最受欢迎的客人。
每到暑期寒假,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母亲实在无法分心照顾,只好将我们兄弟俩一股脑扔到乡下外婆家里。那时城里远没有现在的繁华与热闹,就是电视机也不是家家都有,因此反而不如乡下来的有趣,有大群年龄相仿的小伙伴,有各种新奇古怪的事物,更重要的是没了母亲的管束,自由自在,被人尊宠着,享受着待为上宾的礼遇,也满足了孩子那份懵懂的虚荣心。
每到假期快要开始的时候,舅舅就会准时来接我们。我和弟弟便兴奋雀跃地收拾起自己的小书包,除了作业,最烦恼的是该带上哪些可以炫耀的玩具,哪本小人书表兄弟们应该还没看过,当然还有母亲专门准备的糖果零食。挑来选去,终是有些好的舍不得都带去,放进书包又掏出来,偷偷藏进五斗橱抽屉的角落里。
从城里到外婆家,要先坐长途汽车到县城,再搭乘顺路的拖拉机到镇上,之后还得走上近5里的乡间土路才能到村里。很小的时候,舅舅总是会在镇上相熟的朋友那里寄放上一副扁担,等到了,便用竹筐把我们哥俩一前一后挑了,扁担吱呀吱呀地响了一路,我和弟弟便在那筐里甜甜地睡着。等长大些,就换成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记得是永久牌的吧,大杠和后座会专门裹上厚厚的棉布。仍是一前一后,弟弟坐在前面,总是一边笑着,一边调皮地不停按响着铃铛,我则坐在后面,搂着舅舅的腰。舅舅通常都会穿上父亲送给他的旧军装,这在那个年代是最流行的装束。于是,我时常在朦胧间将那绿色的背影幻化成父亲的样子,脸颊贴在军装上,鼻间嗅着浓浓的男人汗味,却不舍得放开。
对于孩子们来说,夏日的乡下,白日里总有着无穷无尽的可玩之处。钓鱼摸虾、上树打枣、捉青蛙抓知了,整个村子里到处是我们的身影和欢笑声。玩饿了,便会跑到村里的豆腐房讨碗新出锅的豆腐脑,乡亲们纯朴好客,可着劲地让我们放开吃,每次都是捂着肚子蹒跚着走出来,打着嗝都是浓郁的豆汁清香;或是看上了那甜美的西瓜,明知看瓜的爷爷不会追赶,也要学着电影里的战士那样,匍匐着爬进瓜田里,逮着一只瓜也不管生熟便摘下,然后抱着疯狂地跑,看瓜的爷爷便在身后笑骂着:“小兔崽子们,慢点跑,别摔着了!”
乡下的夜晚却是有些难熬。那时农村用电灯还是奢侈的,平常家里多是用煤油点盏小灯,昏昏暗暗,火苗飘忽,家里的光线始终是在不停地晃动,烟火将白墙熏得漆黑,屋子里总有一股散不去的煤油气味,也更添了一份燥热。于是,天热的时候全村的人都会搬了竹床、草席,到傍晚时已经洒过水的晒谷场上,四周的小树林会给空旷的晒谷场带来一缕缕清风,消去了人们的暑气,也吹散了蚊虫。大人们聚在一起拉着家常,孩子们在一旁疯跑嘻闹,跑得累了,被大人唤回,用冰凉的井水冲去一身的臭汗,便捧着瓜果,躺在席上,望着那漫天的银河,一颗一颗闪动着,仿佛就在眼前,伸手便可触摸得到。待夜深时,静静的一弯皓月将大地映得一片雪色,几只萤火虫微弱的光在人边、丛中闪烁,整个世界便只剩下那轻拂的风与蛙声虫鸣。
到了冬天,河里结了冰,也没了那些瓜果吃食,生活要枯燥乏味许多。江南没有暖气和火炕,可那粘在身上的湿冷,让你即使待在屋里也冻得瑟瑟发抖。外婆家里有一只用稻草编织成的像澡盆似的物件,脚底下是空心的,用几根间隔的木棍撑起,大人将灶膛里燃尽的炉灰或火炭用铁盆装了塞进那空当里,人坐在里面,热气腾上来,身上再盖上一床棉被,便成了极好的小火炕,只是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物件叫什么。
这原本是外婆冬天里用的,我们去了,外婆便会掀开被子,把我们紧紧地搂在怀里,一遍一遍地亲,总是亲不够。还会偷偷从怀里掏出两颗已经焐得快要融化的糖果,一人一颗塞进我们嘴里。糖果很硬,远不如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大白兔好吃,但看着一旁眼巴巴地望着的表兄弟,心里还是得意。便有些忘形,将糖果从嘴里抠出来对着他们炫耀,却被眼疾手快的表哥一把抢走,囫囵地塞进嘴里,一溜烟跑个没影。
对于这种行为,表哥肯定是要挨揍的。我也怀恨在心,思量着这回带来的零食要少分些给他,可看着表哥被舅舅揍得哇哇乱叫,倒又有些不忍。整个冬天里,这小火炕几乎都被我们兄弟俩给占用了,那时候自己还觉得心安理得,现在想来真是羞愧。亲人们其实并不是在乎你为他们带去了什么东西,他们在意的只是这份亲情,也是中国人传承千年,内心里最纯朴的待客之道罢了。
好在冬天里还有一个快乐的大年,而且农村里过年的气氛要比城里浓厚许多,家家户户贴春联,挂年楣,也把时常舍不得吃用的零食取出来尽情享用。自制的花生糖、炒米糖、脆锅巴,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大快朵颐。
最热闹的当然还是村里杀猪。青壮的汉子们将养肥的猪四脚朝上地绑了,用担子抬着去屠户的家里,猪嗷嗷地叫,我们前呼后拥地跟着跑。但真当屠户将刀捅进猪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时,我们又吓得紧紧闭上了眼睛。随着猪悲惨的最后一声嚎叫,浓郁的肉香开始在村里漫溢开来,这年就算真正开始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父亲快回来了。
离着大年三十还有好几天,我和弟弟便会每天跑到村口去等,一直等到那个绿色身影的出现,便一起大呼着冲上去,一人抱住父亲的一条胳膊,说什么都不肯再松开。父亲每次都会用他的胡子扎弄我们的小脸,看到我们皱眉的样子便畅快地大笑,然后将我们一边一个放在肩膀上驮起,大步地往家走。我和弟弟搂着父亲的脖子,争抢着去抚摸父亲军帽上那颗闪亮的五角红星,红星闪着,映亮了我和弟弟兴奋的眼眸。
到了晚上,我必定会和弟弟一边一个躺在父亲身边,缠着问他手枪带回来了吗?院里的孩子们都已经摸过他们父亲的枪了,可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呢。父亲总是搪塞着,却也答应一定会让我们见到。每一次纠缠无果之后,只好逼着让他讲故事给我们听。父亲文化不高,没有读过那么多书,所以他只会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说他因为灾荒没有饭吃,饿啊,饿得难受,邻里的乡亲在最困难的时候给家里送来一些米粮,他才没有饿死;又是哪些叔伯在他还是孩子时帮着处理爷爷的后事,或是曾经帮着盖过房子,都要记着,得感恩呢。故事已经重复讲过很多次,说得也不动听,但他会非常认真地说,一板一眼,像在训练他的士兵,我和弟弟却早已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是把身体用力地挤进他的怀里,呼吸着父亲身上让我们迷恋的味道,直到满足地沉沉睡去。
大多数时候,也只有过年才是我和弟弟在一年中唯一能见到父亲的机会,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在那几天里,我们嘴里总是“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像两只跟屁虫,天天跟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会尽量陪着我们,领着我们走家串户去拜年,下雪的时候会和我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晚上也一定要陪着我们睡着才会离开。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每次新年过后没几天,父亲就得匆匆赶回部队。他总是会选在我们熟睡的时候悄悄地走,等我们醒来见不到人影,便会整整哭闹一天。渐渐的,等我们长大一些开始懂事,知道父亲终是要离去,便不再哭闹。只是在知道他要走的时候,我会佯装着在床上睡着,感受到父亲在我们脸庞上轻轻的一吻,一声淡淡的叹息。待他转身离开,我偷偷地睁开眼睛,看着他的背影,那个绿色军装,虽不高大,但在我心目中却是最健壮伟岸的背影。
父亲每次走到门口时,总要回过头来再望我们一眼,看到我睁开的眼睛,他会了然地一笑,将手指放在唇间做个噤声的示意,让我不要吵醒睡梦中的弟弟,然后做个鬼脸,潇洒地离开。我的眼中已满是泪水,却忍着不敢哭出来。
一年又一年,日子就这么重复着。在我已经上了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年春节,母亲一个人独自回到了乡下。我们问她父亲呢?母亲当时的表情有一些僵硬,但还是笑着告诉我们,父亲在部队工作忙,今年没法回来过年,但已经寄了礼物回来给我们。礼物里除了一些部队当地的特产,还有两把用步枪弹壳粘成的手枪,是专门送给我们兄弟俩的。枪的做工有些粗糙,显得制作得有些匆忙,但我和弟弟仍是爱极了那两把枪,用皮带扎在衣服外面,手枪别在腰间,每天都耀武扬威地向小伙伴们显摆。
在那几天里,大人们也从不在我们跟前说起父亲。但在晚上睡觉时,却总能听到堂屋里大人模糊的话语,间杂着外婆与母亲轻微的抽泣,我终于隐约地知道,父亲好像是去打仗了,在祖国的南方,那个靠近越南的地方。
那时的我根本无法理解大人们的担忧,因为在我孩童的理解中,解放军永远都是战无不胜的,父亲一定会成为一个大英雄!那天晚上我是含着笑睡着的,在梦里,父亲的形象和那些电影中的英雄重叠在一起,五角的红星和那红旗般的领章把父亲的脸映得通红,他在看着我笑,手指放在唇间做个噤声的示意,然后做个鬼脸,潇洒地离开,背影渐行渐远,一点点,一点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在睡前也会缠着我讲故事。我会给他讲爷爷头上的红五星,讲吱呀吱呀的扁担声,讲那个不知名的小火炕,讲老屋里晃动的灯影,而待他睡着,自己却噙着泪水,久久无法平静。也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原来牵挂了那么多,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的人生,也是我的来处,或许这便是故乡的意义。
哪里是我真正的故乡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记忆中有着浓浓的爱,有爱的地方便是故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