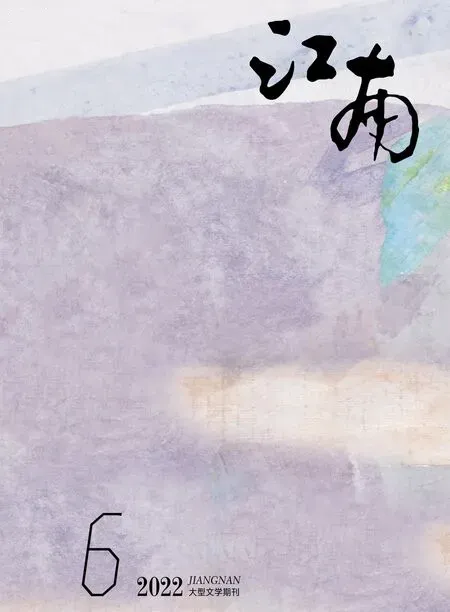俊游踏歌
——美西夏行履迹
□ 苏 炜
一、 歌头:一线瀑—— 波特兰马特诺玛瀑布
白银一线,自山巅倾下。磅礴水声,若近若远,却似从天外飘来。晨风清爽,掠面生芳,仿若热岛中牵出的一脉涧泉,冷沐身心。我等拾阶而上,薄薄的水雾飘降,被初阳一打,石桥变成了虹桥,生色生光。
我站在桥上,眺望不远处的哥伦比亚大河,深流静默,波鳞不惊。身后的贴崖瀑布,则像一束山神的教鞭,抽打着嶙峋山石,发出裂帛的低吼,一若警语轰鸣。水声屏蔽了尘音,我忽而被箍在了静独里。——自我,他者。片刻的抽离,片刻的面对。人生海海,俗世滔滔。寂默一若长夜,独语则如见天星闪烁——
— 是瀑是涧?或涧而成瀑,瀑再而为涧?一线的单纯,一线的丰富。自高而下,因下而高。为热惜冷,因冷知热。跌宕因所求,求之必跌宕。掬水之力有限,有限却缔造永恒。无尽倾吐成有,有则倾吐无尽……
难道,这些,都是她——这遥碧一线,想要昭告我的么?
二、玫瑰魂——波特兰玫瑰园行走
花香,是一个城市的体味。花香,也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我来到这里,仿佛就是为着寻觅这形而下的体味和这形而上的灵魂的——是么?
石头拱门上,铭刻着莎士比亚的名言:万花之中,玫瑰为冠。此刻的她,红黄蓝紫,重重叠叠连山接岭滔滔滚滚地奔涌而来。花瓣或蜷曲或傲张,绽放得这样放达、嚣肆,不管不顾。这一丛翘挺,花骨朵儿拳打脚踢的;那一枝却孤立,只一球巨朵峥嵘怒放。忽而又散散漫漫,东藏一点红西遮一点紫地含羞带嗔,姗姗而来;忽而竟满坑满谷,一个纯色便倾冈夺岭如潮汐起落。细看,却是朵朵眉眼低回的,花瓣儿百啭千曲地似有无尽惆怅哀怨,翻卷着簇拥着向你默默倾诉……你红唇欲语,我可以与你握手相晤、把盏言欢吗?你又淡墨如染,渐染渐深,可以告诉我你属于哪一个花品的色谱色系吗?……毒日泼油,山风剧烈,都压不住你迸张的势能、震慑的群力,以及席地倾天的气场——你,既是莎翁之最爱,难道就不可以也成为我这微末人生的一点天启——或一脉闪电,或一眸秋波,甚至——一道符咒么?
——美,就是应该这样霸蛮泼剌地生长的。因为美,即是自由,即是生命。美,又是有着带刺的自尊的,不要轻易想要攀摘她、依附她或者损毁她。欣赏美,要带刺地欣赏。因为有棱有角的个性,是美的“标配”。每一种美都是独立自适、不可替代的,不要想用牡丹或者荷莲的美、百合或者幽兰的美,去覆盖她、屏蔽她、附庸她。借用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的一语:玫瑰,其实属于某种“燃烧的荆棘”——她性格尖锐火烈而具燃烧的品格。为着美的尊严与追求(也包括她不言自明的造福世人的宏愿),她戴上了荆冠——那是将充满荆棘的生命之力全部释放, 才绽放出如此绝美光华令群芳失色、众生销魂——那是凤凰在烈火中涅槃再生一般的独特伟力和霸蛮品性——美,果真是需要征服与被征服的啊!
热风如灼。我躲到了花架的凉荫里,忽然闻见一阵阵袭来的浓淡清香——波特兰,那是你散发的体味么?或者,是你灵魂燃烧的香味?
三、禅踪——日本花园行
仰翘的竹节水筒,在涓滴坠重后,蓦地一倾,水注瓮池,又复仰回去,再涓滴往还……
四山环静,在为这俯仰之倾注目。
仿佛是火烈之美的前世今生,刚刚步过红红火火的玫瑰园,这里的静穆,顿时将那“体味”与“灵魂”,融化在这苔苍石碧、竹青松瘦里。——空疏。疏朗。疏远。一个“疏”字,成了园林的韵脚。是的,命运曾有的浮沉安排,自然具备的神秘逻辑,以及俗世生活的无尽谜底,都应该可以从这“疏”里寻找问询与答案——低眉的草木,曲隐的小径,端守的石塔,抖颤的溪光……一若云止于青空,行停于流水,梦消遁于烟岚,俗尘,浣洗于清池里。诗人索菲亚·安德雷森说过:“夏日是休息和节日/瞬间饱满得像一枚果实/我们的身体和自然亲如一家”。生命行脚需要停顿,这是夏日成为世人假日的共同缘故吧。正如丘壑需要一道烟霞,灵魂需要一片净土;正是带着这枚“饱满得像果实”的肉身,我们想将丰满释放于虚空,才可能在夏之节日里捕获到一霎清凉;正是在此一刻与自然的亲密交融,我们才可以将“诗与远方”蓦地拉进怀抱,廓清俗世的诸般烦恼,获得一段透明纯真的呼吸。
哦,“无用之用”。原来求的真是“无”,而不是“用”啊!
四、月荷——兰苏园小驻
明明是天光昼白,又是此地破纪录的热浪腾嚣,我却偏偏执念于静夜月色下的想象——眼前的荷塘、曲桥、菱窗、回廊,在淡淡的月色下,会是一番怎么样的景致呢?
日本园林追求“无”——“枯山水”里的枯寂之美,是需要慢步驻足,细味细品的。中国园林尤其是苏州园林,却追求“有”——多变,巧借,曲折,小中“有”大,环转“有”景,狭角里“有”丰富,无空间不风景。如古贤所言:“地只数亩,而有迂回不尽之至;居虽近尘,而有云水相忘之乐。”与日本园林的刻意空疏不同,此刻的兰苏园,却是诚意拳拳地“满”。这件姐妹城市苏州送给波特兰的隆厚礼物(故名“兰苏”,却不甚高明),满满的景观里充盈着满满的精致,连一个转角、一道石阶、一叶棂帘,都经过了仔细雕镂。于是满满的水榭亭阁,便载着我等游子满满的乡愁——连荷塘边那一支翘挺的红莲,都红出如同天安门城墙的那种“中国红”,或者张大千莲画里独有的夺眼艳色,可谓红得超绝出尘却又满带烟火气。因之,我才会在眼前热夏的“有”与“满”中,想象月色荷影、石漏虫鸣的幽静,想象疏窗灯读、鱼戏晚晴的清凉,更想象台阁亭廊与匾额楹联间,横着的那一缕淡烟……
似乎略带刻意,我和妻坐到了竹林下的茶点部。她要了一杯石榴汁,我点了一盏龙井茶。疫情中难得地享受着远土新茶的清香,我们感慨着:刚才听到的园方洋导游向游客作的英语讲解,其深厚的汉学底蕴,将园林旨趣表述得漂亮而自然精准。“万花敢向雪中发,一树独先天下春。”我仔细聆听她讲解“沁香仙馆”里的此一楹联,她解说出雪花纷飞而红梅独美的隽美意境,引起游客中一片赞叹之声。那一刻,我看见一双双蓝绿眼睛,如同荷塘莲灯一样地亮了起来。洋风洋水中,眼前美轮美奂的中式庭园——这一缕中华老酒的馨香,在西语的吐珠漱玉里飘洒挥发,真的让我俩——同在此间大学教授汉语中文的“耕语人”,动情亦动容了。
——“荒漠甘泉”。忽然从凌乱布满流浪汉帐篷的街市,步入如此古雅精美的园林,此语曾蓦地涌上我心头。可是随即,我却解嘲地笑起来。其实,我们所有人,何尝又不是人生荒漠中流浪的过客?只是,那遥远故土的一束古老微光,化作了眼前尘俗世界里一脉甘泉,掬捧着她,享饮着她,你我,又可以再上路了。
五、飞翔之惑——西雅图飞行博物馆感怀
“玲珑的生与从容的死。”这是林徽因追悼飞机失事的徐志摩写下的诗句。步入这个名曰“飞行”的博物馆,入门厅堂里,高悬的就是两架人类最早想跃飞蓝天的原初布翼模型,让我忽然想到徐志摩那篇似乎述及他的宿命的散文《想飞》,也让我把这百感交集的“死生”二字,嵌入了眼前这个专述雄飞壮想的豁达空间里。
人类的飞翔之梦,首先得自鸟的启迪。徐志摩把它称作“上帝给它们的工作,它们替上帝做的工作”。波音公司创办的这个飞行博物馆,却记录着人类追求飞翔的诸般好梦、美梦及其噩梦、畸梦。仔细算算,从背负青天的机身机翼,到遨游太空的星舱银臂,人类把雄奇璀璨的飞翔想象,从布翼玩具化作铁制仙躯,从折翼坠身到月球漫步——自1920年代至1960年代(美国登月之旅为1969年),花了仅仅是区区的四五十年!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当年在踏上月球表面的时刻,曾道出了一句被后人奉为经典的话:“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整个人类的一大步。”然而再仔细想想,贯穿在此高速飞升的奇迹伟业的“从”与“到”之间,其驱动想象与创造的最大动力,是什么?竟然是——战争!是大国暴力的追逐竞争,是人类之间的相残杀戮!眼前这些“国之重器”,其实大都是“战器”。看着从一战、二战战机的笨拙粗糙机身,到当下极速超音机、隐形机、无人机漂亮流线形的提升,笼罩在这“漂亮”背后的,竟是敌我鏖战、生死厮杀的淋漓鲜血、白骨盈野啊!玲珑的科技与惨烈的死亡,竟然需要统一在、捆绑在如此壮观、如此灿烂的人类想象果实里,这,难道就是“玲珑的生与从容的死”之意义么?这样的飞翔,难道也是“上帝给它们的工作,它们替上帝做的工作”吗?!
是的,当我这样的“反战分子”从“美轮美奂”的飞翔产品后面,看到了死生,看到了烽火,看到了残忍,更看到了惨酷——飞翔之翼一变而为思考之翼,步履,就变得沉重不堪了;灵魂心智,更变得难以安生安顿了。我的参观行迹,也就不能不深陷在这“生死”“爱恨”“善恶”与 “战与非战”的情绪纠葛里。然而,作为入世之人、理性之人,我又深知:正如任尔飞翔的“空间”与“太空”不可能有一清如洗、纯澈无垢的“空”一样,从野兽进化而成的人类以及这颗俗人俗世赖以生存的蓝色星球,也不可能是纤尘不染、至善无邪的乌托邦、桃花源和香格里拉。——“恶”,也包括各种排他性的“征服欲”“占有欲”“贪婪欲”等等,可以造就仇恨,也可以激活创造;可以毁损生命,也可以拯救苍生;可以造就资本消费,也可以创制繁荣发展和人性福祉……这就是世道的悖论——那只人类欲望的“看不见的手”的善恶悖论。以暴易暴(而冤冤相报)、以武制武(而武之难辍),这已经是人类社会古今运行无以规避的轮转逻辑,也是我们这个“龌龊卑微的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龌龊卑微的现实”,却又是当今时世——已经进入晶莹通透的信息时代、云计算大统计时代与AI(人工智能)时代,最原初最起始的“内驱动力”!于是,在武力与暴力面前,同时包孕着血光与死亡、智慧与创造的飞翔大梦,就同样无以规避地需要面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峻严抉择了。
由是,我忽然找到,整个飞行展览中,为什么下面两个“飞翔画面”最让我动情动容的具体因由了——
站在机头画着鲨鱼牙齿的古旧战机——1940年代二战中美国援助中国抗日的“飞虎队”战机面前,走进1972年尼克松破冰访问中国所搭乘的“空军一号”的机舱里,心弦,两次都忍禁不住地微微抖颤。不仅仅是时空隧道的穿越,这样两个前后并置的“平行空间”(此乃当今科幻小说与电子游戏里的熟词),将我的灵肉之躯与真实视界,先后同时放进了两个机身的铁盒子里——据史料,当年穿越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的“飞虎队”及当年的美国空军,在支援中国对日抗战的三年驼峰航线中,共损失飞机一千五百架以上,牺牲飞行员近三千人,损失率超过百分之八十——这,这是一个怎么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数字?!这里还有尼克松和周总理两位中西先贤的彩色塑像,搂着塑像拍完照,从舷梯踏入机舱,我的眼角一直是湿润的——承载着当年穿越无数险阻障碍的美中破冰之旅的这个狭小空间,有机玻璃覆盖着的每一个隔间、每一行皮座,都还能听闻到遥遥传来的时代裂变的轻悄足音,触摸到改变历史的那一个瞬间的时代体温啊。——以人类相通相系之本性大爱,以为辅助正义抗争而不惜捐躯千百的牺牲精神,她——这个“她”“它”“祂”,超越了那个排他性的“征服欲”“占有欲”的利己算计与种族算计,更超越了那个为武不尊、冤冤相报的“世代逻辑”——这是一道爱恨交加而由恨转爱,由种族相惜、沟通、合作转换为普世大爱的盛大旅程,此刻的飞行博物馆,为“她”“它”“祂”,留下了最可观、最“铁实”的历史见证!
走出博物馆,友人的车子特意带我们,绕着停机坪上那个“B-52”轰炸机的巨大机身转了一圈。因为我告诉年轻的他们:“B-52”属于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谈论着这一段历史上同样与飞行有关的血火奥秘,我忽然对适才在“战器”面前的步履迷惑感到释然了。——飞翔,就是凌空超越;飞翔,就是诗展开的翅膀。就让飞翔之美,超越尘世的诸般恶念恶忆恶俗恶事吧!此一刻,徐志摩的那篇《想飞》的句子又浮现眼前:“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
六、雪山盟——对话雷尼尔雪山
雪,从来是我心中的图腾——雪花,雪浪,雪山,雪原……为她的皎洁通透,为她的纷繁浩缈,为她的无声无色,更为她的——美与力。因之,将耶鲁书房命名为“澄斋”,家居为“衮雪庐”,与友人共用的微信公号呢,则曰:“雪落大河”。
雷尼尔雪山,更应该是西雅图人的图腾吧。或许因为,此雪山,大概是北美大城市中,唯一一座遥嵌在城市当头、可以与之朝夕相对的宏大景观(外形,则逼肖日本的富士山)。正值破纪录的“热月”,来到此地,人们会随时提醒你抬头远望:在哪里哪里、什么什么天色,会看见怎样怎样的雷尼尔雪山。盛夏酷热里,依旧白雪皑然的那道曲线,真是望一眼都教人沁心清凉。因为路远(所谓“望山跑死马”也),雷尼尔本来并没有在我们此行计划中。可是经不住当地友人的一再热荐——正如“不登长城,何以说到过中国”一样,不访雷尼尔雪山,你也就不算来过西雅图呀!
早起,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跳下车,当这座五十万年前形成的休眠火山顶着凛凛白头逼临眼前,蓦地,我真有一种被迎头一拳重击的感觉。大雪山赤裸的胸膛与起伏脉络向你陡然敞开,清冽的山岚裹挟着苍黛林影围拢着你,巨大的山体与你坦荡相对——这么近,这么近!那盈眼的雪白里,是有明暗、有哀乐、有情绪根脉的。山体走向在向你倾斜,雪山在与你倾身对话。我望着他(雄性的、哥们儿的“他”)说:我来了,你还好吗?热浪当头,谢谢你送来这般的净界清凉啊。他对我笑笑,沉默不语。坐下来,觉饿而打开了备好的午餐,我又以水当酒,举着水杯对他说:陪我喝一杯吧,难得我追着你,或是你陪着我,走了这么一个酷暑长程。我喝下了我的“水酒”,他又对我笑笑——此时一阵烈风掠过,紧了紧衣领,他又回复到那片皓然沉默。我向他的胸脯走去,他扬起了漫坡的野花迎接我——星星点点,黄白紫红,漾拂着、簇拥着向我点头。我来到克里斯汀小瀑布前,掬一捧冰凉的山水洗了把脸,我知道这是他在用雪山的乳汁,为我的倦容醒面醒脑;转过山湾,我又来到另一个纳拉达瀑布前,眼前白练飘飞而啸声震耳,我知道他是在用涧泉清响,为我的役劳盲目醍醐灌顶呢。我搂着搂不过来的千年老树伤痕斑驳的树身,我抚着倒树切面巨大褴褛的年轮,我知道他在用一种老者的声腔,上路前向我唠叨叮咛;我频频回首为他的峻美容颜不舍留影,他就用一种葱绿的腔调对我说:不要光是顾着拍我呀,还有林间那些先人的小木屋呢,还有溪边那个泉眼仍在涌动的古井呢。——雷尼尔,这果真就是你的名字吧,作为一个心魂对象、一个大朋友老兄弟的名字。我吆唤着你,真的不觉得你就听不见,也不觉得你就离我那么远,那么不着边际啊!
——山盟海誓,说的是对爱情的承诺吗?青天朗日,我与你的痴诚对话,难道就不算一种“盟”吗?没有目的,没有终点,享受旅途本身,享受和大山大野、万籁自然对话的过程,这也可以算一种“盟”——生命与自然之新“盟”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乃禅宗最知名之偈语。今天,我千里万里奔你而来,可是“远来有一物,借你拂尘埃”哦!——噢噢,我又想起《坛经》里那个古老故事了。我这究竟算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呢,还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呢?这算是“入禅”了呢,还是“出禅”了呢?六祖慧能言:心去除了妄念,复归清净,叫做“明心”;心思清明澄澈,自性便无遮无蔽地显现出其本来面目,就达到了“明心见性”。——哈,这,可不就是“雪”的根性品格,“雪”的图腾本义么!你啊,“亦非台”的雷尼尔雪山,正是这样一柄立在大地高天的“明镜”,你是在为我作“明心见性”的烛照,为我披上这件“明心见性”的雪白袈裟啊!
谢谢你,雷尼尔。
七、玻璃花之悟——奇胡利玻璃园巡礼
——真有超越自然之美吗?以往,幼齿年代,我曾笃信过“人定胜天”而投身“战天斗地”;“成熟”年华,又曾鄙视过“人定胜天”而深信:自然的伟力,是人不可轻慢而必须敬畏的。但是今天,此刻,美,果真突破了这人天之隔——她是人造,更是天成;既是人创,亦是神功;美可撼人,更可通神——因为我站在了西雅图“太空针”高塔下的玻璃花面前。
这座以个人名字命名——名曰“奇胡利玻璃园”,可以成为西雅图最大地标——“太空针”高塔下的永久性博物馆 ,并且是当地旅游攻略热推的“网红打卡地”,我本来是带着几分踌躇疑惑,步入这个不起眼的小窄门的。因为幽暗,展厅完全不用自然光而用灯光投射,我马上有一种“陷进去”的不祥感觉,却转瞬、随即,就被眼前的景观,嘁里哐啷、丁零当啷地震慑住了!——视网视觉,一时被各种魔性的奇异冲撞着、挑衅着、冒犯着。各种玻璃成品炫目夺睛的奇特色泽、造型,仿佛可触可感的诸般花朵、贝壳、浪花、火焰……或者一枝独秀,或者交织重叠,要么妍丽欲流,要么娇嫩欲滴,要么澄澈欲染。这边,在头顶形成一片艳朵叠加的光影长廊,观赏者仿若潜行于深海之下;那边,平台上纠结成一堆抽象的烦恼丝,如同伸拳踢脚,如同电蛇乱舞……魔幻,怪异,超现实,反自然——却超常地撩逗着你,诱惑着你,更超常地“治愈”着你。很难想象她们——它们,是怎样从千度高温的红火流浆里,吹塑扭铸成如今的奇思怪状的。最令人目眩的,仍旧是色彩——在日常自然的光影下你难以见识到的,每一丛每一瓣玻璃上那些夸张变幻的异色奇色。那是比日常视线下的任何虹霓霞彩、花朵艳色,或者国画泼彩、油画调色盘等等,都要更恣肆、更奇葩也更疯狂的色彩。
是的,自然之美——如江河山川之奇伟,梅兰竹菊之隽永,青砖黛瓦之温馨,小桥流水之清丽……确是永恒而不可替代的;但眼前人造的奇景却在一刹那屏蔽了伟大的自然,让我们瞬间坠入一个仿若天堂(或者地狱)一般梦幻惊怖的情境与诗境里。不错,诗境——这是一场异彩的交响、奇思的盛宴,以及——极致美的淋漓洗礼。及至步出园区花园,那些参差崛现、与乔木争秀的玻璃奇件花树,就更似一场与观者共舞的节庆狂欢了。——“不疯魔,不成活。”忽然想到这句艺坛老话。你甚至可以想象创作者沉浸在创制过程中的迷醉癫狂状态。我由此想起,此间很多似曾相识的奇俏作品,在以往加勒比海的豪华邮轮上,或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宫殿里,都似曾见过她们的奇丽之影。据作品说明,1941年出生的创作者戴尔·奇胡利,正是土生土长的华盛顿州小镇人,甚至所受的艺术教育,也只是在我们刚到西雅图时就造访过的州立华盛顿大学。但其玻璃作品,今天已成遍及全球各种博物馆、艺术展的“标配” 常客与超值宠儿了。我流连在炫丽异彩间,在默默忖思:平凡无奇的出身经历,语不惊人的作者自述(他不断提到母亲儿时讲的故事、海浪形态或热带雨林景观对他的启示),是如何造就出这么一位享誉世界的顶级玻璃奇才的?
想象力—创造力。创造力—想象力。此一刻,这两个词语,在我眼前反复循环地滚腾、撞击。想象力,正是人类智慧之冠上那颗最耀眼的宝钻,也是人类今天所有智慧结晶、奇迹产品的最大驱动力。“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曾读到俄苏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这句话。她把自己的诗歌称为“抒情的冒犯”。其实,一切富有想象力的创造,何尝又不是一种“激情的冒犯”“力量的冒犯”“活力的冒犯”和“偏爱的冒犯”?!借用一句流行网络语:“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对于眼前的奇迹创造者奇胡利,或者对于任何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真正的艺术家、行动家,可以说:“每一个不曾让想象力、创造力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冒犯与辜负啊!”
八、歌尾:安得骑鲸从李白——碧海观鲸记
文题,得自东坡贤弟苏辙的诗句。据云:“骑鲸”一说,始自关于李白的言说。其实,诗仙李白的成仙梦想里,骑过羊,骑过黄鹤,骑过白鹿,甚或骑过青龙(“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却独独就没有骑过大鲸鱼。“骑鲸”故事的来由,传说是李白酒后水中捉月而溺毙,此时就有一条鲸鱼游过来,驮着李白飞到天上去了。宋人梅尧臣的诗作曾如是描写:“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如果再掉书袋,“骑鲸”之说,可是其来有自呢。宋玉在《对问》里说:“夫鸟则有凤,鱼则有鲸。鲸鱼朝发昆仑之虚,暴鳍於碣石,夕宿於孟诸。”可见,古人早把海里的大鲸,比作天上的神鸟凤凰了!
——可是今天,我忍俊不住地雀跃:真的吗?果真吗?俺们要追从李白,出海观鲸甚或骑鲸啦?!
海风凛冽。听从友人建议,登船前就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乘坐小游轮从普吉特海湾出发,前往圣胡安群岛——被称为“西雅图秘密乐园”的海峡海湾,去邂逅每年四月到九月必从此地经过停留,再迁徙到阿拉斯加的虎鲸和灰鲸家族。都说:大海是个剧场。眼前沧海茫茫,碧波滔滔。空间阔大、座椅宽敞的船体浮游在水天之间,一下子显得这么渺小,像一片飘落的枯叶。我忽然想到普希金《致大海》里那几个揪人的句子:“仿佛友人的忧郁的絮语……最后一次了,我听着你的/喧声呼唤,你的沉郁的吐诉……在你的荒凉中……一面峭壁,一座光荣的坟墓……啊,是拿破仑熄灭在那里。”(穆旦译本)不忌波涛抛摇,人们纷纷聚涌到甲板上,手机、望远镜、摄影镜头的长枪短炮顿时林立。果真,我们可以与那些号称地球最大生物的巨鲸族群——那些“大海里的拿破仑”,惊喜相遇吗?未待疑惑成真,船舷的左方右方的海面上,已经各露出几个游动的黑色鳍角,众人惊呼起来。这时站在船舱驾驶座顶部的船长兼导游高声喊叫起来:看,简妮带着她两个孩子,朝我们游过来了!他似乎很熟悉它们,直呼着它们的名字。可不是吗?一大二小的三条虎鲸正跳跃着从船舷边游过,黝黑的流线身影带着棱形的漂亮白斑,腾跳欢跃在浪峰上。刚刚举起手机勉强摄下它们的身影,它们随即便喷着水雾消失在碧波中。甲板上在一片惋惜之声中陷入沉默,人们的目光又开始向四方海面搜寻。不经意间,驾驶舱顶的大嗓门又已经吆喝起来。没分辨清楚船长在呼叫什么,却见一个巨大的灰色鲸背浮现在船舷一侧——哇!大灰鲸!一个鳍背已足足有半个船身长,下面的全鲸将会是何等体量?!——天呐,只要它稍微靠近,巨大鲸背顶扛起船身,小船岂不就真要“骑鲸而行”?!(不久前,电视新闻里确实报道过海钓船被鲸鱼顶起掀翻的画面)乖乖,只见它浮着灰鲸背和游船并头遨游了不到一瞬,马上就潜沉消失在深浪里,我重重呼出了一口大气。“……你觉得,鲸鱼知道我们在看它吗?”我问妻,也在自问自答,“我想它们是知道的,可能在和我们玩着藏猫猫呢。”此时的前方远处海面上,频频喷起串串水雾,跃动着小小的灰黑鳍角。舱顶上传来了导游船长的朗声大笑:“哈,那是一个灰鲸的家族在大派对呢!”
不消一会儿,游船已来到海湾海峡之出口。远远地,却传来了另一艘观鲸船上的鼓噪声。把手机镜头拉近了看,原来是一群虎鲸——足足有六七个跳跃的鳍角,大概又是个小家庭,环绕在船边嬉戏跳跃呢!一个个黑鳍角在水雾间跃动,周围的海钓小艇也围拢过来,形成了一个观鲸舞蹈的小圈子。可惜离我们太远,我们的游船本来是到海峡口追找大灰鲸的。看见过远远的灰鲸把水花喷得很高,船靠近,却又变得缈无踪影。此时天色在变,海景在变,惜才朗晴下一片蔚蓝的海面忽然变得灰紫暗沉,刚刚还是东一个鳍角西一个鳍角的虎鲸灰鲸族群,悠忽之间,都变得无影无踪了。舱顶上,一直手舞足蹈的船长,也久久哑了声。海浪无垠,迷茫一片,“海中拿破仑们”却久久再不现身。我又默念起普希金的《致大海》了:“……我最后一次在倾听/你悲哀的喧响,你召唤的喧响。/你是我心灵的愿望之所在呀!/我时常沿着你的岸旁,/一个人静悄悄地、茫然地徘徊,/还因为那个隐秘的愿望而苦恼心伤!”(戈宝权译本)海鲸之追逐,一下子似乎变得无聊无趣。甲板上的人们只好纷纷回到坐舱里。
果然是“大海剧场”——天地冷暖,盛衰兴灭,只在弹指之间啊。
我舍不得走,倚栏久立。——眼前,鲸鱼是有,还是无?适才的鲸舞人欢,是真,还是幻?哈,又来到那个“有”“无”的永恒诘问了。——我观鲸鱼,鲸鱼也在观我吗?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人之海上追鲸,不正如命运之追人、机会之追人一样,这种“有-无”之间的变化,是奇相,还是常态?是希望,还是无望?偶然孕育必然,必然却也时造偶然。其实,生命的固态才是真危机。生命生命,有生就有变,有变才有命。直面变化就是直面生机——“无”一定会生“有”,危机,也即生机啊!
归航了,仍未见鲸之踪影。烟波落霞间,我却晤见骑鲸的诗仙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