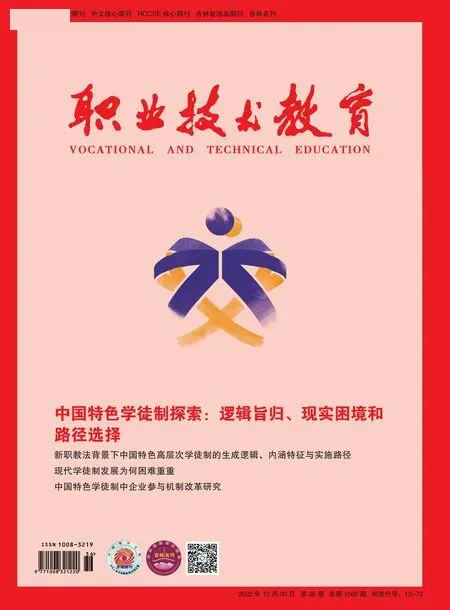近代中国第一所瓷业学堂兴衰动因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邢 鹏
清末维新志士熊希龄等人为振兴醴陵瓷业,积极谋划,多方奔走,最终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在端方、岑春煊等地方大员的支持下成功创办了“官立湖南醴陵瓷业学堂”。该校的创办率先开辟了我国近代陶瓷学校(主要指工业化制瓷方面的教育)教育的先河,为湖南乃至全国陶瓷学校教育、陶瓷产业现代化探索与实践作出了贡献。其釉下五彩的创烧成功,不仅将现代化制瓷工艺融入本土瓷业,更是直接奠定了醴陵瓷业在业界的地位。南洋劝业会上,醴陵瓷业学堂携手瓷业公司一举囊括了前三项奖项中的多个奖项,一举改变了醴陵瓷业以粗瓷为主供给当地民众使用传统印象[1]。本文通过史料爬梳和田野调查,对该学堂兴衰的历史性因素进行历史合力论分析,同时期望能对当下产教融合,尤其是职业教育改革有些许借鉴意义。
一、我国近代第一所瓷业学堂缘何率先诞生于湖南
洋务运动后,我国对瓷业的改革方兴未艾,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江西便开始探索瓷业及其新式教育改革的问题。然而真正付诸实践并创办成功的,则以湖南醴陵瓷业学堂为始。瓷业学堂缘何率先诞生在湖南,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近代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必然
近代以来,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随着外商在我国设厂贸易之后,洋货极大冲击了我国本土经济的根本稳定面。在陶瓷领域就曾出现“人民喜购外货,如中狂迷”[2]的局面,一部分先觉们认识到了“日用而不知”式的文化侵噬的严重性,急切呼吁实业与教育交互进行才能有效抵制外来商品及其文化的侵略。在洋务派、维新派士绅要员的推动下,清末新政时期,我国各地的基于相应实业的新式教育迅速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清末新政中新式教育法规相继出台,建立各级兴学机构,极大地激发了地方绅士投身于新式教育的热情。如国家层面于1903年设总理学务大臣、1905年设学部;省级层面于1903年设学务处;在州县一级于1906年设劝学所。根据清学部总务司编印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1909年全国设立劝学所已达1588所,劝学员12066人[3],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大力推广新学的态度和决心。另一方面则是因巨额战争赔款需要依靠实业征税聚财,从而倒推了实业教育的发展。在瓷业方面,时人认为:“中国苟能变通旧章,仿泰西各式制为杯盘器皿,以与交易,西人乐其适用,断无不欲购之者。”[4]基于现实的逼迫与时人共识,清廷在1903年至1907年间相继颁布了四项奖励发展工商业的章程,分别是《奖励华商公司章程》(1903年)、《奖给商勋章程》(1906年)、《改进奖励华商公司章程》(1907年)、《爵赏章程和奖牌章程》(1907年)。要创办实业,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就是没有相应的新式人才,因此,创办服务于实业生产的新式学堂成为当时的共识。
(二)近代湖湘现象发展的历史使然
湖南自古民风强悍、士风卓厉,这种地域文化基因发展到了近代,形成了“无湘不成军”“督抚半湘人”等近代湖湘现象。湖南士绅也受环境影响具有与生俱来深厚的“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民族使命感。甲午一战,一批批湖湘热血青年为了挽救国运于水火,通过“开学会、立学校、办报社、改书院”等一系列实际行动,广开民智、革除积弊、崇尚实学以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如梁启超评述道:“湖南……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夺矣!”[5]湖湘士绅的实学强国梦得以彰显并迅速成为主流,一方面受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掌管地方行政大权的督抚也有着密切关系。清末督抚的权力随着时局的动荡而迅速增长,他们在“开风气、革弊政、图富强”的政治大旗下,牢牢掌控着自己所辖区域内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便宜行事权,形成了独特的领导集团,从而使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型获得了强大的政治保障。当时《湘报》所载:“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6]近代湖湘文化在当时地方大员的积极革新推动下,形成了“崇尚实学,强国富民”的地域文化,并迅速发展成为了近代主流文化。
(三)内外交困下醴陵窑工的民生诉求实然
清末留学日本东京铁道学校的文斐先生在其《醴陵瓷业考》中记载,清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开设瓷厂,采用龙窑烧制工艺。同治元年(1862年),当地瓷业开始分为做坯、画坯、制泥“三帮”。光绪十八年间(1892年)醴陵制瓷规模达到历史之盛,窑户达480余家,龙窑100余座,年产800余万件。甲午战争的爆发,列强对我国的经济侵略空前。外国资本主义不仅带入大量洋货在我国倾销,还通过在中国内地设办工厂,榨取我国民众血汗。面对洋人的横行和洋瓷的倾销,湖湘志士们理性分析原委,发现洋瓷在资本运作、原料开采、成型技术、烧制工艺、技术传承及生产管理等方面均已进入工业现代化,而醴陵瓷业则仍旧处于农业社会的纯手工业生产状态。相对工业化进程中的理化分析、实验等科学手段,手工业中以感性经验为主的生产模式弱势明显,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各窑户资本不足;二是采取瓷土毫无规则;三是瓷土未能漂细;四是工人贪多求速,手法粗笨;五是瓷器色均带青而鲜洁白;六是用柴料购之远方其价极昂;七是窑户因无资本必向运商预贷”[7]。面对这样的局面,窑工们也逐渐认识到瓷业改良和革新的重要性,但囿于阶层局限性、知识结构的单一性,仅凭该股力量实难改变现状。故当熊希龄与文俊铎向当地窑户宣介醴陵瓷业改良的必要性,提出援入政府资金建新式瓷业学堂、引入社会资金创建新式瓷业公司并将新式技术义务传授于当地窑户的方案时,得到了广大窑工们的“围观延揽,络绎于途,鼓舞同声”的热切欢迎。由此表明,该瓷区具备了改革的内在动因,而且已到了迫切的程度。
(四)近代均利思想的合理化探索与实践
湖湘志士充分考虑到国家需要和社会需求之间、瓷业改良者与瓷业利益固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事物的主要矛盾入手,明确提出“均利”思想,并以之为原则进行瓷业学堂的前期筹建和后期建设工作。首先,“均利”思想体现在顶层设计上,在《熊希龄为湘省创兴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中明确提出,“欲兴工业……须分别专利公利两种,以定办法之次第,其中瓷业学堂的创办就属公利之举,公利就是为大众谋发展,为更多的人民谋福利”[8]。基于此,在振兴地方特色经济方面,熊希龄等人率先在湖南醴陵探索了一条在“均利”思想下的教育与实业相迭为用的改革模式。其次,体现在瓷业学堂的专业设置和生源构成方面,学堂初期次第开设了“速成科”“艺徒科”与“永久科”,即半年制技术培训班和四年制专业技术班。“速成科”主要学习“选土”“制釉”“烧窑”等工科类课程;“艺徒科”则主要学习“模型”“辘轳”“陶画”等艺术类课程。生源则在本地瓷业工人和窑户子弟中产生。最后,体现在筹建学堂不与民争利上。在学堂创办资金的筹措中,熊希龄极力向地方政府申请“公款”,并附切实可行的调研报告,以有效消除官方顾虑,“查醴陵现在粗瓷每年出数至少以三十万串钱计之,照厘局抽厘例,每碗价钱五十文,抽厘钱一文二毫,每百文应抽钱二文四毫,合计当有七千二百串之入款。窑业若衰,即此亦不足恃,倘改良制成精器,其所收厘金必有二三倍于此者。公家此后所获之益可预卜也”[9]。通过算经济账不仅成功打消了官方顾虑,同时还获得了官款支持,如此一来,瓷业学堂不仅能顺利地为省内外培养新式瓷业人才,还通过免收本地瓷工与窑户子弟的学费,取得本地瓷业界的踊跃支持。“均利”思想亦体现在瓷业公司的集资方案上:“该公司议招股本五万元,先有总理袁伯夔观察承认一万元,其余分寄长沙、常德、湘潭及醴陵本埠四处,招集以期利益普及。”[10]除此之外,创办者为了实现本地区瓷业改良的可持续性,在学堂创办后即刻开始筹办新型瓷业公司,这种“前校后厂”的产教融合模式在当时的瓷业界实属首创。
(五)政府支持下官吏绅民间耦合发展的应然
清末“新政”推出后,教育在清政府主导下,各级地方政府督办“改制书院、兴办学堂”的兴学潮席卷而来。湖南在“新政”颁布的翌年,湘绅王先谦、汤聘珍等人就率先办起了湘省第一所实业学堂——湖南农务工艺学堂。1903年,革新派代表赵尔巽接任湖南巡抚,督湘期间,他把发展新学作为开展新政的“第一要务”。对于关乎民生的实业教育,他一贯认为,“实业学堂造就真才刻不容缓”[11],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开风气,兴实学,莫要于求学外洋”[12]。正是在地方大员的大力推动下,湖南新式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04年仅长沙就有34所学堂,其中民立学校19所,官立15所”[13]。赵尔巽调离湖南后,端方受命担任湖南巡抚,在湘任职半年便倡建了八十余所新型小学堂,并且非常注重实业教育的发展。在熊氏向其呈交《熊希龄为湘省创兴实业推广实业学堂办法上端方书》地方经济改革方案中提出:“以吾湘大势论之,目前欲兴工业不可速求,输出宜先为模仿工业,以抵制外货之输入,则成本轻而收效易,人民之学识技能逐渐发达,必不患无新式机械之发明也。”[14]端方欣然接受了熊氏的建议,允许其“次第进行”,从稳妥考虑“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并拨借官款18000两作为瓷业学堂的创办经费。瓷业学堂在政、绅、士、工、商各界人士的合作博弈下,办学不久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两年后,学部鉴于该学堂办学成绩优良,倡议各省有窑业地方向其学习。该倡议一经提出便得到山东、云南、四川等地的积极响应,山东省巡抚杨士骧更是以公文的形式敦促省内瓷区积极效法。除了政府的有力支持,吏绅民之间的有效合作是该学堂得以率先创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904年9月,熊氏在端方的受命下考察日本的教育和实业,归国后便将考查报告呈交给湘抚端方。熊氏提议在湖南创建“数百万人民所托命之源”的“工业徒弟、染织、农林、陶器和图画学校”[15]。同科举人、时务学堂同仁文俊铎提议将改良的对象聚焦在醴陵土瓷业上。据资料显示,熊希龄、文俊铎二人在考察醴陵瓷业时,得到当地窑户的“围观延揽、络绎于途,似人心见解,豁然贯通”式的热烈欢迎。故湖南瓷业学堂的建立不仅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亦是官吏绅民的共同诉求的体现。
二、湖南醴陵瓷业学堂中道衰落的原因分析
该学堂1906年创办,1910年受困于常年经费,永久班学生转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速成班则改办为艺徒培训机构,名为“湖南瓷业艺徒学堂”,1915年再度更名为“湖南省立乙等窑业学校”,1917年学校再度囿于经费而更名为“湖南窑业实验场”,1923年实验场又因战事摧残,最终无形终止。究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五个方面。
(一)办学经费筹措困顿
该学堂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莫过于经费问题。其经费由永久经费和常年经费两部分组成,永久经费为学堂初创时基础设施费用,在熊氏的积极运筹下,该款项由湖南官厘金局借款银一万八千两填充;常年经费即为后期运营费,其数额不菲,且无固定来源,“惟开办以来,将及一载,而常年经费并无款可支”[16],“苟学堂经费允裕,则可求其扩张矣,此磁校将来推广之办法也……值此亏累甚巨,筹措甚难,告贷无门”[17]。面对上述经费难题,熊氏奔走呼告,多次向两江总督端方等陈述实业教育之重要,并恳请在地方盐税、铁路交通税等税赋中抽取办学经费,在多次遇挫之后,继而转向厘金局、水电公司等单位借贷。在当时社会环境风雨飘摇的背景下,对于耗时耗力的民生工程,即便是政府机构也存诸多顾忌,如湖南厘局在收到端方札文支持醴陵瓷业学校时,却辩称:“频年收数短绌,出入不敷,磁业公一司(磁业学堂与磁业公司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旧借厘款壹万捌千金,尚未归还,现实无款可拨”“本署司以湘省公项困竭,原属实在情形。”[18]在求助借贷无门的境况下,熊氏无奈发出瓷校势必因此停办的无奈感叹:“前款不敷甚巨,乃禀请湖南、湖北、四川各督抚宪设法协助……学堂得以支持者两年。……转瞬明年期满,此款仍属无着,磁校势必因此停办。”[19]
(二)学堂创办者与实际主事者理念相悖
醴陵瓷业学堂的领导班底由熊希龄(正监督,实为名誉监督)、文俊铎(副监督)、常先(教务长)、沈明煦(庶务长,后任副监督)等人员组成。熊氏在学堂创办不到一年时,便随载泽、端方等人一起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学堂事务交由沈明煦打理。《为治理整顿醴陵瓷业学堂致沈明煦函》中记载,沈氏在管理上甚不得法,存在账目不清、绩效考核无章、统筹管理不力、预备谋划不足、精简核准不周、研究管理松弛的现象。在面对熊希龄指出的上述亟需改善的问题时,尤其是对待学理与研究管理方面,沈明煦则认为“东洋技师学理虽多明者,然实不及西洋技师经验之富,西洋以德国为最”[20]。当时,在花重金聘请外洋技师与试验研究方面,沈氏不顾熊氏设想而一意孤行,在面对无法破解困局的情况下,沈氏选择辞职来回避问题。基于学堂的管理失序,教务长常先(字少藩)也出现了严重的教学质量问题,从《就磁校亏损替沈明煦辩白致文俊铎函》记载中探知,除上述两位主要管理者决策失策外,管理层内部也出现了互相猜忌和掣肘的情况。
(三)背离教育规律的速成愿望
首先,学堂主事者对于实业与教育的本质与联系认识不足,致使学堂与公司两相受困。依熊氏本意,设瓷业学堂之目的是为了振兴瓷业,瓷业发达后方可挽回利权,富国裕民,亦收反哺教育之功效。然而学堂主事者却未能彻察熊氏深意,而是急于“建功立业”。在瓷业学堂创办未及一年,各项试验均未成熟之际,学校便将取得的成绩溢美报端,“湘省醴陵县瓷业学堂所有试验小窑现已筑成,各色碗品本月底即当出见,其瓷质之佳美虽目前不能与外洋比较,而较之江西景德镇则可争一优点”[21]。适逢袁伯夔观察莅湘,在闻知该地瓷业改良成效非凡后即刻出资扩厂,并出任瓷业公司总理,一座近代新式瓷业公司就此创建,但遗憾的是学堂试验产品未进行中试直接投产,导致瓷业公司运营很快便出现了资金危机。又因瓷业公司骨干员工大多属于一年之速成班毕业生,“既未能高手,法亦多欠敏”。加之学堂高薪聘请的日本技师“多理想而失实验”,因此公司一经试产便问题频发,“醴陵瓷业公司初开办之第一年,每烧一窑辄多损坏,估算成本亏至万余金之多”[22]。其次,在创办实业教育的宗旨与规律上认识不足,导致学堂运行管理失效。瓷业教育的宗旨是“要在进步改良于外人所未及创造之物,而另辟一器一法,以战胜白人”[23]。但当时湖南民众大多对于陆军、政治颇感兴趣,而屑于工商。因此“各学生之入磁校者,咸希冀于毕业奖励一途”[24]。面对千余年遗留下的读书取仕的传统习惯,熊氏无不心忧地指出“然吾辈不从此关打破,则年年费掷无数之金钱,耗尽各职员教员之心力,迄其结果,半途而废,浅尝辄止,殊可忧矣”[25]。而当时瓷业学堂实际的教学内容与运转情况却与普通学校无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熊氏致电学堂副监督沈明喣时指出“磁校本年各科教授,与各学堂普通学无异……多泛论常谈,且涉及于政治学院,实于学生工业之精神有所妨碍,而各教员又彼此不会商联络”[26]的问题,并提出教学改进策略,遗憾的是当时学堂主事者不仅未将熊氏的饬令付诸实施,而且还急功近利的将为期三年的核心课程压缩至一年授完,且课时量安排严重不足,导致教学质量无法保障。
(四)路径依赖下的产品结构失衡
囿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倡办者自身的认知与实践习惯,学堂与瓷业公司不由自主地走向了艺术瓷主导的产业发展方向,在日用瓷、建筑瓷尤其是工业用瓷方面涉及较浅或几无涉及,致使该地的瓷业改革不够彻底。熊氏在考察日本瓷业后指出,华瓷在国际市场上不敌东西洋瓷的主要原因在于“华人不知美术工绌,喜用吉利花样之物,故彼以粗糙之器而得我重价也”[27]。所以该学堂创办初始便将设法改良传统瓷质与瓷器画面定位为办学目标,从《醴陵瓷业学堂之进步》(申报1906第11943号)一文可知,该学堂的主要科目均围绕瓷质与瓷画展开。在公司陷入资金危机而谋求脱困时,其对外募集资金的亮点亦是艺术瓷这一主打产品。在后来的实践中,该学堂与公司亦是如此贯彻,以至于时人给出“江西瓷器以品质胜,与湖南瓷器专以外貌悦人者绝然不同”[28]的评语。在产品结构上,当时决策者其实也认识到了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但基于眼前利益和实际操作难度,未将电瓷、建筑瓷等产品研发提上改革日程。由于醴陵瓷业学堂、公司内部产业结构相对单一,且未能根据时代发展趋势进行超前谋划,导致在后期的市场竞争中逐渐趋于下风,加之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冲击,近代醴陵瓷业的改革不得已在万众瞩目下寂然退场。
(五)地方主官更迭下的政令不一
彼时时局动荡,地方大员调换频仍,改良派与保守派针锋相对,势如水火,由此出现了地方人事倾轧与政出多门的乱象。基于上述风气,致使湖南学务废弛,实业教育成效乏善可陈。对于出现如此被动局面的原因,熊希龄认为是由地方主官的主政观和开拓进取精神的盈亏决定的,“是故值热心变法强毅勇敢之巡抚,如赵尔巽、端方者,则惟有咨嗟太息,等诸无可如何。而遇有持重沉默,不谈新政之巡抚,如陆元鼎、庞鸿书及今岑春蓂者,则从中造化讹言,荧惑视听,使大使视学界如敌国,杯蛇市虎,在在惊人,志图报复”[29]。具体到瓷业学堂的发展建设而言,地方主官不是根据客观事实积极支持倡导,而是视该学堂为前任政绩而排挤。
三、结语
瓷业学堂的创建是我国近代瓷业改革中的典型案例,是基于国家存亡背景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中国家意志导向的具体体现,也是基于民族危难自救下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中士绅力量凝聚的时代写照,更是基于安全成本衡量下民族工商业被迫转型调适蜕变中的自觉意识的彰显。回顾清末民族手工业转型的典型案例,其历史价值和经验启示值得时下反思,主要体现在“改良创新陶瓷工业,战胜白人”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担当、“帕累托最优”思想的自发实践、“官吏绅民”互动机制的自我探索、“公司即学堂、学堂即公司”产教一体思想的自主践行,“因民之利而利”固本教育宗旨的确立,“由爱而专,由熟而巧”人本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急功近利”视教育为谋利手段的逆教育规律行为对教育与产业带来的危害等方面,其对当下职业教育改革、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路径探索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1915醴陵国际陶瓷文化特色街区打造醴陵陶瓷文创新模式
——1915醴陵国际陶瓷文化特色街区打造醴陵陶瓷文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