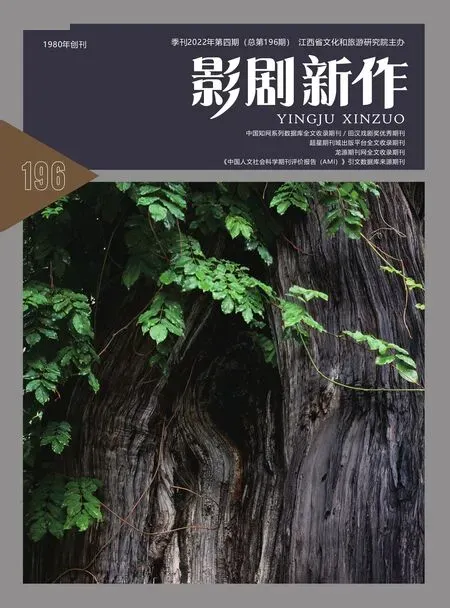戏剧情境对红色文化元素的呈现
——以赣南现代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为例
丁家榕
由盛和煜编剧,张曼君导演的大型赣南采茶现代戏《一个人的长征》展现的是一则关于红色信仰的故事:生活在赣南地区的马夫骡子为信守对红军许下的诺言,历经波折护送苏区中央银行的金子,在长征途中不断追赶红军,最终完成自我发现。它是一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的展演剧目,自2021年春于江西赣州首演以来,与张曼君导演的另外三部大型赣南采茶现代戏《山歌情》《八子参军》《永远的歌谣》并称“赣南红色采茶四部曲”。《一个人的长征》的剧种为赣南的地方戏——采茶戏,因赣南地区是江西革命根据地,被称作红色苏区、革命老区,而该剧又是一个发生在特定革命年代的红色题材故事,故自然离不开红色文化元素。
谭霈生在早期著作《论戏剧性》中详细论述过“戏剧情境”。戏剧冲突包含内因和外因,内因是各种性格对立的性格冲突,外因是能构成典型性格冲突的必要条件,它促使性格冲突尽快地充分展开,而“戏剧情境是促成戏剧冲突爆发、发展的契机,是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条件”[1。]98“戏剧情境包含特定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环境(时代背景、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1]98,可见特定的情境有利于呈现人物性格,让戏剧冲突爆发,其中的事件和环境为外因,人物关系为内因。本文以《一个人的长征》为研究对象,拟分为四部分,从红色文化元素的定义入手,再通过开场的作用、构成戏剧情境的事件对红色革命风貌的呈现和人物关系的变化勾勒出苏区百姓及红军形象做具体分析,围绕文本,具体论述红色文化元素在剧中的渗透。
一、红色文化元素定义
纵观所涉红色文化的研究,笔者发现目前学界中对于红色文化所下的定义颇丰。
其中,本文对红色文化的定义综合了李水弟、傅小清、杨艳春所认为的红色文化的表现形式,即主要体现为革命年代的“人、物、事、魂”。一方面是红色文化的物化形态——红色资源,集中体现为革命年代的“人、事物”;一方面是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红色精神,集中体现为在这些物化形态的红色资源上所承载的精神形态[2]160和“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的中国红色文化,实际上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交互作用,共时存在、历时发展,从而融合生成的一种特色文化”[3]90这两种说法。可见,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化及精神属于同一话语体系,故而由此发展出来的红色革命文化题材属于这一范畴。“红色革命文化已成为中国戏曲众多剧种深入创作的题材,成为‘现代戏’这一题材类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33“红色革命文化的核心是时代和政治。”[4]35从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中的重点内容”[4]33。可见,这一题材本身就是红色文化元素的集大成者,在现代地方戏创作实践中的热度可见一斑。
红色文化元素则是外在形式及内在意义中一切能与“红色文化”相联系的存在,“元素”则是在具体论及某项所涉的具体作品时,红色文化在其中的具体表现。
从意识形态⻆度看,红色文化元素自然包含红色精神,该剧展现的红色精神有长征精神和苏区精神。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伟大长征精神要坚持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要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它是不怕艰险、不畏牺牲、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表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从上述可知,人民是红色精神传承的关键载体,强调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艺术就是人学。同时,红色精神至今有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本身是经过时代考验、实践检验,具备超越性的。
红色革命题材戏曲的创作往往非架空作品,在明确红色文化元素的概念后,需厘清《一个人的长征》是否符合这一题材要求、是否具备上述红色文化元素。首先,《一个人的长征》故事发生的时代为1934-1935年红军长征时期,从广义上看,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从狭义上看,属于红色根据地时期(1927年以后)。其次,该剧围绕“长征”和“信仰”展开,主人公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长征时期的基层小人物。综上,该剧符合要求,具备多个红色文化元素,而戏剧情境能够集中呈现这些元素,故后文详细论述该剧如何在戏剧情境中呈现红色文化元素。
二、交代红色背景,奠定红色基调
“戏剧情境正是通过必要的交代、介绍展示出来的,如果不把各种因素介绍清楚,观众对冲突为什么这样爆发会感到茫然不解”[1]100。《一个人的长征》的序幕及第一场作为整个剧作的开场部分,初步交代了戏剧情境,此部分重点论述如何通过这些因素点明红色背景,为全剧奠定“红色”基调。
序幕是主人公骡子与代表红军一方的邱明亮排长、二号首长的相见场。骡子的第一个动作是“做梦”,他梦见赣南采茶戏,交代出地点是在红色苏区所在地的赣南;他在梦里想着见花姑,点明一组婚恋人物关系。其中骡子与邱明亮的大段对唱,交代了故事的发生有着红军干革命的时代背景。过去发生的事则是马夫骡子喝多了酒,稀里糊涂中,自己喂养的黑骡子被老板卖给红军。主人公的处境体现为,骡子先是和邱排长拌嘴后,面对二号首长欲退还黑骡子并补偿工钱的行动,他决定帮红军拉活换工,加入了红军的中央运输队,踏上长征之路。此处也交代出随后六出戏的戏剧地点转移将以历史上红军长征的行进轨迹为参照,即途径江西、湘江、黎平、遵义、泸定、毛儿盖等地,实现了红色文化元素的渗透。而第一场所描绘红军长征路上的湘江突围中,赶着驮有铁皮箱的黑骡子上路的主人公开启英雄之旅后的处境变为:黑骡子被炸死后,面对被炮弹炸开的铁皮箱中露出的中央苏区银行财产——红军金条,自己该私藏还是护送到底的两难选择。面对“金条出现”这一突发事件,戏剧情境改变,骡子与邱排长的人物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即,从序幕的二人互相“看不上”到第一场骡子藏金在身被邱排长怀疑图谋不轨,再到骡子“一根筋”地认定要亲手交付金条到二号首长手上而拒交给邱排长,最后到骡子发现邱排长负伤,被他掩护着护送金条重新上路。此时,剧中有关红军长征的时限也交代出来了,即:紧急追赶上二号首长,以便及时完成金条的交付,这也给主人公骡子施加了行动压力。“躲过这阵就出来,出来就去追红军。哪怕追到天边外”[5]12。可见,二人虽嘴上不饶人,但面对红军的革命利益时,他们达成共识,并体现出红军体恤百姓的奉献精神。
综上,观众从大幕拉开就能清晰地感知到这一出红色革命题材现代戏的红色背景和红色基调,把剧情走向引向骡子还红军金条这一主线。该剧的开场也清晰呈现出戏剧情境中人物生存和活动的环境是由时限、地点、时代构成的。同时,初步构成戏剧情境的因素还具体呈现为人物的往事、基本交代主要的人物关系及主要人物此时此刻面对的情况。
三、构成戏剧情境的事件对红色革命风貌的呈现
“事件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也可能是现在时态的;可能是由主体的行动构成的,也可能是外在于主体的。”[6]201可见,戏剧事件是对人物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本剧的戏剧事件在这个影响的过程中恰好能够呈现红色革命的风貌。它们既带有红色文化历史的特殊性,也在每一次推进、变化中体现出红色精神,展现出作为红色革命文化题材戏曲作品的戏剧性。
戏剧冲突会在情境的不断变化中发展,本剧产生的戏剧事件呈现出相应的红色文化元素。“事件是人物动作的来源,是激发人物产生某种思想和感情的条件,甚至往往成为人物一生中的转折点。”[1]102可见,事件一旦发生,将对人物产生影响,人物进入情境开始展开一系列行动,行动中核心动作的背后又呈现出人物动机。纵观全剧,“护送金条”是贯穿全剧的核心事件,与之相连的事件能看出主人公骡子在红色革命大背景下作为小人物的“自我呈现”。第二场的事件为,骡子回家后,从未婚妻花姑口中得知父亲被王火彪等国民党势力抓走,面对花姑最初想打金条主意救父亲、王火彪来抓误以为是红军师长的自己时,他选择坚决不暴露自己身上有红军金条,只要放了父亲便主动跟王火彪走。第三场的事件为,面对大余县城集市上因惊马而有生命危险的粤军团长之女古玉洁,骡子勇敢上前将其救下。加入了红军的共青团员古玉洁因骡子救命之恩及他“红军师长”的身份,作为回报让手下逼王火彪放了骡子,得知骡子追红军的急切心理后,二话不说把马借给他,跟他一起追随红军去战斗。第四场的事件为,骡子和古玉洁一路抵达贵州黎平后,休息中互相展现“理想”,遇见已在大余家中汇合,追赶上他们的花姑和邱排长。骡子与花姑的“私奔”误会解开后,四人重新上路,此时在暗处跟踪他们的王火彪已得知骡子知晓红军金条下落。第五场的事件为,追至遵义的骡子一行人发现红军部队已经转移,而此地又为国民党黔军的据点,危机四伏。在王火彪的通风报信下,黔军抓住花姑,威胁骡子说出金条存放处,带他们取金条才能换下她,骡子进行两难选择后假意答应带敌人去取金条换了花姑平安。邱排长发现掉队的骡子落入敌手后,甘愿向敌人开火掩护他护送金条追红军,骡子趁乱跳高坡逃跑,而同样为了引开敌人的古玉洁光荣牺牲。第六场的事件为,跳高坡摔断腿的骡子一路行乞到泸定,落魄之中又碰上仍旧不死心尾随纠缠的王火彪,在被抢金条的生死关头,邱排长及时出现除掉了王火彪,从敌人枪口救下了骡子。第七场的事件为,行至毛儿盖草地的二人因七八天未进食的饥饿折磨,在睡觉做梦时回顾这一趟长征路上的经历。邱排长把干粮都留给骡子吃,自己去摘野菜时陷入沼泽不幸遇难,骡子最后戴上了邱排长的军帽继续追红军。
上述事件可看出,包括序幕和第一场在内的九个事件都是由人物主体在现实中的行动构成,呈现了主人公骡子一路“追红军”走长征路的历程。无论是能够呈现出骡子秉持对红军的一份诚信的开场事件,抑或是第二至第六场中王火彪与白军为抓红军、劫金条而紧追不放的有力事件,主人公都能立即行动起来,不断对抗。开展红色革命的艰难险途中,邱排长、古玉洁都为革命和党组织、为红军长征献出生命,骡子三次被革命队伍的红色力量救下,也救助革命者一次,肩负红军首长交付的使命“我答应过二号首长,这五十根金条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他”[5]18,将和花姑的小家幸福退居其次。因此,围绕红色革命进行的多重事件作为构成情境的必要因素引出“戏”,彰显了红色革命题材戏曲中的红色文化元素,呈现了红色革命风貌。
四、人物关系的变化勾勒出苏区百姓及红军形象
“人物之间的关系如若能在戏剧进展中具有真正的活力,都需要定性化、具体化 。”[6]201本剧的人物被先后置于长征路上追红军还金条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经受红色革命的重重考验,于行动中呈现人物内心世界。在与代表着红色力量的邱排长相处的过程中,骡子自身潜移默化地受其感染熏陶,从人物塑造中逐渐呈现出红色精神。二人一起出场的重点场次为序幕、第一、四、五、六、七场,此部分围绕主人公骡子和邱排长的人物关系展开论述。
主人公骡子“护送金条”这一行动的背后,最初的动机是他对红军的“守信”。“人物关系当然不是戏剧情境的唯一因素,但却是最主要的因素。戏剧中的人物关系,主要指的是性格关系。”[1]108第一场事件的发生,骡子初见金条的心理从“喜得我手脚无处摆”[5]11到“炸死黑骡子的是国民党,算在红军头上就不该”[5]12,再到向红军讨要工钱“两码事情要分开”[5]12的变化,可看出他正常人性世俗的一面。虽然最后是理性压倒了感性做出选择,但是需要一段内心抗争的过程。这也是剧作家把骡子作为苏区百姓形象来塑造,区别于作为红军的邱排长从始至终需坚定地与百姓患难与共、顾全大局等使命特点的合理性。上述动机的转变通过骡子“藏金子”的动作呈现,造成了邱排长的误解,二人险些掐架。而邱排长在炮火中猛地将骡子扑倒而负伤,二人的人物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是,骡子运输金条追红军,邱排长因组织上交代的任务,虽质疑骡子对待这一光荣任务在思想层面的忠诚性,但也因保护金条的义务,于是在第二场中便又回到大余骡子家找他。二是,邱排长在第四场认识到骡子一片诚心,从而解除对他监守自盗的担忧后,主动要求护送他去遵义。三是,二人一起前往的行动呈现出人物关系发生关键变化——从义务保护到主动保护,此后这二人的人物关系中将无信任隔阂。
而为了避免红色革命题材过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让人物关系显得不真实、空洞这一问题,红色文化元素若想呈现得更具体,规避“假大空”,最终要落到对人物个性的准确刻画上。“戏剧的基本任务并不在于把事件的过程叙述清楚,而在于写人,在于塑造人物性格,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于展示人物独特的生活道路和生活命运。”[1]107随着剧中情境发生变化,主人公骡子受到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光靠“守信”这一动机贯穿全剧无法立住人物形象。在第二场至第六场的事件中,文本呈现更多的是他异常倔强的性格,浑身上下充斥着一股韧劲,这使其人物性格更真实可信。以第六场戏为例,即便骡子与邱排长和好后刚被他从鬼门关拉回来,“你莫眼睛瞪着我,金子不少你半分,危急时姓邱的你在哪……一手还牵着那小妖精”[5]22等唱词,让我们感受到创作者依旧保留了主人公惊吓过度后的抱怨情绪,这呈现出骡子爱好耍贫嘴的性格特征,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这一特性也使他不容易泯灭热情,同时显得作为老百姓的骡子性格真实、可爱,与红军之间的关系也是亲切可信的。面对为红色革命献身的古玉洁被骡子无心调侃,邱排长将他推倒。如此一来,第五场古玉洁之死这一事件便成为了他们人物关系复杂化的外部因素。邱排长从第一场未和骡子有正面冲突动作到此时的爆发动作,可见邱排长的直爽豪迈,具有正义感,他不会为了小事真正翻脸,但会为了革命战友被误解而抱不平。当意识到骡子的腿受伤后,邱排长又果断将他背起,骡子趴在他的肩上时,感受到他竟在落泪,“并肩战友儿女情,红旗伴着诗歌飞”[5]22。通过“推倒”这一动作,骡子发现了邱排长也有铁汉柔情的一面,具有人物冲突关系的二人在修复关系后情感拉得更近,也为第七场二人更亲密的关系做出铺垫。同时,红军的形象也做到了真正有血有肉,剧作家同样是把邱排长作为普通人在塑造,他既有战士的血性、重情重义与刚正之气,也拥有普通人的“脾气”。可见,本剧完成了革命题材戏曲在性格关系建立上的“去标签化”,验证了“所谓性格关系,是指这一人物和那一人物在特定的情况下进行交往时,双方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因此,人物的交往就体现为这一性格和那一性格的交流、撞击”[1]112的观点。
第六场的事件进一步升华了骡子和邱排长的人物关系,第七场二人人物关系的变化则达到了顶峰,实现了质的飞跃。第七场中,二人的第一组动作是“分干粮”:二人都饥肠辘辘,邱排长却把仅剩的干粮分给骡子。“想偏你的脑壳!我的食量比你小我看你打仗蛮猛,吃饭好斯文”[5]22,这段白可以看出,二人的关系既是红军长征路上亲密陪伴的“战友”,也是一对欢喜冤家。全剧类似此类幽默的白与唱的段落甚多,诸如随后二人唱赣南采茶调时争辩大步走来是“睄妹子”还是“干革命”,既呈现出长征路上,个性不同的两个人的“初心”——人性本真的欲望和不朽的追求,二者皆是理想也是现实,同时造成的喜剧效果得益于二人的个性在人物关系中的呈现。即,倘若马夫骡子不是这样可爱咋呼、内心坚毅,时而又透露小委屈的性格,邱排长也不是如此大大咧咧、刀子嘴豆腐心的个性,那么二人进入本剧的情境则不会造成这般人物关系的反差感、幽默感。二人的第二组动作是“做梦”,骡子与花姑、邱明亮与古玉洁在梦中相见,一面是花姑等待骡子追红军归家的百姓质朴情感,另一面是邱明亮回忆与古玉洁生前初见对“红星”“军帽”代表的革命理想的热切追求。二人的第三组动作是邱排长沼泽丧命、骡子戴上军帽追红军,也是二人在全剧的高潮动作。“我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像你一样战斗生活。我晓得这叫作共产党员,虽然我现在还够不着,我要参加红军,穿越硝烟战火一辈子跟着共产党,让红星照耀中国。”[5]24骡子醒来后发现邱排长因饥饿摘野菜陷入沼泽,只剩下奋力扔出的干粮和一顶军帽,此处抒情的大段唱中,是长征精神中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映照。也交代出全剧的最大悬念:骡子如何走过长征路,最终归心何处?邱排长是为骡子而牺牲,更是为红色革命而牺牲,这是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的体现。大步走来,方向在前路,这也是骡子对红军“守信”最后落实到的——他被揭开最隐秘、最深层的,最初连自己都未察觉的动机,也即向往红军、支持红色革命的理想信念,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而被揭开的一大动力,则来自于与红军战士邱排长相处时人物关系的微妙变化:从互相看不上到信任危机解除,从被保护、照顾再到埋藏在心的革命信念被唤醒,坚定地继承红军干革命的使命。
“剧中人物骡子,作为一个普通人,劳苦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切身感受中,认识了红军、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革命,走进了革命队伍,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缩影。”[7]25骡子对红军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长征途中的实践检验了信仰的真理。骡子的唱词“把金子安全送还红军”[5]24等类似表达在全剧多次出现,可知,贯穿全剧的送金条动作是他的主动选择,并且面对敌人出现的危机情境,舍身保护金条,这一方面是苏区精神中“清正廉洁”内涵的具体呈现,另一方面则是邱排长、古玉洁等人不怕牺牲也要保护群众的价值观发挥了影响作用的体现。毕竟,在第六场坠崖后独自流浪泸州时,骡子孤身一人是可以选择放弃的,然而他依旧选择带着闯劲奋勇向前。同时,《一个人的长征》更侧重于革命同一战线方(戏剧冲突中的一方)的塑造,对于革命对立面的敌对关系,则仅作为制造冲突的一方,发挥阻碍干扰骡子等人追红军、造成红军战士牺牲的作用,这也符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言“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8]864这一创作规律。总而言之,人物关系的外部数量并不复杂,这能使冲突集中,聚焦于人物关系的内部变化,突出骡子作为苏区群众的成长。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大背景、红军中央银行的金条、中央运输队、长征途中的地点转移、苏区百姓及红军形象、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都属于红色文化元素,同时也较好地呈现在本剧的戏剧情境中。
在红色革命题材戏曲频繁上演的当下,如何创作出不流俗、吸引人的主旋律作品显得至关重要。通过以上层层论述,笔者认为,要融入红色文化元素,关键在于需要使其与创作者创造的独特戏剧情境紧密结合,创作者应当在进行创作时,理解好构成戏剧情境的环境、事件、人物关系三大要素。通过对该类成功作品如《一个人的长征》的分析与研究,期望为后续赣南采茶戏创作提供成功因素的借鉴方法,同时也符合赣南作为中央苏区、红色革命老区的文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