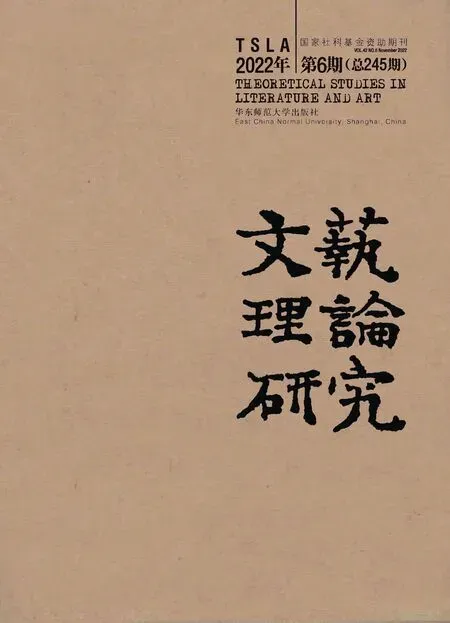哲学的艺术史“修正”与新旧图像学之争
——基于“原作”的辩难
鲁明军
1740年前后,法国画家夏尔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创作了一组(两幅)有趣的绘画,一幅是《猴子画师》,另一幅是《阅读的猴子》。前者描绘的是一只猴子握着画笔正在描摹右边桌上的儿童人体雕像,后者描绘的是一只猴子手持放大镜正在阅读。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认为,“猿类是模仿的生物,创造就是一种对自然的模仿”,所以,“猴子注定是画家永恒的伙伴。当画家再现他周围的世界时候,他就被称为自然之猿;当今天的画家抽象地画画时,他又被那些竞争对手和批评者说成是乱涂乱画的猴子”(《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25)。这意味着,不仅猴子能画出纯粹的笔触和色块,画家在创作中其实也“难逃其动物本性,不管他是再现自然,还是实践一种具有抽象视觉形式的艺术”(2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猴子的模仿只是诉诸动物本性,另一幅《阅读的猴子》说明它还是有理性和智识的。两张画如果合在一起,则恰好构成了画家的一体两面,或许这才是夏尔丹真正的用意。
对于夏尔丹而言,画中的猴子其实即是画家自己。之所以在画中将自己化身为猴子,是为了表明,作为猴子的画家固然有理性的一面,但他终究是只猴子,故不能忽视其理性无法支配的动物性本能。诚如夏皮罗所说的:“如果人是自然的模仿者,他能够模仿所见之物,那至少有一种生物能按照自然看起来的样子或其本质来再现自然。但是,即便在这里,艺术家也难以逃避自己:在一个重要的细节上,客观视角到头来不过是观察者的投射。”(《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25)在这一投射过程中,最难把握的便是理性与经验之外的动物性与先验性。通常情况下,一张画中的理性和经验即其透明性主要体现在图像的主题、画面的风格及其话语结构当中,而其动物性和先验的部分即其不透明性则往往体现在画面易被忽略的细节、局部及不可见处。进一步而言,如果观者只是探掘绘画之理性机制即其透明的部分,则不一定非要观看原作(实物),单靠作品图片便可获得;但若要揭示画面之不透明性,图片或照片显然无法满足这一条件,还须借助,且只有通过作为实物的原作方可有所感知。
“原作”(original works)其实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它看上去像一个本质主义的追问,但又很难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比如,美术馆所展示的和艺术家在工作室刚刚完成的之间很多时候就有着巨大的差别。有时同一张画,也会经历艺术家(或相关专业人士)的覆盖、修补,故至少目前,尚无标准可以确定一张画到底至何种程度才可以被判定为原作,况且这其中还牵涉临摹、补笔、代笔、复制以及赝品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另外,如果说作品图片或照片也是一种创作的话,那么它亦是原作……可见“原作”名义上是一个名词,即“原初之作”,但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和概念。这一点亦暗合了古汉语(如韩愈所谓“原道”)中作为动词的“原”,意即“探求”或“追索”(seeking)。
巫鸿在《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一文中曾就“原物(作)”问题从艺术史的角度作过一个简要的辨析和界定。按照他的区分,“艺术品原物”(original works of art)即“原作”首先是“实物”(actual objects),但又不能等同于“实物”。①从原作到实物再到作品照片(或图片)(image/picture),亦即从“原媒介”(original media)到“次媒介”(secondary media),其实经历了一个“历史物质性”(historical materiality)的演变过程,中间还常常伴随着一个跨媒介的过程。因此,严格地说,本质意义上的原作是不存在的,很多时候,它只是一种承诺和临时的决断。尽管如此,经验层面上的原作(实物)与作品图片(或“原媒介”与“次媒介”)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的区分。也正是这一区分,影响了20世纪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史上两次“论争”:一是夏皮罗对于海德格尔关于凡·高“鞋子”论述的艺术史“修正”,二是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的“(新)图像哲学”(简称“新图像学”)对于潘诺夫斯基“(旧)图像学”的批判性“修正”。如果说前者是艺术史对于(艺术)哲学的不满的话,后者则体现了图像哲学对于(实证)图像学的不满。
一、从不透明到透明:哲学的艺术史“修正”
1968年,夏皮罗发表了《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笔记》一文,如题所示,他所针对的便是海德格尔在经典的《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年)中关于凡·高画“鞋子”的论述。十年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发表了《定位中的真理的还原》(1978年)一文,将此问题带到了一个新的话语视野当中。这是20世纪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学案,时至今日,仍聚讼不已。
夏皮罗指出,凡·高画过不止一幅“鞋子”,前前后后有8幅之多(《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笔记》421)。于是,为了确认海德格尔文中提到的到底是哪幅,他特意写信询问了海德格尔。时年76岁的海氏在回信中说,他是于1930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凡·高的展览上看到了这幅“鞋子”。根据他在文中所描写的“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这一特征,夏皮罗将其锁定在参展作品之一编号为255的“鞋子”(de la Faille’s no.255),并推断它是凡·高在旅居巴黎时的作品,画的就是凡·高自己的——一种当时荷兰人常穿的——“鞋子”,而不是普通农民穿的“鞋子”。夏皮罗掷地有声的推论看似无懈可击,但由于针对夏氏的质疑,海氏没有留下任何回应,所以迄今这依旧是个未解之谜。彭锋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一些新的材料和线索,他发现1930年3月海德格尔在阿姆斯特丹时,并没有举办凡·高的展览,同年9月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Stedelijk Museum)倒是举办过一个题为“凡·高及其同时代艺术家”(Vincent Van Gogh en zijn tijdgenooten)的展览,且正好展出了编号255的“鞋子”。问题是,此时的海德格尔正在弗赖堡大学上课,也没有发现他曾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记录。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其间海德格尔没有去过阿姆斯特丹,也不能证明他3月份去时没有看到过此画,还有可能是海德格尔的记忆出了问题,甚至不排除他是有意在欺瞒夏皮罗(海德格尔69—75)。基于此,还有学者提出海德格尔当时看到的也不是255号,可能是绘有一双女鞋、编号为332a的作品(宋聪聪148—160)。
说到底,这些终究还是猜测和推想。夏皮罗提示我们,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具体哪幅“鞋子”其实并不重要,“仿佛不同的版本可以互换的,每一幅都敞开了同一个真理”(《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笔记》421)。因此,画作是不是凡·高所绘以及是不是凡·高的原作也都不重要,何况也不能完全确认他真的看过凡·高的原作。在海德格尔眼中,“这不是一幅画、一件艺术作品,而是一件制品”(德里达435)。也或许因此,在他对(凡·高)绘画的解释中,“忽略了鞋子的个人性和面相学特征,(但)正是其个人性和面相学特征,使得鞋子成了对艺术家来说如此持久和吸引人的主题(更不必说它们与作为油画作品的画作的特殊色调、形式及笔触构成的表面之间的私密关系了)”(夏皮罗,《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笔记》422)。夏皮罗不满的地方也在这里。他说:
从海德格尔与凡·高画作的遭遇里,他只记得与农民和土地的种种联想的动人的一面,而这些很少能够得到画作本身的支持。它们毋宁说植根于他自己的社会观,带着他对原始与大地的强烈同情。他确实是“事先想好了一切,然后再把它投射进画面中”。在与作品的接触中,他既体验到了太少,又体验到了太多。(《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笔记》421—422)
可见,无论海德格尔的体验是多是少,都似乎与原作(实物)无关。他的论述虽然可能源自观看绘画“原作”的经验,但他忽视了艺术家在作品中的存在,从而抽离了“原作”或作为媒介的绘画本身。如前所言,作品是否是原作,对他而言并不重要。在他的论述和想象中,并没有一个“原作”的意识和承诺。甚或说,他的目的原本就在于此,即“一件作品怎样才能够在既不借助于一份订单的恩典,也不借助于一种社会的察觉和认可而成为一件艺术品”(布雷德坎普32)。就像德里达所说的:
人们永远也弄不明白他[海德格尔]是在围绕着一幅画、一双真的鞋子,还是一双不在画中的假象的鞋子喋喋不休。他的令人失望,也不仅在于他武断而野蛮地对这幅画进行剪裁,把它设定在一个粗陋的框架内,也在于他判断鞋子归属时的自说自话:“一双农民”的鞋子。(425—426)
因此,他认为夏皮罗对于海德格尔的指摘其实是源于一种归属或占有欲望,即画中的鞋子到底是农民的,还是凡·高的(德里达440)。不过,只是停留在归属的欲望上显然简化了争论本身,从根本上而言,它是普遍性观念与特殊性经验之争,是世界观与唯科学主义之争,也是照片与原作之争或“次媒介”与“原媒介”之争。
正是在这一论争中,暴露了艺术史与(艺术)哲学之间的分歧和矛盾。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就是绝然对立的,且不说艺术一直是哲学家论述的题材和援引之资源,即使在艺术史家这里,哲学也一直是重要的理论基础。在《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笔记》发表之前,夏皮罗还写过一篇文章《绘画中的世界观》(1958—1968年),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哲学与绘画的匹配,要求我们既要对作品,又要对世界观和哲学的特征及细节,加以详细分析。但是,对两者之间这种关系的建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知性的,只对一时一地的哲学与绘画之统一性的理论有意义,而不适用于那种认为艺术与哲学中存在着统一性的世界观的一般性理论。(《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67)
就像他承认夏尔丹画中的动物性和先验性的存在一样,在他看来,即便是哲学介入绘画,也是特殊的,也只限于具体的作品,并不具有普遍化的可能,而他所反对的正是艺术被哲学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世界观。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其实也不完全否认绘画的不透明性。帕梅拉·M.李(Pamela M.Lee)在一篇关于夏皮罗手稿的论文中提到,这些难易辨识和解读的手稿表明“夏皮罗是一位思想家,他的这样一种符号学活动旨在抵制某些文本或图像分析流派所提供的无缝解释”(8)。因此,他对海德格尔的“不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后者未能——或者说原本就无意——“直面”作品,未从绘画本身出发,而只是限于图像母题的一般性解释。在这一点上,其与迪迪-于贝尔曼并无二致。不过迪迪-于贝尔曼也不满夏皮罗封闭的特殊性解释,认为重心其实并不在于“鞋子”的归属,而在于绘画本身的真实与否。在他看来,作为艺术史家的夏皮罗“也许相信,把其对象封闭在他所称为的一种‘特殊性’之中,就能保留和拯救它。可是,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却把自己禁锢在了由这种前提——这种理想、这种意识形态——强加给对象的界限之中”,看上去其“最确切的论述可能一定是最真实的”,但实际上,它“不会让这双凡·高‘的’鞋子的精确,尤其是它的归属,能够炫耀这幅画(本身)‘的’真实”(迪迪-于贝尔曼44—45)。那么,到底什么是绘画的真实呢?
迪迪-于贝尔曼认为,绘画的真实即视觉症候。比如颜料,“在这里被当成一种材料原因来理解,而材料要在此按照亚里士多德给它下的定义来理解——某种不属于一种对立物的逻辑,而属于一种愿望和向往(即《物理学》一书中的éphiesthaï一词所指的意义)的逻辑”(迪迪-于贝尔曼373)。可见,这里的颜料不仅是作为形式要素的客观材料或媒介物,更是一种使概念具体化的潜能。而这也是他批评潘诺夫斯基之“图像学”的原因所在。与夏皮罗“修正”海德格尔不同,迪迪-于贝尔曼对潘诺夫斯基的指摘则将其颠倒了过来,体现的是哲学对于艺术史的“不满”。考虑到迪迪-于贝尔曼的出发点也是“图像”,不妨说这是一场新旧图像学之争。
二、从透明到不透明:新旧图像学之争
1939年,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一书出版。这本书虽然探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图像机制,但实际上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文艺复兴艺术史学界。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它已渗透至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史研究中,甚至进入了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等诸多非艺术(史)领域。时至今日,他在“导论”中所总结、概括出来的“图像学三阶论”(“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及“图像学阐释”)依然影响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史研究(潘诺夫斯基13)。
尽管如此,半个多世纪来,潘氏的“图像学”还是遭遇了一波又一波的批判和修正,其中最典型的要数美国艺术史家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的《描绘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1984年)与迪迪-于贝尔曼的《在图像面前》(1990年)。阿尔珀斯指出,一度被视为普遍范式的潘氏“图像学”事实上只适用于文艺复兴绘画及其“叙事性机制”,并不适合分析和解释17世纪的荷兰绘画及其“描绘性机制”(9—20)。这更接近一种方法论的区分,但是犯了和潘诺夫斯基、沃尔夫林一样的“错误”——她建立了“一种新的同一性逻辑:被画在十七世纪荷兰油画上的东西是在那个时代的所谓的‘视觉文化’(巴克森德尔用语)中被看到的东西”,“匆忙地把有关最终原因的主张与形式原因混为一谈[十七世纪的荷兰绘画中的爱多斯(eidos)等于十七世纪的认识论;绘画的划分等于可见世界的科学划分]”(迪迪-于贝尔曼345—346)。相形之下,迪迪-于贝尔曼的检讨则是釜底抽薪式的,其“(新)图像学”所针对的是潘氏“(旧)图像学”之立论基础及其局限与偏颇所在。事实上,从二者各自对于“图像”的不同定义“image”和“icon”,亦可以看出其分歧所在。
迪迪-于贝尔曼在书中提到一个易被忽视的细节。针对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导论”开头那个经典的“脱帽致意”图像志案例,他说:“当我(没有碰到它,而是长时间地)看一幅画时,情景恰好相反:我不可能完全有把握慢慢地推导出一个总的象征,因为面对图像呈现出的无穷变化,我常常会不知所云并不敢轻信和确定自己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东西。”(迪迪-于贝尔曼258)在这段文字的注释中,他引了丹尼尔·阿拉斯(Daniel Arasse)在《潘诺夫斯基之后的画家皮耶罗·迪·科西莫》中的一句话,阿拉斯提议不要用全部的精力来解决肖像画的鉴定(iconographic identi-fication)问题,而要从肖像画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有一些肖像画中可能包含了多种思想,但不一定都是非常清楚明晰的思想。”(迪迪-于贝尔曼258)在第一段文字中,迪迪-于贝尔曼开始用的是“绘画”,而不是“图像”,尤其强调了长时间地观看或凝视;在第二句引文中,他说不要用全部精力解决肖像画的鉴定问题,而是要从肖像画的角度思考诸多非透明思想的问题。虽然迪迪-于贝尔曼关心的是目的,但这里不能忽视的恰恰是他论述的一个微妙的前提,即为什么要从观看绘画——而不是图像——出发。
迪迪-于贝尔曼的潜台词是:一幅画作的构成要素不光是图像题材及其意义,还有诸多经验之外的不可见的细节和无意识的症状。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完全是建立在前者,即透明的图像机制上的,并不触及绘画的非透明部分。但迪迪-于贝尔曼并不仅只满足于指出“图像学”范式及其立论的局限,他更关心的是潘氏“图像学”背后的哲学基础和历史成因,即对于潘氏而言,何以原作(实物)不再重要,而只需图片或照片即可。他的回答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或新康德主义者,潘诺夫斯基所继承的其实是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方法和观念,他们都是目的论者或观念论者,为此,他甚至将瓦萨里也追认为一个“康德主义者”(潘诺夫斯基161)。在瓦萨里这里,素描乃绘画、建筑和雕塑之父,而素描(disegno,亦被译为“迪塞诺”)本质上就是一种“主观的构思”,③它不仅是一个技术性和理想主义的词,也是一个描述性和形而上学的词。而这完全有别于同时期画家和理论家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观点。阿氏常用感性的和“具体”的直觉推演观念,而瓦萨里则是“从观念的先天能力中推演观念”(迪迪-于贝尔曼158—159)。
延续了瓦萨里的观念主义,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基于象征的形式或观念体系,意在建立一种普遍的智性结构,一个普遍的、同一的语法。
他把艺术的认识建成理性曾要求——先是在卡西尔,后是在潘诺夫斯基的思想体系中——人们不惜任何代价找到共性,甚至哲学意义上的归入概念,通过这样,用具体形象表现的现象的感性差异便能找到一个框架、一个模子和一种清晰易懂的普通语法,以便完全把自己归入其中。这就等于做了一次综合的行动,甚至按照康德的意思是一次综合统一行动。(迪迪-于贝尔曼188—189)
正因如此,艺术作品显现出它透明和理性的一面,反之,其另一面即其非透明的先验性和动物性却被完全忽视。对此,贡布里希、迪迪-于贝尔曼等并不买账。贡氏认为:“通过模式主义开始接近现象世界的知性……是一种艺术,它在人类灵魂的深处隐藏得那么深,以至于我们很难发现造化在这里所使用的神秘手段。”(转引自迪迪-于贝尔曼195)迪迪-于贝尔曼的批评相比之下更为彻底,他说:“自从艺术死亡和被解剖以来,一切都变成可见。”(68)换言之,当艺术变得一切可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艺术已经死亡了。
艺术史叙述取决于艺术的内在机制。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艺术史叙述之所以成立,正是得益于他对于图像运作机制的理性预设。对他而言,“首先,艺术是过去的一种事物并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进入了历史的观点中;其次,艺术是一种可见事物,一个有自己特殊身份、可界定的外观、界线标准和封闭的范围的事物”(迪迪-于贝尔曼56)。迪迪-于贝尔曼认为,本质上它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学者—天才”体系这一强大的不容置疑的“照明系统”。在潘诺夫斯基眼中,绘画是绝对透亮的,没有任何阴影,不留下任何剩余的意志(迪迪-于贝尔曼247)。而这样一种透明的知性结构则并非一定要透过原作(实物),作品的图片或照片即可得以揭示。甚至在理论上,印刷图片(或照片)是完全可以替代原作(实物)成为“图像学”论证的依据的。
文艺复兴绘画的透明性机制、瓦萨里的艺术史观念无疑为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但从经验上,直接影响他的还是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图像学”。比如在瓦尔堡这里,就不区分图片(照片)和原作(实物)。从1895年的《北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地区的图像》到1927年的《记忆女神图集》,摄影(照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无墙的博物馆》一书中敏锐地指出,19世纪末以来,摄影在博物馆秩序的建构和艺术史叙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87—88)马尔罗说:
黑白摄影赋予那些实际上只稍稍一致的作品以一种家族相似性。当复制在同一页纸上时,一些千差万别的作品,如一幅挂毯、一部由光照的手稿、一幅画、一尊雕塑、一个中世纪的彩绘玻璃窗,都会失去它们的色彩、机理和深度(雕塑还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其体积),从中受益的是它们的共同风格。(90)
尽管如此,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与瓦尔堡的“图像学”之间还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瓦尔堡诉诸图像运动及其“情念程式”(Pathosformel),而潘诺夫斯基将图像视为一个静态的客观对象,整个论述像一个“祛魅”的过程。瓦尔堡是个尼采主义者,而潘诺夫斯基则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其《图像学研究》甚至还带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迪迪-于贝尔曼148)。诚如迈克尔·波德罗(Michael Podro)所说的:“没有哪个作者会像潘诺夫斯基那样,把艺术的观念视为知识而予以精心阐述并不断完善。也没有哪个作者会像瓦尔堡那样,把艺术如此整合进一种社会行为的意义中。”(225)迪迪-于贝尔曼对于潘诺夫斯基的不满也在于此,他批评潘氏始终将图像置于一个透明的理性框架中,而瓦尔堡眼中的那些魔法一般的非理性细节和无意识症状恰恰成为他“修正”潘氏图像学模式的依据。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解释了迪迪-于贝尔曼何以没有选择李格尔、特别是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在他看来,沃尔夫林的“形式分析”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本质上没有区分。潘诺夫斯基笔下的“艺术史中不存在任何‘自然法则’,并且视象的人类学或心理学只能通过文化模式和‘灵魂的转化’表现出来——因此,没有任何自然状态之类的东西”。而“由沃尔夫林所定义的线性与块性(另译‘线描与涂绘’)、表面与深度等概念之间的对立原型特征则同时失去了它的基础的或先验的价值”(迪迪-于贝尔曼138)。也即是说,无论是潘诺夫斯基,还是沃尔夫林,他们都诉诸理性的模式,都忽视了先验的、自然的变化,即其动物性的因素。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也是瓦尔堡“图像学”——的遗产,亦即他所谓的视觉“症候”(迪迪-于贝尔曼40)。
潘诺夫斯基在《图像学研究》中通过多个不同的图像或观念案例,谱写了一部丰富多彩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图式-文化史,然而,迪迪-于贝尔曼并不关心这一图像机制,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画面细节中感受一种症状,一种不透明性或不可见性,或是一种无所适从,以及无穷变化。这里的不透明性和无穷变化所指的正是画家身上或画面中的动物性——原则之外的细节,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唯有透过原作(实物),才能有所体验和感知。比如,书中提到的安吉利科《阴影中的圣母玛利亚》(1440—1445年)和维米尔《德尔福特的风景》(1658—1660年)这两个案例便清晰地表达了迪迪-于贝尔曼的观点。
如果沿着潘氏“图像学”的逻辑,面对《阴影中的圣母玛利亚》中的“抛洒颜料”和《德尔福特的风景》局部的“色彩震颤”时,就根本无从下手。然而在迪迪-于贝尔曼看来,安吉利科抛洒颜料,模仿的其实是进行“神圣的谈话”时的面孔动作。这是“一个神秘的行为”,“一个被重复的涂圣油的动作”(迪迪-于贝尔曼287);维米尔笔下的德尔福特不再是对十七世纪世界原貌的描写——它的地形概貌或照片概貌……而是“材料与涂层的问题[……]是心灵的震颤和致命的激奋问题——某种我们可以称为一个创伤、一次打击、一种颜色的飞溅”(迪迪-于贝尔曼351)。正是因为这些细节和症候往往出自形式之中的无形物质和透明之中的不透明,更加凸显出原作(实物)的重要意义,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感知到这些细节和症状。
这看似是延续了瓦尔堡的“图像学”传统,但如前文所言,瓦尔堡也没有强调原作(实物),相反,摄影和图片恰恰是他“图像学”的重要基础。这也是迪迪-于贝尔曼与瓦尔堡之间的分歧所在。显然,诸如“颜料抛洒”“色彩震颤”这样的感知细节和“形象表现性”(figurabilité)并没有进入瓦尔堡的视野,他所谓的“间隙的图像学”(iconologie des intervalles)与“情念程式”还是基于图形及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包括图形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种话语秩序,而是一种自主的视觉装置(菲利普-阿兰72)。迪迪-于贝尔曼眼中的这些细节和症候看上去和李格尔、沃尔夫林笔下的形式要素并无二致,但不同的是,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诉诸普遍的、同一的风格和类型,而更强调个体经验及其特殊性。前者是一种图像行为,后者则是一种基于图像事实的表述。不仅如此,即便是通过摄影术的放大,照片的“次媒介”属性——除非照片本身就是原作——也已决定了观者很难从其表面捕捉到真实的细节和症候。当然,它也可能会释放出“非原作”或“次媒介”的某些症状,但这已经远离了原作本身。
三、艺术史与哲学之间的“恩怨”与相互解放
无论是夏皮罗对于海德格尔的艺术史“修正”,还是迪迪-于贝尔曼与潘诺夫斯基的新旧图像学之争,表面看来都是透明性与不透明性之争,前者主张透明性,后者又试图回到不透明性,但若只是止于这样一个层次,显然是简化了20世纪以来艺术史与艺术哲学之间的“恩怨”,以及背后所隐含着的更为复杂的经验与观念之争。
如果说夏皮罗对于海德格尔的“修正”是“特殊性经验”与“普遍性观念”之争,即封闭与开放之争的话,那么迪迪-于贝尔曼与潘诺夫斯基之间的新旧图像学之争本质上则是“特殊性观念”与“普遍性经验”之争,即封闭的开放与开放的封闭之争。“特殊性经验”和“普遍性观念”相对容易理解,难解的是“特殊性观念”与“普遍性经验”。据上所言,所谓“特殊性观念”,即观念并非来自透明的经验,而是来自非透明、无意识的本能,它的起点是开放的、非经验的,目的是通往一种特殊的,甚至封闭的观念。与之相对,所谓“普遍性经验”,意谓经验来自透明的图像机制,并意图建构一个普遍的模式和方法论,它的起点是封闭的、观念的,目的是通往一种开放的经验。由此可见,到了迪迪-于贝尔曼这里,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经验和观念,过度的封闭和过度的开放都不是他的目的,他想找到另一种开放和封闭,即一种有限的开放和有限的封闭。他承认自文艺复兴以来,哲学就一直是艺术和艺术史重要的根基,但他的兴趣并不在于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而在于独特性(迪迪-于贝尔曼 胡新宇B10)。所以,和瓦尔堡一样,我们很难定义迪迪-于贝尔曼的身份。他们的实践既不像艺术史,也不像哲学,按阿甘本的说法,这是一种“无名之学”(nameless science)(阿甘本125—149)。
这些复杂的关系和论证本身尚有待检验,但毫无疑问,所有的分歧和“不满”根本上都源于艺术认知和观念的差异,且在此都不约而同地归结到棘手的“原作”问题。虽然“原作”问题颇为复杂,很难作出清晰的判断和定义,但无论多么复杂,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艺术史家也好,哲学家也罢,在分析和论述一个绘画作品的时候,关于原作(实物)的自觉和承诺是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因此,为了便于表述,本文一开头就对此作了界定和区分,即原作(实物)与图片(照片)或“原媒介”与“次媒介”之别。这一区分粗暴地抽掉或压缩了其“历史物质性”,而将其简化为两个相关物的差别。当然,抽掉或压缩“历史物质性”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艺术史的自觉,相反,恰恰是在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的分歧、冲突及相互的“修正”中,方可探得我们对于绘画、图像或艺术本身的认知,包括对于其“历史物质性”的重新展开和建构。甚至可以说,此处所谓的“艺术史”即追溯并重述艺术作品的“历史物质性”。只是问题在于,无论是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还是基于历史的艺术史研究,都将艺术作品和艺术史预设为一个透明的过程,而忽视了其中的不透明性。
就像迪迪-于贝尔曼所说的,诉诸原作(实物)的前提就是要承认艺术作品的先验性和不透明性。这里的不透明性不仅体现在作品(原物)的表面,也体现在它被历史物质化即艺术史的过程中。当然,如果我们面对和接触的并非原作(实物),而是图片(照片)的话,那么从“原媒介”到“次媒介”(或“次次媒介”,或“次次次……媒介”)的过程本身也是不透明的。前面提到,“原作”或“原媒介”其实是不存在的,它是一个不可抵达的目标,因此我们从一开始所见的就是一个“次媒介”。于是,双层乃至多层的“次化”致使意识并感知原作(实物)的不透明性,进而击破它变得愈加困难。反之,对于“原作”的承诺则变得尤为必要,因为只有基于这一前提,我们才能意识到其中复杂的媒介次化。此时,作为一个天然的“次媒介”,“图像”由于它的模糊性、笼统性和复杂性,反而成了一个相对准确、客观的表述,也是我们分析、论辩的前提和基础。
事实上,无论是夏皮罗与海德格尔之间,还是迪迪-于贝尔曼与潘诺夫斯基之间的“论争”,都可以笼统地归结为“图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图像”是自动地稀释了“原作”问题及其复杂性。比如,在海德格尔的叙述中,他其实并没有将凡·高的作品当作一幅绘画(painting),而是看作图像(Bild),夏皮罗的不满虽然是从一张绘画作品出发的,但在他对海德格尔的图像式“修正”中显然侧重于“picture”,而不是纯粹的“image”。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是围绕“图像”(icon)展开的,但是在迪迪-于贝尔曼的“修正”中,名义上是图像(image)式的“修正”,实际上融合了很多绘画(“painting”和“drawing”,包括“picture”)的基本元素。这里的图像看上去似乎有别甚至对立于绘画,但其实远比这一区分复杂得多。比如德语中的图像“Bild”,虽然不分物质的“picture”和精神的“image”,但海德格尔的图像明显倾向“image”,而不是“picture”;潘诺夫斯基的“icon”则更接近“image”,而不是“picture”;迪迪-于贝尔曼的论述虽然是围绕“image”展开的,但他所谓的视觉症候既来自“image”,亦来自“picture”。为了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迪迪-于贝尔曼援引了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的这段论述:
图像一词有点声名狼藉,因为人们不仅很容易相信一幅素描不是移印的,就是复印的,总之是一件二手货,而且想象中的图像就是我们私人旧货铺里的一幅这样的图画。它似乎与素描和油画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它们都不是只有一种固定的形态。它们既是里也是外,既是外也是里,感觉的双重性使这里的水乳交融成为可能,没有这种里外,我们将永远搞不清想象领域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转引自迪迪-于贝尔曼206)
这里的“图像”融汇了“image”“icon”“picture”乃至“painting”和“drawing”的元素,并和绘画一样,包含着透明性和不透明性。而这也是迪迪-于贝尔曼关于图像的认知和理解。按他所言,在图像世界中,“特殊图像的流星雨和迸发——永远不会把它的对象作为可以用真的或假的、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命题来表达的逻辑的术语呈现给我们”。“图像的‘世界’不排斥逻辑的世界,而是相反。它在玩弄它,也就是说它在其他东西中为自己吸取力量,这是一种作为否定力量的强力。”(迪迪-于贝尔曼207)
显然,无论在夏皮罗这里,还是在迪迪-于贝尔曼这里,“图像”既是对象,也是方法。夏皮罗通过对于海德格尔的“修正”,将图像放回个人的经验与想象中;迪迪-于贝尔曼对于潘诺夫斯基的“修正”,则将图像从透明性机制中解放出来,在不透明性中探得图像的运动潜能。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原作的承诺,“个人经验”和“不透明性”恰恰是建立在原作(实物)的基础之上。而这不仅是夏皮罗不反对哲学介入绘画的缘由,也是迪迪-于贝尔曼与瓦尔堡的区别所在。夏皮罗的艺术史“修正”固然建立在“picture”的基础之上,但他无意由此回到纯粹精神的“image”,“picture”也是绘画的属性之一;迪迪-于贝尔曼也不想重返瓦尔堡的“image”,他并不回避图像中的“picture”元素。这表明,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图像”,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制和概念,而是一种开放的生成性存在和展现。
相比绘画,图像是一个范围更广的概念。在这里,它更像是艺术史与艺术哲学对话的一个介质。也正因如此,重申图像的意义并非将其置于各自封闭的透明系统中,有时候,二者的对话恰恰是通过图像的不透明性展开的。所以,图像并不排斥绘画,因为图像的不透明性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其中的)绘画元素。绘画元素是原作之为原作的条件之一,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不见得是绘画(实物),也许是图片(或照片),但即使绘画,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原作,而原作的不可抵达恰恰说明原作的承诺显得尤为必要。此时,承诺原作不仅是为了激发其不透明性,也是为了承认支配它的透明性机制。只有在这一认知前提下,我们方可真正将艺术史与艺术哲学区分开并联系起来,进而探得它们对话的基础和相互解放的可能。
余 论
两次“论争”距离夏尔丹的《猴子画师》差不多有两个世纪之久,然而在这些艺术史家和哲学家的思想观念中,还是不难看到后者的影子。相信他们的理论与夏尔丹画作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其诉诸绘画之动物性和不透明性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是两次“论争”最适切的图像注脚。值得一提的是,本文讨论的重心虽然在夏皮罗与海德格尔、迪迪-于贝尔曼与潘诺夫斯基之间,但事实上,德里达和瓦尔堡在其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卷入和被卷入不仅让两次“论争”变得更加复杂,也从另一个角度将两次“论争”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关于“海德格尔—夏皮罗—德里达”和“潘诺夫斯基—迪迪-于贝尔曼—瓦尔堡”这两组“三角关系”,前文已作较为详尽的交代,容不赘述。除此以外,还包括以下四重关系:(一)潘诺夫斯基与夏皮罗。潘氏深受德国艺术和哲学传统的影响,但《图像学研究》则充分体现了一种理性、透明和实证的英美学术风格,与之相应,以实证为基的夏皮罗无疑也在英美学术系统中。(二)瓦尔堡与海德格尔。尽管二者的研究领域不同,但反形而上学、反历史主义构成了他们共同的观念和旨趣。(三)迪迪-于贝尔曼与德里达。海德格尔和夏皮罗都诉诸“归属”的欲望,而瓦尔堡与潘诺夫斯基追求的则是图像志及其文化意义。这其中,来自法国的两位激进左翼思想家德里达和迪迪-于贝尔曼则仿佛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比如他们共同追求的表面“痕迹”和“延异”,恰好解构或摧毁了双方的“论争”。德里达显然倾向海德格尔一方,而且在反形而上学这条道路上,比海德格尔还要彻底;迪迪-于贝尔曼亦复如此,他完全是站在瓦尔堡的立场挞伐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透明性机制。(四)除了上述关系之外,夏皮罗和瓦尔堡分别是“风格论”和“图像学”两个同样处在“对峙”中的艺术史传统之典范。与之相对的潘诺夫斯基与海德格尔则是弗赖堡大学时期的同学,虽然前者深受后者的影响,但二者分别成了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代表,这一“对峙”关系也深刻体现了他们之间的差别(范白丁157—163)。有意思的是,正是他们各自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两个文本,引发了这两次著名的“论争”。而这不仅是不同个体和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满”和“修正”,在某种意义上,也多多少少体现了美国、德国与法国三个不同学术和思想传统之间的分野、对话和冲突。
注释[Notes]
① 这主要是针对绘画、雕塑等传统媒介而言的,尚无法涵盖影像、装置等媒介更加复杂的当代艺术实践(巫鸿10—18)。
② 彭锋的结论是:“美学与美术史的视野的确有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它们是不同的,用美术史的视野来否定美学的主张,与用美学的视野来否定美术史的主张,同样是有风险的。”(彭锋75)
③ 法语中的素描(dessin)和构思(dessein)是同一个词根(刘碧旭57—5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吉奥乔·阿甘本:《阿比·瓦尔堡与无名之学》,《潜能》,王立秋、严和来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年。125—149。
[Agamben,Giorgio.“Aby Warburg and Nameless Science.”Potentialities.Trans.Wang Liqiu and Yan Helai.Guilin: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2014.125-149.]
斯维特拉娜·阿尔珀斯:《描绘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王晓丹译、杨振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Alpers,Svetlana.TheArtofDescribing:DutchArtintheSeventeenthCentury.Trans.Wang Xiaodan.Ed.Yang Zhenyu.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21.]
霍斯特·布雷德坎普:《图像行为理论》,宁瑛、钟长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
[Bredekamp,Horst.TheoryoftheImageAct.Trans.Ning Ying and Zhong Changsheng.Nanjing:Yilin Press,2016.]
雅克·德里达:《定位中的真理的还原》,《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唐纳德·普雷齐奥西编,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25—442。
[Derrida,Jacques.“Restitutions of the Truth in Pointing(‘Pointure’).”TheArtofArtHistory:ACriticalAnthology.Ed.Donald Preziosi.Trans.Yi Ying,et al.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6.425-442.]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在图像面前》,陈元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
[Didi-Huberman,Georges.ConfrontingImages.Trans.Chen Yuan.Changsha: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15.]
乔治·迪迪-于贝尔曼 胡新宇:《专访法国艺术史家迪迪-于贝尔曼:谈论艺术是哲学不可少的一部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2015年7月5日B10版。
[Didi-Huberman,Georges,and Hu Xinyu.“Interview with French Art Historian Georges Didi-Huberman:Talking about Ar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hilosophy.”OrientMorningPost5 July 2015.]
范白丁:《〈图像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来源》,《世界3:开放的图像学》,黄专主编。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年。150—169。
[Fan,Baiding.“Some Theoretical Sources ofStudiesofIconology.”World3:OpenIconology.Ed.Huang Zhuan.Beijing:China National Photography Art Press,2017.150-169.]
Lee,Pamela M.Illegibility.Ostfildern:Hatje Cantz Verlag,2012.
刘碧旭:《观看的历史转型:欧洲艺术展览的起源与演变》。台北:艺术家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Liu,Pi-Hsu.HistoricalTransformationofGaze: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EuropeanArtExhibition.Taipei:Artist Publishing Co.,2020.]
安德烈·马尔罗:《无墙的博物馆》,李瑞华、袁楠译,孙宜学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Malraux,André.MuseumwithoutWalls.Trans.Li Ruihua and Yuan Nan.Ed.Sun Yixue.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1.]
菲利普-阿兰·米肖:《〈记忆女神图集〉,艺术史与场景建构》,胡新宇译,黄洁华校,《世界3:开放的图像学》,黄专主编。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7年。70—104。
[Michaud,Philippe-Alain.“Aby Warburg’s Mnemosyne,or Staging the History of Art.” Trans.Hu Xinyu.Ed.Huang Jiehua.World3:OpenIconology.Ed.Huang Zhuan.Beijing:China National Photography Art Press,2017.70-104.]
欧文·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戚印平、范景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Panofsky,Erwin.StudiesinIconology:HumanisticThemesintheArtoftheRenaissance.Trans.Qi Yinping and Fan Jingzhong.Shanghai: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1.]
彭锋:《凡·高的鞋踩出一个罗生门》,《读书》12(2017):69—75。
[Peng,Feng.“Van Gogh’s Shoes Stepping out a Rashomon.”Dushu12(2017):69-75.]
迈克尔·波德罗:《批评的艺术史家》,杨振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Podro,Michael.TheCriticalHistoriansofArt.Trans.Yang Zhenyu.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20.]
迈耶·夏皮罗:《绘画中的世界观:艺术与社会》,高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Schapiro,Meyer.WorldviewinPainting:ArtandSociety.Trans.Gao Xin.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Press,2020.]
——:《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一则关于海德格尔与凡·高的笔记》,《艺术史的艺术:批评读本》,唐纳德·普雷齐奥西编,易英、王春辰、彭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19—424。
[---.“The Still Life as a Personal Object:A Note on Heidegger and Van Gogh.”TheArtofArtHistory:ACriticalAnthology.Ed.Donald Preziosi.Trans.Yi Ying,et al.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6.419-424.]
宋聪聪:《凡·高的第九双鞋——走出农鞋阐释罗生门的一个尝试》,《文艺研究》3(2020):148—160。
[Song,Congcong.“Van Gogh’s Ninth Pair of Shoes:An Attempt to End the Dispute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rm Shoes.”Literature&ArtStudies3(2020):148-160.]
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读书》5(2007):10—18。
[Wu,Hung.“The Return of Actual Objects:‘Historical Materiality’ of Art.”Dushu5(200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