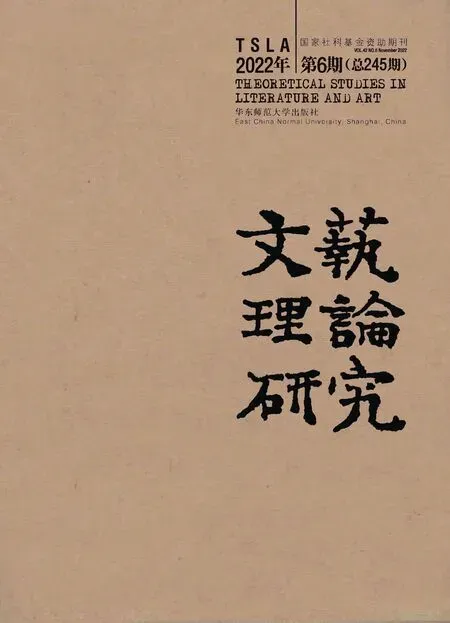重新审视“东方比较文学”
杨 清 曹顺庆
探讨此话题的机缘源自笔者正在编写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20》之“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栏目①。该年鉴接续杨周翰、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以及曹顺庆、王向远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旨在提供系统而全面的中国比较文学信息与资料。与“中西比较文学”相比,“东方比较文学”这一称谓在国内用得并不算多,其成果数量自然也无法与之相媲美。学界对此命题的理解与阐释不一,在研究范围方面有明显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在研究内容方面又在学科范式与具体研究对象之间徘徊。尽管如此,《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10》《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20》将“东方比较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列入其中,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学科史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翻译文学研究”并置,共同组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问题是:“东方比较文学”究竟研究什么?为何要在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下单设“东方比较文学”这一分支学科?其对比较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有何意义?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当下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东方”问题。
一、“东方比较文学”的源与变
“东方比较文学”这一命题出现得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比较文学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时,才被部分东方学研究学者正式提出。但追根溯源,“东方比较文学”这一观念却早已存在。早在20世纪60年代,东方各国“或将比较文学引入大学课堂或积极创办杂志、发表演讲,掀开了东方比较文学的序幕”(曹顺庆 徐行言270)。这一思想又可追溯至法国学派代表人物梵第根的“总体文学”观念,即追求一种“世界性”意义。正是秉持“总体文学”这一追求世界性普遍规律的观念,东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试图“突破比较文学领域内的西方中心主义,将单一的‘总体文学’理论革新为多元的‘总体文学’理论”,并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了比较文学的“东方突围”(曹顺庆 徐行言271)。
在“东方比较文学”诞生之初,学界对其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的划定处于探索阶段,但主要是指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尤其是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东方文学比较。这与当时以季羡林先生为代表的东方文学研究学者的观点不无关系。季羡林先生曾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至少具备两个特点,一个是以我为主,吸收国外优秀内容;另一个就是要“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文化交流与比较文学》2)。季羡林先生将中国文学纳入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这一广阔研究领域,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学在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位置,并以此来纠正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为“东方比较文学”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础。
“东方比较文学”从一开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逐渐延伸至东方文学关系史、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比较,其研究范围呈扩大趋势。1983年,我国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关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建设,并意识到“比较研究中国文学与阿拉伯、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和地区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将中外文学关系、东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等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全盘推出,并列为醒目与振奋人心的长期研究目标”(孟昭毅,《走向世界 回归东方》136)。1985年,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要将东方文学归入比较文学研究范围,而当年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更是将“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单列为一个讨论专题。1986年,北京大学召开了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研讨会,内容涵盖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印度文学与东方文学、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东方各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413)。研究范围明显已从早期将其限制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比较,拓展至东方文学之间以及东方与世界文学之间的比较,甚至延展至东方文学关系史研究。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了《比较文学丛书》,以注重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逻辑组合为划分标准,将当时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内容划分为“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国外比较文学研究概貌”四个板块。其中,卢蔚秋编写了一本《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收录了19篇文章。尽管,《比较文学丛书》与《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并未对“东方比较文学”这一命题进行阐释,但从收录的文章类型来看,主要偏重于东方各国、各区域文学之间的影响与关系研究,如严绍璗的《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韦旭升的《中国文学对朝鲜国语诗歌的影响》、蔡祝生的《缅甸文学的佛本生故事来源》、卢蔚秋的《中国通俗小说在越南》、张鸿年的《波斯文学与阿拉伯文学关系初探》与《波斯文学在中国》等。正如季羡林先生在此论文集的序言中所言,东方近现代文学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东方的文学对欧洲也产生影响,而东方各国、各文化圈之间的文学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4—5)。在此,“东方比较文学”其实就是对东方各国、各文化圈的文学进行影响研究。以上种种学术活动为“东方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范式的诞生埋下了伏笔。此为发展的第一阶段。
“东方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始于其成为一门学科范式。1988年,孟昭毅发表《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刍议》一文,从学科层面探讨“东方比较文学”的规律与特点。自此,“东方比较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分支学科名称正式得以确定。在《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刍议》一文中,孟昭毅从季羡林先生有关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关系的论述中高度提炼,首次系统阐述东方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规律与特点:一是此研究具有东方文学自身发展的纵向、单维的直线性,二是包括东方各文化圈、各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和东西方各国、各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在内的二维横向平面性,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下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纵深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立体性(83—88)。孟昭毅笔下的“东方比较文学”是相对于以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而言的,是对东方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之总括,内容既包括东方内部比较,亦包括东西比较,同时囊括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问题。孟昭毅所提出的“东方比较文学”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意欲纠正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的偏颇与片面性,摆脱欧洲中心论,并避免产生新的东方中心论偏颇。这与“东方比较文学”这一命题诞生之初的内涵一脉相承。同年,《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第3期推出“东方比较文学专辑”,收录了1986年北京大学召开的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研讨会部分论文,主题包括中印文学与神话比较、唐代变文与缅甸佛教文学比较、李白对朝鲜古典诗歌的影响、中朝讲史小说比较、中越文学比较等。此外,该专辑还收录了东西文学比较、国外阿拉伯文学研究等论文。可见,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比较文学”在发展早期,其研究范围较此命题诞生之初有所拓展。
秉持着这一研究观念,孟昭毅出版的《东方文学交流史》(2001年)一书具体践行了东方比较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范式。该书立足中国文学发展史,分区域探讨中国与东北亚文学、东南亚文学、南亚文学、西亚文学之间的交流史,具体则包括中朝、中日、中越、中泰、中缅、中国与新马、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中印、中伊、中阿文学之间的交流关系,基本覆盖了东方内部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学关系。但此书的编撰体例又回到了此命题诞生之初的观念,以中国为中心来审视中国与东方其余国家或区域文学之间的关系,仿佛中国文学并不在东方文学之列。
在“东方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方面,学界存在分歧。孟昭毅在《东方文学交流史》导言中划定了“东方文学”的研究范围:“东方文学一般指亚洲和非洲的文学,不包括中国文学。”(2)正是因为这一认识,《东方文学交流史》主要是指中国与东方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史。而王向远在《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中,按“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东方比较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研究”和“其他”分类收录。其中,“东方比较文学”指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东方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唐建清 詹悦兰485)。王向远所理解的“东方文学”是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而“东方比较文学”乃是以中国文学为中心的东方内部比较,不涉及东西比较。
针对这一分歧,季羡林先生就曾发出疑问:“‘东方文学’的来历和含义是什么?”在季羡林先生看来,“‘东方文学’这个概念既有地理因素,又有政治因素,是亚洲和非洲文学的总称”(《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1)。当下,我们所论及的“东方文学”自然是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国家或区域全部文学在内,但早期的东方文学研究并未将中国文学纳入其中。究其原因,这与当时有关东方文学的认识有关,即将东方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一部分,往往不包括中国文学。然而,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或如梵第根所言之“总体文学”,能够与“西方”对话的“东方”并非印度、波斯、阿拉伯、朝鲜、越南、泰国或者任何一个单一国家和区域,而是包括东方各民族在内的一个整体。东方文学的整体性与差异性是东方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备的一体两面性。东方文学内部语种多、理论杂,不同民族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呈现出多元、差异的理论特征。但东方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言是一个整体。在此强调东方文学的“整体性”,并非忽视东方文学内部的多元特征,而是强调突破国别文学、区域文学的界限,强调东方文学的整体研究,破除的是过去常常将中国文学排除在外的东方文学研究之局限,以挖掘东方内部多语种文学所关注的共同人类命题、共同审美特征,如王向远教授就以“味”这一东方各区域所共有的诗学范畴为纽带,认为在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之上还存在“东方共同诗学”(《“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17)。对整体的强调恰恰是东方文化综合、整体、普遍联系的思维模式之体现,如印度“梵我一体”、中国“天人合一”思想(季羡林,《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4)。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东西文学比较、世界文学研究的拓展,东方文学研究学者意识到了东方文学的整体性,遂将中国文学囊括其中,以此形成完整而多元的东方文学。这也是季羡林先生提出要将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研究范围之内的重要意义所在。
正是因为这一认识的转变,在200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通论》一书中,孟昭毅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之中,所举例子大多为东方文学例子,为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详实实践案例。此外,孟昭毅还在此书中回顾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勃兴的十年(1982年—1991年),并专列一小节论述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问题。在孟昭毅看来,1982年至1991年的十年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十年,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初显雏形的十年,同时也是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勃兴的十年,无论是专著的出版、论文的发表,还是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国内学界围绕东方比较文学展开了具体的研究,诸如《中国文学在朝鲜》《中国文学在日本》《中国文学在越南》《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等专著的问世,以及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1991年北京大学召开的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的展开,将国内学界只盯西方的目光转向东方内部(《比较文学通论》412—416)。
“东方比较文学”究竟研究什么?刘舸、黎跃进认为,孟昭毅所提的“东方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可分为两个层次理解:一是东西方文化、文学的比较,二是东方文化、文学之间的比较(140)。其实,还有第三层意思,即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作为整体的东方文学纵深发展体系,如孟昭毅所言之此学科的一大特点即为世界文学视野下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纵深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立体性。换言之,“东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并未将自身囿于东方内部,而是通过东方内部的比较,更全面、更深刻地进行东西比较,从而在世界文学视野下审视东方文学。这是“东方比较文学”发展第二阶段的意涵。
值得注意的是,孟昭毅对自己所提出的这一概念的阐释亦有所变化。在2006年发表的《季羡林与东方比较文学》一文中,孟昭毅将“东方比较文学”定义为“以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比较研究”(70)。无独有偶,同年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将“东方比较文学”研究范围划定在中国与其他东方国家文学比较之中,在论述近年来“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推进”时,仅论及中印、中日以及中国与东方其他国家文学关系研究(乐黛云 王向远245)。显然,其范围有所缩小,从原来的三层含义缩减至其中的一层,目的在于凸显比较文学中的“东方”价值。这为第三阶段跨文明比较研究视野的东方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着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设发展,国内学者意识到了东方文学在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默认“东方比较文学”为一门分支学科,取其狭义,即东方内部之间的比较。这一时期有关“东方比较文学”本身的探讨较少,反而是具体实践增多。2010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划定“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为比较文学分支学科,其内容包括“中国与东方各国文学关系研究”“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东方文学的综合研究与总体研究”三个方面(曹顺庆 王向远1),收录了9篇文章、6本著作,其研究范围即为东方内部之前的比较,并不包括东西比较。而诸如王志松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日文学关系研究与文献整理(1870—2000)”、葛继勇领衔的“中日合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金柄珉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朝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石云里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日韩古天文图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开展,有效促进了东方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
“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并不等于“东方文学比较研究”。但在学科发展早期,学界存在“东方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比较”混用的情况。比如,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比较文学丛书》下设“东方文学比较研究”子栏目,但最终出版的论文集却称为《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究其原因,还是在于早期学界对“东方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界定不一。“东方比较文学”是作为比较文学分支学科而存在;“东方文学比较”是作为具体研究的对象而存在,强调是东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有了东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存在前提,东方文学的比较才更具学科背景与文化内涵。
一言以蔽之,“东方比较文学”这一命题即是针对国际比较文学界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以及对“东方”认知的偏颇而提出来的,追求一种“世界性”意义;与此同时,此命题又强调世界中的东方,对抗全球化和西方视域中的“世界文学”所暗藏的同质化倾向。无论是包括东方比较、东西比较和世界中的东方三个层面在内的广义“东方比较文学”,还是狭义上的东方内部比较,“东方比较文学”的宗旨始终不变,即立足东方,重视对东方自身的研究,并以此作为开展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
二、从“东西比较”到“东方比较”:回到“东方”
“东方”是东方研究的关键词。之所以关键,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东方比较文学、东方学、东方文学抑或是东方文论研究,一切有关东方的研究均始于“东方”这一概念的含义,其落脚点无不与还原或构建真实的“东方”有关。对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东方”含义进行辨析,一方面源于反思西方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心/边缘”、“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另一方面则是审视东方本身的结果。
“东方”既具地理方位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同时也含文化、美学意义,亦构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季羡林先生认为,“东方”主要是指“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1)。换言之,“东方”乃指政治上的“东方”。孟昭毅教授同样持此观点,他曾简要描述了“东方”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并指出古代中国史上的“东方”纯属地理上的概念,欧洲史上的“东方”即指古代的西亚北非地区,20世纪以来的“东方”则由纯粹的地理概念演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与“西方”对应(《东方文学交流史》1—2)。如若将“东方”定义为政治上的“东方”或如季羡林所言之“第三世界”,那么同为“第三世界”的大洋洲、拉丁美洲国家是否也属于东方?这一定义无疑扩大了“东方”的范围,变成了政治意义上的泛“东方”。李希凡教授就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东方”与政治上的东西方划分无关,而是一种笼罩在“欧洲中心主义”阴霾下的“定义”,并非真正的“东方”(IV)。这也即为何李希凡教授认为,当全盘西化瓦解后,中国学界正在“回到东方”,意欲通过挖掘自身的艺术与美学遗产,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东方艺术与美学的独特体系与形态源流,以便更准确地把握东方艺术与美学规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进行这项工作。
虽然东方无论在制度、文化、哲学、艺术还是器物方面都曾对欧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但西方眼中的“东方”往往含有想象与构建成分,要么被简化为“古老文明”,要么被边缘化,要么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参照性存在。赛义德针对西方长期存在的东方想象,在《东方学》(Orientalism,2003年)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几乎是欧洲的发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异国情调、令人难忘的回忆和风景、非凡经历的地方。”(Said1)无论是黑格尔所认识的静止而僵化的“东方”,还是赛义德所指出的西方想象中的“东方”,均非真正的东方。
有鉴于此,国内学界在大力提倡跨文明对话与比较的同时,掀起了一股“东方”研究浪潮,引发了国内学界以“东方”为学术研究的切入点展开系列研究,要求回到“东方”,甚至还原“东方”,重建“东方”,内容涵盖“东方学”“东方文艺理论”“东方文学”等内容。两者并行不悖,共同促进了东方研究。这是因为跨文明对话与比较的前提是立足本土文化,对本土文明有深入而系统的理解。孟昭毅就总结道:“无论是把比较文学的本质视为‘打通’、‘参照’,还是理解为‘超越’、‘对话’,中国比较文学的立足点、出发点只能有一个,即以中国文学为重要营养成分的东方文化沃土。”(《走向世界 回归东方》148)事实却是,“东方文论长期被西方忽略、歧视和贬低,甚至东方人自身对东方文论的核心范畴及其价值也不甚了解,更谈不上东方文论总体研究以及东西方文论的系统比较研究”(曹顺庆1)。无独有偶,乐黛云在20世纪80年代就意识到类似问题的存在,认为“关于亚洲各文化体系的相互影响还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6)。其实,何止是亚洲各文化体系之间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也同样薄弱。
庆幸的是,国内学者已然深刻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东方研究。随着以“东方”研究为特色而又不囿于东方的《东方丛刊》(1992年创刊)在2018年复刊,国内东方研究再次掀起研究热潮。《东方丛刊》复刊号刊发了一众东方文学研究者的成果,包括王向远的东方学研究、王兆胜的林语堂与东方文化研究、孟昭毅的伊朗与东西文化研究、蒋述卓的中日研究、尹锡南的印度古典文论研究、李忠敏的南非作家库切研究等,还刊发了黎跃进的东方研究重大课题论证纲要《丝路域外经典作家、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与此同时,诸如曹顺庆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古代文艺理论重要范畴、话语体系研究与资料整理”、黎跃进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穆宏燕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世纪东方区域文学年谱整理与研究(2000—2020)”、陈明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东方文学插图本史料集成及其研究”、王邦维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王向远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张玉安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等国家级重大项目的立项,再次印证了近年来我国学界对东方文学、东方文艺理论、东方研究的高度重视。
得益于上述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的落地,国内学界在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逐年增多,仅2020年就有50余篇重要论文发表,内容涵盖中印(印度)、中韩(韩国)、中朝(朝鲜)、中阿(阿拉伯)、中伊(伊朗)、中越(越南)、中泰(泰国)文学或文论比较,还出版了《回声·镜鉴·对话——中日文化与文学》(孟庆枢,2020年)、《交流与互鉴: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论集》(王邦维,2020年)、《从长安到日本:都城空间与文学考古》(郭雪妮,2020年)、《近时世中国与日本汉文学》(张淘,2020年)、《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华文女作家小说比较研究》(马峰,2020年)、《司马辽太郎研究(东亚题材历史小说研究)》(关立丹,2020年)、《蒙古族史诗与印度史诗比较研究》(王艳凤等,2020年)等专著。并且,以往不受重视的东方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比较,比如中阿、中伊、中越、中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相继推出成果,丰富了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内容。这既是东方研究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反过来印证了当前东方研究在国内学界的复兴与研究热度不断攀升。
这种研究热度并非一时的学术时髦,而是我国学者长期致力于比较文学与东方研究的结果。我国学者立足当前国内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现状,力图突破国际比较文学现有学科范式,回到“东方”,不断溯源、挖掘东方自身的丰厚文化内涵,补足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缺失或误读的“东方”,从而还原“东方”。这种“还原”也并非仅仅停留在勾勒出客观真实的东方样貌这项工作之上,而是立足东方,放眼世界,建设完整而又系统的东方学术话语体系。
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东方比较文学”这一概念是必要的。这不仅关系到东方研究,更关系到比较文学学科建设问题。无论是取广义的“东方比较文学”还是狭义的“东方比较文学”,单从这一学科的命名便可窥见其中的内涵:其落脚点在于“东方”,充分认识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学科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同时认识到了东方文学内部的多样性、类同性与差异性,力图突破传统的“中西比较”“东西比较”模式,从“东西比较”转向“东方比较”,从而将研究视域聚焦于东方内部。
此处所说的从“东西比较”到“东方比较”并非要摒弃“东西比较”,而是强调东方本身,强调回到东方,深入挖掘东方丰富的文学与文论内涵,在东方内部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进行“东西比较”。当然,研究的最终目的也并非简单的“东西比较”,而是要深刻认识到东方,还原东方,打破国际上东方的“失语”困境。这并非一句空洞而苍白的“口号”,此文也并非进行某种无力的呐喊与倡导,而是立足当前学界有关东方与比较文学的研究,论证东方比较文学对于我国学界东方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并立足当下,试图解读其在当下可能产生的新意义。
三、“东方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学、东方文论研究
东方文学或文论体系的建设离不开比较文学的视野与方法,反之亦然。自国内比较文学研究起步始,将东方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2002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以“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为题举办了研讨会。该研讨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联姻”,黄宝生等学者认为“这对国内搞东方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希望这次探讨会能借鉴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化对东方文学的研究,同时也通过对东方文学的观照扩大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林丰民127)。此次研讨会释放出一个信号: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联结将生发新的研究范式。而该研讨会所讨论的诸如“中阿文学比较”“印度文学在东南亚的流传与变异”“中日文学比较”“中印文学比较”“中埃文学比较”等命题均探讨东方文学内部之间的比较问题,为东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案例。
从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来看,“比较文学是从西方国家兴起的,而且长期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历来视西方文学为正宗而忽视甚至轻视东方文学,所以,这门人称‘国际性’的学科,其实是片面的、局部的‘国际性’,而缺乏全球性的国际性、真正的国际性”(陈惇4)。“东方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相对于欧美比较文学研究所陷“僵局”而提出来的“良方”。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副主席、日本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芳贺徹就指出,“东方比较文学”其实是站在亚洲文化圈的立场上,将内容丰富而又历史悠久的中国、韩国、日本的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研究范围,从而打破欧美比较文学僵局(91—92)。而这个“僵局”就是启发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不断进行学科范式反思与建设的引子:欧美比较文学虽然标榜自己是在“比较”(尽管后来法国学派声称“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基于历史实证主义之上的文学关系研究),但其“比较”仅限于欧美文化圈,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芳贺徹91—92)。因此,我们应该在跨文明交流与互鉴视野下,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开放性、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科。
这正是“东方比较文学”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意义所在。刘舸、黎跃进在评孟昭毅的《比较文学通论》中有关“东方比较文学”概念时指出,此概念具备以下学术价值:一是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二是有助于东方文学研究的深化,三是有助于发展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比较文学(139—142)。虽然刘舸、黎跃进充分肯定了这一提法对中国比较文学、东方学事业的贡献,但同时也指出此提法只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权宜之计”,因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超越东西方,并质疑其在比较文学前加“东方”二字是否违背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本身的开放性,是否是从“西方中心论”走向“东方中心论”。
不可否认的是,过于强调“东方”的确会引发了对“东方中心论”的怀疑,但基于当前国内有关东方学的研究现状,加上东方本身具备的丰富内涵亟待挖掘,我们怎么强调“东方”都不为过。如果我们连东方文学内部的丰富性、多样性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研究透,连东方内部之间的比较都还没有开展,我们又如何进行东西跨文明比较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单列“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学科研究等并置,共同组成中国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内容,即是一个例证。从中可见学界始终认同“东方比较文学”这一提法的合法性。并且,在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时代,加强以往我们不够关注的文学交流与对话势在必行,正如李伟昉所言,“东方文化、文学之间的相互比较与对话,就是一个亟待加强与重视的研究领域。[……]不仅是基于我们自己作为东方人从整体上认知‘东方’概念内涵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我们在全球化、多元化视野下积极建构与‘西方学’平等对话的‘东方学’的重要前提”(1)。
“东方比较文学”在今天同样具备上述价值,甚至还可以有所拓展,正如王向远所言,“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的资源还十分丰富,大量的学术领域有待开垦开拓,特别是东方比较文学,数千年的积累积淀,需要发掘清理,需要说清楚、写出来”(王向远326)。其中一个拓展方向即为东方丰厚的古代文艺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过去的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往往聚焦文学作品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从主题学、文类学、文学史、翻译学方面切入的比较研究,较少涉及东方各国、各区域的文艺理论比较。
一个完整的文学体系离不开理论体系的建设。借用章太炎先生的话来讲,“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7)。文学要同时包括文学文本与研究文学“法式”的理论,否则就不能完整地构成文学。同理,比较文学研究既要研究文学作品,同时也要进行理论研究,否则就不能算作完整的比较文学。因此,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完全可以将其研究范围拓展到东方文艺理论比较研究;反过来,东方文艺理论研究又可借用东方比较文学研究范式,深入挖掘其丰富文论范畴并进行比较,并在世界文学和总体诗学视野下,审视东方文艺理论的特征与规律,探讨人类共同的“诗心”。
在此强调东方古代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乃是基于一个事实:当前国内外学界有关东方文论研究的成果丰硕,但现有成果大多局限于中西比较,东方文论自身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包括中国古代藏族文艺理论与蒙古族文艺理论)与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古代文艺理论的历史关联的研究很少,以阿拉伯和波斯文论为比较对象的研究更为缺乏。尽管,东方古代文艺理论曾在历史上闪闪发光,但在现代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却并未发出足够的声音。
东方文艺理论既体现了人类共同关注的命题与审美规律,亦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呈现出其自身的独特性。尽管,无论是西方文艺理论还是东方文艺理论,其内部的理论种类繁多、观点庞杂,很难用一两句话就准确、全面呈现整个体系,但立足话语的意义生成方式和言说方式来看,或可把握东西方最显性的理论话语特征。季羡林先生曾总结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主要源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即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东方文化集成·总序》3)。从文论话语意义生成方式来看,西方主要以“逻格斯”为中心,生发出二元对立思想,讲究条分缕析般的分析;东方则较为注重“无中生有”,从无形的“道”看事物一般规律,如庄子所言之“万物与我为一”,讲究综合性研究。从文论话语言说方式来看,西方尤其是当代西方哲学艺术思潮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尤为看重语言和形式对于意义的表述作用,持“语言本体论”或“结构本体论”(杨清 曹顺庆105),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海德格尔所持“语言是存在之家”等观点;东方的文学艺术思想则充分意识到语言和形式的局限性,要求超越有限的语言与形式,追求无限的韵味,如中国文艺理论强调通过“立象尽意”传达无限的意蕴,印度文艺理论的“味”论追求无限“大梵”快乐,阿拉伯文艺理论强调通过“技”去表述隐藏的深意,日本文艺理论中的“愍物宗情”揭示的是“言外之意”的无限韵味(曹顺庆9)。东方文艺理论既具形而上的思维普遍性,即王向远所言之“东方共同诗学”,又在具体的表述上各不相同,形态各异。东方古代文艺理论的比较完全可以纳入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之中,对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波斯为主的西亚文化圈、以中国为主并包括日、朝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包括越、泰为主的东南亚文化圈的古代文艺理论进行横向比较,比较重要文论范畴与话语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东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结 语
“东方”作为“异域”形象,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学术话语中长期面对“被误读”“被边缘化”的处境,甚至东方对东方都不甚了解,忽视了其内部多元化与异质性特征。结果,“东方”在西方的“失语”持续循环式地任由“他者”构建“东方”,东方形象非出自东方之笔,反成于西方之墨。这一现象理应在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东方学研究视野下得以修正,这也是重新审视“东方比较文学”的现实意义所在。国内有关东方文学或文艺理论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和其它研究的开展,将有效推动我国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基于各国各区域之间文学和文艺理论范畴的比较与关系研究,构建起东方学术话语体系。
注释[Notes]
① 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周翰、乐黛云主编、张文定编纂的《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886》,编辑整理了1985年以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上的重要文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只出版了1986年一卷,此后一直未能续编。鉴于此,笔者与王向远决定继北大版《年鉴》后继续编纂,目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008年卷,但因为客观原因再一次中断。然而,中国比较文学界不能没有年鉴。有鉴于此,四川大学双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和比较文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重点研究基地再次承担起比较文学年鉴编撰的重任,拟从2020年卷开始往后溯源,分别以一年一卷(2020,2010,2009)、二年一卷(2004~2005,2006~2007)、三年一卷(2001~2003)、五年一卷(1986~1990,1991~1995,1996~2000)的体式,陆续编完1987~2020年各年度《年鉴》,补齐二十多年来年鉴编纂的空缺,陆续出版发行。目前,绝大部分已经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待出版。其中,2010年卷已于2022年9月出版。自2020年度后,就可做到按部就班一年出一卷。参见曹顺庆、王向远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曹顺庆、王向远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1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曹顺庆主编、杨清副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20》《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21》(未刊)。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曹顺庆:《东方文论的重要价值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外文化与文论》1(2021):1—11。
[Cao,Shunqing.“The Important Value of Ea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ystem.”CultureStudiesandLiteraryTheory1(2021):1-11.]
曹顺庆 徐行言主编:《比较文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Cao,Shunqing,and Xu Xingyan,eds.ComparativeLiterature.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2016.]
曹顺庆 王向远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年鉴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Cao,Shunqing,and Wang Xiangyuan,eds.YearbookofChineseComparativeLiterature(2008).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0.]
陈惇:《序》,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3—6。
[Chen,Zhun.Preface.General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Literature.By Meng Zhaoyi.Tianjin:Nankai University Press,2003.3-6.]
芳贺徹:《东方比较文学的发展能打破欧美比较文学的僵局》,《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991):91—92。
[Haga,Tōru.“The Development of Ea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n Break the Deadlock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JinanJournal(Philosophy&SocialSciences)3(1991):91-92.]
季羡林:《正确评价和深入研究东方文学》,《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卢蔚秋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5。
[Ji,Xianlin.“We Should Correctly Evaluate and Explore Deeper into Eastern Literature.”AnthologyofEasternComparativeLiterature.Ed.Lu Weiqiu.Changsha: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87.1-5.]
——:《文化交流与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前言》,《国外文学》3(1986):1—3。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Preface to theYearbookofChineseComparativeLiterature.”ForeignLiteratures3(1986):1-3.]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文艺争鸣》4(1992):4—6.
[---.“Eastern Culture and Literature.”LiteratureandArtForum4(1992):4-6.]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东西文化比较》,张光璘编。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1—12。
[---.“Preface toTheSelectedBooksofOrientalCultures.”ComparisonofEasternandWesternCultures.Ed.Zhang Guanglin.Beijing:New World Press,2015.1-12.]
李希凡:《序》,今道有信:《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李心峰、牛枝惠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Ⅳ—Ⅴ。
[Li,Xifan.Preface.ComparisonofEasternandWesternPhilosophyandAesthetics.By Imamichi Tomonobu.Trans.Li Xinfeng and Niu Zhihui,et al.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1991.Ⅳ-Ⅴ.]
李伟昉:《关于东方文学比较研究的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5.6(2015):1—5。
[Li,Weifang.“Reflections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ern Literature.”JournalofHen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55.6(2015):1-5.]
林丰民:《“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东方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国外文学》2(2003):127—128。
[Lin,Fengmin.“‘Symposium on Easter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ld at Peking University.”ForeignLiteratures2(2003):127-128.]
刘舸 黎跃进:《东方比较文学体系的建构与异质文化的对话——评孟昭毅的〈比较文学通论〉》,《中国比较文学》1(2002):139—142。
[Liu,Ge,and Li Yuejin.“The Construction of Ea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ystem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Heterogeneous Cultures:A Comment on Meng Zhaoyi’sGeneral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Literature.”ChineseComparativeLiterature1(2002):139-142.]
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Meng,Zhaoyi.GeneralIntroductiontoComparativeLiterature.Tianjin:Nankai University Press,2003.]
——:《东方文学交流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HistoryofLiteraryExchangeintheEast.Tianjin: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1.]
——:《季羡林与东方比较文学》,《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4(2006):70—76。
[---.“Ji Xianlin and Ea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Journalof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ofSuzhou(SocialSciencesEdition)4(2006):70-76.]
——:《东方比较文学研究刍议》,《国外文学》1(1988):82—90。
[---.“On Ea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y.”ForeignLiteratures1(1988):82-90.]
——:《走向世界回归东方——中国比较文学十年潮》,《中国比较文学》1(1993):135—148。
[---.“To the World and Back to the East:A Decade’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ChineseComparativeLiterature1(1993):135-148.]
Said,Edward W.Orientalism.London:Penguin Books,2003.
唐建清 詹悦兰编著:《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
[Tang,Jianqing,and Zhan Yuelan,eds.ACentennialBibliographyofChineseComparativeLiterature.Beijing:Qunyan Publishing House,2006.]
王向远:《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
[Wang,Xiangyuan.Translatology:ANewParadigmofTranslationStudies.Beijing: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2018.]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社会科学研究》2(2020):16—26.
[---.“‘Taste’ Theory and Oriental Common Poetics.”SocialScienceResearch2(2020):16-26.]
杨清 曹顺庆:《中国艺术表现之“立象尽意”与西方语言本体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2022):102—108.
[Yang,Qing,and Cao Shunqing.“‘Lixiang Jinyi’ in Chinese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Western Language Ontology.”JournalofTianji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2(2022):102-108.]
乐黛云:《比较文学的名与实——〈比较文学丛书〉总序》,《东方比较文学论文集》,卢蔚秋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1—8。
[Yue,Daiyun.“The Name and Real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Preface toComparativeLiteratureSeries.”AnthologyofEasternComparativeLiterature.Ed.Lu Weiqiu.Changsha: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87.1-8.]
乐黛云 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Yue,Daiyun,and Wang Xiangyuan.ComparativeLiteratureStudy.Fuzhou: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6.]
章太炎:《文学总略》,《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傅杰编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67—75。
[Zhang,Taiyan.“General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CollectedWorksofZhangTaiyanonAcademicHistory.Ed.Fu Jie.Kunming: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7.6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