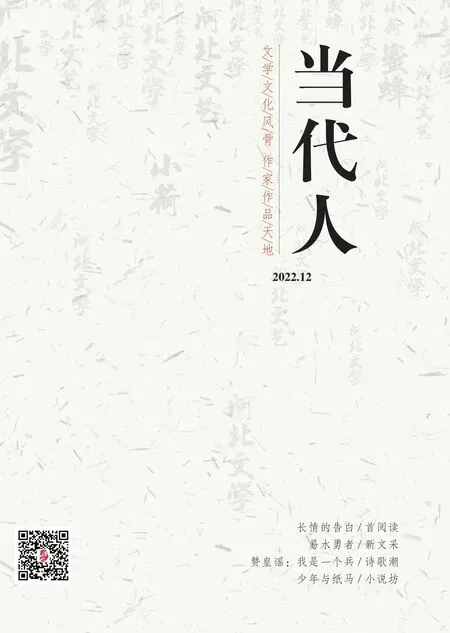幸福线
◇林一
电子离婚证
那款常用软件上线电子证件查询功能的时候,陈建军正在驾驶着6路公交车。十字路口的绿灯还有七秒,在陈建军的概念里是可以行驶通过的。鞋头上昂,像从跑道上昂昂上升的飞机,忽地往下踩了一脚,想着“咻”地穿过这个十字路口。他知道,此时正是上学上班高峰期,错过了一个绿灯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下一个、下下一个绿灯都可能会错过,车上坐着不少心急如焚赶着上班的乘客就会骂爹喊娘了。挨骂倒不要紧,耽误别人上班他心里过意不去。准备要通过斑马线时,一个人影不知从哪儿斜刺里冒了出来,幸好陈建军反应及时,狠狠地一脚踩在刹车板上,一车人往前倾,瞬间市井秽语喷薄而出。陈建军开公交车有二十多年了,这种状况自然能够轻松应对。那个突兀的“闯入者”不知所踪,陈建军拂了把额头渗出来的汗滴,转头低声下气地安抚好每一位乘客,好似那是他犯的错似的。这倒无妨,在陈建军的人生观里,装孙子也是一门生活哲学。
6路是环城公交,绕过两座大桥,直接驶入终点站火车站。陈建军跑6路线跑了好几年,后来公司要给他调岗,换到其他线路,他死活不干。他说,6路线是我的幸福线,我得干到退休呀。说完挠着后脑勺呵呵笑起来。
陈建军说6路线是他的幸福线,是有根有据的。他现在的妻子,戴裴,就是他在6路线上“捡”来的。
陈建军每绕城开一圈驶入终点站,都要在驾驶座位上端起装满茶叶的大玻璃杯,摇晃几下,好让杯中像水草般的茶叶旋转几圈。他打开杯盖,呷了一大口浓茶,端着玻璃杯往值班室去加开水,然后回到座位上玩手机。陈建军玩手机不玩别的,只为看新闻。手机上的新闻APP还是妻子戴裴给他安装的。智能手机好是好,但他不愿意被它绑架,除了看新闻,他就很少使用手机。
点开APP,他睁大眼睛,大拇指在屏幕上慢慢下滑,一条条新闻映入眼帘。
全国首张电子离婚证上线。
真是新鲜啊!现在是越来越便捷了,连离婚证都能够在手机上查看。陈建军在心里嘀咕着。他斜睨了一眼屏幕上的时间,距离下一班发车时间还有五分钟。
新闻还是那些新闻,不过是换了名字,结果大同小异,人世间的苦难大多一样。芸芸众生,大多数人都是来受苦的,谁也休想逃脱。陈建军感觉有些无味,想给妻子戴裴打个电话,又担心她在别人家做保姆正做着事,便作罢。
他继续翻阅手机上的APP,百无聊赖。正好瞧见了前些日子妻子用他手机安装的新软件,点了进去。听妻子讲这个软件可以查电子证件。陈建军想输入身份证号码试试,头脑里先蹦出的是妻子的号码,妻子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他记得要比自己的都牢。点击,输入,然后摁确定。手指滑动,他的瞳孔睁大,木讷坐着。他再次点击,输入,再摁确认。他端着手机,盯着屏幕目不转睛地看着,额头紧蹙,沟壑越积越深,山谷在额头上矗立。他坐立不安,左手撑在充满沟壑的额头上,头皮发麻,好像有很多软绵绵的虫子在头皮上蠕动。屏幕上显示的电子证,是妻子的离婚证。
6路公交车
陈建军的妻子是他捡来的,这认识陈建军的人都知道。陈建军是单亲家庭,他父亲陈战国是汽运公司的员工,跑过长途班线,跑过短途班线,最后死在了公交班线上。为了避开横穿马路的行人,陈战国猛打方向盘,朝车里吼了句,“都趴下,都趴下。”其实当时公交车上就只有他一个人。车子像头发情的公牛一头冲进一块建筑工地里,穿过一堵围墙,陈战国胸腔出血,送往医院途中死亡。同事说,陈战国就是跑长途的命,跑短途会要了他的命。
汽运公司传来噩耗的时候,陈建军正和母亲一起把一罐液化气搬进厨房,他母亲手一松,液化气罐就砸在了陈建军脚上。他没喊疼,耳朵嗡嗡响,回荡着来者传来的话语,“建军他阿爸没了”。他母亲早已晕厥在地上,倒是陈建军手里还呆呆地提着液化气罐,脸颊上的汗液和泪珠交织着。他张开嘴巴,费了很大劲才说,我阿爸怎么没的?来者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说了清楚,陈建军听完后把液化气罐扔在厨灶旁,劈头问了一句,我阿爸没了,我可以代替他开公交车吗?
陈建军就这样名正言顺地顶替他父亲成为一名公交司机,正所谓子承父业,继承陈战国未完成的事业,并且还把公交车开得比陈战国好,十多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当初到他们家传话的那人后来就跟公司的同事说,陈建军这个打靶鬼就是厉害,天生就是块开车的料。
陈建军那时候还在读高中,因为要继承他父亲的职业,所以很快退了学,拿到驾照后就到公交线上班。他母亲并不反对,毕竟公司赔偿一笔款给他们陈家,还安排儿子在汽运公司上班,有编制的,那无疑是陈家的祖坟上冒烟了。陈建军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七八年,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到了二十大几岁,他还没谈女朋友,母亲就坐不住了。他母亲是这样的心思,儿子虽然每天上班时间不长,六个小时,可他每天都要上,一个月就休假四天,那就没有充足的时间谈朋友了。她甚至怂恿过儿子,主动些,看见漂亮的乘客要厚着脸皮要联系方式,不要像番薯似的木讷。陈建军“哦”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他母亲可待不住,就跟到他驾驶的公交车上,稍微看得上眼的女人就上前索要联系方式,以至于一段时间很多女乘客都不敢坐那路公交车。汽运公司的领导找陈建军谈话,陈建军耷拉着个脸,回到家,很不情愿地吼了句,妈,我的事,你不要管了。他母亲心里有气,哭丧着脸,说,你翅膀硬了,我是管不了了。
陈建军调到6路班线是在母亲生病后,公司考虑到他要照顾老人,就特别关照他只上上午班,从早上六点到十点,四个小时。一天,雾气腾腾,陈建军在五点五十分给母亲做好早餐就出了门,准时开出6路首班车。车子从火车站开出,上来一个姑娘,脸蛋精致,模样颇有生气,眼神却呆滞,嘴唇干涩,上来就往投币箱投了一张红色的票子。这可让陈建军有些为难,他拉起手刹,走到那姑娘跟前,说,美女,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一时没那么多零钱找你,可又不能让你吃亏,你到哪里下车告诉我,我就在站台的附近换好零钱给你。那姑娘没有抬头看他,像是小时候看的电视剧《聊斋》里飘出来的女鬼,微弱地说了句“不用”。陈建军跑回驾驶室,启动车子驶出火车站。一直到大桥西站,途中只有零星几个人上下车。那姑娘就是在大桥西站下的,他喊她,她没有理会,恍恍惚惚朝大桥上走。陈建军追了一段路没好继续追,驾驶着6路公交车超过那姑娘。他透过后视镜瞧见她那魂不守舍的模样,一眨眼工夫,她从后视镜消失了。他刹车,下来,只见桥下荡起了一阵水花。他撸起袖子毫不犹豫地从栏杆上跳了下去。这一跳,让他捡了个媳妇。
结婚证
因为陈建军及时营救,姑娘捡回来了一条命。当她睁开眼睛看着那个趴在自己病床前的公交车司机,她就知道她的这条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所以,当陈建军一脸疲倦地揉着眼睛望着她,她劈头来了那么句,你还没结婚吧?陈建军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诧异着,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问。她立马说,那我嫁给你吧。这是一种坚决的语气,不容对方考虑。陈建军当时没坐稳,从床边的木凳子溜了下去,屁股开了花,当然他的心里也乐开了花。等她出院的时候,她拉着他说是顺道去把结婚证领了,生怕他反悔似的。陈建军心里明白,有一种感情叫知恩图报,他没有拒绝,毕竟他急需找个妻子回家。
领结婚证那天,陈建军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戴裴。陈建军没有过多追问她的过去。他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人,是他陈建军的妻子,就足够了。
后来戴裴断断续续告诉陈建军一些关于她的过往,孤儿,当初遇到一些挫折,想不开就寻短见,被陈建军救了一命。
陈建军是个容易知足的人。他没有追问她嘴巴里说的挫折是什么。他比戴裴大了十岁,三岁一代沟,所以他明白他和戴裴之间的鸿沟。他娶她那天,他认真打量了她,是个美人。后来他送了条吊带裙子给她,她穿在身上,他才明白什么叫美若天仙。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她曾经结过婚。其实,他早就应该有所察觉了。新婚那天,他猴急撕开她的内衣,那圆润的乳房左边有一道伤疤,弯弯曲曲,像一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他厚实的手掌小心翼翼抚摸那道伤痕,他瞧见她掉落的泪珠。她的后背还有几道疤痕,左边手臂有几个针孔。这些让他感到诧异,积累在心中很久的话语却不敢说出口。他暗暗猜想,眼前这个女人一定是从如来佛祖手中暂时逃走的猴子。
即便如此,陈建军仍旧停止不了胡思乱想,她是个有秘密的女人。可她在婚后老实本分,连他送给她的那条吊带裙也只在外面穿过一次,还是在他的同学聚会上。她平时都穿保守的衣服,从不化妆。她除了做家里的家务,还会接一些外面的活儿来做,一些零散的家务活儿。她几乎对他百依百顺,两人很少发生争吵。只是在要孩子方面,她坚持要过几年。陈建军自然没有反对。他明白,他把她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确实需要些时间缓缓。
日子过得像流水,潺潺而流,反反复复,陈建军更是把这日子过得跟他开公交车一样小心翼翼。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戴裴躺在身边,陈建军辗转反侧睡不着,感觉身子某个部位长了个肉粒疙瘩,不痛不痒,可那么突兀地长在身上,就有些不舒服。他几次想开口问,话飘出去了一半又被咽回肚子里。
自从知道戴裴离过婚后,陈建军似乎再也笑不起来了。原来他总喜欢从床头柜抽屉里取出红色的本子,那上面写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还有右上角贴着的照片,他在这头,她在那头。他最满意的是两个人的合影,他板寸头,穿着一件夹克,能看见白色的衣领,嘴巴上扬弯成一道笑脸。她穿着一件红色上衣,黑色的打底衫包裹住她的白嫩脖子,露出洁白的牙齿,粲然一笑。他敢断定,那是他们这辈子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笑得那么迷人,现实中,他很少看她如此灿烂地笑过,像是画上去的。陈建军看着红本子,他的内心就暖烘烘的,甚至还会傻呵呵笑上一阵。每当这个时候,做着家务的戴裴就会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问,老陈,你笑啥呢?陈建军止不住笑,边笑边说,笑我自己。戴裴就冲他吐吐舌头,忙活去了。
终究有一次,压制在内心的情绪喷薄而出。陈建军的泪滴落在结婚证上,洇湿了一片。
戴裴从他手中夺过了结婚证,轮到她变得沉默不语。她的手指在合影上摩挲,嘴巴嗫嚅着,很多年前,我有过类似的一本证。那话是减速的,就像他驾驶着公交车驶入站点。
他止住了流泪,手掌在脸上擦拭。老陈,你说做人多累啊,还不如做一只猴子。莫名其妙的话语从她嘴角脱口而出。老陈,你知道吗?我每次洗衣服都特别卖力……他没等她往下说,抢先说了,我知道,你每次洗衣服都使劲搓,甚至还用刷子,你看,我的每一件衬衫都是白净的。
她笑了,他瞧见她的侧脸,那笑容和红本子上的一模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她淡淡地问。
他摇头。
那是因为,衣服再脏还是可以洗白的,可是人……她顿了顿,没有接着往下说,有些怅然地转弯,老陈,你抱抱我,可以吗?
陈建军毫不犹豫地上前一步,用他粗犷憨实的双手紧紧抱住她。她的泪珠打到了他的手掌上。要是有个雨刮器就好了。
一念之间
那段噩梦的开端始于一个娱乐会所。那天的光特别暧昧。环绕房间里扫射的光映在那些红润的脸盘上,烟雾和光雾纵横交错在一块,钩织成一道暧昧的网。她在那个会所上班,号称“公主”,其实就是陪酒的女人。
她坐在榻榻米上有些难为情。他点了她,却把她冷落一旁,一个人背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进到房间里,他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她木讷地站着。他没有往下说,从桌面上拾起一罐啤酒,一饮而尽。她想,他一定不是来找乐子的。可是一个不爱找乐子的男人跑到这地方来,是不是有些不大对劲?
她尝试着主动一些,好歹人家是付了钱来消费的。她拉着他的手要去点歌,他说,我五音不全,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陪你去点,但我不会唱。她说,我可以教你。他却还是说,我坐着看你们唱吧。她差点来了气,嘟着嘴,有些不悦,一小口一小口喝着闷酒,他却坐在一旁,像足了一个正在打坐的和尚。
她再看他,提议,我们玩骰子吧。没想到他点了点头,两个人挤在玻璃桌前。看来是慢热型。
三个六。
四个六。
两个人尽情吆喝着。可不知谁关闭了音乐,屋子里瞬间冷却下来。
那个,我有事,你们玩。他突然起身,那些和他一起来的男人们扬起手指,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他起身离开,还拍了下她的肩膀,她抬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颇有精气神的双眼。那个,你要不要陪我走走?他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
她坐着他驾驶的汽车暂时离开了喧闹的地方。他一路开着,两个人没有说话,而后他们去了江边,吹着风,话仍旧少。温顺的风跑到她的脸颊,她有种想恋爱的感觉。她有些异想天开,如果他向她求婚,她肯定会答应。
还是这里舒服,那儿,太闷了。他双手搀扶着江边的铁栏杆,终于开口说话。她不知如何往下接,不过是相处了一个多小时的陌生人,她还不知道他的名字。这跟以往的情况不太一样,从前遇见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话痨,说个不停,说如何赚了大钱,说她如何漂亮。她正思忖着如何接他的话,他却说,我送你回去吧。
故事似乎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往下发展的可能。他把她送到门口,她住9楼。她犹豫着要不要招呼他到屋里坐坐,他转身就要离开,离开时说了句,谢谢。她有些诧异,望着他离去的身影。
她回到房间,莫名其妙地产生喜欢的感觉。有些徘徊。在那么一个逢场做戏的场合,多半不真实。关上门那刻,她感觉自己失去了和他交往的机会。
她赤身裸体地枕着床沿坐在地上。很多个闷热的夜晚,醉醺醺的她就那样坐到天亮。只是那晚,她格外清醒。
她没想到几个月后,还能在会所再次看见他。他在一个包厢,一个人,放着歌,只点了她一个人。
关于接下来的约会以及结婚,姐妹们嘲讽她说,你在鸡窝里变成了凤凰。她不语。她们的人生就犹如游乐场里的过山车,摇摆不定,起伏上下,都操纵在别人手中。表面是镇定的,内心却荡起了一丝涟漪。
他好像不太介意她在风月场上过班,结婚后,话还是那么少。那段时间他们各忙各的,直到故事偏离了之前的轨道。
那晚的事仿佛是个支点,支离开了正常的情节。他有些古怪,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很久,从卫生间出来后,人变得亢奋。她从他的手提包里找出了锡箔纸和一包晶莹剔透的东西,她才知道,他一直都在伪装着。他把东西甩到玻璃桌上,同时甩下一句话,来呀,来嗨。她强忍着泪珠,没想到她自作聪明地逃离,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摁住她的脑袋,让她吸,那玩意儿通过鼻孔进入体内,她全身抽搐,大脑充血,有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那晚有人报警,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门踢开。
她瘫坐在客厅的布艺沙发上,那棕色的布皱巴巴的。两眼无神,深邃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个警察晃了她一下,你家的打靶鬼呢?他是在追问男人的下落。她不答,就像具被剥离了灵魂的躯壳。等她清醒的时候,警察把她送往戒毒所。
“我要逃,逃得越远越好。”戴裴总是这样呢喃。
最终,她误打误撞上了陈建军跑的6号公交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