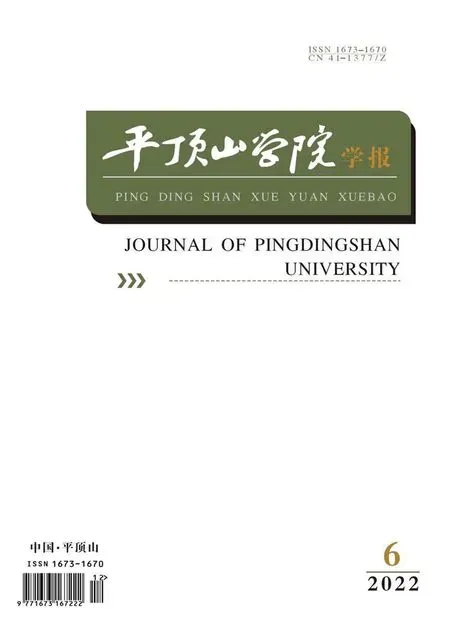论范皕诲《吕氏春秋书后》的贡献
何晓霖,王启才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范祎(1866—1939),字子美,号皕诲,江苏苏州人,民国著名书报编辑人。《吕氏春秋书后》是他的一篇学术随笔,发表于1912年,学术价值高,以往研究者鲜少关注,且尚未有专文探讨;然其在《吕氏春秋》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爰就此略陈管见。
一、《吕氏春秋书后》的价值
1912年第2卷第4期《进步》月刊所载的《吕氏春秋书后》是《皕诲堂随笔》系列中的一篇,共计1 074字。《皕诲堂随笔》(后更名为《老学究语》)仅见于1911—1913年的《进步》月刊,共64篇,为范皕诲在该刊上的专栏随笔,主要内容包括文史哲札记、诗词及其学术观点等,篇幅不长。“书后”是范皕诲常写的文体,在其著述《古欢夕简》中也存有多篇。《古欢夕简序》云:“余45岁(1911年)后迄66岁(1932年),二十余年中夜读之所记。”[1]1可见《吕氏春秋书后》亦属此间精心之作。
《吕氏春秋》是战国秦汉之际的重要典籍,然有汉以降,历代学者对它重视不够,以致吕书研究成为先秦诸子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直到明清易代之际,诸子学兴起,《吕氏春秋》才成为士人研习的对象[2]1。清代中期,《吕氏春秋》研究开始进入“全面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如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等[3]。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思潮的盛行,报业在中国逐渐兴起。民国时期,更是出现了如《国学丛刊》《中法大学月刊》等大量探讨学术为主的报刊。报刊媒体的出现,使民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进而引发了《吕氏春秋》研究的热潮。民国初期,学者们延续传统朴学的治学方法,致力于吕书的校释、整理工作,进一步勘正了高诱注、毕沅校本之讹。这些工作为后世出现更为系统的校释著作奠定了基础,但关于吕书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存在明显不足。范皕诲《吕氏春秋书后》一文,发前人未发之覆,打破了民国初年朴学一统的局面,为吕书的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从近代《吕氏春秋》研究史来看,范文的出现,其创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发掘《吕氏春秋》的文学性
范皕诲对《吕氏春秋》的文学成就评价颇高,认为吕书在周秦诸子中占有“一席之位置”[4]5。他说:
《吕氏春秋》之文字奥衍而精湛,平实而流转,且包蕴宏深,至理名言络绎不绝。良由不韦门客汇集当日所传文章学术之菁华,以捃为此书。虽与《孟》《荀》《庄》《列》之自标心得、自铸伟词者不同,而亦可谓论家之渊薮矣。[4]5
范皕诲将吕书的风格概括为奥衍宏深而平易近人。一方面,在中国思想史上,《吕氏春秋》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它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蕴含着丰富、独特的哲学思想,因而具有精深的特点。同时,吕书作为治国纲领,其著述目的是“通鉴以资治”,为使道理深入人心,所以总体上文风平实自然,不事雕琢[5]64。与早期诸子的争鸣不同,吕书能够搁置众家思想的分歧,海纳百川,融会贯通,所以圭角不是很突出。另一方面,从散文史的角度看,范皕诲认为《吕氏春秋》是“论家之渊薮”[4]5。就论说方式而言,相较于《孟》《荀》多用比喻论证,《庄》《韩》常以寓言说理,《吕氏春秋》呈现出更为纷繁的样貌。多譬善喻,寓言故事频出,修辞繁复,类比推理层出不穷。表现手法之多样,论说艺术之高超,足以使其成为说理文之渊薮[5]64。从文体的发展变化看,战国时期的文章也由《论语》《孟子》的语录体、对话体发展为《庄》《荀》《韩非》等论说体散文。其后的《吕氏春秋》虽与早期“自标心得”的诸子散文不同,然其纲举目张、自成体系,为后世论说文开创了新的体式。故田凤台称其“殿先秦诸子之后,启两汉政论之先”[6]45。此外,吕书在论说时,往往采用事实互见、例证群等手段化繁为简;又能将短小的寓言作为论据嵌入文本,通过有限的篇幅传达丰富的意蕴。因此,曾号称“一字千金”,不可易也;范皕诲亦以为吕书文约义丰,能“变空疏而归之于精实”[4]7,可见其语言之精练程度。
(二)勾勒《吕氏春秋》在汉代的传播盛况
范文第二部分简要梳理了《吕氏春秋》在汉代的传播概况:
《吕氏春秋》在汉世甚为显著。史公既屡称之,与圣贤发奋之所为作同列;而枚乘、刘向之属莫不引用其文;刘安至慕其事而成《淮南子》;东汉高诱则谓为“大出诸子之右”。[4]7
汉代是吕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两汉以来,在反秦风气的影响下,《吕氏春秋》引起了广泛重视[2]1。西汉时期,多数学者对《吕氏春秋》都有所继承,他们对吕不韦及吕书的评价、关注较前代有明显的改变。
首先,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吕氏春秋》大力肯定,将吕书与《诗经》《周易》《春秋》《离骚》等典籍并举,认为都是圣贤的“发愤之作”,使其思想得以流传于世。他还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对吕氏的生平事迹及《吕氏春秋》的成书作了详细的交代。司马迁对吕书的正面评价扭转了世人对吕不韦的偏见,为《吕氏春秋》的传播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其次,吕书的内容常见于其他文学作品中,如枚乘在《七发》中,沿用了吕书对嗜欲之危的说明;刘向的《说苑》《新序》中很多事例和思想都本于吕书;《淮南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都有吕书寓言的影子,足见其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之著。再次,西汉早中期,刘安效仿《吕氏春秋》,编纂了《淮南子》一书,对吕书的结构体系、思想内容等方面也做了全面吸收。沈延国认为,《淮南子·时则训》是汉儒据《吕览》删合而成[7];牟钟鉴则指出,《时则训》是由“十二纪”之纪首篇归拢、补缀而成[8]166。后世学者亦多赞同此观点。从思想内容看,《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淮南子》中有些篇目是直接继承吕书而来;其天人体系、天人关系等也是对吕书“法天地”思想的完善与补充[9]。可以说,从西汉初的陆贾、贾谊、枚乘,到刘安、董仲舒、司马迁,再至西汉末的刘向,都受到《吕氏春秋》的影响,有的模仿其体例加以改造,有的吸纳其思想加以发挥,有的则直接征引了书中的内容,对吕书的接受贯穿始终[10]53。东汉以后,学者们对《吕氏春秋》的关注有所减少,但也并未沉寂。汉末,高诱给《吕氏春秋》全面作注,为后人学习、研究吕书提供了重要版本。同时,他还在序文中对吕书予以高度评价,称其“大出诸子之右”[11]9。这一观点纠正了《汉志》以来将《吕氏春秋》视作杂拼、杂凑的偏见,充分肯定了它在先秦诸子中的价值。总的来说,范文较早关注到两汉时期在吕书传播中的重要地位,并作出相对完整的概述,开启了后世《吕氏春秋》接受研究的先河。
(三)力证《吕氏春秋》为儒家主旨
范皕诲提出《吕氏春秋》当属于儒家,他说:
《吕氏春秋》之著者大都为儒家,故《吕氏春秋》者儒家言也……《汉书·艺文志》以《吕氏春秋》为杂家,岂以间引庄墨而杂之耶?殆亦因吕不韦之故,摈之于儒家耳。
余考《史记·秦始皇本纪》言不韦为相,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李斯者荀卿之徒,乃为舍人于吕氏以掌宾客,明不韦之好儒,而其他宾客固亦李斯之俦,一也。秦并天下之计,儒家大一统主义正与相合。不韦乘此时机而招致宾客游士,以定并天下之事业,惟儒家最为适宜,二也。其后李斯竟成不韦之志,故《李斯列传》云:“(斯)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然则并天下者,不韦始之,李斯竟之,渊源不二,三也。秦始皇幼习于不韦,闻儒家之义最熟,故不韦既以罪死,卒用李斯。而焚书坑士之举,出于荀卿之《非十二子》,亦为之而无所疑难,四也。不韦既近儒,故史于《吕不韦列传》赞曰:“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夫以今人之意,则不韦者,自其前言之,一富贾耳;自其后言之,则大奸匿也。而史公乃独取孔子语,以闻者属之,依《论语》子张之问,则闻与达固皆士也。且不曰吕不韦而曰吕子,良史下语,岂如是之不精当乎?五也。高诱注《吕氏春秋序》,有“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云云,则所集者为儒书尤有明据,六也。有此六证《吕氏春秋》之为儒家可无疑矣。[4]5-7
如上所述,范文提出由吕书著者来判断其学派归属,但具体论据与其观点有一定偏差。前三点中范皕诲主要以吕不韦的个人思想、政治目的及其与李斯的关系为依据,论证儒家主旨说。首先,据《史记》所载,李斯为吕不韦门下的宾客,深得其信任。但在政治上,吕不韦反对秦国实行的法家政策,引进了大批儒士;李斯作为荀子的学生,又在吕氏门下掌管宾客,可见其知晓吕不韦好儒,且顺从了他的意志。其次,吕不韦大权在握时,秦一统天下已成必然之势。作为政治家的他敏感地察觉到“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12]377,因此他组织宾客撰写《吕氏春秋》,力图“把自己在秦国实行的政策理论化”[12]3,作为统一后秦国的治国纲领。与此同时,秦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治国上,秦始皇采用了自孝公以来处于独尊地位的法家主张,实施严刑峻法;但吕不韦认识到,法家过于严苛,并非长久的治国之策。于是,他在《吕氏春秋》中建构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主、融汇其他诸子学说的思想体系,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企图给始皇以理论上的指导[13]83。尽管后来吕氏被免相赐死,《吕氏春秋》的政治措施也未能在秦国推行,但“并天下”的目标最终在其身后实现,并由李斯见证了这一伟业。
范皕诲还认为李斯提议“焚书坑儒”是受到荀子《非十二子》思想的影响。《非十二子》前半部分对先秦诸子学派及代表人物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称其“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14]79,是扰乱天下的邪说;后半部分主要阐述了荀子的政治理想,其出发点是基于能否为现实政治所用,是否“合乎礼法”。荀子身处“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乱世,却又渴望“四海之内若一家”;因此,他以“礼”作为衡量标准,以期通过匡正诸子之说来重新回到一个思想高度统一的社会[14]89-90。尽管荀子以儒家思想谋求用世的尝试失败了,但他援法入儒,吸收法家学说来补充儒家思想。他的两位弟子韩非、李斯也都成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并引导秦国完成了统一的伟业。由此可见,追求思想统一是秦汉文化的基本特征[13]87。从荀子的《非十二子》、《吕氏春秋》的“齐万不同”[12]502,到李斯的“焚书坑儒”,再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不反映了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模式。此外,范文还结合高诱序,指出《吕氏春秋》参考了儒家典籍:一方面,吕书尽可能吸收了儒家思想,以至文中到处可见儒家之说;另一方面,吕书又以儒家思想丰富和改造诸子学说,将百家之言融于一体[13]85。
尽管范文也存在不足之处,但其价值依然不可否认。首先,范皕诲对《吕氏春秋》的学派归属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使其成为吕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民国以前,学者们主要围绕吕书的思想内容展开探讨,如元陈澔在《礼记集说》中提出《吕氏春秋》是当时“儒生学士有志者所为,犹能仿佛古制”[11]1854,带有儒家色彩,并对其所言之礼产生兴趣;明方孝孺称其“论德皆本黄老”[11]1855;《四库全书总目》评曰“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11]1857,对其主导思想有一定的辨析。但总体上来说,该时期是在论述吕书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对学派问题有所涉及,尚未形成独立、专门的研究。可以说,范皕诲是较早、较明确地讨论吕书学派归属问题的学者。其次,范文突破了《汉志》以来的“杂家说”。自班固《汉志》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历代目录学著作多将其归于杂家之学,如《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乃至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等,“杂家说”在民国以前占据统治地位。《汉志》将杂家描述成“兼儒、墨,合名、法”,其特点是有益于王治[16]。但《汉志》对学术流派的划分,主要体现了刘向父子的学术观念[17]。因此,深入探析《吕氏春秋》的学派归属,不能仅以目录学书籍为据。
从儒家主旨说来看,范皕诲认为吕书的学派归属与著者有紧密的联系。此说在民初的吕书研究中属于新见。与《汉志》采取的分类方法不同,范皕诲以吕书著者所属的学派对其进行分类。前者是以思想特征为标准,而后者则是从书籍编纂的角度出发,这种新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程苏东曾指出吕书中存在着大量对先秦文本的截取与借用,于是他将吕书的实际编纂者定义为“钞者”,钞者在文本的生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至于《吕氏春秋》的“钞者”是否大多属于儒家,范文推论应该如此。再次,范皕诲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吕氏春秋》的儒家主旨说,包括吕不韦的思想倾向、吕书的材料来源等,这些都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探讨《吕氏春秋》的命名与结构
关于吕书的命名,讨论最多的两个问题是:“春秋”及《吕览》之名的由来。这在范文中都有涉及。一是“春秋”。范皕诲提出十二纪与《序意》合起来即所谓的《吕氏春秋》。吕书“以时令为首篇”[4]7,故名“春秋”。正如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所云:“春秋二字,乃错举四时之名,足该一岁终始。故古之按年月四时以纪事者,谓之《春秋》。”[19]266“春秋”之名与“十二纪”密切相关。“月纪为首”说也是《吕氏春秋》命名最常见的说法,从郑玄、孔颖达一直到清毕沅,诸多学者均认可此说。“十二纪”为吕书之首,也是全书的纲领,地位最为重要,它按照四季十二月阐明天子的行事制令,故名[20]。二是《吕览》。范文称《吕览》出自司马迁的“世传吕览”说,指吕书的八览部分。《吕览》之名源于《史记》自是无疑,但历代学者大多认为它是称代全书,而非专指八览。由此可见,范皕诲并未从整书的角度阐释《吕氏春秋》和《吕览》两个名称,而是强调它们分别与吕书的两部分有关,这一观点与其对吕书结构的认识相吻合。
在《吕氏春秋》的结构问题上,范皕诲以各部分的完成时间为依据,提出十二纪、八览、六论应作三个部分看待。第一部分是“十二纪”和《序意》。《序意篇》云“维秦八年,岁在涒滩”[12]290,可见“十二纪”当成于秦始皇八年,时吕不韦尚在朝为相。第二部分是“八览”。范皕诲认为尽管“八览”出自“世传吕览”说,却并非吕氏迁蜀后所作。据《吕不韦列传》所载,秦始皇十年吕不韦被免相,前往河南封地;十二年吕氏闻迁蜀之旨饮鸩而死。据此可知,吕不韦实际上并未迁蜀,“吕览之成乃在免相就国之后”[4]7。所以司马迁称吕氏被免后,其门客并未散去;他继续组织门客著书也是寻常之事。总之,范皕诲发现司马迁对《吕氏春秋》的成书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记载,并将此与《序意篇》相互参照,推断出十二纪、八览是分两次完成,因而属于两个部分。
二、《吕氏春秋书后》对后世的影响
范文发表时间较早,它拓宽了《吕氏春秋》文献研究的范围,在清末民初的吕书研究中独树一帜。析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引起对《吕氏春秋》学派归属和思想倾向的探讨。自《汉志》将《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以来,历代学者多视其为杂家;而范皕诲则对《汉志》的归类提出异议,认为刘向也存在“以其人而卑其书”[6]383的偏见,因而有必要对该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施天侔在《〈吕氏春秋〉非杂家乃黄老学派之首要作品辨》中提出吕书当属于道家,《汉志》杂家说是不合理的。他说“凡能自树立为一家之学者,莫不有其一贯之义,或说是系统的思想”[21],认为“杂”是杂凑之义,意味着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故不能自成一派。《吕氏春秋》显然是杂取各家而“自具系统”之作,不属于杂家。接着,施天侔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道家”与《汉志》的“杂家”相比较,指出司马氏所谓的“道家”蕴含的思想更丰富,是融汇了儒墨名法阴阳五家的学说,所以吕书属于“道家”之作。由此可见,范文之后,民国学者对《吕氏春秋》学派归属的认识逐渐突破了《汉志》的限制,开始从杂家的分类标准、吕书的思想体系等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此外,范皕诲以后,多数学者也都认可《吕氏春秋》蕴含着儒家思想。如姜康德在《论〈吕览·夏〉为儒家学术》中提出,《吕氏春秋·夏纪》所蕴含的“长养之气”,正是儒家尊学、崇礼和爱人思想的体现[22]。郭沫若则认为吕书是折中了道家与儒家的学说[23]655。这些都反映了范皕诲识见之敏锐,推动以上问题成为民国《吕氏春秋》研究中备受瞩目的热点。
第二,开启《吕氏春秋》成书研究的思路。范文主要依据《序意篇》和《史记》所载,推断“十二纪”“八览”的完成时间及过程。如上所述,范皕诲认为“十二纪”和“八览”是分两次完成,前者成于秦始皇八年,后者则成于秦始皇十年至十二年间。范氏的“分次成书”说为王利器所沿袭。王利器还在《“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说》一文中,肯定了“十二纪”成于始皇八年之说,同时也认为“不韦迁蜀”并非实指,但对“八览”的写定时间持有不同观点。王利器提出“十二纪”和“八览”语言风格有明显的差异:前者文辞约艳,“体具而言微”;后者则对秦国君主时有讥讽,无所忌惮,二者显然不是同时完成。他推测“十二纪”为吕不韦主持编纂,“其自度稍侵恐诛之心”,因而逾越之词尚不多见;而“八览”则成于吕氏身后,是门人悯其遭遇而续之作,故常含规讽之旨[24]。其后,郭沫若认为《吕氏春秋》整部书成于“秦八年”,他结合金文记载说明“秦八年”即秦始皇八年,而吕书的草创时间大概是在秦六年或七年[23]653。总体来说,民国报刊中关于《吕氏春秋》成书时间及过程的研究,其思路大致上是承范文而来,再从文风、历法等角度寻找新的突破。
第三,肯定了吕不韦及其宾客的编纂行为。在儒家主旨说部分,范皕诲多次强调了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编纂中的作用。范文以后,关于组织者吕不韦的研究渐成重点问题之一。首先,民国后期,报刊中开始出现对吕氏的正面评价。李泰棻在《吕不韦及〈吕氏春秋〉考》中提到,吕不韦虽是富商出身,但其才学足以媲美苏秦、张仪及战国四君子[25]。郭沫若更称其是“一位有数的大政治家”[23]650,充分肯定了吕不韦的历史贡献,彻底扭转了对吕氏否定性评价的倾向。其次,范皕诲之后,更多学者以《史记》为依据,对吕不韦与吕书编纂的关系加以探讨。施天侔提出司马迁对《吕氏春秋》的著者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据《吕不韦列传》所载,吕书是吕不韦使其宾客所著;二是《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吕不韦“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15]648而成《吕氏春秋》,说明吕氏即为吕书之著者;三是《报任少卿书》的“不韦迁蜀,世传吕览”[26]324之说,与范文的观点相同,施天侔也认为吕不韦并未迁至蜀地,所以排除了这一点。此外,范皕诲提出李斯、秦始皇和吕不韦有特别的关系,后世学者多认同其观点,如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代政治》中说:“李斯颇为吕不韦所重用,在《吕氏春秋》的撰辑上他一定是尽了力的。”[23]662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也提到“不韦对于始皇之性之情及行为,亦必多所不满,故书中,常似有讥始皇之语”[27]7,认为吕书“必深触始皇之忌”[27]8。
第四,重视《吕氏春秋》与其他典籍的关系,扩大了研究范围。作为一部汇集群言之作,《吕氏春秋》具有颇高的文献价值,它与先秦其他典籍的关系也为历代学者所重视。范皕诲以高诱序为依据,指出《吕氏春秋》参考了儒书,这一观点为其后学者所认可。尽管负责编纂吕书的宾客可考者甚少,编纂时所凭借之书已多散佚,但仍能就此展开研究。缪钺在《〈吕氏春秋〉撰著考》中说:“《吕氏春秋》中论述事理,颇引《诗》《书》,亦足证撰著者多儒家之徒。”[27]8他从吕书的内容出发,探析其与所征引之书的联系,弥补了范说之阙。范皕诲以后,更多学者开始发掘《吕氏春秋》在先秦诸子研究中的价值,如梁启超《〈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王叔岷《〈吕氏春秋〉与〈庄子〉》等,这些文章大多是以吕书解诸子,主要阐述其他诸子中的问题。可见,民国学者关注到《吕氏春秋》的材料来源及其与其他典籍的关系,但研究尚显薄弱。当然,上述问题至今仍是吕书研究需努力的方向。
三、《吕氏春秋书后》的不足
从《吕氏春秋》研究史看,范文是清末民初吕书文献学研究的转型之作。一方面,该文突破了清代以来朴学研究的局限性,开始从对吕书文本的整理、校释转向对其成书情况、结构体系等学术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该文结构完整、要旨清晰,且涉及范围较广,新见迭出,是民初少有的、颇具学术价值的随笔。
然而,白璧微瑕,范文也有不足,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方法较为传统。如上所述,范皕诲采用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知人论世”的方法,过分关注《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关系,忽视了吕书实际编纂者的作用。另外,范皕诲仍把《吕氏春秋》当作思想个案来研究,未将其置于先秦、秦汉学术系统或诸子学术的演进史中加以考察,进而明确吕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第二,随笔主要论述了吕书文献学方面的相关问题,对文本内容、文学价值等涉及较少,这也是民国《吕氏春秋》研究中的普遍现象。第三,部分观点主观性较强。如在儒家主旨说部分,范皕诲认为孔子与司马迁均对吕不韦持正面评价。《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15]3050范皕诲提出“闻”字并非前人所注的贬义,而是赞美之词。这一观点系其误解。首先,裴骃征引了两则文献注释此句。除子张之问外,裴氏还引用了马融之评“此言佞人也”[15]3051,显然他以为此处的“闻”当作贬义。其次,《论语·颜渊》篇中孔子阐述的“闻”与“达”是相对的概念。孔子认为,“闻”是“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28]146,即博取虚名之义;而“达”才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28]146,是真正实干之才。因此,子张之问中“闻”当是贬义。其次,司马迁认为吕不韦著书是为了与战国四公子比肩,出于个人荣辱而作。此外,受随笔文体的影响,范皕诲以推理代替论证,使文章略显单薄,缺乏很强的说服力。
总体来说,范皕诲的《吕氏春秋书后》依然是民国吕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该文较早地关注到《吕氏春秋》的文学性、传播状况、学派归属,以及命名和结构等相关学术问题,并提出了诸多新见,推动了吕书研究方法的转型,对近现代吕书的文献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吕氏春秋》的研究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