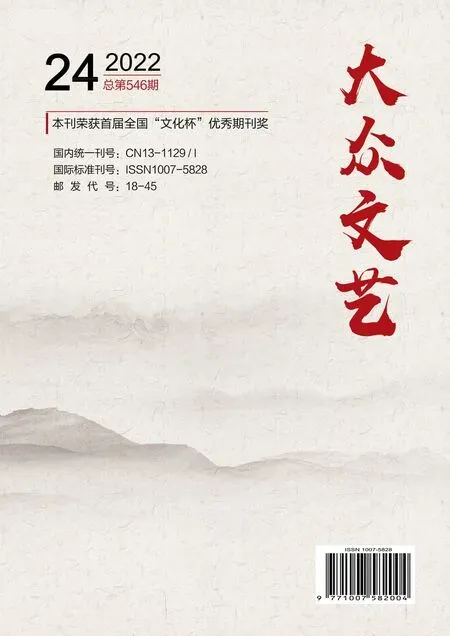知觉现象学:舞蹈道具的“虚”与“虚”之间
郭祺琦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北京 100081)
舞蹈道具在舞蹈界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多数研究者从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学角度出发,分析道具在舞蹈中的功能,探讨其与生活道具的关系,或者结合舞蹈创作、舞蹈教育、民间舞蹈个案进行讨论。此时,舞蹈道具是一个自在存在的物体,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笔者的思维原点则与此相反。几年前笔者在完成编舞作业时,舞伴说过这样一句话:“咱们也选一个道具吧,你看其他组都有道具。”事实上那次编舞作业并没有规定是否使用道具,不过舞伴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舞蹈道具的使用能够作为身体的延伸,增强表现力。如果作品有着明确的意象或情节,这道具又能在其中发挥不小的推动作用。可是这作用是建立在舞蹈编创之前的构思,还是编创过程中的顺势挖掘?但笔者认为,总归是不能为了道具而徒增道具的。
如果拿掉舞蹈中的道具,仍旧能够给人一种与有道具的同样效果的认知,那么这道具是否还有必要?其中,使用和不使用的差异是何种形式的,何种程度的?虚拟道具究竟算不算道具?道具与人的关系是什么?本文探讨的对象即为舞蹈创作中的虚拟道具。
一、虚拟道具的辨析
分析虚拟道具首先应解决的是“道具是否必要”的问题,这就不得不到道具的源流、真实与虚假的反思、实物道具与虚拟道具的比较中考量。
(一)道具的源流
“关于舞蹈道具最早的记录为《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葛天氏之乐》操牛尾而舞的场面。……道具有着不同的来源,它主要体现在自娱、娱人、祭祀、生产、生活、战争方面,也有的舞蹈道具是创造的结果。”另有说法为,在早期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劳动工具的催生对于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正因为此,劳动工具作为初民崇拜之物,被运用到了舞蹈中,作为早期舞蹈道具的重要根源。”可见,舞蹈道具的使用最初与经济生产、信仰崇拜有关。无论是舞者舞蹈时随手操起生活日常用具,还是将信仰和希望寄托于某物,此时这一物体无疑有着超出本体的深厚的意涵,人们真切地相信这道具本身具有某种神力。此时舞蹈道具的重要性往往高于身体表现。
随着舞蹈剧场形式的出现,道具的形制更加精美,但这精美更是为了博人眼球,增强舞蹈的艺术效果。此时,道具的重要性较原初情况有所流失,即使一些道具仍因寓意性、象征性、表意性、戏剧性、技艺性得到格外关注,道具的神秘地位也已然降居至作为文化或意象的思想桥梁,只是在舞蹈场景中唤起人们的某种意识,从而使舞蹈的思想获得更大的张力而已。然而,尽管舞台舞蹈中道具的神圣性遭到抑制,身体中迸发出的虚幻之力也仍旧使人感动。故,尤其道具本身不具有规训下的丰富的文化所指时,将道具虚拟化,同时将身体与虚拟道具的巧妙配合作为一种舞蹈创作思路,本身是可行的。
(二)真与假
物体是否真实地存在着,是否在现实世界占据一定的空间,有某种性质作为它客观实在的依托,或与时间发生着或明显或隐晦的变化,是显然易见的。但是所谓真实物体的性质如何界定?固体、液体、气体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光影构成的舞蹈影像是真实的吗?舞者的肉体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上的,那么影像中舞者的就是假的吗?为什么即使是假的舞者仍旧能够带给我们强烈的精神碰撞?我们的身体知觉和内心波动是那么真实,它随舞者的身体、情绪而牵引。此时,真与假的界限被无限模糊,真与假的视角的价值也由此跃出,由此,关注虚拟道具所带来的全新感受也就不像乍听起来那么荒唐了。如果说这里所谈论的是整体的真或整体的假,笔者提出的虚拟道具的概念所建构的就是真实与虚拟的融合场景。
梅洛·庞蒂曾将梦与知觉单独列出进行分析,以使真与假的辨析落到实处。“古老的争论正是秘密祈求于自在的真,来降低我们知觉的地位,然后胡乱将它们与我们的梦一起扔给我们的‘内在生命’,他这样做仅仅因为一个理由,在时间问题上,我们的梦就曾和知觉一样有说服力——这是忘记了梦的‘假’本身不能扩展到知觉当中,因为这‘假’只是相对于知觉显现,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谈论假的话,我们就应该有关于真的经验。”
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与知觉有所区别。但梦与现实的真实与虚假关系,同舞蹈与现实的关系相似。虚拟道具舞蹈中一些反规则、反常理的结构或逻辑,因为表演性被人们认可,并形成一种奇异的效果。从这层面来看,虚拟道具舞蹈接近于梦的表达。另一方面,从知觉角度来看,虚拟道具虽为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但它真实地出现在人们的知觉中,因此这种知觉又介乎于梦与现实的知觉之间。故,从知觉层面考量,虚拟道具属于一种道具。
(三)虚拟道具与实物道具的区别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一书提出了四种存在方式,为世界存在、事物存在、想象存在、意识存在。舞台舞蹈中演员的肉体是世界存在;或者说他的身体作为一种物质,是事物存在;然而舞蹈时舞者所要传递的情节、情感、内涵,和观众观察时获知的超出舞蹈元素本身和知觉之外的部分,系想象存在;知觉部分则基本可以认为是一种意识存在,这种知觉又可区分为演员对于自己的身体感知,和观众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接收到的演员的身体信息。无疑这里的划分是非常表面的,但将道具的状态与这四种存在方式相对照,则可以获得更多认识道具的视角。
虚拟道具和实物道具在舞台舞蹈中的运用均意在锦上添花,无论是遮蔽了运动的人体而成为视像主体的巨型道具,还是人体受其规训却促成一种独特动态风格的限制性道具,也或者玩转于“掌”握之中的灵动的纤巧型道具,三类道具都表现出非凡的技巧性、叙事性、可塑性、象征性。这种方向上的贯彻并没有在虚拟道具中消失,而且因为其虚拟,需要运用更巧妙的编排技巧和演员高超的表现力。演员与观众关于道具的知觉交流也必须依托于表演者的身体动作与情绪的强调、有意识的指引、身体对于道具作用的反应,来唤醒观众记忆中的共鸣。由此使演员在动觉上,观众在知觉上,相信虚拟之物原本不存在的真实性。也只有这样,虚拟道具在舞蹈中的出现才是成功的。
实物道具则因为实物的自在存在,其本身的出现就可以引导观众的思维走向更丰富的所指,便省去了舞者进行身体运动时的部分工作——刻意划分出注意力去加深人们对于虚拟道具的辨识。编导、舞者在塑造实物道具舞蹈作品时,仅需将脑力与创造性诉诸实物道具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虚拟道具舞蹈在此之上又加入了对于道具本身特质的阐明。
不过这并不是说道具的存在没有其价值,而是构想出一种通过身体呈现的方式来质疑道具的必然性。这质疑不是对于道具本身的,它的使用价值和功能依然没有改变。
(四)虚拟道具表达的亮点
前文既然肯定了道具的价值,但为何非要虚拟?或者说这种虚拟的呈现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与实物道具所不同的感受与功效?这就涉及了虚拟道具在表达时的亮点。
1.另一种技巧性
所有人都不会否认许多舞蹈中都有令人拍案叫绝的道具技巧,它们常常出彩于速度、力度、数量、花样、惊险性、稳定能力、精致程度,这种技艺也成为舞蹈表现中的亮点。同时高超技艺的练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并要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掌握其中的门道。当实物道具消失,我们则用自己的表现能力去体现“道具的存在”“道具与身体的配合”“道具在舞蹈中的妙用”。或许会有人发问,没有实物的束缚,是否会降低道具的技巧性,是为训练的懈怠寻找借口?要知道没有真挚的知觉感受,以及相关知觉的极细致的磨炼,是无法达到明确的知觉传递效果的。在没有实物的明确指向时,对于虚拟道具的技巧性表达不仅没有降低标准,反而提出了更高要求。
2.脱离时空的超验表现
得益于虚拟道具的虚拟属性,舞者在“玩转”舞台时不能不说其超脱了时空的限制。在把握了道具的基本属性,比如形状、大小、重力、质感、用途中的一种或几种之后,道具完全可以凭空出现,凭空消失,以及以一种超乎常理的形式、方式出现在舞台上,并表现在它与舞者的关系上。这近似于魔术中的神奇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超验表现仍需建立在可靠经验的主要特质基础上。相应地,超验表达的发挥也只能在舞蹈场景中虚拟道具的次要属性中着力。
3.增强戏剧效果
人物在表现自身与虚拟道具的关系时,舞蹈的写实特征得以显现,戏剧效果随即产生。它未必一定伴随叙事情节,往写实基础上累加写意的效应亦未尝不可。但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里所述的戏剧效果是运用虚拟道具时浑然天成的,自然而然地带来的知觉体验。它与实物道具的直接表达,以及实物道具的隐喻串联起舞蹈线索的情况,有所区别。
二、舞者与观众分别对虚拟道具的感知
其实不论舞者还是观众,他们作为知觉传播链上的关键节点,在有意识地调动知觉时,都应该去除知觉以外的框架去表现或者感受。也只有提前剥掉附着于身体的世界、社会、政治、消费、媒介等成分,以纯粹的知觉铺就身体交流之基,再充分吸收这些被剥离掉的成分,知觉传播链、舞蹈作品本身、虚拟道具舞蹈的运用才是切实可行的。
(一)舞者的身体与虚拟道具之间的关系
1.身体表现形式
图形在进行知觉传播时,有点状、轮廓、整体、各部分间关系等四种形式,至于具体的判断还需放到舞蹈实践中进行把握。实际上舞蹈的过程也可以看作一个图形在时空中的运动,也即这四种形式在空间中的流动。虚拟道具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在舞蹈中需要着重凸显,虚拟道具在舞蹈中则呈现为点状中一个重要的点、轮廓中的显要部分之一,而各部分关系中与虚拟道具联系越紧密的部分,知觉便越容易显见。梅洛·庞蒂就曾表示知觉并非与所观察物的表现形式、表现形态完全一致,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观者的神经系统被观察物的力量激起的部分。即,“只有当他们的视觉式样向我们传递出‘具有倾向性的紧张力’或‘运动’时,才能知觉到他们的表现性[1]。”
2.力的同构
而且,这四种形式又涉及了结构问题。“造成表现性的基础是一种力的结构,它不仅对拥有这种结构的客观事物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均有意义……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动起来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性的力,实际上是一种力。”显然阿恩海姆同意梅洛·庞蒂对知觉中的力的看法。“知觉活动在组织和建构视觉式样时,意味着客体的‘倾向性张力’与主体的‘选择性简化’交流,由此而产生‘心物同构’。”我们可以从舞蹈中提炼出内在情感之力、身体外在之力、作品深层的意涵之力,一个理想的舞蹈作品中这三种力是应该协和的,这种相谐亦体现为“同构”。至于虚拟道具与人体融合的力的理想化磁场中,虚拟道具之力、身体之力应如处在弹簧两端一般[2]。
3.身体划分方式
法国舞蹈教师代尔萨尔特对舞蹈身体的划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人体作为一种表现媒介,可以大致分出三个部分:精神区域聚集于头部和颈部,躯干属于精神-情感的区域,臀部和腹部则更多地体现出物质性,胳膊的灵活程度决定了它的精神-情感特性,比之灵活程度次一些的腿部就更显物质性。以此类推,身体的每一区域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划分。梅洛·庞蒂的看法则力图去除刻板化:“人体各部分的感官和分布在人体不同的位置上的其他生理机制的行为也都有不同的复杂性水平的说法。”并且,他还提出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从属于一个活动中心,由此将打碎的肢体重新凝合。虚拟道具在舞蹈中必然与肢体末梢接触更多,而较少体现在头颈、躯干上。但是虚拟道具使得肢体末梢主要用于知觉传递、文化信息传达,或者在此基础之上的附加。前文所提到的身体的精神性与情感性,则需要编导和演员从现实生活中借鉴,并投入更多的编创思维。另外,虚拟道具与身体的关系有接触型、非接触型两种,不过非接触的情况也多是将虚拟道具的接触延伸至更远的空间,它必然与人体发生连续的关系,为一种“不接触的接触”。
4.身体的张力与边界
舞者表演时,“具有动力性质的身体形象具有十分不明确的界限……它周围没有任何别的物体,也就没有一个能把它从中分离出来的基度。”然而,若将虚拟道具放到舞蹈表现中,局面就会发生扭转。为了更好地使不存在的虚拟道具呈现“具象”的效果,虚拟道具所在的位置也不得不表现为一种现实的边界,以此在边界上赋予更丰富的想象的意指。
虚拟道具属于舞蹈的一部分,与身体紧密关联,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区别于身体,它在尽量地抽离出身体,舞者也在尽量使其抽离出自身,只是虚拟道具本身不存在,抽离的努力始终是徒劳。而虚拟道具舞蹈所带来的异于其他形式的知觉的冲击,恰恰就在于努力的徒劳。
(二)观众的身体与虚拟道具之间的关系
1.完形
观众观舞时,身体图式会指引观众的视觉将虚拟道具的不存在转化为完形的存在。并且舞者的身体与观众的知觉联系是通过其本质。艺术接受活动本身就是在幻觉的能力互相不能分离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些条件为虚拟道具出现在舞蹈中提供了可行性。此时舞台之上舞者的身体处于一种处境的空间性中,并超然于时间之外。观众调动知觉联动,将自己的身体与舞者的身体——两个原本并无可能实现联通的个体——在知觉的交流处达成贯通。
2.经验与知觉的争议
持传统经验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只有当所见之物能够与人记忆中的知识与情感产生关联时,对物体的知觉才得以生成。与此同时,记忆中的知识与情感也被注入了所知觉的物体。因此才有了这样的说法。“在鲜明的知觉和实际动作之间的习惯,外在界定我们的视觉场和我们的活动场的这种基本功能[3]。”相反,以梅洛·庞蒂为首的知觉论者则称,在人的认知记忆被唤起之前,人的视大小和视形状也会变化,感觉、知觉早已产生作用。
他们争论的是何者为先的问题。在虚拟道具舞蹈交流活动中,没有知觉的主动感知与信息接收,活动本身就没有意义。另外,经验的唤醒早在编创之初或过程中,便作为作品的预设,虚拟道具极有可能就是作品主题得以抒发的出口。
(三)知觉的传达
从知觉一致的角度来看。“由于人们的身体、感觉器官、心理机制具有极高的相似性,所以使得不同人的体验也具有极高先在的相似性。”并且,相似的生活经验更促使知觉主体的体验趋于一致;从知觉不一致的角度来看。“在刺激和感觉内容中,应当承认有一种内在的隔阂,这个隔阂比刺激和感觉内容更能确定我们的反射,和我们的知觉在世界,在我们的可能活动区域,在我们的生活范围中所指向的东西。”
知觉的一致性使得知觉交流顺利进行,知觉的不一致性又是基于个体体验的多样性,多样性产生了无限可能。
三、舞蹈《三个老阿佳》中的虚拟道具运用
《三个老阿佳》的第一部分表现了三位藏族老年妇女一同捡牛粪、堆牛粪的情景,三人嬉戏打闹间,藏族同胞独有的生活趣味随之弥漫出来。其中牛粪、背篓就是虚拟道具。其实,在人物登场的同时,服饰、神态已声明人物形象的民族身份、性别、年龄,这些明确特征的经验先于知觉出现。观众的经验和知觉结合,虚拟道具牛粪、背篓得以快速确认。我们必须承认,知觉纯粹抛开经验几乎是个悖论,只是知觉更直接传达的是普遍的生理、心理、情绪、情感。
(一)以动作彰显
1.对动作的知觉
找牛粪的动作首先体现在脚上,90度背手俯身,右脚向正前蹉出,再收回。脚底紧贴地面。可知牛粪黏性不强、形状扁平、阻力适中。此时虚拟道具处于能指清晰,所指模糊的状态。不过在动作的进行过程中,所指逐渐变得清晰。
捡牛粪的动作则占据更多的内容,舞蹈中有三种典型的捡牛粪动作。第一种,面向牛粪的位置,上身前俯,原本背在身后的右手自然下垂顺势从地上捞起,并在空中发生了停顿,这一停顿是牛粪重力的体现。短暂的停顿之后,舞者顺动势将牛粪举至左耳旁,向身后一丢,背篓显现出来[4]。这一系列动作的显要部位在于右臂的运动,越接近右臂运动的身体也越容易受到关注。第二种,为行进型,抛牛粪的位置由耳旁变为头顶,动作显得更轻巧。抛完后身体整体向下沉,挂在背篓的框边的牛粪被颠到筐底。第三种,为侧向行进型,舞者左手提裙以便进行劳动,下身扎大马步。身体以腰腹为圆心摆动,重心在右腿上时,右手捡牛粪,左腿由体侧上抬,当重心倒至左腿时,将牛粪从头部左侧丢进背篓,右腿从体侧上抬。
三种动作幅度越来越夸张。第一种和第二种很接近生活的表达,第三种则作了一些舞台化处理。老阿佳的动作轻车熟路,可见经常性劳动使得人体适应了这种运动。另外,三种捡牛粪的运动方式都充分借助了惯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2.对调度的知觉
《三个老阿佳》中的调度主要为横线、三人绕圈、横排整体转圈,调度不具攻击性,调度中对于虚拟道具的运用呈现出整体一致的特征,给人整齐有序之感,同时人物之间的动作设置又有着微小差异,也更显真实。当然,调度的安排不仅是为了增加真实感,而且是为了烘托劳动生活的闲适,更显出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
(二)以情绪定性
老阿佳拾起牛粪直接凑到鼻子跟前嗅,面部随呼吸紧缩然后放松,露出喜悦的神色满是轻松和舒畅。许多人认为牛粪是臭的,甚至是遭厌恶的,这与老阿佳的动作、神态中的表现大相径庭。看到舞蹈中它被藏族人民当成宝贝,我们对于牛粪的偏见也随之瓦解。回到历史早期,藏族人民刚发现牛粪时,首先的感受自然是它的清香,却还不至于喜悦。只有人们意外发现其可做燃料之用,体验着捡牛粪的平淡生活的快乐时,牛粪被灌输了更多的情感[5]。
(三)以音乐烘托
舞蹈音乐由拖拉机发动声进入,强弱强弱的声音交替,并逐渐加快,然后消失。拖拉机声音浑厚有力,使人注意力集中,却因强弱交替有所缓冲,瞬时的神经紧张得到释放。随后是牛、鹰等动物的叫声,牛叫低沉,有延续性,鹰唳尖锐富有穿透感,小鸟啁啾,灵动紧促。如此,自然生机尽现,舞者身处的环境铺展开来。
结语
本文由“舞蹈中的道具是否必要”这一问题意识切入,引出对虚拟道具的辨析。首先,从真实与虚拟间的模糊界线引出知觉。随后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逐渐聚焦对舞蹈中虚拟道具的知觉认识。
宏观层面,笔者将知觉的分析放到了实物道具和虚拟道具的比较中,以彰显虚拟道具独特的表达。虚拟道具舞蹈对于舞者的表现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虚拟道具超脱了时空的限制,也更显戏剧效果。中观层面,则把虚拟道具带入舞台,在这一场景中知觉的传播体现在舞者的传递、观众的主动和被动的感知,以及不同身体间知觉传递的过程。并从知觉现象学的角度将图案的知觉引申到舞蹈,最终拓展到虚拟道具与身体的知觉关系。其间又涉及知觉表现形式、身体各部位的知觉形式、“同构”与“完形”、知觉与经验的争议、主体间知觉一致与知觉不一致等问题的研究。微观层面,笔者选取了藏族三人舞《三个老阿佳》第一部分进行分析,舞蹈的动作、调度、情绪、音乐设置,都在宣告着它们与虚拟道具牛粪、背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