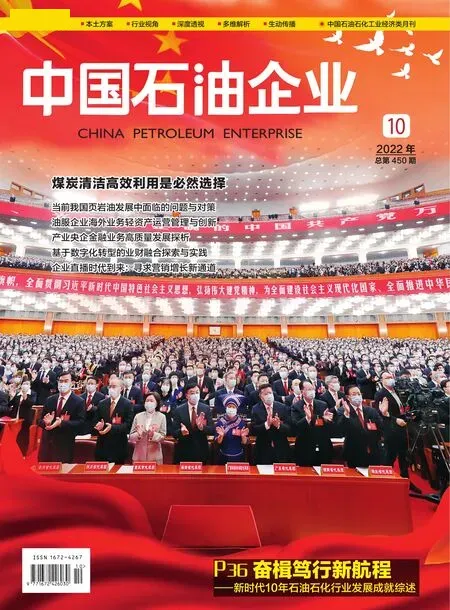“创新是一种乐趣,也是科学家的责任”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机化工专家汪燮卿
□ 文/唐大麟

记者:汪院士您好,我看到您正在电脑上阅读外文资料,是在查找资料吗?
汪燮卿:“双碳”目标里提出今后的石油除了将继续作为燃料使用外,更多地将转化为化工原料,虽然石油作为化工原料从重质油转变成低碳烯烃的生产技术已有将近30年了,但未来仍会有一个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创新的转化过程。所以,我们今年准备出版一本这方面的英文书,我正在组织大家赶稿,你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记者:您提到把重质油转化为低碳烯烃,我了解到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重油制乙烯丙烯,结合我国国情,您觉得我们在重油转化这条道路上还有哪些可以优化的方面?
汪燮卿:从我国资源禀赋来看,重质油偏多,轻质油偏少且不够用,所以国家领导层和权威学者历来重视用重质油生产烯烃,因为它可以缓解轻质油的短缺,提升劣质油利用效率,提高经济附加值。从重质油生产低碳烯烃的开发技术来讲,我们做的比较早,国际上第一套重质油生产低碳烯烃的工业化装置是我国生产的。从石油化工和炼油技术角度来讲,国内第一套出口到国外的成套技术就是低碳烯烃,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至于优化发展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首先应该在原有发展基础上找到新的突破口,这样才能找到下一步优化工作的方向。具体来讲,把重质油转化成低碳烯烃不可能像石脑油一样蒸汽裂解,因为它是一个催化过程,没有催化材料是做不成的。但是在催化过程中,它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无论催化材料的开发还是催化工艺的开发,以及环境保护的要求与成套技术的配套,都应该统筹考虑,这也是目前大家也正在努力的方向。
记者:精细化工正在成为我国石油化工产业主要发展方向,您对此您有何展望?
汪燮卿:精细化工的产品非常多,可以说它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是国民经济发展,还是工业与国防建设,都离不开精细化工产品。如果让我对精细化工的未来发展做展望,那就是“三精”——产品要精雕细刻、工艺要精耕细作,成本要精打细算。例如焦炭,我们现在生产的焦炭很多,污染也很大,但是好的石油焦很缺。不仅我们缺,全世界都缺,所以我们能不能通过精雕细刻、精耕细作、精打细算来生产高附加值的优质焦炭,而不是消耗了资源却没有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我国石油产量突破1 亿吨时,国家曾组织力量研究“如何用好1 亿吨油”;现在我们要把2 亿吨的油气牢牢端在自己碗里,您觉得在新形势下,这2 亿吨油气该如何合理利用?
汪燮卿:虽然现在我国石油产量达到了2亿吨,但仍需大量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这个客观现实我们想努力扭转,石油行业也在下大工夫找油,但是谁也不敢保证结果。当时国家提出研究如何用好1亿吨油,是基于石油可以自给的形势;现在思考如何用好自己的2亿吨油,形势已发生很大改变。这自产的2亿吨也仅仅是我们石油消费量的30%。石油既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资,又是国家的战略物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全面的考虑。我之前没有认真思考过,但觉得深度加工利用肯定是个很重要的方向。因为深加工可以提高石油的经济效益,提升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既要看准技术前沿上的一些问题,更要下工夫去攻克。比如我们刚才谈的重油制烯烃,烯烃下面还可以生产乙烯、丙烯,还有PX,这些都是基本的化工原料。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考虑怎么让劣质的重油尽量多地转化为乙烯、丙烯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最小的碳排放,实现低碳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在新形势下就发展不了,这需要引起大家重视,要在深度加工上有一些和过去所不同的新概念。

图为本刊记者采访汪燮卿院士。
记者:20年前,在由侯祥麟院士负责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报告中,您负责起草了“油气节约使用”“大力发展石油替代产品”等建议措施。从目前我国油气资源发展现状来看,当年提出的一些措施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结合当前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您是否依然主张以上两点建议?有何新的建议?
汪燮卿:“油气节约使用”和“大力发展石油替代产品”这两点,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比如要发展石油替代产品,明确讲就是用清洁能源替代高碳能源,这就需要提高成本投入。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但结果我始终不太满意。以前德国用植物油生产航空煤油,这是清洁燃料,但是它的成本是普通航空煤油的3倍以上,这就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与资金支持。最近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用地沟油生产出来的航空煤油,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适航证书,这种生物航煤是以餐饮废油等动植物油脂为主要原料,与传统石油基航空煤油相比,其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最高可减排50%以上。所以我相信油气节约和能源替代在我国是一定有发展前途的,这两个方向也是不容怀疑的。
目前“双碳”目标的树立,也为以上两点的实施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过去石油工人说“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这个新目标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现在把二氧化碳埋入地底或用它驱油,这肯定是一个方向。但我也经常发散思维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把本来属于破坏环境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利用起来,让它负排放。我们在大西北的这些油田,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是否可以探索在二氧化碳排放时结合一些条件产生化学反应,使其变废为宝。现在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就像我们现在说发明5纳米的芯片一样,但我想如果全世界共同努力,将来这些技术都会实现的。
记者:您刚才描绘的场景,在技术上已经有突破的苗头了吗?

汪燮卿:我还没有看到,这只是我在“鼓吹”。过去这种“鼓吹”会被人说是异想天开,我觉得异想了,天不一定能开,但是不异想,天一定开不了。这句话我不是随便说的,而是有根据的。“文革”期间石油部军管,1972年5月石油部军管会给我们单位来电话要我出差,去长沙马王堆。我那时搞油品化学分析,军管会代表告诉我,石油部计划从四川铺条输气管线到武汉,输气管线肯定会存在腐蚀问题。他在内参上看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女尸保存完好,没有腐蚀,就希望我去把棺液里的成分搞清楚,看是否能应用到油气管道防腐中。我当时一听就觉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但后来再仔细一想,又觉得这个军代表不简单,有想法,也敢想,我很佩服他。所以现在我也鼓励大家要有异想天开的精神,鼓励大家创新,但不能没有科学依据的瞎想。
记者:欧美很多轿车都是柴油发动机,这种车更节油环保,为什么柴油轿车不能在我国大规模推广?
汪燮卿: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国内轿车现在的发动机技术还有待提升,我们现在普通的柴油货车发动机技术掌握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柴油轿车发动机技术难度比柴油货车大多了,所以它需要投入的成本就大,这对于汽车制造企业和消费者而言都是一个大问题。其次因为国内柴油机在排放上与汽油机相比还是有差距。欧洲柴油发动机之所以搞得不错,一是它原来就有基础,柴油英文名“diesel”,就来自于德国工程师狄塞尔,他发明的柴油发动机取代了之前的蒸汽机,这是他们在技术上的基础优势。二是在技能方面,其各种零部件配合后与环保的配合度非常好,高效能低排放。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汽油机能做到,柴油机排放整体还差一些。三是国家政策调控,过去我们说要提高柴汽比,现在要降低柴汽比,把柴油使用量降下来。虽然柴油机功率大,但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要什么事情都做到全面超越恐怕还有困难,所以还需统筹考虑,重点研究。
记者:您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颠沛流离的青少年生活,那段生活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汪燮卿:我觉得那段艰苦岁月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就是遵循自己内心的喜好选择,不人云亦云。那个时候,虽然国家处于战争时期,条件艰苦,但是国家对国民的教育并没有放松,那种启发式的教育使我们每一个人的专长都能够得到发挥,这种教育也让我受益终身。可能现在大家对我们的教育都不是太满意,但我也不悲观。之前我看新闻,有一个偏远地区的女孩考上了北大,但她报志愿的时候没有填大家都追逐的金融、经济等热门专业,而是报了考古,因为她想去敦煌研究古代文物。我觉得她很不简单,突破了常人想要升官发财的传统路径,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我总在想,中国这么大,天地很广阔,如果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把专业分散开来,而不是老挤在一个地方内卷,那么我们的人生机遇都会很多,这样各行各业也就都能做到百花齐放了,那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早日实现。
记者:您在德国待了将近5年时间,您觉得这段留学时光对您日后科研工作的影响是什么?
汪燮卿: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培养了我严谨的科学作风,这5年时间对我科研思想的转变很大。我是1956年去德国留学的,两年后国内就开始“大跃进”。在德国第一年我们都在学习德语,“大跃进”开始后大家都很羡慕在国内的同学,因为“1天等于20年”,所以我们当时总跟德国人说让我们去工厂实习一下就回国吧,德国人就会狠狠地批评我们一顿,说你们来这里主要是学方法的,如果实习一下就回去,那有什么意义。当时国内的基础教育还没有那么严格,所以我们在大学毕业去到德国之后,又从分析化学、微积分开始重新一门门地补课。德国人对那些反应方程式太清楚了,就像我们过去背四书五经一样信手拈来,所以到现在德国都处于全球化工领域顶端位置,这和他们扎实的基础及科学求实的作风密不可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与之相比差距还很大,所以我一直提倡加大对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投入,这个投入不一定会有产出,但关系战略发展。我最近看一个资料,美国用天然气中的甲烷制乙烯和丙烯。看了以后感受很深,他们通过对天然气氧化来实现这个技术,在实验室里已经研究了40年,经历了两代人,到现在都没有工业化。我想我们国家如果干这件事,估计干不到10年就解散了,因为没有利润且前景不明确。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础研究一定要转型,它确实需要付出,有的研究可能立竿见影,很快就有成果,能产生经济效益。有的可能需要非常长时间,但并不是说没有效果这些研究就白做了,我们国家应该加强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战略部署,这样才有希望在全面的国际竞合中立于不败之地。
记者:今年是侯祥麟院士诞辰110 周年,您在清华求学期间就已认识他,侯老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回顾过去,是否还有其他影响您一生的人和事呢?
汪燮卿:我是1951年认识侯老的,那年他回国在清华当教授,而我刚考进清华。在新生迎新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侯老个头不高,穿身红衣服,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但真正接触是在1961年工作以后,1965年我当了研究室副主任,他常对我们几个业务骨干说,你们不仅自己要做好工作,还要帮助周围的人做好工作和研究,8小时是出不了科学家的,应该经常思考。我最敬佩侯老的,还是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能依然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这很不容易。其他对我有较大影响的,我认为是我的中学老师。讲一个故事,那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在我们老家农村买不到白糖和红糖,但是有一种麦芽糖做的糖饼。下课后,我们就花几分钱买一块麦芽糖回教室吃,但这种糖用手掰不开,我们就在桌子上一拍,让它碎成几块,然后大家一起吃。这时候我们的物理老师就会启发我们,你们知道麦芽糖掰不开但可以摔开是什么原理吗?苹果掉下来让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发现一个糖饼定理呢?所以我在中学时通过老师们的启发,在遇到问题时能把学到的知识串联起来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从而可能产生新的思索。这种思维方式的培养,对我日后科学研究思路的打开非常关键,我很庆幸能在思维的孕育期,遇到能启发我灵活思考的老师,这对我一生都很重要。
记者:您曾主持和参与过许多重大化工工艺的研发和生产,回首过去,您觉得自己最骄傲的作品是什么?如果让您总结成功的秘诀,您觉得是什么?

汪燮卿: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就知道了。咱们国家现在会进口含酸原油,因为它便宜,每桶差十几块钱,所以进口含酸原油进行加工可以赚钱。但含酸原油多了以后,会腐蚀设备,所以一个炼厂里面只能进口一部分含酸原油,把它跟普通原油混合稀释以后,可以减少腐蚀性,大部分炼厂都是用稀释的办法来加工含酸原油的。中国海油在惠州炼厂专门安装了一套全不锈钢设备炼含酸原油,但这样投入就很大。所以我就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含酸原油的成分搞清楚,以后通过技术改进,在普通炼厂用普通碳钢来炼,这样有多少原油就能炼多少。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思考路径告诉了我的一个研究生,让他去做试验,结果很圆满,工业化实验也成功了,在上海高桥炼厂也建了加工装置,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中国石化总工程师曹湘洪院士,对这个技术改进也很感兴趣,他就向中国石化主要领导汇报说应该报奖,领导十分支持并希望保密这项技术。但我的上级领导认为,虽然这个技术改造的思路很好,但其技术诀窍一听就明白,太简单了,所以不予上报。很多人都觉得可惜,但对我来讲得不得奖并不重要,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当了院士,无所谓了,而是我觉得如果自己的一些想法能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最大的奖赏。所以当时我带的这个研究生做答辩的时候,去了100多人听他的答辩,而以前的答辩都是在一个小房间里,最多十几个人参加。我觉得创新是一种乐趣,创新也是科学家的责任,我们要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至于成功的秘诀,我觉得是不存在的。但作为一名科学家,在探索客观真理的过程中,首先要对这个探索有兴趣,没有兴趣做不好事情;其次就是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应该穷尽所能,让所有学到的知识都能产生联系,取得应用,就像我前面提到的让二氧化碳负排放。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就会想这些东西,这个思索的过程充满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