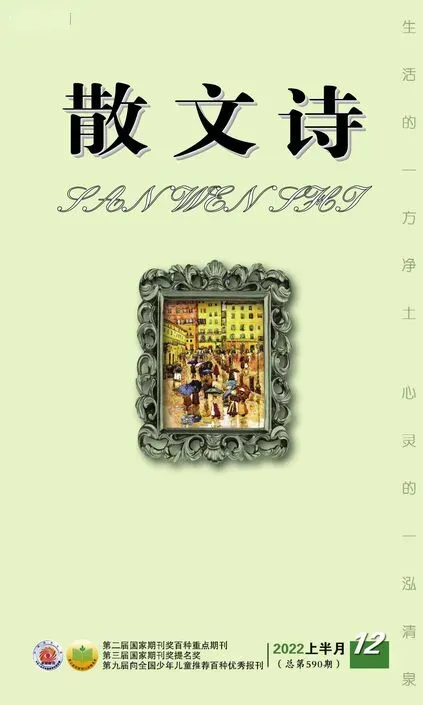我身体里仍珍存一脉故乡之水
◎黄鹏
序章:一身麦芒
将花朵指向太阳,我独自拥抱石头入梦。
俯身走过田园,归来时,我一身麦芒。
太阳不可能天天迟到或缺席。那些散落山野的墓园,实在过于凄凉。在那里,沉睡者太多,打扫者太少。
但我始终坚信:总有一两枚铁钉,既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宿命。
因此,我常如此陈述:世界或人间,我是你与生俱来的一场病症。
第一章:月圆怀乡
九月之杯盛满酒水。
今夜,我遇见有孕在身的盲人。
于岩洞之内栖居,石头和光阴在高塔之上冲锋,我看见众神冲下山来驱散羊群,掠走一座村庄多舛的命运。
雨水不住流淌。
夜宴之人未散,他们手挽岁月,犹如手擎酒杯迟迟不肯放下,在月圆之时,盛开成一树梅花。
站在山峰之上,打量逝去的村庄——飞鸟寂寂,冷风嗖嗖……白色的云朵在天空孤绝地翻飞,半醒的睡梦倔强,在大地投下永恒的光芒。
再次回到故乡,我嘴角上扬,我有一脸的满足需要尽量克制。
每次有人喊出乳名,我都有一阵战栗和兴奋,仿佛故乡的水,再一次流经身体。
稻谷和少女成熟之后,时光老去。我孤独地收割着自己,以及亲人。
秋天拥有一地废弃的血液。黄土地上,麦子散乱,躺下身去,我和它们相依而眠,继续在泥土之中,迎着狂风,结出永不颓败的金黄。
时光中的命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唯有风,还在继续吹奏;唯有离乡者,还在默默承受。
裹紧自己,跃动的命脉里,我是鲜花和硬币的结合体。流年让人躯体平庸为昆虫,随时背负一方受伤的天空。
把意念和兵器放下,我从村庄取回瘦马。像安于生活与农事,我学会安于平淡如水的日子。
第二章:秋日还乡
沿山峦拾级而上,小径,铺满了深邃的黄。
无数次离开又返回,玻璃窗因为早晨的日光而仿若晚上,只是高处点点闪现的星,不再无所顾忌地照耀废墙。
土在下,天在上。
缘何我的故乡,船不高而水空涨?缘何命里缺盐,就算我们一次次地站上山冈,最终也不得不内心空荡地,缱绻于一页薄薄的纸上?
异乡吹来的风,继续吹拂故乡,从一片蛙声中醒来,我不知该去往何处。
东边是神圣的故土,和我所熟络的所有村落一样,漫长时光宛若一条巨龙,总是在每一次转身之时卷起暴风。
当风从林间再度吹来,栅栏外,山谷间,我们的生存如莲藕般湿润,我们怀乡,深深陷入一个季节的金黄与辽阔。
第三章:一双假翅
郊野有着无人能敌的空旷,荒草铺满路途,微风拂过白桦,炊烟下的小屋,寂寥和空荡一如既往。
小雪到来之前,远行与流浪尚需等待,我们的偏头疼和怀乡症再度发作,治愈,尚需一段时间。
天空堆满星辰。高山上,流水边,掐指细算,这是我们相互依偎的第三十五年。
三十多年来,若生命可以重生,一岁一枯荣,不知你和我,羊群、故乡和灵魂,将历经多少遍重生。
无数次独坐黑夜,看长蛇不知疲倦地爬过内心的台阶,我们一任岁月,不分黑白,野草和潮水一般野蛮地弥漫。
到了冬季,一直矗立于旷野的大鸟就要远离,快要消失天际的一瞬,它突然飞回,对同样长着两只假翅却不能飞翔的我们久久低鸣……
厌倦了高度与食物,它遥望的双眼,居然对我们有如此深沉的眷恋。
第四章:木桩上的衣裳
故乡就此不着一语,只在风雨中静静伫立,随时守候着我们回归故里。
像孩时允许我们在她的目送中看牛、牧马,她期望我们继续在她的叮嘱里劳作、搭屋建房。
或者就允许什么也不做,只要我们能像无数叶片一样,从枝头缓慢跌落土地,继续等待着来年的春风又起。
有时,我们若光、似风,不能停止流动,不能止于飞翔,光阴啊,就这样慢慢流淌。
多数时候,我们更像是一件被遗忘在木桩上的衣裳——
年长日久中,我们陷入想象,开始极力模仿主人踏月归来的眼神和步态,该斜的时候斜,该歪的时候歪——不单单是藏青色的那一件,不单单是这个踏着微霜也要离乡的远行人。
第五章:醒与疼
天空中落下的雪花,要么成水,要么成冰。
我们走在路上,始终保持着倒下前的小心翼翼和警醒。
雪还在没完没了地落,两个孤儿在严寒里结伴而行,像两只被遗弃的油桶,悬挂在遥远的风中。
闭上双眼,视线之外白雪满山,多年以前,我们还是吹着口哨的小调皮,敢于骑一朵雪,绝尘而去。
天空和大地——曾是你我厚重的上下眼皮,它们在白昼轰然洞开,又于夜深人静之时合二为一。
那时的故乡深山,你正襟危坐,示意我放下执念,我知道其实关于雪与洁白,你一定有许多话语在心间潜藏。
大雪纷飞啊大雪纷飞,纷飞的大雪,把我们覆盖。
雪大啊雪太大,可是,无论雪有多大,它也无法将时间拦下,无法阻止我们沿着小道回家。
看,天空中那两片迟迟不肯落下的雪,它,其实是我们在这人间,最后的疼痛与清醒。
第六章:一地洁白
洁白的孤儿坠落人间。
紧闭房门,我仍能听清雪拍打大地的声音。
清晨,一切还未苏醒。我索性就做了第一个踏雪出门的人。
多半时候,我的出行,更像一场让自己哑然失笑的闹剧,一切的终结,又仿佛都是雪莫名的凋谢。村庄的雪美丽,山中的雪孤独,久久伫立梦里,太多的人美丽异常却也孤单无依。
关于雪,我最初的记忆还停留在孩提时代。那年除夕——深山雪花大如席,是夜,风雪推门而入,紧随雪进门者,是我务工一年才归的老父亲。
至今,他身后的那团雪,还白得让我无法睁开双眼。
纷飞大雪,让我想起了什么,又仿佛什么都不曾想起。
我想:如果我们的村庄还一直是白雪皑皑,那么,我甘愿枕着一地的洁白,倾听夜。
尾章:回望故乡
以春天的名义在石头围就的村庄相聚,我们把油菜花的芬芳高高举起,我们把酒杯的硬和雪花的软,高高举起。
诗,虽不等于美,但我十分乐意为诗歌和美,同时干杯。
在村庄,古典的余温尚存,春天空前繁盛。
草木不愿在其跟前枯萎,而愿在其脚底生发。我愿意把仇人和时间的顽疾从胸间抹去,把人世所有的美好与兄弟——当作亲人。
月亮和星辰散落头顶,曾经的院落,被岁月打扫得干干净净。
从山麓起身,像云。
多年以来,我漂泊不定,却敬畏于大地上四起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