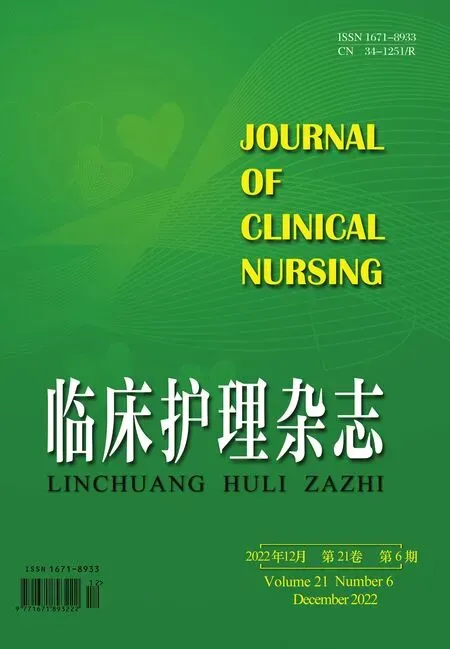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与社会支持及患者死亡态度的相关性研究
陈 红 陈昌英 周淑惠 唐 金
安宁疗护为恶性肿瘤晚期患者常见且接受度广泛的临终护理理念,是指对没有治愈希望、进行性恶化或生存期较短的患者提供专业性、支持性身心呵护的卫生保健服务[1]。预感性悲伤为恶性肿瘤晚期患者主要照护者安宁疗护期间因感知到有可能失去对自己有意义、有价值的人或事物时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反应及行为,主要以照顾者认知迟钝、问题解决能力及照护能力的减弱等形式体现[2]。研究表明[3-4],癌症患者家属预感性悲伤程度是其照护行为、应对方式及患者临终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重视家属预感性悲伤及相关因素的研究对促进患者及家属综合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分为提供情感、信息援助或指导的广义,或当个体生命周期发生变化时来自家庭、同事、朋友等外部支持资源的狭义两类[5]。患者死亡态度是指患者自身面对死亡事件所持有的认知、情绪及应对行为,与患者自身疾病感知及心理灵活性水平密切相关[6]。目前,临床对于照护者预感性悲伤影响因素多集中于心理弹性及认知等方面,对于社会支持及患者死亡态度的研究尚未涉及。本研究旨在探究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与社会支持及患者死亡态度的相关性,为临床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理论依据,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月-2022年6月我院收治的106例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及主要照护者为研究对象。患者纳入标准:均经组织学和(或)细胞学病理诊断确诊为恶性肿瘤;预期生存期>3个月;临床分期均为Ⅳ期。排除标准:精神发育迟滞、痴呆或脑部器质性病变;合并多种恶性肿瘤;中途退出研究者。主要照护者纳入标准:年龄≥18岁;均为患者主要照护者;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上;具备正常沟通与理解能力;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感染疾病;中途不配合研究或退出者。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且患者及主要照护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查阅文献并结合专家建议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对主要照护者人口学与临床学资料进行收集,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文化程度、与患者关系、经济收入、患者疾病类型、病情知晓程度、有无照护经历、患者是否具备基础自理能力等。
1.2.2预感性悲伤量表 采用Theut等[7]编制的预感性悲伤量表(AGS)评定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水平。该量表包括悲伤感、失去感、愤怒感、易怒感、焦虑感、内疚感和完成任务能力7个维度,共26个条目。采用1~5分评分法,总分130分,分值越高表明预感性悲伤程度越严重。
1.2.3死亡态度描绘修订量表 采用死亡态度描绘修订量表(DAP-R)[8]评定患者死亡态度。该量表包括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自然接受、趋近接受、逃离接受5个维度,共32个条目。采用1~5分评分法,分值越高表明患者越趋向于该态度。
1.2.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9]评定主要照护者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条目。采用0~9分评分法,分值范围12~66分,≤22分为社会支持水平低下,23~44分为社会支持水平中等,45~66分为社会支持水平较高,分值越高表明社会支持度越好。
1.3 资料收集方法
发放问卷前,研究者与患者及主要照护者进行交流,并解释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过程。填写问卷前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填写过程如有疑问,采用一致性语言解释;填写完毕后,检查量表和问卷,如有漏项或不完整及时补填。本研究发放问卷106份,回收问卷106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行秩和检验,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评分情况,表1

表1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评分情况
2.2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社会支持评分情况,表2

表2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社会支持评分情况
2.3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死亡态度评分情况,表3

表3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死亡态度评分情况
2.4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与社会支持及患者死亡态度的相关性分析,表4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与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097、-0.326、-0.534、-0.602,P<0.05);患者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死亡逃避、逃离接受维度与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192、0.974、0.619,P<0.05),自然接受、趋近接受维度与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528、-0.680,P<0.05)。

表4 患者主要照护预感性悲伤与社会支持及患者死亡态度的相关性分析(r)
3 讨论
3.1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社会支持及患者死亡态度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各维度中得分最高的前3位分别为失去感(14.88±3.40)分、悲伤感(13.99±3.50)分、焦虑感(12.79±2.51)分,预感性悲伤总分为(76.12±13.37)分,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其原因:恶性肿瘤晚期实施安宁疗护的患者主要目标为帮助患者改善死亡应对态度,安宁度过人生终末期阶段。该阶段其照护者作为相关护理决策及患者病情发展见证的主要参与人员,在面对亲属生存期短暂或病情发展和恶化情况下,对其照护信心及照护负担造成负面影响,并累及其身心、情感,甚至预感到亲属离去而产生预感性悲伤。据报道[10],癌症患者家属预感性悲伤发生率高达26.9%,且贯穿于癌症患者整个病程,在患者临终阶段表现尤为严重,本研究结论与之也具有一定吻合度。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主要照护者社会支持总分为(28.97±5.57)分,处于中等水平。其原因:可能与主要照护者作为患者日常生活主要陪伴者及护理操作协助者,患者该阶段病情发展较快且极易恶化,日常照护任务及护理难度较大,导致照护者其他社会交往关系减弱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死亡态度中得分较高的维度分别为趋近接受(52.45±6.76)分,自然接受(18.45±3.45)分,表明患者更乐于采取接受态度面对死亡,死亡态度较为乐观。其原因:可能与本研究患者均实施安宁疗护有关。安宁疗护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灵性照护模式,利用个体认知、心理及社会因素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多种正性行为与心理激励干预帮助挖掘患者的积极心理,激发个体内在专注力,调动患者主观能动性,发现并体验积极感受,促进癌症事件、应激障碍和负性情绪的调节,进而能有效增强患者心理弹性,改善死亡态度[11]。
3.2 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与社会支持及患者死亡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主要照护者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与预感性悲伤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097、-0.326、-0.534、-0.602,P<0.05),即主要照护者社会支持度水平越高,其预感性悲伤水平越低,与梁思静等[12]研究结论一致。社会支持水平作为个体处理应激重要的外部资源,当获得更高的社会支持后,有助于个体维持良好主观情绪体验,改善自身主观幸福感及心理承受能力,调节身心状态,使其在面对疾病不确定感时可重新进行自我心理评价和调节,在正能量引导下,主动寻求积极信息和重新评估情况,改变应对策略,缓解其身心痛苦症状,降低主要照护者对疾病发展或恶化的不明确性因子、复杂性因子和不可预测性因子的重视度,进而降低预感性悲伤水平。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下降,其获取的信息可使身心情感支持减少,加剧主要照护者的负面情绪,最终形成无助、绝望、悲伤、恐惧等心理环境的不良循环[13]。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死亡态度中的死亡恐惧、死亡逃避、逃离接受维度与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总分呈显著正相关(r=0.192、0.974、0.619,P<0.05),自然接受、趋近接受与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总分呈显著负相关(r=-0.528、-0.680,P<0.05),即患者死亡恐惧、死亡逃避及逃离接受水平越高,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水平越高,患者自然接受与趋近接受水平越高,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水平越低。其原因:患者死亡态度与其自身疾病认知和心理接受程度密切相关,对死亡采取自然接受或趋近接受的患者其疾病应对策略多趋于积极,心理调节能力多倾向于良好状态,在应对疾病发展或病情恶化时均能维持良好且接受的心态,有助于激发其家人与癌症抗衡的自信心、主动性,进而间接影响主要照护者的心理状态与照护效能。而对死亡采取逃避、惧怕或逃离态度的患者,其应对策略多趋于消极,对于疾病发展的阶段普遍存在恐惧、回避且焦虑情绪,进而影响主要照护者日常照护期间心理健康,造成预感性悲伤水平的加重。王沙沙等[14]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年龄、心理弹性、应对方式、文化程度均为癌症患者死亡态度的主要预测因素,提示临床可针对以上因素,积极满足患者心理社会需求、灵性需求,采取认知行为疗法、心智觉知训练、正念干预等深入进行研究分析,为疾病治疗依从性及家属心理状态提供更为有利的正性影响。
综上所述,预感性悲伤为恶性肿瘤晚期安宁疗护患者主要照护者照护期间常见负面情绪反应,且与其社会支持及患者死亡态度存在密切相关性,提示临床人员因充分重视主要照护者预感性悲伤水平,尽早采取科学合理的心理干预措施帮助其维持身心健康,优化患者康复体验与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