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窃曲纹”名实考*
王清雷
(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乐研究所,北京 100029)
作为一种青铜器纹饰,“窃曲纹”一名首见于《商周彝器通考》。该书指出,窃曲纹的命名源自《吕氏春秋·适威》。笔者在阅读几部《吕氏春秋》的点校本时发现,《商周彝器通考》对于《吕氏春秋·适威》中“窃曲纹”一段的点校存在不妥之处,故窃曲纹这一命名似乎尚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同时,在不同的青铜器纹饰研究文献中,对于西周甬钟篆带所饰窃曲纹也有多种不同的称谓,需要做全面的梳理与考辨。
关于名与实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已有深入探讨。《墨子·经说上》云:“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2]350《中国小学史》一书认为:“‘所以谓’,即现代人所说的‘能指’;‘所谓’,即现代人所说的‘所指’。”[3]26其中的“能指”和“所指”,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4]102北宋王安石更是看重名实之辨,他认为:“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则天下之理得矣。”[5]可见,名与实是一个纵贯古今、横跨中西的大问题。对于窃曲纹的研究,名与实的探讨是笔者首先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一、文献学视角的探讨
窃曲纹是古代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纹饰,诸多的青铜器研究著作均对其有专门的阐述,如《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中国青铜器综论》等。
《商周彝器通考》写道:“《吕氏春秋》云:‘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其状(一)拳曲若两环,其一中有目形。(二)两曲线相钩而成一环……”[1]108该书根据窃曲纹的不同形态特征,将其细分为15种。
《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指出:“容庚编纂《商周彝器通考》一书,始有专章论述花纹,列举纹样七七种,略加诠释,但也是一些材料的罗列,没有很好的分析,只供研究者有所取材而已。我们现在再次考察,觉得该章的分类未免繁琐,所以有进一步加以整理的必要。”[6]102故此,《殷周青铜器通论》一书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的修改与删减,例如窃曲纹,该书指出:“窃曲纹为西周后期的主要纹样。《吕氏春秋·适威》篇说:‘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其主要的形状是(1)两端一上一下如S状,中有目形,地文填以雷纹。(2)状长,两端皆曲,中有三目形。(3)如(1)状,两端上下钩曲,中有目形。”[6]115笔者通过对比《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两书发现,《殷周青铜器通论》仅保留了《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的六、八、十这3种窃曲纹,将原来的15种窃曲纹缩减至3种,删减掉80%,可见其删减幅度之大。
《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认为:“窃曲纹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之一。但是何谓窃曲纹,其状如何?仅以《吕氏春秋》‘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似不易确认。”[7]182可见,王世民等诸位先生对于窃曲纹的名实问题已有关注。“由于窃曲纹已为很多人所惯用,本文仍按其旧,分别梳理,以见其形式、变化和年代。”[7]185该书按照“目”纹的有无,将窃曲纹分为两型(有目窃曲纹和无目窃曲纹),每型以下各分5式,共计10种窃曲纹。
《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指出:“窃曲纹是流行于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吕氏春秋·适威》云:‘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后来研究铜器的学者就把一些以抽象曲线为主而构成的纹饰称为窃曲纹了。其实,学者已经指出,所谓窃曲纹,实际上是由动物纹样演变出来的。但目前多数学者既已习惯称这类纹饰为窃曲纹,为了不造成混乱,我们也沿用这一旧名。”[8]547-548按照窃曲纹的不同来源,该书将窃曲纹分为A型(饕餮窃曲纹)和B型(龙纹窃曲纹),其中A型分为3个亚型10种窃曲纹,B型分为2个亚型8种窃曲纹。
《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指出:“被青铜器研究者们通称为‘窃曲纹’的纹饰形式较复杂,但均有共同特征,即每一种图案的主要母题皆是卷曲的细长条纹,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上往往连接成带状,饰于器物的口沿下、盖缘及钟的篆部作主纹饰使用。《吕氏春秋·适威篇》:‘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所述形状与此种纹饰大体相合,故旧以窃曲名之。”[9]578该书将窃曲纹分为五类:S形窃曲纹、形窃曲纹、S和结合形窃曲纹、L形窃曲纹、分解形窃曲纹。其中,该书仅对前两类窃曲纹做了分型分式。将S形窃曲纹分为A、B两型,其中A型分为4个亚型,B型分为2个亚型,Aa亚型分为2式,Ba亚型分为4式,其他亚型不分式。将形窃曲纹分为A、B、C三型,其中A型分为两个亚型、Aa亚型分为2式,其他型和亚型均不分式。
笔者通过全面梳理有关窃曲纹的研究文献,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窃曲纹的命名均源自《吕氏春秋·适威》中的一句,即:“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出于多年养成的学术习惯,笔者马上去阅读《吕氏春秋》的原始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首先想搞明白“窃曲”一词究竟为何意,否则就无法对窃曲纹做进一步的研究。阅读后的结果出乎笔者意料。这是因为,笔者发现文史界几部研究《吕氏春秋》的代表性著作对于这一句的点校均与以上五部青铜器研究著作的版本不同。如《吕氏春秋集释》对这一句的点校为:“‘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未闻)。旧校云:‘“窃”一作“穷”。’孙锵鸣曰:‘窃,未详何物。“有”必是“著”之误。’”[10]《吕氏春秋注疏》对这一句的点校为:“周鼎著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11]《吕氏春秋新校释》对这一句的点校为:“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12]1291从以上三部著作对《吕氏春秋·适威》的点校来看,“窃曲”竟然不是一个词语,“窃”是前一句的句尾,“曲”是后一句的句头,“窃曲”一词竟然根本不存在。这样看来,文博考古界使用了数十年的窃曲纹竟然是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一种青铜器纹饰,这一名称是由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古代文献不同的点校而导致的讹误,这一发现令笔者愕然而不知所措。笔者继续查阅有关文章,发现在2011年已有学者发现这一“乌龙”问题,即《对〈吕氏春秋〉所载青铜器纹饰名称的几点看法》。该文指出:“时至清代,学者们尚不认同‘窃曲’是一种青铜器纹饰,如孙锵鸣注:‘窃未详何物,有必是著之误。’可见当时非但没有‘窃曲’一词,就连断句也将窃和曲分开。”[13]由此可以判定,窃曲纹这一命名应该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是否可以按照以上三部著作的点校,将窃曲纹改称为“窃纹”呢?
《吕氏春秋新校释》认为:“案:‘窃’乃‘禼’之重文。窃、禼同音。《说文》云:‘禼,虫也,象形,读与偰同。’查甲骨文有等形字(见《甲骨文编》附录上一二〇),审此三形,正是《吕氏》此文所谓‘曲状甚长,上下皆曲’。”[12]1300-1301由此可知,“窃”是古代“虫”的一种。《说文》所言之“虫”基本与今日之“动物”之意等同,如《大戴礼·易本名》就有羽虫360种,毛虫360种,甲虫360种,鳞虫360种,倮虫360种的记载。这与今日所言之“虫”含义大相径庭。故“窃”到底是哪种“虫”不得而知。至于甲骨文“等形字”,从字形上来看也谈不上是“曲状甚长,上下皆曲”,比之更符合这8字特征的甲骨文还能找出一些。故此,“窃”为何种样态依然未知。《吕氏春秋新校释》经过进一步考证,认为《考古》1988年第10期图版五的图像“与甲骨文‘禼’字相似,疑即是禼(窃)”[12]1302,该书还附上了这幅禼(窃)的图片(图1)。经笔者查询《考古》1988年第10期图版图片的出处求证,该图像刻画于一件“豆盘底部表面”[14]904(图2)。该豆盘出土于山西省侯马市牛村古城晋国祭祀建筑遗址,时代为公元前450至公元前420年。[14]907从原图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该刻纹为非常写实的一条蛇。如果《吕氏春秋新校释》的考释可以成立,那么窃纹就是蛇纹。在当代青铜器纹饰研究中,蛇纹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被称为蟠虺纹[1]123,在《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中被归入交龙纹[15]7-8,《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正式将其称为蛇纹[9]558,均没有将其归入窃曲纹。显然,这种所谓的“窃纹”与当代文博考古界所谓的窃曲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纹饰。即使《吕氏春秋新校释》的考释成立,“窃纹”与当代文博考古界所谓的窃曲纹也无法对接或者替换,二者名实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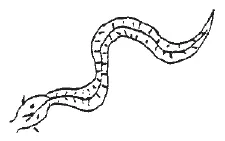
图1 《吕氏春秋新校释》所附“窃”图① 图片来源: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2页。

图2 山西侯马牛村古城晋国祭祀建筑遗址所出豆盘之底部刻纹①图片来源: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牛村古城晋国祭祀建筑遗址》,《考古》1988年第10期。
在有的著作中,窃曲纹又被称为穷曲纹。《中国青铜器发展史》一书中“窃曲纹”条目云:“《吕氏春秋》:‘周鼎有窃曲(一作穷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形状长,两端上下钩曲,有的中间有目形;有的两端上下如S状,中间再填以目纹。”[16]《中国青铜器》一书指出:“兽目交连纹为两兽的某一部分相互连接,所接触之处有一目相连结。……这类纹饰旧称穷曲纹或窃曲纹。”[17]《商周青铜器文饰》一书认为:“形和∽形的变形兽体纹,习惯上称为窃曲纹,或穷曲纹,流行于西周中晚期,春秋早期仍沿用。”[15]25《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一书就将逑钟的旋、舞部和篆带所饰的纹样称为“穷曲纹”[18]。
那么,“穷曲纹”这一称谓是否妥当呢?《吕氏春秋新校释》对其也有考证,该书指出:“旧校云:‘窃一作穷’,是以‘穷曲’为读。曲、奇双声,穷曲即穷奇。穷奇在书传中有三说……第一义为国名,显与《吕氏》此文不合。第二、第三义如虎、如牛,皆不长不曲,与《吕氏》此文言其状‘甚长,上下皆曲’亦不合。明‘穷’字必是误文。别本作‘穷’者,乃因后人不明‘窃’字之义,而以形近之‘穷’字改之,未可从也。”[12]1301由此可知,“穷曲纹”这一命名也不能成立。且“第二、第三义如虎、如牛”,其与当代窃曲纹的纹样特征也无法对应起来,即名实不符。
通过以上考证可知,从文献学的视角而言,“窃曲”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语,故“窃曲纹”这一命名不能成立。另外,“窃纹”或者“穷曲纹”这两种命名与当代所谓“窃曲纹”的实际纹样特征并不吻合,属于名实不符,故这两种命名也不妥当。同时,按照《吕氏春秋新校释》“‘穷’字必是误文”的观点,“穷曲”也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语,“穷曲纹”这一命名自然无法成立。
二、语言学视角的再探讨
从文献学的视角来看,当代文博考古界所谓的“窃曲纹”之实(“所指”),并没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名称。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命名这种纹饰呢?
《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指出:“最近一些学者对部分纹饰开始采用一些新的名称……其中有的较之传统名称确实贴切一些,对此我们必须给予注意。但是许多名称沿用已久,有的尽管未必妥当,因已约定俗成,在使用中一般不会造成误解,且现今仍被多数著作所使用。此外,无论予以何种名称,也都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的,至于在商周时代古人如何称谓之,因没有文献记载,已不得而知。所以,在今天对青铜器纹饰给予定名,主要是要考虑如何便于分类、归纳。对其内在涵义的认识及正名的工作,因为关系到正确认识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与艺术观念,仍必须继续深入探讨,但这是长期的研究方向,其中有的难以在短时间得出定论,不妨仍暂时沿用旧说。”[9]539按照该书阐述的定名方针,对于“窃曲纹”的定名问题,因为“约定俗成”,“不妨仍暂时沿用旧说”这一理由是否合理呢?笔者在初次阅读该书的时候,觉得这一理由非常牵强,并不能令笔者信服。更何况通过前文的详细论证,“窃曲”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语,怎么还能称为“窃曲纹”呢?但是,在笔者阅读了语言学领域关于名实关系的研究文献后,对于“约定俗成”有了新的认识。
《墨子·经说上》云:“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2]350战国末期的《荀子·正名篇》对“名实”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约定俗成”的命名原则。《荀子·正名篇》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19]
《中国语言学史》一书对《荀子·正名篇》的这一段史料作如是解读:“荀子在《正名篇》中所叙述的第一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荀子说:‘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约定俗成就是合理的,不合于约定的名称就是不合理的。名称并非天然地要跟某一实物相当,只要人们约定某一名称跟某一实物相当就行了。约定俗成以后,也就是名实相符了。但是,名称也有好坏之分,如果说出名称来,人们很容易知道它的意义,那就是好的名称;〔如果意义含糊,妨碍人们的了解,那就是坏的名称了。〕’这样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在今天看来还是完全正确的。……荀子在二千多年以前能有这种卓越的见解,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20]
《中国小学史》一书对《墨子·经说上》以及《荀子·正名篇》提出的“约定俗成”命名原则作如是解读:“‘约定俗成’有两层意思:在创制语词之时,名与实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带有任意性;一旦制定语词用以标指特定事物,成了习惯之后,那对使用的人就有强制性了。在荀子看来,名与实的结合,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按照个人意愿的,而是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如果说语言学是用语言内部结构的观点去理解语言的科学,那末,荀子提出‘约定俗成’等原则,便是我国语言学的第一块理论基石。”[3]36
从《中国语言学史》和《中国小学史》两部著作对荀子“约定俗成”命名原则的解读来看,名实之辨首先是一个语言学领域的学术问题。“在创制语词之时,名与实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带有任意性”[3]36,“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20]。初看这条“不讲理”的原则,着实令人大跌眼镜,难以理解,但我们务必要明白的是,《中国语言学史》《中国小学史》这两部著作对荀子“约定俗成”命名原则的解读是有特定语境的,是在语言学的学术范畴内的一个学术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任意性”或“共同约定”。所以,我们来看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语言学家索绪尔从语言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解读。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符号的任意性”。索绪尔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4]102“事实上,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4]103这与《荀子·正名篇》提出的“约定俗成”命名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任意性”的问题,索绪尔指出:“任意性这个词还要加上一个注解……我们的意思是说,它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4]104对于窃曲纹而言,笔者上述的考辨已经证实,“窃曲”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词语,故其也就没有任何“所指”,也就更不是我国“周鼎”上的一种纹饰,但它却成为当今文博考古界基本已达成共识的一种青铜器纹饰的“能指”。这充分体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可论证”和“任意性”,也即《荀子·正名篇》所言的“名无固宜”“名无固实”[19]。但自从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首次将“窃曲纹”(即名或“能指”)与其认为的15种纹饰(即实或“所指”)联系在一起之后,“窃曲纹”这一名称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如《殷周青铜器通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等著作均采纳此说。在当今的青铜器研究领域,如果说起窃曲纹,学者们对其大都是清楚而明白的。由此,窃曲纹就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约定俗成”,“约定俗成以后,也就是名实相符了”[20]。
探讨至此,窃曲纹的名实问题也就可以画上句号了。不仅如此,按照《荀子·正名篇》所云:“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19]即“名称也有好坏之分,如果说出名称来,人们很容易知道它的意义,那就是好的名称”[20]。以此观之,窃曲纹不仅“名实相符”,还属于“善名”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