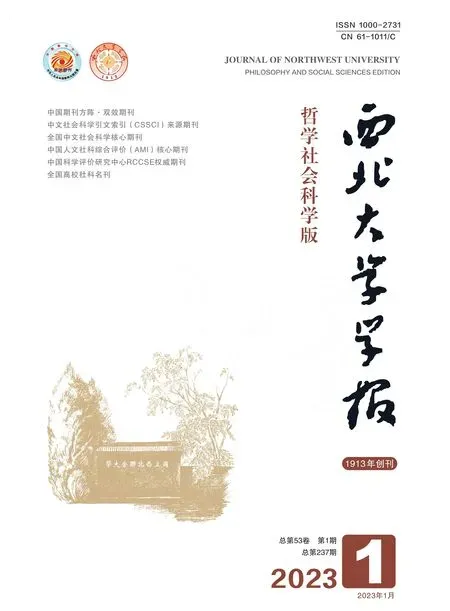伊朗教育世俗化改革及其对两次革命爆发的影响
母仕洪,蒋 真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127)
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稳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近代以来,伊朗历代政府均极为重视教育发展同社会进步、国家兴盛之间的内在关联,教育革新成为伊朗挽救王朝衰落或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关于伊朗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问题,国外学者关注较多。除散见于各类通史性著作的内容外,还诞生了两部专题研究成果[1-2]。相形之下,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少,迄今尚无专文论述,仅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稍有提及[3]163[4]275, 314[5]34, 59[6]52, 91[7]83-84。总体而言,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伊朗教育改革的成就及局限,而对教育改革产生的权力关系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缺乏深入探讨。在伊朗传统社会,国家教育权力由乌莱玛(1)“乌莱玛”(Ulama)一词,又译为乌里玛或欧莱玛,源于阿拉伯语,指具有专门宗教知识的伊斯兰学者。什叶派乌莱玛包括大阿亚图拉(意为“真主的象征”)、阿亚图拉(Ayatollah,意为“真主的权威”)、霍贾特伊斯兰(Hujjatal-Islam,意为“伊斯兰的证据”)三个等级。在伊朗传统社会,乌莱玛是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独家垄断,世俗政府难以直接介入。因而,伊朗的教育改革不仅意味着教育理念之争,更是意识形态之争和教俗权利之争。教育世俗化改革引发世俗统治者与乌莱玛对教育权力的激烈争夺,致使伊朗传统权力结构失衡,构成此后伊朗政教关系曲折起伏的重要因素。20世纪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爆发的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浪潮(2)立宪革命(1905—1911年)和伊斯兰革命(1978—1979年)是伊朗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历史学家彭树智、钱乘旦等人认为,立宪革命使伊朗有了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在伊朗历史上意义重大,标志着伊朗向现代化正式迈进。伊斯兰革命则扭转了伊朗的世俗化发展方向,使伊朗建立了“与东西方政治制度迥异的‘伊朗模式’或‘伊斯兰道路’”,深刻影响了伊朗国家的历史走向。参见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钱乘旦:《论伊朗现代化的失误及其原因》,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第28页;李春放:《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144页。,均同世俗统治者与乌莱玛由此形成的权力张力休戚相关,直到伊斯兰革命后乌莱玛接管国家政权,为双方近百年的教育主导权之争划上了休止符。本文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参阅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cl Reza Pahlavi)[8]、法拉赫·巴列维(Farah Pahlavi)王后[9]、情报部门主管侯赛因·法尔都斯特(Hossein Fardoust)[10]、政府大臣费雷敦·胡韦达(Fereydoun Hoveyda)[11]及美国驻巴列维王朝大使威廉·赫·沙利文(Willian H.Sulliran)[12]等当事人的回忆录或揭秘文件,尝试深入考察伊朗教育世俗化改革的流变轨迹及其与两次革命发生之间的内在关联,达到解释教育改革在推动伊朗社会演变过程中起何种作用的目的。同时,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勾勒出伊朗现代教育兴起和发展的大致脉络,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伊朗教育发展史略有裨益。
一、伊朗传统宗教教育及其面临的挑战
与世界多数国家的教育权力由世俗政府和教育机构操控的境况不同,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乌莱玛执伊朗传统教育之牛耳。自16世纪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定为国教以降,什叶派在伊朗社会中“定于一尊”的法理地位得以确立。伴随着伊斯兰教什叶派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伊斯兰教育担负起塑造宗教认同、教化万民、凝聚人心的职责和使命。此后,乌莱玛逐渐取得伊朗国家教育的垄断权,成为传承伊斯兰文化的火炬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精神导师。不论王朝更迭还是社会起伏,乌莱玛的这一权力始终连绵不绝,从未旁落。伊斯兰教以重视教育著称于世,崇尚知识是穆斯林经久不衰的优良传统。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知识的源泉,通晓更多的知识,意味着拉近同真主之间的距离”,“知识是寻求真理、善行、信仰、道德和智慧的基石”,“在穆斯林的生命观、工作观、幸福观中扮演重要作用”[13]。因而,“传统伊斯兰教将求知视为穆斯林的天职,……接受宗教教育不仅是穆斯林现实生活的需要,更是应尽的宗教上的神圣义务”[14]。知识同信仰一体的观念,奠定了乌莱玛在伊朗传统教育领域无出其右的地位,形成世俗贵胄与乌莱玛集团共享国家权力的圣俗统一格局,二者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

伊斯兰教义蕴含的纲常伦理旨在教化人心,伊斯兰教育注重道德素质和伦理修养,对于培养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和高素质的宗教精英具有优势,对于维系社会道德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意义不容置喙。但是,传统伊斯兰教育以宗教经典为基本教材,教学方式机械古板,主张死记硬背,不允许随意阐发自己的思想。尤其是不容质疑《古兰经》和圣训的信条,对异教文化采取盲目拒斥的态度,呈现封闭性和排外性,禁锢了受众的精神和思维。伊斯兰教育恪守僵化的神学理论,灌输宗教意识形态,学生只知埋首经训,演绎教法,脱离社会现实。陈旧的教学内容、机械化的教学模式以及宗教思维定式的禁锢逐渐使宗教教育落后于时代潮流。在近代欧洲,教育同教会实现分离,世俗教育和科学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支柱力量。从世界变革的时代背景着眼,伊斯兰教育在同欧洲教育对人才培养的竞逐中渐处下风,无法为适应时代变革提供专业化的创新型人才。对于伊朗这样一个古典伊斯兰文明因子沦肌浃髓的国家而言,在西方工业文明强势入侵的大变革时代,实现传统宗教教育的更新关乎国家的存亡兴衰。一言以蔽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伊斯兰教育的目的、方法和内容均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求,革新与时代相悖的传统教育已成大势所趋。
“挑战—应战”模式是驱动伊朗教育改革的直接动因,即在外来危机刺激下,伊朗统治者变革内部秩序,以适应世界局势变化之需要。不过,在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伊朗社会,教育改革的难度绝不亚于政治或社会层面的变革,因为教育领域是宗教保守主义的根基和堡垒。尽管教育改革是革新伊朗社会面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但对于宗教学者而言,教育改革不是乌托邦的序曲,而是灾难的前奏。教育改革势必触动宗教界人士的“奶酪”,引发微妙复杂的政治和宗教权力竞争,牵扯世俗政府、乌莱玛和现代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棘手关系。不仅如此,在乌莱玛眼里,伊斯兰文化是维系伊朗传统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是传统社会伦理的核心,久已被视为规范穆斯林行为的至上准则。“教育则是生产和传播伊斯兰文化、塑造穆斯林信徒的核心方式。”[16]63因而,教育世俗化改革势必触动伊朗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石和精神支撑。重重阻力预示着教育改革之路不会是一片坦途,而是荆棘丛生,与之相伴随的是两次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和近代伊朗社会的变迁。
二、教育世俗化的启动与立宪革命的发轫
19世纪初叶,西方殖民国家鲸吞蚕食伊朗领土,伊朗国势危如累卵。卡扎尔王朝统治者为抵御外力的强烈冲击,实现王朝自我挽救,启动了历时性较长、涉及面宽泛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在许多伊朗人看来,“教育是西方人发展进步的秘诀。于他们而言,对西式教育的效仿不再是离经叛道,而是通向救赎的康庄大道”[1]25。因而,教育改革成为卡扎尔王朝现代化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成为伊朗现代教育的基点,同时揭开伊朗世俗政府同乌莱玛争夺教育主导权的序幕。
卡扎尔王朝的教育改革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其二,创办独立于宗教机构的高等学府,引进外籍教员教学;其三,开办现代中小学校,变革教学内容。派遣学生赴欧进修肇始于1811年,前后分为数批,人数约为60余人,此举首开伊朗教育世俗化之先河[1]47。1851年12月,伊朗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成立,冠名福伦技术学院(Dar al-Funun,德黑兰大学的前身)[17]。该学府秉持实用主义原则,主要教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初设军事学、工程学、矿物学、矿业学、医学、化学、药剂学等学科。该校由政府直接掌控,不受宗教机构钳制,虽正常举行宗教活动,但宗教仪式的引领人由谙熟波斯古典文学的学者充当,将乌莱玛摒除在外,学生凭自愿参与宗教活动[2]21-22。正因如此,该校的创建被视为伊朗现代教育的开端。19世纪70年代伊始,卡扎尔政府着手在德黑兰、伊斯法罕、大不里士等城市兴办现代中小学校。这些中小学在学科设置和人员配置上同传统伊斯兰学校迥然有别,在保留宗教课程的同时,新设数学、科学、外语等学科,在管理和教学人员配置上,主要聘用“海归派”或福伦技术学院毕业生。
总体来看,卡扎尔王朝的教育世俗化改革进展缓慢,流于形式,没有触及基础性教育的深层变革,改革预期同实际成效之间差距较大,但其历史影响不容小觑。首先,培养了一批具有现代知识的专业人才,输入新的观念和思潮,对于革新社会面貌、启发民智具有积极作用。其次,教育改革打破乌莱玛对教育权力的独家垄断,经过改革后,伊朗形成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双轨并行的二元教育体系。最后,教育世俗化改革激起世俗政府与乌莱玛围绕教育主导权的长期争夺和对抗,成为乌莱玛同知识分子联合向世俗政府发难的重要诱因。
卡扎尔政府派遣学生赴欧深造,引进新式教育,催生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伊斯兰教育滋养下的传统知识分子信奉神授君权,认为君主是“安拉在大地的影子”(Shadow of God),鼓吹专制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的优势[18]35。现代知识分子则对这些陈旧观念嗤之以鼻,他们信奉人人生而有权且不可剥夺,主张平等、自由、互爱的社会原则,宣扬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等新思潮[19]50-51。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阶级中,包括皇族贵胄、政府公职人员、军官、乌莱玛和商人等。尽管成分复杂,归属不同行业和社会阶层,但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即通过变革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传统,挽救伊朗民族的历史命运[19]61。尤其是留学生大多前往法国深造,深受启蒙思想浸染和洗礼,他们反对专制主义、宗教教条主义、帝国主义,认为宪政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使伊朗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途径。但知识分子受限于自身实力,无法独立完成上述历史任务。在不同时期,他们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时而联合国王反对乌莱玛,时而联合乌莱玛反对国王,时而同国王反对帝国主义,立宪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同乌莱玛一道反对国王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实践[19]62。
教育改革是军事、政治、经济改革的助力和推手,同时也因其涉及利益纷繁复杂,每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举措都会招致乌莱玛的詈责,激成争论。在因循守旧的乌莱玛抵制下,任何妄图变更“祖法”的改革都会遭到乌莱玛的严厉打压,归于流产。19世纪上半叶,王储阿巴斯·米尔扎(Abbas Mirza)希望输入先进的军事技术,被乌莱玛指斥为“叛逆”。首相艾米尔·卡比尔(Amir Kabir)准备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触及乌莱玛的既得利益,最终也以变法失败、倡导变革者身死人手的惨淡结局收场[20]357。在阿明·道莱(Amin Dawla)主政期间(1897—1898年),他积极推动世俗教育的发展,阿塞拜疆总督米尔扎·哈桑(Mirza Hasan)在大不里士兴建欧式学校,以新式教学方法授课,乌莱玛斥责其为异教徒,新式学校遭到捣毁。阿明·道莱给予米尔扎·哈桑有力支持,邀请他到德黑兰主办新式教育。但阿亚图拉米尔扎·哈桑·阿斯提亚尼(Mirza Hasan Ashtiani)针锋相对,声称新式教育将削弱伊斯兰信仰,在乌莱玛的联合抵制下,阿明·道莱被迫辞职。
乌莱玛之所以对新式教育的发展心存芥蒂, 主要是新式教育侵蚀了其传统权力领域, 威胁到乌莱玛的传统特权和功能。 教育世俗化改革对中下级乌莱玛形成的冲击尤为强烈。 在伊朗传统社会中, 乌莱玛充当初级教师或被富裕家庭雇为私家教师。 在某一区域内, 乌莱玛被视为学识最渊博的人士, 在地区事务中拥有解释权和话语权,备受敬重, 形同名流[21]18。 教育世俗化改革意味着削弱乌莱玛在伊朗社会的传统功能, 社会地位和威望逐渐下降, 以教育为业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除此之外, 乌莱玛还担心, 伴随现代化改革而入的“异教”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同什叶派的传统观念相抵捂, 不利于民众维持传统的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22]111。 其中, 教育世俗化改革对传统宗教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解构, 令乌莱玛难以容忍, 反映了乌莱玛对异质文明侵入的全面排斥。 总而言之, 教育世俗化改革引发的“世俗权力与宗教神权的矛盾和对抗, 成为近代伊朗历史上, 特别是卡扎尔王朝统治时期政治斗争的显著特征之一”[23]492。
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气质特殊且具有使命感的阶层”,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他们“在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和塑造表达的倾向”[24]3,6。伊朗现代知识分子即强烈表现出这种特质。他们虽是教育世俗化改革的衍生品,但自诞生之日起就同卡扎尔政府处于若即若离、貌合神离的状态,渴望通过充当社会潮流的引领者,实现自身的理念和主张。而什叶派乌莱玛则因教育世俗化改革引发的利益冲突亦同卡扎尔政府离心离德,摩擦不断。基于斗争目标的趋同,二者渐趋联合,共同搭建立宪革命的舞台,给卡扎尔王朝造成沉重打击。
三、教育世俗化的深度推进与政教矛盾的激化
巴列维王朝立国后,教育改革成为其现代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之初,礼萨·沙(Reza Shah)面临双重执政危机。其一,乌莱玛势力强大,竭力反对现代化事业,维护自身利益和特权。其二,伊朗社会部落林立,地方部落主义盛行,国家缺乏内聚力和向心力。在伊朗民众心中,次国家的地方和部落认同以及超国家的伊斯兰认同远高于对世俗国家的认同,对宗教权威的信奉和部落首领的服膺不亚于对国王的忠诚[25]39[26]52-53。初生的巴列维政权为压缩乌莱玛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力,加强君主权威,对教育提出相应的变革要求。希望通过限制乌莱玛在教育领域的召唤力,使其复归到专注心灵信仰和主持宗教仪式的闲置状态,这是礼萨·沙进行教育世俗化改革的初衷之一[27]。同时,兴学育才作为现代化变革的基础事业,与之相匹配和适应的教育改革已成必然之势。
围绕上述目标,巴列维王朝开始推行系统的教育改革工程。改革内容大致分为六个方面:
其一,教育权力收归中央政府,由教育部统一掌控。1934年伊朗正式成立教育部,统筹和规划教育改革,形成对教育发展的有效监督和制度保障。教育部整合和分配各类教育资源,遴选与任命教员,从多元价值取向中筛选和贯彻符合社会需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价值观念。
其二,教育类型多样化,形成以通识教育为主体,职业教育、师范教育、技术教育、军事教育等多种教育类型横向并行的科学体系。各种教育类型互为补充,形成系统全面的教育体系。
其三,构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层次分明的纵向型教育体系。1934年德黑兰大学成立,其他省份的省立高等学府也相继创办,伊朗的教育结构趋于完善。明确规定各级教育学业年限,先后形成6—3—3和5—3—3—1等学制[28]。虽然教育政策向基础性教育倾斜,但各级教育呈现均衡、协调发展的良性结构。
其四,男性教育和女子教育并行发展。在伊朗传统社会,女性接受教育的几率微乎其微。礼萨·沙大力倡导女子教育,1922—1941年,伊朗中小学女学生的数量从约7 600人增长到约8.9万人,占比由16.9%上升至28%[1]110。礼萨·沙还开创男女同校、女学生不用戴面纱、女性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等先例,在伊朗社会均属革新的前瞻性措施。
其五,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统一各级学校的教学课程,使用教育部编发的标准教材。1928年,中学开始实行统一的课程设置,开设波斯语、阿拉伯语、外语、地理、历史、哲学、数学、科学、音乐、绘画、宗教等课程,女学生还需要接受家政、厨艺、缝纫、体育等额外课程[29]126。总之,课程设置兼顾学术性和应用性,注重对学生职业基础教育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与之相伴随的是同宗教相关的课程大幅减少,宗教内容在教学中边缘化。
其六,兴办各类世俗学校,大力发展世俗教育。礼萨·沙大幅增加教育经费投资,在政府的扶持下,各类世俗学校犹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培养的学生人数也急剧攀升。1925年,伊朗小学生的数量约为5.6万人,中学生约为1.5万人,大学生仅有600人;到1941年,伊朗小学生的数量增长至28万人,中学生增长至2.8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已突破3 000人[30]62。这些学生逐渐成长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新兴社会群体。
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伊朗的世俗教育体系基本确立。传统宗教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全面减少,其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效用渐趋弱化。从20世纪30年代伊始,伊朗的伊斯兰教育渐趋没落,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处于低潮发展状态。伊朗世俗中小学的学生数量一路飙升,迨至40年代末,世俗中小学在教育体系中已占据主导地位。宗教学校的学生数量则大幅下滑,伊斯兰中学的生源量甚至不足千人[1]102。礼萨·沙逊位后虽有所回升,但二者仍难以等量齐观。1958年,伊朗世俗中学的学生数量为19万人,伊斯兰中学的学生人数为1.3万余人,前者为后者的14倍之多[2]68。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期,伊朗世俗教育的发展更为迅猛。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使精通和谙熟某种技术的专业人才成为步入仕途或获取社会工作的必备技能,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对生源的吸引力陡增,宗教学校的魅力则骤然下降。 许多乌莱玛及其传统盟友巴扎商人也不再把子女送往伊斯兰学校, 而是逐渐倾向于选择世俗学校或前往欧美留学, 以便于将来就业[31]99。 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期推行的四个发展计划中, 伊朗的教育经费预算分别为450亿里亚尔(1963—1967年)、 1 720亿里亚尔(1968—1972年)、 5 510亿里亚尔(1973—1977年)、 25 000亿—27 000亿里亚尔(1978—1982年)[8]114。 学校数量从7 900所增至21 900所,各级学生的容量大幅增长[9]187。1963年到1977年,伊朗全国的小学生由164万人增至407万人,中学生由大约37万人增至74万人,大学生由约2.5万人增至15.4万人[19]431。高等教育的发展令人瞩目,1974年伊朗高等院校已达184所,包括综合性大学、技术学院、师范学院、商业学院、农学院、金融院校、航空院校、军事院校等,种类繁多,行业各异[32]。相形之下,1960年至1975年伊朗全国的清真寺由20 000座减少到9 000座[33]。教界控制的宗教学校数量锐减,德黑兰的宗教小学和神学院数量从32所减少至23所[39]。
在世俗化改革浪潮的引领下,伊朗的世俗教育茁壮成长。伊斯兰教育则同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渐趋衰落。乌莱玛在教育领域的地位被逐渐取代,传统教育权力丧失殆尽。许多以教育为业的中下级乌莱玛面临失业困境,生存压力倍增。在政治领域,乌莱玛则从教育、司法等国家权力部门中逐渐边缘化,政治地位每况愈下。1925年,乌莱玛在议会中拥有24个席位,到1940年已无一席之地[34]223。总之,巴列维时代伊朗历史的深刻变革瓦解着什叶派传统宗教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世俗政治的发展使什叶派传统教界的政治影响日渐衰微[35]。随着巴列维君主专制权力的巩固和膨胀,乌莱玛作为社会精英的传统地位受到空前削弱,伊朗的政教矛盾前所未有地激化。乌莱玛明面上屈从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君主权威,内心却从未放弃角逐世俗权力的诉求。
四、三大群体合流与伊斯兰革命的肇端
面对上述极具说服力的数据,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巴列维政府的教育世俗化改革将以锐不可当之势高歌猛进,冲破伊斯兰教育的最后防线,迎来世俗教育的全面胜利。然事与愿违,教育世俗化改革引发的世俗政治和宗教政治的矛盾激荡,以及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对于教育改革愿望落空的失望,使乌莱玛、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再度合流,共同向巴列维王朝发难。上文已对教育世俗化改革引发的巴列维政府同乌莱玛之间的疏离做了论述,接下来将谈谈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在该问题上是如何同政府分化、决裂的。
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同统治者与知识分子、普通大众对教育改革目标和预期的分歧紧密相关。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都将教育视为国家进步的社会化工具,但三者对教育改革的期望大相径庭。统治阶级将教育视为塑造国家认同、培养国家公仆和弘扬君主权威的手段。在统治者看来,培育忠于国家、效忠君主的“顺民”乃教育之首务,教育体系主要是“为统治政权及其政策动员广泛支持的一种工具”[27]。现代知识分子则认为,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具有独立意识和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从而将伊朗塑造为西方式的公民社会。普通大众寄希望于循教育之路出人头地,跻身上层社会,甚至青云直上,成为官宦之辈。
现代知识分子是指在高等院校接受过现代教育洗礼且具备现代知识素养和思想观念的群体。据统计,1976年伊朗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数已多达75万,教育系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分布领域[36]114。按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应成为拱卫政权的支柱,但巴列维政权对教育领域的严控和知识分子的防范使二者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
现代知识分子在立宪革命中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欲望,鉴于此,巴列维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管控素来严格。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期,伊朗大学成为域外势力渗透和国内反对派沉渣泛起的大本营,成为政府重点防控的对象。自礼萨·沙伊始,伊朗大学的管理权收归教育部,大学校长由教育部任命或政府官员兼任,教师从教育部领取薪水,因而伊朗大学自诞生之时就依附于政权,缺乏独立性[37]。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伊朗大学的学术环境相对自由,只要学术研究不逾越挑战政府合法性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红线,政府很少直接干预其内部事务。迨“摩萨台事件”(3)穆罕默德·摩萨台是伊朗民族主义运动领袖,1951—1953年担任伊朗首相,任内主张石油国有化运动。1953年8月19日,英美情报机构策划“阿贾克斯行动”,推翻摩萨台政府,史称“八·一九政变”。政变后巴列维国王大权独揽,倒向英美怀抱,压制国内左派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将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视为心腹大患,而历次事件表明,高等院校是左派与自由主义者成长和蛰伏的温床。巴列维政府逐渐收紧对大学的管控,具有左派倾向的知识分子被清洗出校园,大学的自由环境逐步丧失。1962年1月22日,伊朗安保部队公然进入德黑兰大学逮捕反对派成员,酿成惨案。时任德黑兰大学校长艾哈迈德·法哈德(Ahmad Farhad)后来回忆此次暴行时说:“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手无寸铁的学生,造成许多学生死亡。一些女学生在教室里遭到士兵凌辱,书籍、书架、打字机、图书馆设备被打翻在地,门窗、桌椅均遭到破坏,一片狼藉,就像野蛮的军队肆掠敌国领土一样。”[38]72-731969年,政府建立由国王直接领导的“最高监管委员会”,委员会向全国高校派驻检察人员,负责监察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危险言论,禁止学生携带武器或宣传材料进入校园。据巴列维情报总管侯赛因·法尔都斯特揭露,随着各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心的不满与示威高涨,情报组织“萨瓦克”(SAVAK,全称为“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专门成立名为“大学和国内高教中心与留学处”的独立处室,负责收集高等院校的情报和监管学生的活动[10]306。据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观察,“在大学校园里,萨瓦克的情报员多得不计其数”,“学生组织受到特别的注意和渗透”[12]70。情报组织在学生团体中发展线人,安插间谍,鼓励检举和揭发,任何反国王、反“白色革命”的言论都将接受调查。知识分子出版著作、组织集会、发表演讲等均受到严格管控,整个学术界万马齐喑,被知识分子称为“最黑暗的极度消沉期”[39]。不仅如此,所有中小学皆被置于政府监管之下,竭力向学生灌输忠君观念和效忠巴列维政权的思想[40]。教室、校园等公共场所悬挂国王肖像,倡导学生宣誓效忠国王,资助宣扬国王政绩的著述出版。总之,统治者渴望借助教育培养人才,但前提是保证对巴列维政权的顺从和国王的忠诚。如沙科拉赫·哈姆达里(Shokrollah Hamdhaidari)认为的那样,巴列维时代伊朗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文化的贵族”(aristocracy of culture),而不是孕育具有思想性和批判意识的个体[41]。
巴列维政府的此种行为引发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大学校园成为反对派阵营组织反政府活动的温床,人民党、民族阵线、伊朗解放运动等反对派组织皆与大学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42]359-360。伊朗大学生成为“20世纪70年代伊朗新中产阶级里最具疏离感和爆发性的群体”[41]。美国学者尼基·凯蒂(Nikki R.Keddie)称,在此期间,“伊朗学生运动规模之大,反政府之激烈,远非任何此类学生运动可及”[43]。德黑兰大学的学生疾呼“白色革命是一个谎言,发动一场红色革命”的口号[44]209。马赫迪·巴扎尔甘(Mahdi Bazargan)领导的自由运动组织公开主张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同时认为“宗教界的支持,对于伊朗任何这类运动的成功都是绝对必要的”[45]162。知识分子同乌莱玛的联合已形成牢固的心理基础,实践层面的合流也愈加明显。
伊朗教育发展现状同巴列维政府标榜的全民教育存在名不副实的窘境。教育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是贵族阶层和中产阶级,城市贫民和乡间农民沾惠受益较小。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缓慢,教育改革不仅没有缩小阶层差距,反而扩大了社会鸿沟。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伊朗有4 204个村庄,平均每25个村庄才拥有1所学校。农村儿童入学率仅有15%,城市儿童入学率则高达70%[2]60。1976年,伊朗全国6岁以上人口的平均识字率为47.5%,以德黑兰为核心的中央省区高达66.1%,东阿塞拜疆为36.3%,克尔曼沙赫为42.2%,库尔德斯坦为30%,锡斯坦俾路支斯坦仅有29.7%[46]。通过对比,中央省区同边缘省份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高下立见。连巴列维国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伊朗的教育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但“至今我国仍有千百万人,特别是农村的成年人和青年人还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25]331。不仅如此,上层社会的子弟家境优渥,自小接受优良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机遇远超平民出身的子女。权贵子弟往往依靠裙带关系进入政府部门或国家机关任职,而寒门子弟大多只能从事收入微薄的普通职业。总之,巴列维时代教育的发展“虽使更多下层社会的子弟得以步入校园,但高等教育仍主要是精英阶层权力合法化的工具,而非贫寒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1]281。教育发展失衡进一步引发阶级分化,中心与边缘、城市与农村、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之间产生社会“断裂”。社会边缘群体对教育改革红利分享较少,由此导致的社会差距使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其满腹怨气成为激化社会动荡的温床。
经过长期的政治高压之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中郁积已久的愤懑达到顶峰,他们率先以革命先行者的姿态向巴列维政府发起挑战。1977年6月,一批40人左右的作家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废除检查制度。翌月,一些知识分子发表致国王的公开信,要求他结束专制统治[11]3。乌莱玛应声而动,充分发挥自身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号召民众参与到反国王的斗争当中。普通大众积极参与反政府运动,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乌莱玛、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等各阶层走向联合,将巴列维王朝送入历史。教育世俗化改革引发的政教斗争、巴列维政府对教育领域的严控以及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社会分化等负面效应成为牵引三大势力合流的重要因素。
五、结 语
教育世俗化改革是伊朗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有效杠杆,挤压了乌莱玛的生存空间,催生和壮大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引发伊朗社会阶层结构的嬗变。同时,伊朗的教育世俗化改革之路具象地反映了近世以来伊朗世俗政权与教权力量的消长与角色定位,牵扯世俗政府、乌莱玛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具体来说,在近代伊朗社会中,世俗政权和乌莱玛的权力分割使政府难以一家独大,当其改革举措伤及乌莱玛的利益时,他们选择联合知识分子等社会群体向世俗政府发难。在教育领域表现为,世俗政府希望剥夺乌莱玛垄断的教育大权,从而引发了乌莱玛的抵制与抗争,构成制约世俗化改革的逆向因素。世俗政府希冀借助教育世俗化改革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型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拱卫王权的支柱和屏障,但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两次革命中均充当了王朝的“掘墓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他们对“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之上,并将他们排斥在权力决策中心之外而喜欢独断专行的政府深感厌恶”[47]43。诚然,很难说教育世俗化改革是伊朗两次革命浪潮的唯一因素,但确实是难以忽视的醒目因素。应当说,教育世俗化改革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叠加和聚合构成两次革命浪潮的根源。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在教育改革过程中能否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平衡与融合,同时兼顾各方利益成为教育改革事业成功的关键,这是伊朗教育世俗化改革提供的一条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