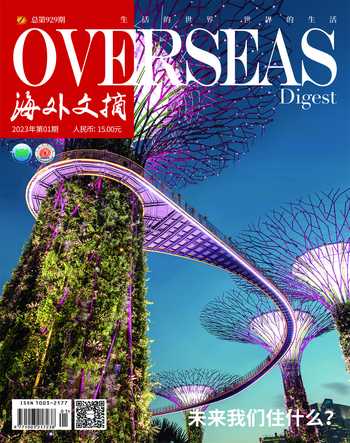红色警报:铁锈!
克劳斯·巴赫曼

铁锈毁坏桥梁、侵蚀建筑、倾覆货船:仅仅在德国,这个沉默的金属吞噬者每年就能造成高達1000多亿欧元的损失。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努力与之作斗争,研发新的保护涂层和能早期识别锈迹的探测器。与此同时,铁锈色却也被一些人认为是高贵的象征,在时尚艺术界占据了一席之地。
1980年5月21日将近11点,只听一声巨响,飞扬的尘土升入天空,德国柏林会议厅600吨重的弧形屋顶突然坍塌,击断了入口处的楼梯,掩埋了大门口,造成五人受伤、一名记者死亡。1999年12月12日,“埃里卡”号油轮在法国布列塔尼附近海域遭遇卷起12米高浪的风暴,断为两截后沉没,造成约两万吨重油外泄入海,海岸遭到污染,数万海鸟死亡。
这两场灾难看上去毫不相干,实际上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由铁锈造成。从化学上看,铁锈是铁的氧化物,是铁和空气中的氧气与水共同作用后的产物。铁锈可谓腐烂之兄弟、霉菌之手足,无所不在,看似微乎其微,毁灭力量却不可小觑。自从人类在火和木炭的帮助下让铁元素摆脱岩石和氧的包裹以来,铁锈就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一旦条件合适,被铸造、锻造或轧平的铁又会重新锈迹斑斑,因为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氧气和第四常见的物质铁太容易发生反应了。而铁锈这个沉默的攻击者会侵蚀人类成果,毁坏高楼大厦,破坏桥梁和车辆。“在静静的深夜,你可以听到一辆福特车生锈的声音。”美国人爱这么调侃。法国人则多年来一直戏称他们的埃菲尔铁塔为“锈塔”。
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腐蚀组织以抵抗“悄悄毁灭”为己任,计算出建筑用金属材料的腐蚀造成的年开支——约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3%。这样看来,2018年,德国的此项开支高达1000多亿欧元。而且,这里的“腐蚀”可能还只是专指狭义上的“铁的锈蚀”。据专家估计,如果建筑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始终坚持防锈,就可以避免大约25%到30%的损失。
| 邪恶的铁锈 |
2019年9月的一个阴天,在德国阿斯拉尔市附近萨尔兰线高速公路的伯恩巴赫谷桥上,一辆载重汽车停在应急车道,车上吊着一个工作台,上面站着三名身穿橘色工作服的建筑工程师。他们是黑森州道路管理局的员工。根据德国法律规定,所有工程建筑必须每六年进行一次“大检”,需细细检查所有建筑构件。“大检”过去三年后,则是一次“小检”,重点检查之前查出的缺陷。这次在伯恩巴赫谷桥上进行的工作便是“小检”。
在德国,桥梁安全问题十分令人担忧。在高速公路和联邦主干道上,共有约39500座桥梁保证道路通畅,此外还有更小公路上的数万座桥,铁道上也有超过2.5万座桥。所有桥梁建筑中都有钢铁,比如起支撑作用的建筑构件或嵌入混凝土中的钢筋。一些桥梁存在大量缺陷,早已无法承受交通荷载。

尤其令交通规划师们担忧的是预应力混凝土制桥梁。在德国,高速公路和主干道上70%的桥梁面积都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施工工艺建成。建筑师们热爱这种似乎能摆脱重力限制的建筑方式,可以让房子高高耸立,也能在山谷和河流上大胆架构拱形结构。
预应力混凝土的稳定性更高,原因在于其中的钢丝和钢绞线。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大力扩建基础设施之时,道路建设者们还没有很好地掌握这种方法。他们使用了易腐钢筋,将桥梁尺寸定得太小,以至于很容易出现裂缝,水分渗入后就极易生锈,有些桥建完不到20年就不得不拆除或翻新。德国交通部已为桥梁的现代化和加固投入数十亿欧元资金,接下来还需要数十亿欧元。
萨尔兰线高速公路也诞生于预应力混凝土施工工艺应用初期,它将莱茵–鲁尔经济区和莱茵–美因大都会区连接起来,在山区路段穿过了大量山谷:从多特蒙德市到阿沙芬堡市的约260公里路程上,共有73座桥,平均每3.5公里就有一座。
伯恩巴赫谷桥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座箱梁桥,即车道下有钢铁或混凝土制成的长型中空桁架作为横梁:长191米、高24米,建于1971年。全德国范围内的《道路信息库——建筑》记录了每座桥的现状。对于阿斯拉尔市附近的这座山谷桥,则写着:双向行驶均不合格,缺陷数超过203处,包括裂缝、错位、中空、水分渗透……但这并不意味着伯恩巴赫谷桥随时可能倒塌,而只是在提醒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采取行动。

虽然已有记录,但常规管控仍然不能松懈。诺贝特·洛尔绑好攀登用绳索,站在工作台末端的升降梯里上升两米,正好来到箱梁下。在距离桥头四米处,洛尔手拿锤子不停地敲打,剥落的混凝土中很快就出现了生锈的钢筋。幸运的是,它们是工程师们所说的“松弛的钢筋”,即那些为加固混凝土而加入的钢筋,而不是会影响桥梁安全的“绷紧的钢筋”,所以还无需过于担心。如果桥梁稳定性受到威胁,工程师们就会立即封锁该路段。
洛尔用红色粉笔画圈,在桥上标记。47岁的阿奇姆·霍夫曼在所谓的“裂纹素描”中用短波浪线标记裸露在外的钢筋。这种素描是用带有地点和范围的缩写符号来记录建筑物缺陷。实际上,对于铁和钢来说,混凝土是完美的“不锈”环境——酸碱值高于12,和氨水相近。“在这样的强碱性环境中,钢筋不会生锈。”霍夫曼说。
但是,桥梁会老化,多种作用机制可能为铁锈的生成扫清障碍,比如碳化作用。几年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会越来越深入建筑材料中,一些成分之间会发生化学反应,酸性环境范围逐渐扩大。建筑工程师霍夫曼说:“如果酸碱值变成8,钢筋生锈将不可避免。而且,混凝土孔隙越多,碳化作用就越严重。”再加上水分,铁就会被腐蚀。水分会不可避免地通过细缝钻入,而对于伯恩巴赫谷桥这样的建筑来说,缝隙可真是太多了。
桥梁质检员们在箱梁下工作之时,桥上仍然车来车往。这里原本预计每天只过车3万辆,而现在每天要通过约6万辆车,其中超过20%是载重汽车,有的重达44吨。有数据表明,每辆载重汽车给桥梁造成的压力堪比2万到4万辆小轿车。更麻烦的是,此处的交通量还有不断上涨的趋势。
萨尔兰线高速路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山谷桥梁都朝北。“冬天必须撒防冻盐,才能保持道路的通车能力。”霍夫曼说,“而防冻盐是建筑钢材之大敌。”氯离子会通过缝隙和气孔向内渗入,在氧气和水分的共同作用下将金属侵蚀出洞。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即使内里已被铁锈大肆侵蚀,建筑表面却常常没有错位和裂痕,看不出损坏。
工作台缓慢开动,颠簸不停。桥体下20米处是穿过灌木丛蜿蜒流淌的伯恩巴赫河。对于这些建筑质检员来说,测量时首先要保证不会头昏眼花。在第一个桥墩后,米夏尔·赫尔德乘着小型升降梯上升,在离桥头58米处发现了一处空心点。为清除松动的建材,赫尔德使用了冲击电钻。“已经很不结实了。”他对同事喊道。碎屑不断掉落,现在这个洞已有20厘米深。赫尔德拍照记录下来。看起来很糟糕,赫尔德却还相对放松,这处损害位于桥梁拱形的边缘位置,对于桥梁的承载能力并不重要,虽然最好还是要修复一下。四小时后,三人结束了工作。第二天,他们还会检查桥梁的其他部分,追踪铁锈的踪迹。

| 铁锈的研究史 |
对我们来说,环境中氧气占比高达20%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并非从来如此。在远古时代,这种气体以自由态存在,含量非常微少。直到大约30亿年前——具体时间点还有争议,海洋中的蓝藻带来了新的物质交换方式:它们利用太阳能将二氧化碳转变为有机物,光合作用应运而生。作为此过程的副产品,氧气在空气中的含量越来越高。这种物质对当时占主导的生物有毒,但显然仍有生命战胜了这一危机,比如我们人类和其他所有依靠这种气体完成新陈代谢的生物。所以说,铁锈是我们能自由呼吸的代价。
全世界大量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艰难而持久地对抗着这种安静的毁灭者。他们寻找能抗氧化的新合金,在原子层面观察被腐蚀的金属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研发新的保护涂层和能早期识别出锈迹的探测器。

杜塞尔多夫马普研究所铁研究部门的科学家们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们的实验室位于一栋砖砌建筑中——尽管考虑到研究对象,似乎钢铁建筑才更合适。在这里,钢铁工人火花四溅的粗野世界和材料研究者们的精巧精确结合起来。在车间大厅,技术工人融合铁和钒、铬、钼或锰等元素,制造出新的合金。在实验室中,科学家们通过原子探头断层摄影观察金属内部,识别各种原子类型的排列方式,同时追踪这种无所不在的金属吞噬者的痕迹。一眼看去,铁锈的产生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潮湿的空气加上铁,就生成了氧化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锈”。“但是,如果更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铁和钢的锈蚀其实是一件更复杂的事情。”领导“腐蚀”工作小组的电化学家米夏尔·罗威尔德尔说。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铁锈层同时由铁和氧气的很多不同化合物以及所谓的“氢氧化物离子”构成。它们有着磁铁矿、针铁矿、纤铁矿等响当当的名号。“所有这些锈蚀产物的体积都比纯铁大数倍,而这让铁锈变得非常危险。”罗威尔德尔说。它会像生面团一样发酵膨胀,产生大量能量,可能让混凝土开裂。
此外,还有大量雨水和冷凝水渗入孔隙。罗威尔德尔解释道,潮湿和干燥阶段的转换决定了铁锈层的组成。它是一个多形式、可变化的对手,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基础设施。
然而,比起铁锈生成的细节,科学家们研究得更多的是防锈方法。一个经典的方法是镀锌。用数毫米厚的锌层来保护钢铁是一种传统的策略,因为锌比铁更便宜,也更容易和氧气、水分发生反应。就算锌层有了划痕,铁也不会被腐蚀,因为锌被氧化后产生的腐蚀产品会再次覆盖在划痕处。
一般来说,锌层上还会再加上另一个保护层,比如漆。在涂装时常常还会植入防腐蚀的物质,比如能在锌层受损时对之进行修复的磷酸锌。这种方法有个劣势:湿度会逐渐耗尽磷酸锌,哪怕其实根本没用上它们。为使磷酸锌在长期的损耗中也足量存在,必须在涂层中大量使用它们,因此它们也可能大量进入环境,造成不必要的环境负担,比如重金属污染。
罗威尔德尔表示,这一点必须变得更加智能。他们正在研发的保护膜能自主确定是否发生了腐蚀,只有真正發生腐蚀时才会释放有效物质。就像我们体内的修复大军——血小板和免疫细胞,只有身体受伤时,它们才会被激发。
在罗威尔德尔的实验室中,“开尔文探测器”正不停地测量电压,如果漆层下发生了腐蚀,电压值就会下降。研究者们在漆层中植入了智能“愈合物质”。它们被装入能感受到电压改变的小箱子中,必要时管道会打开,结束金属侵蚀的物质就会被释放出来。与此同时,马普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还在研究一种能重建受损漆层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实现了真正的‘自愈’。”罗威尔德尔说。
从汽车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钢铁守护者的努力是值得的。上世纪80年代,车厢底部的锈孔或行李舱盖的红色焦痂都还似乎不可避免,对于司机来说,会涂漆和用焊接机是必备的技能。而现在,汽车生产商担保其产品8年到30年不生锈。防锈策略很简单:完美的镀锌铁板和改良漆,避免出现水分汇集的设计,比如门上凹槽。至少在汽车上,这个红色的攻击者已经像只拔了牙的老虎,威风不再了。
| 美丽的铁锈 |
并非对每个人而言,铁锈都是可怕的幽灵,有些人十分喜爱这种红棕色的焦痂,认为它是高贵的象征,甚至用铁锈色为他们的汽车刷漆。
铁锈标志着过去,是活过的证明。和一个越来越被数字化、虚幻化主导的世界不同,这种未经加工的被侵蚀金属象征着冷酷的物质现实。而在每年迎来数万访客的弗尔克林根钢铁厂,这种感受达到了顶点,毁灭性和具有美感的铁锈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这里随处可见管道、升降机、炼铁炉、炼焦炉、大厅和作业台,色彩丰富亮眼:新鲜的锈斑呈橙色,待其老化,就会变成红棕色、棕色直至青紫色。访客们热爱这些色调,喜欢放松地在这里自由漫步。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弗尔克林根钢铁厂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86年,这家百年钢铁大厂停产,弗尔克林根人忍受着失业带来的沮丧和痛苦,希望能拆掉这个锈迹斑斑的庞然大物。如今,大批文物保护者们来到萨尔州学习如何改建和维护钢铁建筑。
58岁的建筑师兼城市规划师安得利亚斯·提姆自2009年起领导着弗尔克林根钢铁厂的文物建筑部门。他的办公室是曾经的炼铁炉办公室。提姆表示,铁锈有好歹之分,“好的铁锈是一层氧化膜,能够保护金属不受进一步攻击。坏的铁锈是会贮藏水分的‘酥皮锈’,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只要下雨,这种铁锈就会增加。”

世界教科文组织的要求让文物保护者们面临一个实际上无解的任务:完整而真实地维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维持这些铁锈的状态,但它们同时也可能毁掉一切。提姆知道,如果他毫不插手、绝不干涉,就会导致建筑物坍塌;如果他想完全维持原状,就必须放弃真实性。
这意味着什么?炼铁炉办公室旁边是炉料厅,以前储藏着1.2万吨原材料。提姆指向一根支柱说:“我们不得不切下一截,换上新的。”柱子被腐蚀得太厉害了,建筑物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但为了维持原样,他们仍然选择了和原先的化学成分尽量接近的钢铁作为替代物。
这位建筑师觉得自己有点像外科医生。他说:“为拯救病人的生命,外科医生有时必须冷酷无情,甚至很残忍,比如截掉病人的一条腿。”
在钢铁厂还生产时,锈蚀根本不成问题。炼铁炉、炼焦炉、热风炉的超高温让湿气无处藏匿,也就无法生出“坏锈”。到停产时,这个钢铁厂产出了数百万吨铁和钢。这种金属被作为钢梁用在建筑物中,作为金属线来围篱笆,作为钢盔在凡尔登的战壕中佩戴,也作为弹壳带来了死亡。它们中很多都走过了铁元素的经典道路:和地球环境接触,回到氧气的怀抱,重回本初,成为铁锈。

[編译自德国《地球》]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