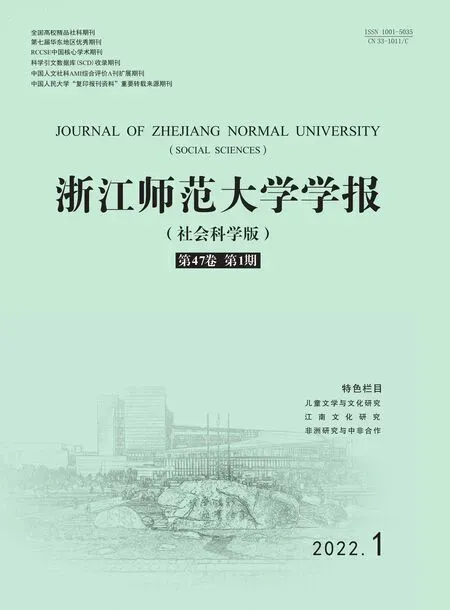幻想的张力与荒野的复归
——汤汤《绿珍珠》的童话美学探究
卫 栋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对于文学或儿童文学来说,“作品评判的尺度不应是‘教育意义’的理念,而应是情感,是自身的自然生发的审美情感”,[1]以艺术审美作为一种至高的享受,以文字传达作者内在的思想,引发读者对美的体悟,是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倡导的文学观念。周作人在《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出版后,重申其创作是“有意味的没有意思”,保留着儿童时代的心境,满足了儿童对于空想的需要。林格伦曾在访谈中表示“只有一个孩子能给我以灵感,那便是童年时代的我自己”,[2]她将自由、快乐、冒险等童年体验融入《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狮心兄弟》等作品的创作中,力图以细节的真实、情感的细腻来夯实童话大厦的根基。作为后起新秀,汤汤继“幻野故事簿”系列童话(《小青瞳》《空空空》《眼泪鱼》)后,完成了长篇童话《绿珍珠》的创作,她书写自然中灵动的万物生命,探寻不可预知的神秘力量,敞开心扉诉说一件件光怪陆离的奇遇。儿童读者能够在作品中发现自己的影子,并将其作为童年生活的延伸。
鉴于此,借助幻想的翅膀完成的具有现实力度的《绿珍珠》,为童话艺术的探索提出了新课题。汤汤一方面以大胆的想象创造出自由的幻想世界,另一方面又“以敏感的诗心,深挚的同情,在童话中对一系列严峻尖锐的现实问题,做出艺术回应”。[3]她用自然的笔触呈现出不同生命个体所坚守的立场,紧扣时代脉搏,言说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立足于童话“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旨趣。叶圣陶曾在创作《稻草人》时融入凄切的笔调,将灰暗的境遇隐藏在低声细语中,对人间的苦难予以冷静而深切的观照。关于这一点,郑振铎也曾指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的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加以防阻。”[4]
一、“二元”世界的阈限与融通
考察近年来汤汤发表的一系列奇幻作品,始终以现实人生为底色,对生活投以热切的关注。她的目光时常聚焦普通人不易察觉的角落,以轻盈的笔墨描摹世界,漫不经心间抵达人的心灵深处。这源自她厚实的生活积累,也与她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别去五厘米之外》以“童年禁忌”限定小妖的生活范围,《门牙阿上小传》以成长为题交代了牙齿阿上平凡的一生,汤汤笃行于“用平凡的事物为道具,开辟出全新的想象疆土”,[5]这些客观存在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体,被冠以童话的特征,赋予其存在的意义与独特的价值,并伴随故事的推进带给人新鲜感与趣味性。短篇童话《念念不忘》发表后,汤汤萌发出写作长篇的想法,她曾为新作题写了一句引子,“绿珍珠,是一眼泉,一片林,一座城的名字”,“绿珍珠”便具备了多重的象征意蕴。它既是绿嘀哩千百年来守护的美好家园,又是人类规划而建的新城市,两个看似独立的空间因一方的闯入而不断发生变化,暗含了作者对童话最初的设计与思考。尽管新作正式出版时省去了这句话,但其理念在作品中得到了延续。同时,作者借由幻想的力量完成对现实世界的观照,并以历时性的眼光审视了近代社会之变迁,重现历史之风貌。
应该说,幻想离不开现实因素的支撑,脱离现实的想象只能算作空想。刘绪源在《美与幼童》中针对想象的特征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其归根结底也是以现实参照物为基础的。因此,以丰沛、绮丽的幻想世界征服读者的《绿珍珠》显然不是一种撇开现实的凌空蹈虚的浅层文学。托尔金指出,“作者创造出一个‘第二世界’,让你的思想能够进入其中。在那里面,他所关联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它是按照那个世界自身的法则运作的。因此,当它存在,当你处在它的空间里,你就会相信它的真实性。而一旦怀疑在你心头悄然升起,魔咒就会被打破;魔法,或者说是艺术,就不得不面对它的失败”。[6]换言之,对作品“第二世界”的塑造需要具备源自现实“第一世界”某种因子,幻想只有依托这种因子才会真实可信。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中,其核心在于把握童话元素中内隐的“物性”。它应该是来自现实生活,在不违背物体合理性的前提下,被作者赋予了某种特别的能力。《大林与小林》中的狐狸平平因为吃惊,竖起的耳朵顶飞了帽子,帽子高高挂在了月亮上,狗皮皮告诉他等月圆之后帽子自然就掉下来了。这则童话的想象很大胆,却也遵循着一定的自然法则。同样,《绿珍珠》中由虚变实、进而延伸到四面八方的月光树林,也是因为过往收集了颗粒饱满的种子,种子在生根发芽后成长为参天大树,只不过这个过程被无限地加速了。诸如此类的形象在生成之时,也完成内部的重新建构,其优势“正如一切虚构的优点那样,在于重新创造,造成一件自然所没有但想必可以产生的新事物。我们称这些创造是滑稽和怪诞的,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背离了自然的可能性,而不是背离了内在的可能性”。[7]这种遵循着物的逻辑的再创造,拓宽了想象的疆域,也证实了童话的想象有其自身的限度。
对童话而言,如何打通现实与幻想的壁垒,实现两个世界的联结是尤为重要的。《绿珍珠》以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为契机,通过身份的转换完成了一次行之有效的尝试。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提出了“前阈限、阈限、后阈限”[8]三个阈限期,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阈限的观念。阈限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讲的过渡阶段,其特质在于新旧交替时的模糊性。处于阈限阶段的人不再是社会结构的服从者,而是进入一种反对的状态中,进而脱离原有的社会身份,促成社会结构的变化。新作中的幻想世界虽是超乎寻常的存在,但包含着人类对自然界最初的认识,而人与绿嘀哩之间所经历的对抗与和解,其实也见证了工业革命开始至今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从这一层面出发,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并把握两个世界的内在机制。在前阈限阶段,以绿珍珠林为代表的幻想世界与人类社会泾渭分明,绿嘀哩是悠长时间中自然的守护者,人类也对自然报以敬畏之心,二者各自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直到人类对自然实施大规模的改造,绿嘀哩才被迫放弃固守的家园。此时,人类逐渐从依附自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傲视自然。在阈限阶段,幻想世界中的绿嘀哩承受了失妹之痛,转而以此为契机破除现实社会的壁垒。自然环境的恶化使绿嘀哩丧失了栖居之地,自然也不再被动接受或服从人类的统治,顷刻间将城市变为废墟,人类先前的主导地位分崩瓦解。在阈限后阶段,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达成和解,以平等的姿态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空间。伴随着科学家童安与绿嘀哩间的互相谅解,人与自然之争才得以落幕。与此同时,它提醒着我们思考如何运用科学技术来换取社会的进步。而绿嘀哩在经历伤痛、报复、反思等一系列过程后,挣脱原有身份的束缚,最终融入新的体制中。这一阈限过程,有效打破了不同场域的界限,促使童话由想象向现实自然过渡。
在工业文明所主导的现代社会,人类的思维观念似乎步入一个怪圈。即凡是传统的、古老的事物都是落后与守旧的,凡是现代的、新生的事物都是进步与文明的。受上述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人类逐渐开始用蔑视自然的眼光来看待世间万物,由先前的万物崇拜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由此,打破了人与自然间的平衡状态,并在人类沙文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将自然与人类的命运割裂开来。当涉及这一严肃而深刻的话题时,汤汤将笔锋转向温情的一面,以“受害者”绿嘀哩的立场重述这段往事,使之更具客观性与真实性。这与童话本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有紧密的关联,也与作者对现代童话精神基底的思索与把握息息相关。汤汤深知,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盲目地追求技术进步并不能带来本质的变化,她借“绿婆婆”之口传达了一个简单而质朴的理念,“我们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守护着一些东西不变,这世界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才能长长久久”。[9]155由此看来,作者希冀以“不变”的法则,为人类社会寻找一种新的信仰。然而,“不变”只是相对的,绿嘀哩以人类的名字介入现实社会,实质上已经进行了一次视角的转化。绿嘀哩化身人类与“木木”的交往对话正是自然界强有力的一次发声,而“童话表现自然生态意识的优势在于,它的泛灵思维特征使作家的叙述得以自然地走入他者生命的意识和立场上,从而较为自如地完成相应的艺术表现”。[10]《绿珍珠》也并非个案,汤汤对生态问题的思索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她曾在《土土土》中因现代建筑替代远去的自然大地而感到忧虑,在《水妖喀喀莎》中因人类不能接纳其他生灵而感到无可奈何。她始终以亲历者的姿态靠近万物生灵,希冀通过平等的对话消弭二者的隔阂,进而达成和解。
透过这部童话,我们可以看到汤汤在寻求自然与人的平衡中做出的努力,这让人想起董宏猷的《鬼娃子》。两部作品都在讨论社会转型初期,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其幻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带有逼真的生活气息与时代的影子。对于董宏猷而言,这是他以宏阔的生命科学视角写作的一种尝试,也是他一贯所坚持的探索精神的印证。而汤汤有所不同,她更注重为两个世界搭建一座桥梁,通过遵循或利用规律等寻找问题的最优解。
二、童话艺术的赓续与创新
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能动的审美反映的产物。在思维定式、创作理念等因素的规限下,文学作品无不显露出创作者的个人气质与心性。在文学理论中,人们将一个作家在长期创作过程中逐渐习得的艺术惯性统称为艺术风格。艺术风格是读者及评论家对作家创作成就的肯定与勉励。概而论之,作家生产出来以供读者阅读消费的文本无不印刻着作家本人的独特的“徽记”与“指纹”。如果说,艺术风格指称的是文本中映现出来的经由作家本人提炼的高浓度的艺术结晶的话,那么,和艺术风格相对应的则是作家在创作中暴露出来的思维固化、才情枯竭等弊端。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有关文学作品“陌生化”的观点,对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的革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1世纪以来,童话的发展衍生出多元化的艺术格局,各种技法的尝试与运用也层出不穷。汤汤运用文学之笔创造出一系列散发着本土想象、极具个性魅力的童话佳作,可谓恰逢其时。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汤汤力图为读者提供观察生活的新视角。她的童话不是为了唤起读者的零星记忆,而是尝试打破长期附着在事物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刻板印象,对其进行重新的审视与定位,继而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她的作品融入了乡村式的生活体验与生命感受,对乡村图景的摹写成为其童话创作的鲜明风格,也因此积累了“陌生化”的文学基因。由“绿珍珠”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学意象更是汤汤大胆的文学尝试,孕育生命的“树脂球”、时隐时现的“长尾鸟”以及“绿血珠”不止一次出现在作品中,为文本注入新鲜的血液,使故事的走向更耐人寻味。
一般来说,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符号载体。作家一方面运用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来提升文本的艺术层级,另一方面将自我的文学理念投射到文本中以增添语言文字的魅力。张锦江在《儿童文学的高度》一文中提到,“作家的想象力只是第一度创作,而进入第二度创作需要用文字艺术地将想象说出来。许多作者仅仅停留在第一度创作上,因而出现了若干平庸的作品。语言的艺术魅力是第二度创作艺术升华的核心”。[11]换言之,儿童文学创作不能只停留在幻想阶段,要融入作家独特的语言风格与艺术技巧。汤汤对笔下的童话世界进行了创造性的演绎,如不久前入选澳门小学语文教材的《红点点绿点点》,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两只幼虫的趣味人生。在这之前,《青草国的鹅》《我很蓝》等作品也一直秉承“为儿童而写”的理念,使用的是属于儿童自己的语言风格。朱自强认为“作品的语言越是自然朴素,越是能产生真正的文学效果”。[12]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事雕琢,以平淡、自然的语言风格贯穿整部作品的《绿珍珠》给儿童带来了浅语的艺术呈现。“一群绿嘀哩,住在树林里。太阳下,月亮里,风里和雨里。天空下,大地里,悠长的时间里。一群绿嘀哩,守护在树林里”,[9]24-26诸如“绿嘀哩之歌”的语言在作品中随处可见,浅近有趣的语言拉近了作者与儿童读者的距离,也避免了常规的说教意味,更具可读性。此外,作品有效地利用语言的简单纯粹强化了叙述的效果。在计划利用人类朋友实现妹妹的重生时,“我的心迟疑着,不安着,像微小的风儿不知往哪边吹”,[9]71这是绿嘀哩“蓬蓬”心底的温柔;而当整个城市被青冈树的树根包围时,根须“朝四面八方匍匐前行,遇到裂缝,遇到泥土,就哧溜溜地钻了下去”,[9]88轻盈的语言舒缓了现实的紧张与沉重,却不经意地牵动着读者的神经。
重视并致力于铺展作品的格局,以期在更为广阔的视域下展示新旧空间的交替,是汤汤新作又一值得深究的艺术经验。全篇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绿嘀哩的诞生、成长与其后生存处境;二是人类与绿嘀哩的交流、对抗与和解。两条线索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张力,绿嘀哩群体的与世无争与“念念”执着的复仇心理互相牵制,绿嘀哩与人类之间信任关系也不时地犹疑徘徊,伴随绿珍珠林从有到无、从无到有的这一历程,童话的层次感愈加鲜明。与此同时,双重线索叙事在文本中构成某种疏离性策略,这一方面增添了读者在文本接受过程中的陌生化感受,使作品的空间维度得以延展,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格局与美学层级。无论是绿嘀哩幻化为人融入现实生活,还是人类利用科技强行揭开精灵的奥秘,这一过程时刻牵动着儿童的心绪,并能有效地破除人与精灵间不易抹平的神秘性与距离感,其“巧妙地利用了儿童‘主客不分’、‘物我同一’的心理特征,创造出一种真实感很强的童话意境,满足了儿童现实与幻想彼此不分的混沌性审美理想的愿望”。[13]此外,作者有意识地临摹大自然的风貌,由精灵之眼窥见自然界最细微的变化,拓展了这一视域的空间内涵。从绿珍珠林的重现到绿珍珠泉的复苏,这一过程的变化隐伏着汤汤个人审美认识与审美情感的双重考量,在作品中也呈现出多元共生的艺术格局。
汤汤在立足于现实基础上将幻想因子漫漶开来之余,将童话艺术的终极指向对准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异化与戕害,由此而来的创伤叙事构成了她童话创作的艺术表征。该童话中一场声势浩大的灾难毁灭了新兴的城市,给人类带来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创伤带给亲历者的焦虑与恐惧是无法言说的,因此他们常常选择沉默。从废墟走出来的女孩“木木”失魂落魄,一连数日不说一个字,面对热情的同学、慈爱的爷爷,她一直在逃避。表面看来这与她受到欺骗密切相关,但实质上是人类普遍命运的表征。科学家童安没有洞悉其创伤的根由,因此并不能为她疗伤;爷爷深刻反思过去的错误并顺利打开她的心结,最终实现了真正的疗愈。作者以理性的视角重审现代社会中的创伤,并将创伤的成因与治愈过程贯穿到童话创作中,使之更具现实意义。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认为,伴随着高速现代化而迈向现代文明的现代社会,生存其间的人类在不知不觉间丧失掉感性的生活认知,取而代之的是由现代工业文明支配下派生而来的僵硬、机械、冷酷的生活态度与心灵感知,人类也会因此受到伤害。无独有偶,在短篇童话《木疙瘩山的岩》中,汤汤也不露声色地道出了无言的伤痛。“岩”作为鬼的形象出现在人类“我”的生活中,“我”把他看作是最要好的朋友,并拜访了他的家人朋友。在得知真相后,“我”的家人将其视为利益交换的筹码,为满足物质需求而牺牲了“岩”。这则童话很简短,但仅仅是“牙齿咬得‘咯咯’响”这一意象,便足以令人体会到“我”的心灵创伤。成人没有对儿童进行正确的引导示范,反而以欺骗的手段迫使儿童服从,带给其难以抚平的成长之痛。儿童是未来的成人,而童年的创伤会以何种姿态出现在成人社会中,又将如何影响现代文明的发展?
故事结尾处绿嘀哩对人类所持的怀疑态度无疑是作家本人透过绿嘀哩对其自身在未来生存境遇中未知命运的隐性表达。汤汤将流动不居的时空交汇于此,使广延性的空间在绵延性的时间长河中获得一段可以触摸的实感。绿嘀哩的惶惑与焦虑折射出《绿珍珠》开放式结尾所蕴含的某种形而上的严肃思考。
三、“荒野文化”的复归与延拓
周作人曾在《童话研究》中写道:“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14]从民间口传文学到佩罗童话,再到格林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童话在其自身的艺术演变历程中无不蕴含着早期人类的生活经验与人生理想。从儿童发生学角度来看,和成人相比,处于低龄期的儿童受社会经验、生存能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成人的规约与指引。随着人类生理机能的不断演进,儿童“生理的感觉、心理的意识、文化的审美”[15]等文学接受水平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对成人作家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究竟以何种方式将有关人生哲理、价值取向等教育内涵传递给儿童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作家就一定要俯就“儿童水平”,一味向下迎合处于“低级状态”儿童的趣味。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是时代精神与自我内在精神的现实投射,成人身份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强作品的魅力。成人将丰富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智慧投射到未来的作品中,书写儿童未曾经历过的人生境遇,使得作品具备了吸引儿童读者的独特观念与思维视角,可以满足儿童“向上”的精神渴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得创作主体只能是成人而非儿童,然而由于二者“代际”的“非同一性”,使得“无论成人作家如何‘俯就’于儿童、体验‘童年’,都无法完全消弭这种代际的隔膜”。[16]外国儿童文学界早已对上述现象进行过探讨,有研究者提出儿童文学作品中由作家塑造的“幻象儿童”与现实儿童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磨灭的文化鸿沟。究其原因,乃是由于成人作家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完全是成人权力话语对儿童读者的压制与灌输,现实儿童被动接受成人强加给他们的意识形态。由此,造成了儿童文学作品疏离现实儿童读者的悖论现象。基于此,如何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尽量消弭、填补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文化裂痕就成了亟须解决的理论难题。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斯蒂芬斯指出,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之初,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已化作无意识内容深藏于心。他进一步指出儿童文学始终囊括五种意识形态图式,其中之一便是在承认健全人格的基础上对人类健康情感的维护与培养,最终指向的是一种非唯我论的、利他的人格精神取向。
从上述观点来看,汤汤的童话作品也暗含着某些预设的意识形态,她在创作手记中曾谈到自己在平衡幻想与现实的同时,“努力找到平常和神奇的共通点,这共通点就是所有生命最真实的情感、最真挚的悲喜和渴望,还有最珍贵的爱,以及对生命和世界本质不竭的探索”。[17]在她看来,儿童文学创作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作品审美功能的把握及儿童心灵的建构。汤汤在触及社会生活的话题时往往会进行深入思考与判断,秉持自己的价值立场,表现出浓厚的现实关怀。上文提到,《绿珍珠》是围绕着两条叙述线索铺展开来的。在绿嘀哩生活的幻想之境中,“蓬蓬”是树林中最年轻的绿嘀哩,她小心地守护着孕育生命的树脂球,在与毛毛虫、鸟儿的斗争中迎来了妹妹“啾啾”,于是教她唱歌,带她洗澡,为她准备漂亮的衣服,一起问候花草与野兽。灵动的画面配以新奇的想象,作者借绿嘀哩的生命体验将爱与善良等情感传达给儿童读者,并提醒他们注意珍惜与呵护。而在人类生活的现实之境中,“木木”是普通的人类小孩,她有体贴的父母,善解人意的朋友,却不知不觉陷入巨大的危机中,社会的发展无形中带给她深深的伤痛。作者讲述的是当下正在发生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故事,指出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裂痕,并试图探索弥合裂痕的路径。此外,汤汤在作品中从不回避关乎救赎、原谅、接纳等一系列的重大议题,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来丰富儿童文学的内涵。这一点在汤汤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枫香树上小路的眼》中的“我”让朋友小路去买糖葫芦,致使他意外发生了车祸,为了逃避责任,“我”对小路的父母撒了谎,因此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但以鬼魂形象出现的小路却并没有报复“我”,而是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积极开导“我”,使“我”鼓足生活的勇气。《哪怕是只丑丑猪》则关注于当下的家庭教育问题,由于父爱长期缺席,母亲又喜欢盲目攀比,“你真是笨猪”这句口头禅伴随着女儿的童年生活,又一语成谶酿成一场悲剧。母亲从这次变故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付出极大的努力去挽回。尽管作品并没有给出圆满的结局,但女儿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爱与关注。儿童在成长中面对重大变故之际将作出何种抉择?儿童在遭受创伤后的未来走向如何?是选择疼痛记忆还是进行自我释怀?对于此类问题,汤汤的探索历程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并不是标准答案。
必须指出的是,儿童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存在着一个“度”的问题,作家如何使既有文本在顺应儿童接受能力之余,又能适当的予以提升与拔高?吴其南在《儿童文学》中指出,文学接受是一种对话,读者通过选择与再创造进入到作者的文本中,并结合自己的主观意识建立起新的认识。但文学对话不同于日常对话,它不是简单的问答,作者也不需要对读者的意见做出回应,而是将潜在的想法凝练到作品中,建立起一种“交互共鸣的对话关系”。[18]现象学文论家英伽登认为,作家在创作和生产文本之余已将诸多潜在空白和不定点安插其间,读者在进行文本接受的过程中,如何进行填补与阐释则构成了读者文学接受的旨趣。进一步说,英伽登在其文论中所提出的读者对文本中某些“形而上质”的理会与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凭读者对文本空白的个人化阐释,“通过自己的想象机能和理解机能重建文本的艺术世界”,[19]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个人的文学审美体验与阅读快感。实质上,作者追求的艺术性与读者的接受度是密切关联的,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潜在读者的抗拒与排斥,而读者也渴望通过作品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就实际创作而言,汤汤所秉持的有关爱与美的文学信念与审美理想,不仅在文本中以游戏精神的方式化繁就简、举重若轻,而且从不轻视儿童读者的文学接受能力,而是将现代性衍生而来的诸多弊病有限度地呈现给儿童读者,立足于原始文明的文化立场为诊治现代文明病开出了有效的药方。
首先,汤汤的童话创作自觉融入了富有游戏精神的艺术气质,体现出儿童文学真正的美学价值。游戏始终伴随儿童的成长,他们的自我意识在游戏中萌发。一直以来,汤汤的童话文本始终流动着自由的气息,以旷野为蓝本的童年书写带给儿童内心的释放与反省。《再见,树耳》开篇是女孩土豆与同伴进行的“大胆”游戏,她对面前的树林既感到恐惧,又充满好奇。在冒险精神的驱动下,她独自一人进入了“鬼叫林”。这一过程虽然让土豆感到不安,但她也因此找到了树耳生活的地方。有趣、好玩只是游戏的外在特征,对自由的追求、生命的尊重才是游戏的内在精神。《小野兽学堂》将课堂搬进了大山深处废弃的百谷村,它不同于一般的学校,前来听课的学生都是小野兽变化而来的,而教师老麦以平等、开放的姿态接纳每一位学生。游走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小野兽”并没有过多地沉溺于身份的追问中,而是在老麦的鼓舞下摆脱世俗的羁绊,释放其蓬勃的生命力。在《绿珍珠》中,从“月光之树”到“月光树林”的延续,童年的游戏精神传递出希望的力量,并冲破了现实的禁锢,实现了自然与人类的双重治愈。在这一过程中,看似不着边际的游戏,实则深埋了信念的种子,从而牵引着绿嘀哩一路成长,也增强了故事的穿透力。
其次,汤汤有意识地将童话作品回归到原始文明中去,继而对现代文明中的某些负能量进行有力的反拨。从文化学上说,人类早期发展阶段的文化属于“荒野文化”,现代人的文化则属于“园艺文化”,两者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是相对立的文化类型。前者散发出来的原始气息无不弥漫着一种自然、朴素、不事雕琢的本真,而后者虽是经过现代文明精心装饰的高级产物,却在某些情况下失却了真实色彩。伴随着经济飞速增长,现代社会衍生出诸多负面问题,譬如消费主义至上、自然生态的污染、人的精神异化及人性扭曲等。可以说,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上述问题对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汤汤将世俗的喧闹融化在自己的涓涓细流中,以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将人们带回到过去。精灵在汤汤童话中的高频次显现,一方面是作家借助精灵这一古老的文化符号同传统相勾连,另一方面是她在面对由理性思潮统治下的现代世界时,将精灵的复活与登场作为从“祛魅”走向“复魅”的重要标志,以此来舒缓现代人的心灵焦虑和精神颓丧。故而,以精灵为切入点创作而来的《绿珍珠》,则为原始文明的复归营造了氛围感。童话中闪着微光的树脂球、嘀哩嘀哩的歌声、古老的清泉,让人无不惊叹精灵家园的澄澈与美好。从故事时间上看,人类对珍珠泉的祝福发生在城市消失之后。这恰恰证实,童话在尚未对两种文化进行定位时,人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回归荒野的可贵。
汤汤在《绿珍珠》中冠之以爱、同情、理解等价值要素,其实质是对儿童读者阅读能力与文学水平的一种肯定与信任。从某种程度上讲,优秀的儿童文学是超越民族与疆界的世界文学。保罗·阿扎尔在《书,儿童与成人》中指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部分儿童文学作品因其具有共通性而成为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佳作。譬如,德国儿童文学作家詹姆斯·克吕斯的《出卖笑的孩子》以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为切入口,对人在金钱面前究竟该择取何种价值进行探讨,并带有神秘色彩和哲理气息。朱自强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中提到,世界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都具备一个鲜明的共性特征,那就是文本中透露出来的对人世间的爱与情感,温情色调乃是经典儿童文学的主色调。儿童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希望,他们的童年体验会伴随自己的一生,继而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发展。作为接受主体的儿童处于成长阶段,其本身具有可塑性与变动性。儿童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只是在生活阅历与阅读经验方面存在不足,而经验的缺失可以通过后天的锻炼来补足。朱自强同时指出经典的儿童文学大抵是一个类似于同心圆的模式,儿童生命中的纯真、善良与成人生命中的经验、阅历相互补充,构成完满的生命价值。在这里,“童年书写并不局限于时间层面的贯通,还包含了成人与儿童主体转换及沟通等命题”,[20]成人的生命价值具有浓缩、升华人生经验的重要功用,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儿童读者的启蒙者、陪伴者和守护者,不能因儿童人生经验匮乏而轻视他们,甚至排拒宏大主题进入到儿童视野。正如班马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中提出的“儿童反儿童化”“以大为美”等美学理念,这些理念既是对以往成规的创作观念的突破,又为某些被人冠之以“禁忌”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提供了理论支撑。按照班马的观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并不拒斥成人读者,恰恰是读者的两栖性证实了其经得起历史试金石的检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运用反刍式的接受,“儿童文学的阅读,是有着一种日后际遇的”,在顺应儿童读者接受能力基础上进行一定限度的阅读拔高也是无可厚非的。这类符合儿童审美旨趣与接受习惯的作品拓宽了儿童阅读的疆域,并对创作者提出新的要求,也即“儿童的阅读行为,以及儿童文学的接受现象,是开放的儿童文学审美功能有可能得以实现和超越的一个重要基础”。[21]如果说,有关儿童文学读者接受方面的理论话题还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黑箱与谜题,那么,在儿童文学的实际创作中,作家已经将儿童读者接受之维进行了有意义的彰显。
从童话大师安徒生开创的艺术童话开始,童话这一古老而又现代的文体便一直散发着自身的艺术魅力。在外国儿童文学界,对世界经典童话的改编掀起了一股后现代儿童文学的艺术浪潮。事实上,无论童话的外在形式如何更新,其内在的价值观念与艺术内涵仍与传统童话之间保持着斩不断的密切关联。汤汤童话艺术王国中内蕴着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的艰难探索,既有对幻想世界的巧思,又体现出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关怀。同时,新作还关注童年个体在遭遇重大打击后的心灵疗愈,将儿童无法言说的创伤放置于家庭与社会的矛盾之中,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作家融入了以儿童为本位的精神品格,指引儿童在困境中追寻精神力量。由此,从人文关怀的立场出发,汤汤童话与传统童话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两者在这一层面上实现了超时空对话。我们也应意识到,童心是超乎国界的存在,但在国际上还缺少对纷繁热闹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关注与讨论,如何跨越不同国别、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来实现作家的理念传递,这是包括汤汤在内的新一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者的艺术责任与文学使命。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