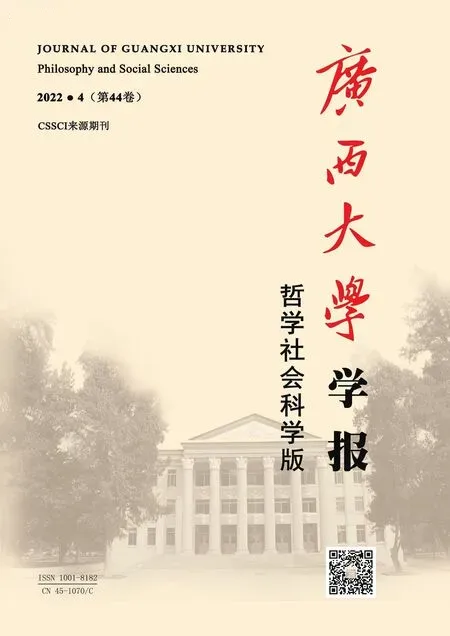德国启蒙运动中的“表现主义”
——对查尔斯·泰勒观点的述论
宋宁刚
加拿大思想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深湛厚重的著作《自我的根源》(1989)中,深入西方从柏拉图到现代主义两千多年的思想史,探寻“主体”(subject)尤其是“现代主体”(modern subject)也即“自我”(self)产生的源头,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变化。在此追究的过程中,他问: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是如何发生的?如此探讨,其初衷是对现代以来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对“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忧虑。因为在他看来,眼下的道德哲学,尤其是英语世界的道德哲学,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怎样做是正确的,而不是怎样生存才是善的”,同时也倾向于“界定责任的内容,而不是善良生活的本性”。①[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3页。参照Taylor C.,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中文略有改动。下同。
一、“现代自我”的产生
泰勒认为,远在柏拉图那里,就有“自我”的问题,它体现为“自制”(self-mastery)。只不过,“自制”是人“通过思想或理性所获得的东西”。②[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第150页。Taylor C.,Sources of the Self,p.115.直到宗教复兴运动以后,才出现真正的“断裂”(fractured)。虽然宗教复兴运动本身也给予了感情以重要性,但18 世纪初以来对自然的新的热爱以及对感受性的推崇,才显示了某些重要的特点。于是,启蒙运动就成了泰勒关注的重点,因为正是在这场思想运动中,才发生了上述人的自我认知的“断裂”。③[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第386-432页。Taylor C.,Sources of the Self,pp.285-320.在对启蒙运动的关注中,泰勒又尤其关注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激进”(radical)态度,以及德国思想家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性推动这两个问题。
其实在《自我的根源》之前,泰勒在《黑格尔》(1977)一书中已对这一思想历程做过讨论。在那里,他也认为现代自我的观念自17 世纪后才真正产生。这种现代自我与之前的主体的区别在于,“现代主体是自我规定的,而按照以前的观点,主体是在同宇宙秩序的关系中得到规定的”。①[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7页。来自古代的主导传统(柏拉图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主体观是,当一个人同某个宇宙秩序打交道时,当他以最适当的方式把它作为理念秩序,通过他的理性来探讨时,人最圆满地完成了自身。据此观点,在宇宙秩序缺席的情况下,换言之,在对宇宙秩序一无所知或与之不发生关联的情况下,自我呈现或主体观念便无意义。所以泰勒说,在那里“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观念”,也即“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同一性观念,我可以替自己规定那个自我、那个同一性,而不涉及我周围的各种情况以及我所在的世界”。②[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8页。
泰勒正确地指出,向自我规定之主体的现代转向是与“对世界的控制……的含义联系在一起的”,也即“现代确定性断定:世界不是一个文本、一个意义实体,这种确定性不是以世界的令人困惑的不可捉摸性为根据而确立起来的,相反,是通过清晰的数学推理,再加上后来日益增加的多重控制,它随着人们对事物规则的把握而得到了加强。这就是最终被确立起来的作为一个中立的、偶然关联的场所的世界图画”。③[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9页。泰勒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导致的哲学观念的变化指向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时代。虽然他也承认,这种转变只触动了17 世纪欧洲少数人,但他认为,那时现代主体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此后,随着新教信仰的衰落,世俗化了的世界尤其有助于培养与其相应的人的主体性。
泰勒用了几个词来表述这个变化:在谈到世界时,他用韦伯的术语“祛魅的”(disenchanted);在谈到宗教发展时,用“世俗化了的(desacralized)”;④后来,泰勒也用另一个术语secular表示世俗/世俗性。见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中译本见[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张容南、盛韵、刘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在论及对固有的意义世界之否定时,他用“对象化了的(objected)”。⑤[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2页。这里的“对象化”是指“世界将被看作是实体化了的意义的世界”,“意义和意图范畴只能应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却无助于他们对世界的思考和活动”,也无助于他在世界中的实践。同时,“对象化”(objectify)这个术语也道出了与新的主体性相对应的一个新的、现代的客观性观念。但是,这种客观性所指并非仅仅外在的自然,也包括作为自然中的对象之一的人,虽然他同时也是知识的主体。
因此,新科学或者说现代科学,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培养了一种机械的、同质的、原子论的、以偶然性为根据去实现人的样式,特别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如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以及英国的孔多塞和边沁等人那里。于是,启蒙运动时代产生了一种“人类学”(anthropology),也即对人的新理解,它把两个观念混合:“第一,与新的客观性相对应的自我规定的主体性观念;第二,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因此完全受这种客观性支配的人的观念。”⑥[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3页。这两方面并不总是协调的。尽管如此,这种混合的紧张还是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观点。也正是这两个基本观点,构成了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对法国启蒙运动的集中批判。它们也成为德国和法国启蒙思想最大的分歧。
二、德国“表现主义”的两种表现
18 世纪的自然神论反映了自我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新意义。这种自然神论在德国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形式,泰勒称之为“莱布尼茨体系的形式”:“莱布尼茨的确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宇宙秩序。在那里,最后的解释是根据终极原因作出的,即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不过秩序是由诸存在、诸单子构成的。”他不仅指出,“那些单子是自我发展的”,而且认为“在现代意义上,它们实际上就是主体”。①[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6页。
泰勒认为,这种自然神论的新变体使德国发展出了一种“后启蒙运动的风气”(post-Enlightenment climate),②[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7页。参照Taylor C.,Hegel,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3.中文略有改动。下同。它融合了法国启蒙运动的许多因素,同时又对它的一些主题提出了批评。其表现在思想上,有两种倾向:批评的思想与艺术的思想。前者集中在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后者集中在对艺术的肯定,目的是通过艺术对人有新的理解乃至新的自我认定,在相当程度上即是后来“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③张瑞臣:《论查尔斯·泰勒“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哲学动态》2021年第5期。
(一)何谓“表现”?
在泰勒的论域中,批评的思想表现于18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狂飙突进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狂飙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批评家赫尔德。赫尔德反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将人性“对象化”,反对把人的精神分解为不同的官能、把人瓜分为肉体和灵魂,也反对脱离情感和意志的精细的理性观念。他主张发展另一种关注“表现”(expression)的人类学。
这里的“表现”,泰勒承认来自以赛亚·伯林,并指出它“必然是一个艺术术语”,但不能与20 世纪的表现主义运动相混同。④[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7页。Taylor C.,Hegel,p.14.正如伯林所论,他对这个术语的使用“采纳了它最宽广、最一般的含义,并不特指20 世纪前几十年的表现主义画家、作家和作曲家”。⑤[英]以赛亚·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郑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在长文《赫尔德和启蒙运动》中,伯林用“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这一术语概括赫尔德的三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贡献之一(其他两个术语为:民粹主义、多元主义)。对于“表现主义”的基本内涵,伯林指出:“(表现主义)这种学说主张一般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艺术)表现了个体或群体的完整个性,人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也就能够对它们理解到什么程度。”更特别的是,“表现主义宣称:人类的所有作品……无论美丑或趣味与否,都不是与它们的创造者分离的客体,它们都是人们之间活生生的交流过程的一部分,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外在观察者不能像科学家(或任何不接受泛神论或神秘主义的人)看待自然客体那样,用冷漠而不带感情的视角来看待它们”。⑥[英]以赛亚·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郑想译,第187-188页。
对于泰勒,“表现”的核心观念则是“人的活动和人的生活被看作各种表现”。首先,他把“表现”作为“表现所呈现的一个理念”来谈论,用这个术语“谈论我们在言说中表达的思想”;其次,他把“表现”作为“意义的赋予活动”来谈论,把它作为“它在外在现实中实现了我们感觉和欲望的某物”。⑦[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8页。Taylor C.,Hegel,p.14.在后一层含义里,被表达的不仅是“主体”,而且是“主体的状态,或者与主体相似的最小单位的生命形式”。更多地在后一层意义上,他说,“新的人类学的核心观念是作为表现的人的活动或生命”。在这种对人的新理解中,人的生命被更多地看成是一种表现,“一个意图的实现,就这个意图不是终极盲目的而言,一个人可以谈论某个理念的这种实现”。这种实现,也可以被看作“自我的实现”。而自我实现(也即适当的人类生活)“不只是确定地独立于实现它的主体的某个理念或筹划的完成”,相反,这种生活还必须具有“附加的维度,主体可以承认它是他自身的生活,承认它从他自身内部得到展示”。⑧[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9页。Taylor C.,Hegel,p.15.
(二)批评的思想
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一种适当的人的生活只有在“我是一个人,这是我的生活”的前提下才是“我自己”(my own),也即生活首先是“某个形式的实现”,人的生活必须首先是属人的,然后才是属我的。属人的生活来自人们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人的观念及其生活方式。到了赫尔德及其表现主义的追随者这里,人类学“增加了这种划时代的要求,即我的人类本质的实现是我自己,并因此提出了这样的理念:每个个体都有自己成为人的方式,它不会以失真和自残(distortion and self-mutilation)为代价,以换得他人的期望(的满足)”。①[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9页。Taylor C.,Hegel,p.15.在此,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翻转。对于后者,首先是符合自己的观念,成为自己,而不是作为普遍的人(类);亚里士多德的命题“成为人、然后成为我自己”被颠倒为“成为我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成为人的方式”,“一个人的适当的行为具体表现为自由主体性的观念”。②[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20页。粗体为原文所有。下同。Taylor C.,Hegel,p.15.这里的“观念”(Idee,Idea),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近代哲学中通常称作“理念”,虽然同为Idee(Idea),却与现代哲学中的意涵不同。如此区分的前提是,近代对人的理解与马克思以来的现代对人的理解不同。在崇尚理性的近代哲学中,将人看作“理性的主体”“理念的主体”;在以物质世界为前提的现代哲学中,将人理解为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主体。成为人(类、并符合类)的问题,即使没有被完全取消或者否认,也在相当程度上被“遮蔽”或回避。
这种颠倒,带来了诸多变化。首先,“实现人的形式”包含着一种内在力量——把它自身注入外在现实中,即使与外在障碍相对抗。亚里士多德哲学把人的成长与发展以及人的形式的实现看作从不断受到紊乱和不和谐威胁向着秩序和平衡趋近。“表现主义”者们则更进一步,把这种发展看作“对于一种内在力量的证明,后者竭力实现和维持自身的形态,抵制周围世界强加于它的那些形态”。如此一来,理念的实现过程不仅是一个与理念相一致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被内在地创造的过程。泰勒指认了卢梭和莱布尼茨在这种理论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卢梭“把善与恶的传统对立重新解释为依赖自身和依赖他者的现代对立”,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则“是自我展示的主体观念的胚胎”。③[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19-20页。Taylor C.,Hegel,p.15.此处,泰勒对于卢梭的论述,似乎对后者的思想前提,即神学统治的背景缺乏足够考虑。而卢梭的贡献正在于,使人不再依赖于神,从而奠定了人在大地上居住的尊严。人不再依靠神,而是依赖自身,自己奠定自己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人是毫无凭借的,可以任意妄为。相反,它要求人回归自然,回归自身的本性(nature,也即自然)。这个“本性”与近代对人的基本理解相关,最直接的联系,即康德的作为“实践理性主体”的人。
其次,相比亚里士多德观念下的自我展示,新的表现观念附加了新内容,即“一个形式的实现澄清或决定了那个形式是什么东西”。④[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20页。Taylor C.,Hegel,p.16.也就是说,一种先定的观念(我是一个人,这是适合我的生活;形式预先决定了形式的不同方式,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的实现)变成了生成的观念(实现本身决定了形式是什么样)。因此对“表现主义”者而言,“一个主体之最充分、最令人信服的表现,是他既明确了他的意图,又实现了他的意图的时候”。它以另一种方式显示了表现主义的新样式与亚里士多德传统间的重要差别:“对于前者来说,人所实现的理念不是完全事先决定的;它只有在被完成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完全的确定。”⑤[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21页。Taylor C.,Hegel,p.16.这就无限伸张了人的主观可能性,也使人的生活显得空前得体、具有尊严。正是“在如此得体的生存过程中,自我不仅完成了自身的人性,而且澄清了自我的人性所涉及的意义。……这种表现主义理论放弃了在意义与存在之间的启蒙二分法,至少在人类生活被涉及的那些方面。人既是生命的事实,又是意义的表现;它的存在表现并不归结为与某个他物相关的一种主观关系,它表现了它所实现的理念”。⑥[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22页。Taylor C.,Hegel,p.17.这样,它就对传统的人的观念——人是理性的动物、其本质是理性意识的存在,做出了新的解释。在“表现主义”的批评性继承(或创造)里,传统观念被更新:人通过表现他的所是,澄清了他的所是,在此表现中承认自身而逐渐了解自身。通过表现,人的生命的特殊属性将在自我意识中达到顶峰。
从以上也可看出,所谓德国“表现主义”的批评思想,是通过对传统的翻转和颠倒带来对人性的释放。
(三)艺术的思想
泰勒把上述与传统的理解不同、同时又作为对近代机械论之反拨的对人的新理解称为“表现主义”。这种从德国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表现主义,坚决地放弃了现代科学对自然的对象化,至少在涉及人性的领域是如此。“在把人的生命看作表现的过程中,它反对意义和存在的二分法;它再次引入了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原因和整体论概念。”①[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22页。Taylor C.,Hegel,p.17.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典型的现代特征,因为它融入了某个自我规定的主体性理念。它的本质实现是主体的自我实现;因此它不是根据与某个彼岸理念秩序的关系(比如人与上帝的关系)来规定自身,而是根据从它自身中展示出来的某物来规定自身。后者是前者的实现,是在那个实现过程中第一次重大的创造。②[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22-23页。Taylor C.,Hegel,pp.17-18.泰勒将“表现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直指卢梭、赫尔德以及后来的德国浪漫派。因为对他们来说,近代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二元论的看法破坏了事物的统一,“在那个统一中,自然原本是思想和意志的愿望与动力。自然为意志提供蓝图是不够的,自然的声音还必须通过意志来说出”。③[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30页。Taylor C.,Hegel,p.23.这个声音在康德尤其在席勒那里,就是通过艺术教养来实现人的完整性。
泰勒认为,这是为18 世纪末欧洲革命奠定基础的关键理念之一,也是此后成长起来的现代文明的根本理念之一。在此观念更迭中,艺术为表现主义思想家提供了必需的范式,因为“艺术对象被理解为某些事物的表现,那些对象除了自身之外并不必然地有所推论”,④[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23页。Taylor C.,Hegel,p.18.它的表现就是它自身,就是它的周延和具体。如此,人就不仅是个体生命的存在,也是具有表现活力的存在。使人具有表现力的是语言和艺术,它们不仅为作为表现之人的生命提供了存在样式,也成为一些特许的中介,正是通过它们,表现才得以实现。因此,新的语言理论、对艺术的新理解,以及对它们的中心地位的新理解,贯穿于赫尔德、狂飙运动的作者们和后来“浪漫派”的作品中。这就是批评的思想之外的另一种,也即艺术的思想。
这种关于艺术的思想,在伯林看来,即“人类的所有作品……都是人们之间活生生的交流过程的一部分,它们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外在观察者不能像科学家看待自然客体那样,用冷漠而不带感情的视角来看待它们。如果这种观点更进一步,那么人类自我表现的每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艺术的,自我表现是人类自身本质的一部分”。⑤[英]以赛亚·伯林:《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马寅卯、郑想译,第187-188页这种艺术理想针对的是18 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以亚里士多德模仿说为基础的艺术观,它在当时的最新变体,是法国思想家——尤其爱尔维修、拉美特利等人的思想。面对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及其继承者,表现主义者不得不创造自己的范式,即一种作为表现的艺术理论,一种意义理论,在其中,语言的意义和符号的意义脱离了意义的其他形式便无法得到明确的指示。具体来说,“当艺术被理解为基本上是一种对实在的模仿时,它可以按照被描绘的实在,或者按照描绘方式来定义。但是,在18 世纪里出现了那些主观转向中的另一个……艺术与美的特殊性不再按照实在或其描绘方式来定义,而是通过它们在我们身上激起的种种感觉,一种特殊的、有异于道德或他种愉快的感觉来辨别”。⑥[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9-100页。
虽然一如前文所提及的,泰勒和伯林都表示,他们所称的“表现主义”与20 世纪的表现主义艺术的概念不同,也与影响广泛的表现主义艺术运动无关,但从此处,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两者间的某种亲缘:它们都是“按照创造来理解艺术,而不再主要用模仿——对客观实在的模仿——来定义它”;它们分享着同一个范式,同一种对艺术之根本的理解,如泰勒所论,“当我,作为艺术家,通过我的作品,通过我所创造的东西,来发现我自己的时候,这个情形已经成为我们的范式”。⑦[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第97-98页。只是后来的表现主义艺术走得更远。
三、“表现主义”的渴望及其问题
从德国“表现主义”的兴起及其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差异甚至批评性对立,可以看出:
第一,“表现主义”存在着对于统一性和全体性的热切渴望(如康德、席勒等)。“表现主义”激烈驳斥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将人性对象化,以及在此过程中对人的理解,乃至由此造成的对人的生命及其真实形象的歪曲,认为他们“分裂了心灵和肉体、理性与情感、理性与想象、思想与意义、欲望与谋划……所有这些二分法都歪曲了人的真正性质”,是对人的“肢解”。①[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30页。Taylor C.,Hege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23.在“表现主义”者看来,如此“被肢解”的人,其自我表现被曲解,因为“他的生命没有表现他,而是表现了有关他的真实情感和渴望的某个虚假替代者”。这种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冲击力,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现代主义思潮的先声。对此,哈贝马斯和大卫·哈维等人都有论及。②[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9-10页;[英]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0-23页。
第二,“表现主义”使自由成为人的生命的一个价值。自由本来就是启蒙运动的核心主题之一,与之相比,“表现主义理论既改变了自由概念,又大大加强了它的重要性”。因为,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所说的自由指摆脱外在控制——主要是国家和宗教权威的控制,以获得能自我规定的主体的独立和自由。但在“表现主义”者这里,自由被看作“本真的自我表现”,“它不仅受到外在侵犯的威胁,而且受到了危及表现的所有曲解的威胁。它可能因为在终极意义上通过外在根源的畸变而失败,但也可以在自我身上定格下来”。③[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31页。Taylor C.,Hegel,p.24.后者往往更为重要。德国启蒙思想与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要差异之一,也正在于从对外在自由的追求,走向对内在自由也即自我的内在规定的发现与追求。
第三,“表现主义”包含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渴望。法国的知性启蒙破坏的正是这种融通与完整。因为对象化了的自然是被经验为外在于自身的。正因此,表现主义者们渴望能在与自然的交融中统一。“他的自我感(Selbstgefuehl)与对所有生命的认同、对作为有生命的自然的认同(Mitgefuehl)统一起来。”④[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第33页。Taylor C.,Hegel,p.25.
第四,“表现主义”者们渴望“与一个更大的生命、而不是关于秩序的合理见解交汇”。要求统一和自由,要求与人相融合、与自然相融合,反映了表现主义意识的渴望。
在关于黑格尔的专论中,泰勒为何花大篇幅讨论“表现主义”问题?如前所及,在泰勒看来,正是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表现主义”得到极大彰显。而这其实也是现代自我滋生和出现的根源,至少是重要的一环。后者也正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泰勒对现代性怀有忧虑,正是因为现代自我的出现,于20 世纪下半叶显示出自身的疲相:“尽管文明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有时人们觉得,严重的衰落发生在刚过去的岁月或年代里——例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有时候,人们在更为长远的历史区段里感受到这种失败:从17 世纪至今的整个近代屡屡被视为衰落的时间段。”⑤[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第21页。虽然两者时间跨度很大,但“衰落的主题仍有某些重合”,衰落的原因更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这恐怕是几个世纪前的思想家始料未及的。
当然,泰勒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这个过程,和许多现代思想家一样,他肯定了这个过程的积极性,同时也发现了其内在的问题及其微妙的复杂性。因此,试图通过耐心地寻绎、梳理这个过程,包括追寻其起源,努力寻找更为切实的出路,既能够“成为你自己”,又不陷入平庸的相对主义和单子论。这也是他持“社群主义”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看来,经由“表现主义”的自我追求而形成的高度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打开了一个责任化(responsibilization)的时代”,“人们被迫承担更多的自我责任”。首先是对自身的责任,然后是对他人及社会的责任。因为在这种空前拥有自由,且自由度高度增长的社会中,个体堕落的机会与自我提升的机会一样多,“没有东西将担保一种系统的和不可逆转的蓬勃向上”。⑥[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第115-116页。
四、余论:几点反思性探讨
不可否认,泰勒对德国“表现主义”的基本渴望的论断是准确的。然而,如果将这些论断还原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要求,它的充实内容是什么?在泰勒这里,我们没有看到对近代精神的整体说明,没有看到他对近代特征的论述。近代精神所要求的自由——泰勒所谓的“表现主义的渴望”,在康德那里,是实践理性主体的自由,也即道德自律;在费希特那里,则是绝对自我的“我要”的原始冲动;在黑格尔那里,则是概念自身的运动,最后达至“绝对精神”的完满。但在泰勒这里,我们没有看到渴望自由的人的自我规定,也即这些渴望自由的人对人的基本理解。
什么是人?在近代,人是能够自我规定的人。而这个自我规定是理性的自我规定,而不是其他什么任意的规定。正是这样的规定,使得近代的精神不同于现代和后现代。也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理解近代的基本精神,以及现代以来的问题:人的本质被剥夺。正如泰勒认为启蒙运动前后存在着思想的“断裂”一样,近代的精神与现代思想之间也并非是全然一致和延续的,没有断裂。
泰勒曾在《自我的根源》的“现代性文化”部分论及卢梭的小说带来的“新情感”,指出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所讲述和唤起的,是“爱、仁慈和献身的德性”,很多读者被其所感动,以至于卢梭收到了来自“狂喜”“激动”而“入迷”的读者的大量来信。主人公于莉和圣普乐的故事令人鼓舞,他们伟大而堪称典范的爱,被泰勒称为是“自我克制的英雄主义,它为以这种方式实现崇高生活的理念所支持”。同时,他又指出,“这种崇拜很容易从英雄主义滑向自我放纵”,因为“在忧伤中体味的是克制、迷失,而不是自我超越”。①[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第399-400页。Taylor C.,Sources of the Self,pp.294-296.这里的“危险”,与其说来自作品,不如说来自读者本身。实际上,也很难想象那些读过此书热泪盈眶的读者都能够在流泪和狂喜之后,从践行的意义上承认小说主人公的生活所昭示的爱、仁慈和献身的德性。如果做不到这些,也即不从行动上“承认”,本质上说,仍是对其作品表达的时代精神的茫然。②戴晖:《语言的创造性——纪念卢梭诞辰300周年》,《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
对此,席勒倒是看得更清楚一些。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想满足一种需求,而无需精神提出什么要求。人们阅读美的心灵的作品为的是使身心得到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觉察不到更高的感情。”③[德]席勒:《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席勒文集·Ⅵ》,张佳珏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4页。中文略有改动。Schiller F.,Sämtliche Werke,Band8,Berlin: Berliner Aufgabe Aufbau-Verlag GmbH,2005,S.500.下同。他甚至指出,即使在最优秀的人群里,也只有极少数人在审美问题上有正确的判断力。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带着强烈的情感、甚至狂喜的阅读,倒是很有些现代意味。在阅读中使身心恢复,而不是提升的阅读,也正是现代以来的“需求”阅读。这种阅读不同于“美”的阅读。因为美“是精神与感官之间协调的产物”,它只能在“完全自由地发挥其全部力量的前提下才能为人所感受和赞赏”。④[德]席勒:《论天真的诗与感伤的诗》,《席勒文集·Ⅵ》,张佳珏等译,第150页。Schiller F.,Sämtliche Werke,Band8,S.506.就此来说,读者对作品的“误读”,未必不是时代群氓对时代精神的茫然与漠然。也正因此,产生出时代的连续性的假象——实在地说,只是因为戴着现代人的有色眼镜去打量过去,特殊时代的时代精神才被遮蔽。
此外,在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论述中,泰勒对从康德经由费希特到黑格尔的思想联系,似乎缺乏充分论述。虽然在《黑格尔》一书中,泰勒对黑格尔的思想做了详尽讨论,但对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与赫尔德强烈批评总体性之思的表现主义思想之间的巨大张力,缺乏充分论述。实际上,在法国启蒙主义与德国启蒙运动中的“表现主义”者之外,同样存在着从康德到费希特、再到黑格尔的思想连续性(或可称为“理性派”)。后者既对法国启蒙运动追求外在自由、并最终堕入难以自我规定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与反思,同时也与德国启蒙运动的“表现主义”保持着必要的张力。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表现主义”一派看作是现代主义的先声(它们共享着很多思想资源与倾向),那么,在德国启蒙运动的“理性派”与现代主义之间,就更多地存在着“断裂”。虽然这是另一复杂问题。
最后,在泰勒的讨论中,似乎也没有充分评估马克思所描述的在资本主义之下起着作用的各种社会过程,而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试图消灭资本主义的“种种革命运动”思潮之一。①Ibid.,p.118.[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第116页。包括大卫·哈维在内的一些当代思想家提醒我们,这个社会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主义、异化、分裂、短暂性、创新、创造性的破坏、投机性的开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愿望和需要)不可预测的转变、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没有关注到形成“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和文化生产者们打造其审美情感、原理和实践的物质语境”②E.C.Bridgman,“Seaou Heo,or Primary Lessons”,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5,No.2 (1836),p.87.[英]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第149页。及其对现代自我的诞生与样态。实际上,这个维度不可或缺。
当然,这些疑问丝毫不影响泰勒思想的力量,也不影响我们对他的现实关怀和思想探索的热诚的肯定,以及对他作为一个行动的思想家的赞许。他说:“一个自由社会的本性是,它将总是较高形式和较低形式的自由之间的战场。没有一方能消灭另一方,但是战线是可以移动的,不可能确定地移动,但至少某些时候对于某些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战线移动是可能的。通过社会活动、政治变革和赢得人心,较好的形式至少可以暂时发展壮大。”③[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第116—117页。同样有理由相信,前述辩驳式的疑问仍有意义,因为泰勒所给出的现代性的根源仍然引人发问和深思,而我们正身处现代性和它的“光晕”之中困惑不已,尤其当今,从高度网络化所带来的原子化的中国现实看泰勒的论述,更有一种切身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