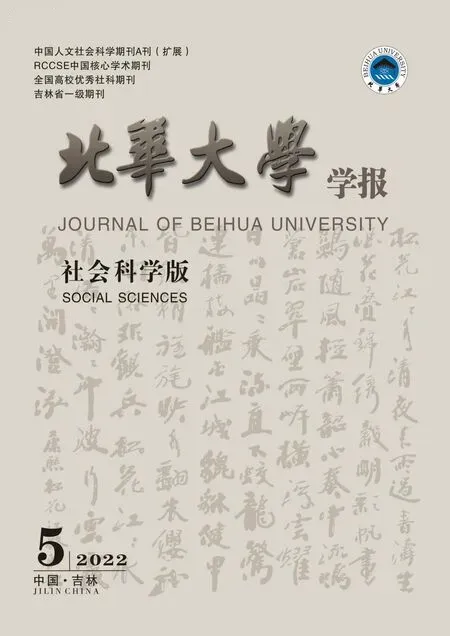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认识
吴 玲
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跻身亚洲乃至世界强国行列的过程中,政界、学术界、新闻界等诸多学者密切关注所谓“中国问题”。每遇中国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或中日关系面临重大抉择时,学者和媒体人纷纷著书立说,重新构筑中国认知的逻辑体系,剖析“中国问题”的症结根源,提出亚洲未来的解决对策。学术领域不同、政治立场各异的学者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问题频频发声,导致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呈现逻辑体系多元、认知倾向各异、终极结论庞杂的状态。纷繁复杂的近代日本中国认识因此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已经出版系列专著梳理与论述这一话题,[1]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既有的优秀研究成果为总结近代日本中国书写的总体特征提供了重要基础。从总体上看,近代日本的中国书写尽管庞杂、繁复,却在认知立场、话语体系上呈现一些趋同倾向或特征。总结评判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认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透视近代日本学者的自我认知。本文通过梳理历史学者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以及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北一辉围绕中国历史与现实展开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宣传,剖析日本学者的中国认识与时代话语体系之间的关联性,关注与评判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在日本近代社会产生的影响,揭示近代日本学者中国认识背后潜藏的对日本国家“世界性地位”的期待和对侵略战争的情感期许。
一、内藤湖南充满矛盾的中国认识
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内藤湖南将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作为同一来源的东方文化看待。从这一认知前提出发,内藤在由衷热爱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同时,也热爱和推崇同一来源的日本文化。在看待中国文化时,作为历史学者的内藤抛开将中国视为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学视角,而是立足宏观历史发展,将中国文化视为不断发展和变迁的不同区域势力在各历史时期互相冲突、融合的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面对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内藤首先从地形构造和历史发展入手,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分割为各民族、各地域领袖在中华大地上纵横捭阖、逐鹿中原的历史。一旦将悠久绵长的中国历史作出这样的分割梳理,则原本统一连贯的中国历史文化在内藤眼中变成了各自分割的地方势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掌握主导权的分裂过程,以“大一统”思想为王朝价值的趋向统一的中国历史在内藤那里变成一个恒久“分裂”的历史。由于内藤认为东亚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在“各自分裂”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必然成为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势力,并且此后将成为“引领整个东亚局势”的中心力量。
早在1894年11月,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地势臆说》,在清代学者赵翼“地势说”的基础上,将自然地理基础作为推动历史文化风俗发展的主要原因,将中国以长江为界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将中国历史地理划分为几个重要地区:长安—洛阳地势、燕京—“满洲”地势、江南地势、蜀地势、两广地势等。认为中国自中世纪以来,地势渐向东偏,宋代以后的“南北朝廷之京城皆靠海”。内藤发表《地势臆说》的目的在于判定亚洲文明中心移动的方向。“中国之存亡,乃当今坤舆之一大问题也,然从其分合之形势,地力人文之所在,征往推来。今概论之,以资文明大势转移之方向。”[2]117-125按照内藤的推演,自宋代以来,中国政权中心不断东移靠海,若延续这一移动趋势,则一直参与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心移动与发展的东方日本必将成为“文明大势转移之方向”。由此可见,内藤论证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目的在于说明日本成为东亚文明中心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媒体人的内藤湖南一直以“文化主义者”自居,并声称远离政治价值。在内藤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极度反感近代日本社会流行的贬低与鄙视中国的情感倾向,他是站在竭力赞扬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展开中国研究的。1899年,对中国文化倾心向往的内藤湖南终于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旅,此后多次访华,表现出对中国局势的格外关心。能够较全面展现内藤中国观的著作是《“支那”论》(1911)、《山东问题与排日论之根柢》、(1919)《新“支那”论》(1924)等。在这些著作中,内藤一方面竭力推崇、赞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却一直谈论“支那亡国”,为日本入侵中国正名。
八国联军侵华至《辛丑条约》签订期间,内藤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多篇评论,如《“支那”问题之现状——关于德国提议》《占领地之处分——中立地提案与“满洲”山东》《领土保全与“满洲”》《“支那”保全与大阪》等。1903年,在内藤湖南发表的社论中,题目与“满洲问题”相关者19篇,与中国问题相关的社论占据一半以上。在这些社论中,围绕如何处置八国联军侵华后的中国问题,内藤主张以确保列强在中国势均力敌的方式保全中国。“东洋之和平,以如此之均衡将可永远维持。若如此,则必然于渤海、黄海沿岸解除诸列强过分强大之武装,后永久之和平将庶几渴望实现。此实需居东洋主人地位之我国奋勉努力。吾辈确信:于中国北部扩大中立地区,确保其安全之责任切不可推卸于他国。”[3]特别是关于如何处理“满洲”的问题,内藤在《代清国谋》一文中主张“利用诸如我邦之强邻援助,交由与此地远无利害关系之我方处分”,从而将“满洲”问题的负担西移。[4]一方面将日本理所应当地视为“东洋主人”,从而理直气壮地替清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在面对列强试图分割中国领土时,又将日本打扮成与“满洲之地”毫无利害关系的“强邻”,试图以“援助”之名,行侵略中国东北之实。
《“支那”论》和《新“支那”论》完整地表述了内藤湖南充满矛盾的中国观。在《“支那”论》“自序”中,内藤提出“此书完全是代替中国人为中国人考虑”[5],语气中满含中国的“庇护者”和“救世主义”情怀,反映出当时日本学者对中日关系所持的一般态度。内藤主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上实行共和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实行松散的地方分权主义(联邦制度),在国防问题上主张“放弃国防论”,认为将来二十余年中,中国绝无国防之必要。因为以现在中国军人的素质,若日俄等列强下决心欲使中国灭亡,则中国绝无抵抗之力。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应维持列强在中国势均力敌,并无维持兵备之必要,以便省下军费,充实国家财政。宣扬否定中国拥有自卫权、否定中国主权独立,支持列强分割占领中国的中国认识。内藤甚至主张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消亡”:“今日之‘支那’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蠢动而已。”既然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向中国倾销产品和进行商业渗透便成为日本国对中国乃至对东亚的重要“使命”,内藤多次提出这一“使命”已经在“满洲”得以实现。实际上,内藤一直非常重视中国东北的资源与战略地位,早在《地势臆说》中便断定:“满洲之地,颇称膏腴,其百年之后,地力之开发,亦为可期。”[2]123可见,在内藤心中,对“满洲”这一“膏腴之地”倾心已久,并将日本势力入侵中国东北这一帝国主义行为看作日本国家的“使命”,上述逻辑中蕴含的帝国主义思维昭然显现。
内藤在《东洋文化史研究》中认为,中国文化具备超越国界的世界主义特性,与中国在文化上处于“一体性”关系的日本也属于超越国界的中国文化领域,因此,日本同样具有了成为文化中心的资格。然而,“今天的中国人面对日本的压迫极其神经过敏”,内藤呼吁“中国人对于日本在东亚所肩负的使命,不应抱有嫌恶猜忌之心”,认为这是新兴文化中心在产生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若干粗暴治疗”,这种“粗暴治疗”有利于给中国民族“注入新血液”“创造新组织”。[6]可见,内藤建构的“亚洲文化一体论”和“文化中心移动说”,试图达到从文化与历史发展角度为近代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寻找理论支撑这一现实目标。
总之,内藤是在否定中国现实国家独立性和完整性基础上阐释其中国观的。内藤的中国认识充满矛盾性和认知“倒错”(1)日本学者野村浩一认为,内藤湖南对中国的国情越是贴近就越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倒错。参见野村浩一著、张学峰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1页)。。主要表现为:在宣扬中国文化值得尊敬且倾心热爱中国文化的同时,断定中国现实国家在实质上已经“消亡”,从而为日本向中国渗透势力作出历史和理论辩解,试图以此消解中国近代蓬勃激荡的反日思潮和民族情绪。在内藤看来,判定中国国家已经灭亡是一种“高于民族大局”,立于“世界人类”文化的高度“尊重”中国文化的作法,然而实质上,内藤充满矛盾的中国观最终必然堕入为日本侵略亚洲大陆寻求历史和现实依据的时代话语氛围中。
二、“东洋学派”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抹杀、歪曲与蔑视
作为“东洋学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对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论断是“尧舜禹抹杀论”。在1909年发表的《“支那”古传说之研究》一文中,白鸟库吉立足兰克史学,质疑亚洲古代传说的真实性。1912年发表《尚书之高等批判——特别围绕尧舜禹》,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意在彻底解构中国古代历史。“尧舜禹抹杀论”彻底否认《尚书》等古籍的史料学价值,仅承认其作为传说的象征性意义,进而将整个夏朝、商朝的历史均判定为“虚构的传说”。白鸟还对中国文化起源产生怀疑,认为“五行思想是从亚述传入中国的”[7],体现出近代日本史学家鲜明的反汉学立场,代表了在刚刚传入日本的西方史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第一批近代史学家共同的认识取向。在上述认知基础上继续推演,便很容易得出中国传统文化起源于西方且落后于西方这一“研究”结论。1930年,白鸟库吉在东洋文库举办的“东洋学讲座”上连续做了7次题为《中国古代史批判》的演讲,这些当时并未公开发表的演讲被认为是其“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8],“东洋学派”彻底怀疑和抹杀中国传统史书的立场在近代日本社会广泛传播开来。
早在1907年10月,白鸟库吉发表《自古以来影响我国之外来文化之性质》,致力于解读在西方文明到来之前,日本接触到的外来文明及其对日本文化的改造。面对日本首当其冲接纳的中国文化,作为历史学家的白鸟深入探索了中国文化的确立问题。白鸟认为:“构成中国文明骨髓的是道德”,“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的思想仅限于现实世界,从而无法达至未来及更深的层面,这导致中国文化缺乏理想性,是保守的、独自尊大的。”[9]39白鸟判定倾向于道德的中国文化缺乏概括力,仅把目光聚焦于事物某种特殊的具体方面。其政治上的体现是家族政治,以家族政治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奉行胜者为王的观念,甚至连夷狄也可以成为帝王。白鸟从居住区域和与周边民族关系出发考证汉民族历史,认为由于汉民族不断向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等的民族接近,并未与比自己先进的优等民族频繁交往,导致“汉民族的文化性质无论如何都是原始的而并非高等的”。白鸟否认中国文明非常高尚的说法,认为汉民族周边居住的野蛮人一旦来到中国的国家范围内,将马上被同化为中国人。如果中国人的理想是高尚的,那么周围的蛮族不可能了解中华文明,亦不可能与中国人融合。从上述关系出发,白鸟断定:中国所谓的文明“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居于低层次的文明”,“中国文明的性质首先仍然是初级阶段的文明。”[9]41“此民族自周代以来长达两千数百年时间里,几乎看不到进化发展。因此,他们的生活从总体上不得不说是保守的。”[10]为了证明中国文化的“劣等性”,白鸟列举文字、信仰、政治体制等诸多例证。白鸟认为中国文字极其原始,拥有四五万汉字的文字“极不方便”;在宗教信仰方面,白鸟认为中国文化拜天神祭地祇,崇拜山川鬼神是“未开化人”“野蛮人”拥有的宗教观念;在政体方面,中国推崇以家族为基础的家长政治,从社会发展史上看,把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大家庭来看待的观念是幼稚的。可见,作为历史学家,白鸟库吉对中国历史文化充满贬低与轻视,认为从文字到政治、宗教、道德,中国文化始终在“低层次”阶段徘徊,这一判断基调深刻地影响着白鸟的弟子津田左右吉和“东洋学派”的后继者们。
在解构中国上古历史的同时,作为“东洋学派”领袖人物,白鸟库吉始终关心“满洲”问题。日俄战争后,日本历史学者纷纷展开对中国东北、朝鲜、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1908年,由白鸟主持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在“满铁”东京支社正式成立。作为历史学家,白鸟在服务于日本政府“经营满洲”这一现实需要的同时,主张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历史地理进行“纯学术”研究。于是,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为基地,白鸟库吉带领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池内宏、稻叶岩吉等学者广泛搜集历史和地理资料,展开对中国东北、朝鲜、蒙古的历史地理、交通、民族、文化的系统性考察和研究。由于研究队伍精干、分工明确,又有来自“满铁”的雄厚财力支持,使得以白鸟库吉为首的“满鲜史”研究在日本中国学研究中确立了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的学术地位。早在“满铁”建立时,白鸟库吉就关注中国历史和“满洲”问题,先后撰写了《“满洲”的过去及将来》《“满洲”问题和中国的将来》等论文,提出“间空地理论”,认为“满洲”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之地”,即处于“间空地状态”。在这一前提下,主张日本政府对待“满洲”的态度应为“维持现状,保持和平”[11]。为了给“间空地理论”寻找历史依据,白鸟详细论证了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自秦代、唐代及至清代均出现过“间空地状态”,是“无主之地”,中国与朝鲜均未在该地区拥有主权。白鸟库吉的上述历史解释,其目的在于将日本在中国东北推行的殖民侵略行为解读为所谓“历史的常态”。
以白鸟库吉为首的经院派历史学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缺乏基本认知,漠视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拥有强大内聚力的“大一统”观念,将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机械地判断为“虚妄”和“分裂”,体现出严重歪曲整体中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作为白鸟库吉的得意门生,津田左右吉在白鸟的中国历史研究基础上,从彻底的否定性立场出发开展中国思想史研究。家永三郎认为津田研究中国的动机在于:立足“停滞的支那”这一固定观念,把中国视为日本传统中否定性因素的根源进行彻底的批判,“从整体上看,津田对中国抱持强烈的否定性态度。”[12]在《儒教的实践道德》《论语与孔子的思想》《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等中国思想史研究著作中,津田判定儒家思想不承认集团生活的道德,不承认人的生活具有社会性,中国人虽然作为“事实上的民族”存在,却不具备民族集团意识,未能发展为国民。由于只有民族、国民的集团性生活才能构成历史的主体,因此,中国尽管存在王朝的历史记录和编纂物,却由于不存在民族集团的意识,故并未书写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没有民族历史的中国人没有世界史观念,这是理所应当的。”[13]可见,与白鸟抹杀“尧舜禹”的存在相比,津田甚至抹杀了整个中国历史。作为历史学家,直至战后,津田在对待中国历史与文化时,仍持全面否定中国历史价值的观点,可见津田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偏见与蔑视之深。正如日本学者的评价:津田的中国观与当时日本政府的中国认识是同质化的,与当时国际主流的中国认识在处理和走向上是一致的,“是从近代日本的视野出发窥视中国的性质,从这一点上来说,津田并非单纯的历史现象的研究者,而是代表近代日本的历史学家之一。”[14]揭示出作为历史学研究者,津田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近代日本历史学者的中国认识在情感上还体现出由“抹杀”发展为极端厌恶和蔑视的情绪。津田在《中国思潮》和《上古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将中国文化的特征归纳为“政治万能主义”“帝王万能主义”,认为中国文化是脱离宗教且轻视民众的,由此推导出中国“不存在现代性意义上的国民观念”。[15]津田的上述判断是建立在彻底批判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作出的,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带有强烈的蔑视情绪。津田评判中国文化是“利己主义的文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极端物质主义和肉欲本位的”。
津田在面对中国文化这一研究对象之初,就对研究对象持有毫不掩饰的负面情绪。早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从事研究工作时,津田就曾经在“鼠日记”中描述对中国历史的厌恶情绪:“权谋与术数、贪欲与暴戾、在虚礼包裹下的残忍行径、巧言矫饰下的冷酷内心,……这些都出自于中国人的头脑,我的头被这些书中散发的污浊空气压迫,感到无法忍受的厌恶。”[16]在津田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中,均渗透出上述极端厌恶情绪,导致在津田眼中,中国文化的自然观是不彻底的,道德观念是“虚伪的”,宇宙观是“机械性的”,中国人因不尊重知识导致没有真正的学问,在政治和道德中却充满着违反事实的空虚的知识。在津田对中国文化充满蔑视的评价背后,蕴含着对日本文化拥有“独特价值观”的高高在上的自大情绪。其目的在于运用理性与蔑视相杂糅的语言表述体系,言辞激烈地论说中国文化的“落后”与“僵化”,从而鲜明地映射出日本文化的“纯粹性”、“独立性”和“近代性”特征。
三、北一辉对辛亥革命的判断
近代日本超国家主义理论的指导者北一辉对中国革命倾注了超乎寻常的“热情”。在1916年出版的《“支那”革命外史》中,北一辉表现出与众多右翼思想家颇为不同的中国观,即摒弃蔑视中国革命的立场,将辛亥革命看作“思想之战争”,是“兴之国魂显现”的过程,是“因经济、政治濒临灭亡之旧国家自身于黑暗中尝试复活、飞跃之革命”。[17]81-82北一辉推断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将建成有组织的有机统一的近代国家,这一判断表明,与其他中国论者相比,北一辉认识到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大一统”要素,注意到辛亥革命的思想文化意义。关于日本应如何对待辛亥革命的问题,北一辉号召以“思想”和“精神”对中国的国家民族主义精神做出有力支持。可见,与物质支援相比,北一辉更注重从国家民族主义出发对辛亥革命进行思想指导和精神支持。北一辉的上述主张无疑来源于其对“国家民族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的推崇。值得注意的是,在展望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及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时,北一辉断定,在国家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中国定会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即通过与外国之间的战争来谋求本国利益,中国首先要发动的必然是中俄之间的战争。中俄战争一旦爆发,日本便可趁机联合中国,将英国势力从南部中国驱逐出去,同时击退俄国,使日本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在北一辉看来,中俄战争是一场未来必然爆发的战争,日本通过与中国结盟从而获取中国东北的企图被北一辉称为“革命性的对外政策”。
综观北一辉对中国革命乃至亚洲形势的判断可以看出,北一辉作出的中国局势判断实际上是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通过对外侵略实现国家崛起这条道路的重新推演。这种从本国民族文化传统出发,单方向推演其他国家现实政治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做法,暴露出国家民族主义者北一辉在思维方式上的狭隘性和“锁国性”。这也是近代日本学者在未能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便从本民族立场出发,试图对中国乃至亚洲做出事实性判断的通用作法。与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西田几多郎等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恶意诋毁歪曲,对中国民众救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冷漠轻视不同,北一辉对辛亥革命的性质作出了深层次的评判,却在憧憬辛亥革命的前途和亚洲秩序时再次回归到立足日本文化认知立场的简单推断上来。这种对中国认知倾向的偏差构成近代日本自我认知、中国认识乃至亚洲认知的弱点。
四、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中国文化观
一生潜心钻研哲学问题的西田几多郎与上述学者相比,对近代日本的现实政治和亚洲、国际形势等问题并未给予关注,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亦未进行专门论述。西田几多郎的中国文化观是在其对日本文化展开系统论证时,作为重要参照系表露出来的。正因如此,西田的中国观一直作为其日本国家观的映射物和对比项,呈现出片段的和非系统的状态。然而,由于西田对日本国家观和文化观的论述是细致的、连贯的,故对其作为参照系提及的中国观也表露出某些明显的观点倾向和结论性主张。
在文化观方面,西田以“文化多元论”对抗“欧洲文化至上主义”,并试图推导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西田看来,当时的世界文化大致可分为来源于希腊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来源于印度、中国的东方文化。“希腊文化的本质是艺术的直观,希腊文化是雕塑的、现实的”;基督教文化强调神的绝对超越性,是“有”的文化。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两大源流最终汇聚为欧洲近代文化,其特色是科学精神、合理主义和实证主义,是站在彻底否定主观立场上的“有”的文化。与西方相对,印度文化是虚无的文化,中国文化是礼俗发达的文化。西田认为,儒家以具有道德性的“天”为教义根源,道家以幽玄的“无”为思考前提。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既不是基督教中所谓恶的东西,又不是近世科学中思考的物质性的东西。那是日月星辰运行之所,天地万物之根源,即人道的本源。天道与人道是合一的。”[18]336-342西田发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特征,但他断言中国文化中“无”的思想是“行为性的”,因此,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关于人格的思考。西田对中国文化的最终定位是“主体的文化”,是“以‘支那’民族的社会组织,即所谓礼教为中心发展形成的文化,具有政治性和道德性特征”。[19]102由于在中国文化的周边不存在与之对立摩擦的强大文化,因此,中国文化缺乏自我否定因素和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是“静止”的而非创造性的,是“僵化”“固定”的文化。
西田承认日本文化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却完全否认日本文化带有儒教性质,主张在日本文化中存在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特殊性”。“在我国文化的根基处存在与中国文化在根本上相异的东西。所谓儒教的道德国家等并未深深地根植于我国文化真髓之中。在我国国民思想的根基处有且只有肇国性事实和历史性事实。我们以此为轴心形成的一个历史的世界。”[19]80西田所说的“肇国性事实”,是指来源于肇国神话的“日本历史”的起源。为了更加明确的表述,西田最终把日本文化的核心定位为日本“皇室”。西田在分析对比日本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时,为了诠释只有日本历史与文化是超越有无对立之上的真正的终极场所即“绝对无的场所”,将中国历史与文化定位为“主体性”“空间性”的“无”的文化,难以达到日本文化“绝对无”的高度。西田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简单地判定为“易姓革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和皇权是“权力的主体”,是“有的场所”,借此突出日本历史上既超越苏我氏、藤原氏等政权主体之上,又包含这些权力主体的皇室处于“超越性”的“绝对无的场所”地位。西田在1934年发表的《从形而上学立场观察东西方古代文化形态》中,着力论证受到中国和印度文化影响之前的日本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原初性”,强调这种“原初性”的日本文化具有“同化”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功能。[18]344
至此,西田几多郎的中国文化观表现出清晰的层次性和目的性。西田将源于希腊的西方文化定位为“有的文化”,属于场所逻辑的第一个层次——“有的场所”;将中国和印度文化定位为“无的文化”,属于场所逻辑的第二层次——“无的场所”。与东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只有日本文化处于超越“有”“无”两个层次的场所逻辑最高层次——“绝对无的场所”。在西田哲学“场所逻辑”的框架中,中国文化是“行为性的”“主体性的”僵化、固定的非创造性文化,以儒教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难以进入日本文化的核心。只有脱离了有和无二元对立的日本文化才拥有东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性”与“原创性”。在西田哲学的文化观中,中国文化一直是在起源上便低于日本文化的“低层次”文化。西田对中国文化的上述武断的定性分析表明,其将中国文化完全当作论证日本文化“独特性”的对照系和垫脚石。可见,在近代日本哲学家那里,中国认识几乎沦为构建日本文化哲学“独特性”“优越性”的简单工具。在西田晚年受军方邀请开展围绕“世界新秩序原理”的论证中,中国亦成为填充“特殊性世界”的一个地区而已。
五、近代日本学者中国认识的共性特征
近代日本各领域的知识分子从近代日本的普遍性认知立场出发,对中国问题展开积极的探讨。通过对上述代表性日本学者中国观群像的分析和总结,可以窥见近代日本中国认识的普遍性观点倾向,并揭示其认识缺陷或误区。
第一,近代日本学者立足日本国家优先立场,判定中国历史上拥有政治与社会分离的传统,进而推导出中国缺乏政治统一能力,必须借助日本力量实现“分割自治”。视中国为近代世界的“落伍者”,贬低近代中国人的“国民性”,否认中国民众具有爱国心,诋毁近代中国的爱国救亡运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近代日本人难以理解中国自甲午战后高涨的反日情绪,诸多日本知识人试图通过贬低、轻视、污蔑中国的排日运动,一厢情愿地认为能够说服中国民众在心理上取消对日抗拒情绪。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瓦解幕藩体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命题,很多思想家围绕这一命题构筑自己的学术观念。这使得在明治时代的思想家那里,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界限,与社会相比,国家占据绝对优越地位。这一认识成为明治时代知识分子观察中国的基础,从而断定只有日本社会才能够在明治维新后全力建设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则被蔑视为原本就缺乏统治能力的社会。明治时代的思想家山路爱山在论述汉民族时,一方面认可汉民族是“文明的人民”,拥有在精神上同化征服民族的“文明的同化力”,另一方面却评价汉民族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没有政治才干”,“缺乏建设国家的力量”。[20]从缺乏政治能力出发,日本学者的中国认识进一步深化为对中国国民性的评价,断定中国的国民性植根于国家与社会分离这一“特殊”传统。主张日本侵略中国的内田良平认为:“‘支那’为一畸形国家,政治社会与普通社会完全分离,形成两个社会,相互间风马牛不相关”[21]。内藤湖南关注中国历史上的乡团自治,以太平天国期间崛起的湘军为例,认为中国乡团自治传统中存在改革政治的可能性,并试图以此为日本侵略中国进行所谓“正当化”辩护。同时,橘朴也认为“官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隔离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现象”,主张充分发挥中国民众自治传统及其能力,以实现“满蒙独立”计划。综上,日本近代学者从明治国家优先立场出发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并寻找现实应对策略,结论均指向利用中国政治与社会分离和地方自治传统为近代日本国家分割中国寻求可行办法。同时,在日本试图蚕食中国的计划受到中国爱国救亡运动抵制后,日本学者又表现出难以理解,继而贬低、诋毁,或干脆宣扬中国“亡国”论。
内藤湖南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认为中国青年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既非出于中国国民的爱国心,亦非起于公愤,而是与袁世凯时期排日运动相同,完全是被煽动的结果”[22]。黑龙会骨干内田良平在观察中国辛亥革命后写下《“支那”观》一文,污蔑中国国民性“极其恶劣”,将中国斥为“畸形之国”。内田的中国研究并非立足学术,因此《“支那”观》并非严密、理性的学术分析,更多的是对现实中国局势和日本对华方针的直接建议。然而,内田的主张与思维却构成辛亥革命期间日本诸多中国认识共同秉承的出发点之一。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赞赏有加的内藤湖南在辛亥革命后发表的《“支那”论》“自序”中也宣称“此书完全是代替中国人为中国人考虑”[23],语气中充满扮演中国“庇护者”和“救世主”的意味。及至1924年发表《新“支那”论》,倡导日本通过对中国的经济渗透,达致“日中亲善”,甚至站在超越现实政治之上的“文化主义”高度高唱“中国亡国”论,竭力为日本入侵中国正名。由于内藤湖南是被日本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学权威,其中国观一方面植根于对中国文化的讴歌与赞美,另一方面宣扬“支那亡国”,为日本入侵中国正名。因此,内藤的中国论屡屡被当作真知灼见,后续的很多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从内藤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出发,将其中国观扩展开来,如稻叶岩吉“‘支那’国际共管论”、松波仁一“‘支那’不统一论”、小川节“中国三分论”、森恪“中国+X论”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第二,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缺乏基本认知,漠视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拥有强大内聚力的“大一统”观念,映照到近代的中国问题这一现实中,诸多学者在探讨近代中国出路和前途时,持“分裂中国论”。
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上,近代日本人作出的评判多为从日本现实国家利益出发的事实性判断,而非对中国文化深入理解基础上的历史性评价。如白鸟库吉的“间空地理论”、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支那’亡国论”、北一辉“改造中国论”等。值得注意的是,被认为在整体对华认识上具有鲜明进步意义的吉野作造肯定对华“二十一条”,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同时却反对将山东权益从德国手中直接归还中国,主张保持日本对山东的特别管理权等立场表明,在信奉近代国际法体系这一“道义”前提下,包括进步学者在内的几乎所有日本学者心中普遍存在着面对欧美列强势力的不断渗入,日本必须在中国大陆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新“亚洲秩序”这一憧憬与决心。为了实现这一决心,日本学者主张分割中国,在中国重要地区确保日本的“特殊利益”,对中国展开经济渗透。
第三,立足近代世界条约体系、弱肉强食的扩张逻辑诠释“日本之天职”,高唱“解放亚洲”甚至“解放世界”的口号。立足近代主义的认知逻辑有助于彻底摆脱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加害者立场,将实质上赤裸裸的大陆侵略“合理化”。
早在最初构建明治国家时,围绕何时实现“海外雄飞”的争论在征韩论争中已经表露出来,最终导致明治元勋内部分裂的结局。随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海外雄飞”具体化为“大陆经略”。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关注到日俄战后“大陆问题”一词的流行,指出这一词藻的变化表明中国问题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亚洲问题”或“清国”问题,而是扩大成了摆在日本面前重于一切的大陆问题,即转化成地理上和物理上的领土问题。[17]48与这一趋势相伴随,学术界和宣传界中国话语的转换表现为以系统学说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历史与暗淡的国家现状间的关联性,打着“帮助中国”“解决亚洲现实问题”的旗号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最终得出由日本继承、取代中国,成为“亚洲中心”乃至“世界中心”的结论。 甲午战后,一跃成为亚洲强国的日本致力于追求“日本之天职”。“日本之天职”的出发点是以日本为中心获得所谓的亚洲“觉醒”或“解放”,是对明治以来“海外雄飞”理想的新诠释,表露出对朝鲜和中国初试侵略锋芒后的日本试图向整个亚洲大陆扩张势力的野心。与内村鉴三、内藤湖南、冈仓天心等试图将“日本之天职”披上伦理性外衣的努力相对,以北一辉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干脆揭去伪善与虚伪的伦理面纱,赤裸裸地立足近代世界的“生存逻辑”,将侵略亚洲解读为日本国家的“生存伦理”,将“日本之天职”进一步发展为极具煽动性的“革命的大帝国主义”。
“亚洲提携”“亚洲一体”等理论经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随着日本成为亚洲强国,“日本之天职”进一步被发挥为“解放亚洲”,及至太平洋战争时期,“解放亚洲”更发展为“解放世界”。在近代日本,诸多知识分子致力于深入追究战争的内在原理。从内村鉴三在甲午战前宣称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人类全体的利益和世界进步之必要开始,作为国家对外行使权力的战争便被赋予了“道义”原理,进而被赋予逻辑性。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战争被诠释为“圣战”,“日本之天职”被抬升到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高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日本社会,只有日本文化才有资格充当沟通东西方文化桥梁的观念几乎成为各领域学者共同标榜的文化理论。这种体现“政治正确”的观念成为多数领域学者共同追求的“完美结论”。不仅如此,日本文明还肩负“超克”近代,成为“世界第一优秀文明”的任务。具体表现为西田几多郎的“世界性的世界”理论以及京都学派“世界史的立场”等。至此,近代日本的中国书写在逻辑上完成了走向“最高层次”的蜕变,直至战争结束,这一理论体系和逻辑构成戛然而止,并在战后再次以效仿美国这一文化强者的方式重新出发。
第四,近代日本学者在论述中国问题时,还体现出试图超越历史形成与现实国家利益,立足亚洲乃至世界视角解读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所谓“超越性”立场。这一“超越性”立场体现为:关注中国历史沿革的时间上的“超越”与重视东亚现实政治形势的空间上的“超越”。
时间上的“超越”主要表现为: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中,存在两种似乎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一,立足西方理论与方法解构、拒斥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彻底否认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塑造作用,体现出鲜明的“脱亚”倾向,为日本文化“优越论”和现实中的日本国家向“满蒙”扩张提供学术基础。具体表现为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南北二元论”“间空地理论”,津田左右吉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批判。其二,将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朝鲜、安南等国文化视为“一体”,统一定位为“东方文化”,否认中国文化在亚洲和世界历史上的核心与主导地位,甚至试图打破民族国家界限,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构成的中国分解为历史与文化沿革、政治与经济发展、民族与宗教构成迥异的多个区域,解构历史上作为整体的中国,从而推导出日本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亚洲文化核心的结论。具体表现为内藤湖南“文化中心移动说”。
空间上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与超越了狭隘国家利益、倡导“世界一家”的宫崎滔天不同,绝大多数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包括民间人士与大陆浪人)均为打着“亚洲主义”旗号的国权主义者,其目标为:通过支持辛亥革命,扩大日本在华权益,为日本分割占领中国提供便利。具体表现为内田良平“中国畸形论”、内藤湖南“中国联邦”设想、吉野作造“革命政府”预判等。
综观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认识,均显露出立足日本文化的认知立场推断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倾向,日本近代学者的一系列对华构想根源于幕末面对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劣等感,以及明治维新后试图超越这一秩序,实现日本“海外腾飞”的最初目标,这也使得近代日本学者的国家认同观念必然拥有面向亚洲和世界的开放性视角,也必须与近代日本国家的对外战略同步。加之近代日本学者在罗织围绕中国的话语体系时,均不自觉地掺杂从日本现实国家利益出发的功利主义、民族主义元素,导致其中国书写中随处可见对中国历史的诋毁、歪曲,对近代中国民众救国运动的冷漠、轻视。这种中国认知必然导致近代日本侵华战争走向失败的最终结局。
—— 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藏品集》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