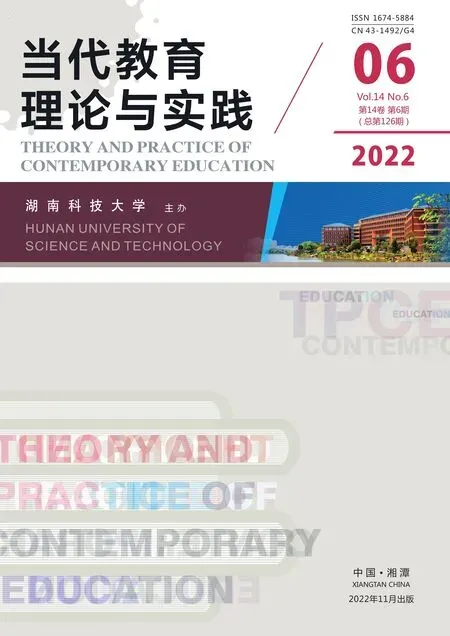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兼容性问题的逻辑勘察
姜建红,杨子飞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传媒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1 高校思政工作中的“大数据狂飙”及其基本逻辑
大概从2013年开始,大数据浪潮开始席卷国内各个领域,几乎每个行业都开始主动或被动地迎接“大数据革命”的到来,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领域[1]。又由于高校中大学生群体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高度信息化,加之近年来高校数字校园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诸多现实原因使得高校思政工作者更有意愿、也更有条件开展思政工作的大数据创新。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将是现在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的重大发展方向。
在这一历史趋势的鼓舞之下,人们对大数据技术寄予了厚望。正如大数据的倡导者所宣称的那样,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是通往未来的必然改变”[2]。将它运用在高校思政工作中,(似乎)必将带来思政工作质的飞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高校思政工作研究中出现了一场“大数据狂飙”。在知网中输入“大数据”和“思政”两个关键词,就能搜索到2 155条相关文献。绝大多数学者都乐观地认为“利用大数据技术,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每个学生的具体细节,可以全面真实地把握每个学生的思想动态”[3]。又或者认为“通过数据挖掘,我们就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真正的学生,真正读懂我们的学生”[4]。
不难看出,人们受大数据技术所承诺的美好理论上的可能性深深鼓舞,对大数据时代的高校思政工作创新前景充满了期待。这一合理期待假设了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之间有着“天然的兼容性”,而这种“天然的兼容性”背后隐藏的总体逻辑是:大数据技术所承诺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可以被转化为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上的现实性。然而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这一逻辑绝非是不证自明的,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尚待仔细勘察。
仔细观察大数据技术在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中的运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从大数据技术所承诺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到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上的现实性之间,其基本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首先,大数据思政的逻辑大前提是认为学生的思想可以被完全且准确地转化为数据;其次,大数据思政的逻辑小前提是认为学生的数据能够被全面地收集,而全面收集的全数据可以等同于真实的学生思想行为;最后,大数据思政的逻辑结论认为在全数据的基础上只需要进行大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而无需因果分析,就能够有助于提升思政教育成效。这三个逻辑节点分别代表了大数据理念所承诺的三个理论上的可能性,而这三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转化为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上的现实性,亦即这三个逻辑节点的有效性程度将直接决定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之间的兼容性程度。
因此,为了准确地评估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之间的兼容性程度,我们有必要仔细且深入地勘察上述三个逻辑节点的有效性程度。
2 数据≠思想——大数据思政的逻辑大前提勘察
让我们先来勘察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兼容性的逻辑大前提,即认为学生的思想观念可以被完全且准确地转化为数据。
大数据的基石即数据。这一数据不同于人类历史中传统的数据理念,传统的数据理念只是将数据看成是人类借以计量事物的符号之一,而大数据理念中的数据就绝不仅仅是一种计量符号,更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大数据理念“将世界看作信息、看作可以理解的数据的海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审视现实的视角。它是一种可以渗透到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大数据理念假设了一个基本前提,即整个世界应该而且可以被完全数据化,即所谓“一切皆可量化”[2],数据化了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大数据的第一个特性(即数据体量上的大Volume[5])就是这一数据化世界的典型特征。
这是大数据理念所承诺的第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将这一可能性直接运用于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中,就意味着可以用数据来代表思政教育对象的思想观念。对此,乐观的学者们认为,“大数据技术为我们观察他人的思想、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工具,就像望远镜让我们可以观察到遥远的太空,显微镜让我们观察到微小的原子世界一样,大数据则让我们可以科学地观察他人内心的真实思想”[3]。然而,是否果真如此呢?
这一乐观的推论显然刻意混淆了数据与思想、思想与行为、虚拟行为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差异。数据可以较好地指征客观的物理世界中的现象,因为客观的物理世界中的现象都是外在的、可见的。因此将世界数据化的理论可能性在客观的物理世界是比较可能(也仅仅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一旦涉及人类社会,情况就会变得异常复杂。毫无疑问,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社会中必定也存在一部分客观的外在现象,这一部分现象可以被数据化,这正是自孔德、斯宾塞以来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们试图把握的研究对象,即所谓的“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6]。这一客观的现象就是人类的外在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到进而被数据化的。
但是,当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以后,人类的虚拟行为与现实行为之间常常不能等同,一个在网络上咒骂某个候选人的网民极有可能在现实中又投票支持那个候选人,此时数据就不能够客观地指征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人类是有思想的,是受到特定文化观念深深影响的。要理解一个人的行为就必须理解他的思想以及思想背后的文化。这意味着人类的行为绝不能被抽象地等同于数据,而必须与他所处的特定文化传统相关联。就连数据本身都是文化的产物,它内生于特定的社会系统中,必然受到该系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影响[7]。更不用说数据所试图指征的人类行为与观念就更是深受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从学生所处的文化传统,转变为学生的思想观念,再转变为学生的外在行为,再将虚拟行为转变为移动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太多的异变、失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一个思想观念可以有很多种数据表现,反之,一个数据可以代表很多种思想观念。尤其是在互联网空间里,网络空间中的人呈现出物质身体可以缺场与身份信息自主建构的新特征,是一种数字自我与物质自我、社会自我与精神自我在网络空间中重构与耦合的新样态,包括多样自我、流变自我、异化自我和各种假我的新形式[8]。在这种情况下,数据与思想观念之间的表征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弱。
一言以蔽之,虚拟行为不等于现实行为,现实行为不等于人的思想,人的思想不等于数据。大数据思政试图将数据等同于思想这一理论可能性是很难真正实现的。如果不顾现实,将大数据技术勉强套用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就不仅仅是自欺欺人,而且还将错失思政工作的核心关切。
众所周知,高校思政工作的主体是人,对象也是人,而且不仅是人的行为,更是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主题就是“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9]。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永远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10]。只有专注于人的思想道德观念,才有可能培育和引导人的思想道德观念,这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关切。如果我们只关注抽象的数据,在数据的海洋里自娱自乐,而完全无法触及学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将大大偏离思政工作的主旨。
3 大数据≠全数据≠真实学生——大数据思政的逻辑小前提勘察
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勘察大数据思政的第二个逻辑条件,即认为大数据思政可以收集到全部的学生数据。
如前所述,大数据理念认为一切皆可以被数据化,因此世界才可以被转化为数据的海洋。不仅如此,大数据理念还进一步认为,当数据的体量足够大的时候,大数据就变成了全数据。可以说,全数据才是大数据的真实含义,只有收集到了研究总体的数据才算是大数据[2]。全数据意味着世界的数据化是全覆盖、无遗漏的。正是因为大数据技术假设了全数据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是可行的,所以才敢进一步宣称大数据可以“镜像”真实的世界[11],进而可以忽略传统的抽样方法以及建立在抽样方法基础之上的因果关系,转而运用所谓全样本数据,观察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理论上说,把握了全数据,也就等于把握了真实的世界。这是大数据理念所承诺的第二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可以说,全数据的理论假设是大数据理念的重中之重。
将全数据的理论假设运用在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中,就是将广泛收集到的学生数据等同于学生的全部数据,进而将学生的全部数据等同于学生的思想行为本身。比如有学者就认为,借助大数据实时、适时、全时的能力,高校思政工作者就能实施时间、空间、社交等多维度叠加分析,把握最佳时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12]。那么,大数据理念所承诺的这一理论上的可能性在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中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性呢?
在高校里,大学生的移动设备保有率、使用率、在线的时长都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群体,高等学校近些年的数字化建设浪潮也使得各种摄像头、感应器、数据采集器早已遍布校园各个角落。这些因素都使得高校范围里的数据生产和采集要比其他部门更加的高效,相应的,高校思政工作所能够获取的数据资源也更加庞大。
从绝对意义上说,无论数据体量有多么巨大,都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数据,这意味着所有的大数据本质上也只不过是部分数据,所谓的“全样本数据”本质上还是一种有限抽样数据,只不过是比传统的样本数据大一点[13]。这首先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类依然生活在互联网之外。在2012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只有约40%的中国受访者是通过网络渠道获取政治信息的。很显然,这40%的人绝对不能代表中国全部人口的总特征[14]。其次,在深度参与虚拟世界的人群中,也并非所有的生活都虚拟化了,那个被虚拟化了的部分并不能代表这群人的全部信息。比如有学者通过分析社交网络上采集的数据来分析人们的政治倾向,但是这种研究没有意识到特定的党派背景、宗教观念等会对网民在社交网络中的行为表现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能在数据中得到应有的体现[15]。最后,在部分参与虚拟世界的人群中的可被数据化的生活领域中,也并非所有的数据都能够被完整收集。比如米歇尔等人利用谷歌图书进行文化分析,他们研究了1 800—2 000年间英语世界文化的流变趋势[16]。这个被认为是大数据研究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所使用的大数据也只是覆盖了人类所有图书的4%,远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文化的整体。
无论大数据理念所承诺的理论上的可能性多么美好,数据的有限性永远都是无法突破的现实,这一点在高校思政工作领域中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前述几个基本事实会导致高校思政工作中所能够获得的数据必然只是部分数据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即在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可以简单地依靠命令或惩罚来改变教育对象的,所有的教育要想有所成效就必须要深入到教育对象的思想、情感中去。而人的思想情感是很难被完整且准确地数据化的。国外有学者认为从教室里安装的感应设备等渠道采集的学生面部表情反映学生对学习情感态度的视频信息,面部表情分析软件可以通过识别和计算一些细微面部动作如抬眉毛、降眉毛、闭紧嘴唇和延展嘴唇等的强度和频率,来推测学生的情感态度如投入度、关注度、积极性、与教师的互动等[17]。这一想法显然严重偏离了思政教育的实际状况。因为学生的抬眉毛、紧闭嘴唇等细节动作可以由众多不同的原因导致,也可以代表完全不同的思想情感。要知道,不同思想文化背景的学生在面对同一语境时被激活的信息是有差异的,构建出的心理空间也会存在差别,解读出的话语意义也就存在差别[18]。大数据技术最多只能够捕捉到与大学生相关的“客观数据”,但是还有大量的与个体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性格特征、现实需要等“主观数据”会对个体思想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19]。而这些“主观数据”是不可能被大数据所收集和处理的。
如此看来,将大数据等同于全数据,又将全数据等同于真实的学生,这一大数据思政的逻辑小前提是有条件成立的。只有那些外在的、客观的数据能够指征学生的部分信息,真实的学生要远比大数据技术所搜集的数据集更复杂、多样。如果忽略这一基本的事实,将抽象冰冷的数据等同于学生本身,就只会令高校思政工作失去根基。
4 相关关系≠因果关系——大数据思政的逻辑结论勘察
最后,让我们来仔细勘察大数据思政的逻辑结论,即认为在获得学生全数据的基础之上,就可以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挖掘数据间的相关关系,而不用关注因果关系,这样就能够有助于提升高校思政工作成效。
如前所述,大数据理念认为当数据体量达到足以涵盖事物整体的时候,传统的抽样研究方法就可以被废弃了,因为抽样的方法就是在数据规模比较小,人类尚不足以把握事物整体的情况之下的无奈之选,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是通过观察局部现象之间因果关系来理解事物的,用以解释局部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知识。现在有了全数据,也就有了“全样本数据”,它使得人类可以不再关心局部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已经没有必要了,而是可以直接从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中获得洞见[20],这种“只注重相关关系而不重视因果关系”的理念被称为是大数据技术带来的全新的认识论[2]。更重要的是,数据科学家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来自数据的洞见是完全可以借助数学模型、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的。这意味着只要把足够多的数据丢进计算机群,数据就会自动“发声”。这是大数据理念所承诺的第三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它是前面两个理论可能性的逻辑衍生物。
用相关性来代替因果性,将这一理论可能性运用于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有学者乐观地认为,利用大数据对数据信息流进行精准挖掘和有效研判的技术赋能,可以实现对思想政治工作服务对象的动态分析和轨迹可视化,精准定位教育服务对象;利用大数据的全景把握和分析功能,可以实现对教育服务内容的精准推送[21]。还有学者认为“通过找出一个关联物并且监控它,我们就能预测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及时采取措施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化解问题和矛盾”[4]。
然而,这一理论上的可能性不仅在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中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还是极其有害的。这是因为相关关系的核心是统计归纳,因果关系的核心是逻辑演绎。相关关系的实质是两个数值之间的此消彼长关系,因果关系的实质是事物之间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关系。人类获得知识是从正确提出和解决“为什么”开始的,因果关系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必须要遵守的[22]。尤其是在高校思政工作中,思政工作者除了要知道大学生正在做什么,更要知道大学生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知道大学生在想什么,而且还要进一步知道大学生为什么这么想,进而才有可能去改变和影响大学生的思想状态,这是思政工作永恒的主题。而对这两个“为什么”的回答只有对因果关系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揭示,数据间的相关性最多只能说明表面上的相关关系。
让我们来看一个经常被国内学界提及的例证:华东师范大学开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预警系统”,通过对学生校园卡消费记录的分析,可以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相应的资助帮扶。这个例子经常被用来证明大数据技术运用于思政工作中的有效性,似乎消费记录和贫困状态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这种弱相关性就做出相应决策,绝对是低效甚至荒唐的。用最简单的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发现,消费水平较低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贫困生,他们有可能只是有着节俭的习惯。总而言之,原因可以有很多种,要想真正有针对性地帮助需要帮助的大学生,就必然要求思政工作者沉下心去分析大学生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
如此看来,在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中用相关性分析来代替因果关系分析,不仅在理论上是绝不可能的,而且在现实中是有害无益的。可以说,只要高校思政工作还试图进入大学生的思想道德领域,那么它就必然高度依赖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如果将理论上的可能性武断地当成实践中的现实性,单纯地将相关性分析运用于高校思政工作之中,必定会导致一个治标不治本的结果。只有找到根本性原因,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思政教育的本永远在人身上,而人的本永远在人的思想观念里。这是一个合格的思政工作者永远都不应该遗忘的。
5 代结语: 正视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之间的“有限兼容性”
综上所述,大数据技术所承诺的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高校思政工作实践中的现实性。经过仔细勘察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相结合的逻辑过程,我们发现:首先,数据不等于思想,大数据思政的逻辑大前提只能部分成立;其次,大数据不等于全数据,全数据不等于真实的学生,真实的学生远比数据集要复杂、多样,大数据思政的逻辑小前提只能有条件成立;最后,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大数据思政的逻辑结论并不成立,高校思政工作高度依赖对因果关系的研究,若单纯关注数据间的相关性,只会使高校思政工作陷入舍本逐末的深渊。
总而言之,前述研究证明了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只具备有限的兼容性,同时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兼容性。
只有正视大数据技术与高校思政工作之间的“有限兼容性”,才能认识到无论技术多么的发达,数据多么的庞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永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做的是“人”的工作,其理念、原则、方法、载体无不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3]。实际上这正是我们长期形成的思政工作优良传统,不应该轻易被抛弃。只有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才能够看清技术的合适位置,进而才能够更妥当地运用技术,而不被技术奴役,最终才能够恰当地运用大数据技术来提升高校思政工作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