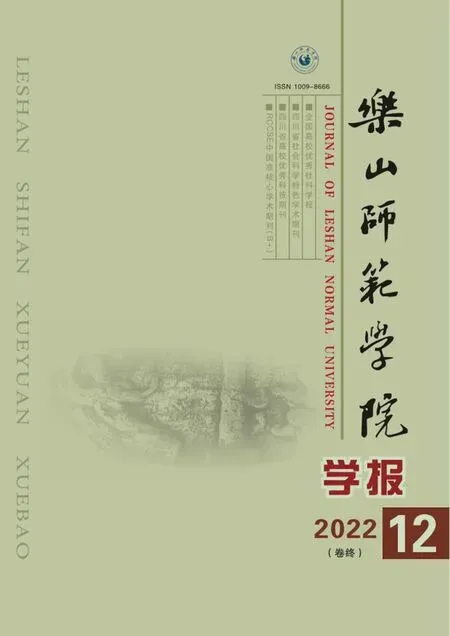苏轼的宦游体验与文学书写
——以签判凤翔时期为中心
申晓清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在儒家入世理想的影响下,自古以来便有无数士人投身政治,以期实现经世抱负。随官员身份而来的,便是因赴任、转任、出使和贬谪等原因而流转各地的宦游经历。对苏轼而言,丰富的宦游经历是他文学创作重要的背景、动力与内容。自嘉祐四年(1059)离开蜀地,直至生命终点,苏轼一直因政治上的任命或贬谪而四处奔波,在空间跨度上亦称得上“身行万里半天下”[1]291。宦游成为了苏轼的一生的生存常态,流转四方的经历带给了他更为丰富的生命体验,他的人生思考也在宦游历程中逐步深化。而在如此广阔的时空跨度中,签判凤翔时期作为苏轼仕途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地方上的政务给他带来了施展才华与抱负的初始空间,官员的身份与责任也开始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切实的影响。可以说,从这时起,苏轼才真正成为了一名兼具文人与官僚身份的士大夫。
现有研究中,不乏对于苏轼早期思想与文学的探讨①,但较少涉及他这一时期具体的体验、心态与形象。因此在提及青年苏轼时,论者多概括性地引用苏辙对兄长“奋厉有当世志”[2]1117的评价。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苏轼签判凤翔时期创作的所有诗文,便会发现他在这一时期心态与体验的复杂性,意气风发的形象也并非是如此稳定且唯一的。那么苏轼在踏入仕途之初,究竟书写了怎样的宦游体验?对于宦游体验的书写又呈现出怎样的情感特点?通过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我们是否能看到青年苏轼更为复杂的形象特质?本文将通过对诗文作品的细读,对上述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探讨。
一、青年苏轼的宦游体验
嘉祐六年(1061),苏轼通过制科考试,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去往全然陌生的地域。个体身份与生活空间的变化必然带来人生体验的新变,而离别、仕宦和游览三个维度的体验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1]120与亲人和故乡的远别是仕宦给苏轼带来的第一道难题。纵使身旁有妻孥陪伴,在面对离别的境况时,苏轼依然流露出难以抑制的落寞。“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1]95,连随行者都惊异于二人分别时的哀伤。然而这份沉重的情感并非无由而发,一方面,苏辙对于苏轼而言,是亲人亦是知己,一旦分别,便意味着曾经持久的陪伴将长时间地失落,无人倾心交流的孤独成为了苏轼首要的情感忧虑。另一方面,苏轼承受的不仅是一次离别所带来的的落寞,而是踏入仕途后便不可避免的屡次离别的隐忧。在《和子由苦寒见寄》中,苏轼写道:“人生不满百,一别费三年。三年吾有几,弃掷理无还。常恐别离中,摧我鬓与颜。”[1]215人生短暂,却可能在离别的境况中度过一个又一个三年,正是对未来亦聚少离多的悬想,使得昭示着开端的第一次离别分外感伤。
当苏轼将送别弟弟的视线收回,正式上任之后,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不时交织而来,成为贯穿这一时期的一条情感线索。嘉祐七年(1062)重阳节,苏轼没有参与官府的集会,孤身一人前往普门寺。在避开重阳花酒的热闹后,幽寂的僧阁让苏轼倍觉孤独,“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1]151,他怀念起苏辙,也怀念起故乡,但仕宦的身不由己只能让他在“独在异乡为异客”[3]131的境况中默默承受远别的苦楚。任职凤翔的三年时间里,在病中、微雪和岁暮这些最使人怅然的时节,苏轼总是会把自己的诗歌寄往都城,向苏辙抒发内心难以自遣的忧虑或怀想。直至任期结束后,苏轼在归途中写下《华阴寄子由》,依然流露出“三年无日不思归”[1]224的深切感怀。
然而苏轼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哀伤的心绪中,早在南行江上时,还未踏入仕途的苏轼便写下“自进苟无补,乃是懒且愚”(《浰阳早发》)[1]70的诗句,他希望以勤勉的作为实现有补于民生政事的期待。可以说,苏轼首次担起官员之职责,就以脚踏实地、积极作为的精神实现了这一设想。初次上任,苏轼便根据凤翔府的实际状况,对现有的弊端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他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针对“衙前役”[4]1327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衙前役是北宋差役的一种,负责运送官府物资并包赔损失,凤翔府常需将终南山的竹木由渭水和黄河运往京城。之前的管理者多忽视实际情况,在河水暴涨时仍要求发运,使得不少差役因竹木的损失而倾家荡产。苏轼将此禀明上司,修改衙规,让服役者根据水情自行决定发运时间,由此衙前之害减半,也让苏轼备感鼓舞。
但公务并不总是朝着苏轼期待的方向顺利进展,繁杂琐碎、无创造性的事务也让他感到疲倦。为民祷雨是苏轼的职责之一,然而这一事务总需在凌晨起行,“马上续残梦,不知朝日升”(《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1]129,起行时还接续着夜晚做过的长梦,从中可想见仕宦之劳顿。拜谒长官同样是官员例行的义务,但若碰上一位迟迟不出的太守,僚属也只能在外枯坐久等。《客位假寐》一诗中对身旁同僚“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1]163的调侃和劝慰,实则蕴含了苏轼自己的苦涩。
苏辙在寄来的诗歌中提及对兄长官职的看法:“问吏所事何,过客及系囚。客实虚搅人,囚有不自由。办之何益增,不办亦足忧。”(《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5]146此时苏轼所要面对的毕竟还是文书、会客、问囚之类的琐事居多,为此而劳碌并无太多创造性的意义,只是为了履行签判的任务。生命在无意义的重复当中停顿,让苏轼感到了深深的失落和倦怠,他觉得自己像一匹被系在厩中的马,空有驰骋千里的志向,“宦游无归时,身若马系皂。悲鸣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1]205类似的比喻在苏轼后期的诗歌中也出现过,在给方外友人法芝寄去的诗里,苏轼感慨自己两年时间转徙三州,“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送芝上人游庐山》)[1]1899,在重复因循之中耗费着自己的生命。初入仕途的感慨在任知州时依然存在,可见苏轼最初并非是因官职低微而有所不耐,而是官僚体系中重复因循的活动确实与他的天性相违背,这种背离带来的倦怠和痛苦几乎贯穿着苏轼的整个宦游生涯。
在处理官务之余,苏轼时常四处游览。篇目众多的记游诗不仅详细地勾勒出他游赏的行迹,亦流露出他对于山水的无限喜爱。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游览诗中共同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情感转换,即从文人雅士的游赏之乐转向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切担忧。嘉祐八年(1063)岁暮,一场夜雪过后,苏轼一早便骑马出行,希望在微雪消融之前赶到南溪欣赏雪景。可是在迫切的期待得以实现之后,天地间的一片寂静却让苏轼想起了雪中的百姓:“谁怜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1]183他们之所以寂寂无声,大概是因冰天雪地之中饥寒交迫的缘故吧。这样的念想消弥了赏雪的雅兴,让苏轼沉浸在了惆怅之中。同一年秋天,苏轼因到磻溪祷雨,在翠麓亭中休憩,走在亭前的小径上,苏轼欣赏着“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1]175的清旷之景。只是当他坐到正午时分的石床上,温热的温度立刻让他想起了最近的旱情,于是对于景物的清赏立刻被“安得云如盖,能令雨泻盆”(《是日自磻溪,将往阳平,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1]175的愿望所替代,苏轼又陷入怅然之中了。雪天中的寂静,石床上的温度,这一刹那的感受触发了情感的转折,蕴含着苏轼对于民生发自内心的关怀。若回顾《南行集》中的记游诗,便会发现苏轼在还未成为一名地方官员之前,这种情感是并不曾流露的。正是官员身份的自觉,使之拥有了不同以往的游览体验。
综上所述,苏轼签判凤翔时期书写了丰富的宦游体验:面对与故乡和亲人的远别,无论是离别时还是任官后,他都没有表现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3]15的超旷,而是真切地将自己的落寞和思念书写下来。当苏真正肩负起签判的职责,便力求以自己勤勉的作为改善民生,实际的成效也给了他不小的鼓舞。但在面对无力改变的境况和繁复琐碎的事务时,苏轼也有着深深的无力感和倦怠感,这份倦怠感反映出的是苏轼天性中对于因循重复的厌弃。在公务之余的游览中,苏轼表现出对于凤翔地域景观的极大兴趣,然而官员的身份自觉常让他在畅游山水时生发出对百姓真挚的关怀和念想,由此消弥了作为文人的游赏雅兴。
二、宦游书写的情感特征
纵观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文学书写,便会发现,当他把目光投向宦游中的自我处境时,情感基调多是低沉的。这里的“低沉”,并非是指消极颓靡,而是因现实处境的不尽如人意或人生思考的困惑所带来的忧惧、犹疑或怅然等并不昂扬的情感意绪。然而当我们回望苏轼初次出蜀,进京科考,进士登第,一举成名,得到了欧阳修极高的赏识和赞誉,一时之间,文彦博、富弼、韩琦等名公巨卿皆以礼相待。三年之后,又入制科第三等。当时的情态,用苏轼自己的话来说最恰当不过:“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6]134青年时的这段经历无疑会让苏轼拥有更高的自我期许,也让他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一个属于自己的远大前程。可是何以在签判凤翔时期的诗歌里,我们难以见到苏轼对于未来仕途美好愿景的期待,反而听到不少低沉之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苏轼这一时期低沉的情感因何而来。除了离别与仕宦这些现实处境所带来的困扰,精神世界的困惑与矛盾也常常让苏轼感到忧虑。
首先是对于时间流逝的忧惧。个体生命存在的时间有限,是一个必然正确却难于被接受的定理。年轻开朗如苏轼,也难以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完全乐观,甚至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岁月,就有了“明年纵健人应老”(《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1]151、“白发秋来已上簪”(《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1]154的叹老之悲。这种真实年岁和感慨之间的错位反映出苏轼对时间流逝的敏感和担忧。而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在《守岁》一诗中得到部分答案: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誇。[1]161
此诗开篇便写出了年岁无法守住的无奈,与此同时,晨鸡啼鸣、更鼓添挝、烛光成烬、斗转星移,一切事物的变化又都在昭示着时间的逝去。苏轼最后转而剖白自己的内心,即将到来的依然是新的一年,为何要为今年的逝去感到惋惜呢?“心事恐蹉跎”[1]161是最终的回答。从广义而言,“心事”可以指向苏轼生命中所有的期待和美好的向往,这些期待与向往若因现实处境被搁置甚至渐渐在时光的流逝中被消泯,便会带来强烈的忧虑。因此,苏轼担忧时间的流逝,在根本上是担忧有限的人生中理想追求的失落。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苏轼这一时期的期待与追求,便会发现共存在苏轼心中的不同期待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同样会带来心灵的困扰,成为苏轼这一时期低沉情感的另一来源。
仕与隐便是共存在苏轼心中难以调和的两种期待。仕宦指向社会责任的承担和人生价值的实现,而隐逸则指向精神的独立自由和心灵的澄净空灵。从纯粹的角度而言,两者天然是相反的方向,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之中,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苏轼也不例外,只是他的独特性在于一生言归而终身未归,思考这一问题的时间跨度几乎涵括了他的一生。早在还未踏入仕途时,苏轼就在《夜泊牛口》一诗中表现出对隐居生活的审视:“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1]10那甘愿与麋鹿为友的深山子,可以在自由无拘的生活中葆有活跃的生命力,而“我”此时却为世味所诱,“汲汲强奔走”[1]10。以麋鹿和深山子为代表的另一种品格和生存方式叩问着“我”的选择究竟是不是正确,从“强”字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犹疑。签判凤翔时期,苏轼对隐居生活依然抱有期待,在为薛周逸老亭所题写的诗中,他想象出“青春为君好,白日为君悠。山鸟奏琴筑,野花弄闲幽”(《和刘长安题薛周逸老亭,周善饮酒,未七十而致仕》)[1]164的美好画面,表达出对于解脱世俗羁绊、与自然为友的强烈向往。在苏轼后来的仕宦生涯中,他不断给自己想象出更多归处,故乡、他乡、田园、山林、江湖[7],可是却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归去。惠州时期,当苏轼回想起自己的过往,甚至认为隐逸山林才是符合自己本心的选择,正如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言:“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故汩没至今。”(《与王庠五首》)[4]1820而当他逐渐成长,强迫他走进宦途的不再是外力,而是在整个时代氛围的影响下,内心确立起来的以经世济民为价值导向的理想追求,这远比外在的压力更为强大恒久,也支撑着他始终没有真正离开仕途。只是苏轼对隐逸这一顺应本心的生活方式有多么强烈的期待和珍视,走向与之相反的仕途时就有多深的犹疑和挣扎。“平生慕独往,官爵同一屣。胡为此溪边,眷眷若有俟,国恩久未报,念此残且泚”(《自仙游回至黑水,见居民姚氏山亭,高绝可爱,复憩其上》)[1]198,这便是苏轼在凤翔时期关于仕隐矛盾的真诚袒露。
最后是世事无常的感触和体会。在赴凤翔签判任的途中,他再度经过了曾经赶赴京城时所路过的渑池,如今见到的景象却是“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和子由渑池怀旧》)[1]96。短短几年时间,就发生了生死、有无的变化,那么在人的一生之中,又有什么是不会发生变动的呢?在《凌虚台记》中,苏轼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历史洪流,并清醒地认识到“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4]350。万事万物的盛衰变化难以预料,不可把握。人事亦是如此,得失成败来去匆匆,并不值得追求和依恃。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苏轼早已明白了官爵利禄的虚幻性。可是如若找不到无常的世事中真正值得追求和依恃的事物,恐怕就会陷入虚幻带来的痛苦之中,苏轼在《凌虚台记》中表现得洒脱洞达,但并不表明对于世事无常的认识没有给他带来精神上的苦恼。当他游览时登上怀贤阁,远望诸葛亮功业未成时的病逝之处,想到这位不知“人也,神也”[4]2642的卧龙先生尚且不能依凭自己的才智实现最终的抱负,历史的成败盛衰非人力所能把握,同时又转眼成空,也难免让他产生“客来空吊古,清泪落悲笳”[1]179的感怀。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从思想的角度回答为何苏轼在签判凤翔时期的诗歌之中少有对于远大前程的美好期待,也少有表现宏图壮志的话语。这并非是因为他在心中否定了仕宦的价值,相反,他对于在仕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依然抱有期待。但是,他的期待当中还有一个与之相反的声音,它指向隐逸林泉的方向,于是本可以用高昂的声调喊出的报效国恩,在另一种愿望的牵扯之下成为了“眷眷若有俟”[1]198的怅然。另一方面,苏轼对于人生世事有着清醒的思索和体认,从历史兴亡与人事变迁之中他都能感受到世事无常,官爵利禄不值得追求,前途在变幻的世事中也难以预料,这种洞见消泯了对未来的盲目乐观,让苏轼以更深沉和曲折的声音传递出自己的志意。在这些低沉的情感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对于自我本心和人生高度自觉的理性思索,这种思索给年轻的心灵带来了愁苦和悲哀,但也为苏轼之后走进更广阔的人生境界提供了最初的可能。
三、青年苏轼的形象
如果将上述低沉的情感表达纳入苏轼的形象建构中,我们或许可以在“奋厉有当世志”[2]1117外,看到青年苏轼更丰富的形象特质。他似乎并非单纯是一个意气风发、迈往进取的儒者形象,在对隐逸的向往与世事无常的体认中,同时蕴含着某种超越性的思考。王水照、朱刚先生把苏轼视作“寄寓”者,所谓“寄寓”,既是苏轼对于人生本质的体认:人的一生便是永恒的人“性”寄寓于有限的人“身”的过程,而人身的有限性就表现在私欲的存在和终归虚无的结局;“寄寓”也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觉悟本质而付诸创造性的活动。也即是说,将对利害得失的本质超越和对创造活动的积极肯定结合在一起,以诗意的态度面对有限的人生。[8]431-438这样的概括自然是建立在对于苏轼一生的观照之上,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还未经历多少人生坎坷的青年苏轼,就会发现,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萌芽时期的“寄寓”者了。
上文在分析苏轼诗歌中流露出的低沉情感基调时,便提及了他对人生有限、世事无常的体认,以及在这一体认之中所蕴含的对于人事之得失成败难以自主把握的思考,这便触及了人“身”的有限性,体现出对于人生本质的自觉思索。同时,青年时期的苏轼也在不断思考着如何超越这种认识带来的忧虑感和虚无感,以形成更积极的人生态度。
早在南行时期的诗歌中,苏轼就有相关的书写。舟行襄阳时,苏轼经过岘山,几百年前,羊祜曾登此山,发出自有宇宙以来登此山者多矣,然皆湮没无闻的感叹。如今苏轼再次登览,在诗歌中留下了相似的感慨:“可怜山前客,倏忽星过罶。贤愚未及分,来者当自剖。”(《岘山》)[1]75人的生命太过短暂,不久之后所谓贤愚都会成为过眼烟云。但是苏轼并不因为“贤愚未及分”而直接混淆二者的界限,取消在有生之年成为贤者的意义。所谓“来者当自剖”,是指尽管个体在人世如同过客,时间的流逝会让一切成败、贤愚成为过往,但内心依然要保有对自我人格与理想的坚守,这便是未经世事时的苏轼竖立起的信念。熙宁五年(1072),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在《墨妙亭记》中再次提到了外物必归于尽、不足依恃的观点,延续了《凌虚台记》中的思考。只是这次在文章的结尾,他提出了“知命”一词:“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4]355物有成坏、人有生死、国有兴亡,面对世事的变动和物必归于尽的结局,依然要穷尽自己的努力,“至其不可奈何而后已”[4]355。至于最终的结果如何,则不在人力可掌控的范围之内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青年苏轼对个体的有限和世事的变幻有着清醒的认识,纵使他也为此感到遗憾和悲哀,但并没有因此而陷入虚无中去,而是不断勉励自己葆有对自我人格和理想的坚守,并在行动上勉力为之。由此可见,对于本质的觉悟和对创造性活动的积极肯定在这一时期已经有所体现,青年苏轼已经显现出“寄寓”者的风采了。
然而之所以用“萌芽时期”作为限定,是因为苏轼这一时期毕竟还没有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对于人生本质的体认中还未蕴含深重的现实内容,创造性的发挥方式也更多指向了仕宦一途。
李泽厚先生在分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提到这首诗是有悲伤的,但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9]129。在我看来,苏轼这一时期对于人生本质的体认也是如此。“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1]97的比喻蕴含着对于人生不确定性的感触,人生所到之处仿佛皆是偶然,一生留下的印记也终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份怅然是轻盈而非沉重的,是青年苏轼在开始展望人生时,从故地重游的经历中捕捉到的情感瞬间。《凌虚台记》中苏轼对于世事盛衰无常的体认展现出非凡的洞达,但在文章的结尾,“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4]350,却以一己之才华与锋芒表露出对凤翔知府陈弼的揶揄。在这种轻盈和戏谑之中,并没有太过深重的现实内容。然而当我们看向苏轼谪居黄州之后的创作,当他的人生在起落之间交替更迭,荣辱得失让他尝尽各种人生况味,这时在诗中反复书写的“人生如梦”“人生苦难”的感触才真正承载了沉重的生命体验。它们不是瞬间的领会,而是一生坎坷曲折中凝聚起来的血与泪。即便是后期的自嘲与戏谑,我们也依然能从中见到悲哀的底色。[10]
青年苏轼明白官爵利禄并非是自己的追求,但在儒家立功、立德、立言的影响下,他对功名是抱有认可之心的。在提出“知命”这一人生态度的《墨妙亭记》中,苏轼认为金石之坚会“俄而变坏”[4]355,而“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4]355。所谓功名,并不等同于官爵利禄,而是指向实际的政绩功业以及由此而来的清名。在“知命”这一坚定信念的鼓舞下,苏轼以积极创造的态度投入政事之中,务求以勤勉的态度有所作为。但是当他年复一年地在宦海漂泊,不断地遭遇中伤诋毁,仕宦以及功名都渐渐地受到了他的质疑。而当他遭遇贬谪的命运,这一价值指向和发挥创造性的方式几乎彻底成为泡影。此时的苏轼却能调适自己的观念,将躬耕田亩、畅游山水、著书立说、吟诗作文等等都变成创造性发挥的领域,真正以一种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而不再为人生有限、功名无成感到悲哀。从在仕途求得功名的执着到渐渐看清功名如幻,在更广阔的人生领域中体会“人”②的生存价值,苏轼对于创造性的发掘更加深广,也体现出更为成熟的“寄寓”思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青年苏轼已然是一个萌芽时期的“寄寓”者,他有着对于人生有限和世事无常的思索和体认,又以“知命”的积极态度面对人生。但因经历的有限,这一时期他对于人生本质的体认并没有深重的现实内容作为支撑,发挥创造性的方式也不及后期那么广阔。但思想的发展终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是青年时期对于人生本质的思考,以及积极有为地创造,为苏轼在之后的宦游生涯中超越深重苦难,达到更高的人生境界提供了可能。
最后要谈及的,是签判凤翔时期在苏轼一生中的意义。这段时期的记忆在苏轼之后的文学书写中很少被提及,确实,如果要与卷入党争之后起落不定的人生相比,这段仕宦经历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但是并不因此就失去了讨论的价值。这个宦游的起点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解苏轼一生思想心态发展的线索:在情感上,对于亲人和故乡的思念,对于自然山水的喜爱贯穿了他的一生;在仕途中,勤勉踏实的作为、亲民爱民的信念是他始终未变的初心;人生有限的忧虑、仕与隐的矛盾、世事无常的感慨,是他反复思索并不断超越的生命困惑。由此可见,苏轼在仕途的起点就已经昭示了许多将要贯穿他一生的命题,在之后的宦游生涯中,它们或被延续,或被超越,直至生命的完成。
注 释:
①相关的研究有曾枣庄《岐梁偶有往还诗——二苏合著〈岐梁唱和集初探〉》,对苏轼兄弟在凤翔和开封两地所写的唱和诗作了专门的探讨,邱俊鹏《苏轼少年时期思想探微》阐释了苏轼少年时期的思想矛盾,张文利《论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诗歌创作》、任永辉《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散文创作》分别论述苏轼这一时期诗、文的创作情况。
②王水照、朱刚在《苏轼评传》中认为,以“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伦理观念,是把人当作“臣”来要求,而佛老哲学对这一观念的补充则重在让人放弃“臣”的身份和责任,过着超脱世外的“僧”的生活,这二者的的互补其实取消了“人”的生存方式,而苏轼还归于“人”的生存境界,并将这种状态下的人生内涵体现得无比丰富。(参见《苏轼评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46-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