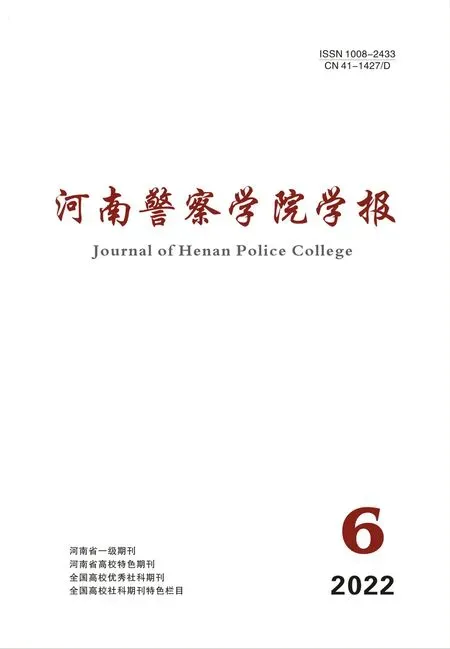对我国量刑情节传统分类之质疑
陆诗忠
(烟台大学 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对量刑情节中的某些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持续的研究,进而形成了不少共识。共识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量刑情节”内涵的理解上。尽管我国刑法学界对此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但并不存在重大的分歧,即不约而同地均将量刑情节定位于定罪事实以外的影响刑罚裁量的某些具体事实情况[1]。二是对“量刑情节”种类的划分上。我国刑法理论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量刑情节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从宽量刑情节与从严量刑情节、罪前罪中和罪后量刑情节、应当量刑情节和可以量刑情节、单幅度量刑情节和多幅度量刑情节、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量刑情节与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同向量刑情节和逆向量刑情节[2]331—339。
本文对“量刑情节”内涵的理解与主流刑法理论并无二致,但学界对量刑情节进行的上述分类,在本文看来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比如,论者将量刑情节分为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量刑情节与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罪前罪中和罪后量刑情节,就难以得到本文的认同。
一、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是否包括“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
主流的刑法理论认为,我国的量刑情节包括“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在本文看来,上述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以本文之见,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任何一个量刑情节都没有体现人身危险性,也不应当体现人身危险性。下面撷取几个典型的量刑情节予以说明,这些典型的量刑情节在理论上通常被认为是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
(一)自首
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对于自首者,立法者为什么要规定从宽处理(包括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处罚)?对自首者从宽处罚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对此,主流的刑法理论认为,有自首行为的,说明其人身危险性较小。比如,有学者认为:“确认自首者可以从宽处罚,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基于因自首而使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减小或者消除,而是因为犯罪人的自首反映其对犯罪行为有所认识和悔罪的表现,即使是因慑于法律的威力而洗手不干,也反映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减弱或消除。”[2]387“自首在本质上,是犯罪人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给国家追诉,它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或者在被动归案后的坦白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自首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减小。”[3]263在本文看来,主流刑法理论对自首从宽处罚的根据进行的阐释并不能令人信服。首先,对于缺乏悔过自新心理但能够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分子,依据刑法规定,这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如此“自首”的犯罪分子很难说其人身危险性减小。其次,《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从该条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刑法对不同自首者是视不同情形予以轻重不同的处理的。“轻重不同的处理”完全取决于自首者所实施的犯罪轻重程度,这与自首者的人身危险性状况并无关联。仅仅基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将自首从宽处罚的根据归结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状况。另外,在理论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具有持续性、不间断性,关涉到其将来犯罪的可能性。行为人在犯罪后是否自首与他将来是否会继续实施犯罪,是没多少关系的。
本文进一步认为,我国刑法之所以对自首者规定从宽处罚,是基于刑事政策方面的考量。具体来说,这是因为其自首行为会使得案件的侦查(调查)、起诉与审判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能够给司法机关、监察机关顺利进行侦查(调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便利,进而使得司法机关、监察机关打击犯罪的行为最大效益化。为此,国家对犯罪分子的“合作表现”应当予以“奖赏”,即在对其刑罚裁量时予以从宽处理。一言以蔽之,自首从宽处罚的根据完全在于国家行为的功利性,与犯罪者的人身危险性并无关联。
(二)立功
“立功”作为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案件,以及其他有利于预防、查获、制裁犯罪的行为。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犯罪人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立功者,立法者为什么要规定对其从宽处理(包括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处罚)?对立功者从宽处罚的根据是什么?对此,学界普遍性地将其归结于立功者的人身危险性:“行为人在犯罪后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表明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痛恨,因而其再犯可能性会有所减小。”[4]568“我国刑法设立立功制度,主要是因为立功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立功犯的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小,同时立功表现可以帮助司法机关及时破获犯罪案件。”[5]798在本文看来,将人身危险性的减小理解为对立功者从宽处罚的根据同样是靠不住的。其一,如果说人身危险性的减小是立功制度从宽处罚的根据,那么有立功行为的犯罪人必然是人身危险性小的人。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犯罪人“在犯罪后能够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在犯罪后能够提供重要线索”,其动机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无法排除那些具有以立功换取较轻刑罚处罚的意图的人,而有此意图的人,很难说其人身危险性较小。其二,如果说人身危险性减小是立功制度从宽处罚的根据,那么受到更轻刑罚处罚的重大立功者应当是那些人身危险性更小的人。但是如此理解并不符合我国刑法对立功的规定。从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来看,重大立功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提供重要线索,从而使得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得以侦破的等。换言之,在立法者看来,某行为能否被认定为重大立功,完全取决于犯罪人所揭发罪行是否重大,取决于其提供的重要线索能否使得重大案件得以侦破。很显然,重大立功的认定与立功者的人身危险性状况并无任何关联。其三,在理论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具有持续性、不间断性,关涉到其将来犯罪的可能性。行为人在犯罪后是否有立功表现,这与他将来是否会继续实施犯罪,是没有多少关系的。
本文进一步认为,我国刑法对立功者之所以规定较轻的刑罚处罚,与立功者的人身危险性状况没有任何“瓜葛”,而是因为“司法成本的经济性”。刑罚作为对犯罪的惩治手段,需要一定的物质支撑,尤其是侦查(调查)、起诉、审判的运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或者提供他人犯罪的重要线索”的立功行为恰恰能够使得办案成本的支出大大降低,节省国家的司法资源,进而有助于诉讼效益与效率的提高。为此,需要对立功者予以法律上的褒奖,即在刑罚裁量时予以从宽处理。一言以蔽之,对立功者予以从宽处罚的根据仅仅在于司法功利效果方面的考虑,这仍然是刑事政策方面的考量。
(三)累犯
依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累犯要从重处罚。立法者对累犯为什么规定要从重处罚?对累犯从重处罚的理论根据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的普遍认识是,被认定为累犯的人有着较大的人身危险性:“累犯之所以从重处罚,主要是因为累犯与初犯相比,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累犯已经因为犯罪被判处一定的刑罚,经过刑罚的实际执行,又重新犯罪,表明其屡教不改,再犯可能性大,因而应当从重处罚。”[5]786“与初犯相比,累犯因无视前刑的体验而具有更大的再犯罪可能性,故许多国家的刑法采取有效措施对累犯进行严厉制裁。”[4]561在本文看来,如此理解是经不起推敲的。若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理论根据解释为行为人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则不好解释在个别情况下犯罪人再次犯罪不是因为无视自己的刑罚体验,而是由于其他特殊原因,比如因受被害人的严重迫害而故意犯罪。基于如此原因而再次犯罪的,就不能说犯罪人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也就是说,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仅仅将其归结为其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很显然是不够科学的,具有片面性。那么我们能否说,对累犯从重处罚的理论根据是“再次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呢?显然也是不能的。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形式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程度都是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包含主观罪过形式、犯罪目的、犯罪动机)和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作为犯罪形式之一的“再次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同样应取决于“主观恶性(包含主观罪过形式、犯罪目的、犯罪动机)”和“客观危害性”。质言之,“再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与“初次犯罪”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性相比并无特别之处。是故,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理论根据无论是解释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还是解释为“再次犯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都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进一步认为,对累犯予以从重处罚仍是刑事政策方面的考量:经过刑罚体验的犯罪人竟然再次犯罪,这表明行为人与法律是不合作的,在政策上具有强化应受谴责的必要性,即应予以较重的刑事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并不包括“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即便从批判刑法学的角度来看,“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也不应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其一,人身危险性并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如将“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作为量刑情节,那么法官在对被告人裁量刑罚时必须要判断其人身危险性。可是,如何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以及人身危险性的程度?现代科学还没有达到能够预测一个人将来是否会犯罪的水平,从目前来看并没有可行的操作方案。既然不存在测量人身危险性的科学方法,被告人基于人身危险性程度所承受的刑罚就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依据。因此,基于不确定的主观臆测而对被告人削减或添加预防刑的量,就是错误或非正义的,“在未确立人身危险性或反社会人格的具体测量标准下,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必然陷入定罪量刑上的主观臆断,甚至刑及无辜,这已有惨痛的教训”[6]。其二,将“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作为量刑情节难以形成公众法情感的认同。一方面,被告人因此有可能在其责任刑之上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导致其权益被过度剥夺。因为即使被告人所犯之罪轻微,但由于该罪能够显示其具有较强的犯罪倾向,也可以对之处以严厉的刑罚。另一方面,被告人还因此有可能在责任刑之下承担较轻的刑事责任,这将不利于对刑法法益的保护。也就是说,如果被告人没有人身危险性或者人身危险性较小,即使是极为严重的犯罪,也可以对其处以较轻的处罚,然而,上述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出现相同社会危害性程度的犯罪行为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处罚,这必然会导致公众对法情感认同的缺乏。因此,既然刑罚要与责任相适应,就不宜将“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作为量刑情节。
本文反对将“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事实”作为量刑情节,这不仅对于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当前的刑事司法也具有纠偏的价值。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随机选取了特定期间内特定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作为研究样本,并以一些重大社会影响案件作为辅助性研究素材,对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状态与特征等进行了研析,发现人身危险性已经成为裁判文书上的“高频词”。本文还注意到,裁判文书大多没有阐明被告人为什么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或者较小的人身危险性,比如,(2019)粤0305刑初1495号刑事判决写道:“综合考虑被告人吴桂耿、吴小颖的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认罪态度等,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桂耿、吴小颖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其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亦可达到惩戒之目的,本院决定对被告人吴桂耿、吴小颖适用缓刑。”在本案中,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适用的,但是裁判文书并没有说明其依据是什么。再比如,(2008)下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写道:“本案中被告人马某、李某携带事先准备的犯罪工具,已选定对象尾随伺机抢劫,虽因客观原因而未着手实施未造成损害后果,但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故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即使有的裁判文书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有所阐述,也大都采用犯罪手段、犯罪后果予以佐证,但如此“佐证”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有重复评价之嫌。比如,(2009)浙温刑初字第150号判决书写道:“吴书义虽系受纠集者,但其事先与被害人不存在直接纠纷,却积极参与殴打,也足见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依法应认定为主犯。”再比如,(2009)汴刑终字第100号刑事裁定书写道:“经查,被告人朱敬甫虽伙同他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了被害人,但在绑架过程中并未伤害、体罚、虐待被害人,后因未勒索到赎金主动将被害人送到村干部家,其绑架他人的行为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二、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是否包括“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情况”
权威教科书认为,体现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量刑情节,是指主观上或者客观上说明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量刑情节,如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犯罪对象等即属于此类情节,它们大都是在犯罪过程中发生的[3]256。 该观点获得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2]338-339。但在本文看来,将“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之一并不妥当。本文并不否认,诸如“犯罪手段”“犯罪结果”之类的事实的确能够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但将其视为量刑情节,这恐怕与我国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是不够契合的,而且在理论上也难以立足。
“犯罪手段”“犯罪结果”,其影响的往往并不是具体的刑罚裁量,而是法定刑的升格。这可以从我国相关刑法规定上予以求证。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或者造成严重残疾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此规定中,“犯罪手段”很明显是影响故意伤害罪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此规定中,“犯罪结果”很明显是影响非法拘禁罪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即便在某些犯罪中,“犯罪手段”“犯罪结果”不是影响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也是确定基准刑的因素。也就是说,“犯罪手段”“犯罪结果”是不能够成为量刑情节的。
从刑法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应当将“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理解为量刑情节。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因为“犯罪手段”“犯罪结果”与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一样,是决定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基础性因素。如果说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低配”,那么“犯罪手段”“犯罪结果”则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中配”“高配”。如果我们将“犯罪手段”“犯罪结果”视为量刑情节,就无法解释我国的法定刑是“相对确定法定刑”这一客观现实。在本文看来,我国刑法之所以给所有的犯罪所配置的刑罚都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就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任何一个犯罪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等其他的犯罪事实,而这些犯罪事实影响着社会危害性程度。质言之,为了能够对具体个案的处理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立法者必然会将法定刑配置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而且所配置的法定刑必然会融入“犯罪手段”“犯罪结果”这样的事实。在此意义上,犯罪手段、犯罪结果要么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要么是确定基准刑的基本事实,而不应成为量刑情节。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犯罪对象”作为量刑情节是否存在法理上的自足性?在本文来看,“犯罪对象”同样不能成为量刑情节。这是因为,将“犯罪对象”视为量刑情节,会过于强调犯罪对象在犯罪社会危害性整体评价中的权值,同时也不符合适用刑法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首先,在理论上犯罪的本质被认为是对犯罪客体的危害,并非是对犯罪对象的危害。我们须知,犯罪对象的不同并不会导致犯罪客体的变化。其次,“量刑上一律平等”是“适用刑法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应有之义,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犯罪对象的不同会对刑罚的裁量产生影响,这其实是对被告人量刑的重大不公,也就无法做到“量刑上一律平等”。
我们也注意到,从相关规定来看,犯罪对象似乎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来对待的。比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的严重程度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但这里的“犯罪对象”均具有特殊性,已经超出了犯罪对象的一般意义:它要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犯罪客体,要么体现为特定的刑事政策。详言之,强奸罪中的“幼女”恰恰体现的是被害人的身心健康这一犯罪客体;我国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将“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规定为特殊的犯罪对象,这其实是在贯彻执行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予以特别保护的刑事政策。而这种“特别保护”的背后并不必然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有不少学者将“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预备”都理解为“量刑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也将“未遂犯”视为量刑情节,但在本文看来,上述理解是存在疑问的,并不符合量刑情节的基本内涵。众所周知,量刑情节必须是定罪事实以外的“事实情况”,而“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在刑法理论上是犯罪行为进展过程中基于各种原因而停止下来的犯罪形态。某个行为能否被认定为“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取决于相关犯罪事实(比如犯罪停止的时空因素、犯罪结果是否发生、犯罪行为停止下来的原因,等等)的认定,而这些事实都是犯罪过程中所出现的事实,自当属于定罪事实的范畴。我们怎么能将犯罪过程中所出现的“定罪事实”理解为量刑情节呢?这岂不是有重复评价的嫌疑?再者,我们思考一下诸如“累犯”“自首”“立功”这些典型的量刑情节,就不难发现,它们都非犯罪过程中所出现的事实,并不属于犯罪行为本身。在此意义上,我们也不宜将“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预备”理解为“量刑情节”。
本文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还将“从犯”视为量刑情节。但这同样是不够妥当的。我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根据该规定,某犯罪行为是否为从犯行为,取决于该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这里的“作用大小”完全取决于犯罪行为过程中所展现的特定事实,其自当属于定罪事实的范畴。是故,基于同否认“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预备”为量刑情节同样的道理,从犯也不能被理解为量刑情节。
此外,在理论上将“盲人犯罪”“聋哑人犯罪”视为量刑情节也是不合理的。这是因为,“盲人犯罪”“聋哑人犯罪”同样属于犯罪事实的范畴,且对他们从宽处罚,也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而并非社会危害性的考虑,具体来说是国家对残疾人予以“特别扶助”的法律政策在刑法的具体体现。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将“坦白”“当庭自愿认罪”“退赃、退赔”“ 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规定为量刑情节,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量刑情节并非体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事实。道理很简单,上述量刑情节并非犯罪行为本身,而是犯罪行为结束之后所出现的某些事实。
需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体现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事实本身是不可能成为量刑情节的。这是因为,如果量刑情节真的能够体现社会危害性,那么所有的量刑情节就必然是“应当”量刑情节,不可能存在“可以”量刑情节。其理由就在于,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体现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量刑情节,必然会影响到量刑,也必然会成为“应当”量刑情节。然而,刑法的相反规定,“无情”地告诉我们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量刑情节,不可能是体现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事实。
综上分析,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量刑情节既不体现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也不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所体现的是我国相关的刑事政策。这样理解就能够较好地解释为什么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量刑情节绝大多数都属于“可以”量刑情节了。这是因为,刑事政策不能违背法治原则,法治原则的基本理念和精髓就是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律不仅仅是事实,它也是一种观念或者概念,此外它还是一种价值尺度”[7],是检验其他社会系统的价值标准。在刑事政策领域,法治原则要求国家和社会对犯罪作出的一切公共反应,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刑事政策作为社会系统内的子系统也必然要以法律为价值标准。在此意义上,法治原则的神圣使命就是要对刑事政策进行整体制约,刑事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受到法律的支配和约束。也就是说,刑事政策意义上的量刑情节对刑罚裁量的影响应当是有限的,必须受到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制约。即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的时候,刑事政策意义上的量刑情节将无法发挥作用;而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尚不够极其严重的时候,刑事政策意义上的量刑情节可以对刑罚的裁量产生影响。
三、我国刑法中是否有“酌定量刑情节”
酌定量刑情节是指法律没有作明确而具体规定的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和实务上都获得了普遍的承认:酌定量刑情节是审判人员在量刑时应酌情考虑的各种事实情况。不过,在笔者看来,将“酌定量刑情节”纳入我国刑罚裁量情节体系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
其一,“酌定量刑情节”与罪刑法定原则无法“和谐相处”。如果我们承认“酌定量刑情节”的存在,就意味着审判人员在量刑时应当考虑此类事实情况。但问题是,审判人员考虑“酌定量刑情节”在法律上有无依据?进一步说,如果审判人员考虑酌定量刑情节,这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我们须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只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其实,罪刑法定原则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其他内涵。比如,刑法所规定的刑种如何适用、各种罪的具体量刑幅度以及影响刑罚裁量的因素有哪些,这均应当由刑法加以规定。如果“影响刑罚裁量的因素”(即量刑情节)有哪些,不是由刑法予以规定,而是由司法者予以灵活掌握,这就难以为罪刑法定原则所接受。一方面,酌定量刑情节并非法律明确规定,却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轻重产生积极影响,这就使得酌定量刑情节的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强烈的抵牾。另一方面,酌定量刑情节的存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严重不符。罪刑法定主义意味着立法权限制司法权,“司法权如果没有立法的限制,擅断就不可避免,专横也在情理之中”[5]88。总之,只要我们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坚持刑罚量的增加与减少都应当有法律的明文规定,酌定量刑情节在刑罚裁量情节体系中就不应存有一席之地。
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承认酌定量刑情节与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该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该条规定明确了量刑的基本原则为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的“犯罪事实”是指“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这里的“法律”就是指刑法。然而,一方面,酌定量刑情节属于定罪事实以外的事实,它不可能属于“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范畴;另一方面,酌定量刑情节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由法官予以灵活掌握的事实,它很显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范畴。既然酌定量刑情节既不属于“犯罪事实”的范畴,适用酌定量刑情节又不是“以法律为准绳”,那么理论上、实务上就不应承认酌定量刑情节的存在。
其二,“酌定量刑情节”与法定刑的配置因素形成悖论。刑法理论通常认为,酌定量刑情节主要有以下几种:(1)犯罪的手段;(2)犯罪的时间、地点;(3)犯罪对象;(4)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5)犯罪的动机;(6)犯罪后的态度;(7)前科(1)在这7种酌定量刑情节中,“犯罪对象”不应成为量刑情节。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既然“犯罪对象”不能成为量刑情节,当然也就不能成为酌定的量刑情节。。
在笔者看来,在上述酌定量刑情节中,“犯罪的手段、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的对象、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犯罪的动机”应当是法定刑的配置因素,立法者在为具体个罪配置法定刑时已经充分考虑了上述因素。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才能够正确解读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有关“起点刑”“基准刑”“宣告刑”的规定。根据该意见,对“起点刑”进行修正而形成的是基准刑,这里的修正因素恰恰是诸如犯罪手段、时间、地点、次数、后果、动机之类的其他构成事实。这就足以说明,这里的“其他构成事实”其实就是法定刑的配置因素。如果我们再将“犯罪的手段、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的对象、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犯罪的动机”理解为“酌定量刑情节”,其实就是在否定其为法定刑的配置因素,而这与立法事实不符。
其三,“酌定量刑情节”与刑法的相关规定严重不符。在笔者看来,将“犯罪后的态度、前科”理解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由法官在量刑时予以灵活掌握,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犯罪后的态度”不宜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犯罪后的态度”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刑法不可能认可所有的“犯罪后的态度”,它肯定是有所选择的。实际上,我国刑法只是认可了“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积极赔偿、退赃”属于“犯罪后的态度”范畴,而对其他的“犯罪后的态度”是不予承认的。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和实务上承认其他“犯罪后的态度”是量刑情节,显然与相关的刑法规定不符,这其实就等于人为扩大了刑法的认可范围,是对刑法规定的明显违背。再者,“前科”也不宜理解为酌定的量刑情节。从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来看,刑法并不是认可所有的“前科”,它只是有条件地承认特定的“前科”即累犯。将“前科”视为酌定量刑情节,意味着不仅“累犯”这一前科要从重处罚,累犯以外的其他“前科”也要受到从重处罚,这显然是不符合《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的。
四、将量刑情节分为“罪前量刑情节” “罪中量刑情节” “罪后量刑情节”是否妥当
在我国刑法理论上,根据量刑情节与犯罪行为在时间上的关系,将量刑情节分为罪前量刑情节、罪中量刑情节和罪后量刑情节。所谓罪前量刑情节,是指在犯罪实施之前所出现的对量刑具有影响的各种事实情况。比如,犯罪人的一贯表现、前科即属于这一类量刑情节;所谓罪中量刑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所出现的对量刑具有影响的各种事实情况,如犯罪结果、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等,均属于这一类量刑情节。罪后量刑情节,是指在犯罪实施完毕后所出现的对量刑具有影响的各种事实情况。比如犯罪后的表现即属于这一类量刑情节。
在本文看来,我们应当只承认罪后量刑情节,而不应当承认所谓的“罪前量刑情节”和“罪中量刑情节”。不应承认“罪前量刑情节”,因为诸如“犯罪人的一贯表现、前科”并没有被刑法认可为量刑情节,自应排除在量刑情节之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理论上,“犯罪人的一贯表现”能否对量刑产生影响?在本文看来,这是不能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犯罪人的一贯表现”之所以在理论上和实务上被认可,是因为其体现着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状况,但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认可人身危险性。这在前面有关章节中已经进行了论证,此处不赘。
之所以不应承认“罪中量刑情节”,是因为诸如“犯罪结果、犯罪手段、犯罪动机”之类的“罪中量刑情节”都是犯罪事实,属于确定基准刑的考量因素,故而应排除在量刑情节之外。之所以承认“罪后量刑情节”,是因为它属于定罪事实之外的事实状况。当然,我们并不是承认所有的“罪后量刑情节”,我们只是承认刑法所规定、认可的罪后量刑情节。
五、结语
量刑情节的科学分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无论是对我国量刑情节体系的立法完善,还是对有关量刑情节的规范性司法文件制定,抑或是量刑情节的司法适用都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从已有的量刑情节来看,应该说我国的量刑情节有很大的立法空间。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所有的量刑情节,都是体现刑事政策的量刑情节,并没有体现社会危害性的量刑情节,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我国刑法应当考虑设置一些能够体现犯罪社会危害性已经降低的罪后量刑情节,比如,退赃、积极赔偿,并将其设置为“应当”量刑情节。另一方面,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体现人身危险的量刑情节在法理上不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刑法今后增设量刑情节时,就不应增设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
既然我国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量刑情节体现的都是相关刑事政策,那么基于立法与规范性司法文件的应有关系,有关量刑情节的规范性司法文件就只能增设体现相关刑事政策的“可以”型量刑情节,否则应为无效的司法文件。
本文对“我国量刑情节都属于刑事政策意义上量刑情节”的揭示,对量刑情节的适用具有一定指导价值。既然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都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那么根据刑事政策与法治之间的应有关系,“可以”型量刑情节的具体运用应当取决于犯罪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不应是其他因素。再者,酌定量刑情节存在的“非法性”“不合理性”决定了其应是司法实践中所被驱逐的对象。最后,理论上所谓的“罪前量刑情节”都是体现行为人人身危险的事实,然而,“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的事实”都是一些有悖基本法理的事实,而且与现有的刑法规定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因此司法实践中将“犯罪人的一贯表现、前科”纳入量刑之中的做法应当被“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