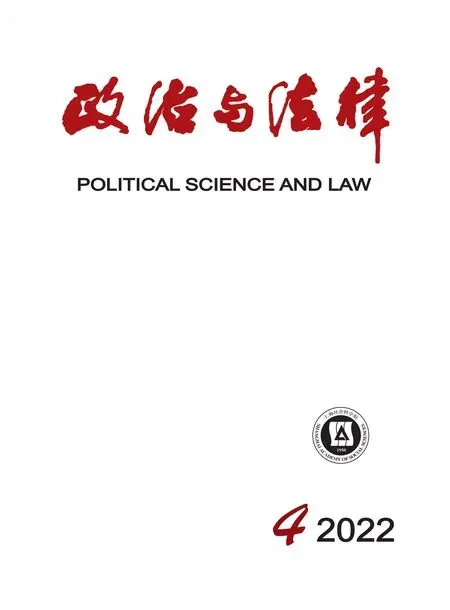刑法因果关系中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区分
李会彬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1)
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理论中最为复杂也最具有争议性的理论之一。至今已发展出条件说、合法则的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危险现实化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等多种学说。自合法则的条件说开始,学者们就有意识地将规范评价的内容纳入因果关系的判断中,从导致结果发生的自然意义上的诸多条件中,选择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条件作为结果发生的原因。毋庸置疑,将规范评价的因素纳入因果关系理论中,对于判断复杂因果关系中的结果归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规范评价内容的引入,势必产生事实判断因素与规范评价因素的区分问题,即在复杂因果关系中,某些以相对不确定性或者概率形式出现的事由,究竟是事实判断问题还是规范评价问题?例如,择一因果关系中的不确定事由,究竟是一个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历来存在争议;客观归责理论中的风险升高理论,也因疑似将事实判断的内容错误地归入规范评价的范畴而受到广泛置疑。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区分至关重要,前者依赖于证据法裁判原则进行判断,后者依赖于实体法的价值评判标准进行判断,两者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淆。但就目前来看,学界存在着将部分事实判断问题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进行解决的倾向,客观造成了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侵袭现象,从而不当规避了程序法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对入罪条件的限制,导致了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张。基于此,笔者就刑法因果关系中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区分问题展开探讨,并意图构建区分标准,以利于司法实践中刑法因果关系的准确认定。
一、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因素与规范评价因素
就绝大多数相对简单的刑事案件而言,刻意区分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因素与规范评价因素的意义不大,因为,两者一般情况下是一致的,确定了事实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就确定了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例如,甲用刀将乙杀死,无论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判断,还是规范上的因果关系判断,甲的行为都是导致乙死亡的原因。但对于复杂的刑事案件,如多因一果和存在介入因素的刑事案件,就需要在明确了自然意义上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从规范评价上明确哪一个条件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以将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因此,事实判断因素与规范评价因素都是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同时,由于两者属于不同层面的东西,在适用时应予以严格区分。
(一)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因素
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因素是指自然意义上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一般认为,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说”主要从事实层面理解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即如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确立了“若无前者,则无后者”的自然因果联系,则行为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175 页。据此,事实因果关系主要是依据客观规律和自然法则予以确定,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客观属性。由于“条件说”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因果关系的自然属性,因此,引入规范评价内容的其他因果关系理论,虽然都对“条件说”进行了批判,但依然是建立在“条件说”(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也即,即使需要对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规范评价,也必须遵循因果关系的自然属性,先确定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再以某种标准如“相当性”或者“危险关联”确定该种原因是否应该归责于行为人。〔2〕参见刘艳红:《客观归责理论:质疑与反思》,载《中外法学》2011 年第6 期。以常见的“介入车祸案”为例,甲朝丙开了一枪,丙受重伤,后丙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在送医途中遇到乙酒后驾车发生了车祸,丙当场死亡。在对本案中的因果关系进行规范评价之前,首先必须明确事实上的因果流程,即甲的行为和乙的行为是导致丙死亡结果发生的条件。只有在这些事实清楚的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从规范评价上确立一个标准来判断介入因素是否中断了因果关系,从而最终确定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究竟应归于甲的枪击行为还是乙的酒驾行为。假如本案中事实上的因果流程不明,如枪击行为是否为甲所为不能查清,酒驾者是否为乙也不明确,那么,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规范评价也就毫无意义。只有确立了“行为与结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客观联系才有资格成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3〕参见董玉庭:《从客观因果流程到刑法因果关系》,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5 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事实因果关系是规范评价的对象或者素材,如果事实因果关系不清,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规范评价也难以保证客观公正。这决定了引入规范评价因素的各种因果关系理论的具体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评价的对象或者素材都是相同的,其判断的基本流程也是相同的,即首先进行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然后再进行规范评价,同时,事实判断因素是各种引入规范评价因素的因果关系理论存在的基础。
(二)刑法因果关系中的规范评价因素
在刑法中探讨因果关系的目的在于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仅进行因果关系的事实判断,在存在复杂因果关系的案件中并不能完成刑事责任的结果归责,这也是在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引入规范评价因素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事实因果的判断,只涉及认定关系链是否存在的问题,不涉及关系链是否中断的问题,是价值无涉的事实判断过程。〔4〕参见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9 页。仅仅将其当作一个事实问题来把握,难以完成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中所担当的使命。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还应当从刑法角度加以考察,使之真正成为客观归咎的根据。〔5〕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第 283 页。仍以上文所举“介入车祸案”为例,按照“若无前者,则无后者”的自然因果关系公式,甲和乙的行为都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时,如何进行结果归责就成为问题。一则,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对他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6〕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76 页。但从自然因果流程来看,甲的枪击行为并没有直接造成丙的死亡;乙的行为虽然直接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但如果没有甲的枪击行为,就不会发车祸,也不会造成丙的死亡。因此,将死亡单独归责于甲或者乙似乎都不合理。二则,二者并非共犯,不能根据“部分负担全部责任”的原则将丙的死亡同时归责于甲和乙。因为,除共同犯罪以外,“部分负担全部责任”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其他犯罪类型。〔7〕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69 页。因此,仅从事实因果关系角度进行判断,并不能完成复杂因果关系中的结果归责。这时,引入规范评价的因素,就有助于解决复杂因果关系中的归责问题,即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刑法规范的要求确定一定的标准,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异常,初始行为是否实现了法不允许的危险,如果介入因素异常,初始行为没有实现法不允许的危险,则不能将丙的死亡结果归责于甲,反之,则应将死亡结果归责于甲。由于介入因素是否异常、行为是否实现了法不允许的风险的判断,主要依赖于人们的经验和刑法的规范要求设定的一定标准确定,并且不能依据证据法的原则予以直接证明,因此,它属于规范评价的因素。基于此,如果说事实因关系是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客观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8〕参见[美]卡茨·穆尔:《刑法基础》(影印本),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4 页。那么规范评价因素则是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基础之上的,以人的经验和价值观念为基础、不能用证据直接证明的价值评判标准。
(三)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事实判断主要是从自然意义上理解刑法因果关系,实现因果关系的自然因果流程的判断,揭示了刑法因果关系的自然属性;规范评价则是根据人们的经验和刑法规范设定一定的标准从事实因果关系中发掘出具有刑法意义的原因,实现结果归责的判断,揭示了刑法因果关系的法律属性。以这一对基本概念为基础,可以总结出两者具有如下关系:(1)两者是评价对象与评价标准的关系。事实判断用于明确规范评价的素材,确立了自然意义上的因果流程,也就确立了规范评价的对象;规范评价用于确立刑法意义上价值评价标准,它从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刑法规范中提炼出规范意义上的评判标准,以自然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判断对象,挑选出刑法意义上的条件作为结果发生的原因。(2)两者是客观判断与主观判断的关系。事实因果流程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能为人所直接感知、并且能够直接用证据予以证明的自然现象,因此,对事实因果流程的判断主要根据证据裁判规则运用各种证据进行客观判断。因果关系的规范评价,则是以人的生活经验和刑法价值观念确立的评判标准为基础,对事实因果关系进行刑法上的结果归责,它不能依据证据法规则运用证据予以直接证明,因此,主要表现为主体对事实因果关系的主观价值判断。(3)两者采用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由于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和规范评价属于不同层面的东西,这也决定了两者在判断时必须遵循不同的部门法标准,即事实判断采用证据法裁判原则确定的标准予以确定,并受刑事诉讼法“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约束。规范评价采用刑法实体法确定的标准予以确定,主要受刑法基本原则的约束,而不受“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约束。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因素与规范评价因素是刑法因果关系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两者对于解决复杂因果关系的结果归责问题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缺一不可。但同时,事实判断用于明确刑法因果关系的自然属性,规范评价用于明确刑法因果关系的法律属性,这也决定了两者必须采用不同的判断方式,即事实问题应依据证据法裁判原则予以确定,法律问题应根据刑法规范确立的价值评判标准予以确定。因此,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都必须予以严格区分,不能将事实判断问题纳入规范评价领域,也不能将规范评价的问题纳入事实判断领域,否则刑法学可能完全变成政治学科了。〔9〕参见易益典:《监督过失型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载《法学》2018 年第4 期。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发现,随着学界对刑法因果关系中规范评价问题的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似乎越来越强调刑法因果关系中规范评价的作用,甚至有意模糊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多的在事实因果领域难于确定的事由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这可能会造成规范评价因素对事实判断因素的不当的侵袭,从而规避了程序法中“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对入罪条件的限制,造成了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接下来,笔者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二、刑法因果关系中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不当侵袭现象
在因果关系理论中引入规范评价的因素,有利于解决复杂因关系中的结果归责问题。但规范评价因素倾向于将事实因果关系中的某些以不确定或者概率形式出现的事由纳入其评价范畴,以价值判断的方式解决某些无法确切查清的事由,这虽有利于解决复杂因果关系结果归责的问题,但也可能造成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不当侵袭。根据笔者的观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已经出现了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侵袭现象,主要表现在合法替代行为的因果关系、择一的因果关系和概率型的因果关系中。
(一)合法替代行为的因果关系中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侵袭
合法替代行为的因果关系所讨论的问题是,行为实施了违法行为或者没有遵守和履行相关义务,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假如行为人实施了合法行为,或者遵守和履行了相关义务,损害结果仍然会发生,那么是否还能将危害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呢?〔10〕参见海尔穆特·库齐奥、张玉东:《合法替代行为:因果关系与规范保护目的》,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 年第5 期。以德国著名的山羊毛胡案为例:一家画笔厂的厂长,没有遵守规定对山羊毛胡进行消毒,就让他的女工们对山羊毛胡进行加工,四名女工因此感染了炭疽杆菌而死亡。后经过查明,当时的消毒流程并不能将这种欧洲当时尚不知晓的细菌杀死(案例1,山羊毛胡案)。〔11〕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一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5 页。本案中的事实因果流程是清楚的,但由于本案是一个不作为的犯罪,要实现对不作为行为的结果归责,就需要明确不作为与作为的等价性,因此,本案自始至终都需要纳入规范评价的因素进行判断。即在明确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除了确认厂长具有作为义务、具有履行能力之外,还要确认本案具有结果的避免可能性,才能最终确定厂长的不作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体到本案,其关键点在于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由于厂长即使履行了消毒义务,也不可能将炭疽杆菌杀死,也不能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它没有实现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不对死亡结果负责。由于结果避免可能性这一规范评价因素的判断,建立在“假设实施一定的被期待的作为,结果就不会发生的”〔12〕参见[日]大谷实:《刑法总论》(第二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210 页。的基础上,而不是以现实发生的因果流程进行直接的判断,并且需要融入判断主体的价值评判标准,因此,笔者将其称为假设型的规范评价因素。
假设型的规范评价因素,有利于解决合法替代行为因果关系的结果归责问题。但是,假设型的规范评价因素,也必须以事实的因果流程作为判断基础,如果事实的因果流程不清,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假设型规范评价也难以得到确切的结论。如果在不能得出确切结论的情况下仍然进行归责,则可能造成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侵袭。例如,按照德国的交通法规,汽车与行人必须保持1.5 米以上的距离,但行为人甲驾驶汽车超越行人乙时,只保持与行人乙0.75 米的距离,造成了乙的死亡。事后查明,乙由于醉酒倒在甲的汽车轮下,被汽车后轮胎压死。德国法院否认了甲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理由为,即使甲与乙之间保持了1.5 米以上的距离,乙的死亡结果仍然可能发生(案例2,违规超车案)。〔13〕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336 页。对于此案的判断,无论是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还是采用危险现实化理论,一般都只能得出甲不构成犯罪的结论。但是,坚持客观归责论的学者提出了“风险升高”的规范评价标准,按照这一规范标准判断,甲应当构成犯罪。其理由为,虽然不能确定被告人实施合法行为是否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但只要能确定被告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升高了法不允许的风险,即可实现结果的归责。〔14〕[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一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7 页。并且,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假设卡车司机保持安全车距,骑车人是否还会发生事故死亡,这是并未发生的假定因果关系,在不明时不应该依此对被告做有利的认定。〔15〕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版,第 163 页。这似乎有效解决了其与“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冲突问题(对于此问题后文还有详细探讨)。
笔者认为,首先,先不论这一规范评价标准是否合理,对上述情形能否进行规范评价就存在问题。这是因为,规范评价应当是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也即只有在事实因果关系清楚的情况下,规范评价才具意义。本案与上述的“案例1 山羊毛胡案”在事实因果关系层面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山羊毛胡案中,消毒行为不能杀死导致女工死亡的炭疽杆菌、女工并非死于消毒行为所应杀死的病毒感染这一事实是明确的,据此而进行“不具有避免可能性”的规范评价也就没有任何疑问。但在本案中,作为“假设被告人合法驾车,死亡结果是否会发生”的这一规范评价因素的基础事实是,被害人也同时醉酒并倒在了被告人车上,违规驾车行为是否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结果的事实并不明确。换言之,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究竟是被告人的违规驾车行为所致,还是被害人的醉酒行为所致是不明确的。在这一基本事实不明确的情况下,应首先依据证据法的裁判原则进行判断,而不是进行假设性的规范评价。上述主张“假设……,不应该依此对被告做有利的认定”的论者显然是混淆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之间的关系,意图以规范评价代替事实判断,从而规避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
其次,即使单从“风险升高”理论的内涵来看,“风险升高”只能说明“违法行为”的危险升高了,并不能说明违法行为必然导致事故,而且,即使导致事故也不必然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可以说风险升高与死亡结果之间还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并且中间还存在着“事故”这一中介,那么,因何风险升高了就要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就肯定了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我们似乎从“风险升高”理论中难以得到确切答案。如果非要推导出一个答案,也只能得出风险升高理论将犯罪既遂的标准进行了前移,即其实质上是在处罚导致危险升高的行为,而不管犯罪结果与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确切的因果关系,这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犯罪类型,而非单纯建立一种因果关系判断的规范标准。可见,风险升高理论的实质是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因果不清的问题,体现了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侵袭。
根据笔者的观察,合法替代行为因果关系中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侵袭现象不仅发生于理论探讨阶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相类似的案例。例如,被告人赵达文驾驶桑塔纳小客车由北向南行至北京市海淀区某路段时,因超速采取措施不及(这一路段限速为60 公/小时,赵达文当时车速为77 公里/小时),其所驾车辆轧在散放于路面上的雨水井盖后失控,冲过隔离带进入辅路,与正常行驶的杨某所驾驶的富康车和骑自行车正常行驶的相某、刘某、张某、薛某相撞,造成相某、刘某当场死亡;张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杨某、薛某受伤。经北京市某交通支队认定,被告人赵达文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该案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其中二审法院认为,因赵达文违章超速,故遇井盖后已无法控制车速,导致采取措施不及,是造成此次肇事的一个原因,……驾车行为本来就是一项高度危险作业,其有义务随时注意道路上的各种状态,以便采用有效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但赵达文超速行驶,致使其遇到紧急情况后,虽采取了措施,但已不可避免,造成了三人死亡、两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因此应承担刑事责任(案例3,赵达文案)。〔16〕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中刑终字第3679 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本案判决理由虽然没有直接援引客观归责论中“风险升高”的理论,但从其判决书中“因赵达文违章超速,故遇井盖后已无法控制车速,导致采取措施不及,是造成此次肇事的一个原因。同时,驾驶员驾车是一项危险作用,其有义务随时注意道路上的各种情况……”的语言表述来看,实际上包含了“风险升高”理论的内涵,即法院判决中隐含的逻辑是,赵达文驾驶汽车超速属于制造法所不允许的危险,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他都应该负责。〔17〕参见周光权:《风险升高理论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兼论“赵达文交通肇事案”的定性》,载《法学》2018 年第8 期。但是,本案在事实因果关系上就存在重大疑问,即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的后果,究竟是被告人的超速驾驶行为所致,还是随意散放于路面上的井盖所致,自始至终都没有查清,在基本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进行规范评价,将事故结果归责于被告人,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诚如周光权教授所言:“在没有侦查实验或其他有力证据对履行义务的结果如何进行确定时,直接认定结果归属于赵达文的超速行为,判决结论难以令人信服。”〔18〕周光权:《风险升高理论与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兼论“赵达文交通肇事案”的定性》,载《法学》2018 年第8 期。本案的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侵袭现象。
(二)择一的因果关系中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侵袭
择一的因果关系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分别能够导致结果的发生,但在行为人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竞合在一起导致了结果的发生。〔19〕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94 页。例如,甲与乙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同时开枪杀丙,且均打中了丙的心脏,丙死亡(案例4,两枪共效致死案)。〔20〕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175 页。本案中的事实因果关系是明确的,即甲和乙的枪击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均发生了作用,均可直接造成乙的死亡。但是,仅依靠事实的因果关系难以完成结果的归责。因为,根据若“无前者,则无后者”的事实因果关系公式,没有甲的行为,丙同样会死亡;没有乙的行为,丙也同样会死亡。这时就需要引入规范评价的因素进行进一步判断。条件关系修正说认为,如果除去一个行为结果将发生,除去全部行为结果将不发生,则全部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条件。甲乙均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既遂。〔21〕参见周光权:《刑法总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23 页。条件关系修正说虽然是建立在条件说的基础上,但是这种观点已纳入了规范评价因素的内容。即它打破事实因果关系判断的传统公式,将导致结果发生的多个条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归责时又将整体划分为部分分别判断,认为他们均独立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已充分体现了评判主体对事实因果关系的价值评价。当然,本案除了采用条件关系修正说进行判断外,也可以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以一般的社会经验为规范评价标准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相当性;或者采用危险现实化理论,以行为是否使危害结果的发生进一步现实化为规范评价标准进行归责;又或者采用客观归责理论,以是否实现了法所不允许的危险为规范评价标准,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但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标准进行判断,其基本前提都应该是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清楚的基础之上。
在择一的因果关系中纳入规范评价的因素,有利于解决其结果归责的问题,这种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进行规范评价的前提是,事实因果流程是清楚的。如上述“案例4 两枪共效致死案”进行规范评价的前提是,被害人死亡结果是无意思联络的甲乙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二人都击中了丙的心脏,发挥了相同的作用。但在现实中,能够确切无疑的运用证据证明“案例4 两枪共效致死案”的情形并不容易,很多类似案件处于事实因果关系不明的状态。例如,甲与乙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同时开枪杀丙,只有一枪命中了丙,丙死亡,但究竟谁命中的丙无法查清(案例5)。又或者,甲与乙在没有意思联络的情况下,同时开枪杀丙,一枪命中了丙腿部,一枪命中了丙的心脏,后查明命中心脏的一枪致丙死亡,但究竟谁命中了丙的心脏无法查清(案例6)。与上述案例4 相比,这两个案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即其基本事实因果关系不明,在案例5 中,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击中了丙,在案例6 中,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击中了丙的心脏导致丙死亡。在事实不清的基础上,即使这两个案件符合条件关系修正说的标准(除去两加害人的行为,死亡结果就不会发生),也不能适用该标准进行规范评价,只能按照证据法“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裁判原则,认定甲乙都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但部分学者认为,二人都应以杀人既遂处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无人对死亡结果负责,既不符合社会报应观念的要求,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22〕参见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5 年版,第353 页。并且,独立实施了能将他人杀死的行为,也导致了他人死亡的结果,既违反常识,也不合理,因此不能以未遂犯处理。〔23〕参见[日]大谷实:《刑法总论》(第二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2 页。还有学者指出,上述情形只有侵害了重大法益(造成他人死亡或者重伤的结果,或者其所犯罪名会被判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时,才能以犯罪既遂处理。其主要理由为,第一,这种因果关系并非纯粹的疑案;第二,刑法兼顾保护社会功能;第三,刑法不应遗漏罪行;第四,以既遂归责并非完全违反刑法原则。〔24〕参见张小虎:《论刑法替代因果关系的归责:理论基奠与事实根据》,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9 期。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无论采用哪种规范评价标准,也不论其规范评价标准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单就其在事实不清的状态下进行规范评价就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本案中究竟是谁的行为导致了丙的死亡并不明确(二人同时实施的行为各有50%的概率导致被害人死亡),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问题。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问题是一个可以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予以证明的问题。没有理由在不能查明时,就将其纳入规范评价领域,以规范评价标准进行结果归责。否则的话,是否任何因证据不足不能查清的问题都可纳入到规范评价领域进行解决呢?因为,上述论者的规范评价标准并不具有针对性,放在任何案件中皆可适用。那么,以此推之,在一些存疑概率更低的案件中,同样可以适用上述标准进行结果归责。例如,上述案例5、案例6 将死亡结果归责于甲和乙的错误概率为50%,而根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大量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案件,实际上比50%的错误概率要低得多,那么,是否就可根据上述规范评价标准将这些案件认定为犯罪呢?因为,将上述规范评价标准纳入到这些案件中同样适用,即这些案件的“错案概率较低,刑法兼具保护社会的功能,刑法不应遗漏罪行,疑案从有并非完全违反刑法原则”。〔25〕参见张小虎:《论刑法替代因果关系的归责:理论基奠与事实根据》,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9 期。但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将事实不清的因果关系问题纳入规范评价中去解决,混淆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之间的关系。
这一问题也同样不是一个仅存在于理论上的问题,我国也真实发生过相关的案件。例如,雷某与孔某相约比赛枪法,以8.5 米远处一树干上的废瓷瓶为比赛目标。两人共用一支JW-20 型半自动步枪轮流各射击三发子弹,均未中的,其中一发子弹穿过树林,将行人龙某打死,不能查明击中被害人的子弹由谁所发。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及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两被告人构成过失犯罪,分别判处4 年有期徒刑,但没有适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案例7,两枪过失致人死亡案)。〔26〕参见程新生、汤媛媛:《共同过失犯罪与刑法因果关系——“从误射行人案切入”》,载《法律适用》2008 年第9 期。在本案中,事实因果关系是不清楚的,雷某或者孔某打死丙的概率也都各有50%,无法确定死亡结果究竟由谁引起。同时,本案中的二人主观上应为疏忽大意的过失,而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共同犯罪仅限于共同故意犯罪,不能根据“部分负担全部责任”进行归责。因此,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两被告人都不应该构成犯罪。既然如此,法院因何将死亡结果归责于雷某和孔某呢?由于原判决书没有进行详细的说理,我们已不能知晓当时法官的判案依据。但根据笔者的推测,其很可能和上述论者的逻辑是一致的,即从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不应放纵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被害人利益等一般的刑法价值目标考虑,对两被告人均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了刑罚。这实际上是以实体法上的价值评判标准来弥补事实因果判断上的不足。本案的判决结果,同样体现了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侵袭现象。
(三)概率型的因果关系中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侵袭
概率型的规范评价因素是指,一个行为是否导致结果的发生,不能依据证据法规则予以明确证明,只能以概率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将概率的高低作为规范评价的标准,以确定结果的归责。如在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中,介入因素的判断就只能以概率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能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进行证明。例如,甲欲杀丙,用刀将丙砍成重伤,丙生命垂危,在医治中,由于医生乙的一般医疗过失行为,丙死亡(案例8,介入医疗过失行为案)。本案中基本事实因果关系是清楚的,即甲致丙重伤,乙的一般医疗过失行为直接使重伤的丙死亡。但如何进行结果归责,仅依靠事实因果关系无法得出结论,这就需要进行规范的评价。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观点,需要结合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判断:(1)实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引起危害结果;(2)介入因素是否异常;(3)介入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27〕参见黎宏:《日本刑法精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4 页。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不能以精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只能以概率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对于实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判断,只能得出致人重伤的行为比致人轻伤的行为,所引起的致他人死亡结果的可能性要大,至于大多少,无法得出精确的数据。再如,对于介入因素是否异常的判断,只能得出在追杀他人的过程中,逼迫他人逃入车辆疾驰的高速公路的情形,比逼迫他人逃入一般的交通道路的情形,使被害人被车撞死的概率更大,至于大多少,也无法得出精确的数据。并且,这些以概率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由,只能依据经验进行推断,无法用证据予以直接证明。具体到本案而言,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甲将丙砍成重伤,使丙生命垂危,是引起丙死亡结果的重大的危险行为,中间虽然介入了乙的一般医疗过失行为,但在对生命垂危的人进行治疗中出现一般医疗过失行为并不异常,并且其对死亡结果的贡献程度也较低,因此,甲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既遂。
在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中引入概率型的规范评价因素,有利于完成因果关系的结果归责。但在疫学因果关系中,引入概率型的规范评价因素,则可能造成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侵袭。疫学的因果关系(或称流行病学上的因果关系)是指,根据科学的观点,尽管不能完全弄清从某种条件直至结果发生的因果经过,但利用统计学方法在与对比群体的比较中,同样存在认定一定的事实现象与侵害结果之间高度联系的情况。〔28〕参见李冠煜:《日本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及其借鉴》,载《政治与法律》2014 年第2 期。换言之,就疫学因果关系而言,用因果关系公式检验,并不能确切的得出若P(行为)则发生Q(危害结果)的联系,充其量只能得出若P(行为)则Q(危害结果)发生的概率会升高的结论。〔29〕参见劳东燕:《事实因果与刑法中的结果归责》,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2 期。从该理论的基本内涵可以看出,其所直接解决的问题是,在不能完全确定行为与结果是否具有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只要确定了行为使危害结果的发生达到一定概率,即可从刑法上确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使其与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中的概率型的规范评价因素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第一,在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中,概率型的规范评价因素主要用于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异常,是否导致了因果流程发生了重大偏异;而疫学因果关系中的概率型规范评价因素则直接用于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二,在存在介入型的因果关系中,事实因果流程是清楚的,如在述“案例8 介入医疗过失行为案”中,甲致丙重伤,乙的一般过失医疗行为致乙死亡,其事实因果流程已得到证据的证实。但在疫学因果关系中,基本事实因果流程不清楚,即行为是否导致了结果的发生,只能得出一个概率性的结论,不能完全得到证实。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在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中,引入概率性型的规范评价因素的目的,是在事实因果关系清楚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原始行为人和介入行为人之间的刑事责任;而在疫学因果关系中,引入概率性型的规范评价因素的目的就是为了直接解决事实因果关系不清的问题,即行为是否能够引起结果的发生,只能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并且不能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得到确切证明,这时就以概率型的规范评价标准肯定行为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因此,在疫学因果关系,概率型的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侵袭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除了上述三种情况外,在假定的因果关系中也存在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侵袭现象。例如:在死刑执行时,甲以私人身份撞开了死刑执行官,自己充当死刑执行官并且在他的位置上开动电椅,将死刑犯乙杀死(案例9,私自执行死刑案)。〔30〕参见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载《法学研究》2006 年第2 期。对于本案,有观点提出,假如没有甲的行为,乙照样会因此执行死刑而死亡,因此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条件关系。〔31〕黎宏:《日本刑法精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 年版,第114 页。这种观点显然是将假设的未实际发生的情况(死刑的正常执行)作为了判断事实因果关系的依据,但假设的情况是一种规范的评价因素,其应该建立在已发生的事实因果关系基础之上进行价值评判,而不是以假设的规范评价直接改变已发生的事实因果关系。据此,本案已发生的基础事实是:甲私自执行死刑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乙提前死亡,预定的死刑执行行为并未实际发生;而不是假设的未发生的事实:即甲不私自执行死刑,乙依然会被执行死亡。因此,根据已发生事实进行判断,甲应当对乙的死亡结果负责。可见,在对假定的因果关系判中,同样体现了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的侵袭现象,但由于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多,笔者不再详细展开讨论。
三、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形成侵袭现象的理论依据及评论
实际上,无论是风险升高理论,还是在存疑的择一因果关系中和疫学因果关系中引入规范评价的因素,自其提出之日起就受到违反“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质疑。但尽管如此,这些理论不但没有因为质疑而停滞不前,反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和支持。究其原因就在于,学界存在着刻意用规范评价的方法解决事实判断问题的理论倾向。笔者认为,刻意模糊规范评价和事实判断的界限既可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也有损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应严格区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
(一)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领域形成侵袭现象的理论依据
实际上,合法则的条件说、相关因果关系说和危险现实化理论,基本都严格区分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因素与规范评价因素,在事实因果关系不清的情况下,遵循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对犯罪作出处理。但是,随着近年来客观归责理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支持这一理论,并倾向于用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判断问题。该理论认为:(1)因果关系归责的本质在于规范评价,结果归责应符合法秩序追求的目的。具体而言,归责的评价才是因果关系的本质,而且,规范评价不可能来源于实然的存在,只能从法秩序的目的中推导。因此,结果的归责应着眼于法秩序所追求的目的,并合乎此种目的。〔32〕Vgl.Schiinemann,Uber die Objektiver Zurechnungl,GA1999,S.215.(2)在风险社会中,严格遵守传统的归责模式,一概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不能有效预防和合理分配风险。具体而言,现今社会是一个科技发达的高风险的社会,因果关系日益复杂并且难以得到确定与证明,仍然完全遵守传统的归责模式,不能有效预防和合理分配风险。为了防止集体不负责的现象恣意蔓延,不能一概运用罪疑惟轻原则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33〕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5 页。(3)对于无法严格按照精确的因果法则进行归责的事实,可承认概然性的归责方式。即在因人类举止方面难以运用精确的因果法则进行归责时,就应当承认概然性的归责方式。我们不能够期望认识到,所有的过程都是通过精确的因果法则决定的,当一个因素影响了作为结果的概率值,且无该因素,概率值就会发生变化时,该因素就是概然性解释中的合法则的组成部分。〔34〕Vgl.Puppe,Die Beziehung zwischen Sorgfaltswidrigkeit und Erfolg bei den Fahrl ssigkeitsdelikten,ZStW99(1987),S.603.(4)以上述三点为基础,风险升高理论和疫学因果关系在按照传统的因果类型难以实现归责时,但在提高了结果发生概率时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从预防与合理分配风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归责模式较之于传统模式更为有效。〔35〕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载《中外法学》2014 年第 1 期。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该理论认为结果归责应着眼于法秩序的追求目的,而非实然的存在,在因果关系难以证明时,排斥“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一概适用,同时承认概然性的归责方式。这些基本观点都表明,该理论有意将某些事实不清的问题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以规避“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对犯罪认定的限制。
正是在上述基本理论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判断问题的具体观点,以此规避程序法“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第一,认为假定的因果关系属于价值判断领域,不适用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有学者提出,在遵守和履行一定的义务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结果避免可能性就是一个假定因果的关系,在不明时不应该依此对被告做有利的认定。〔36〕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版,第 163 页。即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不是事实证明,不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这种价值判断需要通过因果流程的假设来进行。基于事实的复杂性和变量的多样性,由此只能得出一个概然性结论。〔37〕参见陈璇:《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 4 期。按照这一观点,上述“案例2 违规超车案”和“案例3 赵达文案”中,由于“假如被告人实施合法行为,能否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属于假定的因果关系,就属于价值判断的问题,即使其基础事实并不清晰,也不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同时,两被告违法驾车的行为无疑升高了发生危险结果的概率,根据风险升高理论,两被告人的行为都应构成犯罪。第二,认为“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属于价值判断的领域,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德国有学者将因果关系中的不确定事由分为“原则上可查明的事由”和“原则上不可查明的事由”。认为对于原则上可查明的事由存疑时,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但对于原则上不可查明的事由存疑时,不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如以遵守或者履行一定的义务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结果避免可能性就是不可查明的情形。〔38〕Vgl.Stratenwerth,Bemerkungen zum Prinzip der R isikoerh hung,FS Wilhelm Gallas,1973,S.229.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在假设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因果流程将会如何发展,对此人们只能以概率的形式推测其基本趋势,而无法给出确定回答。因此,以概率的形式肯定结果归责就成为必然选择。〔39〕参见陈璇:《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 4 期。按照这一观点,上文中的“案例2 违规驾车案”、“案例3 赵达文案”以及存疑的择一因果关系和疫学的因果关系似乎都可归入“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都可纳入规范评价的领域解决,从而规避“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
(二)对以规范评价方式解决事实不清问题的观点的评论
综上可以看出,学界存在着将一些在事实因果关系领域难以查清的问题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进行解决的理论倾向,并构建了具体的理论以规避其与“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冲突。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存在如下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就其基础理论而言,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某些事实判断不清的问题,如果应用于立法层面是完全合理的,但应用于司法层面,则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因为,随着现代风险社会的来临,从预防和分配风险的角度来看,对那些日益复杂且难以查清的问题,可以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将其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如我国刑法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种事实不清的状态直接规定为犯罪,这就有效解决了在无法查清国家工作人员的不明巨额财产的来源渠道时,不能以犯罪处理的困境。再如,在日本和韩国,为了解决存疑的择一因果关系中难以定罪的问题,这两个国家都以立法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规定。日本刑法典第207 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暴行伤害他人的……在不能辨认何人造成了伤害时,即使不是共同实行的,也依共犯规定处断。〔40〕参见大谷实:《刑法各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 页。韩国刑法第263 条规定,因数个独立行为竞合发生伤害结果而无法判明孰为死伤原因的,以共同正犯处罚。〔41〕参见[韩]金日秀、徐辅鹤:《韩国刑法总论》,郑军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07 页。这就有效解决了在存疑的择一因果关系中难以归责的难题。但是,这样的归责方式必须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前提,在立法没有修改之前,就意图从司法判断层面将事实不清的问题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因为,将某些事实不清的问题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就等同于创造了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如在刑事立法没有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规定为犯罪之前,就对国家工作人员拥有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并且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情况以犯罪处理,显然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同样的情形类比在上述案例2 违规超车案中,在没有查明死亡结果究竟是违规驾车行为所致,还是被害人自身的醉酒行为所致的情况下,就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并以犯罪处理,等于是将违规驾车的风险升高行为作为了犯罪处理。这实质上是将结果犯罪的归责要求降格为了危险犯。〔42〕Vgl.Schlüchter(Fn.39),S.676;Duttge(Fn.39),§ 15 Rn.178.转引自陈璇:《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载《中外法学》2012 年第4 期。因此,它实际上已不再是司法判断上的一种因果关系归责理论,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在立法没有修改前就以犯罪处理,自然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第二,认为假定的因果关系属于价值判断领域,实际等同于用假设型的规范评价因素,来掩盖事实因果关系不清的问题,以此规避“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因为假设型的规范评价因素(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也必须以事实因果流程为基础,如上文“案例1 山羊毛胡案”由于基本事实清楚,所以对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能得出确切的结论,而“案例2 违规超车案”“案例3 赵达文案”由于基本事实不清楚,所以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因此,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能否得出确切结论完全取决于基础事实是否清楚,那么,以结果避免可能性判断是价值判断为由回避“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等同于是以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基础事实回避“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这无疑是欲盖弥彰,不具有合理性。而且,如果按照论者的逻辑进行推定还可能出现不可思议的现象,例如,现实发生的因果流程一般是“因为A(行为),所以B(危害结果)”,但条件说的判断公式是“没有A,就没有B”,显然,条件说也是“假定的因果关系”。那么,能否得出由于条件说的判断公式是假定的因果关系,是价值判断的领域,不能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的结论呢?这显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上述“假定因果关系”理论的实质仍然是欲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因果判断不清的问题,混淆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关系。
第三,认为“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属于价值判断领域”的观点,同样会造成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的不当侵袭。这是因为,一是该标准过于模糊,无法准确判定哪些属于“原则上可查明的事由”,哪些属于“原则上不可查明的事由”,这必然造成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侵袭的现象。例如,根据论者的观点,上文中的 “案例3 赵达文案”中的因果关系属于“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也可能将其归属于“原则上可查明的情形”。假如该案视频监控清晰,井盖散落位置和被害人所处位置明确,根据车辆型号和车速状况,通过侦查实验的方式模拟当时的情景进行检验,是能够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鉴定出事故发生的原因究竟是赵达文的超速驾车所致,还是散落于道路上的井盖所致的。但是,由于将其归于“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就可以规避“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司法人员可能更愿将其归于“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以更有效的方式实现结果归责。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存疑的择一因果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是否可查明或者不可查明,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二是因何具备了“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就不再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缺乏法理依据。例如,疫学的因果关系属于“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不能确切的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确定的因果关系,只能确定一定的概率值。但是,实体法为犯罪认定提供法律标准,程序法为犯罪认定提供事实标准。而在疫学因果关系难以得到证明时,就从规范评价的角度以概率值的方式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显然是以实体法标准代替了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
综上可以看出,在司法判断层面,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判断不清的问题,可能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并且,在这一基本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假定的因果关系属于价值判断”和“原则上不可查明的情形属于价值判断”的观点,都混淆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关系,将本应属于事实判断领域的问题,纳入到规范评价的领域解决。这必然会直接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破坏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为,根据犯罪认定的一般原理,刑法为犯罪认定提供法律标准,即确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刑事诉讼法为犯罪认定提供事实标准,即确定对事实的证明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43〕参见陈银珠:《论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顺序——以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功能区分为视角》,载《法律科学》2012 年第3 期。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司法者不能随意地在因果关系难以得到证明时,就以规范评价的方式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这实际上是以规范评价的标准规避了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违反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而程序公正对于保障司法正义至关重要。诚如有学者所言:“两个人分一个蛋糕,最公平也最能够为双方接受的办法是,由其中的一方将蛋糕切为两份,同时给另一方优先选择蛋糕的权利。事实上,不管我们怎么分割,切开的两份蛋糕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均等的分量。”〔44〕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4 页。因此,实体正义永远都会存在偏差,而程序正义则可以对这些偏差进行适当修正。在司法认定中,司法者应当承认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45〕参见蔡仙:《过失犯中风险升高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反思》,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4 期。既要承认冤假错案不可避免,也要接受因事实不清而放纵犯罪的可能,不能因为发现存在放纵犯罪的可能,就改变既有规则,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判断问题,因为,其蕴含着更大的危险,即破坏程序正义的后果是可能增加冤假错案的发生概率。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刑事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应予严格区分。
四、刑法因果关系中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区分标准
鉴于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着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判断问题的倾向,并且也出现了混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现象,因此,应建立明确的区分标准将两者区分开来,避免规范评价对事实判断侵袭现象的出现。由于事实判断主要用于明确事件发展的因果流程,即解决事实因果不清的问题;规范评价主要用于明确结果的归责判断,即解决法律责任不清的问题。以此为基础,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区分。
第一,如果该事由一般情况下主要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进行证明,并且一般能够得出确切结论,应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如果该事由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一般不能明确查明,只能根据人们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刑法规范确立的价值评判标准进行推导,并且一般无法得出精确结论,只能得出概率性结论,应属于规范评价问题。例如,甲与素不相识的乙发生争吵,甲在乙的胸部打了一拳,乙倒地死亡。后经查明,乙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甲对乙的打击行为引发了乙的心脏病导致其死亡。在本案中,甲打乙一拳的事实,乙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事实,打击行为诱使心脏病发的事实,甲并不知晓乙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事实等,都是能够依据证据法的证据规则予以查明的事实,因此应属于事实判断问题。而对于甲在乙胸部上打一拳的行为,在多大概率上会碰到正巧有心脏病的乙,并诱发心脏病致乙死亡的判断,或者说甲是否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的判断,则是规范评价问题。因为,这一事由只能根据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刑法规范确立的价值标准进行推导,无法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进行证明,只能得出概率性的结论,而且进行这一判断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行为人是否要承担责任,即解决刑事责任不清的问题。
第二,如果需要查明的情形只涉及事件的基本因果流程的判断,应当归入事实判断领域,而不管该事由是否可通过证明规则予以查明。如甲将乙杀死,甲的杀人行为与乙的死亡结果之间的关系就是涉及基本因果流程的判断,无论该因果流程一般情况下是否可通过证明规则予以查明,只要事实不清,在司法认定中就不能纳入规范评价领域以解决归责问题,只能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处理,否则可能直接造成冤假错案。如果需要查明的情形只涉及刑事责任的划分问题,不涉及事件的基本因果流程的判断,则可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归责问题。如在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中,尽管介入因素异常性的判断只能得出一个概然性的结论,但由于介入因素的判断不涉及事件基本因果流程的判断,只涉及刑事责任划分问题,因此可以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例如,甲追杀丙,丙在逃跑时被乙开车撞死。本案的基本因果流程是,甲追杀丙,丙被乙开车撞死,只要该事实清楚,就不存在冤枉甲或者乙的可能,因为甲和乙的行为都是导致丙死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接下来对介入因素异常与否的判断,就只涉及划分刑事责任的问题,即甲与乙谁对丙的死亡结果负责。既然是归责的问题,当然要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
第三,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即先进行事实判断,再进行规范评价,如果事实判断不能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得出确切的结论,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规范评价也就难以划分责任。因此,一般情况下事实判断不清时,不能再进行规范评价。当然,如果在特殊情况下,事实判断不清的状况并不影响规范评价的归责结果,则依然可以进行规范评价。
以上述三条标准为依据,笔者拟对刑法因果关系中存在争议的情形作出如下判定。
1.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
在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中,对于介入因素是否异常的判断,属于规范评价问题。因为,第一,介入因素是否异常的判断,一般情况下不能根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予以直接证明,只能根据人们的经验进行推导。如在上文“案例8 介入医疗过失行为案”中,介入医疗过失行为是否异常,只能根据人们的经验进行推断,并且只能以概率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第二,介入因素是否异常的判断并不涉及基本因果流程的判断,只涉及行为人之间的刑事责任划分问题。在“案例8 介入医疗过失行为案”中,甲致丙重伤,乙的医疗过失行为致丙死亡,这一基本因果流程是清楚的,之后对介入因素是否异常的判断,只是为了明确甲和乙对丙的死亡结果应负怎样的刑事责任。明确责任的问题,当然应该作为规范评价的问题予以解决。第三,由于判断介入因素异常与否的基础事实是清楚的,因此可以进行规范评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事实因果不清的状况并不影响规范评价的结果,仍然可以进行规范评价。
例如,被告人王某将骑着人力三轮车的被害人杜某撞倒,王某逃逸后,另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再次碾压躺在道路中间线上的杜某并逃逸,杜某当场死亡。法院认为,死者颅脑损伤、胸腹部损伤(内脏挫伤)是两次作用形成,两处损伤均可导致被害人死亡(案例10)。〔46〕参见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4 刑终174 号刑事裁定书。本案属于典型的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但唯一存疑的是,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究竟是第一次事故所致,还是其后介入的第二次事故所致?这也是本案产生争议的原因所在。但是,由于这一事实不清的问题并不影响规范评价结果,仍可进行规范评价以实现结果归责。这是因为,本案中存疑的事实因果可能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死亡结果由第一次事故造成;二是死亡结果由介入的第二次事故造成。在第一种情况下,从规范评价上判断,王某的第一次事故直接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应归责于王某;在第二种情况下,发生第一次事故后,被害人躺在公路中间具有极大危险性,从规范评价上判断介入的第二次事故并不异常,死亡结果仍应归责于王某。无论以哪种事实进行规范评价都不会冤枉王某,因此,王某应对交通事故的死亡结果负责。
2.合法替代行为的因果关系
在合法替代行为的因果关系中,对据以判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基础事实不清的问题,不能将其纳入规范评价领域予以解决。第一,该事实是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在一般情况下能够查明的事实,如上文“案例2 违规超车案”和“案例3 赵达文案”中,如果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其基本事实是能够查明的。而且,它也不属于依据人们的经验、价值观念和刑法规范确立的标准进行推导的事实。第二,该事件涉及案件的基本因果流程的判断。如上述“案件2 违规驾车案”涉及的基本事实是,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究竟是违规驾驶行为所致,还是被害人的醉酒行为所致,并不清晰;“案例3 赵达文案”涉及的基本事实是,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究竟是超速驾驶行为所致,还是散落于道路上的井盖所致,并不清晰,这都涉及事件的基本因果流程事实。第三,在基本因果流程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只能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进行处理,不能将其纳入规范评价的领域解决。
例如,甲于1995 年5 月1日驾驶客运大客车在滨海公路的某连续转弯路段超速行驶(该路段限速为50 公里/小时,甲的车速为66 公里/小时),在发现迎面行驶过来的乙车违章越过双黄线驶入自己车道时,甲因来不及采取刹车措施,导致两车相撞,导致乙脑挫伤、颅内出血送医后死亡的。(案例11)〔47〕参见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63-64 页。本案与赵达文案极为相似,台湾地区法院经过六年的审判换了40 多位法官进行审理,最终判定甲无罪。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的争议集中于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即假定被告遵守50 公里/小时的限速规定,是否能够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但是,如前所述,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应该建立在事实因果关系清楚的基础之上,在基本因果事实不清的基础上进行规范评价,必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换言之,根据案件的证据情况,本案并不能确定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究竟是甲的超速驾车行为所致,还是被害人的违章越线行为所致,在这一基本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是否具有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规范评价也必然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这也是几审法院40 多位法官经过反复审理仍然不能停止争讼的根本原因所在。笔者认为,本案问题的症结在于混淆了事实判断与规范评价的关系,本案的判断重点应在于基本事实问题,即被告人的超速驾驶行为是否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这一基本事实不明,在基本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只能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得出甲不构成犯罪的结论。而不是用“假设被告人合法驾驶,结果是否具有避免可能性”这一规范评价要素转移视线,掩盖事实不清的问题,规避“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争议。正如林钰雄教授所言,本案应该讨论的是:“当事实不明时,到底要如何裁判?”〔48〕林钰雄:《刑法与刑诉之交错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81 页。
3.择一的因果关系
在择一的因果关系中,在基本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规范评价。如“案例4 两枪共效致死案”,甲乙二人共同打中了丙的心脏,造成了丙的死亡,甲乙二人对丙的死亡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在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如何划分甲乙二人的责任当然只能依据人们确立的规范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但在存疑的择一因果关系中,基础事实不清的问题就不能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解决。这是因为,第一,这些不明事实一般情况下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能够查明,而且不属于只能根据人们的经验、价值观念和刑法规范确立的标准进行推导的事实。如在上述“案例5 两枪过失致人死亡案”中,如果有监控录像、目击证人的存在,就可以确切的证明案件事实的发生过程,确定究竟是谁的枪击行为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第二,存疑的事实涉及基本因果流程的判断,如在上述“案例5 两枪过失致人死亡案”中,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究竟是甲的枪击行为所致,还是乙的枪击行为所致并不清晰。第三,在基本因果事实流程不清楚的情况下,只能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进行处理,不能进行规范评价。
例如,被害人因为停车问题与小区保安高某发生冲突,高某持金属暖气阀门连续击打被害人头部4次,致被害人头破血流。后高某被警察带离了现场。被害人的儿子赶来后,误以为他的父亲是被赵某所伤,于是上前推搡赵某。赵某随即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围攻被害人的儿子,被害人为保护儿子被赵某纠集的人员用棒球棒击打头部1次。在整个殴斗过程中,被害人始终意识清醒,后自行驾车赴医院就医。后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因被钝器击打头部致颅脑损伤,已构成重伤,但无法确定究竟是被高某用金属阀门击打所致,还是被赵某纠集的人员用棒球棒击打所致,抑或是前后两次击打合并所致。由于前后两次伤害行为对最终结果的原因力大小(0-100%)难以量化评价,所以这三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案例12)。〔49〕参见高志:《论因果关系不明场合下同时犯的责任归属》,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 年第10 期。笔者认为,本案的基础事实并不明确,即被害人的重伤结果究竟是高某的打击行为所致,还是赵某所纠集人员的打击行为所致,没有查清。并且,这些事实属于涉及基本因果流程的事实,不能纳入规范评价领域进行解决,只能依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认定被害人的重伤结果不能归责于两行为人。
4.重叠的因果关系
重叠的因果关系是指,两个以上的单纯不能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偶然的重叠到了一起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的情形。例如,甲乙二人出于杀死丙的意图,在事先没有联络的情况下,分别让丙服用了不能达到致死量的一半的毒药,但双方的毒药合在一起达到了致死量,导致丙死亡(案例13)。本案的基础事实也是清楚的,即甲乙毒药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丙的死亡,而且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在基本事实因果关系清楚的情况下,剩下的就是确定责任的问题,这时就需要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进行价值判断。按照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观点,由于甲和乙的行为非常偶然地重叠到了一起导致了丙的死亡,不具有相当性,因此应否定相当因果关系,甲乙只能分别构成杀人罪的未遂。〔50〕参见[日]大谷实:《刑法总论》(第二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202 页。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提出两者是“共效的因果关系”,其作为相当因果关系补充应认定甲乙分别构成杀人罪的既遂。〔51〕参见张小虎:《论刑法替代因果关系的归责:理论基奠与事实根据》,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9 期。
例如,被告人张某在未取得医师资格以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办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活动。2012 年6 月4 日,被告人在对有心脏疾患的赵某进行诊断治疗中,采取了心脏按压、人工呼吸及注射过期的硝酸甘油注射液等措施。上述措施均无效,被害人赵某于当日死亡。经鉴定,被害人赵某符合因急性心肌梗死、轻度脂肪心、患冠心病等心脏疾患导致急性心功能衰竭死亡。鉴定意见载明:被害人生前患有心脏疾患是死亡发生的基础;张某非法行医,盲目治疗、施救与死因二者间虽无直接因果关系,但是张某的行为客观上一定程度延误了抢救时间,失去了抢救机会,在赵某的死亡过程中负有一定责任,建议参与度为50%。〔52〕参见梁云宝:《回归与突破:我国刑法因果关系在归属层面的厘清》,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在本案的判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的参与度为50%的判断,是表明张某对赵某死亡结果所起作用大小的判断,不是对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判断。因此,本案中行为与结果的基本事实因果关系是清楚的,不能以因果事实不清为由直接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对被告人做出罪处理,而是应当从规范评价上确定张某对死亡结果50%的参与度应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根据上述的不同规范标准,如果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张某不对赵某的死亡结果负责,如果采用“共效的因果关系说”,张某应对赵某的死亡结果负责。
5.假定的因果关系
在假定的因果关系判断中,要注意严格区分实际发生的因果事实与假设的规范评价要素,两者不能混淆。规范评价应当建立在实际发生的事实的基础上,而不能以假设的规范评价因素改变已发生的事实。如在上文中“案例9 私自执行死刑案”中,实际发生的事实是甲以私人身份撞开了执行死刑的执法官,开动了电椅的按钮,导致被害人死亡,执法官的执行死刑行为并未发挥任何作用。规范评价应当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判断,即甲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死亡结果应归责于甲。而不应该以“假如甲不开动电椅,被害人依然死亡”这一未发生的情况作为规范评价标准,否定已实际发生的事实,认为死亡结果不应归责于甲。
6.疫学的因果关系
对于疫学的因果关系而言,虽然疫学的因果关系也是一般情况下依据证据法的证明规则无法查明、并且只能以概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它是涉及基本因果流程的事实(违反上述第二条标准),即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这一基本事实不能查清,因而不能进行规范评价以实现结果归责,只能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法裁判原则进行处理。
五、结 语
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中,刑法用于明确刑罚的处罚范围,保证国家权力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运行,刑事诉讼法用于明确追诉犯罪的步骤和方法,保证国家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运行方式运行,两者有各自独立的价值和功能,忽略任何一方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具体到犯罪的认定,实体法保证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罪名和刑罚进行定罪量刑,防止肆意定罪的情况出现;程序法规则保证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认定犯罪事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外,规范评价不能干涉事实判断问题。但从上文的研究来看,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中,广泛存在着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判断问题的倾向,这实际上是不合理地规避了程序法“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对犯罪认定的限制,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诚如美国刑法学家乔伊·撒马哈所言:刑法犹如一个钟摆,摆的一端是公众对政府滥用权力的恐惧,从而要求限制国家权力;摆的另一端是公众对犯罪的恐惧,从而要求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去打击犯罪。〔53〕Joel Samaha,Criminal Justice,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1,p.10.以规范评价的方式解决事实不清的问题,无疑削弱了程序规则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实质地扩大了刑罚权的范围,将“钟摆”偏向了国家权力的一端,这必将不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因此,笔者主张,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判断中,事实判断问题与规范评价问题应予严格区分,使其按照各自的规范标准(程序法标准和实体法标准)进行判断,唯有如此,才能使犯罪追诉活动在实现打击、预防犯罪功能的同时,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