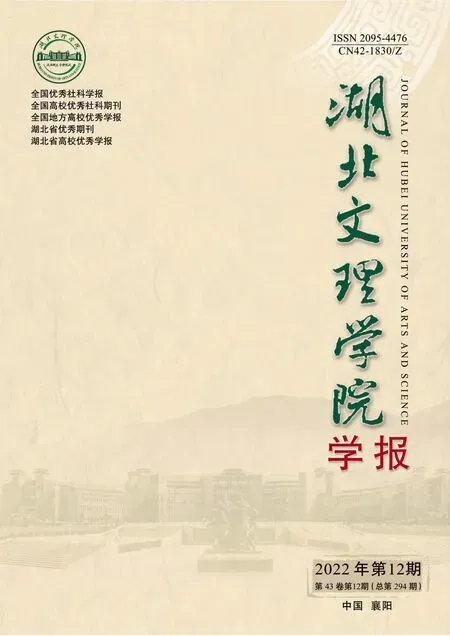《三国演义》的性别空间叙事
游翠萍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710072)
《三国演义》是一部极具空间感的历史小说,它描写了从汉末的群雄争霸,到魏、蜀、吴三国鼎立,再到晋统一中国大半个世纪间,不同军事集团之间大大小小的地理空间争夺战。空间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社会关系和地位的变化,甚至是权力结构的变化。《三国演义》呈现的既是具体的地理空间,也是政治、权力角逐和更迭的空间,也是各种社会关系生产和重构的空间。从女性主义地理学批评来看,空间不是中性或客观的存在,而是性别化的,“空间和地方不仅本身被赋予了性别……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它们都反映和影响了性别被建构和理解的方式。”[1]231-232本文研究《三国演义》对于空间的性别建构和权力关系,并探讨小说文本如何呈现女性的空间移动以及性别空间中的权力反转。
一、“性别隔离”下的空间特征
《三国演义》是一部男性的史诗,相比上千个男性人物,女性人物不过寥寥八十余人。以阶层分,有上、中、下层的女性,以中、上层女性为主;以外貌性情分,有美女、才女、烈妇、良母、贤妻、妒妇等。在小说中可以看到,男性可以在自然、城市、战场、官府、衙门、寺庙等各种空间中自由行动,而女性活动的主要空间是相对封闭的家宅空间的后面,如后宫、后堂、后院、后园等:
当日帝在后宫,正与伏皇后私论董承之事至今尚无音耗。[2]214
少顷,孙权入后堂见母亲,国太捶胸大哭。[2]462
(董)承心中暗喜,步入后堂,忽见家奴秦庆童同侍妾云英在暗处私语。[2]210
(郭常)遂宰羊置酒相待,请二夫人于后堂暂歇。[2]243
(辛)敞急入后堂。其姊辛宪英见之,问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2]925
歌伎貂蝉的活动也集中在后园、后堂空间:
至夜深月明,(王允)策杖步入后园,立于荼蘼架侧,仰天垂泪。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允潜步窥之,乃府中歌伎貂蝉也。[2]65
允预备佳肴美馔,候吕布至……接入后堂……二青衣引貂蝉艳妆而出。[2]66
天晚酒酣,允请卓入后堂……允教放下帘栊,笙簧缭绕,簇捧貂蝉舞于帘外。[2]67
(吕布)系马府前,提戟入后堂,寻见貂蝉。[2]70
作为战利品被曹丕纳为妻的绝色美女甄氏,在史书中记载其出现地点为“室堂”,曹丕“入绍舍”[3]54,但小说明确标记为“后堂”:“(曹丕)提剑入后堂。见两个妇人相抱而哭。”[2]288
《三国演义》性别空间的建构表现了作者性别观的空间维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女有别”的性别回避礼仪制度,在空间上主要以“男外女内”的空间区隔为基础。《礼记·内则》为“男女有别”确立了明确的标准:“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4]1468,“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4]1462中国古代的性别回避制度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隋唐以前是推行时期,相对宽松,隋唐以后是确立时期,渐趋严格[5]。“男女有别”既是礼仪,同时也表现了“男尊女卑”的权力关系,因为“所有的范围界定、建立边界……目的都是对某个时空的意义进行固化”,“这些想要固化意义的做法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权力斗争的原因”[1]9。
在小说中,作者并不特别细致地描写和区别人物在家宅空间的行动细节,往往以“后堂”统一指称。但是,在某些章节中,作者对人物的空间行动却有非常详细的描写,借助这些空间移动细节,我们可以观察到作者性别空间建构的逻辑和性别空间中的权力关系。
从小说来看,作者对于“男女有别”的空间礼仪制度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男性主人掌握着家宅空间的权力,空间限制并不施于他,但其他男性则不能随意逾越。如王允离间董卓与吕布,就以男主人的身份在前厅、后堂自由地摆设筵席;而刘备三次到诸葛亮草庐拜访,除了其弟和服侍的童子,并未见到其他女眷。如果男性主人无法掌控空间权力,导致权力被女性掌控,或被外人掌控,或空间性别隔离失效,从而导致出现空间越权、越界行为,就会带出极大的麻烦和问题,如刘表妻蔡夫人。蔡夫人是一个强势界入丈夫事务的女性,很想立自己的儿子为长,因此“凡遇玄德与表叙论,必来窃听”,当听到刘备劝刘表说“自古废长立幼,取乱之道”时,又知道刘备非久居人下,劝刘表早点除去刘备,刘表不肯,她就召集手下去杀刘备。小说中多次描写刘表邀刘备入后堂饮酒,而蔡夫人总是躲在屏风后偷听,偷听之后再向丈夫进言,丈夫若不许则自主行动。在这里,蔡夫人的“屏风偷听”既是试图突破空间界限,也是越权,在行动上已经逾越了“男外女内”“女不言外”的事务之界。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所以作者对于空间的安排和想像都带上作者所处时代的烙印,而与汉代实际空间状况有差别。蔡夫人能够躲在屏风后偷听,明显看出此处的“屏风”是比较高的,起隔离内外的作用。但实情是,“从战国到三国,由于席地而坐,几、案、衣架和睡眠的床都很矮……床的用途扩大到日常起居与接见宾客。不过这种床较小,又称榻,通常只坐一人,但也有布满室内的大床,庆上置几。床的后面和侧面立有屏风。”[6]52如图1这样低矮的屏风,其实是不太容易作偷听之用的。

图1 汉代带屏风的榻和案[6]52
空间越界情况出现在皇室,后果就更加严重。如汉灵帝驾崩后,董太后和何太后争权,董太后被何太后之兄何进鸩杀,而后来何太后及少帝也被董卓杀害。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在董卓废少帝、立献帝及弑君的过程中,皇宫内部的性别空间区隔完全被破坏,少帝及太后根本无法掌控皇宫的空间权力:
卓命扶何太后并弘农王及帝妃唐氏于永安宫闲住,封锁宫门,禁群臣无得擅入……遂命李儒带武士十人,入宫弑帝。帝与后、妃正在楼上……儒大怒,双手扯住太后,直撺下楼,叱武士绞死唐妃,以鸩酒灌杀少帝,还报董卓。卓命葬于城外。自此每夜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2]32-34
东汉皇宫为洛阳南北宫,北宫中有永乐宫和水安宫作为皇后妃嫔住处,但是北宫和南宫都用作朝廷,元旦的大朝会规定在北宫的德阳殿举行[7]135。汉少帝及太后、唐妃被幽禁在永安宫,而董卓及其武士可以任意出入皇宫,这一空间越界显示了皇室权力旁落的情形。
此外,作者对男性的褒贬态度也具体表现在是否有空间越权、越界行为上。试比较一下吕布和关羽这两个豪杰面对空间性别隔离的态度。吕布在董府自由出入,无所顾忌:
作者以“径入”“潜入”“窥探”“偷目窃望”等来描述吕布不守空间规范的行动。吕布逾越性别空间界限在《三国志·吕布传》中也有记载:“卓常使布守中閤,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3]74与此相反,关羽在与刘备失联,暂降曹操,独自保护两位嫂夫人的情况下,从不逾越性别空间界限:
关公收拾车仗,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于路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见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许昌,操拨一府与关公居住。关公分一宅为两院,内门拨老军十人把守,关公自居外宅……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曰“叔叔自便”,关公方敢退回。[2]222
即使发生紧急意外情况,关羽也严守男女有别、尊卑有序的行为规范,不入内院,“整衣跪于内门外”问询和安慰,不失礼仪和性别空间界限:
一日,关公在府,忽报:“内院二夫人哭倒于地,不知为何,请将军速入。”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问二嫂为何悲泣……关公曰:“梦寐之事,不可凭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请勿忧愁。”[2]223
《三国演义》主要呈现中上层女性的空间状态,而汉代中下层女性不仅从事纺织刺绣之类的室内活动,也参与农业劳动、家庭饲养、酿酒、手工制造以及卖酒、小商小贩等经济活动,比较上层女性,下层女性活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8]。即便是皇宫的妃妾宫女,其出路也不是终身幽闭后宫,而是有出宫女、赐宫女婚配、随王就国、置园陵中等多种出路,女性生活的空间和环境相对还比较宽松[9]。但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元末明初,儒家礼教思想已经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其写作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二、女性空间移动的四种模式
虽然按儒家“男女有别”的理想来看,女性尽可能被静止地安置于家宅的后院,负责纺织、刺绣、家务、生养等内部事情,但女性的空间移动和越界还是不可能完全避免,不仅家宅内部的移动和越界很难避免,战争、婚嫁还可能带来更大的空间移动行为。总体来看,《三国演义》中女性的外部空间活动较少,女性的空间移动主要与政治变迁、权谋、战乱、出嫁、归宁有关。如甘、糜二夫人随刘备的胜败而迁移,孙夫人在荆州和东吴之间的来去,吕布女儿作为政治联姻工具被父亲送来送去等。《三国演义》在处理女性空间越界行动时有其清晰的立场,作者的褒贬也暗含其中。
例(40)是“A到VP”格式作宾语的类型,“自己笨到没朋友了”作“感觉”的宾语。例(41)是“A到VP”格式作补语的类型,“离谱到想抽自己”作“错”的补语。例(42)是“A到VP”格式作定语的类型,“实力低到爆”作“角色”的定语。例(43)是“A到VP”格式作谓语的类型,“方便到你都不相信这在祖国”作句子谓语。
一种是因战乱迁徙而发生的空间移动,往往与苦难相联,如跟随刘备在战乱中流离的甘、糜二夫人。在战乱中,刘备多次弃妻(子)而走,两位夫人或被俘虏,或被追兵追杀,其空间移动充满苦难和不幸。以甘、糜二夫人长坂坡经历为例:
(赵云)拍马望长坂坡而去……军士曰:“恰才见甘夫人披头跣足,相随一伙百姓妇女,投南而走。”……夫人在后面望见赵云,放声大哭……甘夫人曰:“我与糜夫人被逐,弃了车仗,杂于百姓内步行。又撞见一枝军马冲散,糜夫人与阿斗不知何往。我独自逃生至此。”……只见一个人家,被火烧坏土墙,糜夫人抱着阿斗,坐于墙下枯井之傍啼哭。云急下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见将军,阿斗有命矣。望将军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将军可护持此子,教他得见父面,妾死无恨!”……糜夫人乃弃阿斗于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2]360-362
刘备带领樊城百姓进行战事转移时,甘、糜二夫人是乘坐车舆和兵仗保护的,但战败之际,只能丢下这些,甘夫人“披头跣足,相随一伙百姓妇女”逃命,糜夫人带着阿斗,又受了伤,不能逃了,抱着孩子坐在一家烧坏了的土墙下的枯井边啼哭,其情形十分凄惨。赵云提议糜夫人上马,他步行死战保护糜夫人和阿斗,糜夫人唯恐自己成为拖累,跳井而死。
还有一种是与婚嫁、归宁有关的空间移动,如孙夫人。“不爱红妆爱武妆”的孙夫人,执着、专一、刚烈,其外部空间移动虽然不是充满苦难却充满惊险。从东吴到荆州,从荆州返东吴,孙夫人的空间移动是在男性引导下发生的。去荆州,是刘备方欺骗她荆州有失,靠她保驾护航得以从东吴脱身;回东吴,是孙权方骗她母亲病危。而且,往返两次都有追兵。陪刘备去荆州,是与孙权追兵相对抗;返东吴,是与蜀汉方赵云、张飞相对峙。
还有参与战事的女性空间移动,如祝融夫人、赵昂妻王氏等。祝融夫人是小说中唯一上了战场的女性。祝融夫人骑马上战场打仗,与男性一起饮酒,其行动显得自由而豪放。
忽然屏风后一人大笑而出曰:“既为男子,何无智也?我虽是一妇人,愿与你出战。”获视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蛮,乃祝融氏之后,善使飞刀,百发百中……夫人忻然上马,引宗党猛将数百员、生力洞兵五万,出银坑宫阙,来与蜀兵对敌。[2]768
孟获与祝融夫人并孟优、带来洞主、一切宗党在别帐饮酒。[2]775
祝融夫人和孙夫人一样,都是喜欢舞刀弄枪的女性,性情都很刚烈,但孙夫人作为东吴郡主、大家闺秀,出门依然是坐车而非骑马。至于祝融夫人虽然行动自由,但明显作者看她是尚未受教化的蛮族人。再如赵昂妻王氏,其子赵月随马超为裨将,赵昂担心儿子有失,但王氏宁舍儿子也鼓励丈夫争战,“雪君父之大耻,虽丧身亦不惜,何况一子乎!君若顾子而不行,吾当先死矣!”不仅如此,王氏还把自己的首饰资帛拿出来,“亲自往祁山军中,赏劳军士”,激励众人奋勇争战[2]553。可以看到,这类空间移动其原动力来自于男性主导或对忠义、忠贞的道德回应,其空间移动也往往只是一个短暂的越界过程。
还有一种女性的空间移动,作者的态度则是比较保留或隐晦的,需要细细体察才能明白,如张济妻邹氏的空间移动,曹操因贪恋邹氏的美貌而折将丧子:
一日操醉,退入寝所,私问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操之兄子曹安民,阿操意,乃密对曰:“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文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操闻言,便令安民领五十甲兵往取之。须臾取到军中,操见之,果然美丽……是夜,共宿于帐中。邹氏曰:“久住城中,绣必生疑,亦恐外人议论。”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次日,移于城外安歇,唤典韦就中军帐房外宿卫。他人非奉呼唤,不许辄入。因此,内外不通。操每日与邹氏取乐,不想归期。[2]148
汉代对于寡妇再嫁的态度是开放的,《三国演义》中此类例子很多,如刘备娶吴夫人,赵范欲以寡嫂许嫁赵云等。邹氏丈夫张济已死,其侄张绣降曹操,面对曹操及其兵丁的强权,邹氏实在不容易有选择的机会。但在作者笔下,邹氏似乎并非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这在作者的空间叙事中可以看到。首先,邹氏被看见的空间颇显暧昧,是在“馆舍之侧”,并非女性正常的“后堂”空间,且在晚上,被曹操之兄的儿子曹安民看见,告诉曹操,这让本来只打算找妓女的曹操改变了主意。相较而言,另一位同样被强占的女性甄氏被曹丕看见,是因曹丕不顾禁令,直接闯入袁绍家后堂发生的;其次,邹氏主动提出不要久居城中,免得引起怀疑和议论,曹操于是带她住到城外去,“每日与邹氏取乐,不想归期”。如果单从结果来看,邹氏无意中也算完成了一个“美人计”,导致曹操损失爱将爱子。但很显然,作者并没有将其与貂蝉并列,小说对邹氏下落也无交待。那么,使邹氏与貂蝉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很明显的区别在于:邹氏的空间行为并非男性主导,不过是女性自我筹划,而貂蝉的空间行为是男性主导的,出于铲恶除奸、匡扶汉室的正义目的。由男性主导、出于正义目的就是“美人计”,没有男性主导而只是自我筹划,大概就只能算是“祸水”了。“美人计”与“祸水”,其实是一体两面。
总体而言,女性外部空间移动不多,以战乱、迁徙、婚嫁、归宁等为主要原因。被动迁徙的女性,往往以牺牲者形象出现。主动参与空间移动的女性,或为男性权威者所托,或为忠义、忠贞的缘故。不过,这种空间移动只是短暂的、特殊的,并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行为,归回女性空间才是正常的。如果女性的空间移动既不是出于被动,又不是男性所谋,也不是为忠义、忠贞,其空间移动则会被打上暧昧可疑的印迹。
三、性别空间中的权力反转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男女之间地位的差异因为空间的安排而被日益强化,性别化的空间为女性获取知识制造了障碍,这一障碍进一步被男人利用为其再生产服务,性别化的空间被男性所操控,也成为权力的空间[10]。虽然空间权力由男性掌控,但这并不排斥在局部空间领域里,女性实现一种权力反转。如果女性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获取了性别空间隔离之下所不能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就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或暂时掌控空间权力。
首先看美人计中的貂蝉。整个美人计是在王允主导下实施的,但是,在关于貂蝉的叙事中,可以看到貂蝉是一个主动的空间越界者和空间掌控者。她深夜在花园叹息,故意地使王允听到,从而设下美人计,将她从王府送到董府,她又在董府随机应变地离间董卓与吕布,与吕布在后花园相会,故意使董卓看见,两人生嫌隙,最后导致吕布下决心杀董。从王府到董府,貂蝉很明显地控制着空间主导权。此前包括曹操在内的几位英雄在刺杀董卓中都功败垂成,而貂蝉表现出如此随机应变的智慧和能力,远超男性之上。
貂蝉能够如此,与她的身份和经历分不开。貂蝉是王允府上的歌伎,应是家妓。家妓是在古代王侯或官僚家庭里执事的女乐,“家妓”是从“宫妓”(宫廷女乐)发展而来的。“从夏桀女乐开始,这一群体的地位就非常低下,西周以来直到清末,一直是贱民阶层。而封建等级制度的核心是区分‘尊卑贵贱’,严禁良贱通婚是周秦以来历代在婚姻条件上奉行的一条准则,汉唐期间则尤为统治阶级所注重,每每被列入法律条文里。”[11]历代贵族官僚蓄养的女乐与妻妾不同,主要为满足其声色之欲与礼俗仪节的需要,多与歌舞戏乐有关。因此从阶层上看,貂蝉属于“贱民”阶层,以声色娱人,也承担贵族官僚家庭中礼俗仪节的需要。恰恰是貂蝉作为以声色娱人的“歌伎”贱民身份,使得她逾越了加之于贵族女性和有身份地位女性的“男女有别”的空间隔离,可以为各色人等表演歌舞,“貂蝉在王允府中可谓阅尽了天下人。这就使她对各种官僚的心理、之间的关系和利害冲突都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正是这种生活经历使得貂蝉善于把握董卓和吕布二人心理,在他们面前显得游刃有余、应付自如,不留破绽。”[12]这从王允提出实施美人计又担心泄漏招致满门抄斩,而貂蝉的回答是“妾自有道理”“大人勿忧”[2]66,可见其沉着、笃定非同一般。
关于孙夫人的空间叙事也相当有意思。最初她似乎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美人计工具,不管是孙、刘两边,还是吴太夫人那边,她都是一个不在场者。直到孙夫人出现在“洞房”这一空间,突然来了一个空间权力的大反转:
数日之内,大排筵会,孙夫人与玄德结亲。至晚客散,两行红烛,接引玄德入房。灯光之下,但见枪刀簇满,侍婢皆佩剑悬刀,立于两傍,唬得玄德魂不附体……管家婆进曰:“贵人休得惊惧。夫人自幼好观武事,居常令侍婢击剑为乐,故尔如此。”玄德曰:“非夫人所观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暂去。”管家婆禀覆孙夫人曰:“房中摆列兵器,娇客不安,今且去之。”孙夫人笑曰:“厮杀半生,尚惧兵器乎!”命尽撤去,令侍婢解剑伏侍。[2]466-467
孙夫人本是孙刘政治联姻的工具和牺牲品,但孙夫人却成功地反转这一空间认知。从洞房的兵器陈列,到孙夫人笑刘备“厮杀半生,尚惧兵器乎”的言语中,可以看到孙夫人从空间到精神气质上,都占据了上风,完全出乎人们对于一个洞房内新娘的想像,也使得之前的关于孙夫人的美人计空间想像被反转过来。既不是貂蝉式的女色空间,也不是吕布女儿式的祭牲空间。在貂蝉美人计实施过程中,貂蝉出现于卧房、窗前、妆台、绣帘、花园等空间中,建构出一种具有旖旎、私密和情色意味的女性空间。而吕布女儿作为父亲政治交易的棋子,一会儿“宝马香车”送出去,一会儿又被抢回来,一会儿又被吕布“以绵缠身,用甲包裹,负于背上”准备突围送出去[2]172。从头至尾,她更像一个祭品,没有发出一句声音。孙夫人由于特殊的条件,“自幼好观武事,居常令侍婢击剑为乐”,好观刘备所云“非夫人所观之事”,获取了女性空间中没有的知识和能力,从而获取了空间的权力。洞房花烛夜,女性往往以其柔弱娇媚成为男性观看的对象,而在这个“枪刀簇满,侍婢皆佩剑悬刀”洞房空间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被吓得“魂不附体”“大惊失色”的男性“娇客”,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也被打破了。
同样,吴中女丈夫孙翊妻徐氏,突破空间界限,为夫报仇。徐氏是一个“美而慧,极善卜《易》”的女性[2]334,在丈夫孙翊被害那日卜一卦,大凶,曾力劝孙翊不要出去会客,孙翊不听,结果出事了。在孙翊被害、自己被仇人逼嫁的危急情况下,徐氏没有被吓住,先假意答应仇人的要求,然后密召孙翊心腹旧将二人入府,设下计谋,又召二人提前埋伏在暗室中,再邀请仇人入府在堂中饮酒,待其既醉,再邀请其入密室,让提前埋伏的旧将将仇人杀了。邀请男性入府秘密商议,与男性在堂中饮酒,邀请男性进入密室,都是逾越两性空间界限的事。但徐氏如此行事,是为夫报仇,是值得称许的。在徐氏复仇的过程中,其空间移动虽然只在府内前堂、后堂、密室中转换,但她完全掌控了家宅空间权力。
当然,无论是貂蝉、孙夫人、徐氏还是其他获得空间权力的女性,其获得的空间权力都是暂时的。作为一个虚构人物,貂蝉在完成美人计之后就失去了空间权,被吕布取去。后来,当吕布面临危机举棋不定时,作为吕布之妾的貂蝉表现得非常软弱无智,劝吕布“将军与妾作主,勿轻骑自出”[2]170,完全不像其当初在王允面前“妾自有道理”“大人勿忧”的冷静笃定,这是作者无法自圆其说的叙事裂隙。作者也改写了孙夫人与刘备并不和睦的婚姻(1)据《三国志》记载,孙夫人与刘备的婚姻似并不和谐。《法正传》:“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赵云传》:“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让刚烈的孙夫人在空间行动中自始至终都忠于刘备,甚至最后当她听到误传刘备已死的消息时,选择了投江自尽。至于徐氏,完成复仇任务之后,空间权力就转移了,“不一日,孙权自领军马至丹阳……取徐氏归家养老。”[2]335
总之,空间并非中性、客观的存在,而是有性别的,包含着权力关系。通过对《三国演义》空间与性别关系的考察,可以看到传统的“性别隔离”制度如何影响了小说关于性别的空间叙事。在“性别隔离”制度下,男性掌握着广大的空间权,而女性主要居于家宅的“后面”,外部空间活动非常少,多是在男性主导、保护之下进行。被肯定的人物,无论男女,都有合乎这一规范的空间占位或空间移动;反之,逾越了空间性别界限的人物,其品格往往被置于可疑的地位。当女性因为特别的机遇、地位、阶层而获得一些非女性空间可以获取的知识和能力时,也可能实现空间权力的反转,暂时掌控空间权力甚至逾越空间界限。在《三国演义》性别空间叙事中,由于不同的空间叙事意图之间会发生冲突甚至悖论,从而形成文本叙事的裂隙,呈现了“空间隔离”制度下性别空间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