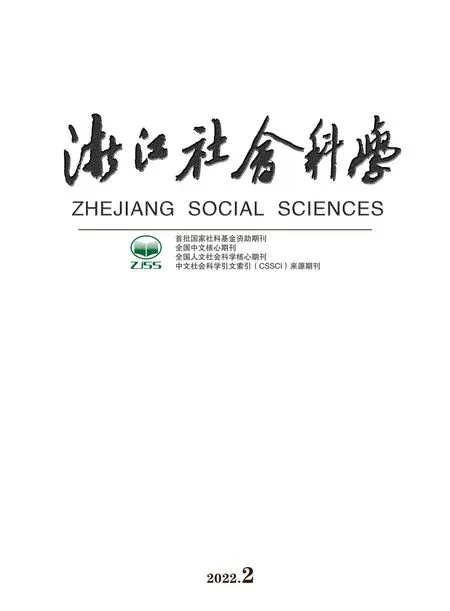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前提批判*
□ 杨韵韵 刘同舫
内容提要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小资产者”立场和“先验的上帝”假设进行了批判,从而揭示出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前提性局限。蒲鲁东在对所有权合法性的质疑和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建”中完成了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并由此形成了一定的历史意识。但他将历史规律归结于某种观念的逻辑演绎,因而无法提出变革所有权和建构未来社会形态的可行性方案。马克思指认出蒲鲁东的历史意识是植根于“小资产者”的狭隘、精致的利己主义,其根本目的在于捍卫“小资产者”的个人财产与私人利益,所以蒲鲁东的理论非但无法将人类社会引向未来的光明前景,甚至可能会诱使人们倒退回中世纪。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无法理解与把握“现实的人”在物质生产实践过程中创造了人类历史这一客观事实,只能将历史规律诉诸“先验的上帝”这种“冒牌的黑格尔词句”,陷入了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泥淖。
历史意识是承认与尊重历史规律并依据历史规律考察研究对象的历史起源、发展历程以及未来趋势的一种思维自觉和理论素养。①蒲鲁东在考察所有权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思维,但是他无法基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揭示出客观的历史规律,其历史意识存在着明显的理论限度。马克思整体性地考量与辩证性地批判了蒲鲁东的历史意识,既肯定蒲鲁东历史意识的理论意义,又揭示出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前提性局限。学界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意识批判的研究,主要围绕马克思与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结论的差异问题,②相对忽视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意识局限性的发生条件的剖析和批判。考察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探讨马克思对蒲鲁东形成历史意识的两大前提——“小资产者”立场和“先验的上帝”假设的批判,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意识的评价尺度,进而深刻理解马克思与蒲鲁东在历史意识前提性问题上的本质差异。
一、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形成及其限度
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形成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中认为,只有以历史的眼光厘清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的起源及其发展历程,才能判断所有权究竟是否具有合理性。蒲鲁东这种追问所有权发生学的研究旨趣体现了其历史意识的萌芽。在《贫困的哲学》中,他进一步将考察所有权与探究人类历史紧密联系起来,涉足政治经济学领域以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寻找规避所有权弊端进而建构未来社会形式的方法。蒲鲁东声称依据历史规律审察所有权制度与构想理想社会图景的观念体现了其历史意识的确立与形成。但蒲鲁东的历史意识奠基于“小资产者”的诉求和唯心主义观念之上,没有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难以发掘所有权的产生原因及其超越方式。
蒲鲁东对小生产者窘迫生存境遇的切身体悟,为其萌生出以往经济学家普遍缺乏的历史意识奠定了现实基础。蒲鲁东生于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早年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后成为箍酒桶的工匠师傅,随后又尝试经营酒馆生意,最后以惨淡局面而告终。蒲鲁东迫于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很早便辍学谋生,最初在印刷厂做工,之后与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小型印刷厂。蒲鲁东历经生活的磨难,曾亲眼目睹小生产者在大资本家的挤压下失去生产资料或个人财产而沦为社会底层贫困群体的真实场景。蒲鲁东总是以“时代的苦难的见证人”的身份自居③,他曾扪心自问:“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的痛苦和苦难呢? 难道人类应该永远是不幸的吗?”④蒲鲁东对这些问题的思索,蕴含了对人类社会不平等根源的现实追问以及未来应当向何处去的理论反思。蒲鲁东怀着对解决诸多历史问题的执念和消除社会贫困的希冀,广泛涉猎神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语言学等相关领域的书籍。他在考察所有权问题时,发现鲜有政治经济学家从历史发生学视角探究所有权的起源与形成等前提性问题,并由此展开了对所有权演进历程的探索。
在《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一书中,蒲鲁东强调探究所有权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对于正确理解所有权具有重要意义,这体现出其历史意识的萌芽。首先,蒲鲁东批判性地指出,既往的政治经济学家正是由于缺乏对所有权产生原因的研究,才会理所应当地认为所有权是一切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他们基于所有权制度讨论社会财富如何增殖的致思取向完全忽视了“所有权本身是否合理”这一前提性问题。蒲鲁东认为,“普遍承认所有权的事实并不能使所有权合法化”。⑤在其他经济学家止步的地方,蒲鲁东继续前进,指出“所有权是否合法”这一问题应当回到其发展历程之中加以历史性的审视,即通过考察“所有权的根源、它产生的原因以及它长久存在和行将消灭的原因”,⑥从而在历史维度上判断所有权是社会经济的“自然条件”还是某一阶段的特殊产物。其次,蒲鲁东阐述了所有权的发生过程,认为所有权产生于人们尚未充分认识正义观念的阶段,伴随人们对正义观念的深入理解,所有权制度将被“占有制”取而代之,此时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占有一定的财产。在蒲鲁东看来,正义是人类区别于禽兽的社会本能,在正义本能的驱使下,人类社会最初表现为“共产制”的社会形式。随着人的自主意志和推理能力的发展,人们出现了“占为己有”的私欲,加之人们由于思考力的限度往往曲解正义观念,这导致了正义逐渐被遮蔽,人类社会也开始进入“私有制”的重要时期。“私有制”时期是暂时的,“恶或错误及其后果,是两种对立的能力——本能和思考——相结合后的第一个产物;善或真理则必然是第二个产物”。⑦蒲鲁东认为,当人的思考能力和社会本能逐渐趋向同一,人们达到完全理解正义的内涵和原理时,人类社会就会进入“个人平等占有财产”的历史阶段。
直至撰写《贫困的哲学》时,蒲鲁东才清晰地认识到,探究所有权的产生根源、寻找克服所有权本身缺陷的方式必须要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如何探索历史规律呢?蒲鲁东认为人类历史的奥秘蕴藏在经济领域之中,应当通过重建政治经济学来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从而确证所有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位与演变趋势。
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改造,其历史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不断深化。在研究对象上,蒲鲁东认为诸多政治经济学家通常以零散的经济现象为考察对象,忽略了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全貌的考察,以至于他们把眼前的经济现象理解为某种永恒不变的事实。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应当以人类社会的总体状况为对象,探究人类社会不断变迁的历程和规律。“这门科学的对象包括的不仅是某一个时期的人类秩序”,“而是社会存在的一切原则和全部希望,就好像一切时期和一切地点的社会进化一下子都集中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上,从而使各个时代的联系和各种现象的次序一目了然”。⑧在研究方法上,蒲鲁东认为,政治经济学需要结合哲学的方法,以此来发掘人类社会的秩序。以往的经济学家只对经济事实进行实证考察,“他们眼前确实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许多可供建造宏伟大厦的材料”,⑨却找不到“建筑师”和“总图样”。在蒲鲁东看来,哲学的思辨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亟需的“建筑师”。政治经济学已经提供了“有关人类在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的最明显和最普遍的习惯、传统、成规与实例的最原原本本的历史”。⑩现在的任务在于诉诸哲学方法重新研究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从而探寻出经济发展的精神与哲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的秩序与规律。正如有学者指出,蒲鲁东“想做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黑格尔,企图对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作出‘规律性’的阐释”。⑪蒲鲁东声称《贫困的哲学》不仅是涉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作,而且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历史论著。
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相比,蒲鲁东具备较为自觉的历史意识。遗憾的是,蒲鲁东并没有触及到真实的人类历史及其规律,而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曲解为经济观念的逻辑演绎,将历史规律归结于上帝对人类社会的支配与指引,因而他的历史意识存在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其政治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真实的人类历史进程,进而难以提出变革所有权制度和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可行性方案。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开篇就奠定了唯心主义的基调。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受着某种最高意志的支配,这个意志存在于社会之外,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社会朝着一个不可知的目标前进”,⑫这一最高意志就是上帝或某种普遍理性。蒲鲁东声称自己所研究的是“符合观念顺序的历史”,他认为事实只是观念的有形表现,“社会所经历的过程恰恰和理性创造概念的过程完全一样”,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⑬
在蒲鲁东那里,社会历史的更迭变成了经济范畴“正—反—合”的逻辑运动。基于人类社会历史是经济观念演绎史这一判断,蒲鲁东强烈反对采取革命手段来推翻现存社会制度,认为应当以“文火”烧毁所有权的弊端,即寻找一种能够调和一切现存矛盾的经济观念。由于没有揭示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历程和真正规律,蒲鲁东的历史意识在探寻变革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社会方式的过程中难以彻底地发挥作用,他自以为建基在客观规律之上的“救世良方”事实上沦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马克思对蒲鲁东“小资产者”立场的批判
马克思在充分阅读蒲鲁东的著作和了解其历史意识的整体面貌基础上,揭示了蒲鲁东是立足于“小资产者”的立场,⑭坚决主张要根据历史规律探索克服所有权弊端的理想社会形式。对“小资产者” 生存境遇和现实诉求的关切构成了蒲鲁东历史意识以至其全部理论体系的前提。蒲鲁东关于人类历史规律以及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在欧洲工人群体中广受欢迎,无形之中对工人阶级传播了错误、扭曲的思想观念。为消解蒲鲁东造成的影响,马克思对其“小资产者”立场的局限性展开批判,指出“小资产者”立场决定了蒲鲁东运用历史意识的原初目标和最终归宿具有强烈的利己性质,蒲鲁东提出的历史规律和理想社会形式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者”的乌托邦之梦。
马克思对蒲鲁东“小资产者”立场的认知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初次接触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时,他十分欣赏蒲鲁东带有强烈历史感的批判风格,曾在1842年《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把蒲鲁东归入共产主义者的行列,并认为与其他共产主义者的著作相比,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尤为值得“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⑮到了1844年撰写《神圣家族》时,马克思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及蒲鲁东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但已经隐约地意识到蒲鲁东的立场在本质上没有超越以往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一方面颂扬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有可能促成国民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⑯另一方面又批评蒲鲁东没有摆脱国民经济学的前提限制。马克思认为,“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都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⑰蒲鲁东显然没有对这种前提进行过多的反思,所以他关于所有权起源及其发展历程的考察仍局限于国民经济学的范畴之中。直至1846年蒲鲁东发表《贫困的哲学》,马克思才充分地认识到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审视与批判从始至终都植根于“小资产者”的生存现状和利益诉求,指出蒲鲁东真正关切的是如何维护“小资产者”的财产。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⑱受限于这种“小资产者”的矛盾心理,蒲鲁东必然无法接受私有财产通过自我否定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洞察到蒲鲁东的历史意识是建立在“小资产者”的现实诉求之上的,加之欧洲的工人群体对蒲鲁东所提出的历史规律以及相应的社会改良方案深信不疑,马克思对蒲鲁东相关结论的看法逐渐从一种模糊不清的暧昧态度转向了全面批判的立场,即展开对蒲鲁东理论立足点的彻底批判。梅林曾提及,“法国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的最卓越的代表就是蒲鲁东”。⑲蒲鲁东之所以能够在工人群体中获得极高的认可度,一是因为他关于在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改建社会的思想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是因为他本人作为小生产者的苦难遭遇在法国工人中易于引发共鸣。就第一点来说,与蒲鲁东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未能走向历史的深处以探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所有权视为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把私有制视为永恒不变的神话,拒斥任何面向未来的进步;空想社会主义者则无视历史传统,凭借头脑的幻想,企图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上建立公有制社会。蒲鲁东声称自己的“救世良方”奠基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逻辑之上,“一个从‘科学’角度来论证社会变革的著作无疑会受到广大工人的欢迎”。⑳就第二点来看,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小资产者”与“无产者”在诉求上具有许多共通之处,当蒲鲁东从自身成长经历出发考察所有权的历史根源,高呼“所有权就是盗窃”,力图在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探究如何走向自由、平等的社会形式时,工人阶级难免产生较为强烈的思想共鸣。面对蒲鲁东及其理论引发的工人阶级观念混乱,马克思认为公开披露蒲鲁东的立场局限,显得尤为迫切与必要。
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蒲鲁东时刻表现出对历史的敬畏感,但是“小资产者”的立场从前提上限制着他运用历史意识的原初目的和最终归宿,致使其难以涉足真实的人类历史。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力图引导人类社会走向绝对平等的历史阶段的目标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小资产者”的幻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心目中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占有相同的财产,这种平均主义式的“平等”观念带有浓厚的“小资产者”的道德色彩。在空洞且狭隘的平等原则的指引下,蒲鲁东妄图找到某个最完满的社会形式,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成为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私人财产的“小资产者”。蒲鲁东的这一目的无法在真实的历史中得以实现,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头脑中构想出某种符合心意的历史规律。蒲鲁东依据“小资产者”的道德标准评判出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认为历史的进步表现为新的经济范畴对旧的经济范畴“坏的方面”的克服,人类历史体现为他所排列出的“经济系列”。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试图通过两大卷经济范畴就能“编排出”的人类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造的结果,在其中根本洞察不到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真实的历史面貌,而仅仅只是看到那位为了实现“小资产者”与大资本家的财产平等而在“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蒲鲁东囿于“小资产者”的视野,难以客观全面地考察人类社会的进步趋势。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表面上看似通过揭示历史的客观规律而指明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实则却是“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如果说经济学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通过否认历史来证明资产阶级私有制是自然的、永恒的,从而让历史止步不前,那么蒲鲁东则从“小资产者”在现代社会中的悲惨遭遇出发,致力于在历史的客观逻辑的基础上确立一种贴近“小资产者”诉求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始终以“小资产者”的眼光批判现代社会、描摹未来社会,其历史理论的归宿只能是根据歪曲的历史规律,将人类社会引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之前的中世纪时期。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在讨论分工的演化时不自觉地将现代分工和中世纪分工对立起来,蒲鲁东指责现代工厂中的分工导致人的劳动丧失了专业性质,认为工人不能只懂得别针工艺的某一部分,而应该能够生产出一个完整的别针。当蒲鲁东强调工人都需要掌握某项产品的全套工艺时,其思想上的返祖倾向已经表露无遗。马克思评价道,蒲鲁东“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他在考察各类经济现象时,意识不到它们对于全人类进步的革命意义,而只关注它们侵占“小资产者”利益的一面,这使得他所建构的历史趋势始终是指向中世纪的。
为了消解蒲鲁东对欧洲工人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马克思站在救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高度上批判了蒲鲁东“小资产者”立场的狭隘性。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固然敬畏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趋势,强调在历史的进程中重新审查所有权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但其本意并非在于消除一切私有财产,相反是为了捍卫“小资产者”的私人财产;蒲鲁东自以为找到了历史的客观规律,指引着人类社会通往自由的、平等的历史阶段,实际上却是妄图让人类社会倒退回中世纪。通过对目的和归宿的细致剖析,马克思揭露了蒲鲁东“小资产者”立场的局限性。
三、马克思对蒲鲁东“先验的上帝”假设的批判
在揭露并批判蒲鲁东“小资产者” 立场的同时,马克思还批驳了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另一个前提——“先验的上帝”假设。蒲鲁东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之前预先假设了存在一个上帝规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秩序,他认为探索和把握历史规律之前必须承认这一假设。为了驳斥蒲鲁东,马克思首先剖析了蒲鲁东为什么需要提出“先验的上帝”假设,其次指认了蒲鲁东“先验的上帝”假设对黑格尔哲学的误解,认为其只是“冒牌的黑格尔词句”。
蒲鲁东在认识到确证历史规律对改建现代社会的重要意义后,便致力于以抽象的思辨方法考察经济现象背后的人类历史秘密。在《贫困的哲学》中,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在纷繁杂乱的现象背后呈现出特定的进步趋势,是因为受到了某种特殊力量的支配或天命的启示,“那些追随博胥埃、维科、艾尔德和黑格尔之后埋头于历史科学的人,迄今所作的努力都不过是证明确实存在一种支配着人类全部活动的天命”。蒲鲁东将这种类似于“天命”的神秘力量称之为“上帝”。蒲鲁东的“上帝”不同于神学中的造物主,而更接近于德国哲学中的“理性”,是一种具备了古典哲学内涵的存在人类社会之外的“最高意志”。基于“先验的上帝”假设,蒲鲁东建构出其所谓的合乎理性逻辑的人类历史规律。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之所以需要依赖“上帝”来支撑自己的历史意识,是因为他无法从现实的人的实践这一前提出发来解释人类历史。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物质生产中不断积累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得以连续、不断进步的基础。作为人类积累性生产活动的产物,生产力对于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每一代人都无法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只能在前一代人已经积累的生产力基础上进行新的生产,创造出新的生产力,“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正是伴随生产力以及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才得以实现。然而,蒲鲁东却无法理解人们之间的这种“物质的联系”。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批判道,蒲鲁东已经“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他尝试对所观察到的进步趋势及其背后的规律作出合理阐释,但是他根本看不到社会的发展与个人行动的关联性。为了赋予历史以意义,蒲鲁东只好假设出一个“先验的上帝”,从而用“上帝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存在某种客观逻辑”。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既不理解人如何成为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物,又极力想要说明历史,最终只能把历史的进步归功于“上帝”,强调只要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规定就可以掌握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理。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关于“先验的上帝”的假设是对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的拙劣模仿。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他经济学家都把分工、货币、资本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当作是永恒不变的范畴,蒲鲁东却试图借助黑格尔哲学中的“理性”、“辩证法”等范畴和方法,说明这些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而呈现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秩序。但蒲鲁东并不能准确地理解和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只是“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 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马克思指认蒲鲁东的先验假设只是“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所谓“黑格尔词句”是指蒲鲁东沾染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属性;所谓“冒牌”,则意在说明蒲鲁东没有领会“无人身的理性”由于辩证运动而形成历史的真谛。通过对比蒲鲁东的“上帝”与黑格尔的“理性”,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先验的上帝”假设的双重错误。
马克思批驳蒲鲁东的“上帝” 延续了黑格尔“理性”的唯心主义性质,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先验前提。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对“唯物主义”冷嘲热讽,对自己从德国哲学中采撷的“普遍理性”、“上帝”等抽象观念引以为豪,他坚信人类社会的一切事务一定受到某种绝对力量的限制与规定,从而把历史研究建立在对“上帝存在”的先验假设之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这种借用“上帝”名号阐述历史的做法与黑格尔以“理性”演绎呈现历史的观点具有同一性。无论是“上帝”还是“理性”,都是头脑中臆想出的“虚假观念”,以虚假的存在物为前提,蒲鲁东和黑格尔不可能提供关于人类历史的正确解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从“理性”出发,将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当作是思维中发生的一切,认为人类社会是“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异化,使得“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蒲鲁东基于“上帝存在”的前提展开对经济关系起源以及人类历史演进的探索,把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的来源归结于天命的启示,又将现实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理解为无形的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的有形表现。蒲鲁东同黑格尔一样颠倒了观念与现实、思想与事实的关系,他所建构出的人类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
在批判蒲鲁东先验假设的唯心主义属性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批评蒲鲁东由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其在“先验的上帝”的基础上所建构的历史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完全忽视了辩证法的客观意蕴。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史,即理性把自己设定为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黑格尔摒弃了任何的外在干涉,只关注理性的自我演绎。然而,蒲鲁东无法理解和掌握黑格尔辩证法的真谛,“理性” 的辩证运动演变成机械地划分出经济范畴的“好”“坏”两面。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上帝”丧失了辩证法的内在生命力和客观性原则,其无法像“无人身的理性”一般呈现自身的演绎逻辑,相反需要“社会天才”作为自身支配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和助手。对蒲鲁东而言,“上帝”是真理的创造者,而“社会天才”是真理的探索者,它通过感知上帝的智慧与启示,不断地提出新的经济范畴以克服旧的经济范畴的弊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新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历史就是“社会天才”追随上帝、寻找真理的漫长过程。对此,马克思批判道,蒲鲁东所谓的“社会天才”实质上就是他自己,他无法理解黑格尔“理性”的自我运动,只好自己充当“社会天才”的角色,借助“上帝”的名号,主观地描画出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通过剖析蒲鲁东的“上帝”与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先验的上帝”的形而上学局限。
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历史意识具有理论局限性,没有实现基于客观历史规律确证人类社会的“现在”与“未来”的理论任务。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者”立场和“先验的上帝”假设,揭示出蒲鲁东虽然表现出历史意识的觉醒,但他所声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及改建资产阶级社会的方案实质上是披着“科学”与“革命”外衣的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前提所展开的彻底批判,不仅解答了蒲鲁东关于人类历史及其发展趋势的探索为什么失败以及失败在何处的问题,而且体现了马克思始终关切无产阶级与全人类命运的无私精神和以“现实的人”为前提探究历史规律的唯物主义原则。考察马克思对蒲鲁东历史意识的前提批判,裨益于从多维视角反思蒲鲁东历史意识的理论限度,能更加凸显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与革命性。
注释:
①参见陈先达、臧峰宇《历史科学的前提与历史思维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年第1 期。
②有学者基于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文本考察,聚焦两人的共同问题域,系统地从所有权及其扬弃方式、社会分工与人的自由、机器与自由个性、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等诸多视角呈现出马克思与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理论上的观点分歧,认为蒲鲁东将社会历史理解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而马克思强调社会历史是“现实的个人自身发展构成的社会历史”。(参见杨洪源:《〈哲学的贫困〉再研究:思想论战与新世界观的呈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有学者围绕马克思与蒲鲁东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定位的不同认知结果,指出蒲鲁东不了解“人类社会生活存在的历史性特征”,将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然社会,而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相应的思想观念都是历史的存在。(参见张一兵主编《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 页;仰海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历史性思想》,《哲学研究》2020年第5 期)
⑤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或对权利和政治的原理的研究》,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序言”第15 页。
⑪⑳余源培、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2 页。
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蒲鲁东“小资产者”立场的批判只是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身份定性,而不是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争辩。(参见Johannes Hilmer.“Two Views about Socialism:Why Karl Marx Shunned an Academic Debate with Pierre-Joseph Proudhon”,Democracy & Nature,Vol.6,No.1,200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思想家的个人身份与阶级立场的区别,思想家的“资产者”或“无产者”身份本身确实不会对他的理论内容造成影响,但当思想家基于“资产者”或“无产者”的现实境遇建构自己的理论时,“资产者”或“无产者”的立场就构成了其理论内容的前提部分,从而影响到理论内容的科学性。马克思指认蒲鲁东的历史意识立足于“小资产者”立场,其本意不在于说明蒲鲁东“小资产者”的身份,而在于从前提层面批驳蒲鲁东的相关理论,揭示蒲鲁东不是从“无产者”而是从“小资产者”的生存状况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进而批判他无法以“彻底革命的意识”探索出真实的历史规律。
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 页。
⑲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 卷,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