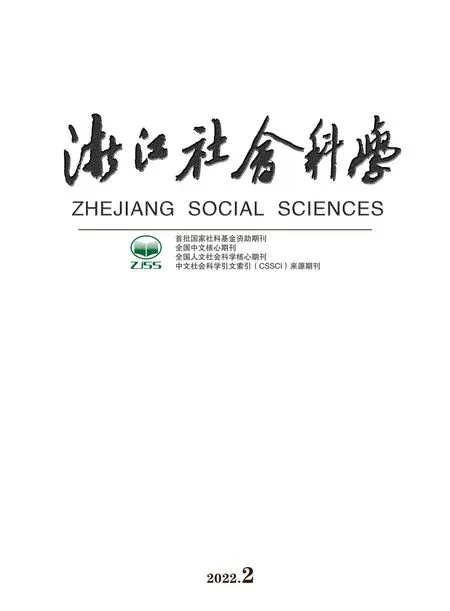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资本奴役关系透视*
□ 张一兵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的眼中,人类社会独有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正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观念和范畴都必然与特定时间中的物质生产关系赋型相关联。并且,他将这一物质关系进一步指向在经济的社会形式中出现的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产阶级的历史时间中的生产关系伪饰成天然的、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历史性的一种本质遮蔽。
1846年到1849年,马克思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进程中,确定了生产关系概念,在进一步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塑形的同时,也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中较多关注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问题。很显然,这仍然是一个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话语缺席的时期,马克思尽可能用“实证科学”的事实话语,来客观描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各种奴役现象。最终,马克思科学地认识到资本是一种支配性的统治关系,从而为下一步透视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市民社会话语IV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
1846-1847年,马克思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最后,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C,其中最重要的是“居利希笔记”。这是他对古·居利希①的“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1845年耶拿版第1-5 卷(G.Gülich.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des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 Bd. I-V,Jena,1830-1845)一书的摘要。②这一笔记中,马克思进一步找到了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和进入经济学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学研究中,他第一次接受了劳动价值论,并站到了李嘉图的立场上。
1846年6月,正当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时刻,蒲鲁东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贫困的哲学》(以下简称《贫困的哲学》)③一书。这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创立了科学方法论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后,蒲鲁东却在他们正在进入的经济学领域中,抛出了一个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构式构序和塑形出来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学话语通过貌似社会主义的形象来全面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这使得蒲鲁东的理论一经提出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我的推论是,蒲鲁东的这本书基本上是受马克思1844年用哲学话语批判经济学影响的结果。因为那时候,“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终夜争论经济问题”(恩格斯语)④。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蒲鲁东讲自己批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则会讲透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沾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得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⑤恐怕,这正是我们在分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看到的马克思那种极其复杂的黑格尔现象学话语构式。这一定深深打动和吸引了蒲鲁东,所以让后者“沾染了黑格尔主义”。可是,当不懂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蒲鲁东去模仿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时,马克思已经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错的学术悲剧。
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十分郑重地致信给俄国自由派作家巴·瓦·安年柯夫,作为他11月1日来信论及蒲鲁东的经济与哲学观点的答复。⑥有趣的是,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前不久曾致信马克思,说他“等待着您严格的批评”,马克思的正式答复就是1847年出版的 《哲学的贫困》。也是在这两个马克思用法文写作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认识深化,其中,最重要的进展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奴役本质的揭露,以及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的生成。
首先,在《致安年柯夫的信》(Marx an Pawel Wassiljewitsch Annenkow)中,我们先是看到了马克思那个独有的市民社会IV 的概念。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civil society/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从作为政治交往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话语I,下沉到劳动和需要体系的市场关系的市民社会话语II,再由黑格尔生成超越“第二自然”的批判性的市民社会话语III。关于这一观点,我已经有过初步的讨论⑦。我们需要注意,这个在资产阶级社会之外的特殊的市民社会IV,几乎贯穿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观察的整个过程。他批评蒲鲁东“没有从现代社会制度(l'état social actuel)的联结(engrènement)”中去了解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⑧这是明确标识观察社会的非物像场境特征,engrènement 是指突现在主体际关系中的社会场境关系赋型。因为,社会并不是蒲鲁东所说的什么“人类无人身的理性”,“社会(la société)——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Le Produit de l'action réciproque des hommes)”。⑨马克思的这个“交互作用的产物”,是在否定蒲鲁东将社会看成一种先验主体的看法,但它极为深刻地呈现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存在观。这个以engrènement 为本质的社会定在,既不是旧唯物主义直观中的对象物的堆砌,也不是没有了人身主体的理性构境,它是在特定时期、由特定的人们以特定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具有特定性质的、活动的、相互作用的共同生存关系场境。这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认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断言,在更大社会空间中的延伸。依马克思的看法,
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un certain état)下,就会有一定的(telle)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telle société civile)。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正式表现的一定政治国家。⑩
在《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⑪,我已经指认这八个“一定的”突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独有历史性时间特质,其实,这也会是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重要基础。从这一表述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当马克思从客体向度去描述社会定在的时候,他总是从社会生活的内在关系构序和构式本质出发的:一是生产力发展一定状况,这是一个深埋在主体劳作工艺和客观动能中的功能性水平表征; 二是生产力的历史性的构序质性决定了一定的交换的消费方式,这是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构序之上构式出来的特定商品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关系场境; 三是这种经济关系所塑形的家庭关系、阶级关系筑模起来的社会制度,即市民社会(IV);四是市民社会之上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里的法文话语实践中,出现了在德语中无法表达的有深刻含义的词语细分:马克思专门使用了法语中特有的société civile,以区别于他同时使用的société bourgeoise。马克思在此信中五次使用société civile 这一术语。从马克思这一表述的具体构境来看,这个société civile并不是特指资产阶级社会,而是在德语中无法区分的市民社会IV,即在社会赋型结构中那个决定了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性基础。然而,马克思这个时候的观点也由于历史知识的缺乏带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这个“市民社会”只是建立在已经出现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组织之上,它虽然会是一定政治国家(包括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结构性基础,但它并非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全程。应该指出,马克思此处关于市民社会IV 的内核,主要还是基于一定生产力水平之上的交换和消费活动中的交往关系,还不是更深刻的生产关系概念。生产关系的概念是在不久之后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形成的。
第一,市民社会IV 的历史性转换。在马克思的进一步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民社会IV更清楚的赋型所指。马克思说,蒲鲁东“混淆了思想和事物(les idées et les choses)”,他不能透视第一层级的物象化迷雾,所以无法理解“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rapports matériels)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base)。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⑫也是在这里,我们遭遇“基础”这个重要的表述。这个作为社会结构基础的本质,是让个体以一定的方式生存的“物质关系”。我以为,这同样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场境存在论的重要体现,在马克思这里,他谈及人及其个体,观察社会生活,从来都不是停留在人的肉身和对象物的感性直观现象上,而是非物像地在关系存在论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描述其人对自然和人与人的物质活动构序和关系赋型上。可是在这里,马克思是专门提醒我们,虽然人的社会关系赋型是非实体的场境存在,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rapports matériels。这说明,在马克思的眼中,人类社会独有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正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马克思将这一物质关系进一步指向在经济的社会形式中出现的经济关系。
在此,马克思还基于历时性的视角,进一步说明了这个作为市民社会IV 的经济关系基础的历史性改变。他说,当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le mode de leur commerce)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马克思还专门解释说,“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这里的交往显然已经不是赫斯的类本质交往,也不是狭义的经济学语境中的交换,而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活动关系,之后,马克思将用生产关系这一更加科学的概念取代它。关于这个作为市民社会IV 的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基础的历史转变,马克思非常具体地分析到,比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régime réglementaire du moyen age),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relations sociales)”。⑬这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只是封建宗法关系的场境存在直接依存于血亲关系和土地上的农耕生产力,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整个封建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基础。而当资产阶级在新型的工业生产进程之上构序和塑形起来的商品-市场经济活动,开始在封建社会的内部发展起来之后,“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如果想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变革基础性的经济关系和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于是,这就有了英国1640 和168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即“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⑭在那里,
一切旧的经济形式(formes économiques)、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l'ancienne société civile)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transitoires et historiques)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mode de production),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⑮
这里出现作为旧有的société civile 正是市民社会IV,即决定了其他社会关系的经济关系,也是作为政治国家基础的经济关系(结构)。中译文竟然漏译了l'ancienne société civile 中 的société civile,只是译为“旧社会”,这样整段表述的构境意思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的这个市民社会IV,即人们在一定时期中获得的“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的,这是对历史认识论中那个历史性时间维度的另一种表达。并且,这个暂时和历史的社会结构的基础将随着生产力的新发展,由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由此,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基础结构,是以经济的社会形式中的生产、消费和交换活动的经济关系构成,这当然不是贯穿全部历史的“社会基本矛盾”,只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出现和发生作用的规律。
第二,市民社会IV 与观念意识形态的本质。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错误时,指出他虽然看到了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却不能正确在非物像的视域中理解人们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场境中进行生产,也无法理解经济关系(市民社会IV)在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且,他更不能在关系意识论中透视到,一切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都不过是一定经济关系的历史性抽象和反映。马克思说,
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⑯
蒲鲁东的错误,在于他将自己手中的观念范畴当作了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无法意识到观念的本质只是一定历史时间下特定社会关系的抽象表现。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的本质是“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一致的,只是,他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关系意识论原则的基础上更具体地指认,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观念和范畴都必然与特定时间中的经济关系赋型相关联。所以,历史时间性的社会关系场境,会以一种人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先验构架,直接决定了人与社会的全部精神构境方式和历史质性。因而,这些观念和范畴,作为康德式的先天综合判断,将会与特定的经济关系赋型构架一样,都是历史的和暂时的,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认识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
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leurs facultés productives)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rapports);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les catégories économiques)只是这些现实关系(ces rapports réels)的抽象(des abstractions),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⑰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真的是关系场境存在优先的,他时时刻刻告诫我们必须从一定历史时间中的社会现实关系入手观察社会定在,必须考察人们在特定生产力水平之上构序和塑形起来的相互关系,人们的意识和观念只是这种特定社会负熵关系场境存在的历史性的主观映现。因为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蒲鲁东主要是在讨论经济学,所以,他将自己手中的经济范畴都看成了非历史的先验观念,他无法理解,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关系场境本质是由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构序的历史质性的改变也必然改变这种关系性存在的历史质性,进一步,一切经济范畴都只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赋型的产物,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是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⑱其实,这一观点与上述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国家的表述一起,就会塑形起基础决定政治国家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完整理论。
其次,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历史性关系定性。第一,在历史认识论的维度中,资产阶级社会必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暂时的经济关系下的现代私有制。针对蒲鲁东抽象地讨论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历史性出现的机器、分工等问题,马克思告诉他,在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封建社会中,“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⑲并且,农耕自然经济关系场境中,并没有机器、分工和竞争作为特定生产力历史构序和经济关系赋型的产物,这些工业生产工具、新的劳作方式和市场交换中才出现的复杂经济关系场境,会是在特定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才会历史性发生的事情。具体些说,机器系统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基础的工业生产构序的历史性产物。针对蒲鲁东将机器当作抽象经济范畴的错误,马克思说,“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relations de notre régime économique actuel)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⑳如同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的“拉犁的牛”一样,机器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业生产的工具,而不是经济关系,在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经济关系之下使用机器,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盘剥劳动者的武器,这种特定的关系性奴役场境并非机器本身的过错。同样,在封建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分工,因为只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逐渐发展起来以后,才出现了在14-15 世纪早期资产阶级殖民主义制造的世界市场中出现的奴役性国际分工,“在英国开始于17 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 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分工。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对分工的理解已经开始发生重要的改变。
第二,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是一种间接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奴役关系下的直接奴隶制。这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新的认识。因为蒲鲁东抽象地讨论奴隶制与自由,而马克思则告诉他,奴隶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在不久后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更深入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作为一种经济范畴,奴隶这一概念不过是对历史性的“奴隶制(l'esclavage)”社会关系赋型的主观映现。马克思还告诉蒲鲁东,“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中,历史上出现的直接的奴隶制却在殖民主义奴役关系中畸变为一种新型的直接奴隶制。马克思深刻地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对殖民地人民的直接奴役关系建构起来的间接奴隶制 (l'esclavage indirect)。那么,什么是殖民地建立新型的直接奴隶制(L'esclavage direct)呢? 马克思在这里说,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pivot de notre industrialisme actuel)。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colonies)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commerce du monde),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 工业(grande industrie machinelle)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
这是一个奇怪的历史时空错位关系。直接以可见的强暴式的掠夺方式建立起来的奴隶制,是很多欧洲国家在中世纪之前处于不发达的经济发展阶段时出现的社会历史形式,然而马克思却发现,这种直接的奴隶制却成为今天资产阶级“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美洲的直接奴隶制的残暴掠夺和压榨,就没有棉花;没有大量的棉花,就没有欧洲现代工业中的纺织业。在今天欧洲大陆已经绝迹的直接奴隶制,资产阶级却在另一个现实空间——“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种公开的殖民主义奴役,也成了资产阶级社会(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世界贸易和大机器工业无法缺少的条件。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标榜的“文明”,其实是另一个落后土地上通过殖民主义直接奴隶关系支撑起来的间接奴隶制。其实,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本质是“间接奴隶制”的认定,还有一个更深的构境层面,即在他后来完成的资产阶级通过形式上平等交换,而实质上无偿占有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实现的。
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奴役本质
不久之后,马克思用法文写作并公开出版了全面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 一书的论著——《哲学的贫困》。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马克思展开了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他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批判的重点不再是批评蒲鲁东那种明显的黑格尔式的观念决定论,而在于分析他的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隐含的深层唯心主义,这其实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先导性,即当蒲鲁东面对经济学研究时,他一方面满怀激愤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可另一方面却又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出现的社会关系之反映的经济范畴永恒化。实际上,这也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非历史的意识形态本质。
首先,是马克思在此第一次直接论说了李嘉图与黑格尔在面对资产阶级社会态度上的关系:“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末,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很显然,与《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同,此时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构式上不再主要根据还有一丝主体向度残余的斯密,而基本上转到了客体向度中李嘉图的立场上来了。这当然是马克思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获得的新进展。我们发现,马克思已经在直接肯定李嘉图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了。这个不同于经济学称谓的“历史学家”,并非真的是说李嘉图是一个历史学研究者,而在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向度上,指认李嘉图的经济学话语无意识达及的客观性维度。所以马克思会认为,李嘉图“已经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bourgeoise)的理论”。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八次使用了不同于société civile(市民社会)的société bourgeoise 一语。实际上,这正是德文中已经转喻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个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根据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们知道李嘉图“把人变成了帽子”,是指他的经济学客观上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畸变为物(帽子)的过程。后面,马克思将会用人与人的关系场境颠倒地畸变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事物化批判理论,接着李嘉图往下说。然而马克思又说,李嘉图的观点的确是“把人变成了帽子”,但这不是因为李嘉图观点的“刻薄”造成的,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客观事实本身就是刻薄的。在这里,马克思直接反对法国人本主义文学家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攻击。马克思的这种肯定的态度,与《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对李嘉图的简单否定(“犬儒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进一步,马克思指认在黑格尔那里,他又“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过去我们在解读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时,大多认为这是在批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其实不然。依我的解读,马克思说黑格尔将李嘉图的“帽子”变成了观念,其实是发现黑格尔看到了李嘉图客观呈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场境中发生的事物化颠倒,但他又用体现绝对观念的国家与法批判性地超越它。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在市民社会III 的批判构境中,将事物化了的原子个人在市场无序交换的经济必然性王国中的物性自发构序状态重新扬弃为自由王国中绝对观念。这是马克思更深一层的批判性构境。
其次,是对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生产关系的科学透视。这是原先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那个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际交往关系,向生产领域关系场境赋型的逻辑下沉。马克思在谈及蒲鲁东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不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内生产,他不明白,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人们总会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赋型场境中的共同活动,这些社会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发生历史性改变。
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 (rapports sociaux déterminés)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nouvelles forces productives)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la société avec le capitaliste industriel)。
这当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层级非物像认知中的双重观点,如同改变外部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当下发生与消失一样,作为社会定在本质的人们的社会关系赋型场境,也是当下发生并迅速消失于人们的共同活动之中,但是,如同一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活动塑形出特定的对象性产品(麻布、亚麻)一样,人们同时也不断地将这种怎样生产和生活的关系赋型场境历史性地再生产出来。在许多年之后,列菲伏尔在《空间生产》(1974) 中将生产关系场境的生产变成了社会空间的历史本质。马克思在历史认识论的维度上指认,当生产力获得新的进展时,人们也会改变自己怎样生产的构序方式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赋型。手推磨时代的自然经济生产力,必然赋型出帝王将相高高在上的封建宗法性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而蒸汽机开创的工业生产时代,一定会产生出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场境存在。马克思批评蒲鲁东,指出他根本不能理解这种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境关系存在本质,比如,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看到的“货币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La monnaie,ce n'est pas une chose,c'est un rapport social)”。这也是那个交往异化构式的没影点。在《穆勒笔记》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的物性货币,被透视为人的交往类本质关系的异化。在此,货币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可见的对象物背后,捕捉到不可直观的社会关系场境,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非物像的科学透视感。我们在生活中遭遇金钱,经验常识会简单地将其视作财富,而马克思则让我们深一步发现,这种物性实在的本质,其实是一种被遮蔽起来的社会关系之伪境。在这里,马克思还没有进一步说明,这种社会关系是怎样历史性地颠倒为“物”的,即经济关系的事物化颠倒,以及物化错认的复杂机制,这一点他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逐步破境的。
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发现,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质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rapports de production),“这种关系正如个人交换一样,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货币,并不是直观中可见的对象物,它是一种隐匿起来的社会关系,这是过去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的问题,但是,从《穆勒笔记》开始,这种从交往关系的异化中透视出来的交换,主要还是停留于流通领域中的,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市民社会IV时,大多使用了一定生产力水平之上的主体性的交往关系,这一观点一直持续到不久前的《致安年柯夫的信》。而这里,马克思直接指认出,货币除去是一种流通领域中发生作用的交换关系,同时,它也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正是这个生产关系代表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筑模质性方面。显然,这离那个可以带来新的金钱的金钱——资本关系更近了一步。可以发现,在过去马克思使用人对人主体际交往关系的地方,他开始使用下沉到人对自然构序的生产关系的概念。马克思的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正是在此时形成的,这应该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场境关系存在论中最重要的进展。其实,广义的生产关系应该再科学地区分为两个构序层:一是那个“怎样生产”的劳作活动构序和塑形的根本性关系,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功能水平之上的劳动分工与协作等狭义的生产关系; 二是这种劳作中的生产关系再赋型整个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关系(如经济的社会赋型中的经济关系场境)的本质,由此再规制全部上层建筑的场境关系。这里,马克思还提出,非物像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以及“这些关系(rapports)本身是怎样产生的”。这也就奠定了走向对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生产关系本质进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这应该是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明自己的经济学探索主旨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研究的逻辑缘起。
其三,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在于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永恒化。有了生产关系概念这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不同程度地越发深刻起来了。在马克思看来,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有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 (division du travail)、信用(crédit)、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rapports de la production bourgeoise)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rapports)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mouvement historique)。
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任何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都必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中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赋型相适应,因此都是历史的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和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分工”、“信用”和“货币”都是特有的历史时间中赋型的生产关系,它们只是近代工业生产发展和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的历史产物。实际上,这里“分工”是出现在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分工,它属于狭义的技术生产关系,而“信用”和“货币”则是在狭义生产关系之上生成的经济关系。马克思在同期写下的《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斯密和李嘉图的学生都会知道,现代私有制是整个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bürgerliches Produktionsverhältnis)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即“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这说明,在马克思眼里,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一个物性对象堆砌的客观实在总体,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场境关系存在,它是一种复杂“生产关系的总和”支撑起来的“现代私有制”,这本身就是一定社会“历史运动”的产物。
马克思分析说,“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productivité matérielle)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les principes,les idées,les catégories)。”这一观点,正是前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关系意识论的进一步展开说明。这也是本文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意识论的用意,因为不能进入关系意识论的构境,是根本不可能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相关表述背后的非物像具体观念赋型的。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中出现的思想观念,只能是特定历史时间中社会关系场境的主观映现。“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relations)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produits historiques et transitoires)。”社会关系场境存在的特殊时间质性,规定了相应观念和范畴的历史性本质,这也是历史认识论的核心构序点。对此,马克思结合欧洲的历史现实举例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 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可是,
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 世纪或者18 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forces productrices)、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rapports d'homme à homme)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l'histoire réelle),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作剧作者又当作剧中人物(les auteurs et les acteurs de leur propre drame)吗? 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这是《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比较重要的一段表述。第一,一定的原理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原理只不过是一定时期中的人们怎样生存的关系场境的映现,具体说,这就是一定历史时间中人们的“怎样生产” 的劳动塑形方式和能力,以及这种生产构序方式所生成的人与人之间怎样发生场境关联的活动和相互作用构式,决定了这些关系场境主观映现内容的关系赋型本质。相对于个人生活和认知活动而言,这就是社会历史先验构架之上“先天综合”观念架构的隐秘作用关系。第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所指认的人们即是创造这一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其中的“剧中人物”,在存在论上,它直接体现了一种根本性改变,即工业生产构序通过给予自然物质存在以全新的用在性方式,人成为世界的主人;可当资产阶级创造出商品-市场经济王国时,却又使社会关系赋型场境变形为经济力量支配人的他性舞台,人离开了自然存在的脚本创作了自己的历史,却又成为这一剧本中被无形驱使的木偶角色。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存在论中的奇怪悖论。而在认识论维度上,根本性的认知对象异质性转换为: 我们是在看我们自己表演的作品,但我们却认不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第三,马克思强调说,这种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的存在论和非二元认知构架中的特定关系场境,不会出现在11 世纪欧洲的农耕时代中,因为人不是自然经济的剧作者,人只能历史性地成为18 世纪工业文明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物。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能是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14-18 世纪)人们借以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以及这一经济关系发展的“个人主义原理”的特殊规律性。这是社会关系场境存在论和历史认识论理论赋型中的一次重要的进展。
然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视为人类生存的自然(天然)形态,视为亘古不变的非历史的东西。马克思分析道:“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 一种是人为的(artificielles),一种是天然的(naturelles)。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la bourgeoisie sont des institutions)是天然的。”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学说史上,这是从重农主义开始强调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非人格化“自然性”构序意向。而从实质上看,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rapports de la production bourgeoise)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lois de la nature)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lois éternelles)。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Ainsi il y a eu de l'histoire,mais il n'y en a plus)。
这里的“自然规律”当然是在黑格尔的“第二自然”反讽的构境中使用的,它具体是指处于资产阶级盲目市场交换和竞争的经济熵增中自发构序起来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是排除了过去农耕劳动中的主体意志和经验习惯后的非人格化客观运动机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这种经济熵增和自发构序运动法则被伪饰成最符合的人天性的“自然法”和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性的生产关系就成了永恒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说得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中,是承认了历史的进步性,而一旦自己坐了天下,则将资产阶级的历史时间中的生产关系伪饰成天然的、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历史性的一种本质遮蔽。
三、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发生学与经济学研究
首先,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历史分析。这应该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第二次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发生做这样的历史描述,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天然的自然秩序,而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特定生产构序和经济关系赋型的产物。这恰恰针对了上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第一方面,从统治阶级主体来看,马克思说,“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bourgeoise)。这是说,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步生成的,然后才会有从政治上推翻封建专制,并将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新世界的可能。同时,马克思也是从主体的构境中使用capitaliste (资本家)一词,来表征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主体代表。在此书中,马克思近20 次使用capitaliste 一词,并且比较集中地使用capitaliste industriel(工业资本家),以表现与农业土地上的主体所有主——地主的不同质性。在后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本质——资本统治关系形成了全新的科学认识之后,capitaliste 一词才从主体视位中的资本家主体转换为描述社会客观本质的资本主义的形容词。这是后话。
第二方面,从客观社会结构发展进程来看,“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formes économiques)、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公民关系(relations civiles) 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l'ancienne société civile) 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这里,我再一次看到马克思精确地用法文中不同于société bourgeoise 的société civile,来表征市民社会IV,即作为政治制度直接基础的经济形式。这里有三个隐性构境层:一是马克思注意到资产阶级社会是从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这为他之后科学地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复杂社会赋型中同时包含多重异质性生产方式的观点,奠定了先期逻辑构序条件; 二是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旧有的社会定在开始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创造了一定的基础性认识; 三是马克思精细地区分了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之上“公民关系”的场境存在,并且指认这种关系是由旧有的封建社会关系场境的废墟中得以塑形。
第三方面,从客观工业生产发展的进程来看,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构序基础也是历史生成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比较重要微观推进,可在逻辑构序的具体分析中,它似乎开始接近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因为它的话语实践开始不再具有一般社会运动的普遍特征。如果说,封建社会的生产基础是手推磨式的劳作构序和塑形,那么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基础则是蒸汽机,即机器系统的工业生产技术构式。这是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已经说明过的观点。不过这里分析更加具体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是非自然的工业劳动。他说,与农耕劳作中的自然经济不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给的,而是工业(l'industrie) 生产出来的”。这是一个物质生产构序中在社会负熵源上的质性差别,在过去自然经济的畜牧业和种植业中,绝大部分生产产品都是自然物,人的劳动生产只是在选择和优化生长条件上作用于外部自然对象,并不能根本改变无机物质和生物存在的自然有序性和负熵构式,而在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直接物质基础的工业生产中,则是由劳动构序和创造出来的社会负熵中的非自然产品,因为工业生产中的劳动生产,已经开始直接构序和塑形物质存在方式。其实,这恰恰是经济学话语中配第发现不同于“自然财富”的“社会财富”的基础,当然也是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客观前提。这才真正历史性地生成马克思所指认的特定历史现象: 人既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又是这一历史的剧中人的关系存在论场境。这是马克思在历史认识论中,第一次明确指认出认知对象的改变,即从外部自然的物性对象存在向人的活动构序产物的转换,而工业劳动生产的特殊构序和负熵质也会改变认识活动构境的本质。马克思说,“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 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直接生产力构序基础,而“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工业生产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的赋型。先是工场手工业生产构序中劳动分工的出现,这是劳作构序中的技术生产关系。马克思说,“工厂手工业的特点不是将劳动分解为各个部门并使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去从事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拜比吉《关于机器和工厂的经济性质》(CH.Babbage,Traite sur L’E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Paris: Bachelier,Imprimeur -Libraire pour Les Sciences)一书里关于这种劳动分工的相关讨论。这是发生在工场手工业中资本支配下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态度与不久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处于劳动异化构式没影点处的分工证伪是明显不同的,这可能是马克思第一次正面描述斯密等经济学家已经指认的劳动分工,虽然这一分析并不十分具体。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讨论了简单协作和劳动分工问题。然后是机器化大生产构序的历史在场,“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操作的组合”,机器的本质是从劳动主体构序和塑形对象的活动和协动关系转向客体性的工具系统工序赋型,机器生产促进了原先在工场手工业中出现劳动分工(协作)。“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vice versa〔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不难体会到,这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比较少有的对社会物质生产过程的客体向度描述。当然,这种描述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非物像透视的第一层级构境之中。因为,这是在观察非直观的物质生产构序在工业阶段发生的具体对象性塑形和构式方式的变革,这里的机器系统和分工,都是客观生产技能赋型的新方式。我推测,这些新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此时马克思正在从事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从乌尔、拜比吉等人那里对现代工厂和机器生产的研究成果中获得的。我也注意到,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摘录到拉博德关于协作问题的论述。这种客体向度的描述,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经常出现在马克思思考相对剩余价值发生的客观条件中,当然,他也具体讨论了机器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作为资本的力量对工人的外部压力。最后,由于机器和蒸汽等自然力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并且,“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绕道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道开辟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体系,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必然促进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赋型的空间扩展和自身生产力的强劲发展。
其次,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初步经济学分析。这当然也是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成果。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致安年柯夫》中的哲学分析不同,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公开讨论了此时他眼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构序的历史性质和经济关系赋型的特质。一是资产阶级社会中交换成为统治关系。这是一个接近经济学的判断,但却内嵌着特殊的政治批判。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产品,整个工业存在都转化商业(toute l'existence industrielle était passée dans le commerce),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l'échange)”。这是说,工业生产所塑形的劳动产品,已经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直接需要(效用),而是为了功利性的商品交换,工业生产构序为资产阶级商品-市场经济创造了客观前提,而交换关系则使工业生产本身赋型为商品生产。为此,马克思还进行了历史认识论中的比较分析,他说,与封建社会中的交换不同,“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superflu),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对象;而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一切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这也意味着,交换关系统治了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当然,这种关系场境存在作为社会负熵质,却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特有熵化和自发物性关系构序的事物化伪境。因为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的缺席,马克思在此并没有去深究这种关系颠倒的根本原因。他告诉我们,今天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temps de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de la vénalité universelle),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市场价值(valeur vénale)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金钱世界,人们生活中的“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 都必须在市场中找到具有交换性的“市场价值”,甚至过去不能交换的爱情和良心都成了买卖的对象,通俗地说,人的一切存在都必须先拿去变卖才能存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见赫斯的影子,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此处对交换的分析已经是从经济学的话语来塑形的。在马克思将来的经济学研究中,他将历史性地说明,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历史性转变,在交换关系背后,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不是交换关系成为统治,而是资本的抽象关系成为统治。并且,同样是在批判金钱关系,与《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构式不同,马克思这里并没有现象学式的批判认识论构境,而是基于经济学话语中的“市场价值”居统治地位的事实指认,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才被彻底改变。当然,“市场价值”还不是一个准确的经济学术语。
二是以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的规律成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历史规律。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错误中,马克思对比了蒲鲁东与李嘉图的观点,“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节点,因为这可能马克思第一次公开肯定劳动价值论。这也应该是马克思在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我们一定要注意,劳动时间和价值关系都不是可以直观的物性实在,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入口,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非物像的关系场境存在论。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李嘉图的价值论 (théorie des valeurs) 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interprétation scientifique); 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李嘉图承认“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恰恰是从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归纳出他的理论公式的,这个公式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抽象。与《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与劳动价值论擦肩而过的情况不同,此时他已经意识到,李嘉图(斯密) 的劳动价值论将是自己进一步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剥削的努力方向,这对他科学地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统治的本质将是关键性的一步。从认识论的维度看,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构式基础,从斯密转向了李嘉图。有趣的是,在马克思思想构境的深层,原先在《巴黎笔记》中肯定斯密经济学内嵌劳动主体性本质,否定李嘉图经济学基于客观物性系统(“犬儒主义”)的态度有了一种奥妙的改变:李嘉图经济学中从现实经济关系出发的劳动价值论,更有可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走向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剥削秘密的揭露。
三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活动中客观发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指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过程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当然也是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在他读到的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等人那里,已经谈到了这种经济危机现象。在这里,马克思提出,“在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工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l'anarchie)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都处于自发性活动的总体无政府熵增状态之中,这既是商品-市场经济进步的内驱力,也会是产生自身复杂矛盾的根源,由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由于不可避免的强制(fatalement contrainte),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de prospérité,de dépression,de crise,de stagnation)、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这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的话语中,第一次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活动内部矛盾的历时性发展状况,科学地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走向消亡的努力。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高举起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全新基础。
注释:
①居利希 (Ludwig Gustav von Gülich,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派领袖。1810—1812年,他曾在哥廷根大学进修财政学(国民经济学),1817年在柏林洪堡大学旁听经济学。1830年出版了《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并于1842、1844 和1845年先后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至五卷。
②Karl Marx: Exzerpte aus Gustav von Gülich.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VI/6,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3.
③此书在1846年6月出版,马克思于12月读到此书。以下简称《贫困的哲学》。该书中译文参见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 卷,徐公肃、任起莘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 页。
⑤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 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1、31~32 页。
⑥安年柯夫(Pavel Vasilievich Annenkov 1813-1887):当时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的通讯员。他在巴黎看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后,于1846年11月1日写信给马克思,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由于书商的拖延,马克思到这年的12月底才看到蒲鲁东这部著作,他用了两天时间浏览了一遍,就用法文给安年柯夫写了这封回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6~488 页。Karl Marx,Marx an Pawel Wassiljewitsch Annenkow,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Ⅲ/2,.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79,S.70-80.
⑦参见拙文《马克思“市民社会”话语实践的历史发生构境》,《东南学术》2021年第1 期。
⑪我已经完成《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第二稿。此书不久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