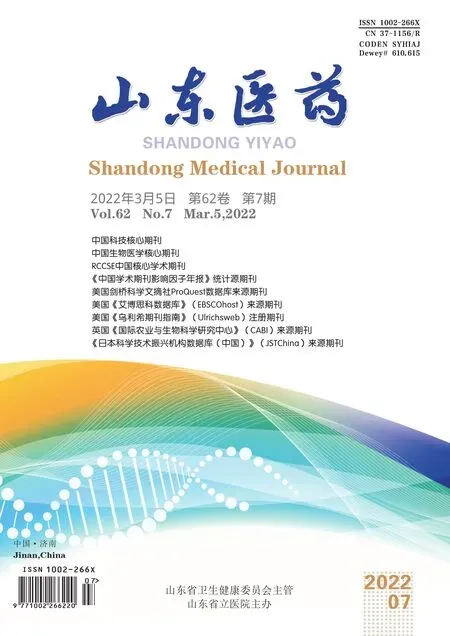诱导痰检测技术在支气管哮喘中的应用进展
张亚丽,蒋毅
1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太原 030001;2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支气管哮喘(哮喘)是常见的呼吸系统慢性疾病,其本质是慢性气道炎症,由多种细胞和细胞因子参与。诱导痰检测是通过雾化吸入高渗盐水诱导产生痰液,进而分析其中细胞成分和上清液可溶性介质的一项技术[1]。作为气道采样的一种非侵入性方法,诱导痰检测具有无创、安全、可靠、简便、可重复、更易被患者接受的优点。已有研究表明,诱导痰和自然咳痰的检测结果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2],所反映的气道炎症结果也与其他传统有创技术结果具有一致性,故诱导痰检测常用于不能自主排痰的患者。诱导痰中的细胞学计数被广泛用于哮喘的诊断、分型、炎症水平的评估,其非细胞成分如细胞因子等在哮喘中的作用也在临床实验中被反复验证。近年来,组学在国内外各项研究中的运用不断成熟。对诱导痰成分进行组学分析,特别是转录组学与蛋白组学分析为哮喘诊治、病理生理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3]。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1 诱导痰细胞学计数
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在临床上已被广泛应用,主要是对其中的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所占百分比进行分析。目前尚无公认的诱导痰细胞计数参考值范围[4]。
诱导痰细胞学计数结果与传统诊断、评估哮喘方法具有一致性,但其在哮喘分型、病情评估、个体化治疗上的作用不可替代。研究发现,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与肺功能中1 s用力呼气量(FEV1)、1 s用力呼气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EV1%)、1 s用力呼气量与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均呈负相关[5-6]。对比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与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呼气峰流速(PEF)变异率、基线FEV1、FEV1/FVC%、口服糖皮质激素后FEV1的变化等在哮喘中的诊断价值,发现痰嗜酸性粒细胞的敏感度(86%)和特异度(88%)最高[7]。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反应的气道炎症水平可用来评估病情,还可根据诱导痰中细胞学计数所占比例比将哮喘分为四种表型:嗜酸性粒细胞型(单纯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2.5%,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1%)、中性粒细胞型(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1%)、混合细胞型(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2.5%且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1%)、寡细胞型(各细胞比例均在正常范围)[8-9]。不同表型哮喘患者表现为不同的临床特征。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在重症哮喘患者中显著增高,可见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可能与哮喘严重程度、肺功能下降有关。也有研究证明,诱导痰中性粒细胞比例的升高与哮喘严重程度密切相关[10]。中性粒细胞比例增高还多见于老年哮喘患者,或空气污染、细菌、病毒感染的哮喘患者[11-12]。连续监测痰中嗜酸性粒细胞以量身定制成人哮喘治疗方案可能会减少哮喘恶化,这在儿童哮喘中也同样得到证明[13-14]。
临床中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可反映气道炎症类型及水平的动态变化,借以评估治疗效果,及时调整治疗方案,还有利于长期优化管理和评估预后。但目前由于时间和成本问题,在临床工作中进行频繁的诱导痰分析被限制,其在临床实践中的诊断和治疗价值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发展。
2 诱导痰中的细胞因子
诱导痰中各种非细胞成分中,细胞因子检测在临床及各项研究中的运用最为常见。诱导痰中细胞因子主要是由气道上皮细胞和各种免疫细胞产生,在哮喘发病的各个阶段发挥作用并参与哮喘的发生和发展[15]。根据引起气道炎症的免疫反应不同,哮喘可以分为2型与非2型,分别由不同的细胞因子介导。呼吸道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是哮喘的病理特征,Th2型细胞因子IL-4、IL-5、IL-13、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参与嗜酸性细胞的活化、增生、聚集曾被认为在哮喘发病中起主要作用;IL-4、IL-13还可促进免疫球蛋白E的分泌,促进气道炎症的形成与维持。近年来研究发现IL-13还参与维持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重塑,在哮喘中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重视。参与非2型哮喘发病的细胞因子及可能的机制:IL-8、TNF-ɑ、白三烯B4趋化形成肺组织中性粒细胞炎症;IL-17介导的3型免疫反应;干扰素-γ介导的1型免疫应答;全身性炎症反应(由IL-6介导)。还有一些由气道上皮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IL-25、IL-33、IL-8,作为促炎因子,促进各型免疫反应的极化,在哮喘发病的初期起重要作用。
哮喘患者诱导痰中细胞因子水平与正常对照组之间有着明显差异已被反复验证,且与疾病严重程度、控制情况密切相关。曾有研究表明,在重症哮喘患者诱导痰中GM-CSF、IL-26明显增多[16]。近期的研究也发现,诱导痰中TSLP、TNF-α等水平与哮喘严重程度密切相关[17],IL-6与FEV1、FEV1/FVC呈显著负相关[18]。还有研究证明,诱导痰中TNFR1和TNFR2在中性粒细胞型哮喘和重症哮喘患者中明显增加,其水平还与肺功能、哮喘控制情况、年龄密切相关[19]。研究发现,IL-5、IL-17a、IL-25 mRNA高表达的患者肺功能参数明显下降;哮喘未控制组痰中IL-5、IL-17a、IL-25 mRNA表达高于哮喘控制组,IL-5、IL-17a高表达的哮喘患者中未控制哮喘发生率显著高于低表达的哮喘患者,IL-5、IL-17a、IL-25高表达的患者哮喘往往难以控制[20]。
除了对哮喘病情评估,诱导痰中细胞因子检测在不同哮喘表型的病理生理分析上也被广泛应用,为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老年哮喘患者中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升高,IL-1β、IL-6、IL-8、嗜酸细胞活化趋化因子-1、GM-CSF、与Th17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蛋白表达升高。研究还表明,老年哮喘患者痰中IL-6、人类巨噬细胞炎性蛋白3α水平升高与哮喘控制率降低显著相关,痰中中性粒细胞、IL-1β、IL-6和人类巨噬细胞炎性蛋白3α水平升高与过去12个月住院风险增加相关[21]。关注诱导痰中细胞因子的检测有助于针对老年哮喘患者这一特殊人群制订新的管理策略。FEV1快速下降的哮喘患者诱导痰中IL-5、IL-8水平明显上升。这些因子可能是哮喘患者FEV1加速下降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22]。检测分析诱导痰中细胞因子虽然还没有广泛运用于临床,但在哮喘的发病、病情评估、个体化治疗等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反复验证。
3 诱导痰转录组学
转录组学在整体水平上研究细胞或组织中基因的转录情况,反映不同组织或细胞中基因转录的总体特征。利用诱导痰转录组学可以对异质性的标本进一步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哮喘的认识,为哮喘的发病机制研究及诊断提供新思路,甚至可能为治疗提供新靶点,特别是近年来被用于重度哮喘,使重度哮喘研究有了全新突破。
一项研究采用无监督聚类分析法对哮喘患者痰与血转录组分析确定了三个具有不同临床和生理特征的“转录内型”,其中两种与重度哮喘特征相关,表明哮喘个体中存在着与年龄、发病年龄或持续时间无关的常见、稳定的基因表达模式,其中严重哮喘患者中基因表达存在系统性改变[23]。BAINES等[24]对哮喘患者诱导痰的全基因组基因表达谱采用皮尔逊中心完全链接算法进行聚类分层分类,将哮喘在转录水平上分为三种表型,第一种富含嗜酸性粒细胞,第二种富含中性粒细胞,而第三种表型不遵循粒细胞炎症模式。这与之前根据诱导痰细胞学分类确定的嗜酸性、嗜中性和寡细胞型哮喘的炎症表型相似,但并未对混合细胞型单独分类,混合粒细胞性炎症哮喘被视为一种过渡型炎症,根据细胞计数比例被归在第一类或第二类中。这三种基因表达差异与哮喘症状、免疫和炎症反应均有关。这项研究支持了哮喘的分子异质性,为进一步探讨哮喘表型的病理机制提供一个框架。
近年来诱导痰转录组学被运用于特殊类型哮喘机制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一项研究对重度哮喘患者、非重度控制哮喘患者、非重度未控制哮喘患者、健康对照组的诱导痰转录组分析发现,与其他组相比,重度哮喘患者的基因差异性表达。其中最明显的是CLC,它是嗜酸性炎症的标志,可能反映严重哮喘患者痰嗜酸性粒细胞的升高,进一步通路分析发现p38通路基因高度表达,这表明p38信号通路在严重哮喘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p38通路可能为重症哮喘潜在的治疗靶点[25]。KIM等[26]对老年患者诱导痰进行转录组学分析,根据聚类分析,将老年哮喘患者分为两个不同的分子簇,其中OXPHS基因集在一个聚类中显著丰富,EMT基因在另一个聚类中显著丰富,这两种基因分别与氧化应激和细胞衰老引起的细胞组织重塑有关,提示这两种机制参与老年哮喘的发生与发展。
4 诱导痰蛋白组学
随着质谱和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蛋白组学被应用于多种疾病的研究[27]。通过对生物材料中的数百个蛋白进行测序,可获得大量生物学信息。对人体在疾病或疾病前期表现出的或优先表现出的蛋白质进行测定、鉴别有助于发现疾病新的生物标志物,为哮喘发病机制、诊断及特异性治疗提供新思路。
对哮喘患者诱导痰进行蛋白组学分析,发现不同临床表型哮喘患者蛋白差异表达,同样,不同蛋白组哮喘患者临床特征也有所不同。一项对诱导痰蛋白组学综合质谱分析的研究发现,典型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CVA)、胸闷变异性哮喘(CTVA)患者的痰液中有23种蛋白分泌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而这三种哮喘患者的诱导痰在蛋白谱和蛋白水平上无明显差异,再次验证了典型哮喘、CVA、CTVA具有相似的发病机制。但三种哮喘患者痰液中的部分蛋白表达存在差异,这些蛋白可作为不同临床表现哮喘的特异蛋白,用于其机制、诊断、治疗等的进一步研究[28]。对哮喘控制良好与控制不佳患者的血液和诱导痰进行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在血液和诱导痰中均可测得一组生物标志物,其在两组间浓度存在差异[29]。SCHOFIELD等[30]对246例受试者(206例哮喘患者)的痰上清液采用无偏标记定量质谱和拓扑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基于蛋白质组特征的相似性,将哮喘分为10个蛋白质型,其中3个为嗜酸性粒细胞型,3个为嗜中性粒细胞型,2个为粒细胞炎症较低的特应型,另外2个根据其粒细胞偏向被归为嗜酸性细胞型或嗜中性粒细胞型,实现了比目前仅通过粒细胞计数表型更深层次的分层,这三种粒细胞分型各有其对应的临床特点,而其蛋白组型之间存在差异,又相互联系。
诱导痰蛋白组学还有利于哮喘早期诊断及与其他疾病的鉴别诊断。一项针对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黏液分泌过多患者的研究,通过诱导痰蛋白定量方法,成功鉴别出一组蛋白质,它们可以不依赖于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功能学检查,对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阻肺和哮喘-慢阻肺重叠进行早期诊断,证明了诱导痰蛋白组学在鉴别气道疾病方面的潜力[31]。同样,对已确诊为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的患者诱导痰蛋白组学进行分析,分别可鉴别出一组蛋白,其表达在不同疾病中存在差异[32-33]。相较于一种生物标志物,蛋白组学在哮喘诊断、鉴别诊断方面表现出其优势。
综上所述,诱导痰细胞学计数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其非细胞成分在各项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也已经很成熟,近年来组学在诱导痰中的应用为哮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且随着检测技术的成熟、成本的降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生物信息可从诱导痰中获取,并用于临床工作与实验研究。诱导痰检测技术在哮喘的诊断、监测疾病、研究发病机制和治疗中的潜力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