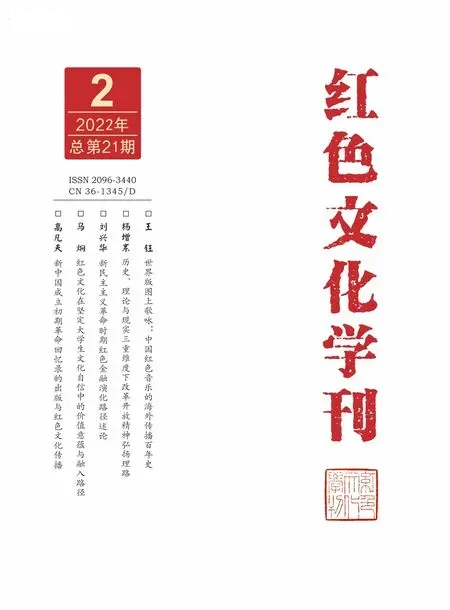1944—1945年国共两党关于“党性”的大论战
王 琪
学界现有研究对“党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本质和内涵的认识,鲜有学者对1944—1945年间这场国共双方关于“党性”的论战进行比较完整、系统的梳理。因此,本文拟从国共双方的论战与互动作为切入点,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观的生成逻辑与内涵发展,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和实践中是如何推动自身党性观走向成熟的。
一、论战缘起:“增强党性”运动之兴起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1)毛泽东:《实践论》(192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词语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并被赋予不同的政治内涵。“党性”也不例外,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中重要概念之一,其最早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建党学说,直接译自俄文“партийность”(2)注:这是一个性质形容词词干+ость的名词结构,是一种表示性质的抽象概念。俄文名词партия翻译为“党”,形容词партийный翻译为“党的”,而名词化的形容词партийность则被翻译为“党性”,它是名词,但又不同于具有实质指称的名词“党”。这与当时的一种革命话语的翻译习惯有关,当时的中文翻译者认为加上“性”字可以抽象地表达出形容词名词化所代表的那种抽象的观念和意识。一词,即党的意识、党的观念。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不断锤炼自身,自身的理论自信也开始逐步建立,逐步形成了一套中国化的“党性”话语体系,特别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需要,“党性”概念被引入到党内教育当中,一直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所发起的“增强党性”运动堪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门针对党性开展主题教育的政治运动,这也恰恰是1944年国共双方论战的缘起。
抗日战争局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为革命队伍补充新鲜的血液,但“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也使得“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使得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页。。更加危险的是,抗日战争局势的瞬息万变也为各种错误思想认识提供了滋生的温床。1939年,毛泽东分析当时党内存在问题时,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与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4)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602页。对此,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凝聚党的组织力、巩固党的权威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党性”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自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提高党员修养、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抓手。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其建党理论并不成熟,也未能对“党性”概念作出具体诠释。到1941年“增强党性”运动发起之前,经过20年的革命锻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大大推进,为这一时期党性观的发展准备了条件。随着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国共合作达成,开始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党内整顿的时机。党中央进驻延安以后,毛泽东就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增强党性问题进行了深刻研究。1941年1月,他在《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特别提出要重视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的问题,其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同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分析了违反党性的各种错误表现、危险性及其主客观原因,提出要加强党性锻炼、纠正违反党性行为。会后,党中央起草并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增强党性”运动正式开始,并成为延安整风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纠正党内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分散主义等“反党性”倾向,中央制定了详细的执行办法来“增强党性”,毛泽东亲自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报告,还主持制定、编印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重要整风文献,号召全党锤炼党性、增强党性,一时之间党内之风焕然一新。
二、论战契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考察
从1941年“增强党性”运动正式开始,为何关于“党性”的论战迟迟到了1944年才爆发,其中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在论战的核心事件和论战的发生时间中有一个时间差,原因就在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严密的信息封锁,使得外界起初对中国共产党这场“增强党性”运动并不知晓,直到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考察,对延安的信息封锁被打破,“增强党性”运动才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之中,引起了国内外颇为留意国共关系及中国共产党问题的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双方对于“党性”的正式论战则是在1944年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后正式拉开序幕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考察正是这场论战的发生契机。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在全党开展“增强党性运动”。但起初国民党方面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自娱自乐”,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和兴趣。特别是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虽暂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减。面对外界众说纷纭的国共关系,驻渝外国记者欲亲赴共产区进行观察报道。1943年11月6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率先向国民党当局正式申请赴延采访,蒋介石了解后批复:“应从缓议。”(5)武燕军等:《抗战时期在渝外国记者活动纪事》,《重庆文史资料》第30辑1979年版,第195页。此后驻渝外国记者多次提出访问延安的要求,国民党均以内政事务为由予以拒绝。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纷纷表态,美国更是直接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次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梁寒操终于宣布,蒋介石已同意外国记者赴延采访,但此后对具体赴延日期借各种理由一再拖延。几经斟酌,4月10日,国民党当局最终选定了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6名外国记者和9名中国记者,另外加上2名领队和4名工作人员,总计21人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正式组建。
从1944年6月9日至7月12日,记者团在延安共采访了34天。这是自1939年以来,新闻界首次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长达5年的全面封锁。随后,中外记者们一系列通讯报道的公开发表,使国内外各方开始对延安有了更多的认识,而1941年的“增强党性”运动也在此期间进入了各方的视野,一场关于“党性”的大论战已经箭在弦上。在各方媒体对延安进行深入考察和报道的过程中,外国左翼记者和国内一些中间派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报道,使得原本牢牢由国民党所掌控的舆论主导权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逐渐摆脱由于长期遭受国民党舆论封锁的被动困境,借此机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与国民党方面就“党性”问题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论战过程中加深了自身对“党性”的理解和认识,推动自身党性观走向成熟。
三、论战内容:“人性·党性·个性”之争
1944年7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考察结束,一场关于“党性”的论争已在酝酿之中。这场论战起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考察,至1945年上半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前后归于平静。各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及其“增强党性”运动的看法莫衷一是,国民党将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消灭个性”“压抑人性”的一个把柄予以猛烈攻击,而中间派也对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运动之成效大为震撼,中共则对其中一些错误观点予以直接反击。正是在与国民党方面一些错误言论的交锋中,在党性与个性、人性三者关系的论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得到升华,并最终走向成熟。在这场关于“人性·党性·个性”的论争中,中国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以及中间派人士围绕中共的“增强党性”运动进行了不同的解读(6)论战中涉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间派(主要是报刊媒体),但中间派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派别,只是在政治观点上并不彻底倒向两党任何一方,在本次论战中他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却是挑起本次论战的一个关键要素。,主要是围绕着党性这一核心概念,以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党性与人性的关系为两大论争焦点,进行了不同视角下的叙事和解读。
(一)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消灭个性”与“彰显个性”
在延安视察的过程中,不少记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增强党性”运动,而对于这场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旨在“增强党性”的主张,大家看法并不一致,党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这场关于“党性”的论争的焦点之一。
率先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是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间派的记者。当时主张“忠实地介绍、自由地批评”的《新民报》记者、中间派代表赵超构在其《共产党员》一文中,对当时延安政治环境中生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共产党员身上有着“百分之九十的党性”和“百分之十的个性”。这种党性使共产党员“同志爱必然超过对于党外人的友谊”,“个人的行动必须服从党的支配”,“个人的认识与思想必须以党策为依归”,使得他们成为“精神上的苦行头陀”(7)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尽管赵超构认为这种“增强党性的意义,即是减弱个性,要求党员抛弃更多的个人自由”,但是由于这种党性,共产党员虽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却成为延安社会“结实的细胞”(8)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85—90页。。同样的另一位中间派记者代表孔昭恺也认为,在“严密训练与监督”之下,党员的党性增强“当属必然”,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个性消失”。但与赵超构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看待这种党性不同,孔昭恺的态度更为肯定,认为“为了贯彻党的政策”,增强党员的党性是必要的。(9)孔昭恺:《西北纪行之八:中共十八集团军与陕甘宁边区(二)》,《大公报》1944年7月13日。中间派记者率先关注到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运动并加以报道,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国共两党舆论战中的重要话题,此后国共双方对“党性”问题的论战正式拉开了帷幕。
面对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一些记者的疑问,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直接的回应。1944年7月,《新华日报》刊登了《人性·党性·个性》一文,很好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党性和个性关系的理解。文章首先从党性的阶级属性出发,对于党性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党性是与阶级性是一致的党性,同时党性又是阶级性集中的东西,党性是集中的阶级性”,而无产阶级从不隐瞒自己的党性,“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利益是整个人类解放的利益,是和人类大多数利益相一致的利益”(10)《人性·党性·个性》,《新华日报》1944年7月22日。。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所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利益、整个人类解放的利益,党性与党的阶级立场相统一,是阶级性的集中反映。文章同时强调:“承认阶级性和党性的存在,并不是否认个性的存在”,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个体个性的多样性,人们的个性必然有所差异,“中国共产党党性是党的一切优美个性的统一体、集合体。作为共产党员的个性,只能以党性为基础”,“在革命的锻炼中,放弃自己与党不合的、反动的旧个性,创造与党性相合的、革命的新个性。”(11)《人性·党性·个性》,《新华日报》1944年7月22日。也就是说,共产党员的个性是与党性相一致的个性,是与革命相合的个性,也只有在党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自己的多才多能,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而如果说中间派记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增强党性”运动尚抱有“理解之同情”的话,国民党方则彻底将其作为攻击中共的箭镞,并冷嘲热讽中共的“增强党性”运动不过是“减弱个性,以至消灭个性”(12)《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大公报》1944年8月5日。。返程不到一个月,8月5日,国民党方面记者在《大公报》撰写的《延安视察的感想》一文中写道,“中共尤其重视党性之增强,一股强烈的党性,贯彻在党政军各个方面,流驻在政府及社会的一切”,“在党言党,这诚然无可批评,而在冀求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国民的立场来看,总觉得其中有些问题”(13)《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大公报》1944年8月5日。。紧接着,该文从政党的内部建设转到寻求建立民主国家的国民的立场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增强党性”运动进行批判:“所谓增强党性,相对就是减弱个性,以至消灭个性,是要党性支配一切,主持一切。民主政治植基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精义,剥茧抽丝,其核心是尊重个人,尊重个性。”(14)《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大公报》1944年8月5日。妄图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增强党性”运动是与民主政治的精义和核心相背离的,是“反民主”的,是不利于民主国家国民之养成的。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批驳了《大公报》上的这篇文章:“有一位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个性、身体和精神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1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可见,毛泽东将中国人民个性的独立与解放建立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正是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解放被这三座大山所压抑的人民个性。至于如何理解党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不能把党性和个性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1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341页。可见,“个性”与“党性”互为表里、辩证统一的,“党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个性”,凸显“个性”恰恰是彰显“党性”的应有之义,增强“党性”正是实现“个性”的必由之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个性是“创造性的个性”而非“破坏性的个性”。毛泽东指出:“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可见,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舆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党性”的认识更加清晰了,同时也争取了舆论上的主动权,获得了更多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同情。
(二)党性与人性:“抽象的人性”与“具体的人性”
党性和个性之外的一个论战焦点是关于党性与人性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记者在《大公报》撰文写道:“一般民主国家也有党,但那种党是在宪政轨道上活动,公开竞争,合法竞争”,“党与党彼此尊重对方,党内也各尊重个人人格,实无总觉得应该更向民主的方向努力。”(18)《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大公报》1944年8月5日。这实际上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为“非法党”,是超脱于宪政体制之外的“非民主的政党”,同时暗示中国共产党对外既不尊重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对内不尊重党员的个人人格,实际上需要“朝着更民主的方向努力”。该文最后更是直接发出“坦率的劝诫”:“民主是尊重人性的,坦率一句话,与其增强党性,何如增强人性。”(19)《社评:延安视察的感想》,《大公报》1944年8月5日。其言外之意不外乎反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增强党性”运动,主张增强“人性”、建立“民主”,劝说中国共产党回到宪政体制和国民党的领导下活动。同时《新潮月刊》也为“增强党性运动”专门撰文,指责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强化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政治运动:“增强党性运动是增强毛泽东集中统治威信的运动”,“党高于一切”和“一切服从党”的口号实际上“消失了个人的‘人性’”,也消解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族性”(20)金风:《关于中共的“增强党性运动”》,《新潮》,1945年第2卷第1期。。此外,中间派记者赵超构也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个体人格和气质品性感到“吃惊”,认为“增强党性”似乎已经开始磨灭“女同志”作为女人的“人性”:“政治生活粉碎了她们爱美的本能,作为女性特征的羞涩娇柔之态,也被工作上的交际来往冲淡了。”他认为最可作为具备这种“党性”的共产党员代表的不是模范党员,而是“女同志们”,她们“都在极力克服自己的女儿态”,侃侃而谈国家大事,而对修饰、服装等均不理会,婚姻、育儿等家庭生活也已“减到非常简单的程度”。因而,女性该有的精致在她们身上并无体现,反而“原始母权中心时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渐在她们身上复活了”(21)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90—91页。。
面对关于党性和人性的种种讨论,甚至是误读与攻击,中国共产党适时作出了回应,通过对人性这个概念的剖析指出了党性与人性之间的共通性,指出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人性观上的局限。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了人性问题的本质,从阶级性出发对国民党方面的攻讦进行了回击:“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2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0页。这种阶级人性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性思想的一种深化,人性只存在于具体中而非抽象之中,一个从未在社会中生活过的人、与世隔绝的人,绝对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只有以具体的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的个人为基础,才能抽象出具体的人性。同样地,植根于封建土壤的所谓“仁者爱人”以及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关于人性自由、平等、博爱的“超阶级”主张,其本质都是脱离具体社会关系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非科学抽象,是难以真正在现实中实际践行的,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毛泽东还旗帜鲜明地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无产阶级的人性”的主张亮了出来:“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2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0页。可以说,毛泽东所肯定的“当然有的”人性即是人之为人的共同本性,但他始终强调要在社会中去考察人性,无产阶级的人性与其他阶级所鼓吹的人性不一样,是要联系人民大众的、非个人主义的人性。在后来的多个场合中,毛泽东仍常常提醒党员们不要“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24)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而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5)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对比之下,国民党的“人性观”显然是虚伪的、脱离群众的、落后的“人性观”。
《人性·党性·个性》一文对这一攻击则进行了更为直接的反击。文章指出,“每一个社会阶级都站在自己的角落来看人性的差别”,因而地主阶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对“人性”的认知亦有所区别。可以说,“人性与阶级性一致,各种人性观的矛盾,反映各种阶级性和阶级观的矛盾”,而“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不同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性观,“无产阶级的人性,就是有历史以来最善良,最优秀的人性,因为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代表历史最前进的革命的阶级”(26)《人性·党性·个性》,《新华日报》1944年7月22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将国民党方面关于人性问题的庸俗理解提升到了哲学的层面来加以反驳,既肯定了人性的共性,又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性是带着阶级性的,鲜明地主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段中国共产党对“人性”“党性”“个性”三者的关系做了具体论证分析。概而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党性”与“人性”“个性”并不是相悖而存在的,而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即实现人性的解放、个性独立,其前提是推翻压迫,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要完成上述任务,就一定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保持党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党员干部完成革命、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条件。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诠释逻辑中,人的个性与人性必须以党性为基础,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和实现。可见,相较之前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对“党性”概念的诠释,这次诠释使得“党性”概念内涵愈加丰富、完整。而且,抛开论战本身不谈,这场论战对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宣传无疑是利大于弊的。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各种资料的披露加上各方的报道,特别是《大公报》《新民报》等颇具名望与影响力的中间派报纸的相关报道,实际上都让关心中共边区政治与民主状况的外界人士对此有了一个较为理性、客观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意义不言而喻。
四、论战之外:透视中国共产党党性观之突出表征
斯金纳认为,思想史的重点“不是关注借以表达某些概念术语的特定‘意义’,而是追问运用概念的意图、考察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与更深层次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联”(27)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1: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4.。通过国共两党对于“增强党性”这一问题的论战,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性观的一些突出表征。
第一,中国共产党党性观的突出表征之一是仍从属于阶级叙事的革命话语,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党性”概念诞生于马克思列宁的建党理论,是“共产主义教育最重要的原则”。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党性”概念,无论是强调党员个人思想观念的改造,还是注重组织、纪律、品性道德的锻造,党性始终是“带着阶级性的”和革命任务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建设、净化革命队伍的实践中产生的,在根本上都是服务于党在革命时期的发展需要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与价值取向的体现。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所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此情况下,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性”观念特别强调组织性与纪律性,这正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淬炼忠诚于革命的党员干部,锻造能肩负时代使命的革命政党。“增强党性”就是要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规范其行为,保持中国共产党革命队伍的纯洁性,进而加强党的建设。因此,“增强党性”是凝聚党的组织力、提升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党性”的内容和形式必然打上革命实践的烙印,从属于阶级叙事的革命话语。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观开始从宏观叙事中关注微观个体,关注到党员作为个体的生命属性和个体属性,强调“党性”与“个性”“人性”的辩证统一。党性是政党的固有属性,个性是指人的特性和性格,人性是指人的品性。人性是个性的基础,人性又是党性的基础,有人性才可能有个性,有人性才可能有党性,但三者都统一于阶级性、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所强调和追求的党性是与个性、人性高度统一的党性。淬炼党性有利于提升人性,涵养个性有益于修养党性,因此增强党性并非消灭个性和人性,相反地,三者相互促进,共同塑造人的品格体系,这才是“增强党性”的题中之义和理想状态。中国共产党将宏观叙事与微观个体的生命书写相联结,指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才是实现个人解放、人格独立的前提,因此“增强党性”首先要坚持党性,党性是第一位的,但坚持党性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性、发挥个性。
总而言之,从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所体现出的理论品格来看,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中的相关概念予以中国语境下的运用与诠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理论中的“党性”概念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的政治和精神属性,表现为政党的阶级属性、宗旨原则和党员的道德、品质、立场、作风、修养,同时强调“人性”“党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党性”概念的诠释与塑造,其内涵表征愈加丰富,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得以从中延展和生长。直到现在,“党性”一词仍是中国共产党日常话语中最广泛使用的词汇之一,并渗透到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当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