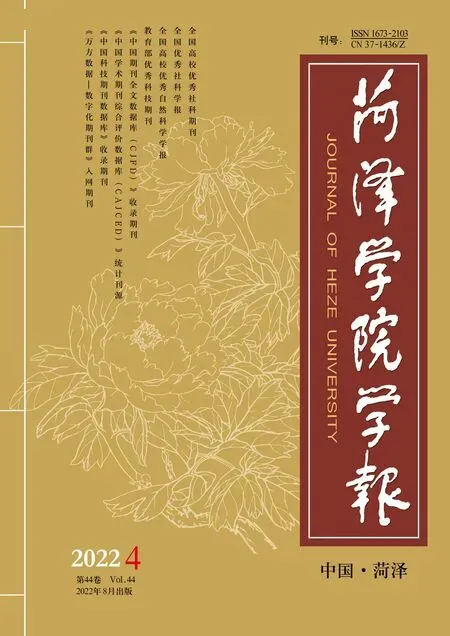拉斯普金《活着,可要记住》中的空间叙事*
鲁亚萍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000)
瓦连京·拉斯普金(Valentin Rasputin,1937-2015)是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被称为俄罗斯“乡村小说”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典型的道德型作家。他的作品多描写俄罗斯农村的日常生活,探讨精神和道德危机下的“众生相”。《活着,可要记住》自出版以来便受到读者和学者们的关注,并获得1977年苏联国家奖金。
《活着,可要记住》延续了拉斯普金的叙述传统,通过刻画安德烈和纳斯焦娜两位主人公的悲剧形象,深入探讨了精神道德的矛盾与冲突。拉斯普金没有浓墨重笔地描述战争的恢弘场面,而是将战争作为叙述背景,在多维空间的交叠转换中,深入思考由战争引发的精神道德问题,包括人性的复杂,个体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的责任,以及社会舆论的愚昧和无情等。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悲剧定义为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强化了时间在叙事学中的重要性。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Josef Frank,1885-1967)在《现代文学的空间形式》中首次提出了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形式问题。到了20世纪50年代,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在文艺领域展开了“空间诗学”理论探索,提出了两个核心空间诗学意象即“内心空间”和“外部空间”,这对后来的社会空间和叙事空间的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后期,批评理论界出现了“空间转向”,传统的注重时间而忽略空间的叙事理论也开始关注叙事空间,如西摩·查特曼(Symour Chatman,1928-)在《故事与话语》中提出了“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的概念,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提出了“地质空间”“时空体空间”“文本空间”的概念。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901-1991)的“空间生产”还是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权力空间”、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的“超空间”、哈维(David Harvey,1935)的“时空压缩”以及索亚(Edward W. Soja,1940-2015)的“第三空间”,空间理论批评都致力于重新发掘空间本身的价值与内涵,更加关注人类在空间维度中的生存和发展。
在《活着,可要记住》中,拉斯普金通过构建地质空间、时空体空间和心理空间,刻画了主人公的多重性格和悲剧命运,强调了个体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的责任,探讨了个人与社会伦理的关系,以及社会舆论的愚昧和无情等。运用空间叙事理论分析《活着,可要记住》为我们研究拉斯普金文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一、地质空间
地质空间指的是“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既包括物也包括存在于空间中的人,“是最高层次的建构,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独立于世界的时间结构和文本的顺序。文本可以通过直接的描述来表现地质空间,亦可以通过叙述的、对话的甚至随笔的方式来展现……对实体颜色、材料和类型等的描述也被视为地质空间构造的一部分”[1]。在地质空间的书写背后隐藏着作者深层次的隐喻含义,文本的空间不是静止的“容器”,而是一种蕴含多维文化信息的指涉系统。拉斯普金在《活着,可要记住》中刻画了四个主要的地质空间:浴室、阿塔曼诺夫卡村、小岛和安加拉河。
首先,通过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一九四五年——战争最后一年年初,正值隆冬,但是这一带还不算太冷。可是,和往年一样,到了洗礼节前后,严寒仍然超过了零下四十度”[2],拉斯普金刻画了浴室这一重要的地质空间形象。正是在这样的寒冬,安德烈从战场逃了回来,他已经受了重伤,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之后,本以为可以光荣退伍,但领导依旧命令他上前线,他害怕再也见不到家人,就偷偷地坐上了回家的列车。
他不能让别人知道他逃了回来,但是,想要挨过这个寒冬也绝非易事。安德烈回到家乡,最先与家人取得联系的场所是自家的浴室。正是在自家的浴室里,他“偷”到了可以帮助自己活下去的工具,如斧子、烟草、滑雪板等。作为地质空间的浴室,是文学、绘画、电影等艺术作品中的常见隐喻形象,如比利时作家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的《浴室》(1985)以及法国画家大卫的《马拉之死》(1793)均深动地刻画了浴室这一具有丰富隐含意义的地质形象。浴室是专供人洗澡的地方,在文学作品中常指洗去人的精神或名誉上“污点”,然而在《活着,可要记住》中,在浴室里安德烈不但没有洗去自己精神和名誉上的污点,反而在逃亡的路上越陷越深。
故事发生之初,作者描写了纳斯焦娜怀疑丈夫是否从战场逃了回来,很快她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在浴室里纳斯焦娜烧好热水终于等来她的丈夫,“是你,安德烈,天哪!你从哪儿来?”[3]作者有意将安德烈与妻子安排在浴室里见面,并准备好了洗澡水,是在暗示希望安德烈在见到村里人之前不仅洗去身上的污垢,也能洗去精神和思想上的“污垢”。作者在理解和同情安德烈逃离战场的同时,希望他能够不忘自己作为一名公民对祖国和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浴室似乎没有起到作用,“懵里懵懂的纳斯焦娜忽然似有所悟:是丈夫吗?刚才和她在一起的,该不会是个会变的怪物吧?……心想:他要真是个会变的妖怪,不是更好吗?”[4]安德烈拒绝回去,他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能硬着头皮走完剩下不多的路。
其次,作者在《活着,可要记住》的第二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另一地质空间:阿塔曼诺夫卡村。“阿塔曼诺夫卡村这个名字是从它以前更加响亮,也更吓人的名字——拉兹鲍伊尼科沃(强盗)得来的”[5]。过去村民以“检查”到勒拿河淘金的过往工人为生,外乡的老人们对这个村子没什么好的印象,认为这个村里的人都干过抢劫。这个村子一直是孤零零的,而如今村里只有三十户人家,有五栋已经人去楼空,年轻人都想着搬到人多热闹的村镇。作者对村子的描写暗示了安德烈日后选择当逃兵是有历史渊源的,最初的村民以剥削他人为生,而安德烈明知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刻,他没有为国家而战,没有尽到公民的义务,而是离开了战场走上逃亡之路。
此外,安德烈一面抱怨着村子,却又思念着村子。在他逃回来后,村子成了他永远回不去的地方。因为村子代表着法律,代表着社会舆论。他知道回来后就会面临着军事制裁和村里人的诟骂。但是村子里有他最爱的人:父亲、母亲和妻子,也有过他最美的回忆。正是因为强烈地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他才逃了回来。他说服自己,这总比战死沙场,永远见不到家乡强。安德烈复杂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他并不是彻底地仇视社会,他本可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重新开启一段人生,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回到家乡,东躲西藏,远远地观望这片故土和家人。
再次,拉斯普金在《活着,可要记住》中描写了横亘在阿塔曼诺夫卡村和安德烈之间的安加拉河这一地质空间。一方面,安加拉河象征着社会的道德底线[6],安德烈越过了这条道德底线,他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通过描写安加拉河的不同形态,推动了故事的情节发展,暗示了主人公的一步步堕落。
起初,冰封的安加拉河是静止的,纳斯焦娜能够比较轻松地越过安加拉河来到小岛和安德烈会面,此时故事的情节刚刚展开,纳斯焦娜知道自己怀孕了,但是阿塔曼诺夫卡村的村民还完全没有对纳斯焦娜起疑心。随着春天的到来,安加拉河开始解封,“冰面变成了病态般的青色;岸边,不仅在岸边,布满了冰窟窿,横穿河面的冰道,已经变黑,两侧开始融化,几只乌鸦在上面走来走去,发出不满的叫声。”[7]解冻后的安加拉河汹涌奔腾,此时故事情节逐渐转向高潮,纳斯焦娜的“肚子起来了……一座小山似的,很明显了。”[8]公公开始起疑心,他发现纳斯焦娜最近一直心不在焉,他当面质疑:“他到底在哪?”[9]纳斯焦娜惊讶之余,只能胡诌一些假话糊弄过去。
到了夏季,安加拉河完全解冻,“显得又浓又暗,岸边涟漪粼粼,中流波澜壮阔,油光闪亮。”[10]此时故事情节真正发展到高潮,村里人都知道纳斯焦娜怀孕了,她被婆婆赶出了家门,村民开始怀疑安德烈是否逃了回来。终于她再也无力承受巨大的压力和屈辱,就在她准备划船去找安德烈时,她一头扎进了水里。“受到拍击的安加拉河,发出一阵溅水的响声,小船摇晃,在夜里微弱的光线中,荡起一圈圈的波纹。但安加拉河水猛力一冲,就把它们挤碎、吞没了。流水如初,没留下任何痕迹。”[11]安加拉河恢复到一如既往的深沉和汹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故事到此结束。读者不禁唏嘘感叹,纳斯焦娜的离去似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不仅没有引起村民们的同情,甚至没有人在意,社会舆论的愚昧和无情通过纳斯焦娜的悲惨结局得到了生动地表现。
最后,拉斯普金在《活着,可要记住》中详细的描述了安德烈逃亡的小岛。这个荒无人烟的岛屿不仅是安德烈最后的避难所,也是他“兽性因子”的归属地[12]。“这里,过去就很少有人来,如今更不会有人钻进来。”[13]这不仅暗示了安德烈的孤独处境,也预示了他身上的兽性因子将控制人性因子。安德烈独自徘徊了很久,反思自己的命运,可终究找不到出路。在岛上他不仅学会了狼嚎,眼睁睁地看着山羊断气,也“力求不放过这个动物临死前的每一个动作”[14],甚至将邻村的一头母牛和小牛赶到岛上,宰杀了它们。这“不仅仅是为了弄点肉吃,还是为了满足这些天牢牢扎在心里,能够支配他的欲望——触动一下别人,让人们知道他的存在”[15]。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共同构成了人的本性,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16]。安德烈在岛上游离于人群之外,不受伦理意识的制约,实则与野兽无异。
“小说叙事中,空间是与小说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相结合为故事铺开提供动力,也为人物塑造起到辅助作用”[17]。拉斯普金在《活着,可要记住》中通过对浴室、阿塔曼诺夫卡村、安加拉河以及小岛等地质空间的描写,说明没有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没有对国家的义务意识和与祖国共命运的觉悟,人就会失去驾驭自己的能力,不仅给他人带来痛苦,自己也最终会沦为野兽般的存在。同时,纳斯焦娜的悲惨结局,也批评了社会舆论愚昧和无情。
二、时空体空间
时空体是巴赫金(Bakhtin Michael,1895-1975)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学理论概念,他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指出,“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之称为‘时空体’。”[18]时间和空间在文学作品中是有机统一的,不仅具有体裁的意义,决定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还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根据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左伦提出了时空体空间,分为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共时层面的时空体空间指的是在任一时间点上不同客体在静止或运动的状态中形成的空间关系;历时层面的时空体空间指的是在特定的文本中客体在不同空间中运动所形成的空间移动轨迹,它受到作者意图、情节阻力、人物性格等因素的影响。
共时层面,安德烈在整个叙事的进程中主要呈现出运动的状态,而以纳斯焦娜为代表的阿塔曼诺夫卡村则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安德烈的运动是其主动做出的选择,战争刚开始他就应征入伍了,战场上他不是最勇敢的,也不是最胆小的。负伤后,军队准许他休几天假,回家和亲人团聚,“但是,安德烈估计错了……他马上出院,但要他立即返回前线。”[19]安德烈的悲剧命运由此拉开了序幕,起初在回前线的途中,他只是想折回家去看一眼就立马离开,可是在回家的车上就已经耗费了三天,继续往前走,两天也不一定能够到达。他知道自己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无法回头。
以纳斯焦娜为代表的阿塔曼诺夫卡村呈现出相对静止的状态。阿塔曼诺夫卡村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前就存在了,不仅是一个封闭的地理区域,“这个村子从初建至今,一直孤零零的,在右岸离它最近的卡尔达村,也在二十俄里以外。”[20]在思想观念上也是保守的,纳斯焦娜在丈夫缺席的情况下居然怀孕了,这不仅招致了公婆的驱逐,也受到了村民们的讥讽和嘲笑,最后投河自尽,连自己的尸体都未被允许葬在村里。村里的人对逃兵一直持零容忍的态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安德烈在逃亡的路上越陷越深,自始至终不愿回去自首。因此,总体来看,阿塔曼诺夫卡村在叙事的进程中呈现出相对静止的状态。
对于呈现安德烈的运动所产生的文本效果主要有两方面:主题上,通过安德烈的视角再现战争的罪恶和残酷,推动情节的发展,同时揭示了安德烈逃亡选择的复杂性,战争打破了安德烈平静的生活,使他的灵魂失去了平衡;结构上,呈现安德烈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与纳斯焦娜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相呼应,促进了小说双层叙事结构的建构。此外,通过呈现阿塔曼诺夫卡村的相对静止状态,一方面表现了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公正和无法僭越,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每个个体都应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存亡联系起来,自觉承担对祖国和社会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历时层面,安德烈的运动从战场开始经历了哑女塔尼亚家,家乡阿塔曼诺夫卡村和小岛,形成一个单向运动轨迹。安德烈在战场,“在侦查员当中,古西科夫被认为是可靠的伙伴。连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们也愿意和他结对,以便相互掩护。”[21]作者在此处埋下伏笔,通过描写安德烈在战场上的表现,与后文安德烈的一步一步走向堕落形成对比。在一次重伤后,他为自己寻找借口,他的仗已经打完了,现在应该让别人去打了,他有理由等待康复回家。但是部队没有成全他的愿望,要求他返回战场。极度失望和恼火的他,选择当了逃兵。他先是在塔尼亚的家躲了一个多月,这位温柔体贴的哑女尽自己所能为安德烈带去温暖和爱心,但是安德烈似乎意识到了这种幸福只是错觉,他不辞而别。回到家乡阿塔曼诺夫卡村后,他寻找机会回去看望自己的亲人,家乡的一切都没有变,他感到心里空荡荡的,经过磨房时,他竟然想要放火烧掉磨房,为的是“叫人们对它留下炙热的记忆。”[22]对于村民来说,安德烈已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了,但他希望村民们还记得他。他在安加拉河对面的小岛上找到了藏身之处,小岛上没有法律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他学会了狼嚎,无情地杀死一对母牛和小牛,过着野兽般的生活。通过创造从塔尼亚的家到小岛这一单向运动轨迹,拉斯普金有意刻画安德烈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充分展示了作家对战争的反思,对战争中每个普通命运的关怀。
《活着,可要记住》中,拉斯普金从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构建了小说的时空体空间。在时空体空间中,安德烈的运动轨迹呈现出单向动态趋势,而以纳斯焦娜为代表的阿塔曼诺夫卡村则呈现出相对静止的状态。小说中时空体空间的交替,清楚地记录了安德烈如何一步步越过法律的底线,走向社会道德深渊的过程,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个人性格的矛盾和复杂。
三、心理空间
心理空间是由美国认知语言学家福克尼(Gilles Fauconnier,1944-2021)在其著作《心理空间》中提出的新概念,他认为,“心理空间是当我们思考和谈话时,为达到局部理解和行动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概念。”[23]也就是说心理空间是人的流动意识的集中地,陆扬在评论索亚的“第三空间”时也指出,“空间既被视为具体的物质形式,可以被标识,被分析,被解释,同时又是精神的建构,是关于空间及其生活意义表征的观念形态。”[24]我们既可以像分析地质空间那样去解构心理空间,也可以将心理空间看作是各种关系的映射和反映。在理解心理空间时不仅仅需要考察文学文本的空间特征,还应考察心理空间构建的方式并揭露其深层意义。
拉斯普金在《活着,可要记住》中建构了以安德烈和纳斯焦娜的回忆和对话为中心的心理空间,故事的情节在现实和回忆之间来回切换,不仅突出了战争的残酷,深化了主人公性格的复杂,同时拓宽了小说的阐释意义。一方面,小说开篇通过安德烈的回忆揭示了安德烈在战场上虽然不曾退缩过,但他也有自私的一面,他只想为自己而活着,而忘却了作为一名公民对祖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刚到战场他就负了伤,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安德烈尽最大的努力适应战争,他不是最勇敢的也不是最胆小的,“总之,他和大家一样,不比别人好,但也不比别人差。”[25]他没有英雄主义的奋勇精神,也没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只是机械的执行命令,并且不想死在战场上。
另一方面,安德烈并非完全丧失了人性,他深爱着妻子,“我刚睡着,一个姑娘从白桦树下向我走来,白桦树离我们很近。我好像不认识她。她穿着一件破连衣裙,又饿又累,光着脚,一点也不像你。但不知为什么,我认定那就是你。”[26]这一梦境凸显了安德烈对妻子的思念和柔情,同时这一梦幻而浪漫的心理空间与战场上刀光剑影的血腥地质空间形成强烈对比,突出了战争的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拉斯普金没有一味地对安德烈进行批判和斥责,而是深入剖析他的心灵历程和思想感情的变化,以表现人性的复杂。
拉斯普金对纳斯焦娜心理空间的构建突出了一个未被战争摧残的心灵的纯洁和美好,与安德烈被战争扭曲的性格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小岛上的过冬房里,纳斯焦娜独自回忆起婚后第二年独自去培训班看望安德烈的情景,走了七十俄里后,纳斯焦娜在又小又暗的木屋里见到了安德烈,两人身上的钱虽然勉强够糊口,但是记忆中的安德烈温柔多情,“她被自己的回忆所激动,双眼满含温情。”[27]纳斯焦娜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的拮据和不易,而倍加珍惜安德烈带给她的温柔和爱。此刻安德烈的回忆则“更凶,更强些,只要它想,总能占上风。”[28]他听不见纳斯焦娜的声音,总是想起有关战争的回忆,一切细节让他恐惧、战栗,似乎现在依旧身处枪林弹雨之中,他痛苦地呻吟。战争给他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痛苦和摧残。
在《活着,可要记住》中,拉斯普金通过构建安德烈和纳斯焦娜的心理空间,引导读者在故事与现实之间搭建认知桥梁,将过去与当下并置,透过人物的回忆与感受,揭示了战争对人身心的摧残,反映了作家对战场上人们渴望生存的心情的理解和同情。
作为一名传统道德的精神捍卫者,拉斯普金巧妙地运用空间的隐喻功能和叙事功能,在《活着,可要记住》中构建了地质空间、时空体空间和心理空间,将主人公置于不同的空间,深入剖析其内心世界,揭示了战争的无情和对人性的摧残,表现了人性的复杂,再现了安德烈跨越道德底线,陷入道德深渊的过程。谴责了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行为,强调了每个人都应坚守法律和社会道德底线。而通过描写无辜者纳斯焦娜的悲惨结局,则批判了社会舆论的愚昧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