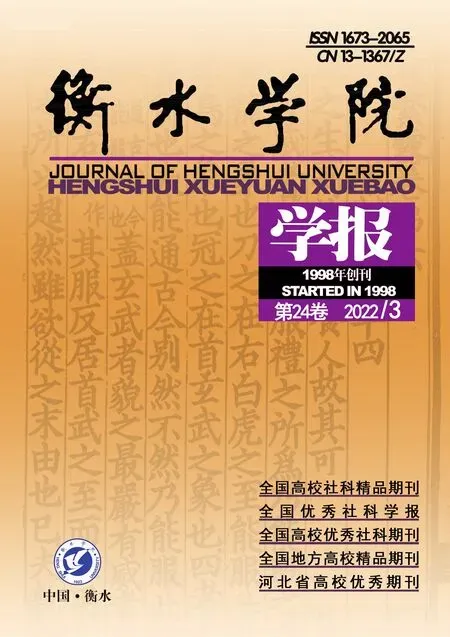人性论视野下荀子的“养心致诚”思想
冯 硕
人性论视野下荀子的“养心致诚”思想
冯 硕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不苟》的“养心致诚”思想和《中庸》论“致曲”文段相似,荀子对后者进行了创造性继承和改造,使之从德性品格转化为知性品格。荀子知性品格的致诚思想,其内核是以心知仁义为逻辑前提,强调在“志意”层面上加以诚笃和力行。《不苟》的养心致诚理论是和其性恶善伪的人性论思想高度一致的,其中“虚壹而静”的工夫作用于“知道”,而《不苟》的养心致诚则作用于“可道”,两者共同构成了荀子道德工夫论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荀子的致诚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是材朴之性,而材朴之性就在《性恶》篇中“善伪”二字中,这是此前所常忽略的。
荀子;养心致诚;知性;情性;材朴之性;志意
荀子《不苟》篇提出“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的理论命题,学者多已注意到《不苟》这段文字和《中庸》下篇论“致曲”极为相似,历代注家中也多引《大学》《中庸》文本和义理来解释,如清人刘台拱:“诚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终也。以成始,则《大学》之‘诚其意’是也。以成终,则《中庸》之‘至诚无息’是也。”[1]46然而,《荀子》和《大学》《中庸》毕竟学理进路不同,尤其是两者的作为道德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相去殊远。所以,有必要联系荀子人性论重知性、重符验的精神品格,尤其是结合荀子人性论的最新研究进展,来揭示荀子养心致诚理论的特殊意义。
一、“致诚”对《中庸》致曲工夫的改造
《不苟》篇论“致诚”,和《中庸》论“致曲”一段相仿,历来学者多用思孟学派的思维范式来解读,但从人性论的角度思考,两者的人性立场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所以在两个文段“形似”的背后,实际潜藏着荀子颇有特色的改造。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不苟》)
“致”,按杨倞,训为“极”[1]46,“致诚”即极其诚,意思是诚的工夫做到极致。“诚”是君子养心的最好途径,诚的工夫做到极致,就不须从事其他的养心之术。诚做到极致,只是守仁,只是行义而已。真诚地执守仁爱,就可以把仁爱表现于外,仁爱表现于外就能神明,神明能够使人迁化。真诚地遵行义,就可以理顺万事,理顺万事就能做到明达通澈,明达通澈就可以改变。变和化交替兴起,德则可以比于天。
《中庸》“诚”的工夫有两个路径:一是圣人的“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一是圣贤以下普通人的“诚”,须“择善而固执之”,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工夫和修养。后者即“致曲”的工夫: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
朱熹注曰:“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其次则必自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也。”[2]33推致善端之一偏,虽是一偏不影响诚体之存有。“形者,积中而发外。著,则又加显矣。明,则又有光辉发越之盛也。动者,诚能动物。变者,物从而变。化,则有不知其所以然者”[2]33。经过形、著、明、动、变、化的环节,达到天下至诚。
理解“致曲”的工夫,关键在三个环节:“曲”的成因是什么?“曲”为什么能推致?如何推致?据朱熹,“曲”乃是本然之性落实到气禀之性上有所偏导致的,“曲,是气禀之偏,如禀得木气多,便温厚慈祥,从仁上去发,便不见了发强刚毅”[3]。而曲所以能够推致,在于曲虽有偏弊,“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2]3。推致的根本在于诚之本体常在无息,故人虽致一曲,可以由此一曲之善,推致其他,使本体复明。推致的方法,与朱子继承二程对“格物致知”的理解相贯通,便如伊川所言:“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4]这一渐进工夫亦朱子为《大学》作补传所说:“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2]7
《不苟》和《中庸》这两个文段同时出现了“诚”“致”“形”“明”“变”“化”六个概念,区别在于,《中庸》多出了“著”“动”“曲”三个概念,而《不苟》则增加了“仁”“义”“理”“神”四个概念。《中庸》“致曲”之“致”是推致之意,由局部推致全体;《不苟》“致诚”之“致”,训为“极”,非立足于本体而推致之意。荀子取消了“著”“动”,反对夸大道德本体的实践功能,而增加了“仁”进路的“神”和“义”进路的“理”;同时将原来出于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变”和“化”,拆分为两个路径,将“变”和“化”两个概念等量齐观,认为两者的交替兴起,可以比之天德。两者都描述了从一般的诚达到至诚的具体过程,区别在于荀子为“诚”增加了仁、义两个具体的道德内容和目标,出现了“诚心守仁”和“诚心行义”两个命题,而《中庸》则是从一曲之诚沿着“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的路径一以贯之地推致扩张,最终达到至诚。
由于《不苟》这段文字和《大学》《中庸》《孟子》所讨论的内容和概念相仿,学者多认为《不苟》受思孟学派影响,并用思孟学派的思维范式和概念做解读,而对荀子如何创造性地改造而使之兼容于荀子自身的体系却少有阐发。荀子改造《中庸》,其特有的人性论立场不可忽视,主要体现为两点:一是和《中庸》不同,荀子不承认诚体作为道德本体,因此其致诚工夫不得不依赖于具体的道德内容——仁义;二是荀子注重人性中知性的充分发挥,使其致诚理论带有鲜明、有特色的知性品格。
在展开这两点论述之前,有必要对荀子人性理论中的知性特色予以界定和说明。以“欲”“求”所代表的情性和以“可”“知”所代表的知性是荀子在《富国》《荣辱》篇提出的人性理论[5]。知性不仅可以认识“物之理”(《解蔽》),而且是人的道德认知、辨别、判断能力,是一种道德理性。牟宗三把荀子归为儒家中的智性系统,承认知具有认知、思辨能力,但不承认知性的道德创造能力。其实,礼义起于知性(知性对情性的思虑、选择),知性不只是先天的能力,其在后天的“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性恶》)之伪,是礼义产生的关键。荀子对知性的发挥是其人性论的特色,这和《中庸》诚为本体、扩充推致相比采取了不同的进路。
首先,《中庸》诚体本来圆满自足,“诚之”的工夫是接近或者复归本体的修养过程;《不苟》中的“诚”本体地位已失,那么离开本体后的工夫论何以可能则是荀子面临的挑战。荀子的做法是确立具体的道德内容,以弥补诚体缺失后的空位,也就是下文所论的仁守和义行。“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确立了“诚”的道德内容和目标,这进一步要求《中庸》由“诚”而“形”“著”“明”“动”“变”“化”的一气呵成的“诚”的修养体系断为两截,分为“仁-形-神-化”和“义-理-明-变”内外两个环节。荀子注重“分”,在这里“化”和“变”两个概念也有了明显的区分:其中“变”所表达的内容是指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化”则指人的内在品格动态的迁化[6]。荀子确立“仁”和“义”的具体道德内容,是配合知性理论而得以成立的;对荀子来说,仁义不是现成地存在于人性之中的,而是知性所知,知而后行的。
其次,荀子致诚理论的知性品格主要体现在“义-理-明-变”这一环节中。《荀子》一书“理”凡见106次,其中“文理”出现16次,乃对礼义而言,如“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礼论》),“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论》),“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性恶》)。《不苟》单独言“理”:“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是指知性对情性的对治而呈现出和、静的状态。《议兵》篇的“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可与《不苟》相互参证。荀子的“理”是礼义背后的规律、道理,是知性对治情性后的合宜的情理。“明”在《荀子》中出现200余次,多和表示知性的概念连用,表示智虑聪明而达到的明通清澈的状态,如“知则明通而类”(《不苟》),“智虑致明”(《荣辱》),“智惠甚明”(《正论》)。“行义”是对外的,涉及环境中的物事,因此知性接物而知类统合,理顺物事的道理,才达到智虑精澈的通明,进而引导万事万物的改变。《不苟》知性品格的致诚思想大体接受了《中庸》“自明诚”的路径,而拒绝了“自诚明”。荀子接受、继承了《中庸》“学而知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后天人为修习路径,但对“生而知之”“不勉而中”则持有怀疑甚至批判态度。《不苟》显然深受《中庸》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思孟学派的依附或者回归,荀子对《中庸》的改造就在于他对知性的强调,同时也就是对《中庸》诚本体思想的拒斥。
二、《不苟》致诚思想知性品格的内核
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以性善论为背景;《中庸》的“诚”圆满自足,也是实有其德的;而荀子的致诚思想是以性恶善伪说为背景的。如果简单地接受荀子的“致诚”思想和思孟学派无甚差异,甚至主张《不苟》完全受思孟学派影响,显然是不合理的。养心致诚理论是否和荀子性恶论兼容是备受学界注意的问题。然而,笔者在上文已说明,《不苟》的养心致诚理论是以荀子的知性人性论为基础的,而知性人性论和传统的性恶说,以及如何与养心、致诚理论兼容是接下来要予以阐释的;养心致诚理论与性恶论的兼容问题,也因此转化为知性人性论和性恶论的兼容问题,笔者也将为此试作解答。
《不苟》篇论以诚养心,并非诚体本身向外的扩充和推致,而是以仁义为其道德内容和目标,既然如此,仁义何以能成为道德内容和目标的根据就成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在思孟学派那里,仁义不在外,而是诚体本身具有;在荀子,仁义并非诚体本有,那么诚心守仁、行义的前提便只能诉诸智性的道德认识功能——心知(知性)。《性恶》: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可能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
《性恶》篇上半部分以情、欲言性,而后半部分却揭示出荀子并不单纯以情性为性,而在另一个侧面强调人的成德作生的先天根据——“仁义法正之质”“仁义法正之具”。“仁义法正”的可知性和可能性,所诉诸的人性根据并不是情欲,而是《荣辱》篇所说的“材性知能”。仁义落实在心知上,仁义的可知、可能,其人性根据在知性。
心知仁义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心生而有知”(《解蔽》),人天生具有道德认知的潜能;另一方面是仁义有“可知可能之理”,可以为人所知。具体言之:一方面,仁义在外而不在内,仁义是外在的,之所以能够为人所接受,是因为知性使外在道德内化,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心“知道”“可道”(《解蔽》)的能力。仁义源自心知,而非心中现成地本有,所以荀子极为强调环境教育和后天学习的重要。另一方面,仁义又并非全然在外,而是有着先天的人性依据。因为如果仁义只是外在,就无法解释最初(第一个)外在的仁义从何而来的问题。对荀子来说,最初的仁义、礼义如何产生一直是一个核心疑难。如果道德知识都是外在的,人只能通过学习把外在道德内化,那么最初的外在道德知识何以产生,初看起来似乎无法得到解释。《性恶》篇对礼义如何产生做出了回答:“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礼义产生于圣人的“思虑”和“伪”的积累。“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可见,礼义并不仅仅是知性的创造,而有赖于先天的情。没有先天的情,则心“择”的功能无法体现,所以才说“无性则伪之无所加”(《礼论》)。所以,礼义虽然是伪起,但还是以性为根基的。凡伪,皆是性之伪,不是空的伪。虽然《性恶》主要讲性伪分,而性伪合已在其中。“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礼论》)。荀子以阴阳比喻性伪,两者并非绝对对抗,而有彼此促进、依赖的一面。所以,道德知识对后人来说的确是外在的、现成的,是先王创造的,但是人并非只能被动地接受。道德是圣人因为“积思虑,习伪故”,通过人人皆有的“材性知能”(《荣辱》),经过后天努力“壹于道”(《解蔽》)而创造的;后人、普通人也能专心一志地使用自己的“知能材性”,“足以知其有余,可以为君子之所为”(《荣辱》)。圣人的所思、所虑、所伪,是后天的,是众人所不具备的;但圣人之能思、能虑、能伪的性则和常人无异。因此,仁义对普通人来说,首先是外在的,是先王创制出来的、现成的、美俗良俗之中本来就有的,需要众人积极学习、效法;然而人人皆有知外在仁义之“材性知能”,便保留了由内而外通达仁义的可能性,使外在的仁义有了生根的可能。
质言之,心知仁义有两个路径:一是普通人以外在的仁义为法,积极学习,加以内化,从而守仁、行义;二是人人皆有“仁义法正之质”和“仁义法正之具”,可以积极地运用,从而由内而外地接纳、认同甚至创造仁义。荀子这一知性通达仁义的路径异于《中庸》,“致诚”的内涵也因此与之不同:《中庸》的“致诚”是主体依据诚体从一隅、一端到全体的推致,而对于荀子,因为“诚体”不在,“诚”的工夫不是以诚体前提,而是以心知仁义为逻辑前提的知性活动。换言之,“致诚”是心知仁义,而后养心以诚,这也便是荀子致诚理论知性品格的内核。
《不苟》的“致诚”是“诚”于守仁、行义。唐端正先生指出,荀子“所谓诚,不指性而言,但也不指仁义善道本身,而是指健行不息地守仁守义。故‘诚’不着重在致知上,而着重在笃行上”[7]。王楷进一步指出,“荀子所以养心以诚者,其根本的意义就在于意志的净化和定向”[8]。他们认识到,《不苟》的“致诚”和“养心”,是道德意志层面的,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心理基础。“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王霸》)。其中“诚义乎志意”直接表述出这一层意思,可为明证。先秦儒家各派均可以在道德意志的层面谈“诚”,如《大学》,然而以心知仁义为前提,则只有荀子。
“诚”是达致仁义的工具,是“实践仁义的手段”[9]。《中庸》从一曲之诚推致全体之诚,诚本身实有其德,无须外助;《不苟》的致诚工夫以心知仁义为前提,而作用于志意,“诚”在《不苟》这里变得工具化了,“诚”的工夫也由德性品格转变为知性品格,这是荀子对《中庸》的一大改造。
三、“致诚”作为“可道”工夫
进一步,“致诚”作用于“志意”体现出工夫论层面的何种特色,“志意”和荀子性论中的知性、情性的关系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澄清。荀子极重“志意”,凡见20次,散见于《修身》《儒效》《王霸》《礼论》《赋》诸篇;抑或单独称“志”或“意”,“志”见96次,“意”见42次,亦遍见于各个篇章。今试举数例分析:
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修身》)
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荣辱》)
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儒效》)
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礼论》)
荀子多次把“志意”和“智虑”“血气”并列(与“血气”并列,凡3见,分别在《修身》《君道》和《赋》;与“智虑”并列,凡5见,分别在《修身》《荣辱》《天论》《正论》,其中《正论》2见),一方面足见其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则透视出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血气”对应荀子在《性恶》篇极为强调并加以详细分析和展开的情性(以情欲言性);“智虑”则对应着心知能力,包括认知、判断、思虑、权衡等功能,在《正名》篇中体现为“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的心虑能力,它构成“起伪”的关键环节;“志意”则是人的自由意志。荀子既排斥“纵情性”(《非十二子》),也反对“忍情性”(《非十二子》),而主张“志意”须“修”。荀子三次谈到“志意修”,分别在《修身》《正论》《礼论》。从“修”的效果看,大儒之志能“安公”,众人之志“不免于曲私”;这与《修身》篇“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之旨相一致。从形式看,“志意”至少含有三层意思:1)意志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2)意志的真诚;3)意志(面临诱惑或阻碍)的顽强。意志的真诚系于内在的真实无妄,而意志的顽强则为外在力量所考验,反映的是意志的韧性和强度。“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指的是意志的坚定不移,是意志的顽强;而在《不苟》和致诚联系起来的“志意”,和《王霸》“诚义乎志意”均反映的是意志的真诚——人产生道德认知和判断后,加以肯认、专心一志进而笃行的功能。
“志意”相对独立于“智虑”,“智虑”的“所知”未必便是“志意”的“所择”,用荀子的话说,人固然有“知道”的能力,但是现实中人可能“可道”也可能“可非道”(《解蔽》),甚至可能会“纵情性”。《解蔽》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其中,“知道”是智虑的结果,“可道”“守道”“禁非道”则是志意的工夫。《正名》:“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在荀子看来,心知道是先决前提,从“知道”到“可道”,需要“致诚”工夫才能实现顺利过渡。有学者认为《不苟》论“诚”和荀子的整体思想不一致,荀子的养心论应该是《解蔽》篇的“虚”“壹”“静”的工夫,而非“养心莫善于诚”[10]。实际上,荀子的“致诚”乃作用于志意,以心知为前提。“虚壹而静”是“知道”的工夫、智虑心的工夫,“养心莫善于诚”“诚心守仁”“诚心行义”则是“可道”的工夫、志意心的工夫。“可道”而后笃行才是《不苟》致诚思想发挥功能之处。
荀子在《正名》中给出了性的两重界定:“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第二义的性乃是接物所引起的各种生理和心理欲望[11],可概括为由物接引所致的情、欲之性。显然,知性不属于第二义的性,而只能属于第一义的性。那么,“志意”又何所属呢?就志意的对象、内容及其在经验世界的活动而言,属于伪;就志意作为先天的潜能的话,则无疑属于第一义的性。《解蔽》:“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是心知的一部分,既然心知被排除出第二义的性,那么志意也没有理据属于第二义的性。据此,“志意”在人性中有先天根据,但主体在后天的经验世界对“志意”的运用则属于伪的范畴。“致诚”“诚心守仁”“诚心行义”,因此都是伪的工夫。把“诚”置于伪的范畴,暗含着对《中庸》“诚者,天之道也”的批评。“天德”因此是“伪”的极致,是“极其诚”的结果,是工夫论现象,而并非是天生而有、赋予人的德,也不是在形而上意义上说的,反映出荀子重符验的品格。如果说荀子借用了《中庸》“致曲”文段中的部分概念是属实的,但是如果认为荀子在思想上也“模仿”了子思,仿造了一个类似子思的致诚思想,则不能成立。荀子对《中庸》的改造和创造,不仅不是“模仿”,反而有批评的意思,这是值得注意的。
最后,“志意”与荀子工夫论中的“精”“壹”“积”思想相接通,荀子在《解蔽》中说:“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农精于田”“贾精于市”“工精于器”,而君子精壹于道,荀子把君子“壹于道”称之为“正志”。《不苟》篇把“诚”的内容和目标集中于仁、义上,实际上便是“壹”于仁义之道,它和《解蔽》“君子壹于道”的精神是一致的。“精”和“壹”都是真诚、专一后而精通的意思,均属于伪,是性伪合的结果。荀子的“精”“壹”又蕴含着“积”的思想。《儒效》:“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精”“壹”的前提是“积”;通过不断地积累,才能达到“精”“壹”。总之,《不苟》致诚思想和“精”“壹”之道的精神和主旨是高度一致的,并非荀子思想中的不和谐之处。不难发现,荀子的致诚思想反映的人后天积极、专一的努力,是和“积伪”概念相适配的,其理论特色完全区别于子思。
《不苟》致诚思想的立论基础在于“心知”和“志意”。“虚壹而静”工夫在“知”,“养心莫善于诚”工夫在“可”,两者一起构成了荀子道德工夫论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由此可见,荀子的致诚思想确有精思和特色,是先秦以智性系统讨论“诚”思想不可忽视的文本。
四、致诚的人性论根据:材朴之性
最后,笔者将对性恶论和知性、志意的关系作出说明,探讨性恶论和养心致诚论的兼容性问题。
近年来荀子人性论已成热点,以往对荀子人性论所做标签化、简单化的处理得到了明显改观。和传统观点不同,现今学者多已认识到性恶说需要严格加以限定才能成立——《性恶》篇所讨论的性是就情、欲而言的,且情欲本身也并非恶,所谓性恶是从情欲倾向于恶所显出恶端和情欲泛滥无节制所导致的恶果两个方面才得以成立的。徐复观认为荀子是以欲为性[12],梁涛认为严格地说只有情(欲)才属于性,根据《性恶》对恶的定义:“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偏险”属于恶端,而“悖乱”则属于恶果[13];日本学者岛一则认为《性恶》所言性是被“情”所附加限定的[14]88。“心知”和“志意”,属于第一义的性,却非但不是恶端,而且还蕴藏着创造道德和礼义的可能。而《性恶》篇所讨论的“性”乃是情性,也就是以情欲言性: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
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同上)
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同上)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同上)
“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是以身体欲望而言;“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就人的官能在情欲的反应而言。《性恶》开篇所“顺是”的性,“好利”“嫉恶”“好声色”三例均指情性而言,而通观《性恶》全文不见其以官能、知性、志意为恶的观点和论证,可见性恶说的性乃是特指情性的,很可能对应于《正名》篇对第二义的性的界定。在《正名》篇,第二义的性所论“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确如冯耀明所指出,是接物、可以为外物所诱的性;作为性,此时还未经人为的放纵和顺应,故处于自然状态。相反,《性恶》篇不见以心知、官能、志意为恶的证据,反而似乎刻意遮蔽心知、志意本来的功能,来观察情性在缺乏心知和礼义约束后无节制的后果。《性恶》开篇即言“顺是”二字,很多学者早注意到“顺是”句是性恶说得以成立的关键,却未能从“志意”的角度阐释“顺是”二字。其实,“顺是”是“心知”的遮蔽,也是“志意”的故意。只有当“心知”被遮蔽,“志意”盲从情性,才能看到情性无节制导致“犯分乱理”的恶果,并以此来提供反对孟子性善的理据。下文言情性“好利而欲得”“不辞让”“劳而欲休”,都把“心知”“志意”遮蔽,都是此义。
官能是人的先天本能,不杂人欲,如目能看,耳能听,足能行,可知官能显然非恶;“志意”可以志在“曲私”,也可能安于“公”,其本身不恶;心知“可道”“中理”(《正名》)则成为人为善的必要条件,心蕴藏着成善的可能。《性恶》篇所论性恶,是限定于情欲之性的泛滥这个意义上的。韩德民认为:“荀学所谓‘性’,就狭义言之,就是自然性的欲望,就广义言之,亦包括禀赋自天的认识判断能力。”[15]《性恶》所言性恶说,是狭义的性,而非《正名》所界定的第一义的性。日本学者岛一进一步指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有两重属性。其一称之为‘情性’,生而有之,‘不事自然’,肆意放任之则导致社会混乱。其二则被称为‘知虑材性’‘知能材性’‘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是朝向既定目的的、人的主体性的、能够认识实践的能力。换言之,荀子的本性论本质上具有二重结构。而后者的‘性’乃是人认识、体认社会规范以及致力于学问的前提条件。”[14]90此说极有洞见!材性是荀子人性论的重要构成,以往以性恶理解荀子过于狭隘。而心知、志意与性恶说的相互协调,也须借助材朴之性解释: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礼论》)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荣辱》)
《礼论》的“本始材朴”一句是性朴论立论处,然而我们更关注“材”字而非“朴”字。“朴”照性朴论者的理解属于价值判断,即性在价值上不足以言善恶,而是朴的;可联系上下文,这里荀子要强调的是性伪关系,性是伪的资材,为伪提供了可能性;伪是资材基础上的人为加工或改造。“无性则伪之无所加”,强调的是对于后天的伪来说,性是必要的先天材具,即“材性知能”。《劝学》:“彼人之才性之相县也,岂若跛鳖之与六骥足哉!”这里的“才性”也即“材性”,这里荀子不是在说性善恶与否,也并不意在提出性朴说,对性作出价值判断,而是重新申明材性,主张伪必然借助先天材性而后成其为伪,材性必借后天的伪才能自美。回到《性恶》篇所说的“性质美”,非指情性,而是指材性而言。
《不苟》篇的主旨是行为要符合“当”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义之中”,而一切符合礼义的人的活动,无不依靠材朴之性才能实现;在“守仁”和“行义”的实践活动中,也不得不依靠材朴之性。人的一切在礼义之中的活动,所必须借助的性,都属于材朴之性;而人的一切超出礼义、乱礼义的活动,所借助的性,往往是情性的放纵。心能知、志意能求是先天的材朴之性;心知、志意在后天的有所知、有所求,则属于伪。《荣辱》的“材性知能”,即《礼论》的材朴之性;亦即涵摄在“善伪”二字中。建立在“心知”和“志意”基础上的养心致诚理论,粗看和性恶说不一致,其实乃“善伪”之必要条件。性恶说的关键在“善伪”而不在“性恶”,其完整的表述是性恶善伪说。
荀子的养心致诚思想,其人性论上的根据是作为材朴之性的心知和志意,《性恶》篇上半部分以情欲言性,两者都是荀子人性理论的核心。心“知道”、志意“可道”,则可以对治人的情性之趋恶、泛滥倾向。材朴之性,使“知道”“可道”“起礼义,制法度”(《性恶》)成为可能;而“道”“礼义”“法度”之治的对象是情性。处在张力关系的材性和情性均为荀子人性论的重要组成,在这个意义上,《不苟》的致诚思想和性恶说无疑是兼容的。
[1]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1571-1572.
[4]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88.
[5] 梁涛.荀子人性论的历时性发展——论《富国》《荣辱》的情性知性说[J].哲学研究,2016(11):46-53,128,129.
[6] 佐藤将之.掌握变化的道德——《荀子》“诚”概念的结构[J].汉学研究,2009,27(4):35-60.
[7] 唐端正.先秦诸子论丛·续篇[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175.
[8] 王楷.荀子诚论发微[J].中国哲学史,2009(4):64-71.
[9] 梁涛.荀子与《中庸》[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73-78,111.
[10] 蔡仁厚.孔孟荀哲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486-489.
[11] 冯耀明.荀子人性论新诠:附《荣辱》篇23字衍之纠谬[J].“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2005(14):169-230.
[12]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5.
[13] 梁涛.荀子人性论的中期发展——论《礼论》《正名》《性恶》的性-伪说[J].学术月刊,2017(4):28-41.
[14] 岛一.荀子的本性论——关于其二重结构[J].国学学刊,2011(3):86-93.
[15] 韩德民.荀子与儒家社会理想[M].济南:齐鲁书社,2001:134.
Xunzi’s Thought of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ature Theory
FENG Shuo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 thought of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in the bookis similar to the theme of “Zhi Qu”, a chapter in the book. Xunzi creatively inherited and transformed the latter from moral character to intellectual integrity. The core of Xunzi’s cultivating sincerity thought of intellectual integrity is based on the logical premise of knowing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emphasizing sincerity and practice at the level of “will”. The theory of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in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its human nature theory of wickedness, kindness and hypocrisy, in which “emptiness and tranquility” notion acts on “understanding the Taoism”, while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theory inacts on “accepting the Taoism”, and they constitute the two successive links of Xunzi’s theory of moral methodology. The human nature of Xunzi’s thought of sincerity is based on the nature of simplicity, and it is embodied in “kindness and hypocrisy” in the chapter entitled “Evil of Human Nature”, which used to be overlooked by researchers.
Xunzi; “cultivating mind and sincerity”; the nature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sentiment ; the nature of simplicity; will
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09
冯 硕(1989-),男,山东枣庄人,在读硕士。
B222.6
A
1673-2065(2022)03-0072-07
2021-09-16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