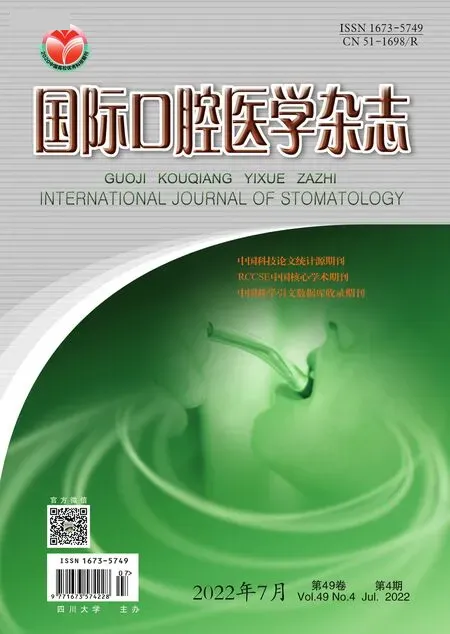变异链球菌与白色念珠菌相互作用在龋病发生中的研究进展
李姗姗 杨芳
1.青岛大学口腔医学院 青岛 266003;2.青岛市市立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青岛 266071
龋病是一种常见的生物膜性疾病[1],如不及时治疗,会影响患者的咀嚼功能、社会心理环境及生活质量。变异链球菌(Streptococcus mutans,S.mutans)具有极强的产酸性及胞外合成葡聚糖能力,被认定为致龋菌[2]。有大量口腔微生物参与龋发生[3-4],这些微生物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5]。Raja等[6]发现:96%的患龋儿童口腔中可以检测出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C.albicans),而在健康个体中只有24%,因此龋齿的发生可能与C.albicans有关。研究[7]发现S.mutans和C.albicans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本文就这两种细菌致龋机制、相互关系及抗混合生物膜治疗作一综述。
1 S.mutans和C.albicans的致龋作用
S.mutans是革兰阳性兼性厌氧菌,是幼儿龋病(early childhood caries,ECC)的关键病原体,具有产酸、耐酸以及形成生物膜等多种毒力特征,可有效催化葡萄糖基转移酶(glucosyltransferase,GTF)将膳食蔗糖转化为胞外葡聚糖(exopolysaccharides,EPS),成为口腔中胞外多糖主要生产者。当牙齿表面暴露在蔗糖中时,S.mutans可通过多种方式产生致龋作用。1)S.mutans浮游细胞产生GTF,利用蔗糖合成细胞外基质,将其包裹于其中形成物理化学性能稳定的生物膜[2],生物膜结构促进了S.mutans与其他微生物(如牙龈卟啉单胞菌、链球菌、梭杆菌)在牙齿表面的定植,进一步形成生物膜的支架核心或基质,同时为自身代谢提供碳源,有利于繁殖以及混合生物膜的形成[7-8]。2)S.mutans代谢糖类产酸,使环境酸度降低,并降低唾液的缓冲能力,成为低pH环境下的优势菌[9-10]。此外,EPS基质作为一种限制扩散的屏障,可加速生物膜牙齿界面酸性微环境的形成,这种通过调节糖代谢途径以及在酸性环境中生存的能力是S.mutans致病的关键机制。3)与其他微生物共聚时,S.mutans依靠分泌化学信号分子来监测菌群密度并调控生理功能[11],在基因和信号分子的协同作用下增殖、扩散到其他部位。
C.albicans是人类阴道、呼吸道、口腔等器官黏膜的常驻菌之一,是口腔内最主要的念珠菌种[12-13]。C.albicans是革兰阳性兼性厌氧菌,可在酵母、假菌丝和菌丝3种细胞形态相互转换[14]。酵母与菌丝生长形态的转换与其致病性密切相关。菌丝有助于C.albicans高效摄取营养,而其优异的黏附能力也是C.albicans定植和致病[15]的关键因素之一。C.albicans能分泌甘露糖蛋白,与黏膜表面的糖蛋白受体结合,使酵母相细胞黏附于黏膜表面。当人体免疫能力下降时,C.albicans成为机会性病原体,由酵母相变为菌丝相,大量摄取营养并繁殖、黏附于机体黏膜表面,引起相应疾病[16]。C.albicans与龋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儿童中尤为明显[17-18]。Raja等[6]的研究显示:儿童龋病的发生与C.albicans携带率呈正相关。Xiao等[19]发现:患有严重ECC的儿童很可能是由他们的母亲传染的,因为这些儿童的母亲具有非常高的C.albicans检出率。Klinke等[17]在一项体外实验中证明:C.albicans能以较高的速率引起大鼠晚期龋。Falsetta等[20]发现:C.albicans可通过促进龋病生物膜的形成引起猛性龋的发生。
2 S.mutans与C.albicans协同致龋作用
在ECC中,S.mutans和C.albicans常共存于菌斑生物膜中[21-22]。Sztajer等[18]发现:S.mutans和C.albicans可形成混合生物膜,且其生物膜量、活菌量明显高于单菌种。Klinke等[17]在一项于啮齿类动物模型上进行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单一感染C.albicans或S.mutans的大鼠,同时感染C.albicans与S.mutans大鼠的龋病发病速度明显增加。C.albicans与S.mutans的共生作用以生物膜为媒介,其作用机制与以下因素有关。
2.1 GTF
S.mutans在代谢过程中可产生细胞外GTF,而GTF衍生的EPS是跨界生物膜发育的关键中介,它们与C.albicans的共存可诱导S.mutans毒力基因的表达。Falsetta等[20]在一项体外和体内共同培养研究中发现:C.albicans可显著提高S.mutans的EPS产量,并诱导gtfB、fabM等毒力基因的表达,使生物膜量显著增加。Hwang等[23]使用原子力显微镜探索GtfB与C.albicans相互黏附作用的强度和结合力,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作用力。C.albicans分泌产生甘露糖集聚于自身细胞外壁为S.mutans分泌产生的外生酶GtfB提供结合位点,形成稳定的化学键,调节跨界生物膜的发育。这种共生作用,可促使EPS大量产生,形成致密混合生物膜,同时也为这两种微生物提供大量碳源,加速微生物繁殖,使混合生物膜中生物量明显多于单菌种生物量。由此推测,S.mutans与C.albicans的共存可能加速龋病的进展或引起复发。
2.2 蔗糖
蔗糖的存在有助于C.albicans与S.mutans混合生物膜的形成。缺乏蔗糖时,C.albicans与S.mutans几乎没有物理黏附[24];而蔗糖存在时,两者之间的黏附作用显著增强[16,25]。Marsh等[24]发现:细菌可以代谢蔗糖产酸,有利于致龋性微生物的生长以及EPS的产生。蔗糖是混合生物膜形成的重要营养物质,当蔗糖浓度增加时,pH值显著减小,有利于致龋菌产生生物膜并增强脱矿作用。与相等浓度的葡萄糖和果糖相比,蔗糖显著加剧了釉质矿物质的流失[26-27]。
2.3 SigX因子
SigX是S.mutans群体感应的主要调控因子。Sztajer等[18]将S.mutans与C.albicans共同培养以探索二者间的跨界信号交流,结果发现:SigX在混合生物膜中有较强的诱导作用,而在单菌种生物膜中较弱或无作用。此外,双菌种生物膜培养基能够激活SigX,而且这两种微生物均能从混合生物膜的生长中获益。该结果提示:未来龋病的治疗可从考虑阻断二者之间的SigX信号交流入手。
2.4 非生物膜因素
非生物膜因素也参与S.mutans和C.albicans之间的相互作用。麦角甾醇是C.albicans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可发挥毒力功能。王峥等[25]发现:将C.albicans的麦角甾醇合成通路突变株与S.mutans共培养,S.mutans生长能力及毒力显著增强;继而使用抗真菌药物氟康唑抑制麦角甾醇通路后,可见其促进生长作用受阻。该研究提示:氟康唑有成为龋病防治新型药物的潜能,可以进一步研究。
3 S.mutans与C.albicans的相互抑制作用
C.albicans分泌的群体感应分子法尼醇[28]可影响细胞黏附、生物膜构建及生物膜细胞的离散。Fernandes等[29]发现:该信号分子对S.mutans的生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该研究采用定量方法评价法尼醇对2种菌形成的单一和混合物种生物膜的影响,观察到2类生物膜的总生物量和代谢活性显著降低。但Kim等[21]学者发现:法尼醇可双向影响S.mutans生长,低水平的法尼醇能促进S.mutans菌落扩大,而高浓度时会限制其生长。目前法尼醇在2种菌的跨界信号交流中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议。Willems等[22]发现:C.albicans可通过抑制S.mutans产酸以延缓牙体硬组织的脱矿。Barbosa等[30]发现:S.mutans的培养滤液可明显抑制C.albicans的数量及菌丝态的形成,提示S.mutans可以分泌某些物质来调控C.albicans的形态并降低其致龋性。
4 具有抗S.mutans和C.albicans生物膜活性的化合物
近年来,许多学者报道了与抑制口腔S.mutans和C.albicans生长有关的化合物,这些抑菌方法在不同的作用模式下展现出良好的抑制效果。
4.1 抑制生物膜形成
一些化合物和技术具有抑制生物膜的功效。在抗生物膜的研究中,氯己定(一种广泛应用于控制菌斑和念珠菌感染的活性剂)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31]。低浓度的氯己定与顺式-2-癸烯酸联合使用后,能够有效分散S.mutans与C.albicans形成的单菌种及双菌种生物膜[32];氯己定葡萄糖酸钠联合酪醇在抗二者单一和混合生物膜方面也表现出良好的效果[33]。除了抗菌剂外,一些化合物,如一种可释放氟的义齿树脂对S.mutans与C.albicans也显示出很好的生物活性反应。以甲基丙烯酸甲酯、2-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为单体的共聚物通过限制生物膜的生长显示出控制疾病的潜力[34]。除了化合物外,光动力疗法作为新型抗菌疗法可以利用光和光敏剂产生的光动力效应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在抗生物膜中也有积极的作用。Fumes等[35]发现:光动力疗法对C.albicans生物膜无明显影响,但对S.mutans微生物膜具有抑制作用。Trigo-Gutierrez等[36]以C.albicans、光滑念珠菌和S.mutans多物种生物膜为研究对象,评价光敏剂氯铝酞菁在阳离子纳米乳液中的应用效果,发现该技术可致生物膜光失活,降低菌落计数。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光动力抗菌技术在S.mutans和C.albicans生物膜感染管理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还有一些抑制剂通过增强抗菌剂的活性实现对生物膜的抑制。细胞外多糖抑制剂聚维酮碘与抗真菌药物氟康唑联合使用可有效抑制α-葡聚糖的合成,从而抑制C.albicans与S.mutans混合生物膜的形成,提示碘衍生物的加入可提高氟康唑的疗效[37]。此外,噻唑烷二酮-8能够破坏各种微生物的生物膜形成,包括S.mutans与C.albicans两者的混合生物膜[38]。
4.2 抑制细菌/真菌病原体活性
一些药物可通过抑制S.mutans与C.albicans活性从而控制生物膜形成。Elshinawy等[39]发现:壳聚糖、纳米银和臭氧化橄榄油对S.mutans和C.albicans具有抗菌活性,这3种药物联合应用具有抑制混合生物膜的潜力,且安全性良好。另外,几种合成化合物,如氯化十六烷基吡啶、溴化十六烷基三甲基铵和植物松油素-4-醇也显示出对S.mutans与C.albicans显著的抑菌活性。
另有一些化合物同时具有抗菌和抗生物膜的特点,如六氮化硼纳米颗粒对S.mutans同时具有抗菌和抗生物膜的活性[40]。
5 小结
尽管医学界和科学界作出了巨大努力,龋病仍是严重的口腔问题之一。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龋病发病机制中的重要因素。S.mutans和C.albicans相互作用的致龋机制及混合生物膜治疗已得到广泛研究,治疗方法如光动力疗法,以及具有抗生物膜活性的化合物等揭示了不同的抗菌潜能和应用前景。未来仍需更多深入的体内和临床研究,以便有针对性地预防并治疗龋病及其他口腔感染性疾病。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