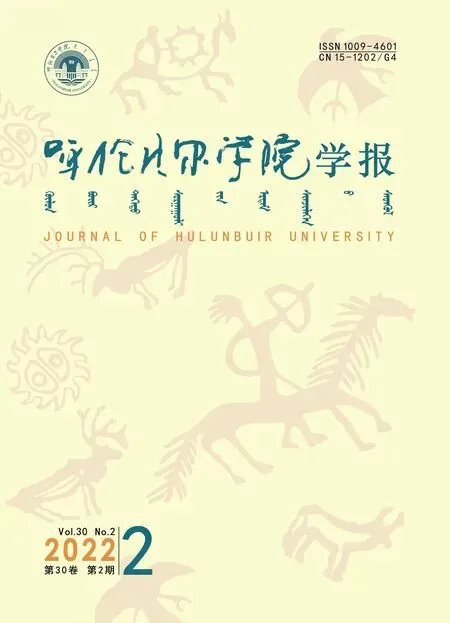从《北巡私记》和《鸿猷录》看“元室北迁”的历史书写
王 平
(呼伦贝尔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8)
妥欢帖木儿即为元顺帝。顺帝在元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久,统治大元最后30多年,几乎占了整个王朝的三分之一。他是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君主,执政前半段亦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在后期统治中,顺帝面对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更化”政策的失败,加之灾害频仍、经济凋敝、起义不断、治国无方,继而个人转向沉沦、颓废,成为亡国之君。能否客观公允地看待顺帝这一历史人物,利用现有史料还原其真实形象尤为重要。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军在明军势如破竹的兵锋下节节败退,顺帝被迫撤离大都,这是蒙古族失去对中原的统治,退居朔漠的标志性事件,但官修《元史》《明太祖实录》在修撰之中因尊明正朔统治的需要,对该史事记载存在失实、简略、零散的弊病,使我们很难管窥元室北迁的全貌。现利用较为完整记载该史事的元入明人刘佶的《北巡私记》和嘉靖时期高岱撰写的《鸿猷录·克取元都》对其进行梳理,以再现“元室北迁”。
一、关于《北巡私记》与《鸿猷录》
《北巡私记》一卷,明刘佶撰。刘佶,江西临川人。元末为枢密院属官。刘佶在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随元顺帝退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次年任监察御史。明洪武三年(1370年)奉命与翰林院承旨观音奴由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东南)赴陕西,奉命诏扩廓帖木儿北奔勤王。后记其经历撰成私记,正如作者所言“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佶所知者,以备异日之掌故”[1]。书中所述为作者耳闻目睹之事件,对元顺帝退出大都后图谋恢复的情况及朝中动态叙述甚详。元明交替之际,记述元顺帝退出大都后的情况史料极少,因而此书的内容显得尤为珍贵。关于本书作者姓名,然书中却言:“初九日,诏观音奴公赍手诏赐扩廓帖木儿,征其入卫。观音奴公奏请以监察御使张佶从行,上允之。初十日,佶从观音奴公入见,十一日启行。自二十八年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事,佶所知者,撮其大要载之,以备异日掌故……”[2]。根据这一史料,观音奴公奏请以监察御史从行的张佶,即为本书作者。诸家著录之刘佶与书中“张佶”当有一误。此书自明初迄于清末,一直未见刻本传世。清咸丰九年(1859年)的莫有芝抄本也不知出自何本。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柯劭忞得此书时,称之为“稀世之秘笈”“如获海外奇珍”[3]题解。此言不无道理。之后,罗振玉将其辑入《云窗丛刻》(《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中。
《鸿猷录》十六卷,明高岱撰。高岱,字伯宗,号鹿坡居士,湖广京山(今湖北)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历官刑部郎中,景王长史。高岱善属文,一生著述甚富,《鸿猷录》之外,尚有《樵论》《楚汉余谈》《西曹诗集》等著作,但均已亡佚。《鸿猷录》亦名《皇明鸿猷录》,是高岱所著明朝当代史著作。该书虽不以纪事本末为题,记事起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仇鸾事败,选择期间重大史事予以囊括,归纳为60个专题,各具原委。大致由“太祖开创丕基”(22目)、“成祖肃清内难”(6目)、历代“诛戮权奸”(8目)、“剪除盗贼”(11目)、“讨伐蛮夷”(12目)共五部分构成。[4]提纲挈领、疏而不漏、缕析条分,为后人研究明史的梗概提供了方便。
《鸿猷录》中的《北伐中原》《克取元都》《略下河东》《勘定关陇》《北征沙漠》《己已虏变》《平固原寇》《兴复哈密》《抚定大同》《追戮仇鸾》等十三篇是有关蒙古的专题史料。卷五《克取元都》篇记载了洪武初年明军入据大都(今北京),进克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史事。《鸿猷录》是明人所撰明史中较早的一种,是存世所见的明人第一部纪事本末体著作,且本朝人记本朝事,史料丰富、叙事明晰,一直为学术界所重视。
该书在《明史·艺文志》著录。关于此书的主要版本有: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刻本;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高思诚刻本;明万历七年(1579年)顾氏奇字斋刻本;万历八年(1580)罗瑶刻本;明抄本;另有《纪录汇编》等多种丛书本。
二、 两书对“元室北迁”的历史书写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六月,徐达统帅的明北伐军势如破竹,二十九日,山东诸会合于东昌,闰七月初二日,达帅师发自汴梁,进取邯郸等地,十一日会师临清,进兵元都顺利进行。此时的妥欢皇帝如梦初醒,润七月十九日作出军事部署,对此《元史·顺帝纪》云:“诏复命扩廓帖木儿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陽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籓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具如前诏。”[5]但此时元朝统治阶级内部已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勤王之师无法召集。二十三日,明军水陆并进,进逼通州,负责守卫的卜颜帖木儿出大都迎战,败绩被擒死之,元军溃灭之势已成。
对此,高岱《鸿猷录·克取元都》开篇不遗余力,尽力记述,字里行间强调明军所向披靡、战术精当,元军节节败退的场景。云:“洪武元年戊申闰七月,徐达率诸将既克长芦、直沽等处,进抵河西务。郭英首与元兵战,生擒达达判院。遇元平章奄卜、大战,击破之,俘获人马甚众。距通州三十里为营,深沟高垒,为持久计。众请速攻城,郭英曰“吾师远来,敌以逸待劳,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雾,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骑三千直抵城下。元将五十八国公率取死士万余,张两翼出,战良久,英佯败,敌乘胜来追,伏兵起,截其军为二,斩首数千级。元知院卜颜帖木儿力战,死之。擒元宗室梁王孛罗。二十七日夜三鼓,遂克通州。徐达率叶云龙等俱以师会。”[6]
可见,高岱在《鸿猷录·克取元都》开篇中,将明军按照朱元璋既定方针挥戈北伐,攻取山东,转战河南,一路势如破竹,一统之势已然明了的史实细致陈述。
二十八日,妥欢帖木儿至清宁殿,召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与群臣同议避兵北行之事。朝廷上下“惊慌失措、无复守志”[7]。
《北巡私记》记为:“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曰,惠宗皇帝御清宁殿,召见群臣,谕以巡幸上都。皆屏息无一言,独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公力言不可,大意谓贼已陷通州,若车驾一出都城,立不可保,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请死守以待援兵。上曰:“也速已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遂退朝。佶待罪枢密属官,知院出,佶遇于中书省,问曰:“大计如何?”知院惟痛哭而已。中书左丞相庆童,国之老成人也,叹息曰:“吾知死所,尚何言哉!”既而知院密语佶曰:“今夜必有举动,君去就何如?”佶曰:“朝廷大计不敢问,愿从公后,可乎?”知院颔之。是夜,漏三下,车驾出建德门,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从者左丞相失烈门、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住、参知政事哈海、翰林学士承旨李百家奴、知枢密院事哈剌章、知枢密院事王宏远等百余人。从者(此下有脱文),佶匹马遇知院公于道中。”[8]
而《鸿猷录·克取元都》则云:“元主得报,大惧,集三宫后妃、太子等议北避兵。迟明,召群臣会议。端明殿门开,有两狐自殿上出,元主叹曰:“宫禁深严,此物何从来?殆天所以启告朕也!朕岂可复作徽、钦衔璧事耶?”遂决计北徙。左丞相失烈门、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留固守京城。不花恸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去之?”皆不听。命淮王帖木儿不花、丞相庆童留守燕京,夜半,开建德门出,由居庸关北去,如上都。”[9]
观察两段史料,可以看出:第一,《私记》中详实记载了顺帝召见群臣,商议逃至上都的史实,此时知枢密院事哈剌章公以“金宣宗南奔之事”作为历史鉴戒力劝顺帝待援兵、保都城,但由于也速已败,形势危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救兵不至,然事已至此,固守京城无异于束手待毙,顺帝十分无奈。另外,《私记》亦详实记载了朝中官员此后的焦虑之状以及随惠宗北奔上都的君臣众人,这在《鸿猷录》均不见记载;第二,元明鼎革之际,《私记》作者刘佶供职于元朝廷,虽然其“枢密属官”和“拜监察御史”文职官员的职位不高,毕竟他是统治集团中的人,在政治认同方面一定倾向于故元,并准确、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朝廷大政,《私记》的书写以元为正统,从“北巡”书名便可见一斑,体现了刘氏的忠君情结。在他的笔下,依然使用“至正二十八年”的年号,“惠宗皇帝”的帝号,“巡幸”的尊号等。高岱笔下的蒙古虽退居朔漠,但对明廷威胁依然极大,此时的明朝趋于腐朽,又缺乏积极的政策,致使双方矛盾加剧,蒙古族方面侵边频繁、兵连祸结。而高岱作为生活在嘉靖时期的士人,忧患意识深重,通过经世之作表达“华夷有别”的正统观念,希冀为现实政治统治服务。如此,高氏则制定“洪武元年”“元主”“克”详备的书法;第三,《克取元都》篇目中洪武元年戊申闰七月(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曰)“端明殿门开,有两狐自殿上出,元主叹曰:‘宫禁深严,此物何从来?殆天所以启告朕也!朕岂可复作徽、钦衔璧事耶?’”[10]这一祥瑞之事,《北巡私记》记作“(至正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是曰,有狐数头入行殿,直至御座下。御史大夫阿剌不沙见上,极言亡国之兆,上曰:“天意如此,朕将奈何?”[11]古人重视祥瑞之说,作为此时已退居上都的顺帝在漠北见狐视为其亡国之征。但两条史料记载的时间不同,一为,至正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另为,洪武元年戊申闰七月(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曰)顺帝召开御前会议,议北避兵。笔者认为,“顺帝遇狐”之事出现在,至正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当更为可信,私记作者刘佶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人仓皇北逃,逐日记载亲历目击,对于行营见闻情况记载甚详,此事当属确凿无疑。而高岱将此条史料杂糅于议北避兵之时,实有意为之,用“狐”代指“胡”,阐述元亡的天命观,甚至用一种神秘主义的手法来进行历史叙事。
“二十九曰,车驾至居庸关。时经红贼之乱,道路萧条,关无一兵。车驾至,亦无供张。帝太息曰:“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是曰,诏也速率本部兵趋行在。”[12]在刘佶笔下,上都、应昌时期的北元朝廷,经兵夑败毁,断垣残壁,满目疮痍,面对如此狼狈不堪的境遇,顺帝不胜唏嘘!八月初二日(庚午),大都失陷。明改大都为北平。刘佶此时已随顺帝逃亡漠北,关于此事经过,《北巡私记》采取的是听闻追述手法,记载甚略,“(八月)初五曰,也速奏京师失守,淮王及丞相庆童死事。参知政事张守礼自京师奔行在。”[13]而此时距大都沦陷已过三日。
关于明军攻克大都的场景,《鸿猷录·克取元都》则详实记述:“达入城,坐齐化门楼,执其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迭、朴赛因不花、右丞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戮之。又获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玉玺一,玉印二。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元宫殿门,以兵守之。宫人、妃、主令其宦官护侍,禁戢士卒,毋得侵暴。人民按堵,市不易肆。人谓曹彬下江南不过是也。达下令,凡元朝大小诸臣,皆令送告身于官,署民籍中,违者有罚。元翰林待制黄殷仕耻出见,欲自投井,为其仆所守乃,乃诒其仆曰:“吾甚愧,何从得酒饮醉而出可也。”其仆喜,入市取酒,殷仕遂投井死。左丞丁敬可,总管郭允中皆死之。学士危素寓僧寺,亦欲赴井。一僧止之曰:“公可无死,公死是亡国史也。”遂往见达。后仕国朝,仍学士官。”[14]
关于此段史料需交代,第一,关于元朝传国玺下落的史事。秦之后,“传国玉玺”作为历代帝王的正统符应的象征。史载元朝这一枚传国玺,由顺帝携往塞北。此后,蒙古族历代大汗均以玺相传,以维固自身统治合法依据。也先称汗时,也将传国玉玺为自己受天命合法统治依据,云:“大元田盛大可汗致书皇帝, 往者元受天命,主夷夏。今已得其位,尽有其国土人民、传国玉玺。”[15]据叶子奇《草木子余录》云:高帝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少传玉玺,一王保保死者先后四十余万人。”[16]《克取元都》的前段记载明显沿袭于《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八月庚午条。因此,《克取元都》篇中此条记载不明确,无非是“胡运既终”,为朱明王朝下一步“奉天征讨”寻找借口罢了;第二,本段记述元翰林,待制黄殷仕“耻出见”,“投井死”尽忠事迹近百字,《实录》未载。由此可见,《鸿猷录》的作者高岱不惜笔墨,记述忠元之士的忠义行为,贬抑失节迎降、弄权利己之辈,完全是站在纯粹的封建“忠君”观念立场之上褒扬“忠元”之士,宣扬其“天命”所在。
事实上,当时的北元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均还拥有相当大的实力。大元虽灭,退避草原的北元政权仍与明朝遥相对峙,欲图恢复对中原的统治,成为明朝一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朱元璋灭亡元朝的战略目标此时转变为消灭北元政权,他认为北元“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17]。此后,进行了两次颇为重要的军事行动,直至“元主远徙沙漠,遇春乃引兵还燕”[18]。
三、两部文献历史书写基调形成的原因
通观两部展现顺帝撤离大都的史著,之所以展示如此的历史场景,并形成不同的书写模式。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撰述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政治立场决定著书目的。《鸿猷录》的作者高岱一生主要生活在正德、嘉靖之际,关于这一阶段蒙古族历史发展状况,叶向高的《四夷考·北虏考》中,记述云:“正、嘉之际,黠酋暴兴,族类蕃滋,近世未有。曾铣发愤建谋,欲倾其巢穴,还我旧疆,而帷幄搆争,萧墙生衅,伊吾之剑未呜,而身首异处矣。岂不痛哉!虏既得志,益肆凭陵,鸣镝天都,彻烽大内。师中之寄,委于匪人,骑士材官,云蒸雾集,而不敢以一矢加遗。虏氛日恶,厥有由然。穆皇初岁,虔刘汾、石,几无孑遗。属天厌乱,孽虏扣关,遂缘舔犊之恩,用蠲放麑之德,桑葚既食,好音是坏,驯异类于坫,拯氓隶于干戈,亦云盛矣。而玩愒寝生,军实耗坠,迎佛掠番,狡谋百岀,金钱内尽,藩篱外撤,故识者忧之。”[19]危机促人反思,实际上《鸿猷录》的撰写,作者是从“资治”和“经世”的目的出发,汲取历史上本朝防御蒙古族经验和教训,高岱认为“庚戌虏变,余亲所目睹其事者。大抵人狃于宴安,吏牵于文法,事怠于诿避,兵习于惰游”[20]。因此,嘉靖、万历时期有关明蒙关系史著大量的涌现,与明朝日趋腐败、边防弛弱、将领懦怯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是留心蒙古族史事的著者对现实时势的强烈要求,是时人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危机的应答。其中“克取元都”篇完整记载了故元蒙古族退出中原的经过,明朝对故元蒙古势力打击的过程。因此《鸿猷录》的编写原则,是为现实政治服务,修史者完全贯彻明朝官方的认可,他把对时局的认识贯彻其中。
而刘佶,虽身世不详,但此人曾随惠宗北奔上都,时为“枢密属官”,至正二十九年(1369)正月初九“拜监察御史”。三十年(1370)正月十一从观音奴赍诏赴陕西征扩廓帖木儿入卫。职位不高,但参与机密甚多,私记生动记载了元顺帝仓促的弃守大都、病死应昌的历史脉络,作者对惠宗败亡路线的选择、途中的狼狈之状、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倾轧等,都有形象的载入。双方的政治立场必然影响自身史书的编撰。
其次,二书史源不同亦影响书写情况。高岱《鸿猷录》博采众说,勾稽历史,褒扬忠烈,高岱在《鸿猷录·自序》中云“惟是先臣之纪述传志,暨诸书疏案牍,无不参质考订”。[21]通过考证前人传记主要包括:《皇明历朝资治通纪》《后北征录》《北征记》等。[22]上述传记多出自名家之手,多为当代史著和当事人之作,是明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采择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量史料,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对重要的事情加按语评论,以一种非常可观的方式勾稽历史碎片,目的是在叙事中发人深省,总结元亡明兴的历史规律。
《私记》的史源十分明确,作者将随惠宗逃亡北迁途中之所历,生动形象记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23]的北元初期的历史。
结语
通过对两部书中关于“元室北迁”全面的梳理与比勘,可以发现,客观的历史事实虽然是历史书写的主要依据,但同一历史事件的编纂由于受到作者政治立场和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著者片面地处理历史资料与评价人物之时,层累的塑造一套历史面相,以便维护皇权,服务当朝。这使我们对史料甄择之时,应注意避免受一些刻意构建的影响,方有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