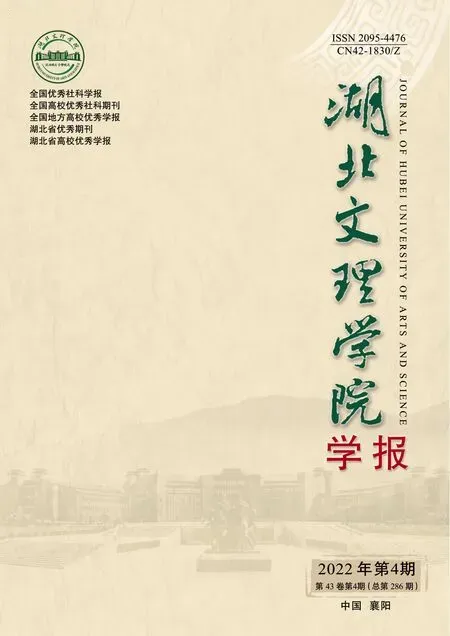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美学价值
孟慧敏
(合肥经济学院 基础课教学部,安徽 合肥 230000)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探讨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直译与意译、翻译意境、翻译风格。传统翻译美学重视感觉与经验,忽视分析与规范;现代翻译美学则强调翻译的艺术性特征,并试图调和内容与形式的矛盾。[1]翻译美学的最高美学价值是令译文有与原文一样的感染力,英语文学翻译作品作为美学翻译的下位概念,自然也以实现这一价值为最高目标。英语文学翻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追求审美与准确间的平衡。本文试图从翻译活动、翻译客体、翻译主体三个方面探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美学价值。首先,从文学翻译概念、特征、过程及标准出发,理解翻译是一种审美再创造的过程;其次,从翻译涉及的客体(文本)出发,理解英语翻译作品中所涉及的直观与非直观的形式价值;最后,从翻译涉及的主体(译者)出发,理解英语翻译中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之间的能动性关系。
一、文学翻译的审美创造性
(一)文学翻译的内涵与特性
文学翻译自产生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思考与讨论。茅盾认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原作的艺术成就;钱钟书主张“化境说”,即文字转换过程不可生硬,同时又要保存原语风味;郑海凌在《文学翻译学》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性的转化过程,翻译者要在掌握原语文本的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基础上用另一种语言将其再现出来,并给译文读者以美的体验。[2]由此可见,文学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符号的相互转化,而且是需要再现原语艺术形式的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
文学翻译与其他类型翻译的差异就在于其艺术性。文字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其一为非艺术性原语翻译,包括文件及各种应用性文书;其二为艺术性原语翻译,包括各种体样的文艺作品。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来看,翻译首先要注意语言形式与语义的对应关系(科学性),其次要关注语言表达与接受的关系(艺术性)。因此,文学翻译的审美性并不局限于艺术性作品的翻译。当然,艺术语言翻译更为综合,它不仅要求准确无误地传达文本原意,而且要求具有一定的艺术再现能力,这样才能准确表达出原语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
文学翻译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社会历史和作家自身经历都存在于原语作品中,这种客观存在只有经过翻译者的能动性创造,才能在译语中得到体现。翻译的成功与否与译者是否理解原作,以及对于译语的把握程度相关。译者将原语作品中的社会图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艺术化的再创造。文学翻译不仅追求科学真实与艺术真实,而且追求同等的接受效果。翻译过程是一个主客统一的过程,译者一方面要对异国文化报以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要考虑如何令本国读者方便接受异国文化。因此,翻译作品也是译者理解、阐释、审美后的精神产物。
(二)文学翻译的审美过程
翻译美学理论提出,翻译实践实际上就是审美主体在自身审美条件的基础上,对审美客体的认识、转化和再现的过程。也就是说,翻译者对原语中的意象组合产生审美感受后,通过译语表达的过程。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翻译概括为两个基本步骤,即理解与表达。[3]认识是“美”跨文化传递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理解审美客体的第一步,而且是进行转换与再现的条件。
语言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发展,是人类文化载体。想要成功传播原语中的审美感受,就需要对原文的文化特征进行深入的认识。译者认识英语原文过程往往经历了从直观到理念的过程,包括从直观感受到联想,最终到理解的过程。译者的直观只是对刺激反映的结果,是审美主体态度的产生阶段;联想则具有一定的能动性,需要译者补充译文中可能缺失的审美部分;理解则是译者通过一定的分析与调查,挖掘原语文本中隐藏的文化要素。转化是翻译的又一重要环节,它以移情为基础,译者需要克服与原语作者的时间、历史地域和民族心理文化间的差距,努力再现原语美感,还需要对所理解的内容去伪存真,进行加工改造。再现就是移情感受转换加工后的最终展现,其本质就是通过内省的理解转换为外显的直观,也就是以最合适的译语形式表现原语的艺术特征。因此,翻译审美就是模仿与重建的过程。
(三)文学翻译的审美标准
美所包含的范围很广,科学将之定义为“精确”,艺术则将其定义为“优美”。整体来讲,美意味着完美。文学翻译的审美目的决定了它以再现原语文学为最高目标。文学翻译与其他类型的文学欣赏不同,不仅需要准确表达文字结构的特征,而且要尽可能表现源语读者可以感受的文学之美。不管是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还是许渊冲的“三美(音、形、意)”,都强调了翻译作品对美的追求[4]。因此,不同的审美标准下对于译文美的认知存在差异。
综合以上见解可知,文学翻译的重要标准之一便是形式美。形式美是美学的重要范畴,美的形式与其本质密不可分。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表明,作品各要素间独特的组合形式是有“意味的”,它不仅构成作品,而且引起人们的审美情感[5]。形式的意味来自人们实践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化与心灵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固定的表现形式,比如诗歌中的节奏、韵律、排列方式,散文、小说、戏曲在结构、风格上的追求等。因此,翻译要根据不同文本类型的表现习惯调整表达形式,以适应译语读者的表达习惯。文学翻译的另一个标准便是忠于原文。译者需要不偏不倚地忠实呈现原文内容与思想,因为离开了内容真实,美就毫无意义。这也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投入感情,与作品融为一体,这样才能真正表现原作的情感。
二、英语文学翻译审美的形式价值
(一)直观形式价值
美学中的“形式”是一个复合概念,与感性相关。美学的形式包含三个层次,即外在形式、内在形式与理念形式,它们分别诉诸自然、情感与意志。审美主体通过外在形式感知审美对象,内在形式则是感知向认知提升的中介阶段,理念形式则指向审美对象的含义。[6]因此,外在形式是直观形式,内在形式与理念形式则是非直观形式。
语音是审美信息的基本呈现方式之一。语音审美的基础单位是音位,不同的音位组合形成不同的语音形式。英语的语音形式主要体现为两种:音律与音韵。英语的音律即音节的强弱。以诗歌为例,包括六种形式:升格、抑扬格、抑抑扬格、降格、扬抑格、扬抑抑格。一行英语诗歌通常包含一到八个音步,最常见的是抑扬格五音步。原语读者可以通过不同的诗歌节奏构想不同的诗歌意境。例如,格雷(Gray)的《墓园挽歌》“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7]此诗为常见的五步抑扬格,韵式为“abab”,“day”与“way”押/ei/韵,“lea”与“me”押/i:/韵,给人一种回环往复的美感。郭沫若译文翻译为“暮钟鸣,昼已暝,牛羊相呼,纡回草径,农人荷锄归,蹒跚而行,它全盘的世界剩给了我与黄昏”。译诗中轻重相间,并且用逗号可开,有停顿之感,并且以ing进行了押韵,但各行音步不统一并且是扬抑格,在原诗徐缓哀伤之情中添加了一些轻松。19世纪中期,英语诗歌中出现了自由体,不过依然看重“内在节奏”;而汉语诗歌并不关注轻重律,更关注音高。汉语模仿英语中的常见韵式并不难,但是根据译者翻译理念的不同,也有人认为应该重视诗歌意象而非语音形式。
词语是审美信息的又一重要呈现方式。词是字形、语素和音节的结合体,也是组成句子与篇章的基本要素,可供审美的要素十分丰富。双关语就是词汇形音的不同对应方式而形成的一种审美现象。英语中的双关语很多用于调侃幽默,诗歌中较少使用。不过莎士比亚(Shakespeare)常在作品中运用,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场中,罗密欧朋友在格斗重伤后说“you shall find me a grave man”,这里的“grave”有两重含义,即“坟墓”与“忧伤的”,这句话也暗示了好友的悲剧结局。除了双关这种修辞手法外,还有诸如暗喻、明喻、对比、夸张、对偶、反语、反衬、拟声等修辞手法,都是通过词汇层面来实现的,有的是单纯语音层,有的也涉及语法,数量最多的还是音、形、义的综合体现。因此,尽可能保留原语文本中的直观形式特点是体现其美学价值的重要方面。
(二)非直观形式价值
翻译除了对两种语言外在美的形式转化外,更重要的是不同民族文化间的转化。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会形成性格、思维与价值倾向,这种心理特征与其他民族相异。这种陌生的气质特征必然会导致交际障碍,进而引起译文与原文无法真正对等的状况。
汉民族具有内倾性的性格,重视整体思维;而英语民族具有外倾性的性格,注重解析思维。[8]整体思维不关注逻辑分析,更关注直观感受,因此,汉民族更习惯于领悟式的含蓄美;而解析思维更注重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过程,习惯追问事物形成原因及发展原理,倾向于理性美。例如,成语“披星戴月”是一种隐喻式的表现方式,本出自唐代吕岩的《七言》“击剑夜深归甚处,披星带月折麒麟”,其中包含了诗人及后来使用者的情感倾向,但在英语中被翻译成“go to work before dawn and comehome after dark”,“journey under stars and moon”或者“toil night and day”[9]。翻译后的情感倾向遗失,“辛劳”之意明确点出才可以,也就是说,思维方式影响了审美方式。
外倾性格决定了西方民族更关注外部的客观真实,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艺术应该模仿自然。汉民族关注自我与外物的结合,更倾向主观,因此,中国的许多艺术不追求细节形似与真实,偏重写意表现。中文的句法结构与语义信息隐藏;而英语句法结构与语义显露。例如,“披星戴月”英译要将这种具体发生的原因通过“work”“journey”“toil”等具体化的方式交代清楚。在这种思维影响下的西方审美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能够从某一个角度深入观察事物,但是缺乏整体性把握。例如,哈代(Hardy)小说《儿子的否决权》的开头部分以固定视角对女主人公的头发进行了描写,“To the eyes of a man viewed it from behind, the nutbrown hair was a wonder and a mystery. Under the black beaver hat, surmounted by its tuft of black feathers...seemed a reckless waste of successful fabrication.”[10]这段细腻的描写客观展现了人体的某一个部分,这种风格在西方其他作家笔下也十分常见。中国对于小说人物的描写则不同于西方,作家常常将他人的视角与自己视角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融合的感觉。例如,《红楼梦》写王熙凤登场时,“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是作者的视角,紧接着黛玉的视角“这来者是谁”,最后是作者与人物二者视角的融合“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由此可见,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是思维方式、叙事手段与审美价值的翻译,需要完成非外在形式的转换才能体现原文的美学价值。
三、英语文学翻译审美的主体价值
(一)审美客体的制约性
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是美学中两个相互依存的重要范畴。翻译美学中的审美主体是译者,而原文则是审美客体。因此,翻译审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客辩证统一的过程,翻作离不开译者的主观审美,审美主体的价值得到体现。不过,译者的审美虽然具有个体性,但是并非任意主观,因为其必须受到翻译原文的限制。审美客体对于审美主体的限制正体现了翻译学的实质。
原语中的形式特征既体现了内容价值,也体现了思维与审美价值。直观形式系统是语言表达的重要手段,然而它的转换过程受到许多限制。如上文所说,中文翻译无法完整再现英语诗歌中以韵律、修辞为代表的直观形式。非形式直观系统也体现了对审美主体的限制,它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形式。非直观形式与作品风格有关,它通常表现了原文作者的情感与意志。如上面所举的“披星戴月”的英译缺乏对“辛苦”的感叹之情。此外,还存在思维方式与文化差异导致的审美限制。如爱尔兰诗人叶芝(Yeats)《茵尼斯芙丽湖岛》中的诗句,“I will arise and go now,and go to Innisfree…While I stand on the roadway, or on the pavements gray, I hear it in the deep heart's core.”[11]诗歌不仅描绘了当地的地理环境,而且展现了作者渴望归隐的心理感受,诗歌背景限制了译者审美。以上三种限制主要影响翻译的转化和再现,时空限制则主要影响认识阶段,这一限制是每一个审美主体都需要面对的。翻译的第一步需要翻译者对原文进行还原,也就是说需要通过语言词汇并结合个体的生命与文化体验,认识或想象作者的文化体验。翻译者如果不能真正进入作品,不能走进作者所处的时代,其解读也就无法取得成功。[12]
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交流形式,翻译审美主体受到原语结构特点、表达习惯、思维文化与时空的限制。翻译主体通过原语的结构及语言了解其文化,才能正确理解作家所表达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艺术审美。审美主体在与审美客体视域融合的过程才能完成审美价值的再创造。
(二)审美主体的能动性
审美客体对审美主体具有制约性,但审美主体也有一定的能动性。能动性就是审美主体的价值体现。译者如何将原语作品的美展现出来,与审美主体的条件及潜能有关。只有审美主体能动地与审美客体相互作用,才能充分体现文学翻译的审美效果。翻译实际上是译者主动向文本靠近的过程,主体的能动因素会体现最终的审美结果。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应当具备三个层次,即文化知识、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如此才能完成审美价值的转化与传播[13]。
审美主体的知识积累是审美意识产生的条件。人对美的感觉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翻译者自身的知识与文化修养越充分,其审美能力就越突出,由此可知文化知识对于审美的重要作用。不了解作家经历及文学主张,就无法理解其作品的文化内涵。例如,乔伊斯(Joyce)就处于先进的欧洲文明与朴素的爱尔兰文化之间,只有了解了作家的经历,才能理解《死者》中“死”的隐喻内涵。翻译者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仅进行字面翻译无法完成艺术再现,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审美价值。
审美主体对美有感知和理解的能力,即审美意识。人的感知通常与直观感觉相关,文化知识的积累会使这种感觉由直观向理念过渡,这样审美主体就具备了较高的审美能力,能在审美活动中发挥能动性。人的审美具有综合性,既有感性,也有理性;有情感,也有志向。译者审美的能动性可分为两种:稳定性与变动性。其中,稳定性即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持有稳定的态度,对某一作品持有较为稳定的审美评估,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感知原语文字进行审美再现[14]。也就是说,审美主体有一定的审美标准,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保持不变。变动性针对的是审美客体中的模糊性存在。[15]因为无论是作者的写作意图还是读者的阅读感受,都是可变的,所以译者应该确保自己的审美功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把握审美客体的模糊部分。
审美主体在反复审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审美感知,便是审美经验。因此,可以认为审美经验就是深化后的审美判断。正如鉴赏家更被看重的是审美经验一样,成熟译者的能动性也体现为经验中深化的审美态度。审美经验产生于审美实践,丰富的审美经验才能使得审美主体更好地再现审美客体,进而完成审美价值的转换与传播。
文学是“言、象、意”相融合的语言艺术,文学作品的翻译是以“美”为核心价值的语言转换过程,需要译者以译语将作品的形式风格、思想内容完整地再现出来。翻译是主体对客体认识、转换、再现的过程,也是译者与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英语文学翻译作品中的美学价值需要从三方面来认识,首先是翻译活动的审美创造性、英语文学翻译审美的形式价值、英语文学翻译审美的主题价值三个方面。文学翻译本身是一种审美活动,不仅追求科学真实与艺术真实,而且追求同等的接受效果。文学翻译在模仿与重建的过程中达到对完美的追求。形式价值主要有直观形式价值与非直观形式价值,前者体现英语文学作品中以音、形、义为代表的外在形式价值;后者则体现为以思维、文化为代表的内在形式和理念形式。主体价值主要体现在客体对主体的制约性与审美主体的能动性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了翻译主体的能动性受到限制,这源于翻译本身的转换特性;后者体现了翻译主体能动性对审美价值传播的作用,以及价值传递时的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