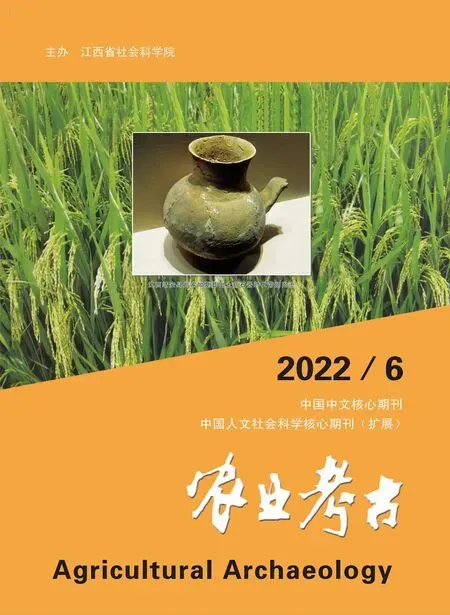湘赣地区古代越人的铁器化进程
文国勋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铁器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特别是东周时期,铁器极大的推动了社会历史变革[1](P2)。南方楚地是较早使用铁器的区域之一,湘赣地区的楚文化遗存中也大量出土有铁质工具,为楚国农业生产和“荆新地”开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P67-71)。黄展岳[3](a.P142-157)、高至喜先生对湖南地区楚人遗存中出土铁器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但并未涉及土著越人使用铁器情况[3](b.P270);彭适凡先生则对赣境地区出土铁器也进行了详细梳理[4](P108-113),但部分出土铁器遗存性质和年代值得商榷;林蔚文先生结合文献和出土文物对湘赣周边的闽、浙、粤、桂地区越人的冶铁业的发展和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5](P69-76);杨清平、谢广维先生对广西地区先秦两汉铁器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认为广西铁器大部分从岭北楚地传来[6](P76-83)。黄展岳先生认为南越国出土铁器绝大多数在原楚地和中原战国汉初墓中找到相同器形,可见之间源流关系[7](P107)。本文试通过对湘赣地区越文化遗存中出土铁器的梳理,探讨越人使用工具的铁器化进程和成因。
一、湘赣地区越文化发展概况
湘赣地区处于长江中游南侧,各有一条自南向北流经的河流,即湘江和赣江。虽它们之间有幕阜——罗霄山脉相隔,但山脉间河谷相连,自古两地文化相通。《战国策·魏策》引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8](P782)《山海经·第六·海外南经》载:“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今之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是也”。[9](P238)史籍多记载先秦时期湘赣地区存在大量的越人,《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越,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10](P177),一般认为这些越人是百越的一支。春秋后,楚人进入湖南地区,《后汉书·南蛮传》载:“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11](P2831)。至战国时,楚越在湘赣地区边界形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张守节《正义》注:“永、郴、衡、潭、岳、鄂、江、洪、饶并是东南境,属楚也。袁、吉、虔、抚、歙、宣并越西境,属越也”[12](P1751)。其后秦始皇也是“南取百越之地”,汉吴芮更是“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13](P1894)。由此可见,从西周至西汉早期,历经楚秦汉三嬗,湘赣地区的越人一直聚族生活于此。
从考古出土的越人遗存来看,湘赣地区越文化大致在西周中晚期之后,土著的文化统一性明显加强,各地文化因素基本相同[14](P86)。出土大量青铜铙、青铜镈被认为是本地越人所用礼乐器,且多采用祭祀性单个埋葬[15](P123)。春秋时,湘赣地区越人主要分布在湖南的资江、湘江流域和江西全境,但越人习俗有较大的地域区别,湖南越人墓多为狭长型土坑墓,带腰坑,随葬越式鼎、刮刀、削等典型越式青铜器。赣东北有悬棺葬,多随葬大量木器、硬陶器等。战国后,湘赣越人主要分布在湘江中上游和赣江中上游和赣东地区,越人墓中有宽坑和狭长形,墓内除越式青铜器外还多随葬硬陶器和原始瓷。至秦汉一统后,文化逐渐走向统一,除早期偏远之地还可识别出越人墓外,大部分是在汉墓中保留了一些越文化因素。本文不再对有区域差异的越人进行族属分析,而是将其都纳入广义的越人当中探讨。
二、湘赣地区越人生计模式和工具使用传统
湘赣地区自古物产丰富,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且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两周之时所生活的越人,“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11](P2829)对于越人的耕种方式,多认为是“火耕水耨”,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 无 千 金 之 家[12](P3270)。裴 骃 集 解 引 应 劭 曰:“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汉书·地理志》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13](P1666)
此外,在江西九江磨盘墩遗址下层出土有扁棱形石镞和橄榄形网坠,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湖南衡阳周子头春秋越人遗址出土的石器中,大量石箭镞、网坠出土;攸县网岭渡头湾春秋越人遗址也采集有网坠、石箭镞等石质工具。平江红门遗址战国越人墓葬M2中随葬有铁锸和网坠。都显示越人在火耕水耨的同时还兼有渔猎、采集食物。此种复合的生计模式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
工具的的使用与生计模式相辅相成,湘赣地区越人一直存在使用小型加工类工具的传统,并在各时期的越人墓葬和遗址中均有出土。如湖南株洲白关西周晚期越人墓中出土铜刮刀、斧、锛[16](P127)。春秋时期,湖南桃江腰子仑墓地二类越人墓中出土铜器197件,其中斧、铲、削等工具占104件;[17](P511-539)湖南衡阳赤石M315中出土有铜斧、钺等[18](P47-54);江西樟树观上墓内填土中夹杂铜锛、残石斧、残石锛,墓壁保留的工具痕迹与铜锛吻合[19](P47);江西瑞昌檀树咀春秋遗存中出土石锛2件[20](P58);湖南衡阳周子头遗址出土有3件青铜箭簇,还有134件石器,有石斧、锛、刀等;江西贵溪崖墓中还出土有锛、削等木质工具。
战国后,攸县鹅公岭M1中就出土有青铜斧、锛、铲、钻、凿、刮刀等[21](P102-107);江西新余陈家遗址战国遗存中就出土有石锛、斧、刀等;江西临川罗家寨遗址中还出土石器12件,有石斧、锛、刀等。另外,还出现一些窖藏的铜工具:位于湘赣交界山脉中的阳新星潭出土一件铜鼎,鼎内堆放铜斧53件[22](P76);江西广昌头陂出土一件印纹硬陶内,出土有铜钺、刮刀、斧、锸等工具[23](P123)。
统计发现:湘赣地区越人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铜石木器并用阶段,原因在于其所分布的丘陵山地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古老的使用传统,让越人的生计模式转变和社会生产发展都较为缓慢。这些铜石木器一起构成了湘赣地区古代越人农业生产各环节的工具体系,但还不足以引起生产力的重大变化,只能为新的金属工具(铁质器)的发展开拓方向[24](P85)。
三、湘赣地区越人遗存中铁器的分期和年代
春秋以后,南方地区各国新的金属工具铁器开始流行和推广,湘赣地区越人遗存中也开始出现铁器,结合遗存性质分析,对涉及越人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铁质用器进行统计,大致可将这些铁器分为三期:
第一期:湖南益阳桃江麦子园遗址H10出土铁斧1件,标本H10:24,长方形銎,刃部残缺,残宽6.53、厚3.4、残高9.7厘米(图1,1)[25](P89);益阳陆贾山M183出土有铁屑,器形不明[26](P20);江西九江磨盘墩遗址上层出土3件,器形和尺寸不
详[27](P61)。
第二期:湖南岳阳平江红门M2出土铁锸1件,尺寸不详[28](P108);平江瓮江红茶初制场遗址出土铁斧1件,宽6—7、厚3.5、通高13厘米[29](P40);郴州资兴旧市M357出土铁锸1件,标本M357:1,凹字形,楔形銎,弧刃,宽12.5、通高6厘米(图1,2)。铁锛1件,标本M357:4,长方形銎,单面刃,宽5.8、残高6.8厘米(图1,3)[30](P115)。江西武宁石门毕家坪墓葬中出土铁斧1件,长方形銎,平刃,尺寸不详[31](P3)。
第三期:江西九江大王岭遗址出土残铁器5件,可辨器形有锸,尺寸不详[32](P3);九江磨盘山遗址出土铁斧1件和铁镰1件,尺寸不详[33](P254);吉安新干界埠粮仓遗址纵沟中出土铁斧2件,尺寸不详[34](P2);抚州临川罗家寨遗址出土平刃铁斧14件,均为长方形銎,通高约14厘米(图1,4)。弧刃铁斧1件,宽6、通高11.5厘米。铁锸4件,凹字形,弧刃,宽约7.5、通高约8厘米。另还有铁鼎腿、铁釜等残片[35](P43)。湖南郴州资兴旧市M234出土铁锸1件,标本M234:1,凹字形,楔形銎,V形刃,通高8厘米(图1,5);郴州高山背墓出土铁刮刀1件,宽约2.5厘米(图1,6)[36](P176);永州鹞子岭M20出土小铁刀1件,尺寸不详;M21出土铁鼎1件,敛口、圜底近平,蹄形高足,口径21.2、通高21.2厘米[37](P50);永州蓝山五里坪M31出土铁刀1件,柄残,残长16.6厘米(图1,7)[38](P13)。

图1湘赣地区越人遗存中出土铁器
通过对比分析三个阶段出土铁器的伴出器物,以确定三个阶段的年代:
第一期中,益阳桃江麦子园遗址H10经碳十四测年推测为春秋时期,灰坑内包含楚越两种文化因素器物。春秋后,作为南下的先进文化楚文化在湖南形成的早期楚遗址在文化因素上都比较单一,多有楚式鬲、盂、罐等典型器出土,如岳阳临湘大畈遗址和罗城遗址小洲罗地点,因此,麦子园遗址推测应是受楚文化影响的本地越人遗存,灰坑中出土陶罐与桃江腰子仑越人墓腰坑内所出陶罐相同。九江磨盘墩遗址中发掘者依据上下层出土器物和纹饰陶片的差异,将上层遗物定为春秋中晚期。益阳陆贾山M183为随葬铜礼器和玉器的春秋晚期高等级墓葬,高成林先生认为该墓是受楚文化影响较深的越墓[39](P283-291)。综上,该期年代定为春秋中晚期。
第二期,平江红门M2出土越式硬陶瓿与长沙战国墓M1848内出土相近,平江红门M2和资兴旧市M357所出越式鼎与长沙黄泥坑54M5鼎相近,属于楚越文化融合型铜鼎,在战国时期楚越墓葬中常见,向桃初先生将其定为战国早中期。平江瓮江第三层出土铁钁伴出铜钟、越式铜鼎足、硬陶器(含米字纹硬陶片)等,应为越人遗存。综上,该期年代为战国早中期。
第三期中九江磨盘山遗址伴出印纹硬陶罐、高足陶灯、石矛、砺石等,被一米格纹陶盆覆盖;武宁石门、高安郭家山、上高塔下、郴州高山背和永州鹞子岭等墓葬中所出越式鼎与向式D类Ⅲ、Ⅳ式鼎相似,且伴出瓿、碗、杯等原始瓷,都为战国晚期越人墓葬。资兴旧市M234墓内出土硬陶瓮饰方格纹和叶脉纹组合,罐饰米字纹,形制与衡阳玄碧塘西汉早期墓同类器物相同[40](P214),蓝山五里坪M31陶瓿与广州汉墓I型陶瓿相同,都随葬典型越式陶器。综上,该期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湘赣交界的株洲炎陵胡家坳遗址第三层中出土铁器残块[41](P350),赣南定南田螺塘遗址采集铁斧1件[42](P3),因其伴出器物都较少而无法分期,年代大致为东周时期。另彭适凡先生还提到1976年在新建县大塘赤岸山战国遗址中还出土有一扇铁质斧范[35](P254),是铸铁生产的有力证据。
四、湘赣地区越人铁器化特征
依据上文对三期中出土的可明确器形的铁器所进行的分类,大致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两类,列表如下(表1):

表1湘赣地区越文化遗存中出土铁器统计
第一期为铁器使用初始阶段,铁器出土在湘西北和赣东北地区的遗址和高等级越墓中。种类简单单一,与越人常用青铜和石质工具类型相似,目前保存下可见铁器器形只有斧。第二期进入发展阶段,分布在湘江流域与幕阜——罗霄山脉之间偏远山区地带。虽增加了器形种类,但都为工具类,其中锸在战国楚墓中多埋葬于填土之中,为起土之用。越人对铁锸的使用是越人工具使用的一大飞跃,对其生产力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第三期进入普及阶段,分布最广,涉及到湘江上游和江西大部分地区。在种类、数量上都有质的飞跃,出现农业生产中用于破土翻耕的“V”形锸,谷物收割的镰,生活所用鼎和釜都已使用铁器,此时湘赣地区越人已基本完成铁器化进程。相较于之前铜石木并用阶段火耕水耨的生计模式,该期的湘赣越人已具备有转变为以铜铁器为主进行稻作农业耕种的条件,今后还需要在越文化生产生活相关遗存中进一步检测实证。
总体来看,铁器在湘赣地区越人遗存中传播存在着由北向南扩散发展的趋势。但与楚人遗存内出土铁器类型比较,越人遗存中铁器使用也稍有不同,即耕垦用具中多为弧刃铁锸,V型刃铁锸出土较少,目前仅资兴旧市越墓M234出土一件;中耕用具中不见六边形横銎铁锄[43](P77);加工工具中不见铁夯锤,此类夯锤印痕多见于楚城城墙夯土和楚大墓墓室内青膏泥上,在江西贵溪崖墓中出土过木质桩锤(M6:13)[44](P13),其侧柄方式与楚式銎口朝上装柄不同。
五、湘赣地区越人铁器化的成因
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发展程度来看,湘赣地区越人的文化相对落后,并且在其遗址中并未发现早期冶铁遗存,由此我们认为越人的铁器化进程与当时的铁器发展和社会文化格局密切相关。
(一)楚国铁器的推广
两周之际,中原地区人工冶铁制品已有较多发现,有学者认为楚地可能为古代中国早期生铁技术发展的中心之一。在楚人南下湖南之前,湘赣地区并无铁器出土。伴随楚文化南渐,其后发现较早的铁器都出土于春秋晚期的楚人平民墓葬中,主要为仿青铜器的铁生产工具,如长沙龙洞坡M826出土铁刮刀1件;长沙识字岭M314中,日用陶器组合(鬲、钵、罐)与铁锸1件同出;常德德山M12出土铁刮刀1件;长沙杨家山M65出土铁刀、铁剑、生铁鼎各1件。此时的铁器出现都在楚人南下湖南重点控制的常德、长沙古城周边。
战国后,楚人逐步控制湖南全境,楚人墓葬中开始大量出现铁器,其流行程度甚至比楚国核心区和其他列国都要多,包括铁质生产工具和铁兵器出土,湘西北沅水下游楚墓中出土铁器32件。铁工具有:锸、斧、夯锤、削、刮刀等多种类型;益阳黄泥湖M246、M532、M40、M680、M576等仿铜陶礼器战国楚墓中随葬有铁锸、钁、刀、环等;湘北汨罗永青村I期战国早期墓M18、M45、M81中随葬有铁刀和铁锸[45](P59);平江红门遗址T1H1中也出土铁锸1件(图1,8),该遗迹内伴出的陶豆、钵等在战国楚墓中常见,该灰坑应为楚文化遗存;湘中韶山灌区中晚期楚墓中随葬有铁凿、斧、刀[46](P52);湘南资兴旧市部分战国晚期至汉初墓葬中,随葬陶鼎、敦、壶(M186、M230、M462)和鼎、盒、壶(M166)组合,伴出铁削、锸等。大量铁器的使用为楚人保持了在湘赣地区的优势地位,推动“荆新地”的开发。
楚人进入洞庭湖东西两岸平原后,与本地越人已有接触,第一期益阳和九江两地属于湘赣地区北侧早期与楚人密切接触区域,因此两地出现铁器显然是受楚人的影响,而同时期湖南偏南区域的衡阳赤石、耒阳水泥厂、资兴旧市等春秋越墓群中尚无铁器出土。到第二、三期越人的铁器发展扩大与本区域楚人的铁器发展是大致重合的,因此,湘赣地区越人的铁器化是在楚文化南渐和楚人铁器推广的前提下发生的。
(二)楚越文化的不断融合
战国后,楚国内外交困,面对三晋北争中原受阻。楚国加强了对南方边鄙之地的开发。《战国策·秦策》载:“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南攻百越。”[8](P216)《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楚威王时齐国遣使者说越王,即有“庞、长沙,楚之粟也”[12](P1749)。使得湘赣地区成为楚国的重要粮食产区。在文化上,楚文化逐渐与本地越文化融合,典型特征为遗迹中出现大量楚越器物共存现象。如楚墓中随葬有越式鼎,这种薄胎附耳三细足外撇鼎被认为是楚越融合的一种产物。资兴旧市战国墓中出土这种鼎41件,鼎底部多有较厚的烟炙,为实用器。也有楚墓在随葬仿铜陶礼器组合之外加入越式铜削、刮刀。江西境内虽然楚墓发现不多,但在越墓中多发现楚式漆器随葬,如近年来发掘的国字山墓群M1中漆瑟、立柱上的纹饰等与九连墩楚墓同类器上的纹饰极为相似,S16内出土的对鸟悬鼓也是江汉地区楚文化常见器物[47](P49)。另外,湘赣越墓中随葬扁茎剑在战国后逐步被双箍剑和空首剑所替代,与楚墓中随葬铜剑形制趋于一致。
在楚人的治理下,形成了湘赣地区楚越不断融合的社会文化格局,为越人吸纳和采用外来先进铁器提供了基础环境,越人可通过交易、移民、战争等多种方式就近从楚人手中获取铁器。同时,越人铁器化在第三期时的普及也成为楚越文化融合的最终重要成果之一。战国中晚期广西桂林地区集中有较多铁器发现,且广西平乐银山岭越墓中出土铁器与湖南战国墓出土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因此,岭南地区铁器化的进程与岭北湖南地区在时间上是相接续的,都同样来自楚人的影响。
六、结语
湘赣地区一直是古代越人的重要居住地,随着东周时期铁器的推广,楚文化的南渐,湘赣地区越人也开始了铁器化进程。春秋时期,与越文化相关的遗址和高等级墓葬中已开始出土有铁器;战国后,越人铁器使用迅速发展,在越人的遗址和平民墓葬中均有铁质工具出土;至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越人完成铁器化的进程,较为普遍地将铁器运用于生产和生活,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湘赣地区越人的铁器化进程受益于楚人铁器的推广和楚越文化的融合,其铁器化的的进程使越人接触到当时更先进的生产工具,逐渐走向楚地的农业耕作模式,为湘赣地区越文化顺利融入秦汉文化的一统奠定了基础,更为湘赣地区越人融入华夏民族一体起到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