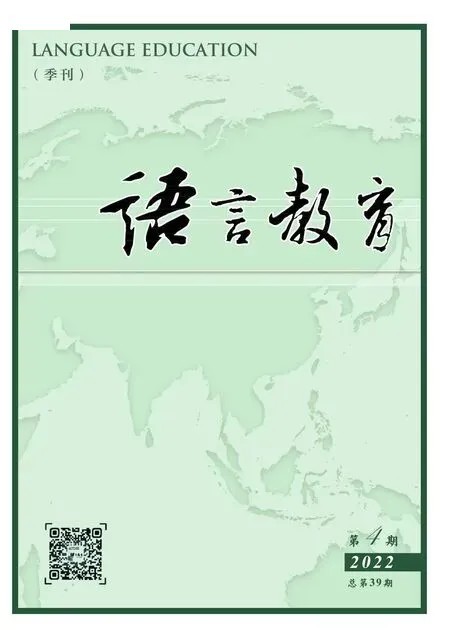风流妇的“误读”与重写
——《罗克珊娜》与复辟经典喜剧的互文性解读
李 尼 王爱菊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北武汉)
1.引言
作为英国18世纪文学经典,笛福的终作《罗克珊娜》(1724)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女主人公罗克珊娜独立奋斗的历程及她与不同地位男性的周旋史。小说序言部分自称为“影射小说”(RomanClef)。里凯蒂(Richetti)指出,这样不断强调纪实性的标题与序言设计一方面是因为“笛福想模仿当下畅行的丑闻轶事和秘史等文学体裁”;另一方面,“让人联想起复辟宫廷”(Richetti,2005:269)。林克尔(Linker)指出,“小说创作于乔治一世的英国,但叙事时间却转移到了复辟时期,这样笛福就能批判复辟宫廷。同时,罗克珊娜兼具‘机智’和‘美貌’的人物形象,让人联想起那些1670年性喜剧中更加放荡不羁的女性,尤其是威彻利和康格里夫式的”(Linker,2011:116)。
在“两种泾渭分明的文学形式并存的复辟时代”,作为“更具有时代特征,更现实主义地关注国内当代景况,特别是复辟精英们花天酒地生活”的复辟喜剧“在展示社会生活,特别是男女关系时,绝少掩饰的写实取向是空前的”(黄梅, 2015:27)。对婚姻的鄙夷和鼓吹开放性关系,使得复辟喜剧饱受道德评论家诟病,以至于复辟喜剧就是不道德的代名词。其中,学界公认最为经典的三部复辟喜剧为:威廉·威彻利(1641—1715)的《乡下女人》(1675)、乔治·艾特利吉爵士(1634—1691)的《风流人物》(1676)以及威廉·康格里夫(1670—1729)的《如此世道》(1700)。《乡下女人》中浪子霍纳(Horner)与菲吉特太太(Mrs Fidget)的婚外情在“瓷器”场景中达到顶峰。《风流人物》里多利蒙特(Dorimant)不仅对天使般的淑女哈里特(Harriet)穷追不舍,也与热情开放的布琳达(Belinda)和拉芙莱特夫人(Mrs Loveit)纠缠不休。《如此世道》中“丰满的寡妇”①McMillin, S.1997.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Comedy[M].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Inc., 306.中文为作者自译。韦斯福特夫人(Lady Wishfort)和狡猾的玛伍德(Mrs Marwood)毫不掩饰自己对贵族才俊的占有欲以及对婚姻、生育不屑一顾的态度。
然而,国内外关于《罗克珊娜》与复辟文化观照的研究略显欠缺。张在新援引德勒兹的解域理论分析了《罗克珊娜》中反传统的人物性格和小说结构(张在新,1997),王建香等分析了受规训的女性身体在现代性僭越后受到惩罚(王建香 朱芳,2013),陈栩创新运用空间理论及读者接受理论剖析了作品(陈栩,2019,2013)。林克尔讨论了卢克莱修主义与奥维德书写对女性浪子文化的影响,并在分析形象流变时提及罗克珊娜与复辟喜剧女性,但遗憾未详述两者之间的联系(Linker, 2011)。康韦(Conway)对“新教徒的妓女”(Protestant Whore)这一形象的研究丰富了学界关于复辟文化在18世纪早期的共鸣研究。然而,就《罗克珊娜》的分析而言,她主要关注的是情妇叙事与宗教冲突的关联,未将经典复辟喜剧文本纳入分析的范畴(Conway,2010)。本文将从文本的互文与历史语境的互文两个层面分析《罗克珊娜》对复辟喜剧及复辟时代女性形象的“误读”与重写。
2.互文理论、“误读”与重写
2.1 理论前溯
互文理论的主要推广者为后现代学者克里斯蒂娃。她在丰富发展了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互话语空间(Interdiscursivity)之后,从文本生产角度出发,将文本分为现象文本(Phenotext)和生殖文本(Genotext)(王瑾, 2005)。
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特将克里斯蒂娃的概念进一步传播。他认为,在当代社会,作者已经步入了死亡。对应克里斯蒂娃的两种文本划分,巴特从读者接受角度出发,提出了可读文本(Readerly Text)与可写文本(Writerly Text)。不同之处在于,可写文本消解了各种明确的规则和模式,允许以无限多的方式表达和诠释意义(王瑾,2005)。巴特认为可读文本转化为可写文本依靠读者创造力的发挥(王瑾,2005)。阅读是一次嬉戏,是寻求差异性的一次嬉戏,是使文本变得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增殖,是无始无终的重读。每一次阅读不是寻求文本的真理,而是获得一个新的文本,每一次阅读不是抵达文本的本质,而是扩大文本的疆域(王瑾,2005)。
2.2 “误读”
继巴特之后,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误读的概念。他认为文本之于前文本的关系是一种爱恨交织的俄狄浦斯情结。后辈作家要模仿先驱者,又要超越他,创作时有一种“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童明, 2015:98)。当面对前辈伟大的传统时,他必须通过对前文本进行修正、位移和重构,来为自己的创造性想象力开辟空间(赵一凡,2006)。布鲁姆的理论蕴涵了一种与罗兰·巴特“作者之死”截然相反的思想:它从巴特那个由无数匿名引文组成的文本空间,转向一种互文建构。与“正读”崇尚文本意义的复原不同,“误读”是一种强调读者创造性的文学阅读方式(王瑾,2005)。布鲁姆认为“影响压抑和阻碍着诗人的创新,但他要做的不是逃离或否定,而是通过有意的误读来偏离影响,修正前人的创作,达到创新的目的”(王瑾,2005:74)。所以,“误读”又可谓“创造性的背叛”,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王瑾,2005:84)。这样,“谁影响谁”的正常秩序就被颠倒过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后来的人以特定的方式“创造”了前人,因为任何对于前人的阅读和理解都创造了一个特定的前人,前人和他的作品就好像是一种等待后人去创造的带有可塑性的、留有空白的“文本”。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意识”不但没有被略去,反而更具体了(童明,2015)。
2.3 重写
在巴特的嬉戏解构,布鲁姆的创造性升华后,文本迎来了自我的重构。随着阅读观的改变,出现了各种“有立场的读者”(Situated Readers),而任何文学影响和接受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与接受主体所处的文学环境和作家自身的审美倾向有很大关系(查明建, 2000)。他们的解读为的是“重写”。重写意味着,我针对你的故事重新叙述,把我的不同观点写入新版本。重写,既是读,也是写(童明,2015)。
重写是作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利用互文策略,创造出“后来的文本”。在巴特破除了文学“影响”研究的成见后,“后来的文本”赢得了地位的平等。因为后人对前人的阐释反过来构成并不断重新构成前人的文本。前文本的经典地位看似由原作者建立,实际却往往是在后人的阅读和重写中建立的,这就是“后来的文本”作为互文的重要性。因此,创造性的作家通常也是优秀的阅读者,如朱利安·巴恩斯《10章世界史》对圣经挪亚方舟故事的变体重写,简·里斯的《茫茫藻海》对《简·爱》的重写,艾丽丝·默多克的《黑王子》对《哈姆雷特》的重述(沈春燕李利,2021)等。
3.“男女人”与“美德女帮”:文本形象的狭义互文
以热奈特为代表的狭义互文观主要研究一个文本与可论证存在于此文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在《隐迹稿本》等作品中,热奈特创立了“跨文本性”概念,并将其分为五种类型。其中第一类互文性,又叫“文本间性”,指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忠实(不同程度的忠实、全部或部分忠实)存在。它包括引语(带引号,注明或不注明出处)、抄袭(秘而不宣的借鉴,忠实于源文本)、影射。《罗克珊娜》对复辟喜剧的直接引用,即小说标题“罗克珊娜”(Roxana)曾出现在康格里夫《如此世道》第一幕中,“女皇帝,苏丹王后”“噢,罗克珊娜拉”(McMillin, 1997:263)。自德福南(D’Avenant)的歌剧《罗得岛之围》(The Siege of Rhodes)(1661)起,“罗克珊娜”就是妓女的代名词。除引用外,《罗克珊娜》与复辟经典喜剧之间更主要的互文关系还是人物形象的影射,即“男女人”(Man-Woman)与“美德女帮”(Virtuous Gang)。“男女人”出自罗克珊娜的独立宣言:“我要做一个男子汉一般的女人;我生来是自由的,死也应该自由。”①天一 定九 译.笛福.罗克珊娜[M].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4: 190.以下出自本书的引用只夹注页码。“美德女帮”出自威彻利《乡下女人》第五幕第二场(McMillin, 1997:71),以菲吉特太太为首热衷假面舞会的贵族风流妇们自称为“美德女帮”,明明放荡不羁,却要矫饰成名门淑女。无论是罗克珊娜还是复辟经典喜剧中的风流妇,都因其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了主动地位,而被视为游离的怪物。她们所代表的是一种男性化、放荡张扬、甚至危险的女性形象。她们或不满婚姻制度里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或不囿于温顺服从的传统女性形象,展现强势的操控。通过对复辟经典喜剧中性别对抗的“误读”,笛福在强调其中经典复辟风流妇形象的基础上,重塑了新世纪的危险女人(Femme Fatale)。
3.1 父权社会的流放者
罗克珊娜被称为“刚勇的男女人”(Amazonian Man-Woman)(McMillin, 1997:190)。《如此世道》中的马伍德太太(Mrs Marwood)拥有“亚马逊精神,一个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McMillin, 1997:267)。对典故的引用彰显这类女性与父权社会的格格不入。笛福笔下“独立自主的女人不是妓女就是小偷”(Pollack,2008:144),霍纳讽刺菲吉特太太最大的美德就是矫饰(McMillin, 1997:7)。对风流妇形象的污名化,在文本中随处可见,因为传统父权社会宣扬温顺服从的女性形象,稳固现有的婚姻制度,强调男女公私领域活动的区分,而“男女人”和“美德女帮”打破了这些规约,成为父权社会的流放者。
复辟经典喜剧里的风流妇人们放荡叛逆,从不把规矩放在眼里,并且崇尚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韦斯特夫人喜欢喝酒,还说让后代自己繁衍去吧,她不会再生了(McMillin, 1997:306)。米拉芒说:“我永远不会结婚。除非我搞清了自己的意愿和乐趣”(McMillin, 1997:269)。马伍德夫人说:“被抛弃也比从来没爱过强”(McMillin, 1997: 266)。与生活优越的贵族太太们相比,罗克珊娜则表现出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坚毅。因为父亲、兄弟与丈夫的失误,她饱受挣扎,但她展示出了与社会所期待的屈从女性不一样的女性形象,并从此拒绝倚靠婚姻提供保障。“男女人”与“美德女帮”对婚姻的抗拒有多重原因上的同异。首先,她们都在婚姻中体会到了冷落与挫折,从而导致信任缺失。罗克珊娜“发觉人们对妻子总是冷冷冰冰的,对情妇可就感情强烈了”(145)。“美德女帮”聚在一起讨论:“这年头妻子太受忽略了。男人们把自己和金钱都投入到豢养剧院里的小情人里去了”(McMillin, 1997:23)。罗克珊娜的第一次包办婚姻让她发出肺腑之言:“女人千万不能嫁给一个傻瓜,哪怕做个老处女也罢”(5)。对于荷兰商人的表白,她确实真心地愿意和他在一起,但一想到同他结婚,或者同别人结婚,就会极其反感(178)。然而,“美德女帮”因未能在婚姻中获得足够的激情、贵族浪子未履行爱情誓言而感伤,而罗克珊娜生活在重商与道德说教增强的18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社会,她对婚姻的失望则来自流动社会对安全稳定的摧毁。
因此,出于对现存婚姻制度的怀疑,她们提倡订立自由契约以保障自我权益。在17-18世纪之交基督教“夫妻同体”观念影响下,妻子的法律地位缺失。已婚妇女没有个人的法人身份。普通法还赋予丈夫控制妻子居住、迁移和社会交往的权利以及把她们视为个人财产的权利(许洁明 王云裳, 2019)。而洛克在《政府论(第二篇)》中提到,“婚姻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的自由契约而形成的”(洛克, 2016:60)。《如此世道》中的著名“条约场景”(Proviso Scene)即展示了对婚姻制度不信任的米拉芒是如何通过与情人订立自由契约,以保障自己串门、写信、穿着、隐私被尊重等方面的自由(McMillin, 1997:297)。同样,罗克珊娜也发现“婚姻法不站在女人这边,不受保障的女人只能依靠丈夫的好意与情谊”(167)。她认为“一个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是一个自由人,是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婚姻法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163)。所以《罗克珊娜》里有这样的情节:在她纠结是否与房东姘居时,对方给她看了一份契约。契约规定以后在各方面都将像对一个妻子一样地对待她,并注明了决不抛弃她,否则将赔款七千镑,还有一张他死后三个月支付给她或者她的让受人五百镑钱的证券(43)。通过创造性“误读”,笛福将契约的关注焦点由生活的体面转向了经济的保障。在父权制盛行的复辟社会,“美德女帮”通过与下层阶级私通以反抗贵族厌女症,不仅是对婚姻不公现状的还击,同时也威胁到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稳定。而“男女人”想要通过身体打破阶级壁垒,获得地位提升,更重要的是攫取金钱保障。与复辟经典喜剧中风流妇们矫饰的策略类似,罗克珊娜通过拒绝与自我克制以达到长远的目标,而擅长矫饰的人通常也是操纵的高手。
3.2 私人关系的主宰者
在以家庭为主的私人领域中,存在着多重人际关系,如夫妻关系、父(母)子关系、主仆关系等。在性别关系的权力平衡上,男性通常与主宰(Dominance)相联系,而女性则意味着服从(Submission)。无论是“男女人”还是“美德女帮”都暗示着女性特质的褪去和男性强势的附着。在福柯看来,性与权力彼此缠绕。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使性摆脱权力的控制就是要在性上做到完全的随心所欲,是性方面的“越轨”和“犯规”(李银河,2009:117)。
复辟经典喜剧中的风流妇与罗克珊娜都呈现出对私人关系的权力角逐,希望完成从服从者到主宰者的转换。“美德女帮”是贵族浪子避之不及的吞噬者。她们俯视男性,并将其当作消遣的工具。《乡下女人》中霍纳被调侃成“没了刺的公蜂在蜂巢里被女人们包围,压迫推搡”(McMillin, 1997:32)。她们公然拿男性隐私打趣,通过幽默和玩笑获得更多的权力。她们对性别关系的掌控建立在自信与机智之上,如《如此世道》中的米拉芒从不认为女人的外表需要依靠男人来评价(McMillin,1997:274)。同样,罗克珊娜也自信而残酷。她对男女角色有着清晰的认识,认为女性被定义为“消极动物”,“是福是祸全取决于她丈夫”(165)。普通的甜言蜜语无法突破她机智的见解,如“叫我来把舵盘,但船由你来指挥,就像大家说的,在海上,小伙计站在舵盘旁,给他命令的却是领航员”(166)。然而,“美德女帮”与“男女人”主宰的方式与目的却不尽相同。前者通过滥情和越轨抗议,以期挽回关注,然而往往未达成目的。而罗克珊娜将身体商品化,以此交换地位与金钱,代价是放弃女性自然的母性权力。就像她说的,“虽然我能抛弃我的贞操和出卖自己,但我不能放弃我的钱”(162)。因为性自由,她实现了自己的财政独立,利用富有或有权势的男人不断上攀,积累自己的财富与权力。然而,她“不关心孩子也不那么爱孩子,只打发艾米为她付抚养费”(288)。即便是吻自己孩子时内心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快乐,不由自主地要抱她,但判断力帮她甩掉了这个念头(302)。
同时,在18世纪英国的私人领域中,主仆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私人关系。洛克曾说,“一个自由人充当另一人仆人,赋予主人支配他的暂时权力,并不超过契约所规定的限度”(洛克,2016:63)。复辟经典喜剧中的风流妇与女仆之间保持着必要的界限,有时会通过对话凸显机智女仆对主人的裨益,如拉芙莱特夫人的女仆珀特(Pert)警醒她道:“一个时髦的先生非常忙碌,通常是有了新情妇”(McMillin,1997:106)。与复辟经典喜剧中的女仆类似,艾米是机智的代名词。她帮助罗克珊娜度过困难,又进言献策。然而,与艾米的关系进一步体现了罗克珊娜强烈的主宰欲望。她安排艾米与房东同床并在一旁观看,是对主仆关系极大的僭越。主仆的亲密行为在表面上是禁止的,哪怕发生,通常也是男性主人的特权,然而罗克珊娜不仅实施,还说自己毫不在乎,并认为“我的女仆也应该是一个妓女,这样以后才不至于骂我是妓女”(49)。纳夫罗特(Nawrot,2017)认为,罗克珊娜信任、依赖艾米,形成了一种更像是同伴姐妹的合作关系,从而打破了传统私人领域的人际规约。笛福公开地表达过自己对女性主宰的不认同。尽管他同情女性,但他同样批判那些颠倒性别秩序并拒绝依赖丈夫的女人(Mason,1978)。所以,笛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虽然争取到了独立,但大多成了被社会摒弃流放的边缘人(Mason,1978)。
4.新教徒的妓女与天主教的大利拉:历史层面的广义互文
以巴特和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广义互文观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查明建,2000)。复辟文化在《罗克珊娜》中的确是有证可循的。首先,生活于复辟时期的笛福(1660—1731)是商人、政论者,还是历史与宗教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其次,罗克珊娜的理财顾问罗伯特·克莱顿(Robert Clayton)是复辟时期真实的政治家。同时,罗克珊娜直接引用了复辟时期闻名于世的查理二世的情人——喜剧女演员内尔·格温(Nell Gwyn)的名言,称自己为“新教徒的妓女”(Protestant Whore)。
4.1 新教徒的妓女
《罗克珊娜》中有很多细节指向英国复辟历史上著名的内尔·格温。罗克珊娜曾说,“我虽然是一个妓女,但我是一个新教徒的妓女,我不管怎样也不能把自己装作是一个天主教徒”(73)。而“新教徒的妓女”正是内尔·格温的经典名言。据载,某次内尔·格温坐在马车里被一群愤怒的暴民当成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法国来的天主教情妇朴茨茅斯公爵夫人,并拦住了去路,她说:“请注意,我可是新教徒的妓女”(Herman,2005:162)。从此,新教徒的妓女成了18世纪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形象主题。罗克珊娜从荷兰回到英国后,住到“蓓尔美尔街(Pall Mall)上的豪华大公寓里去了”(182)。而查理二世也曾在靠近圣詹姆斯公园的蓓尔美尔街为内尔·格温提供了住处。这一例证让罗克珊娜与内尔·格温的联系更为明确。与复辟历史密不可分的内尔·格温1650年出生于妓院,因从戏院丫头一跃成为宫廷情妇,而闻名于英国(Conway,2002)。
康韦认为新教徒的妓女形象代表了唯信仰论(Antinomian)的新教徒对法律道德的淡然。因为新教徒信奉“因信称义”:信徒得救的关键与任何善行无关,只在乎信”(韦伯,2019:305)。罗克珊娜称自己“为了一口面包,抵押了忠诚、信仰、良心和贞淑,或者说,为了感恩而毁掉了我的灵魂;把我自己交给魔鬼,以此来感谢我的恩人”(39)。也就是说,她为生计所迫,无奈走上这条道,这与内尔·格温的想法不谋而合,她也认为“自己仅是从事着与性有关的职业”(Conway,2002:220)。复辟时期,贵族们纷纷排斥格温,认为她出身低微,是下流的暗娼和戏子。普通民众则与此态度相反,认为如果国王的情妇与其是个法国来的天主教徒,还不如是个新教的英国女人。许多中下层民众欣赏格温通过才能、刻苦和幽默,脱离贫困,成为名媛的故事(Herman,2005)。换言之,内尔·格温是完美体现新教伦理的人,这一点也与罗克珊娜的数个身份属性相符,如罗克珊娜是雨格诺教徒,法国雨格诺教徒和英国非国教派,作为民族宗教上的少数者,因在政治舞台上毫无用武之地,故而被驱往营利的轨道上(韦伯,2019)。
与罗克珊娜热衷财富积累一样,宫廷名妓(Courtesan)与王室的紧密联系成了腐败的影响,甚至有取代王室之嫌(Conway, 2010)。格温曾说自己一年只需要500磅,但实际却从国库里支出了6000磅,还把自己的儿子变成了享受俸禄的圣奥尔本斯公爵(Duke of St.Albans)(Trowbridge,2013)。所以罗克珊娜说,大人物为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人浪费大量财富是满不在乎的,而我正好成了他们这种恶行坏癖的弱点的明证(78)。与罗克珊娜一样经历过贫困的内尔·格温其后也获得了经济保障:国王临终前对约克亲王嘱托,“不要让可怜的内尔挨饿”。而后来詹姆士兑现了承诺,让格温舒适地生活了后半辈子(Herman,2005)。
4.2 天主教的大利拉
除了代表新教伦理的内尔·格温,《罗克珊娜》中也闪现出另几位具有重要意义的宫廷情妇,即拥有天主教背景的卡斯尔梅恩夫人(Lady Castlemaine)和路易丝·德凯鲁阿勒(Louise de Kroualle)。卡斯尔梅恩夫人本名芭芭拉·维利尔斯(Barbara Villiers),是一名天主教徒,成为查理二世情妇后,被赐名为克利夫兰公爵夫人(Duchess of Cleveland)。因其滥情放荡的行为、火爆的脾气和天主教的背景,她受到了民众的抵制,并于1668年妓院骚乱后成为讽刺诗的对象。路易丝·德凯鲁阿勒是路易十四派往英国的间谍,她很快被查理二世安置并获得了公爵夫人的头衔,即朴茨茅斯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rtsmouth)。出自《圣经》《士师记》第16章的大利拉(Delilah)是非利士人的奸细,为了钱财诓骗迷恋上自己的参孙说出神力的来源。此后,大利拉就是妖妇的代名词,而大利拉正是当时议会给路易丝·德凯鲁阿勒所起的绰号(Linker,2011:19)。曾流亡法国的查理二世,不仅接受路易十四的资金,还如此推崇法国情妇。人们担心日益明显的法国影响会摧毁英国。与包法利夫人仅憧憬浪漫的贵族生活不一样,这些宫廷情妇对地位、权势与财富充满觊觎,所以作家们时常讥讽以她们为原型所塑造的野心勃勃而又内心纠结的浪荡女人形象。
她们所拥有的共同特征就是美貌与虚荣。作为国王的首位情妇,卡斯尔梅恩夫人漂亮而且非常自信。罗克珊娜也因为知道自己长得漂亮而充满虚荣心,失去丈夫成为寡妇时也没有忘记打扮自己,让大家知道她是有名的“普瓦图的俏寡妇”(61)。她们深知自己的优势,从而自如地操控局面。比如,曾与丈夫一起前往过荷兰的卡斯尔梅恩夫人脾气非常火爆,经常对国王怒颜相向,不顾场合地发脾气(Trowbridge,2013)。她还与威彻利以及年轻侍从们暧昧,逼着查理二世认来路不明的私生子(Herman,2005)。《罗克珊娜》中就设置了亲王说他一定会认他与罗克珊娜的儿子这一情节。查理二世的王后、里斯本的凯瑟琳一直无子,还得忍受卡斯尔梅恩被任命为自己宫廷侍女的羞辱,就像《罗克珊娜》中塑造的法国亲王妻子,后悔自己没有给他留下孩子。
与普通美貌和爱慕虚荣的风流妇不同的是,这些“克利奥帕特拉”为追逐权势、财富筹谋奔走,并能力超群。卡斯尔梅恩夫人按照路易十四的指示,尽可能不让查理颁布宗教宽容法案、不重开议会(Herman, 2005)。与后期依靠勋爵赡养的罗克珊娜类似,她每年直接从国王那里领取15000英镑,并且与珠宝商的关系也很好,信誉也不错,因为大家知道国王会为她买单(Herman,2005)。为法国效力的朴茨茅斯公爵夫人也身负重任:诱导查理二世向荷兰开战;说服查理二世改宗;促成继承人约克公爵娶一个法国公主(Trowbridge,2013)。扮演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之间的信使,不仅使她获得了英国公爵夫人的头衔,还有路易十四奖赏的法国地产(Linker,2011)。和克利夫兰公爵夫人一样,她把政府空职标价售出,收受佣金,还做把犯人卖到西印度群岛的生意(Trowbridge,2013)。结合此背景就不难理解,亲王告诉罗克珊娜,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几乎都能用钱买到爵位。罗克珊娜准备找密探打听首任丈夫时说,在法国,这种人有的是(102)。而罗克珊娜陪法国亲王微服出游意大利时还想着自己的财产,一想就很高兴(114)。种种特征都成为影射朴茨茅斯公爵夫人的佐证。
5.结语
复辟经典喜剧中以“美德女帮”为代表的风流妇们对婚姻的怀疑态度和对自由契约的推崇极大地影响了《罗克珊娜》中的“男女人”形象。在认为女人是易碎的器皿(Weaker Vessel)的18世纪,复辟经典喜剧与《罗克珊娜》中的风流妇形象在以夫妻与主仆关系为主体的私人关系中表现出了强势的操控性。同时,贴上“新教徒的妓女”标签的罗克珊娜直接影射著名复辟人物内尔·格温,而出身法国,极度渴求头衔与财富的罗克珊娜也符合当时英国对法国文化与天主教的惧怕与反感。另一方面,从对婚姻双重标准的控诉、强调女性身体与情绪的特征、性别对抗中强势的反击以及机智的调侃在罗克珊娜身上的展现,《罗克珊娜》也对复辟经典喜剧做出了选读。换言之,笛福通过阅读与重写,建构了复辟喜剧的经典地位。
复辟喜剧中的风流妇形象挑战了贵族绅士的男子气概,而罗克珊娜通过商业活动僭越性别界限,进入隶属男性的公共领域,正是笛福作为作者/读者对复辟时期双重文本的“误读”与重写。在农业经济盛行的传统英国,社会地位主要来自身世背景的传承。复辟经典喜剧中的风流妇通过越轨,破坏了血统的纯正以及继承的合法性,扰乱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秩序。随着17世纪末重商主义的兴起、经济个人主义与社会流动性增长,资本积累和个人欲望超越了亲情关系与家庭忠诚的规约(Borsing,2017)。罗克珊娜通过出色的商业运作,跨出属于女性的家庭内部(Domestic Interior),占领了属于男性领域的政治、经济权力游戏,导致男性族长制家庭经济的衰落。另一方面,在利维坦、原子论与伊壁鸠鲁主义盛行的复辟时期,风流妇的放浪形骸并未受到过分苛责。而当中产阶级兴起,社会舆论转向感伤主义的道德说教后,罗克珊娜式的浪荡女受到了现实与心灵的双重惩罚,所以,与复辟经典喜剧不同,《罗克珊娜》中出现了大量自白式忏悔,读者清晰地见证了她的内心是如何从“开的一个窟窿”(46)到“穿了一个孔”(289)的心路历程。
弗兰克·克莫德在阐述文学经典内涵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美学概念:愉悦和变迁。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带给读者愉悦的感觉,并能经历时间的考验从经典的文本变为现代性的文本(王卫新 隋晓荻,2012)。从卢克莱修《物性论》提供智性基础的复辟经典喜剧,到心理小说《罗克珊娜》和关注女性内在的《帕梅拉》(1740)、《克拉丽莎》(1749),再到菲尔丁的《汤姆·琼斯》(1749)和萨克雷的《名利场》(1847),风流妇的形象在延续中变迁,并在“误读”与“重写”中不断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