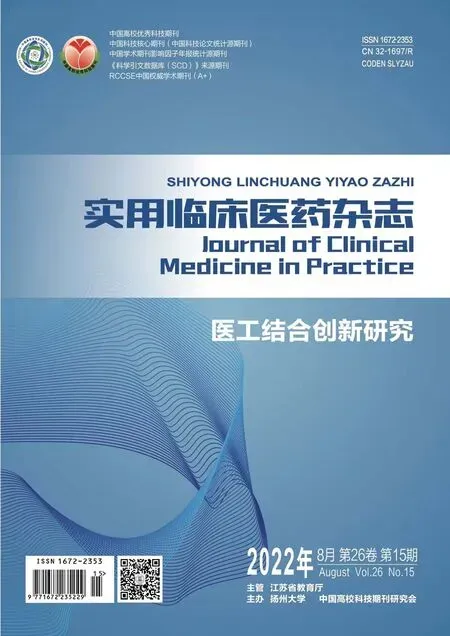表观遗传学改变与中药活性成分靶向抗肿瘤的研究进展
黄 力, 严小蓉, 吴君华, 冯 岗, 徐维国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1.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2. 肿瘤科, 四川 绵阳, 621000)
恶性肿瘤是一种由多种病因引起的正常组织或细胞无限增殖与发展的疾病,发病率与病死率较高[1]。西医主要采用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对恶性肿瘤进行治疗,但均易出现术后复发、转移、药物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2-3]。中医药治疗恶性肿瘤的不良反应少,联合其他疗法可达到增强疗效和减轻不良反应的效果[4-5]。因此,抗肿瘤中医药的研究与开发是目前临床肿瘤治疗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基于表观遗传学改变的抗肿瘤作用逐步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但基于表观遗传学改变的中药活性成分靶向抗肿瘤具体作用机制还不完全明确。本文从表观遗传学改变与相关药物、基于表观遗传学改变抗肿瘤作用、中药活性成分通过调节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非编码RNA(ncRNA)、染色质结构重塑靶向抗肿瘤等方面对中药活性成分的抗肿瘤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基于表观遗传学改变的靶向抗肿瘤新药的研发提供思路。
1 表观遗传学改变与相关药物
1.1 表观遗传学改变
表观遗传学改变是可逆的,是临床抗肿瘤研究的一个潜在靶点。表观遗传改变能够通过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ncRNA调控、染色质结构重塑等来调控基因的表达影响肿瘤进展[6]。随着表观遗传学改变与相关药物研究的不断深入,表观遗传改变药物可能是肿瘤治疗的新方向。
1.2 表观遗传学改变相关药物
表观遗传改变药物包括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DNMTis)[7]、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s)[8]等,而DNMTis包括核苷类抑制剂、核苷衍生物抑制剂、非核苷类DNMT抑制剂。HDACis主要有针对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的belinostat和多梳抑制复合物2亚基的增强剂(EZH2)的抑制剂EPZ-6438。
1.2.1 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核苷类抑制剂: Azacitidine和Decitabine是常见的核苷类抑制剂,低剂量核苷类抑制剂可激活因甲基化沉默的细胞周期蛋白,从而促进细胞分化,而高剂量核苷类抑制剂可导致细胞凋亡[9]。研究[10]发现, Azacitidine甲基化机制后,将其应用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临床治疗中。但核苷类抑制剂存在不良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甚至突变损伤、骨髓抑制等,限制了其在恶性肿瘤中的临床应用。
1.2.2 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核苷衍生物抑制剂: Zebularine是常见的核苷衍生物抑制剂,具有低细胞毒性和增敏放化疗等优点,可能与促进DNMT与DNA的结合形成共价复合物相关[11]。Zebularine可诱导复制依赖性DNA双链断裂,该断裂优先通过同源重组修复[12]。Zebularine以环磷酸鸟苷-AMP (cGAMP)合酶(cGAS)和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STING)依赖的方式导致干扰素应答水平增高,特异性地敏化cGAS-STING通路对DNA刺激的反应[13]。
1.2.3 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非核苷类DNMT抑制剂: 非核苷类DNMT抑制剂已广泛应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14]。MC3353是一种喹诺酮类非核苷化合物,能下调肿瘤细胞中的DNMT3A蛋白水平,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15]。SGI-1027是一种与AH057高协同作用的非核苷类DNMT抑制剂,能够作用于受DNMT1调控的下游效应分子, AH057与SGI-1027的组合通过促进细胞凋亡和周期停滞协同抑制肿瘤增殖[16]。谷胱甘肽S-转移酶P1 (GSTP1)甲基化抑制剂SGI-1027可调控DNMT1、DNMT3启动GSTP1启动子甲基化,从而导致肿瘤细胞的增殖、迁移、侵袭和耐药[17]。
1.2.4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HDACis抗肿瘤机制可能与抑制细胞分化、周期生长、血管生成、细胞凋亡及免疫调节有关。HDACis对多种恶性肿瘤都有抗肿瘤作用[18]。HDACis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有疲劳、骨髓抑制、胃肠道紊乱等,多为轻度至中度[19]。HDACis可调控周期蛋白抑制黑色素瘤的增殖,促进其细胞凋亡[20], 但对于启动子甲基化的基因沉默,HDACis却无能为力,且HDACis作为单一治疗剂在实体瘤中的治疗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并且还可能出现耐药性。因此,HDACis联合放疗、化疗、光疗、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的相关研究[21]已逐步深入。
然而,这些表观遗传改变药物DNMTis、HDACis仍存在耐药性、不良反应及应答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表观遗传改变药物的临床应用。研究发现,表观遗传药物与其他手段联用具有很大的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的潜力,可一定程度上改善药物应答率低的问题,但具体的作用机制还不完全明确,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 基于表观遗传学改变抗肿瘤
表观遗传学改变并不影响DNA的碱基序列,但遗传表观被改变,而DNMT、组蛋白修饰、ncRNA、染色质结构重塑是恶性肿瘤进展的关键步骤。因此,调控表观遗传学改变对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诊断及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2.1 基于DNA甲基化抗肿瘤
DNA甲基化是在DNMT1、DNMT3甲基转移酶的作用,以共价键结合S腺苷甲硫氨酸(SAM)的甲基进行DNA修饰[22]。肿瘤细胞的特征在于异常的DNA甲基化(全基因组低甲基化和位点特异性高甲基化),主要针对基因表达调控元件中的胞嘧啶磷酸化鸟嘌呤岛(CpGI)。CpGI甲基化主要靶向以蛋白H3第27位赖氨酸K三甲基化(H3K27me3)标记的低基因表达为特征的启动子,用DNA甲基化取代组蛋白修饰确保更稳定的基因阻遏。DNMT1主要通过DNA复制后将甲基转移到半甲基化的DNA链上来维持甲基化, DNMT3可甲基化未修饰的胞嘧啶残基,称为从头甲基化[23]。DNA甲基化诱导抑制性和紧密结合的染色质结构,这可减少参与DNA修复、凋亡、分化、耐药性、血管生成和转移的基因的表达。肿瘤中基因启动子的超甲基化导致细胞周期蛋白下调[24]。因此, DNA甲基化可应用于早期肿瘤的诊断和预后研究,针对DNA甲基化的抑制剂在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中发挥重要的抗肿瘤作用。
2.2 基于组蛋白修饰抗肿瘤
组蛋白是包裹DNA的核蛋白,经翻译后修饰如组蛋白中氨基酸的甲基或乙酰基的添加或去除,可通过构象的改变促进或阻碍转录因子的表达发挥抗肿瘤作用。组蛋白修饰是在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ATs)、HDAC、组蛋白赖氨酸K甲基转移酶(KMT)、组蛋白赖氨酸去甲基化酶(KDMs)的催化下调节组蛋白表达的动态过程。HDAC的活性减少了组蛋白的乙酰化,导致DNA/组蛋白复合体的致密化,从而参与恶性肿瘤的进展[25]。组蛋白甲基化是在KMT催化下添加甲基,可被KDMs去除,从而导致组蛋白去甲基化影响转录表达。H3K79me3与卵巢癌染色质转录活性区域相关的组蛋白标记,组蛋白甲基转移酶H3K79处的甲基化由类端粒信号传导干扰物(DOT1L)催化, DOT1L激活促进同源盒蛋白HOXA9的转录, H3K79甲基化与参与DNA损伤反应和细胞存活机制的基因调节过程[26]。EZH2是一种表观遗传修饰因子,是多梳抑制复合物2 (PRC2)的成员,通常参与转录抑制。EZH2是PRC2复合物的酶催化亚单位,可通过H3K27的三甲基化改变基因表达, EZH2可抑制细胞增殖、侵袭、肿瘤转移、血管生成和化疗抗性[27]。因此,组蛋白修饰可调控抑癌或促癌基因的转录,进一步影响肿瘤细胞的功能,且调控组蛋白修饰一定程度上可参与抗肿瘤作用。
2.3 基于ncRNA抗肿瘤
ncRNA是一种能被转录但不能被翻译为蛋白质的功能性RNA。ncRNA包括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微小RNA(miRNA)、环状RNA(circRNA)等。LncRNA可通过调控肿瘤细胞状态、分化、发育等影响肿瘤的进展,可能与染色质重塑、转录、RNA编辑、RNA降解、翻译调控、RNA剪接等相关[28]。circRNA不仅可调节蛋白质的定位和活性,还可与miRNA结合,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转移[29]。ncRNA可调控肿瘤代谢重编程、致癌蛋白的稳定性和EMT过程等来发挥抗肿瘤作用。因此, ncRNA虽不能翻译蛋白质,但参与恶性肿瘤进展的多种生物学过程。
2.4 基于染色质结构重塑抗肿瘤
染色质结构重塑与基因表达、沉默、DNA复制和修复等相关。肿瘤细胞利用多种可诱导染色质结构转变的ATP依赖性染色质重塑复合物来维持染色质处于动态状态。ATP依赖的染色质重塑复合物主要分为模拟转换(ISWI)家族复合体、转换缺陷/蔗糖不发酵(SWI/SNF)家族复合体、INOsitol需求80(INO80)家族复合体、染色质解旋酶和DNA 结合结构域(CHD)家族复合体[30]。通过DNA易位,ISWI和CHD亚家族滑动核小体并排列成规则间隔的阵列。而SWI/SNF亚家族从染色质中置换核小体,促进转录机制和DNA修复因子在DNA上的募集。除DNA易位外, ISWI、CHD和 INO80亚家族为核小体的组织和编辑保驾护航。SWI/SNF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存在突变, 20%~25%的胃癌、结直肠肠癌、甲状腺癌等恶性肿瘤中有显著突变[31]。INO80复合物参与端粒调节、着丝粒稳定性、染色体分离及DNA复制稳定、合成恢复、损伤耐受等过程[32]。CHD重塑通过组装或拆卸核小体,进一步改变核小体之间的物理间距和交换组蛋白变体[33]。因此,染色质结构重塑可调控相关基因的表达、沉默、DNA复制和修复,或参与端粒调节、着丝粒稳定性、染色体分离等过程,导致恶性肿瘤的进一步发展。
表观遗传改变不仅可应用于早期肿瘤的诊断和预后研究,还可通过调控抑抑癌或促癌基因转录或改变染色质结构,调控相关基因的表达、沉默等,参与恶性肿瘤的进展。但恶性肿瘤治疗的表观遗传改变药物仍存在耐药性、不良反应及应答率低等问题,极大地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预后。因此,积极寻找高效、安全的药物及治疗方式对肿瘤患者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3 中药活性成分调节表观遗传学改变靶向抗肿瘤作用
随着高通量测序的不断发展,表观基因调控物的各种突变已被证明是恶性肿瘤发生的驱动因素。表观遗传学改变修饰已广泛的应用于分子机制的探索和靶点药物的开发。近年来,基于表观遗传学改变的中药活性成分的靶向抗肿瘤作用的研究逐步深入,极大丰富了中医药抗肿瘤的机制研究。
3.1 中药活性成分调节DNA甲基化靶向抗肿瘤
DNA甲基化异常被认为是恶性肿瘤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DNA过甲基化的抑癌基因作为肿瘤早期诊断、预后评估和治疗预测的生物标志物具有重要价值。刘红[34]研究结果提示,中药单体吴茱萸碱、小檗碱影响Hsa-miR-429、Hsa-miR-497-5p表达,靶向调控甲基转移酶DNMT1、DNMT3表达,从而调控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转移及耐药性。中药蜈蚣提取物干预中低转移潜能人肝癌HepG2、高转移潜能HCCLM3细胞后检测其DNA甲基化,结果显示蜈蚣提取物可调控其甲基化位点,抑制人肝癌HepG2、HCCLM3细胞的增殖[35]。TO KKW等[36]研究发现,姜黄素可上调趋化因子CXC亚家族CXCL8、CXCL1、CXCL2地表达,导致结直肠癌(CRC)细胞耐药表型的逆转, CXCL1的甲基化参与该过程,可作为CRC患者的临床预测指标。
3.2 中药活性成分调节组蛋白修饰靶向抗肿瘤
组蛋白修饰与染色质结构的开启或关闭状态有关,从而导致基因转录的激活或抑制。研究发现,肿瘤进展与改变组蛋白的染色质调节因子的异常表达有关。组蛋白的乙酰化在肿瘤中被解除管制,这可能导致异常的超级增强子的形成和激活促进肿瘤进展的相关基因。黄超[37]发现,吴茱萸碱、小檗碱干预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诱导结肠上皮NCM 460细胞系后,可上调组蛋白3赖氨基酸4三甲基化(H3K4me3)、H3K27me3表达,下调H3K9me2、波形蛋白的表达,提示吴茱萸碱、小檗碱能通过稳定染色体数目、调控异常组蛋白修饰模式而发挥抗肿瘤作用。TIAN N N等[38]发现,姜黄素下调肝癌细胞EZH2、Hotair的表达,从而抑制EZH2特异性催化的H3K9和H3K27的三甲基化,姜黄素通过Hotair/EZH2/组蛋白修饰调节轴抑制HCC的生长和转移。
3.3 中药活性成分调节ncRNA靶向抗肿瘤作用
LncRNA与miRNA靶向的mRNA竞争影响miRNA介导的基因调控,这种相互竞争的内源性RNAs机制和网络结构将miRNA与翻译后调控的蛋白质编码对应体隔离,成为LncRNA生物学功能的主要分子机制。ZHANG S S等[39]研究发现,雷公藤内酯醇(TN)处理鼻咽癌细胞破坏LncRNA Thor-胰岛素样生长因子2结合蛋白1(IGF2BP1)的结合,导致LncRNA Thor耗竭,下调IGF2BP1 mRNA靶点的表达, TN腹腔内给药能明显抑制小鼠皮下鼻咽癌移植瘤的生长。因此, TN通过调控LncRNA Thor-IGF2BP1信号抑制人鼻咽癌细胞的生长。苦参碱(MAT)是苦参注射液中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也是苦参注射液的主要化学成分。LI L L等[40]研究发现, LINC 00472在鼻咽癌组织中呈明显低表达。MAT上调LINC 00472来增强细胞程序性死亡蛋白 4(PDCD4)的表达,同时MAT升高PTEN, 下调磷酸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I3K/Akt)蛋白表达。因此, MAT通过调控PTEN/PI3K/Akt通路上调LINC 00472, 促进PDCD4的表达,抑制鼻咽癌细胞生长和转移。
3.4 中药活性成分调节染色质结构重塑靶向抗肿瘤作用
染色体结构重塑可调控下游基因的表达,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Brahma相关基因1(BRG1)的缺失或抑制与细胞周期蛋白(CCN)B1、转化生长因子-β结合蛋白2(LTBP2)的下调相关。BRG1与CCNB1启动子直接结合,通过与E2F转录因子1(E2F1) 相互作用在缺氧刺激下激活转录。BRG1通过改变靶启动子的组蛋白修饰调控CCNB1和LTBP2的转录。BRG1招募一种组蛋白H3K9脱甲基酶3A(DM3A), 敲除目标基因启动子二甲基H3K9, 从而激活转录。DM3A基因敲除可减少肺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达到BRG1沉默的效果[41]。LI X等[42]发现, MAT有效抑制5-氟尿嘧啶(5-Fu)积累的CCND1表达, MAT通过上调E-钙黏蛋白和降低波形蛋白水平来降低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细胞的运动能力,减轻上皮间充质转换(EMT)。因此, MAT通过调控CCND1/Wnt信号通路抑制NSCLC细胞的EMT。WANG Y等[43]研究结果提示,半夏脂溶性提取物下调培养的人宫颈癌(CC)相关树突状细胞(TADC)的细胞因子信号抑制物(SOCS1)的表达,激活Janus 激酶2(JAK2)、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1(STAT1)、STAT4、STAT5的磷酸化。因此,半夏脂溶性提取物可能通过激活JAK2-STAT1/STAT4/STAT5信号通路调控TADC的活化来发挥抗CC的作用。
在中医的“辨证论治”“治未病”“既病防变”等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已广泛应用于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预后。中医药可通过调节表观遗传学改变发挥抗肿瘤作用,但对于中药活性成分或单体抑制肿瘤进展的分子机制研究尚不深入,尤其是基于表观遗传学的中药活性成分抗肿瘤作用的研究,还需更深入研究。
4 小 结
本文从表观遗传学改变角度地角度对中药活性成分靶向抗肿瘤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其调控基因的表达、沉默、DNA复制或修复、染色体结构重塑等过程发挥抗肿瘤作用。基于因此,表观遗传学改变的中药活性成分靶向抗肿瘤的研究对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及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中药吴茱萸碱、小檗碱、姜黄素、雷公藤内酯醇、MAT及中药蜈蚣、半夏等提取物可通过调控表观遗传学改变抑制胃癌、乳腺癌、卵巢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增殖、转移与迁徙,促进其凋亡及逆转抗肿瘤药物耐药等。因此,基于表观遗传学改变的中药活性成分靶向抗肿瘤作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药抗肿瘤作用机制的科学内涵,但中药活性成分的抗肿瘤作用机制需要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