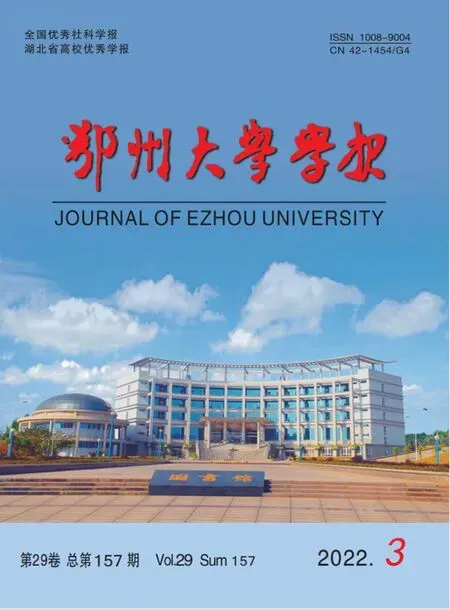《周易》中“桑”的意象解读
李露菲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大同 037006)
“桑”作为一种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广泛的应用,并且超脱其原有的自然物象意义向一种具有民族记忆的文化意象和审美意象发展。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原始先民便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桑树已经大量种植,桑树在原始先民的民俗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种桑、采桑这些农事活动蕴含着先民朴素的原始信仰和精神内涵,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了独特的意象,“桑”作为意象其文化溯源可以追溯至《诗经》《周易》等先秦文学中,在《周易》中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记载,这句卜辞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民俗文化和哲学思想等。
“意象”是中国审美艺术的母题,人们将内心的情感意识与外在的客观物象相互集合而构成可以表情达意的意象,“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1]《周易》中的“象”作为“意象”形成体系中关键的一环,其中所描述的诸多自然物象,如山、牛、履、桑等,一旦进入到意象世界中就有了超于物象本身的内涵,而成为一个具有诸多隐喻的意象。《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是原始先民对天地万物最朴素的认识,通过对农事活动的归纳总结出“桑”的意象。
一、生命崇拜
(一)生存之思
“生生”是《周易》的精神内核与关键母题,蕴含了《周易》对“生”的重视和关于生命的智慧。“生”是生存、存在、繁衍、生殖、产生,《周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2]在此,“生”是生命的运化,是八卦的产生方式,也是天地万物产生的基础,这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也是天地万物的基本属性,没有“生”天地万物则不会存在,“桑”也依附于“生”,《周易·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桑”的“生”即存在本身就体现着天地的大德,“桑”作为自然存在物,其基本属性就是生存和客观存在,这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二)生命繁衍之敬
“生生之谓易”形成了《周易》以“生生”为核心的生命哲学之思,“生生”是生命的运化,生命的不断繁衍发展,前者之“生”是生存、存在,是天地间万物情况的本质属性,后者之“生”是孕育、繁衍,是天地万物以生命而流变发展繁衍,存在依附于发展繁衍,发展繁衍如果没有存在便无生命,生命存在与发展繁衍相辅相成,生命存在结合发展繁衍才能生生不息。“桑”作为自然物象的抽象化总结,所展现的正是自然原始旺盛的生命力和自然的孕育繁衍之道,程颐先生的《周易程氏传》将“系于苞桑”注为:“桑之为物,其根深固,苞,谓丛生着,其固尤甚。”[3]“桑”作为自然物,其根系强劲牢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桑”作为原始先民对自然的朴素认知和抽象化产物,它与《周易》中其他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一起构成了天地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有“系于苞桑”“枯杨生稊”“羝羊触藩”“十朋之龟”等,这些物种与原始先民共同和谐的生长在大地上,野性、自由地栖息在天地间。
“桑”意象在形成过程中还寄寓了生命繁衍的隐喻,这是原始先民将自然之道与人文之道相结合所提炼出对于生命繁衍的崇敬。桑树,树木高大笔直,叶大而厚可用于养蚕,果子可用于果腹,易于生长,往往引荫成林,所以具有生命繁衍的隐喻。孔颖达《周易正义》解说,《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上篇三十,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下篇三十四,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而无分阴阳与男女,均以“生生”为第一要义。[4]“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位于上经中的否卦,隐喻了阴阳之本始,在先秦文学中,先民以“阴阳”来阐释宇宙万物的发生繁衍。所谓阴阳交感而产生万物,阴阳和合所表达的正是天地万物的繁衍和宇宙的生成,“易”便是日月,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配化合生成天地宇宙繁衍出万物,阴阳二气交通,则草木繁衍,“桑”正是草木繁衍的象征。
(三)生命之变
《周易》的核心表述“生生之谓易”正是体现了发展变化之学,“易”也正是《周易》的内在核心,“易”所揭示的正是生命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程颐《易传序》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5]“易”由日月构成,一阴一阳的内部矛盾相互运化相互冲突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演变,这揭示了事物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生命万物要做到保存生机就需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所展示的正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辩证发展变化的状态,《周易·系辞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君子要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即使是国家安定也潜藏着不稳定的因素,当国家危亡之际就要不断积蓄力量保存实力,待时机成熟重振旗鼓,这便是辩证发展的思维,亡与存是国家内部的一对矛盾,国君只有时刻关注存亡之道的矛盾发展才能保存国家的平衡,《周易》另有“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国君运用发展变化的道理去治理国家,百姓也才能安居乐业。
二、祭祀占卜
三皇五帝时期,生产力低下,人类对宇宙、自然、天地的认知并不深入,当时的人们依靠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繁衍生息,在拥有绝对力量的大自然面前,通过以己度物的想象将大自然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所有的物种便都具有了灵力,自然万物也有了各种各样的神,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先民对大自然也产生了宗教崇拜之心,并通过原始的祭祀占卜活动祈求与自然之神取得联系,《周易》作为“卜筮之书”其中记载的卜辞卦象便是神谕,通过占卜吉凶取得神灵的预言,并通过祭祀祈求神灵的保护,这些祭祀占卜活动涉及原始先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战事情况、婚恋习俗、农业生产等,蕴含着先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也是先民与自然相平衡的智慧。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周易》中的第十二卦——否卦之一,“否”表示的是否定的含义,它所阐释的正是国泰民安与国家危亡、小人得道与君子道消的对立矛盾,在国泰民安的盛世要居安思危,在国家危亡之际要积蓄力量,在小人得道的黑暗时代君子要坚定立场,在君子道长的时期也要时刻提防小人,否卦所代表的是由阴阳相冲突转化到阴阳相和谐的状态,饱含初六、六二、六三、九四、九五、上九六个卦辞,分别代表的是对人类社会君子小人之交、国家发展安定的经验总结,其中出现的“茅茹”“苞”“桑”也被打上了原始宗教迷信的色彩,预示国君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国家就可以像桑树一样生生不息,桑树枝繁叶茂生长旺盛,在占卜往往代表的也是吉兆,朱熹的《周易本义》将“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阐释为:“苞,与包同。古《易》作“包”。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时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则吉。然又当戒惧如《系辞传》所云也。”国君大人等当占卜到这个卜辞,则是代表吉兆,但是也应该像《系辞传》中所言的一样居安思危。
另外,结合先秦文学中其他有关“桑”的记载和先民的祭祀文化活动,“桑”还代表社树,先民在桑林之中展开祭祀活动,并折桑树枝叶给神灵、祖先上供,《帝王世纪》则云:“汤自伐桀后……祷于桑林之社。”[6]由此可知,桑树作为社树在汤之后种植广泛,桑树也具有了神灵的意味,可上通神灵下达民情,为百姓祈福。而《周易》中用桑树在预示吉凶也暗含了桑树的神圣价值,通过桑树可以展现神灵的预言。
三、以农为本
“桑”成为古代先民重要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载体,与当时古代先民大量种植桑树是分不开的,当先民大量种植桑树,生产生活都与桑树有密切联系的时候,“桑”才能够表现出先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凝结着先民的祈愿,郑玄的《郑氏周易注》中对“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阐释为:“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圣人有命,咸曰其将亡矣。其将亡矣,而圣乃自繋于植桑,不亡也文选五十二。犹纣囚文王于羑里之狱,四臣献珍异之物而终免于难。繋于苞桑之谓集解。”表明圣人倡导种植桑树,桑作为吉兆也代表了先民将桑树种植丰收作为希望,也展现了先民对农耕的重视。[7]在原始社会中,“桑”确保了先民穿衣蔽体并使得先民逐渐摆脱寒冷通过衣物进行保暖,桑树的种植直接关系到养蚕缫丝衣服的制作,在原始社会中以男耕女织为生产主体,桑树保证着“织”的正常进行。
四、男女婚恋
原始社会中男女婚恋的进行与先民以农为本的生产活动和对生命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先民种植桑树通过桑树获得“衣之始”的生产资料,并将桑树看做是社树,在桑林中展开祭祀活动,而桑树又是生生不息是生机勃勃原始生命力的代表,[8]所以商周时期,先民就将人类繁衍、风调雨顺、自然生长等意识联系起来,首先,桑林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活动区域,而且主要是部落中的女人进行采桑活动,农田桑林也就成为了男耕女织、男女约会的圣地。其次,桑林作为祭祀活动的展开区域,也是男女在此地相互舞蹈狂欢的地方,例如在《诗经》的《鄘风·桑中》就描述了男女在社林中欢闹,在桑林中表达爱意的场景。“桑”的意象出现于《周易》的上经,事关阴阳交感,而男女涉及《周易》中的下经,事关男女相亲,而阴阳相感和合产生万物,之后产生男女,男女相亲产生夫妻之后便代代相传,男女所对应的也是阴阳,桑树枝繁叶茂生生不息寄托着原始先民对生殖繁衍的崇拜,在生殖崇拜背后也展现了先民 对爱情的追求。
由于《周易》崇尚“生生之谓易”,对生命的崇拜贯穿其中,“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寄寓着原始先民对生命力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出于对自然万物的朴素认识和对自然的崇敬,“桑”也蒙上了神秘色彩,为原始先民的祭祀占卜服务,“桑”可以成为文化的象征与原始先民的生产活动密不可分,“桑”的种植直接关系到原始先民的衣着保暖,在生命繁衍和祭祀活动的基础上,“桑”也隐喻了男女婚恋的发生。“桑”意象所隐喻的这些文化内涵,是原始先民千年的文化积淀,挖掘“桑”意象背后的隐喻,是对中华民族生命认同感的追寻,也是对后世文学创作中“桑”意象中的文化内涵寻找落脚点。